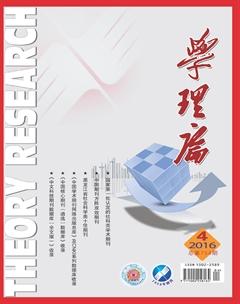论西南联合大学课程的特点与启示
阮慷
摘 要: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成功范例,它的成功经验需要我们从多方面去探求和研究。从西南联合大学的课程着手,总结其特点,并分析其对我国现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启示与意义:一是“大教育家”型的大学校长是保证课程质量的前提;“大师”级的教师队伍是提高课程质量的关键;“大”的学术氛围是维持课程质量的源泉;先进严格的课程管理是确保课程质量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西南联大;课程;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4-0213-03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一所与抗日战争相始终的著名大学,由北平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三校联合而成,简称西南联大。这所大学仅仅存在了八年,但它所创造的价值与遗留传承下来的精神、传统,却无疑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的无形资产。陈岱孙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前言中提道:“西南联大,不只是在形式上弦歌不辍,而且是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为国家培养出一代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西南联大,这所其实体虽然今日已不复存在的大学,其名字所以能载入史册,其事迹所以值得人们纪念着,实缘于此。”[1]国外有学者称:“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2]但据现有调查显示:“研究杰出人物(西南联大教授)、校歌校训碑文、人才培养、办学实践和联大精神等,是国内西南联大研究界较为关注的热点论题,而系科建设、课程教材、教育教学等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3]课程作为教学赖以开展的依据和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对西南联大办学的成功有着极其重大的意義和影响。所以,应当重视西南联大课程研究的开展与进行。从分析西南联大的课程着手,探究西南联大在此方面的特点,总结其成功的宝贵经验,得到有益的启示,这将对我国现代高等教育课程的改革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
一、西南联大课程的特点
(一)“通才教育”的课程思想和理念
通才教育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是西南联大的办学宗旨,它贯穿于西南联大的整个教育教学培养计划之中。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提出:“窃以为大学期间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也所以自通于人也”,“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这些主张是十分切合大学的教育规律的,同时也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
在梅贻琦的领导下,西南联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保证“通才教育”的思想和理念在课程上得以贯彻实行,如:大一国文、大一英文、伦理学、中国通史为全校共同必修课。除此之外,文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的学生还需要选修西洋通史等两门人文、社会科学基础课,一门自然科学课程;理学院学生需要再选一门社会科学课、两门本专业以外的自然科学课程。根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本科教务通则》第30条的规定,“学生在修业期间内,须修满一百三十二学分”。若各院共同必修课以54学分计,则共同必修课学分占总学分的40.9%,比重相对较大[4]。这种课程设置,体现出西南联大“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思想,努力使学生在自然、社会及人文三个方面都能得到“通识”,实现多方面共同发展。
“通才教育”的课程思想和理念以及其指导下的具体相关课程设置和教学安排使西南联大所培养出来的学生的知识视野大为拓宽,学科知识日益丰厚,综合素质与能力表现相对较强。正是在这种“通才教育”的课程思想和理念指导下,西南联大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杰出人才。
(二)大院系的课程组织
抗日战争时期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大多内迁高校的教育教学设施设备资源严重匮乏,但学生对知识的渴求没有因此被扑灭。在西南联大里,情况同样如此。仅拿课程资源为例,一方面课程资源有限短缺,但另一方面“通才教育”课程思想与理念却要求实现学生多方面发展。于此种矛盾情况中,实现院系课程资源共享对学生的高品质培养上尤显积极作用与影响。
至1944年,西南联大共开设了5个学院26个学系,有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除此之外,工学院还下设电讯专修科,师范学院里还有师范专修科、先修班和体育部[5]180。西南联大在课程组织上以大院系来组织课程,将学系纳入相关学院,并规定相关的学院必修课。如文学院规定所有学生除全校公共必修课之外还必须学习文学院学生所要求的公共必修课,包括哲学概论、一门自然科学和两门社会科学,计22学分[6]。
这种形式的课程组织,使学校课程资源得到合理充分的优化利用,缓解了教育教学资源短缺匮乏对学生求学寻知方面造成阻碍等问题,让学生获得了广泛的知识,实现了多方面的发展。
(三)注重基础课程
注重基础课程的教授与学习是西南联大在课程方面又一显著特点。这也是“通才教育”课程思想和理念在课程实施上的又一表现。
在西南联大,学生升入二年级以后才可以选本院系的课程,因为在此之前所学的全是必修课,而必修课都是基础课[5]181。国文、英文、中国通史、伦理学等全校必修课均属基础课程范畴,西南联大规定任何学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上学校基础课。另外,西南联大对基础课程的重视程度之高还表现在,为提高基础课程的教授质量,便于使学生正确充分地打好知识基础和更好地掌握知识结构,西南联大基础课的讲授大多由系主任或有经验的教授担任,以确保学生基础知识的正确性和扎实性。一、二年级的基础课程,即使是像大一国文、大一英文等班次较多的课程,也是由知名教授来教授[7]。联大还专门设立了一年级学生课业指导会。许多系还明文规定,一年级结束时,某一两门基础课达不到标准(60分或70分),不准升入二年级。基础课不及格者,不予补考,必须重修[8]。正是这些严谨的基础课程教授,使西南联大才培养出了众多优秀的后继人才,也使得杨振宁在多年之后依旧回味感激在西南联大的学习给自己今后所得成就所打下的优良基础。
(四)以学分制和选课制相统一佐助课程的实施
西南联大于1929年颁布的《大学规程》中规定大学“一律采用学年兼学分制”。该规程还规定了学生所学学程的最低标准。即除师范学院以外的各学院,学制为四年,在这段时间中必须修满132个学分才能取得毕业资格,确切地说,是取得毕业资格之一[5]179。西南联大在实行学分制的同时另外兼用学年制,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本科教务通则》第25条就规定:“本大学采用学分制,但学生在校修业期限至少四年。”第29条又规定:“各课程按学分计算,每学期每周上课一小时为一学分,实习或实验两小时至三小时为一学分。”[4]114实行这种学年制加学分制相结合的制度,对于学生是大有益处的,体现着以人为本和对学生负责的精神。采用学分制,可以使学生根据自身的兴趣特点去选择自己喜爱的课程,令学生的自主权和能动性得到充分运用发挥,满足了不同的学生对不同的知识的需求。另外,也使课程本身得到了发展,帮助课程结构的改革与建设,使传统老式的格式化课程模式转变成更能满足学生需求的新式形态。采用学年制则保证了课程实施的到位和学生培养方面的质量,让每一学分的“含金量”都得到保障。
除学分制外,为佐助和配合课程的实施,西南联大还辅之以选修课加必修课的选课制度。另外,西南联大的选课制度又一个特点是同一门课程由几位教授来讲授,每个教授所讲内容取各家之长,所采取教学手段也因讲授者而异,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偏好和需要退选或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和课堂。这种选修课加必修课的选课制度,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程选择,拓宽其视野,也使课程得到了激活,获得了改进,帮助其更好地实施。
(五)密切联系实际
为适应抗战特殊时期的特殊要求,顺应时代的发展,西南联大的课程在开设与教授上体现出了一些战时特点。
西南联大根据抗战需要,八年间先后开设了一些配合抗战的新课程,进行“学术爱国”、“学术救国”和“学术参战”。例如,曾经开设一门名为“理想与现实”的课程,在讲授与探讨中有计划、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关注国家社会安全问题,直面严峻的民族矛盾和本民族危机,使学生将自身的发展与国家、民族、社会的发展相联系统一,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责任感。另外,为了直接服务于抗战,仅土木系就开设了军事运输、军用桥梁、堡垒工程、要塞建筑、军事卫生工程等18门适应抗战的新课程。除此之外,西南联大历史学系还与图书馆合作成立“中日战争史料征集会”,发动学生一起收集整理日军侵华的罪证,并依此开设了“战史资料收集试习”课程。再者,为解决战时工业、农业中的急迫问题,开设了“农业机械”等课程,以解决现实问题[6]。除了为顺应抗战需求和其他实际情况开设新课程以外,西南联大也对原有课程的开设、学分数与讲授进行调整与改造。如在课程讲授过程中不仅文科教师注重对学生进行民族文化的弘扬,理工科的教师也十分注意结合教学实际进行民族文化的价值教育。其他教师,如杨振声等也在课上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以树立和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4]113。另外,西南联大还注重结合云南本地风土民情、文化习俗、自然环境来组织课程。当然,西南联大课程的进行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忘紧跟国内外学术潮流和国内外时局的变化与发展而更进与发展。
西南联大课程密切联系实际,为国家社会培养所需要的人才,注重对学生实际能力进行培养。首先,实践中才能出真知,课堂上所学的理论知识用实践去检验;其次,通过实践,可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所学的知识才能牢固;再者,西南联大物资设备匮乏,添加实践环节能弥补这一不足,同时还能培养学生实际能力。所以不管是工学院、理学院、文学院、法商学院,还是师范学院,都拥有各自相配套的关于学生实际能力培养的课程。西南联大课程紧密联系实际,注重对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使一部分师生走出了只重理论而忽视实践的误区,也因此培养出了大批为抗战时期和新中国建设时期做出极大贡献的适用性人才。
二、西南联大课程研究的启示
(一)“大教育家”型的大學校长是保证课程质量的前提
大学校长应该是大教育家或大教育理论的实干家,他能够根据教育规律进行教育安排和活动,并能根据时代要求和教育实际提出自己的教育思想,在教育实践中能够注重对先进教育理论的研究,还能将学校办出特色,越办越好。
教育部派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人为常委,但实际上张伯苓因长期在重庆担任工作,蒋梦麟也因其他事务繁忙而不在昆明,因而西南联大实际上是由梅贻琦一人主持和掌管。大多办学事务都是经梅贻琦之手安排和处理的。梅贻琦作为一个懂教育的大学校长,在大学的培养目标上,坚定培养“新民”;在办学理念上,始终贯彻“通才”的教育思想;在学术研究上,尊重百家,努力创造一个优良宽松的环境,保证学术研究自由和思想自由;在学校管理方面,实行教授治校;在教师选聘上,任人唯贤唯才,积极聘请国内外一流学者。这些方面都为课程质量的保证提供了可能性。
所以,为了保证课程质量,遴选一个“大教育家”型的大学校长至关重要,这不仅关系到课程的制定与安排,也关系到课程的实施与开展。
(二)“大师”级的教师队伍是提高课程质量的关键
一所一流大学的成立与声名远播,离不开一流大师的助阵与努力。“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教师作为课程的直接传授者,对课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至关重要的。所谓“大师”,是优秀教师中的翘楚精英,他们不仅学贯中西,汇通古今,还拥有师德和探究精神。西南联大正是有这么一群真正意义上的大师大家,才保证其课程的先进性和高效性,保证了课程的质量。
西南联大历经八年多,其教师常年维持在三百五十名左右,以保证教学活动的平稳正常运行。在这350名教师中,教授、副教授级别的教师有179人,超过总人数的一半。在这179人中,97人为留美,56人为留欧,3人留日。5位院长均为留美博士,26位系主任,除文学系以外,均为留学归来的学者[6]。这在当时的国内高校中是极为罕见的。文科方面有陈寅恪、朱自清、闻一多等名师,理科方面有华罗庚、陈省身等教授,他们师德高,学术造诣深,且拥有较高的教师专业素养。这些人组成了西南联大强大的名师阵容。
强将手下无弱兵,正是拥有这么大规模的“大师”级教师队伍,加上所处的是一个思想自由的优良学术环境,西南联大课程质量之高为全国所惊叹,培养出来的人才之多为世界所震惊。
(三)“大”的学术氛围是维持课程质量的源泉
“大”的学术氛围使学生在进入学校的同时即可被强烈的学术氛围所感染,从而自然而然投身于学术研究之中。梅贻琦说:“凡一大学之使命有二,一曰学生之训练,一曰学术之研究”,“为完成此使命,故其发展之途径不徙限于有效之教学,且当致力于研究事业之提倡。此在学术落后之吾国,盖为更不可缓之工作”[5]35-37。这种“大”的学术氛围使得教师、学生都能坚定认真地潜心学术研究。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虽已经满腹经纶,名满学界,但仍旧精心治学为求完善,追求营造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这种营造又非闭门造车,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研究去发展学术,另外教授间经常相互探讨、听课,以交流经验。西南联大所营造出的学术气氛有两个特点:第一,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强调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中西交融汇通。第二,支持学术自由,倡导百花齐放的学术研究局面。这种优良的学术气氛给西南联大带来了诸多好处:提升了学校的学术地位,是学校不断发展的重要条件;创造出一种优良的学习环境;产生一大批研究成果和名师名家,为当时后世,为云南乃至全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使得课程内容不断更新。西南联大就是以这种“大”的学术氛围不断促进学术研究的快速发展,让课堂教学、课程展开蓬勃发展。
(四)先进严格的课程管理是确保课程质量的重要条件
西南联大有着先进严格的课程管理。其先进表现在:首先,先进的课程理念,即强调学术自由。教师有教的自由,学生有学的自由;其次,先进的课程组织,即大院系的课程组织;第三,先进的课程实施,即选修制和学分制。其严格表现在:第一,任课教师选任严格,尤其是全校必修课,一般都由知名教授任教;第二,学生选课规定严格。规定每学期所选课程以17学分为准,不得超过20学分,不得低于14学分[6]。第三,课程成绩评价严格,如选修课不及格,不得参与补考,必须重修。
先进严格的课程管理是确保课程质量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先进严格的课程管理有利于明确规定课程的选择、组织、开展与实施,使其分工合理有序,并能有章可循。同时,使课程资源得到充分优化管理,提高教育教学效率,减少不必要的经费开支,也使学生更好地得到知识传授和知识框架构建,便于其基础的巩固和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所以说,要使课程质量得以保证,少不了一個好的课程管理的支撑。
虽然西南联大在悠悠历史长河中只存在了八年,但它的影响却一直延续至今。它诸多宝贵的办学经验仍需我们去研究和探讨,其中,对其课程方面的研究也不可懈怠。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需要继承历史积淀下来的种种优良,更要不断去发展和创新,获得更高的成绩。
参考文献:
[1]张曼菱.照片里讲述的西南联大故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
[2]何华炜,周晓玲.西南联大课程的特点与启示[J].高等理科教育,2008(6):8-12.
[3]王晓燕,徐颖.对西南联大课程设置和教学管理的研究[J].新课程研究,2011(12):11.
[4]封海清.西南联大的文化选择与文化精神[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110.
[5]杨立德.西南联大的斯芬克司之谜[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180.
[6]王根硕,延立军,陈秋生.论西南联合大学课程的特点及启示[M].高等理科教育,2008(6):9.
[7]刘海峰,史静寰.高等教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87.
[8]赵新林,张国龙.西南联大:战火的洗礼[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12):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