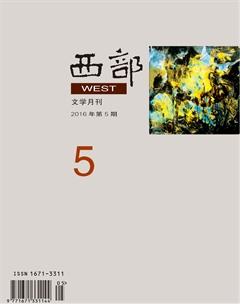流瓶儿:你有几条路
一辆小巧的白色宝马车又停了过来。作鹏装作漫不经心地从自己的车上下来,伸了个懒腰。宝马车主是个女人,一直偏着头在打电话。作鹏等待时机,清了清嗓子,拉了拉肚皮上的蓝格子衬衣。再抬头看,那女人已锁了车门预备走了。
作鹏伸了伸脖子,嗓子干没发出声。那女人忽然站住,打开手包看了看,快步回来开走了车。作鹏耸了下肩,不自在地原地转了一圈。秋天的太阳暖暖地照着他,他的脸有些热。他把两只手插进裤袋里,将脚下的几片黄叶踢进了树丛。
他敞开车门,一只脚放在车外,斜坐在驾驶座上。很快,一辆越野车停了过来,四个车门都打开了,随后下来四个女人。作鹏拍了拍放在车外的一条腿,像是在掸灰尘,其实上面什么都没有。女人们很忙,叽叽喳喳地说话、穿衣、拿包、笑。走了三个女人,留下一个女人。那个女人也像作鹏一样,敞开车门坐着,仍旧在忙。她脖子里夹着手机说着话,在一个大包里翻腾着。作鹏换了几种坐姿,下车提了次裤子,检查了一遍车窗。
还没找到机会,离开的三个女人嬉笑着小跑着回来,开走了车。
第三辆车又停了过来。作鹏一把关了车门,放低车座躺了下去。他交叉了两只手环到脑后枕着,这躺姿并不舒服,甚至有些费劲。他躺着不动,竖起耳朵听到嘭、嘭两下关门声,还有说话声。他犹豫了片刻,还是微微地起身向外张望了一眼。是辆黑色的车,还可能是高档的新车。
已过中秋了。车窗外的蓝天有些恍恍惚惚,很多年没有认真看过天了,有些陌生,像是撞见了多年不见的旧邻居。蓝天下树上的叶子都黄了。作鹏不是个浪漫的人,他抽了一下鼻子把脸扭到一边,看到挂在车窗边上的一个红色小袋,里面装着薰衣草。他坐起身扯下来,使劲从开着的车窗扔进车前的绿化林带里,又向窗外看了下,人已走了。是辆奥迪越野,跟老胡的是一款。他重新躺下,仍旧是不舒服,他也仍旧躺着不动。老胡在城里经营建材,跟他虽是同龄人,却使人觉着老胡更年轻。多半是因为老胡当过兵,仍留着短寸头,腰挺背直,说话有板有眼。他一直是农民,怎么看也就是个农民。一个城里人和一个乡下人,无亲无故的,竟然成了朋友。
他扔出去的薰衣草,是几个月前去伊犁采的,他和董中叶还有老胡,一行三人。董中叶是他老婆。
董中叶长相算不得漂亮,四方脸上绷着已松弛了的暗黄的皮,眼睛大,眼皮双。长有这类面孔的人,骨架也大,腿也长。快五十岁的人了,仍然黑丝袜配短裙,一头黄卷毛,不,新近改成暗红色了。她干活是把好手,只是不用在挣钱的棉花地里,而是用在家里的院子里。一片菜地,一群鸡鸭,说是留着自家人吃,可哪里能吃得了,她另有用处。
第一筐菜送给了女儿打工的理发店老板。作鹏想得出董中叶的样子。她定是端着笑盈盈的方脸,先将高八度又透着娇羞的笑声传进店里,见老板回过头来看她,才略显迟疑地扭进去的。那老板,作鹏后来见了,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小伙子,一头长发在脑后束着,皮衣皮裤,一副不与俗人为伍的清高派头。中叶跟他说,当时老板客气地打了个招呼,又继续忙着给人理发。她说,地里的菜下来了,自家吃不完,拿来分给大家吃。老板说,谢了,他单身一个,都是下饭馆吃饭。她呵呵一笑,从筐里拿出个袋子,新烤的小油馕的焦香味儿一下子弥散开来。一时,店里闲着的师傅徒弟们全都围了上来。老板忙完后,也拿了吃。这一吃就清高不起来了。这之后,董中叶就常做了好吃的送去,好吃是一说,她在家做好,又坐一个小时的小班车送到城里来的精神,才是最打动人的。
董中叶说,老板是女儿的师傅,就应长一辈,以后不许老板叫她阿姨,要叫姐。老板真的叫她中叶姐,店里的一众姑娘小伙也都叫她中叶姐,女儿是必须要叫妈,辈分全乱了。一众人还帮她修眉化妆设计烫发,帮着参谋买衣服,从那开始董中叶改头换面打扮起了自己。
作鹏的世界就像他种的那片棉花地,规规矩矩。董中叶是他地里的一条小道,结果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延伸了出去,伸进了城里。
路子正是由那理发店打开的,董中叶一来二去的跟理发店的常客也熟了。那几年棉花势头正旺,手头也宽裕。中叶拿出农村人的热情请人吃饭,凡是发现对方是有些路子和用处的,就长久地将友谊保持下去。她送的自家产的绿色蔬菜,很难使人拒绝。
第一件办成的大事,是儿子进城里的重点中学。作鹏完全没料到董中叶能办成这么大一件事,儿子不但进了重点中学,还进了重点班。自然是花了钱的,但很多人有钱都找不到门送。感谢宴,作鹏也去了。一帮陌生人亲切地叫他哥,那天老胡也在,他们初次见。女儿帮董中叶化了妆,一张大白脸,蓝眼皮下粘着假睫毛。“老妖精”三个字憋到了作鹏的嗓子眼儿,女儿抢先抱住他的一只胳膊,说是她给化的妆,这叫与时俱进。女儿也化了妆,同样的妆容在不同的两张脸上,对比效果简直有些骇人。董中叶笑眯着眼,羞答答的样子让作鹏直起鸡皮疙瘩,一帮人都夸她今天漂亮。作鹏不忍再看,想必大家也是出于礼貌客套一下。他也只唉哟了一声。谁知道,董中叶从这天起认真要保持这样一张妖精脸。
为了儿子上学方便,他们在城里租了套房子。作鹏回到棉花地里,董中叶留了下来给儿子做饭陪读。儿子放假了,董中叶回村里,端着涂了厚厚脂粉的大方脸去四邻走动。村里一帮不甘心的半老徐娘,把她的装扮当作时尚风向标,复制出各种版型的她。但她们比不过她,单是身材这一项,她就赢了。更何况,她的骨子里向外透着娇气,走路扭腰,举手是兰花指,涂了红指甲的兰花指。
入冬农闲了,村里人包车进城来跳舞。董中叶知道哪里好,什么文化宫,角落里的大众歌舞厅,领着一群人到处去跳。女儿逼着作鹏一起去跳,三跳两跳的,他倒也喜欢上了。在闪烁不定的昏暗灯光下,在老旧的音乐里,董中叶的大白脸忽然变得悦目起来,同时也很醒目。左右晃着,三步四步,董中叶这时是没有笑脸的,微微偏向一边,高傲得像电影里的女人。作鹏正好相反,简直绷不住要笑出来。年轻时在地里下苦,现在人到中年了,倒要过过年轻人的日子。作鹏开始觉着天地一新,耳目一新,思想也崭新了。其实关键的一点,是他们有钱了,吃得起,跳得起。一帮人不知不觉得成了很好的朋友,村里几个,城里几个,包括老胡在内。
作鹏不知自己怎么就成了中心人物,玩笑围着他开,吃饭他坐上座,一帮人还簇拥着去给他买衣服,不管什么款式都往他身上套,他对着镜子笑到岔气。董中叶蹬着七寸高的高跟鞋,一只手挎着提包,笑盈盈地围着他走一圈,向营业员一招手道,再给换一件。一边一跺脚,向旁边的朋友们撒娇道,你们这些参谋说句话呀?老胡,你是最有发言权的,你说。老胡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局外人似地远远站着。听了她这话,一瞪眼佯装生气道,你老公穿衣服,怎么我最有发言权,这话说得真是。一行人哄笑起来。董中叶一只手背遮了嘴,笑得前后晃,随后一甩手挺直了身子作生气状向作鹏道,你兄弟欺负我,你管不管?作鹏装作要去打老胡……不大的一间服装店,被他们闹得乌烟瘴气。营业员小姑娘们暗暗互使眼色,做出打冷战的样子,一边继续耐着性子服务,咬了牙夸董中叶漂亮,不像上四十岁的人。董中叶脸上是笑着的,可是不吃奉承这一套。讨价还价一番之后,眼珠一转道,效果还差点。她的态度始终是好的,甜蜜地谢过营业员,然后招呼一众走人,气得小姑娘直骂她是人妖,可是又不对,人妖是指男人。
那些日子不知怎么那么多事,吃不完的饭,喝不完的酒,作鹏每喝必醉,每每都是老胡送他回家。
作鹏在车里躺得不耐烦了,坐起身,打开车门下来。他究竟躺了有多久,停在旁边的车已不见了。这些人的运气真好。作鹏狠狠地拍了拍车后盖。
嘿,作鹏站在这干啥?作鹏面前忽然闪出村里邻居老王的脸,吓了他一跳。
我,我,我那个过来给采棉机买个配件。作鹏不自然地答。
老婆子呢?老王是一脸的笑容,却掩盖不住小眼睛里透出的狡猾。作鹏迅速将脸转向一边,他要掩盖住自己已洞察一切的眼神,答道,口里探亲去了。
真去了还是假去了?作鹏猛得转过脸来。老王迅速地哈哈一笑道,开个玩笑,怎么可能有假。他的小眼睛极快地在作鹏脸上寻找蛛丝马迹,然后又伪装出毫不在乎的样子,拍了下作鹏的肩问,去不去打麻将?作鹏从不打麻将,村里人都知道。作鹏勉强挤出半个笑容,说不去。老王又在作鹏的肩上拍了一把,转身走了。这一巴掌拍得作鹏的心像皮球似地在胸膛里上下狠跳了一会儿。虽然如此,但那巴掌是热的,是活的,有人情味的。
不能继续站在那里了,村里人一向都是结伴进城,刚遇见老王一定还会遇见其他人。而且,作鹏忽然觉着自己必须睡一会儿,简直迫不及待地想睡一觉。他上车放倒车座,这次他让自己躺舒服了。闭上眼睛睡过去,睡着了就什么都忘了。
可是有车停了过来,重低音伴着机器人似的老外的歌声,先是在“闷罐”里,随后向他敞开。他死死地闭着眼。听到两男一女在说笑,年轻人的声音。他们停了车却并不关音响,也不走开。作鹏感觉出有人靠在他的车门上,并随着音乐节奏晃动着身体。有烟味儿飘进了车内。
他们在说微信,提到了什么视频。他们在说什么朋友圈,说什么转发。其实他们混乱地说了很多,入了作鹏耳朵的只有这几个词,是生生向他的耳朵里扔进了几把刀。
作鹏从来是懒得去弄手机里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女儿硬要教他。两个人坐在沙发上,女儿的头顶着他的脸颊,一遍遍地教他,他学不会,女儿捶他的肩,嫌他笨,教不会。其实他是故意学不会。董中叶在一边不耐烦地叫,吵死了,别教你爸了,他用不着。
人该怎么活,老天是给了几个模子的,譬如作鹏这样的男人,应当闷头干活挣钱,万事不管。穿什么,吃什么,与邻里处关系,跟外界打交道,全交给老婆。孩子们长大了,也有钱了,作鹏心甘情愿就这样活到老活到死。可是哪有那么容易,这路要断。
三天前的晚饭,董中叶把菜炒糊了而且没放盐,这事从没发生过。董中叶把菜盘往桌上一推,就慌慌张张出去了。她把手机落在了厨房。作鹏有预感,知道早晚得发生点什么事。他翻看了她的手机,在微信里发现,村上一个不大来往的姓田的小子给中叶发了两条消息,一条是视频,一条只有两个字:五万。视频虽然黑乎乎的,但能认得出是在他们常去的一个舞厅附近,里面吵吵闹闹的,听见田姓小子在跟人打什么赌,说是两百块,说录下来免得不认账。画面摇摇晃晃,几个半大小子按住一个人在翻那人的口袋。作鹏莫名其妙,不明白什么意思,再看时才发现,车灯在他们背后扫过时,画面的一角,老胡正抱着董中叶的肩,向她亲下去。董中叶穿着新近买的一件大红色羊毛半长大衣,腰上系着条黑皮带。老胡穿着件咖色羊毛休闲装,是他们一起去买的,他和老胡一人一件。作鹏刚放下手机,董中叶就跑回来找手机了。她不怀疑作鹏会有什么发现,在她眼里,作鹏就是个只会干活的傻子。
五万块钱。作鹏拿了盐罐回到餐桌前,将没放盐的菜全部吃了下去。瞒住自己,得花五万块,这价不低。仅凭这一小段影像就要五万块钱,那么之前那段得值多少钱呢?
外面的说话声没了,音乐声又关进了“闷罐”,随后安静下来,车开走了。
作鹏睁开眼,降下车玻璃。天色开始有些暗了,他从吃了午饭后,就停在了这里。他远远看到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倒计时牌闪着逐渐变小的数字,一轮完毕,又来新的一轮。如果这世上真有月光宝盒,时间可以倒流重来一轮的话,他会怎么做呢?
上周的那场酒他少有的没有喝醉,几杯下去之后,他就开始偷偷向水杯里吐酒,觉着时机差不多了,开始装醉。在那前一天,他回家撞见董中叶在和女儿吵架。他问怎么了?女儿瞪着红红的眼睛冲到他面前,抓住他的胳膊,尖尖的指甲几乎要掐进他的肉里。她说,爸,你能不能刮刮胡子,能不能穿得像样些?你能不能不要一天到晚只知道干活挣钱,能不能不要喝醉?他还没反应过来,董中叶大叫一声道,闭嘴,还轮不到你教训你爸。说着过去将她推开到一边,继续道,我们大人的事,你没资格管,没资格说话。女儿瞪着眼睛望着他,如果倒计时,足有十秒。女儿摔门出去了。董中叶说,女儿嫌他形象不好,给她丢人了。他假装信了。
作鹏装醉,装作一堆烂泥,由着老胡架着他,连拖带拽地把他弄上车。董中叶夹出尖细的嗓音,跟朋友们道别,一边笑道,老胡是作鹏的专职秘书兼司机。老胡的肝做过手术,不喝酒。作鹏觉着董中叶的笑声里透着醉意,快乐到极点的醉意。到家后,他被放到了客厅的沙发上,电视打开了。他打起响亮的呼噜。程序应当是这样的。
他竖起耳朵。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上天安排的吧。他努力从电视的音乐声中分离出那两人的说话声。他们没怎么说话,先后上了卫生间。然后不是大门,是卧室的开门声,关门声,反锁门声。他的脑袋里轰隆隆地开过了一列火车,在几乎被毁灭的听觉里,不久便跳闪出董中叶呜咽着的叫床声。电影里、新闻里、所有听说过的故事里,这会儿他都应当跳起来去打去骂,再狠点可以去杀。而事实上,他突然怕到了极点,竟然趴在那里完全动弹不得。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完全失去了对时间的判断,外面响起了敲门声。是女儿,她在外面叫,开门。
还有比这更可怕的噩梦吗?可惜不是梦。
他清楚地听到光脚在地上跑的咚咚声,听到卧室的门打开又关上,听到开窗的咯吱声。窗外有防护栏,老胡可以躲在那里。他听着似乎安静了下来后,才起身去开了门。女儿看见他的第一句话就是,爸你又喝醉了?他立刻踉跄着堵住女儿的路,问她回来干什么?女儿问,我妈呢,哪儿去了?他向后甩了甩脸,道,里面睡了。女儿向后面狠狠地翻了一个白眼,然后又瞪着他道,你也快去睡吧。说完重重地拉上门走了。老胡的皮鞋赫然摆在门后的架子上。
这些值多少钱呢?
他说要加快采棉进度,开始夜间去采棉。他白天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卧室的床再没上过。董中叶察觉到了吗?她受了不小的惊吓吧,一件连着一件。
这事,一天要在作鹏的脑海里过上八百遍。他抓起擦车布下了车,大力地在擦车引擎盖。
昨天,他去了老胡老婆工作的银行。她不在窗口,但从大玻璃窗看得见她。一身藏蓝色西装,对着电脑敲键盘,脑后盘着个髻,皮肤是自然的白晰。她的男人跟董中叶滚到了一张床上。董中叶的脸是粉擦白的,像霜打过的茄子。
他不是没想过,他去世不久的父亲在患病期间留下了不少安定片,他已找了出来,也想好了,可以放进董中叶喝的柠檬蜂蜜水里。害了她,他也跑不掉。家里现成有农药,有绳有树有煤气有刀,他要死很方便。可是女儿就要结婚了,儿子就要考大学了。
那女人有感应似的,转过脸向他看过来,用疑问的眼神扬了扬下巴,无声地向他发问。作鹏忙摇了摇头。其实他们一起吃过一次饭,当时人多,她怕是已不记得作鹏了。可是,女人突然再次转过了脸。扁薄而清秀的一张脸,这次有了表情,是与职业礼节毫不相关的惊骇。她半张着嘴,尖尖的下巴微微地在抖,一缕头发滑了下来,停在她雪白的脸颊上。她缓缓地抬起手,摸到脸颊上的头发时,却一下转过脸去,背向着他一动不动。想必她是知道了。作鹏转身走了。
作鹏问自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听说,这世上有种动物,今天扎一针,一星期后才有反应动一下。他是反应迟钝吗?或者是窝囊,敢怒不敢言?那女人抖动的下巴和一转身,忽然之间让他觉得很耻辱。他回到车前,发现车被城管锁了,车窗上插了张处罚通知书。他低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街道边上画出了整齐的停车位。他的车停在了线外。
他全速开车回了家,下车后到车后备厢里拿了一把扳手。董中叶正背对着门坐在一个小凳上,院子的水泥地上铺了一地的红辣椒。她的脚旁放着一把剪刀和一双手掌染红了的黄胶皮手套。她坐直着身子正在打电话,说,什么叫没办法,你不要逼我……他慢慢举起扳手,她的红色卷发没有打理,干巴稀落乱糟糟地披在肩上,她的红发根是白的。他一直举着扳手。董中叶对着电话由哭到骂,咆哮之后挂断电话。她把电话扔到地上,把头埋进一边的胳膊弯里。太阳西斜,他举着扳手的手酸了,他的影子盖住了她的影子,除了那只慢慢放下的扳手。她忽然发现了他,吓得从板凳上摔倒在辣椒堆里。她的样子和表情丑得让他没法儿再看下去。
作鹏擦完引擎盖接着擦车身,擦车窗。自家的棉花再有两天就采完了,后面还有五六家在排队等他的采棉机过去,狠狠地忙完这两个月就好了。两个月,董中叶的头发也长出一些了。他剃光了董中叶的头发,那白发根才是她真该有的样子。他绑董中叶时,她还以为他要杀了她。她怕得直哭着求饶,让作鹏想起他那晚在沙发上的害怕。是同一种怕吗?
翻过这个年头,他就五十岁了,一个五十岁的老汉,不怕一个人生活。
擦好车,他重新坐进车里。
这时一辆银灰色的小面包车停在他的车旁,那里位置宽敞,却是不能停车的。一个中年男人下了车,作鹏略略犹豫了下,迅速下了车。那边,他对那个男人向另一边空着的车位指了指说,有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