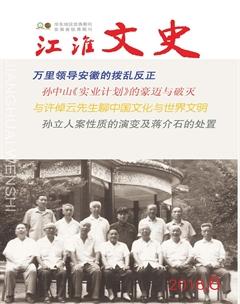由“兵变案”到“匪谍案”
李传玺
1955年5月25日下午6点,一位政工人员来到台湾凤山诚正新村东二巷98号郭廷亮家门口,对正在家中请客的郭廷亮说:郭教官,校长请你立刻到他办公室去一趟。此时郭廷亮正担任步兵学校少校战术教官。听到“立刻”二字,他想都没想就跟着走了。这一走,直到27年后才回到家中。
郭廷亮就此被捕,台湾就此拉开了孙立人兵变案——郭廷亮“匪谍案”大搜捕的大幕。
大搜捕及其罪名
由于此案是从抓捕郭廷亮开始的,后又以郭廷亮“匪谍案”作结的,因此郭廷亮就成为此案的引子。
抓捕郭廷亮,就是根据5月24日监控他们的政工人员的密报进行的。密报称孙立人旧部郭廷亮等人企图趁蒋介石6月6日南部亲校时,“藉口改善军中待遇,秘密发动叛乱”。
都有哪些政工人员呢?
时任台湾“国防部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后来说,保密局特工从1950年初孙立人几次与带有“共”字号人员的接触后,就开始监视他了。这次告密的人中有海军政战部第四科科长袁金贵。
“监察院”关于孙案的调查报告中记载有这些人:陆军军官学校少校校官孔惠农、教材科中尉科员史崇惠、陆军第十师政治部第四科科长原景辉等。
从这些回忆和记载来看,当时台湾国民党部队确实特工遍布,告密成风。而盯着孙立人及其亲信,不仅时间长,恐怕还布满多个层级和渠道。
郭廷亮被捕后,几个孙案关键人物,也就是与孙立人来往密切的年轻军官相继被捕。
时任“陆军总部”第五署第四组组长江云锦(孙案二号人物,主管部队督训工作),副组长是王善从(三号人物,安徽东至人、许世英的外甥)、于新民。第四组下设3个小组,分别负责北部、中部和南部驻军的督训,小组长分别是陆心仁、蒋又新和郭立人。这些人被认为是孙立人联络部队的主要骨干。几个人同时被捕。
时任第九军第二处上尉军事情报官的刘凯英当天去郭廷亮家,吃饭时出去一会,再回来时,郭廷亮已被“请”走。看到有2个陌生人上来问话,身为情报官的他一看情形不对,立即开始逃亡,曾去孙家向孙立人报信。孙立人要他回部队,并给了他一些路费。两个星期后被捕。
郭廷亮被捕时,身上装有一本红色电话簿,上面记着一些亲友的名字,这成了政工人员抓捕谋叛人员的“线索”,一时间抓捕了300多人。那段时间军中人心惶惶,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成了孙立人的“爪牙”。有时候潜藏的政工人员引着大家发牢骚,这边发完,那边就成了抓捕对象。孙立人案刚发生时,一名士兵就广播上说孙立人是“匪谍”向连长陈洪玲报告,陈连长叫这位士兵不要听信谣言。没想到这位就是隐藏的政工,陈洪玲就因为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而随之被捕。
经过甄别,到11月份,还剩下108位。再经过查证,原先以“孙立人兵变案”关系人身份被捕的副师长余世仪、炮兵指挥官伍应煊等73人,不予起诉,无罪开释。还剩下35位,其中郭廷亮、江云锦、王学斌(第十军第四十九师上尉参谋)、田祥鸿(第九军上尉情报官)、王善从、于新民、孙光炎(第七军第六十九师中尉排长)、陈良埙、刘凯英9人是核心。另外26位是赖卓先、邓光忠、李仲瑛、杨永年、冉隆伟、张茂群、王其美、郭立人、金朝虎、范俊勋、杨万良、陈江年、赵玉基、田雨、朱日新、白崇金、王霖、李太远、许达明、高培宾、陈业成、陈世全、窦子卿、张熊飞、沈承基、傅德泽。
关于他们的罪名可从郭廷亮的“犯罪”材料中总体看出:
缘被告郭廷亮前充新一军连长……抵台后即与“匪”方联络,初无积极活动,迨四十三年夏,奉孙立人命,调陆军总司令部服务,并秘密至各部队从事第四军训班毕业生联络工作,知孙不满现状,且有少数军训班同学对孙立人未能升任参谋总长表示不满,时适“匪”帮叫嚣攻台,并派李姓“匪”谍与被告联络,促使进行兵运工作。被告认为时机已到,遂决意进行,以配合“匪”军攻台之企图。乃著手利用孙立人关系,积极联络军训班同学。经被告刘凯英、田祥鸿、王学斌、孙光炎、赖卓先、王其美、范俊勋、杨万良、陈业成、陈世全、冉隆伟等协力进行结果,计在各部队建立联系关系达百人以上,分别指定负责人员进行秘密联络,由被告郭廷亮、田祥鸿、刘凯英随时向孙立人报告,并经常接受孙立人发给之活动费用。经郭廷亮、田祥鸿、刘凯英三被告决定于四十四年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伺机制造国军大规模变乱,占领据点,控制南部,必要时对国军高级将领实行杀害。郭、田二被告于五月初至各部队指示各负责联络人加强活动,控制部队,把持通信部门,威胁部队长,扣留政工人员等行动计划,并设指挥所于关庙,先后由被告王学斌、赖卓先、李仲瑛、杨永年、郭廷亮、田祥鸿等两度至关庙、龙崎一带侦察地形暨通信设备,至同月十五日,被告郭廷亮在台北晋见孙立人,奉孙指示指挥所应设于虎头埤。被告南返后,复召集王学斌、赖卓先、邓光忠于十七日同至新营侦察地形一次,积极进行叛乱活动。
被告江云锦、于新民为孙立人多年旧部,在陆军总部主管督训业务,自四十二年起,即秉承孙意,经常派督训官被告郭廷亮等藉督训机会,至部队联络军训班毕业生,并于四十三年夏,由被告于新民将所联络之各部队负责联络人员造具名册,送交孙立人。嗣由孙指示被告江云锦试验所联络人员通讯效能。被告江云锦即于四十四年五月十八日著被告郭廷亮、刘凯英、许达明等,召集第九军所属各团负责联络人员,即被告金朝虎等十余人,在台南雀经济食堂,秘密集会,席间发表反动言论,以德国隆美尔比拟孙立人,煽动叛乱,并嘱与会人员提高警觉,注意保密。经将开会情形报告孙立人,并奉孙立人明告其叛乱计划,嘱于举事时随赴南部共同进行。
被告王善从因曾办理搜索训练,得孙立人赏识,四十三年夏,率80军搜索实验队在林口演习;同年六月,孙立人交卸陆军总司令前数日,召被告嘱包围阳明山官邸,俾其实行兵谏。当日被告王善从、陈良埙即照孙意,前往阳明山实地侦察地形,准备行动;同年十一月,被告王善从又奉孙立人之命,拟具包围高雄西子湾官邸计划,并接近要塞官兵,刺探要塞警备情形,复与被告陈良埙随从孙立人至西子湾实地侦察官邸地形;四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复奉孙立人面嘱,前往屏东候命行动;二十八日被告陈良埙奉孙派遣,乘汽车南下通知预约候命之被告刘凯英等,以孙有事不能来,并告以郭廷亮被捕消息。事后用电话以暗语向孙报告。(见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孙立人传·下》第757页)
1956年2月6日,这35人以“郭廷亮匪谍案”被起诉,9月29日宣判。15人以非法方法颠覆政府罪判处死刑,后经政治处理给予减刑。他们是:郭廷亮先被判死刑,同一天由蒋介石特赦减为无期徒刑,江云锦、王善从、田祥鸿、孙光炎、刘凯英各15年刑期,王学斌、赖卓先各12年刑期,陈良埙8年刑期,邓光忠、李仲瑛、杨永年、冉隆伟、王其美、张茂群各10年刑期,另20人以违背职守罪均判3年。
1958年4月8日,胡适回到台湾,一次在与蒋介石见面时,建议释放孙案有关人犯(一说台湾“总政治部”第四组组长宋公言,抓捕郭廷亮者,去找他的老师王公屿,请求蒋介石释放江云锦等人)。蒋介石同意后,蒋经国说,放人可以,但要分批,不能一起放,还必须具结出去绝不向任何人透露被捕后的情形。
此时已到1959年上半年,判刑3年的,已经释放,于是台湾当局于5月7日、9日和26日分3批释放了除郭廷亮、孙光炎之外的13人,这13人实际只坐了4年牢。郭廷亮是核心人物,背负着太多秘密,不能随便释放;孙光炎因为在狱中也见不得别人说孙立人坏话,还同别人争辩,结果被打得很厉害,最后发了疯,没有人愿意接他出狱。
郭廷亮等人材料
是如何“整”出来的
郭廷亮等人的材料都是怎么得来的呢?根据有关资料,全来自这些人的“自首书”或“自供状”,而这些“自首”或“自供”并不是这些人根据实际的自白,全是根据“案件制造者”的有意设定,在残酷刑罚威逼下的无奈招供。
为了制造实际证据,造成社会影响,在原定6月6日蒋介石前往南部进行检阅那一天,也就是所谓孙立人要趁机实行兵谏那一天,蒋经国亲自布置了一出“双簧戏”。“根据亲自参加演习的张瑞峰的口述经过,大致可知所谓南部兵变是政工单位制造的假象。他们先在屏东农校,集中300人,都是15至20岁左右的士兵,这些士兵是从军、师中的卫生队直属单位抽调来的。因为卫生直属单位没有军训班同学当排长,其他部队都有军训班同学当排长,而制造假象者有所恐惧,故而抽调卫生兵。300名士兵聆听‘国安会副秘书长蒋经国训话,他说:‘……现有丧心病狂的高级将领,要乘‘总统亲校时谋刺‘总统,你们是部队的忠贞分子,‘总统的安全要靠大家的保卫……随后,这些卫生队员编成小组,每组4名,另外加2名宪兵,担任机场的战备检查。6月6日,亲校日上午,亲校部队进入北机场时,检查小组检查出有士兵在背包内装稻草,稻草下放弹药,检查小组的宪兵紧急迅速地将他们带上卡车。按照规定,校阅时不能带弹药,而这些被捉走的人,反而谈笑自如,毫无惧色。”张瑞峰当时是卫生兵,他奉调参加演习,对这情况感到奇怪,认为有问题。几十年后,张瑞峰和有亲戚关系的王霖相遇时,无意中说出了这些,并说:“这事我在30多年前就知道是假的。”(见九州出版社出版《孙立人案相关人物访问记录》第55页)
亲校那天,谷正文还装模作样派了100多名保密局人员在虎头埤守候一天,准备围剿架炮准备攻击机场的“叛军”,自然毫无所获。
可此时郭廷亮等人的口供全没出来,或者出来了全对不上号,怎么办?
郭廷亮被捕当天即被送上老虎凳进行残酷刑求,10天后奄奄一息才被放下,郭廷亮居然扛住了。
5月28日,第十军第四十九师工兵营上尉通信官赖卓先被捕。6月1日,在接受“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审问时,面对兵变指控,义正词严地说:“我有三点事实证明,‘总统亲校绝无发生兵变的可能:第一,凡是参加亲校部队,为了阵容排面整齐,把原有的建制打散,临时重新编成校阅的队形。表面上站在校阅场上是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而实际上那个连、营、团的官兵,都是新编成在一起,彼此都不熟识,上下情意也不可能事先有所沟通,而且各个士兵校阅时持有的武器,与平时使用的武器又不尽相同,如一位机枪兵,因临时编组成六○炮手,他又怎么会使用六○炮呢?像这样临时编组而成的部队,怎可串通起来实行叛变而挟持‘总统呢?第二,凡是参加校阅的部队,只准携带编制的武器,却严格规定不准携带子弹,自动武器连弹夹都不准携带,甚至不准个人携带钢笔、戒指、笔记本、硬币等日用品,连军便服所有的口袋均须缝上,先由各队军事干部严密搜查,最后各级政工干部再行复检,同时规定各班的政治战士,须互相监视,有无人违规。如此有枪无弹的部队,人数虽多,还能兵变么?同时还有一个实枪实弹的宪兵加强营,在场保护‘总统安全,而有枪无弹的受校官兵敢起来叛乱么?第三,你们既然把我抓起来,必认为我有嫌疑,实则屏东亲校,我已奉命留守,这是有案可查的,怎说我参加兵变呢?”毛人凤被他说得无可应答。
既与实际亲校阅兵情形不符,又无口供印证,此案的实际制造者们有点骑虎难下。经过一番苦思,决定将主题由“兵变”案推向“匪谍”案,让郭廷亮扮演“匪谍”自首。这个主意是后来接手此案的特勤室主任毛惕园想出的。毛惕园说:“如果让郭廷亮承认自己是‘匪谍,而其工作则是策反孙立人,结果是孙立人也同意进行叛变,并交付经费供其串联。”郭廷亮如此坚强,这着能行呢?毛惕园设计了一个软化利诱的圈套,乘毛人凤赴美就医的机会,找了个人头,假扮毛人凤,“两人”向郭廷亮劝诱并担保,只要肯担下“匪谍”罪名,保证他军法审判时,得以无期徒刑结案,并在适当时机,给予减刑,特赦,此外,政府还会负责照顾他一家老小,并且给他一栋房子。之后,“二毛”还给郭廷亮亲笔写下保证书,交给郭廷亮夫人李玉竹。
7月15日,一套已经编好的“匪谍”自首书和口供笔录摆到了郭廷亮面前。让郭廷亮骇异的是,居然加进了共产党要他进行兵运工作的诸多细节,以及要在蒋介石亲校时呈递意见书,视情况许可,激成兵变,以达成为共产党进行兵运工作目的的“罪状”。为了一个国民党员的“政治责任”,郭廷亮虽然心有不甘,心下狐疑,只好照单全收了。
郭廷亮的“口供”出来了,后面的就好说了。那些同时或随后抓进来的,或直接用刑,或送进郭廷亮刑求室,“观摩”郭廷亮用刑,或关在刑求室隔壁,听郭廷亮或其他人受刑的惨叫,如此折磨他们的神经,摧毁他们的意志。然后逼着他们按照设计好的“自白”和“口供”,比照着写,再反复修改,以符合从“兵变”到“匪谍”的要求。
王学斌回忆,他们把他关在一间暗房,审讯开始,先下马威打他两个耳光,并威吓说:“有话实讲,不要作假。”他回答说:“没什么事,有什么可以讲的嘛!”见不能这样取得口供,他们便开始以恐怖的刑具用刑,像老虎凳、烤栗子(用强光照射眼睛)、坐冰(身体脱光,然后拉到零下温度中冰冻)。刑讯的人都是政工,写了很多“口供”,要其承认孙立人分派他谋反的任务,并照着写,不照着写就再拉去用刑。
此案一干人犯的“罪状”就这样出来了,案件的性质也由“兵变案”变成了“匪谍案”。
抓捕郭廷亮等人不是目的,目的在于整肃孙立人,至此外围工作已经理清,剩下的就是如何处理孙立人了。
如何整肃孙立人
看最后那份起诉书,孙立人的“罪行”何其严重。其一,提供经费,利用郭廷亮、江云锦等人在军中联络,培植个人势力;其二,被郭廷亮等利用进行叛乱活动;其三,试图利用武力进行兵谏。说实在话,这其中任何一条,都足以置孙立人于死地。
此案从抓捕郭廷亮等人,到最后判他们的刑,再到追究孙立人的责任,蒋经国都随时向蒋介石汇报。如果说蒋经国主导着案件的定性,蒋介石则主导着处置孙立人的定性。
到10月21日那段时间,几乎每个星期的反省录、每个月的反省录,甚至每隔两三天的日记,蒋介石都会记下孙立人案件的进展,对孙立人处置的思考,以及由此案引起的痛苦和对孙立人的痛骂与愤怒。比如,6月18日周反省录说:“本周苦痛忧患较多,而以孙案及与美有关问题为甚。”6月25日周反省录中说:“孙案全卷审阅已告段落,刺激颇深,加之美顾问对我增师金门之反对态度,殊令人愤懑悒郁,又伤心神不少。”
蒋既想整肃掉孙立人,但似乎从一开始就不想由此真的结束掉孙立人的性命。
蒋介石的日记清晰地记下了这一切。
首先是孙案性质的变化。在5月28日大搜捕之后一段时间,蒋介石对此事一直定性在“阴谋事件”。5月反省录第五条开头一句便是:“孙立人组织暴动陷害之阴谋”。到了6月28日,同毛惕园开始对郭廷亮劝说承认是“匪谍”相对应,蒋介石的定性发生了变化,“审阅孙案中首犯郭廷亮等前后供词,可断定此案又为‘共匪利用孙为傀儡叛乱之阴谋也”。7月9日周反省录中说:“主犯郭廷亮尚未将其与‘共匪关系彻底招供也,此为一老共党员,潜伏在孙之左右无疑。”12日记道:“郭廷亮‘匪谍组织必有其接代任务分子,未参加此次叛变者之隐伏,应重加侦审。”21日记道:“孙案郭廷亮口供已明,其为‘共匪造成我内部矛盾与叛乱颠覆之阴谋甚为显著。”23日周反省录终于认定:“对孙案以郭‘匪谍口供与自白完全明了,乃可作最后决定矣。”
其次是对孙立人的痛骂。5月28日蒋介石周反省录中指斥为“洋奴性成”,因为此段时间传来“最近美国务院忽令其情报人员,密查孙在军队中势力如何”。6月30日月反省录中说:“立人之愚拙余本知之,即其性质之滞钝卑鄙,尤其是‘污泥便丑之劣性余亦知之,但不料其荒谬狂妄,不计利害亦至于此耳。”7月3日,看江云锦自白书,记道:“乃知立人诚一糊涂虫也,危险极矣。”21日,日记如此评价:“孙之表现与性质,甲、亏虚;乙、糊涂;丙、无知;丁、无耻;戊、拖延不决。”针对孙立人坚不承认的表现,蒋介石万分恼怒,28日骂道:“此人绝无男子气质,如此不足为异。”30日周反省录中说:“孙立人案办开始,先不令其出席军事会议以息群愤,但其本人仍做茫然无事之状,仍不愿承认其包藏‘匪谍不轨之事实。其人既无丈夫气,亦无军人魄,可说毫无人格,只知恃外凌上,恶劣成性之汉奸,实为张学良之不如。”并顺便将“国舅”宋子文骂了一下,“此张、孙二人皆为子文所力荐者,子文贻害国家,不仅其本身作恶多端而已,可痛”。
其三是苦心焦虑如何处置孙立人。10月6日,蒋介石有个总结,半年来对孙立人案,“更觉寒心”,夜间睡眠常常恍惚。其过程为:6月23日,蒋介石开始正式考虑如何惩处孙立人。当日,指示“国防部长”俞大维审核孙立人案,俞大维建议对孙案“宽大,不加处分,仅供孙了解此案之内容,乃以装作不信此事对孙有关了之”。对此,蒋介石26日记道:“俞之消极已极,但亦有其见地耳。”7月5日,蒋介石首次列出对孙案处置的“手续”:“明告立人此案之经过供词”;“对军事会议公开报告与判定”;“以不信孙会主谋此案之态度,免予追究,但其应告假反省悔过,不得再用此种‘匪谍与交接杂友”;“彼可言行自由,不予拘束,但对此案无论对任何人必须照此实情明告,不得另有托词假言,否则自将公审”。9日再拟孙案处置方针,“甲、令其告假离职,待罪悔过,但不开除其参军长原缺,派员代理。乙、调其为战略顾问副主委,与顾墨三(顾祝同)对调,使其与叛将专家(白崇禧)并列,但仍令其闭门思过,不得任意说话。丙、直调其为战略顾问,仍令其自反自检,不得任意言行。待其悔过自新以后,另候任用”。7月15日,又作另一种考虑,“对孙可说明,其如读书果有心得,且能反省自责,且将来可派其赴美,但此非其时,以美国环境不良,反动分子太多,彼必其陷害不能自拔,故准其告假专心读书修养”。如此看来蒋介石还是参考了俞的建议,同时还想借重孙与美国的关系。
但到第二天即16日,随着郭廷亮的“匪谍”自供此时出笼,蒋介石的思考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对孙案以法语而言,至少应停职候查后候审,否则应免职查办以息公愤而维军纪。原因,甲、此案为‘共匪早在国际上扬言台湾之渗透程度比所传者更佳,是乃美政府在事前所收得情报。乙、此案人证与确据皆有事实,不得已时皆可公开。丙、此案主动乃为‘共匪渗透颠覆,而为我破获彻底并未为‘共匪所算,孙不过是一被动盲从,故于政府之威信并无所损。丁、孙之美友以事实俱在,不能为其抱不平洗冤,或以此反对我政府。戊、此在美人心目中以有证据之事,而且为其所主动,不能认我为法西斯也。己、现在美国不能放弃台湾,不能因此停止援助。”蒋介石由此态度出发,当天周反省录中再次明确:“对孙案之考虑,轻重利害之间适当处置,惟对内对外之关系,应以公正事实为据,不能全以外人关系而置军心与纪律于不顾。但对外利害与美国心理,亦不能完全抹煞,故决以‘停职候查,据‘期以实情之案语处之。但不公开,使‘共匪对此案之猜度也。”
以后蒋介石对孙立人的处置基本上沿着这个思路进行。蒋介石26日让陈诚(“副总统”)、叶公超(“外交部长”)、张群(“总统”府秘书长)等人向孙立人通报郭廷亮案情及其应负责任。孙立人根本不承认自己与此案关系及其应负责任。面对孙立人的辩白,张群和叶公超明白告诉他不要持这种态度,还是承认所负责任自请处分为好。虽然当日晚蒋介石接到了孙立人“停职候查,恳求保全”的请求,但得知孙谈话时的态度,还是非常愤怒。30日,再度召集陈诚、张群等人商讨如何处置孙立人,决定从31日开始不让其出席军事会议,第二天由陈诚通知他,并“将孙案重要口供交阅后,观孙心理与行动有否悔悟之意,再定处分,务使仁至义尽也”。8月1日,又让张群“将郭、江等自白书交孙反省”,让黄伯度督促孙立人写出引咎辞职报告。
孙立人不得不屈服
那段时间,社会上关于孙立人的传言很多,家人和朋友听说后,都替孙立人担忧,并且劝他出走。他说:“我没做错任何事,为什么出走?如果我出走,假的诬构也会被人说成真的。”“所谓君子坦荡荡,我没有什么可怯惧的。”
7月31日上午,蒋介石要在北投召开扩大军事会议,孙立人准备参加。这时陈诚的电话来了,请孙立人先去他那儿一趟。两人在陈家谈了2个多小时。孙立人仍然直言以对,自己对此案一点也不知情,自问没有任何过错,如果一定要追究责任,他愿辞去军职;自己原本是学土木工程的,大不了今后再去做老本行。
就在那天的会上,蒋介石在军队内部宣布了“孙案”经过,并决定追究孙立人的责任,限制其行动自由。
上午11点,孙立人从陈诚那儿回到台北南昌街官邸,发现卫兵已经换成宪兵,家中所收藏的抗战时俘获日军的战利品和美英将领赠送给他的纪念品都被收缴。第二天一早,宪兵明确交待,从今天起,要孙立人不要再出门;随之“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前来宣布,从今天起,孙立人毋庸再到“总统”府上班;电话线同时被切断。孙立人漫长的软禁生涯就此开始。
这边张群刚走,那边“总统”府第一局局长黄伯度和第二局局长傅亚夫一同前来,将郭廷亮等人的自白书和300多被捕军官名单交给孙立人,建议孙立人引咎辞职。
虽然孙立人在陈诚那儿说愿意辞去军职,但真到了这会儿,孙立人心中仍然不服,“我问心无愧,何咎之有?为什么我要引咎辞职?”
黄伯度也是安徽舒城人,与孙家世谊,与孙立人都排行老二,都被两家人称为“二哥”,但此时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并撂下狠话:“如能主动辞职,则可保全部属300多人性命,家人安全也可获得保障。”黄的这一态度,让孙家人后来对他充满了不满。但如果了解蒋介石此时的思考与决定,黄的表面态度下可能隐藏的是对孙立人及其一家甚至所有受牵连部属的一种隐性保护。后来由陈诚领衔的调查委员会所形成的调查报告,虽然对蒋氏父子作了顺从,但考虑此时政治气候,也应视作是对孙立人的隐性保护。
经过三天三夜的痛苦思考,无奈的孙立人只好于4日开始拟写辞职签呈。堂妹孙敬婉回忆:他常夸耀自己的睡觉本领,就是站着也能睡几分钟,可是这一次不行了,他本不肯自己辞职,因为他不能承认那些虚有的事,认为有辱他的人格,但因事涉300余人的性命,“那一夜,他可真没睡过一分钟,他在考量自己的人格重要,还是那些人的性命重要”。
孙立人逐字逐句斟酌,定稿后,交给黄伯度过目,黄根据蒋介石的要求,提出意见加以修改,最后由其带回呈交。可不久就被退回,说一些地方文意或字句不妥还要修改。孙立人只好委曲求全,参照要求再改。如此反复5次,费时一周,才终于交上了一份与郭廷亮等人自白书内容一致,又让蒋“总统”满意的辞职书。辞职书的签呈时间“定”在8月3日。
孙立人的原辞职书:日昨黄、傅两局长奉命交阅江云锦等供词资料,惊悉职涉有重大之罪嫌,钧座未即付之法办,尤见格外爱护之恩德,天高地厚,感激涕零。而职以随从三十年,尽忠效死,犹恐不及,乃竟发生此种情况,不但五内如焚,急悚万状,且愧对钧座,直欲剖腹以明心。惟应抚衷深切反省,职实有应向钧座引咎请于惩处者:一、郭廷亮为职多年部下,来台后又迭任用,乃竟为“匪谍”,利用职之关系,肆行阴谋,职竟毫不发觉,纵非袒庇“匪”谍,实属异常疏忽,有亏职责。二、两年前,鉴于部队士气低落现象,为要好心切,爰指示督训组,于工作之便,从侧面联络疏导,运用彼等多年同学友好关系,互相策勉,为国效忠,原属积极性之动机,不觉为时既久,竟改变性质,不但有形成小组织之嫌,且甚至演成不法之企图,推源究根,实由于职处事之不慎,知人之不明,几至贻祸国家,百身莫赎。职性急躁,每遇业务之困惑,即显示心情恳切之态,而口齿滞顿,不善说话,虽是有口无心,或辞不表意,使人发生错觉,亦职深以为警者。
最后定稿:窃职材识庸愚,惟知忠义,自游学归国,预身宿卫以还,念八年间,自排长以迄今职,纯出于钧座一手之栽培,恩深谊重,虽父母之于子女无以过之,对于钧座尽忠效力,不惜贡献其生命以及一切,冀报万一,为职此生惟一之志愿。属当国家危难,奉命练军,“匪”祸方深,求效心切,但问事功,未虑得失。于人材方面,急于搜罗,疏于甄别,竟致贤愚未辨,瑕瑜互收。近者陆军部队,发生不肖事件,奉副“总统”谕示郭廷亮案情。日昨黄、傅两局长奉命交阅江云锦等供词资料,职涉有重大之罪嫌,钧座未即付之法司,仰见格外爱护之恩德,天高地厚,感激涕零!职随从垂三十年,尽忠效死,惟恐不及,乃竟发生郭廷亮及江云锦等案情,不但五内如焚,急悚万状,且愧对钧座,直欲剖腹以明心曲。连日深切反省,职实有过错,应向钧座坦率自陈,请予惩处者:一、郭廷亮为职多年部下,来台以后,又迭予任使,乃竟是“匪谍”,利用职之关系,肆行阴谋,陷职入罪,职竟未警觉,实为异常疏忽,大亏职责。二、两年前鉴于部队下级干部与士兵中,因反攻有待,有表示抑郁者。为要好心切,曾指示督训组江云锦等于工作之便,从侧面联络疏导,运用彼等多属同学友好关系,互相策勉,加强团结,以期领导为国效力,原属积极之动机。不意诲导无方,竟致变质,该江云锦等不但有形成小组织之嫌,且甚至企图演成不法之举动,推源究根,实由职愚昧糊涂,处事不慎,知人不明,几至贻祸国家,百身莫赎。上述二事,均应接受钧座严厉制裁。伏念弱冠之年,即追随钧座,今已两鬓俱斑,无日不在培植之中,感激知遇,应有以上报。乃今日竟发生此种不肖事件,抚衷自省,实深愧疚!拟请赐予免职,听候查处,倘蒙高厚,始终保全,俾闭门思过,痛悔自新,则不胜感激待命之至。(见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孙立人言论选集》第429页)
两相比较,前者虽然也是指责自己处事之不慎,知人之不明,异常疏忽,有亏职责,自请惩处,但也凸显了动机与可能的误会,特别深含其中的是,孙立人的语气于表面看去的卑中自有一种坚强的亢;后者表面看去,词句相差不大,但内含却发生了质的变化,在郭廷亮部分,“毫不发觉”变成了“竟未警觉”,突出了对郭的放纵;江云锦部分,“企图”变成了“举动”,突出了实际的威胁,孙立人由“旁观者”变成了“涉入者”。最主要的是后者的语气,孙立人一下变得那么卑贱,似乎在跪着乞求蒋介石的饶恕,而软禁只不过是孙立人因罪惩罚自己以求自赎的自请,蒋介石的目的终于实现了!
为什么说黄伯度这样做对孙立人起到了保护作用?因为就在这两天,蒋经国拿来陈良埙、王善从的自白,直指孙立人自己试图谋叛,差点让蒋介石推翻原来设想。4日日记,“昨晡经儿来后公园报告陈良埙亲笔自白书,证明王善从所供,孙在去秋派其二人到我后草庐住所侦察地形,设计包围之企图是实,此乃所万万不能料及也。应将此原件交孙审阅后,再定最后处置办法”。看来蒋经国是想置孙立人于死地,彻底解决孙立人。恰此时,蒋介石要张群和黄伯度二人汇报3日同孙立人谈话情形,二人救了孙立人一命,“孙亦自觉无言可辩,乃承认郭廷亮‘匪谍及其军训班在部队组织,致成今日恶果,应负其责。但仍不承认其主动谋乱之大罪,惟亦并不如过去之强辩,只求‘总统开恩,保全赦免而已。至此乃可告一段落,即照原定方针,以停职(候审)彻查为第一步程序也”。5日,黄伯度拿来了孙立人经过其斟酌修改的辞职稿,请求保全与停职候处的话验证了两人的汇报,也让蒋介石没有向蒋经国方向倾斜。
对孙立人的处置还得顾忌美国的态度。7月19日,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对此进行分析。7月反省录中说:“孙立人谋叛案已经大白,故决心予以处置,惟其手续与方法应加慎重研究,勿使美国及其反蒋派引以为独裁之口实。”8月6日,蒋介石就此事听取美国顾问的意见,“美国顾问以此事属内政表示不愿过问之意。现在应顾虑各点:甲、吴逆国桢对孙案免职查办时必在美作激烈反宣传,英国亦必助其宣传,以引起美国舆论对我不利之新潮。乙、孙之美友如麦唐纳及若干议员、记者,亦必怀疑对我攻讦……戊、今孙即自呈其悔罪书,对此事发表不妨从缓,不待布置与宣传妥当后暂不宣布。己、应令孙自动宣布之办法。庚、此案应在八月内公布,不可在联合国大会时,或在美国会明令召集时发表也。”鉴于此,孙立人的辞职书要反复修改,以符合蒋“自动宣布”的要求。
就在孙立人辞职书成型的同时,蒋介石于8月12日派“外交部”次长沈昌焕前往美国,争取美国政府理解。之后,于8月20日下午两点半向外界正式公布孙立人案。在这个过程中,接受“驻美大使”顾维钧的建议,成立了所谓九人调查委员会,“依据一个公正团体所调查的事实来采取行动”,并“向世人说明,‘中国政府绝对公平”。
8月20日,台湾公布了孙案。陈诚当天日记:“‘总统发布命令:(一)‘总统府参军长、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因‘共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并请查处,应予照准,着即免职,关于本案详情另组调查委员会秉公彻查,报候核办。(二)派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组织调查委员会,以陈诚为主任委员,就‘共谍郭廷亮案有关详情,彻查具报。”
调查委员会8月26日由陈诚召集召开第一次会议,启动调查,至10月8日调查结束,前后开会9次。9月5日,就调查委员会工作,蒋介石听取张群、黄少谷等人的汇报,批评调查委员会“意见纷歧且不得要领”,并作出明确要求,“第一次报告应求简明迅速,不必过求深入,但应作精详之另一准备,以备不得已时之不能不公布其重要罪证之一部分也”。同时发布了调查委员会结论出来后,进一步处置孙案所有人员的命令,“孙案第二步处置方针,甲、‘匪谍郭廷亮交军法审判。乙、其余从犯皆系被‘匪谍渗透诱惑,事前确不知郭为‘匪谍,企图颠覆之阴谋实系无知妄从或‘奉命行事,应即交治安机关依照其情节轻重分别惩处。丙、孙立人关于本案误用‘匪谍,几乎贻害国家,自知责任重大,引咎待处,既经免职,姑念其相从多年,对革命不无建树,今既深自悔悟,应准其悔改自处,以观后效”,“孙辞职书应与郭供词同时发表”。(见台湾“国史馆”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9册第493页))
在蒋介石的命令下,调查委员会只能顺从,一切结论已成定论,之后的一切所谓公正审判与处置只能在蒋介石的命令中打转。
10月8日,调查委员会将形成的调查报告,连同有关调查笔录、重要文卷及7份调查录音,一起呈报蒋介石。8日最后一次会议,何应钦因去日本治疗眼疾没有参加,其他8名委员联署了报告。
那就按此拿出最后的方案来吧。经过连日苦思焦虑,19日,蒋介石与张群、蒋经国商议后,终于拿定了主意。“对孙教训之方针。甲、自认对孙教导无方。乙、令孙注意二事:子、往日毁谤政府与领袖之言论、政工党务对顾问自失体统之言行,应彻底自反,与直供其过错自白。丑、平时对其策划鼓惑之无形‘匪谍,阴谋卖国之人员,应从速提供姓名,以免再害国家。以此二事为其报效国家之急务,亦为其有否悔改诚意之表示也。如其此时不能直供,则将来恐又有牵累其自身,不仅为害国家而已。”——这恐怕是蒋经国对孙立人是“主犯”推论的坚持,也可能是其设下的陷阱,如孙立人真的直供,不仅彻底毁了孙立人在众人心目中的形象,也是对推论其为主犯的印证。好在从现在能看到的资料中,孙立人没有直供,不仅没有掉入陷阱,也保住了自身形象。
当日,蒋介石将处置手谕起草好,并决定第二天公布。随后把陈诚、张群、俞大维、黄镇球等人找来进行推敲。“始对命令中之‘自新、与报告书中之‘苦谏字样拟加修正,因无其他适当字替代,故仍未改也。”之后又让张群等人命令孙立人,以孙的名义第二天早上约见记者,公开表示悔过,以配合“手谕”发布。孙立人又坚持住了,虽然当天表示同意,可21日早上“称病不见”。蒋介石得知后,立即召来张群一问究竟,“据黄伯度见孙后,以肚泻甚烈,实有病。问孙对报告书有何感想,彼速称丑极愧极,但其对调查会报告第五章‘负责以罪议惟轻之意见甚感云”。黄伯度可能又一次替孙立人作了遮掩。
10月21日,蒋介石处理孙案的手谕终于发布:“查陆军上将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并请查处一案,据调查委员会呈报彻查结果,经准予自新,由国防部随时查考,以观后效,并明令公布在案。所有因案逮捕羁押人员,著即按其情罪分别讯侦处理,迅予结案。其中确属无知盲从,情有可原者,应予从宽发落。”
孙案的处置至此结束,从此开始了漫无期限的软禁岁月。
从这些史料看来,这是一起不折不扣的“冤案”。蒋经国、彭孟缉是真想、真要置孙立人于死地,哪怕不择手段制造冤案。虽然蒋介石站在蒋经国一边,维护儿子的利益,要扶持儿子上位,但从开始就没下定要了结孙立人的决心。
当然也要看到,陈诚、张群、黄伯度等人虽然一味顺从蒋介石旨意,但在汇报孙立人问题上,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替孙立人作了力所能及的“减轻罪责”,以及隐藏在表面态度后面的丝丝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