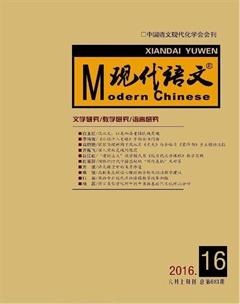缺失性情感的诗性表现
苗珍虎
摘 要:《小雅》诗群的诗歌创作偏重于缺失性情感的表现,在对自然的观照与人性的探寻中充满人生的感喟与迷惘,带有鲜明的现代派诗歌特征。
关键词:《小雅》 诗群 诗学
创立于1936年的《小雅》诗刊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期刊,《小雅》诗群无论是在诗歌形象的塑造、思想情感的抒发,还是在诗歌意境开拓方面,其诗学取向大致是“驮着人世的悲哀”(沈圣时《李白》,见《小雅》第4期,下注只标明刊期)寂寞的歌唱,在悲天悯人的缺失性情感抒写中体现出鲜明的现代派诗学特征。
从身体直接感知的物质形态与特征而言,诗歌形象包括味觉形象、听觉形象、视觉形象、嗅觉形象和触觉形象等方面,《小雅》诗群多借助这些形象将内在抑郁的情感喷涌而出。李章伯的《望儿归》(第1期)借“南归的雁声”“哀鸣的蟋蟀”和“永不回来的足音”等听觉形象突出母亲渴望亲人归来的殷切期盼与无望的等待。林丁的《酒》(第3期)借“酒”之味觉形象拓展诗歌的诗性空间,化抽象为具体,“把悲愤掷出胸腔”,将复杂的心理体验化为可触可感、充满力量的动作行为,抒发诗人失意状态下的理性认知与自我安慰。佚名的《除夕》(第5、6合期)借“炮竹”“冲霄的烟火”之视听形象抒写孩童纯真无邪的快乐,反衬“众人皆欢我独愁”的失落及其对时光飞逝的悲鸣……
另一方面《小雅》诗人通过个性化的人物形象来传达普遍性的人类情感体验,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吴奔星的《行云》(第1期)中“疲倦的泪遂潸然下洒”抒发出“异邦的放逐者”的漂泊惆怅,展现出孤苦无依、思家恋家、怅然若失的游子形象。李长之的《北海夜游》(第3期)夜晚冥思“人事多苟苟,令湖山蒙羞”“见人间之藐小,思天地之悠悠”“想永恒之常住,悲人性之脆薄”,诗歌将绘景与写人结合在一起,讴歌了自然之永恒,慨叹着人世之沧桑,饱含阅尽世态炎凉后的淡泊与从容,彰显出一个理性而又冷静的智者形象。林庚《夜》(第3期)显示出夜越深、情越真的怅惘,在“清白的夜之灯下安慰了别情”中,展现出“人生如一曲哀愁”的深层次孤独意识的“过客”形象。
就思想感情的表达而言,《小雅》诗群的诗歌创作涉及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等,其基调多为悲伤、愁苦、郁闷、遗憾、哀怨等缺失性情感。
在抒写缺失性亲情方面,《小雅》诗刊第2期中路易士的系列诗歌较有代表性,诗人的《黄昏小景》没有勾勒出常见的家的温馨,而是写尽了诗人的颓废与感伤:“倚着颓败的家门/默默地,我们遥看西天”;家庭氛围是凄凉冷落的:“晚饭时妻的琐碎的话——/几年前的旧事已如烟了/而在青菜汤的淡味里/我觉出了一些生的凄凉”(《傍晚的家》);夫妻之间也没有应有的默契,而是“纵有温情已迢迢了/妻的眼睛是寂寞的”(《二月之雪》)情绪状态尽是灰色虚无,这是诗人心情苦闷的内在表征。
在复杂情感的抒情言志上,李章伯的《寄》(第1期)堪称典范之作:
离弦之箭是无法挽回的,/我能挽得住你吗?/今朝你是决定走了,/走了,永不回来!//我只好/在月光清冷的坟头,/为你开一朵向阳花。
小诗以对话的形式展现了诗人对逝者由留恋到哀悼的情感起伏。“离弦之箭”的比喻形象恰当,以极强的客观速度来彰显生者渴望挽留逝者的极度无助,蕴含着生命流逝的无限感伤。“挽回”而不是“收回”似乎有些突兀,语义上的矛盾形成情感上的丰富性,一个“能”字反映出诗人的无奈,蕴含着生死离别已成事实的惆怅。“你是决定走了”,这种化死亡的被动无助为逝者的自觉主动似乎不合情理,但这种埋怨式表述更能反衬出诗人所受的巨大打击与彼此的真挚情感。两个“走了”的回环往复构成低沉徘徊的缅怀基调,表现出一种绝望悲怆的柔性情感。
第二小节诗人的情感由自然情感的激越回归到心绪平复后的缓冲,写出了不得不接受友人亡故的哀痛与缅怀。“坟头”直接点明生离死别,“向阳花”这一诗意而又显得浪漫的暖色调使得诗歌瞬间产生了鲜明的画面感,增强了诗歌的绘画美,它与“月光清冷的坟头”孤寂黯然的冷色调形成鲜明的对照,前者代表着白昼阳光下的旺盛生命力,后者代表着黑夜笼罩下死一般的寂静冷清,冷暖意象的矛盾对立使得小诗具有了无限的张力,丰富了诗歌的审美意境。
诗人用“开一朵向阳花”而不是“栽”,是化实为虚,省略了向阳花由“栽”到“开”的漫长等待,而直接进入“开”的繁盛艳丽,更能突出一份温暖与诗性。
在标点符号的使用上本诗能够呈现出直观的情感走向,一个反问句,一个祈使句,显示出强烈的感情流向,正如吴奔星所言:“标点符号在诗里,不仅是形式问题,它也与诗的内容所带来的感情色彩和语气有关。”[1]这首诗构思精巧,用语朴实无华,却能于平淡之中见波澜,令人回味悠长。
在诗歌意境拓展方面,《小雅》诗群在写景抒情及其意象的组合上呈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准。
沈绿蒂《春夜雨》(第5、6合期)题目中涉及的三个意象构成了情感跃动的多重转折:“春”寓意喜庆温暖,但时间却是在黑暗寂寞的“夜”里;“夜”让人怀想家的温馨,而雨水却弥漫了归途的心情;虽然雨水打湿了“破浪的帆篷”,但诗人还是有所希冀的等待,“待明日之太阳吧,迎风送来杨花”。几重跌宕起伏将诗人恋春又伤春的复杂矛盾心情描绘得淋漓尽致。
李白凤《无题》(第5、6合期)以质朴无华的语言表现出社会生活中人际交往的复杂:“我之来/没有得罪过谁/然而/默默地——/你像冬风/我像花。”当如花一般的纯洁友善与真诚遭遇人性卑劣的暗流涌动时,诗人没有换来相应的温馨回馈,反而迎来了对方那寒风般刺骨的冷漠,情感丰富,集委屈、倾诉、谴责、不解于一体,“默默地”突出了不经意间关系淡化乃至恶化的出乎意料,平静中彰显的是内心深处巨大的心理波澜,在莫名其妙受到伤害的痛苦思索中蕴含着无可奈何的对于人情冷暖的感喟。
诗歌创作中最能体现诗人创作意旨与思想感情的莫过于意象的准确运用,《小雅》诗群的缺失性情感表现多借助于生动表意的“梦”意象展示出来。
“在梦的空间/有一首神秘的诗——/是我写不出,/你也看不懂”(邓梅诗《我从》,第5、6合期)。梦的隐密性与不可言说性利于传达抒情主人公内心深处细腻的情感轨迹,揭示出人物感性与理性碰撞下取舍的纠结与矛盾,梦的虚幻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抒情主人公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与愤懑。
李章伯的《蒲公英》(第1期)托物言志,轻盈飘逸但命运短暂的蒲公英,“她的梦深藏在露珠里”,而露珠同样是无法控制自己命运的弱者,突出了梦想的脆弱与无助。路易士《归来吟》(第2期)看到“初恋的街”“十年来我的梦的摇篮”没有一丝甜蜜的感觉,映入眼帘的只有“黯然的脸”和“幽灵似的三五行人的彳亍”。吴奔星笔下的梦是“银色的”,如同“荷叶上银色的珠”,在清婉中透出好梦易醒、佳境易逝的感伤(《人生小唱之二银色的珠》)(第2期)。李佛波将“梦的轻盈”与“幽森的古寺梵钟”作了对比,衬托出失意人的“心的颤动”与无限哀怨《薄印》(第3期)。李章伯《无题》(第3期)“梦之舟道寄泊于孤星”传达出诗人漂泊的黯然神伤和对居无定所的寂寥惆怅。
《小雅》诗群笔下的梦意象看似诗人自由意识的诗性挥洒,更多的是诗人潜意识的流露,寄寓着诗人独特的心路历程,在似梦还真的艺术情境中阐述着诗人对人事的敏锐认知。
从庄周梦蝶开始,中国文学作品中虚幻的梦境常带给文学的是富有浪漫情调的想象空间,催生作家的创作灵感与艺术直觉,揭示抒情主人公深层次的心理需求,成为诗人抒情的有效手段,“梦与其说是一个事实性判断,不如说是一个价值与意义的询问。”[2]
《小雅》诗群的诗歌主题及其形式体现出现代派诗歌的典型特色,缺失性情感与蓝棣之概括的“青春的病态”是相通的,这是由于1930年代特殊的时局与诗人普遍的困顿有关,“有个人的郁结和民族的郁结,有对政治者的绝望,以及青年们在畸形的大都市文明中的失落感”[3]。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省教育厅2012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项目“《小雅》诗刊及其诗群研究”项目编号:[2012SJD75000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吴奔星:《人生口哨》,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57页。
[2]张曙光:《梦与觉:一个典型的存在论论题》,学术研究,2004年,第1期。
[3]蓝棣之编选:《现代派诗选》(修订版),1986年版,前言,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