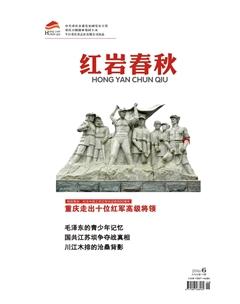堂屋
朱芸锋
重庆市荣昌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曾获重庆新闻奖。
马蹬坝村的民居,几乎都修建在山脚下的坝子周围。民居之间相隔不远就会有一个院子,而每个院子通常分为上屋、下屋或侧屋,聚居着10多戶人家。
一个院子里能够住在上屋的人家,当然是很有身份的,要么是长辈,要么是长房。因此,不同院子之间的村民相互沟通或找人议事,通常会跑去上屋。然而,小时候的我们却对上屋躲得远远的,即便是躲迷藏,也偶尔才有胆子较大的敢钻进去。在上屋那排房子的正中,一般都有一间特别宽大的屋子,那是堂屋。我们不敢去堂屋,不是因为那里多么神圣,而是害怕摆放在堂屋里的两样东西:灵神牌位和棺材。
棺材在马蹬坝不叫棺材,而被叫做“方子”。如果一个院子的人家较多,往往有许多棺材上下几层地垒在一起,将整个堂屋的空间挤压得异常地逼仄。另外,棺材会让人自然而然地想到在它里面迟早会躺进去一个曾经活着、却不会再活过来的人,心里就会不寒而栗。
无论家境贫富,为每位老人准备的棺材都要用上好的木材。马蹬坝是个山间坝子,坝子周围的大山都是茂密的树林。山里最好的木材,当属柏木。寒冬腊月,当村民们忙完农活准备过年的时候,专门给老人制作棺材的木匠师傅也就开始出门干活。听老辈人讲,做棺材最讲究的就是整个棺材都不能用铁器,哪怕是一颗钉子。通体都用传统的卯榫固定大小部件,使整个结构严丝合缝。
如此高超的技术要求,简直就是在打造一件艺术品。村里的老人对自己将来使用的棺材呵护有加,也就不奇怪了。在我记忆里,我们院子里有一位宗世老祖祖,不苟言笑的他常常佝偻着腰,手里一直捏着永远冒着烟气的叶子烟杆。老祖祖住院子北屋,但他却将自家的稻谷存放于堂屋的棺材中。隔三差五,他便要去堂屋打开棺材撮取稻谷,或者就是简单查看属于他的那口棺材。彼情彼景,至今令人感到某种诡异。
3年前冬天的一个夜晚,外公终于没能扛住疾病折磨,走完了他80多年的一生。当我不远千里回老家奔丧,一脚跨进停放着外公棺材的堂屋大门,刹那间一股肃然之气迎面而来,令人不禁悲从中来。
原本低矮狭窄的堂屋,此时却成为了一个满装记忆并不断释放的容器:外公抱着我在堂屋坐席吃饭;舅舅或姨妈在堂屋操办婚礼;我和表弟、表妹们吃着外婆煮的咸鸭蛋,在堂屋玩耍嬉戏……这些场景,瞬间变得清晰,似乎就在眼前。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明白,为什么老家的人们无论外出多远,最后都想叶落归根;我也终于愿意去理解,为什么那些并不高大华丽的堂屋,即使变得残破简陋,仍被一辈又一辈村民视若精神庙堂,代代传承相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