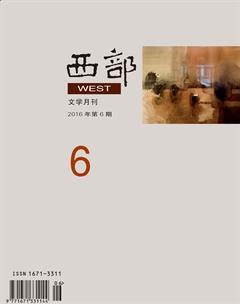抵达
张存学,男,生于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祖籍甘肃靖远县。作品主要发表于《收获》《十月》《中国作家》《上海文学》等。作品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中国2005年最佳短篇小说》等选刊和选本选载过。出版中篇小说集《蓝丽》。出版和发表长篇小说《轻柔之手》《坚硬时光》《我不放过你》和《白色庄窠》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
周燕站在阳台上看到刘堪朝这栋楼走来。周燕想,刘堪终于来了——他来向她的姐姐周凌霞告别。但现在这房子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姐姐周凌霞出去了。周燕猜想刘堪在别的地方已经找过她姐姐,没有找到后他便朝这里走来。
周燕从阳台上退到客厅里,她坐在沙发上沉默着,将目光对着墙上的一幅画。画上是两只红色的手,两只手都张牙舞爪地张开着,手的上方是几个形象模糊的红色污团。周燕将这幅画挂在墙上的那一天,周凌霞看了半天,然后皱了皱眉头说:“这是啥玩艺儿?就像两只血手。”周燕没有解释什么,更没有解释这幅画的确是用两只血手印上去的,画中的红色就是她的血。那天,她用刀片割破自己的手时,看着血慢慢洇出,越洇越多,她就想到一双在空中扬起的红色血手。她找来一张纸,将两只手印在纸上。干完这些,她平静地处理好伤口,站在阳台上,目光对着深蓝的天空。天空飞过一只鹰,鹰平缓地舒展着它宽大的翅膀,向远处滑翔,然后,慢慢消失。
“血色之手”的画在那一天慢慢阴干。阴干后的两只血手呈现着暗红的颜色,阴沉,凝重。第二天,周燕将这幅画装裱后,挂在了墙上。
敲门声响起。周燕挪动步子走向被敲响的门。她打开门,看着站在门口的刘堪。刘堪的神情和她想象得差不多:这是个被伤害的男人——被她姐姐也被他自己伤害的男人。他的眼睛灰蒙无光,棱起的鼻梁显示着无奈与颓丧的情绪。周燕让进刘堪。刘堪走进客厅时问周燕:“你姐在不在家?”
“不在。”周燕说。
刘堪迟疑着,似乎拿不准是该离开还是等周凌霞回来。
“她出去了。”周燕看着刘堪说。
刘堪神情恍惚地在客厅里转动着身子,他的目光最后落在了墙上的画上。这幅画他已经看过多次,一个月前他曾长时间地伫立在这幅画前,他看了好长时间,就像以往看这幅画时一样,他沉默着,不询问,也不对它说什么。现在,他看着这幅画,然后将目光转向周燕。
“这是你的画?”刘堪问。
周燕点了点头。
“这是你的两只手?”
周燕迟疑了一下,又点点头。
“是用血印上去的。”刘堪说。
周燕吃了一惊,但她马上又显得平静异常。
刘堪的目光漫过眼前的周燕,似乎在注视着一片空茫之地。那片空茫之地虚幻、遥远,周燕从刘堪的眼中看到了那片空茫之地,那虚幻和遥远有种褫夺的力量。周燕甚至感觉到那片空茫之地能将呼吸、能将鲜血夺走——血在空中飞舞,然后无影无踪。
刘堪的目光重新回到周燕身上,他说:“我要离开这地方。”
周燕平静地看着刘堪,她已猜测到刘堪要离开德鲁这地方——她想象过刘堪的许多情态,眼睛变得疯狂,举止懒散或者乖张;她甚至想象过刘堪将他的愤怒倾倒给周凌霞;但最后,她想象到刘堪只能向周凌霞告别,离开这里。
“要多长时间?”周燕问。
“说不上。”刘堪避开周燕的目光。
现在周燕的神情却迷蒙起来,她注视着先前刘堪目光中的那片空茫之地,有一些形状不明的影子在那里跳动。混乱的影子,它们的跳动不具有任何意义。待到她回过神时,刘堪已朝门口走去。
周燕突然返回自己的房间,从柜子的最里面翻出一个包,然后飞快地追上已经走出门的刘堪,将包塞到他的手中。
刘堪接过包稍稍显出意外之态,然后他拿着这个包慢慢朝楼下走去。
2
周燕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去的刘堪。刘堪夹着那个包——就像夹着一个身外之物,他似乎对周燕给予的这个包并不在意。这一点周燕已经预想到了。这个比她大五岁的男人几年来一直将心思放在她姐姐周凌霞身上,对于他来说,她只是周凌霞的妹妹,一个反复无常而且有些怪诞的女孩子。他将他的目光放在远处看这个女孩子,看着她慢慢长大,看着她一些不合常规的举动,包括那幅印有两只血手的画。只有这个男人一眼就看出了那是用血印上去的。血在飞舞。这个二十岁的女孩的心在开启着一扇阴暗的门。他看到了这扇门,但他从来不肯进入。
周燕想象着这么一种情形:刘堪拿回那个包,他不经意间打开它,然后他看到包里的衣服,衣服的颜色和黑色闪亮的纽扣会让他记起那是他的衣服,但那件衣服已经被剪成条状,就像一面被剪成条状的旗帜。他抖起那面“旗帜”会看到整齐的剪痕,惊愕和深思同时呈现在他的脸上。这也是周燕所要达到的效果。她用这件被她亲手慢慢剪破的衣服给予他重重一击,同时表明她的存在——她必须存在于他的世界中,让她的存在挡住他的视线,让他旋转、停滞。
想到这里,周燕露出了一丝笑容。刘堪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她的视野中。她返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想她下一步该怎么办。刘堪的离去已经无可挽回,他或许会回来,或许永远离开这个地方。
钥匙拧动门的声音响起。周燕转向被钥匙拧响的门。门被打开,走进了姐姐周凌霞。
周凌霞走进屋里脱掉外衣,她撩了撩黑色闪亮的长发,这长发在很多时候遮去了她的半张脸,她的一双眼睛因此就像从深水中泛出的两团光,朦胧而又闪亮。正是这双眼睛让男人们心荡神迷。
“刘堪来过。”周燕对姐姐说。
周凌霞没有说什么,站在饮水机前咕咕喝下一杯水。
“他说他要离开这里,”周燕说,“他好像是来向你告别的。”
“我知道了。”周凌霞说着坐在沙发上。
“你知道他要走?”周燕转向姐姐。
“我知道,几天前他给我说过。”
周燕紧闭了嘴。这种情形她已经料到。这个和她共住一处的姐姐从开始就与刘堪纠缠不清,这些她都清楚。周燕坐下来,这个时候,她感觉到先前那片空茫之地进入她的心中,那虚幻的空茫之地在她心中愈来愈真实,它向外扩延,越来越大。
周凌霞点燃一支烟。她抽烟的姿势随意而优雅,烟夹在她的手上,就像夹着一支无形的羽毛,轻盈,飘逸,不具目的性。
就像一片云,无法被轻易抓住。周燕站起来走向厨房时这样想。周燕走向厨房是因为她听到了楼下的摩托车声。她站在厨房窗前,透过玻璃,看到身材细长的陈韦熄灭了摩托车,他将头上的头盔取下来犹豫着——他盘算着怎么敲响门、怎么见周凌霞。
周燕看着楼下的陈韦就想到了刘堪。和刘堪一样,这个男人对周凌霞紧追不舍,不同的是,刘堪具有沉郁、忧伤的特性,而他始终是风风火火的,将对周凌霞的痴情毫不保留地呈现在脸上,而且始终骑着摩托车风风火火地飞来飞去。周燕想,陈韦更像电一样闪来闪去。
楼下的陈韦将头盔抱在怀中,他仍在犹豫。头盔是红色的,那是醒目的颜色。周燕看着那红色的头盔慢慢滋生起一种想象,红色无限蔓延,这是恶意的蔓延,冰冷,阴暗。在这种想象中,一个身影远去,那是刘堪的身影,他拒绝了他自己,并试图颠覆他在这里的一切。
而这个时候,另一个男人的出现填补了刘堪留下的空白。周燕注视着楼下的陈韦。现在,她不由自主地将陈韦看作是她几年来一直神往但怨恨不已的刘堪。
陈韦终于上楼来。他敲响门的时候,周燕仍站在厨房里。敲门声时断时续。坐在客厅沙发上的周凌霞不会理睬这敲门声。
周燕从厨房里走出,拉开门让陈韦进来。陈韦咧嘴向她笑了笑,随后便朝客厅走去。
周燕走出门外。她下了楼梯,然后朝街上走去。
3
刘堪离开德鲁城是一九九二年七月十日。在他乘上通往省城的班车时,他才想起周燕给他的包。他离开德鲁的前一天晚上,将周燕给的包随意塞进行李包中。这是个不大的包,它被塞进行李包中立刻被其他东西淹没。现在他想起了这个包,站起来从头顶的架上取下行李包,将它拿出来。
刘堪打开包,看到了黑色闪亮的纽扣。他愣了一下,然后将这件衣服抖开——这是他的衣服,他认出来了,同时对这件剪成条状的衣服惊讶不已。
刘堪不得不回想。五年前,他陪同只有十五岁的周燕乘车到达省城,然后又乘火车去千里之外的一个县城。在那个县城里,周燕十八岁的哥哥周夏将要被处以死刑。一个月前,周夏被判刑的消息传到德鲁。消息是通过周燕父亲的信到达的,信是写给周凌霞的。周凌霞拿着这封信长久地坐在黑暗的屋子。她手中的烟一明一灭。刘堪走进周凌霞的屋子里,透过从窗户照进的月光看到周凌霞像个幽灵一样一动不动地坐着,她的长发遮去了她的半张脸,黯淡的眼睛泛着冰冷的光。刘堪打开灯。周凌霞的另一只手捏着父亲的来信。刘堪站在她面前时,她仍一动不动地坐着,过了好长时间,她将手中的信递给刘堪。
刘堪看完信回想起几年前的周夏。那时周凌霞的父母亲离了婚,父亲带着周夏离开德鲁回到他的老家——那个县城,在那里落了脚,并开始了不同于德鲁的生活。母亲和周凌霞、周燕留在了德鲁。不久,母亲又嫁给德鲁城里一个搞建筑的经理。这个姓李的经理在年轻时一直追求周凌霞的母亲,现在他终于如愿以偿。几年前的周夏是一个白净、文静的中学生,他的头发总是梳得整整齐齐。几年后他成了一个死刑犯。刘堪拿着信感到世事难以预料。他放下信看周凌霞时,她依然是一副慵懒的神情,脸上没有悲伤,更多的是处在世事之外的神态,冷漠而又显得遥远。
这封信的内容没有透露给周凌霞的母亲。她母亲四十多岁,尽管年轻时候的容颜仍旧可寻,但经历了离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坎坷后,她的头发已经泛白。刘堪征询周凌霞的意见后将这信的内容告诉了周燕。周燕站在他的面前,整个身子在摇颤,但没有流泪。刘堪拍打着她的肩膀,他想将周燕的眼泪拍打出来。这种拍打最终起了作用,周燕在不住的摇颤中流出了眼泪。
火车在黑夜中奔驰。刘堪在火车的呼啸声中昏昏睡去。半夜他睁开眼睛时,坐在对面的周燕睁着眼睛对着窗户,而窗户外是漆黑的夜晚,偶尔有星星点点的灯光闪烁在漫无边际的黑暗中显得孤寂而凄然。刘堪劝周燕睡一会儿。周燕只是看了刘堪一眼,然后又把目光投向窗外浓重的黑夜。
在离开德鲁之前,周凌霞说她不愿去父亲那儿,不愿去见那么一个兄弟。说这话的时候她坐在自己的宿舍里。“既然他快死了,见他又有什么用?”刘堪站在周凌霞面前看着她,他再一次透过面前这张脸、这双眼睛感到一片旷远的原野,这片原野是灰云低垂的原野,忧伤和发不出声的呼喊充斥其中。这片原野让人痴迷而神往。这片原野早已存在,许多时候,刘堪面对它无力拔身而去,他只能不断地走入,愈是走入,原野愈是向前扩延。
“烦你陪周燕去一趟,周夏最希望见到的也许是周燕。”周凌霞对刘堪说,她这么说的时候,慢慢站起来,语气中充满了恳求的意味。
火车到达那个县城时,已是晨光微露的时刻。刘堪和周燕下了火车,走到出站口时,火车又在他们身后鸣笛而去,轰隆隆的声音撼醒大地。
被剃短了头发的周夏已经与几年前的他迥然不同,几年前那个周夏的影子在面前这个周夏的身上已荡然无存。面前的他目光呆滞,显示着他这个年龄对于死亡的麻木、迷惘,同时夹杂着没有尽头的恐惧。刘堪站在一旁,看着周燕,这个十五岁的姑娘所表现的与他想象的截然不同,她没有眼泪,也没有颤抖,而是平静地面对她的哥哥。这种镇定的神态让刘堪吃惊。平日中的周燕总是不安分,一双眼睛转来转去,而现在,她像个成年人,像个深谙世事的成年女人。
周夏伙同别人抢劫银行时打死了一个银行职员,这种罪责是无法被饶恕的。刘堪和周燕去看周燕的父亲时,周燕的父亲向他们叙述了周夏犯罪的一切。这个父亲已经被打垮,他的脸上聚集着皱纹,叙述的声音苍老而又低沉。在他的最小的女儿面前,他最终失声痛哭,说是他没有管教好周夏,周夏初中毕业后就混入社会,结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他甚至用皮带、棍子等各种手段阻止儿子和坏人鬼混,但没有用,他眼睁睁地看着儿子走到了今天这地步。
周燕一直沉默着,她在父亲的叙述中目光漫向别处。刘堪想,她那时的样子似乎在注视灾难扭动的身影,灾难在她的视野中露出凶恶的面目。尽管如此,灾难依然是捉摸不定的,它在它的世界里神秘地注视着世人。
周夏受刑的那一天,刘堪没有看到周燕。刘堪从他住的旅馆里走出时,漫天飘着雪花。公判大会是在那个县城的体育场进行的。刘堪走进体育场时,周夏和其他犯人已被押出。那是惯常的情形。周夏被押到一辆车上,车上是荷枪实弹的武警和警察。警笛声一直响着。刘堪寻找着周燕的身影。他想周燕在这个时候肯定会守着她的父亲。刘堪走向周燕父亲家,但家里只有周燕父亲一个人,他躺在床上,面色苍白,眼睛无光。
刘堪直到晚上才在一个不大的舞厅里找到周燕。那是个灯光幽暗、混乱而张扬着乖戾气息的舞厅。周燕和一个小伙子搂在一起慢慢扭动,她的脸贴着那个小伙子的脸,身体与小伙子身体紧挨在一起。这让刘堪万分震惊。他走上前去将周燕一把提转开来。然后他瞪着那个小伙子。小伙子凶光毕露地对着刘堪的目光。呼啦啦又围上几个小伙子,他们留着长发,目光凶狠而又放肆。刘堪看到了他们手中的啤酒瓶和露着白刃的刀子。
刘堪回想他那时像个真正的男人,没有畏惧感,他更多的是愤怒,那愤怒是对着周燕的还是对着那帮小伙子的他说不清。他站着,将周燕挡在身后。他感觉到他的手上被递上了一把刀子。是身后的周燕递给他的。他感到意外,同时将刀子举起来。那是一把七寸长的腰刀,它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寒光。他举着刀子,拉着周燕的手向后退去。
那帮小伙子没有追出来。刘堪选择退出的举动不伤他们的面子。刘堪在退出舞厅后仍紧紧拉着周燕的手。现在,让他万分惊讶的是这个来探望临死的哥哥的姑娘居然带来了一把刀。他们在夜晚白雪飘舞的街上走着,然后,刘堪站住,他双手紧紧箍住周燕的肩膀,紧紧盯着周燕的眼睛,想从周燕的眼睛中看出这个姑娘到底是怎么回事。周燕平静地对着刘堪,但她的身子在打颤——因为寒冷而打颤。刘堪放下手,将自己的外套披在周燕的身上。他什么也不想问了。一个刚刚失去亲人的姑娘或许就是如此,但寒光闪闪的刀让刘堪百思不得其解。
黑色的外套一直被周燕穿回德鲁,从此它就消失了。刘堪曾经问过周燕他那外套的下落。周燕说:“丢了,不知丢到了啥地方。”
现在,这件外套又回到了刘堪手上,它已经被剪得破烂不堪。刘堪想象剪子握在周燕手上的情形,剪子就像一把刀,她平静地砍斫着一个形象,这个形象在她的砍斫下成为碎片。而她胸中深怀的一切都是不明的,它们是深渊,冒着寒气,同时也混合着血之光。五年过去,这个姑娘事实上被刘堪忽视,就像忽视一道闪电,它在谜一样的深渊中向上闪烁,而他却没有注视它。
4
周燕走在街上。她戴着一顶蓝色的帽子。这顶帽子已经有两年时间被搁置一旁。两年后的今天她重新戴上它,她坚信,这顶帽子依然会传递召唤的信息。
一九八九年的整个一年里,德鲁城里拔刀子、不断打架闹事的小伙子们都知道鹰这么一个姑娘。鹰在一次几十人的斗殴中出了名,当时她穿着男性的衣服,手中挥舞着一把长刀。她冲向对方的时候,眼中冒着可怖的凶光。这么一个凶光逼人的姑娘立刻唤醒她身后的小伙子们,小伙子们跟随她跳跃着,挥舞着手中的家什朝对方冲去。冲在最前面的鹰足以震住对方几十号人马——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个胆气冲天的姑娘,她奇怪的装束,她那刀子般的眼睛,让他们迷惑和胆寒,让他们不知所措。最后,在鹰还没有冲上来时,他们哄然四散。
从此,鹰成为德鲁街头一个有名的人物。十七岁的鹰总是穿得奇奇怪怪,她的名号不断被传播,到了后来,不管是哪一方的小伙子见了鹰都恭恭敬敬。鹰无形中成为德鲁街头小伙子们的头。当她戴着蓝色帽子的时候,有人就会聚集在她的身旁,他们替鹰买喝买吃,替鹰摆平一些不顺眼的人。鹰头上的蓝色帽子因此也就成为一种信号——召集别人的信号。德鲁街头的小伙子以给鹰做事为荣,一旦鹰戴着蓝色的帽子出现在街头,他们便蜂拥而至。
三年前,周燕对自己成为鹰的角色感到厌倦。在成为鹰的最初日子里,她曾经有过兴奋和疯狂,她参与过多次斗殴,但更多的时候,她只是发号施令。在那段时间里,她游荡在街头,并不断喝酒,喝醉的时候只是一个劲地冷笑,冷笑的声音阴森而可怖,旁边的小伙子们都噤若寒蝉。到了那一年最后的日子里,周燕对这种日子厌倦了。街头那些小伙子有的被警察抓走了,但她对此并不放在心上,她的厌倦来自于另外的地方。
从此她退出街头的斗殴。
事实上,周燕在那一年中一直期盼被扇耳光的情形,但那种情形一直没有出现。这是后来周燕才明白的。
那一年之后的一天,周凌霞看着躺在床上的周燕。当时是星期天,上午的太阳光照进房间。周凌霞看着这个妹妹,然后将她摇醒。
周燕睁开眼睛,看着一脸疑惑的姐姐。
“鹰就是你?”周凌霞问。
周燕揉了揉眼睛,现在该到她吃惊了,她吃惊的是姐姐周凌霞居然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还不知道自己就是街头上那个著名的鹰。周燕看着姐姐,然后点了点头。
周凌霞愣住了。她没有想到这是事实。她长时间地盯着周燕,然后说:“真没有想到你是那个大家都知道的鹰。”
周燕没有说什么,那时她明白她成为鹰的一年也是她最愤怒的一年,愤怒来自何方是不明的。在愤怒的同时,她一直隐隐期盼着自己被扇一耳光。
周夏死去三个月后的一天,周燕坐在母亲的家里。这个家严格来说是继父李胖子的家。发了财的李胖子把整个家弄得富丽堂皇。他将周燕母亲娶到这个家时欢天喜地,两个女儿跟随母亲也住到了这个家里,不久姐姐周凌霞就搬到了她单位的宿舍里。一天母亲出去了,家里只剩下周燕和继父李胖子。李胖子穿着一身睡衣,不断地走进周燕的房间,围着周燕转来转去。周燕不动声色地坐着,她想,这种情形又来了——继父对她涎着脸,眼睛在她身上[睛] [留]来[睛] [留]去。继父最后一次进来时手里端着一盘水果,他将水果放在她面前时一只手搭在了她的肩上。这双肥厚的手顺着她肩膀往下溜时,她站了起来,并顺手提起了早已准备好的斧头。斧头被举起时,继父惊得睁大了眼睛,他抱头向外跑时,斧头落在了他的脚后。
那一天,周燕拾起斧头将家里的东西砸了个一塌糊涂,然后离开那个家,直奔车站。十几分钟后,她乘上了通往省城的班车。
三天后,刘堪出现在她面前,这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逃到省城,她住在亲戚家,她对亲戚闭口不说离开德鲁到省城的原因。她也不说她的学业,不说她所在的德鲁中学的情况。亲戚从她嘴里问不出什么,只好给她的母亲打电话。她母亲接到电话后就哭了起来。她拒绝在电话里与母亲通话。之后,她想象着要么是母亲要么是姐姐周凌霞来省城将她接回去。她想再一次逃走,逃向更远的地方,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这种打算。她想,以后有的是时间。第三天,她等待家人来临,但出现在她面前的是刘堪。
刘堪要她第二天就跟他回去。
她说:“我不要这么快回去。”
刘堪看着她,眼中充满了怒火。“你还得想想你的学习。”刘堪说。
“我无所谓。”她说。
刘堪无话可说,他在她面前转来转去。
周燕也看着刘堪。这是个不善言表的男人,在他生气或者发怒时,只能转来转去。周燕甚至希望刘堪在她面前这样转下去。
刘堪突然停了下来,他一把将她从椅子上拽起,大声说:“你得为家里人想想。”
周燕挣脱刘堪的手,重新坐到椅子上,说:“我自己会回去。”
刘堪突然扬起手朝周燕脸上扇去,清脆的响声回荡在屋子里。周燕被打懵了,她捂住脸看着刘堪,而刘堪似乎也被自己的举动惊呆了,他睁大眼睛看着周燕。
空气凝滞不动。周燕的亲戚站在一旁呆愣着,不知所措。周燕一动不动地看着刘堪。刘堪在她的这种目光中进退维谷,他甚至希望周燕哭喊或者对他谩骂,但周燕却像石头一样不动,她的眼睛就那么对着刘堪。
第二天周燕跟着刘堪回到德鲁。一路上,她一言不发,而刘堪则向她不停地道歉。一直到德鲁,她都对刘堪的道歉没有回应。
母亲和姐姐周凌霞问她为什么要逃到省城,为什么要将家砸得一塌糊涂,她什么都没有说,只是说她想搬出来住。就这样,她搬到姐姐周凌霞的房子里。
刘堪那重重的一巴掌,落在她的心里。两年后,她离开德鲁中学成为街头有名的鹰时,她还一直记着那一巴掌。那一巴掌一直晃动在她的脑海里。
周燕走在街上没有看到熟悉的面容。蓝色的帽子没有召唤来任何人。这两年里,她在姐姐周凌霞介绍的一家单位当打字员,她在这种沉默的时光中生活。现在,她以两年前鹰的姿态出现在街头上,她坚信她依然能召唤那些听命于她的小伙子。她觉得不对头,没有人注目她头上的蓝色帽子,也没有人向她走来。
走过一家烤西式面点的店铺时,她朝里望了望,玻璃橱柜和橙红色的桌椅有一种明亮、温暖的气息,几个穿白色大褂的人在里面忙乎。周燕走过这个店铺,然后她听到身后的脚步声。她回过头,看到店铺里的那几个穿白色大褂的人站在她身后。
“鹰。”其中一个叫她。
周燕认出这几个人都是两年前跟随她的小伙子,他们面容没有多大变化,但神情却变了,都是那种平庸的满足,当年那种疯狂和不安的成分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几个小伙子将周燕请进他们的店里。小伙子们看着周燕头上蓝色的帽子说,两年前那一拨癫狂在德鲁街头的小伙子们现在大都改弦易辙了,他们有的离开了德鲁,有的平静下来,继续学业或者从事某种营生。“现在又是新的一茬儿。”其中的一个小伙子对周燕说,“他们知道你,但他们有他们的头儿。”
小伙子们说起了两年前的一些事,他们在冬天穿着长统靴,黑色闪亮的靴子在德鲁街头踏出一片铁蹄般的声音,还有闪亮的刀子、血、飞奔跳跃的姿态,还有酒、疯狂的举动、厮杀、啸叫和永远不安分的眼睛。
周燕走出店铺,她将蓝色的帽子捏在手中。她觉得她像一个傻子。
一个被她注目了五年的男人突然离去,留下的空茫只能以两年前的那种疯狂不安加以填充,而且,把陈韦看作刘堪的一半——被她恨的一半的话,她需要以一种疯狂的举动对待他,需要纠集起两年前的小伙子们,让陈韦尝尝皮肉之苦。
现在她觉得这种想法过于幼稚。
5
周燕只能观望风风火火的陈韦。
陈韦骑着摩托车不断出现在周燕和姐姐住的楼下。他有时从楼下上来,敲开门后站着或坐在屋子里的某个地方神情恍惚地对着周凌霞,他的眼中充满了期待,也充满了凄然的哀怜——对自己的哀怜。周凌霞冷漠地对待陈韦,她做自己的事,或者懒散地看电视,或者看一本无关紧要的书。陈韦涨红了脸盯着她,有时说一两句关于他和她之间事的话,但往往得不到周凌霞的回应。周凌霞最多瞥一眼他,然后又旁若无人地做她自己的事。陈韦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他似乎在绞尽脑汁寻找一个突破口,但往往没有结果,最后他只好转身离去。
有时候,陈韦将摩托车停在楼下,在楼下转来转去。他看起来毫无信心而且犹豫不决,最后骑上摩托车又离开了。
周燕看着这一切。如果是在以前,她不会将这些情形放在眼里,那时她更关注的是刘堪,刘堪对周凌霞的一切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即使有些情形她无法看到,她也能通过一些蛛丝马迹推想出那些情形。
现在刘堪走了,她只能把陈韦当作刘堪的另一半加以观望。一段时间后,她观察到了陈韦的一些特性。陈韦的风风火火带在他的每一个动作中,除此之外,他喜怒无常,动辄大吵大嚷,或者沉默得像个呆子。陈韦的一双眼睛陷在眼窝里,那双眼睛有时如电般闪烁,显出他对某一对象的执著,同时又显出他那易于躁动的特性。
有一天,周燕在上班的路上看到陈韦和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吵嚷着。陈韦的摩托车停在当路,那个人的自行车躺在摩托车旁。很明显,摩托车和自行车相撞在一起了。陈韦跟那人越吵越凶时,她看到陈韦眼珠毕露,凶光四溢。一会儿后,他动手揪住了对方的衣领。对方也不依不饶。陈韦更加怒气冲天地挥舞起拳头。拳头落在对方的脸上,鼻血立刻流了出来。暴怒的陈韦仍不停手,直到把对方打跑为止。
周燕看着这一切。血和挥舞的拳头让她有一种冰冷的感觉,同时,她隐隐看到这么一种景象:陈韦不断地挥舞拳头,他的肢体疯狂扭动,周围的一切在他的扭动中纷纷退去,然后,这个疯狂的男人以怪诞的举动结束自己的生命。
6
关于刘堪和姐姐周凌霞的关系,周燕现在在回望中慢慢看到迷雾深处的一些情形——那是无法被淹没的情形。他们两个,在漫长的时光中相互融入、背离和孤独,同时又伴随着绝望和处在幽暗深处的颤抖。
刘堪五年前出现在周凌霞面前时,是一副沉静忧郁的样子。他站在周凌霞宿舍前等待着她。周凌霞在宿舍里透过玻璃窗看到了刘堪,她长时间地看着,然后走出宿舍,沉默地和刘堪朝另外的地方走去。
那个时候,周凌霞已经谈了几个男朋友,她和那几个男朋友相处的时间,最长都不到三个月,他们先后都被周凌霞甩掉了。甩掉最后一个男朋友时,周燕有一天看到她独自坐在宿舍里吸着烟。当时是黄昏时分,屋里光线暗淡,周凌霞背对着窗户,手中的烟一明一灭。她的脸朦胧不清,弥漫着一种诡秘的气息。
在后来的日子里周燕慢慢知道了这么一些情形:刘堪和周凌霞是高中同班同学,他们在快毕业的那一年经过漫长的揣摸、猜测最终确定了关系,但在毕业后他们又分手了。周燕了解到,他们在那时狠狠地吵了一架,是周凌霞首先挑起的。在与刘堪的交往中,她一开始就寻衅吵架——不安分的因素一直潜藏在她的心中,她和刘堪的关系因此一直是怪诞和离奇的,而刘堪一直忍受着。周燕想,刘堪也许一开始就感到了周凌霞身上那种躁动、倔强的力量,这种力量呈现为独特的神情时让刘堪着迷并深陷其中。
这样一个姐姐永远都想将她自己拔离地面。这是难以说清的一种情绪。在慢慢成长的过程中,周燕想周凌霞和她一样背对着一个破碎的家庭,更确切地说,她和姐姐都背对着混乱的失去了根基的生活。也许,姐姐比她感觉得更深。一片空茫之地,她们都从那里走出,然后注视它,并被它驱赶。
有一天,周燕看到姐姐和一个陌生小伙子走在一起。从举止和衣着上能够看出那个小伙子不是德鲁人。周燕不久便知道那个小伙子来自省城,他是周凌霞一个女同学的亲戚,周凌霞是在女同学家认识那个小伙子的。周凌霞不断地和那个小伙子出入,交往得热火朝天。那个时候周燕已经看出姐姐急迫的心情:她想尽快地将小伙子抓到手,然后借这种关系将自己拔离德鲁。一个月后,小伙子走了,从此再无音信。在一段时间的等待中,周凌霞渐渐明白自己只是被那个小伙子耍弄了一番。当周燕问起那个小伙子时,周凌霞说:“那是一堆狗屎。”
永不安分的周凌霞没有就此罢手,周燕一直注视着姐姐,姐姐的目光飘移不定,神态如梦般虚幻。她仍努力想抓住什么,她不断地谈男朋友,又不断地甩掉他们。每一次和男朋友交往后,她都有一种失败的感觉,但她还是不肯罢休。在后来的日子里,她又转移了方向。她在物资公司上班,在工作的过程中,她慢慢弄清了一些抓住钱的门道,于是,她在德鲁街上开了一家商店,并雇了两个人为她经营。她就这样将钱牢牢地抓住。
周燕在那个时候已经能够洞察姐姐的一切,她看着姐姐风风火火地一边上班一边为她的生意操劳。她在不长的时间里,挣了不少钱,然后买了一辆半新的吉普车,驾着那辆吉普车跑来跑去——很多时候,她只是平白无故地驾着它飞驰,飞驰在德鲁郊外的公路上,然后,在很远的地方又折转回来。
许多夜晚,周燕看着周凌霞独自坐在房间里,灯光是幽暗的——这是她独处时一贯的情形。她吸着烟,一动不动,白天风风火火的神情已荡然无存,她就那么坐着,任由时光在黑夜中流失。周燕看着这种情形,她明白姐姐那深幽的心中仍然空空荡荡。有一天,姐姐向人打问起刘堪的下落。别人对她说,刘堪在离德鲁四十公里外的草原上当教师。她迟疑了几天,最终拨响了那个学校的电话。
后来,刘堪出现在周凌霞的宿舍前。周燕想,这是个一往情深的男人。几年来,他一直没有忘掉周凌霞,心中充满了爱,也充满了恨。
草原上阴云弥漫。草原尽头的山峦被浓重的阴云覆压着,雷声在不远处响起。周凌霞驾着她的吉普车在草原的沙路上奔驰。天色向晚,再加上浓重的阴云,整个草原上是一种风雨欲来的沉重感。刘堪所在学校的白色墙壁在灰暗中异常醒目。周凌霞驾着车朝那学校奔去。当她将车开进学校时,大雨倾盆。刘堪听到车声从宿舍里出来,看到从车里钻出的周凌霞。
在宿舍里,周凌霞撩动着她的长发转来转去,然后她说要喝酒。刘堪看着周凌霞,他拿出了酒,然后将火炉生着,屋子里立刻涌起温暖的气息。刘堪又手忙脚乱地弄了一盘肉,他们坐下来,兴奋地喝着酒。
半斤酒喝下去后,周凌霞沉默下来。她点着一支烟走出宿舍。雨已经停止,乌云散去,月亮皎洁如璧。周凌霞长时间地站在院子里。一支烟抽完,她又抽了一支,然后,她返身进入宿舍。刘堪明显地感觉到她先前那兴奋的劲儿已过去。坐在灯光下的周凌霞沉默了片刻后又要喝酒。刘堪一动不动地坐着,他说:“再不能喝了,你已喝多了。”周凌霞看着刘堪,然后自己动手将酒倒入杯子里,她喝了两口后突然将杯中剩下的酒泼向刘堪。酒顺着刘堪的脸往下流着,刘堪一动不动。周凌霞嘿嘿笑着,起身将屋中随手可拿的东西扔向刘堪。刘堪躲着,最后,他抓住了周凌霞的手。周凌霞平静下来,她幽暗的目光对着别处。这一夜,刘堪和周凌霞一直这么坐着,就像两个遗世的孤独者,只有沉默。
刘堪在德鲁参加一个聚会时,周凌霞也在座。刘堪想到周凌霞也参加了这个聚会。他走进酒店包间看到周凌霞坐在一个男人身旁,她的一只手搭在那个男人的肩上。看见刘堪进来,她不动声色,手仍搭在那男人的肩膀上。刘堪坐下来,他没有显出过分的愤怒,只是再次看了周凌霞一眼。而周凌霞身旁的那个男人,他是熟悉的,他曾经是周凌霞的男朋友,后来被周凌霞甩了,现在,他们又是一副亲密的样子。酒气冲天中,周凌霞一直像个豪迈的女侠,她大口喝酒,大声与身旁的男人唱嘶哑的歌。刘堪也喝着酒,但他控制着自己,他有一种被撕裂、被抛在空中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与周凌霞的交往中不断出现。现在他只能忍受。有时,他也想在某个瞬间将周凌霞撕裂和暴打,但这种想法往往又被另一种情绪所淹没。他喝着酒,看着周凌霞的表演。那个男人这个时候也得意忘形地搂着周凌霞,目光还不时地对着刘堪——那是挑衅和胜利者的目光。
聚会结束,周凌霞扶着那个男人的肩膀走出酒店。街上路灯灿烂,但行人稀少。夜已很深了。刘堪站在街边长长出了口气。他看见周凌霞朝那男人脸上狠狠扇了一巴掌,清脆的巴掌声在空荡荡的街上回荡。那个男人手捂住脸愣在那里。周凌霞朝刘堪走来。
“我喝多了。”周凌霞走到刘堪面前说。
刘堪双手插在裤兜里。他现在想给面前的周凌霞一巴掌。
周凌霞拉起刘堪的手,她说:“你想给我一巴掌,我看出了你有这意思。”
刘堪没有抽出自己的手,他抓住周凌霞的胳膊朝前走去。
周燕想,他们是一对恋人,也是一对仇人。在德鲁的许多日子里,他们在房子里默默长坐,两个人抽着烟,有时也喝着酒。那是孤寂的时刻,就像日落后的黄昏,暧昧而幽远。
有一天,周燕走进姐姐的屋子时,看到姐姐和刘堪相互沉默地坐着,他们显然又剧烈地交锋过一次。风暴过后,他们相互融入沉默中。看到周燕进来,刘堪站起来,对周燕笑了笑,然后走出屋子。周燕跟随他走出门。站在门口,她看着刘堪,夕阳橙红色的余晖中,刘堪的背影显得哀伤、无助。周燕长时间地看着。那一刻,这个男人进入她的心中,他再也不能被拔走了。
那一年,她十五岁。之后,她的哥哥周夏在那个县城里被抓。
周燕和姐姐周凌霞住到一起的一年后,她们搬进了一套楼房里。楼房是周凌霞买的。和姐姐住在一起,姐姐并不过多地过问她的事,这个妹妹的所作所为她不十分放在心上。
刘堪后来调回了德鲁,他有更多的时间与周凌霞在一起,但他从来不参与周凌霞的事。周凌霞白天上班或者忙生意,她不断地出入各种场合,与各种各样的男人打情骂俏。晚上,她有时和刘堪在一起,有时独自坐着。独自坐着的时候那种鬼魅般的神情在持续,她对着窗外的黑夜,目光迷离而朦胧。
周燕想,刘堪在相同的时间里也许也独自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他的目光也是迷离和朦胧的。同时,这个男人的忧伤显现在脸上,他的孤独感更加坚硬,在他注视的前方,他和周凌霞在不明的背景下扭动、挣扎、尖叫或者沉落,沉落在他们各自的深渊中。
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周燕想象出刘堪最后一次见到周凌霞的情形。那是一个白天,刘堪破例去找周凌霞,最后他在一个杂乱的家属院中找到了周凌霞,她和一个男人躺在一间房子的床上。刘堪进去时,那个男人吃惊地跳了起来,而周凌霞一动不动地看着刘堪,眼中平静如水。刘堪转身离开后,她点着一支烟。她的目光变得深幽起来。在烟雾中她望着屋顶,她想,这样也好。
这件事之后,周燕首先从姐姐的神情中发现了不对头。那几天,姐姐一直呆在家里,白天和晚上她都坐在窗前,一动不动。周燕从她的神情中猜出她和刘堪发生了什么。她找了个借口去找刘堪,刘堪对她的到来显得有些意外。她坐在刘堪的对面,而刘堪一直神思恍惚。他明显瘦了,一双眼睛灰暗无光。她问起了他和姐姐周凌霞怎么回事。“你姐姐有另外的男人。”刘堪说过后又后悔起来,他显然不愿在任何人面前说起他和周凌霞的事。
周燕想,刘堪并不是仅仅因为姐姐周凌霞和那个男人的事而决然离开德鲁的,那件事只是一个因素。在和周凌霞漫长的交往中,他耗尽了精力,他的爱和痛苦并存,而且他早已看到 这么一种前景:他和周凌霞都在做无望的努力。那件事结束了他的这种努力,同时也结束了周凌霞的努力。
周燕在观望刘堪,她不断地去刘堪那里。刘堪要离开德鲁的意向越来越明确。她就这样看着这个男人——这个男人将要扯断他以往的一切,将要走掉,将要把周凌霞抛在脑后。他也要离开周凌霞的这个妹妹,她对于他来说无足轻重,甚至从来都不在他的视野之内。
7
陈韦是在两年前认识周凌霞的。两年前的一天,陈韦拿着他的小口径猎枪从灌木丛中走向公路边他的摩托车时,看到周凌霞开着吉普车从公路上驶过。吉普车走了不远就停了下来,周凌霞从吉普车中下来,她撩了撩长发,然后掀开引擎盖子看发动机出了啥毛病。周凌霞穿着一件红色的外衣。红色的身影让从灌木丛中走出的陈韦头脑一阵阵发响。在寂无人烟的原野上,出现这么一个姑娘,而且驾着车,这让他心驰神往。他走向周凌霞。在快走到吉普车跟前时,他咳了一声。这一声让正在修车的周凌霞抬起头来,她首先看到陈韦手中的枪,接着看到他肩上垂挂的兔子。周凌霞只是这么看了一眼便又低头修她的车,她明显地对这个男人感到厌恶。车修好了,她上车,然后又看了一眼站在路边的陈韦。陈韦眼睛发直地对着她。她在启动车的时候想这个男人肯定还会来找她。
周燕在刘堪走后的这几天里看着频繁出现的陈韦,向姐姐周凌霞说起了陈韦。周凌霞对于周燕所提起的话题感到奇怪,这个妹妹从来不在她面前说她的事,但自刘堪走后,这个妹妹似乎特别关心起她的事来。她没有过深去想,她对周燕轻描淡写地说了她和陈韦初次相遇的情景。她说,自那次相遇后,陈韦就不断接近她。“我对他没有任何兴趣。”周凌霞说。
“他是那种得不到手就不罢休的男人。”周燕说。
“他的脑子有问题,你没有看出吗?”周凌霞说。
“他脑子的确有问题。”周燕说。
追不到周凌霞,陈韦变得疯癫起来。周燕在观望这个男人的时候想他迟早有一天会出事。周燕从别人嘴里了解到,陈韦在油库工作,星期天他总是骑着摩托车去野外打猎。他打不着猎物的情况下就骑着摩托车在野地里狂奔,他脱掉他上身所有的衣服,赤裸着身子,赤裸的身子在阳光下泛着白光。摩托车最终会陷进一片沼泽,或者在某个塄坎上熄火,那时,他就气急败坏地咒骂沼泽、塄坎或者摩托车。
陈韦的心神不定让油库的经理不满起来。这个姓黄的经理几天来一直对陈韦叨叨个不停。一天中午,姓黄的经理刚叨叨完,陈韦便拿起了他的小口径猎枪,将枪口对准经理的后背,经理还未反应过来时,枪响了,经理扑倒在地。拿着枪的陈韦愣愣地站着,然后他明白他干了什么。他快速离开,他想他只有尽快逃走。在出大门口时,守大门的老汉看着他。守大门的老汉听到枪声,在他疑惑地看着陈韦时,陈韦也给了他一枪。老汉倒下去,但没有死去。过了很长时间,老汉挣扎着爬起来,拨通了公安局的电话。
陈韦向德鲁南面的山林跑去。他提着他的小口径猎枪,没有人注意他。整个晚上他都在山林深处度过。白天来临,他登上山顶朝远处的德鲁城看着,但只能看到那些楼房、水塔和高高的烟囱。到了第三天,由于饥饿他晚上偷偷下了山。他潜入德鲁城里,敲开一个朋友家的门。朋友是单身。陈韦用枪逼住他,让他弄吃的。
警车不断地在德鲁城里窜来窜去。德鲁城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了陈韦杀人的事。警察到处追捕,所有与陈韦相识的人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他们担心逃走的陈韦突然来寻找他们。
周燕听到陈韦的消息后,首先想起鲜红的血。陈韦在空中跳跃、奔逃。血在追赶他。血悬在他的头上,让他眩晕,让他不知所措。这是必然的情形。周燕想到这里感觉到她心中潜藏的一条汩汩流淌的河,它变成了血色的。红光闪耀,而她和那个离开的刘堪行走在这条河中。
两天后,陈韦的那个朋友再也不能提供给他任何吃的,陈韦只好让朋友出去买一些饼子。朋友在街上的一个饼摊前买了一大摞饼子,在付钱的时候,他向饼摊的主人说明了陈韦的下落,并让饼摊主人尽快报告给公安局。
大批的警察立刻包围了那间房子。陈韦明白是朋友出卖了他,但他再也不愿杀人,他放走了朋友,然后拿着枪对着窗外的警察。警察的喊话声不断。他顽固地与警察对峙。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将近天黑时,他朝外放了一枪。警察的枪声大作,但没有击中他。他从容地将枪口对准自己的下颏。枪响了,他死了。
包围陈韦的过程中,许多人在远处观望。之后,那种场面不断被人描绘。在陈韦被围的时候,周燕坐在自己的屋子里,她听到了枪声。她想,那个男人的生命终于结束。接着,空茫感来临。焦虑和颤抖从心中泛起。周燕注视着墙上的血之手,现在,那双手成了呼喊之手,它们扬向空中,扬向幽暗的深处。
8
陈韦死后,没有人将他的死与周凌霞联系起来。在人们看来,陈韦的死是他的性格所致。在陈韦死后的第三天,周燕看到姐姐眼眶发黑,头发凌乱不堪。长时间的睡眠不足使她看起来邋遢又慵懒。她趿着拖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尽管如此,她还是在晚上对着窗户长坐。她手中的烟被点燃,隔好长时间她才吸一口。她就那样举着烟,烟灰燃了一大截后自行跌落。
周燕明白,周凌霞的这种状态并不是因为陈韦的死,陈韦不在她的心中。她是因为刘堪,也因为她自己。刘堪走后的几天里,她除了在晚上长时间静坐外还能在白天干她的事,还能喝酒、交际,打扮得光艳四射。但现在,刘堪走后的空茫慢慢显示出来,她再也无力支撑起她虚假的形象。她的一半、她的对手和可以占据她心灵的人走了,她因此将自己完全显露出来。在夜晚她像一个鬼魅,在白天也是如此。
周燕看到了这些,但她不愿和姐姐说什么。她们是姐妹,但她们都知道,她们难以交流,她们不谈她们的父母亲,不谈死去的周夏,也不谈那个脑满肠肥的继父,也很少谈刘堪。
一个星期后,周凌霞又焕发了精神。周燕看着她在穿衣镜前打扮她自己,看她涂抹口红,看她将黑色的长发整理得飘逸飞扬。她又走出家门,开着她的吉普车上班或者打理她的生意。
周燕还注意到姐姐又恢复了交际,她又喝起酒,而且每晚回来的时间越来越晚。她散发着浓浓的酒气,进门后倒头便睡。她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长时间坐在窗前注视窗外的黑夜了。
一个男人被周凌霞带进她自己的生活中。周燕知道这个叫李孟的男人,他在机关工作,相貌平平,而且不善言语。周燕还知道这个男人和姐姐是中学同班同学,是那个班最不起眼的男生。
周凌霞带着这个男人不断走进家中,而他每一次到来后都显得拘谨而小心。他看周凌霞的眼色行事,并主动找一些活干。周燕看着这个男人,对姐姐不可思议起来。
一个晚上,周凌霞对周燕说:“我要结婚了。”
“跟谁?跟那个叫李孟的人?”周燕问。
周凌霞点点头。
周燕没有说什么。
“不对劲吗?”周凌霞说。
“不对劲。”周燕说。
“我想过一种平淡的日子。”周凌霞坐下来认真地对周燕说,她还从来没有对周燕这么认真过。
“你这样救不了你自己。”周燕说。
周凌霞看着周燕,她没有想到这个妹妹会如此说。她站起来,走进自己的房间,然后关上门。
周燕在这个夜晚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遥望远去的刘堪。这是静谧的时刻,刘堪的样子在她头脑中清晰起来。他是一个被绝望拽走的人,他和周凌霞共同走入一片荒凉之地,然后,那片心灵挣扎、扭动、绝望过的荒凉之地,只剩下他们无力的影子,他们再也无法沟通,再也无法携起手来。
现在,周燕想象自己就站在那片荒凉之地上,她需要这种境地。她想,她其实从很早开始就站在一片荒凉之地上,所有多变的世事都在她身旁纷纷而过,她由此从很早就坚硬起来——从十五岁或者更早,一个身体单薄的丫头就这么走过世事的烟云站在这片荒凉之地上颤抖、思念。鲜红的血是她头脑中固定不去的一种情结,在这种情结中,血色展现着它的美丽和眩目的色彩,而这也是孤寂的时刻,也是需要爱的时刻,爱和鲜红的血色交融在一起,它们生成梦想——幽暗的梦想。她梦想和刘堪那样一个人共同扭在一起,在荒凉之地,在孤寂的时刻,在血与爱的交织中向下跌落,跌落在黑暗中。那个过程将成为永恒。
周燕现在无法想象出刘堪在何处,但她能想象出刘堪走路、喘息的样子。他依然孤独,他的忧郁、他的绝望的眼睛,她都能想象得出。周燕甚至想象刘堪在异地的某个大街上向前走动,城市的喧闹声响在他的耳畔,他的目光漫漶着散淡的情绪。
这样一个男人是否会重新回到德鲁,周燕不得而知。她知道自己不会主动去寻找刘堪。远去的刘堪让她想起天空中的一些鸽子。白色的鸽子在蓝色高远的天空中飞过,白色的翅翼闪耀着银色的光芒,一晃而过,天空又恢复了宁静。然后,它们又从遥远的地方飞旋而至。
婚礼在平静中进行。这是个小型的婚礼,简单、平淡。参加的人数有限,主要是李孟的家人和他几个亲近的亲戚。周凌霞这一方只有周燕和母亲参加。继父没有来,他仍惧怕周燕,便借口出差了。周燕明白,他不仅仅惧怕她当年手中的斧头,他还惧怕他当年在德鲁街头莫名其妙挨过的几次揍,那些情形也只有周燕清楚。当然她的继父后来也明白了那是著名的鹰指使别人所为。
母亲的头发染成黑色,她在婚宴上尽量作出笑容,但她的悲戚时时流露出来。两个女儿就像从她手中挣脱的两只鸟,她们飞走了,很少眷顾她,只是有时给她一些钱,以此来显示她们的存在。她处在尴尬之地,一面是李胖子,一面是两个女儿。时间长了,这种尴尬麻木起来,她只能遥望两个女儿。
婚礼平淡地进行。周燕坐在母亲身旁。母亲抓住她的手,她没有拒绝。这是一种陈旧的亲情,对她来说已经没有意义。周燕不时地看着姐姐,她和李孟一起向在座的亲人敬酒,她微笑着,遮掩内心深处的无奈与平庸感。
婚宴结束后,周凌霞和李孟被一辆黑色的小轿车送走,周燕陪着母亲在街上走了一段,然后在一个十字路口,她们分手。周燕看着母亲的背影,那是一个日渐苍老的背影,忍受背离之苦,在挂念和回望中孤独下去。周燕想,她们家现在活着的人都是如此,彼此孤独,而在遥远的那个小县城里,父亲的孤独又加上了对死去儿子的守望。
现在,姐姐的房子里只剩下了周燕。结婚后,周凌霞虽搬到了李孟的新房里,但她所有的东西都留着,所有的东西都原样不动。周燕看着这些东西,她明白,它们表明它们的主人离去得并不坚决,那场婚礼并不能将周凌霞牢牢地拴在某个地方,飘摇感在暗处浮动。周燕想,姐姐以与李孟的结婚来结束她过去的状态,但她结束不了。
9
周燕观望婚后的姐姐。两个月过去,周凌霞和李孟平淡地过日子。初冬的第一场大雪突然降临,十月的德鲁城包裹在厚厚的白雪中。白雪消尽时,高原的寒冷日渐加重。周燕时常坐在窗前,遥望北面皑皑的阿尼太告山,它在晴朗的天空下峥嵘而巍峨。周燕想,刘堪就是在那个方向消失的。高峻的阿尼太告山永远遮挡了北面的一切——天空和大地都被它遮挡了。
隆冬时分,周燕得知周凌霞不断和李孟吵闹。吵闹的发起者和主角当然是周凌霞,她时常无端向李孟发难。不善言语的李孟只能被动地接受,更多的时候,他像哑巴一样一言不发,但这没有用,周凌霞依然无故吵闹不止。她披散着头发,像泼妇一样骂个不停。李孟忍受了一段时间后,从家里逃走。他住在别处,三四天后又回去,又接受周凌霞的无端辱骂。李孟再次逃走。
一个月后,周凌霞回到她原来的房子里。她坐在窗前长时间沉默着。她的神情依然是她以前的那种神情,手中举着烟,目光迷离而黯淡。
晚上,周凌霞对周燕说,她准备离婚。周燕没有说什么,这种结局,她已料想到。
离婚手续很快办了下来。周凌霞又搬回到了她原来的地方,和妹妹周燕又生活在了一起。
她的容颜也在慢慢变化,她依然有着质感的美丽,但更多地掺杂了阴鸷的成分。她的一双眼睛更加深幽,她的神态充满了神经质。她彻夜长坐,就像以前那样。白天她慵懒地躺在床上。她的那个店铺已经盘给了别人,而她所在的单位也处于困境。她再也没有勃勃雄心了,再也不会出入于觥筹交错的聚会了。对于男人,她再也不愿提起。
姐姐走向了她深渊的深处,而周燕只能以一个旁观者看待这一切。对于姐姐,她什么也干不了,况且她也不想对这个姐姐干什么。
又一场大雪来临,窗外白茫茫一片。周凌霞站在窗前,她长时间看着窗外飘飞的雪花,然后转过身来看着周燕。
周燕迎着周凌霞的目光。
“你二十一岁了。”周凌霞说。
周燕看着周凌霞,没有说什么。
“你脑子里一直装着一些怪里怪气的东西。”周凌霞又说,“像你这样的年龄,是不是有些太早?”
周燕无言以对。
“你对我怎么看,是不是已经不可救药了?”
“我没有想过。”周燕说。
“我知道你脑子里怎么转。”周凌霞说,“我知道你一直想着一个人。”
“什么?”周燕说。
“你一直想着刘堪。”周凌霞说,“你对他好像早就不对劲了。”
周燕看着周凌霞,然后点了点头。
“我应该早就看出来,”周凌霞说,“他是一口深井,跳下去就再也上不来了。”
“你对他来说也是一样的。”周燕说。
周凌霞看着周燕,“看起来你比我还清楚。”
“我一直看着你们。”周燕说。
“你已经陷进去了。”周凌霞说。
“我知道。”周燕说。
周凌霞看着周燕然后转向窗外,她说:“你没有错。”
周燕没有说什么。她对周凌霞已无话可说。
“雪越下越大了。”周凌霞说着转过身显得疲倦地坐到沙发上。
这时,周燕从周凌霞的脸上看到了一种不易觉察的阴郁之光。它稍纵即逝。
周凌霞在一个上午死去。她跳楼而死。周燕从单位赶回来时看到很多人围在楼下。警车的红灯在闪烁。她拨开人群看到姐姐躺在雪地里,她的脸是苍白的,但死去的神情安详而自然。
在姐姐死去的这个夜晚,周燕枯坐在窗前。窗外夜晚中的灯光扑朔迷离,各种声音汇集成河流,它们在空中轰轰回响。慢慢地,这些声音随着夜深而沉寂下来。周燕想,死亡就像翩然而至的一只鸟,它的到来即使有预兆也来得过于轻盈了。面对这种死亡,没有泪水,也没有哀痛,只有空茫感不断涌来。在这种空茫感中,她升腾、飘飞,就像一根羽毛,没有重量。
葬礼在第二天进行。简单的葬礼,但来的人还是不少。许多人都是周凌霞生前的好友,他们诚心而来,唏嘘或者哀叹。葬礼将要结束时,周燕站在稍远的地方,她看着那高耸的烟囱,它刺向天空。一会儿后,灰色的烟从那里冒出,一个死去生命化成烟的形态,飘散在空中。周燕想,她现在安宁了,再也不会在她自己的世界里左突右冲了,再也不会扭动和呼喊了,幽暗对于她来说已经过去。
葬礼结束后的晚上,周燕打开一瓶酒,她要好好独自喝一番。她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沾过酒了。现在,她想她得好好喝一番。第一杯酒泼洒在地上——为了姐姐的亡灵。接着,她喝了起来。酒使她真实起来,她想,她得好好琢磨一下不断到来的灾难来自何方,是怎样的手搅动着不宁和躁动。她这样想着感到二十一岁的她走过的路已经太多。
十几杯酒喝下后,她的眼泪终于流出,这是一个奇迹,已经有很长时间眼泪没有流出过了,现在,它们终于汩汩流淌。
10
刘堪得知周凌霞死去的消息是在两个月后的一天。那天有个从德鲁来的同学在省城找他,他和那个同学坐在酒吧里时说到了周凌霞。那个同学说她死了时,刘堪举着手中的酒杯一动不动,一种久远的苦涩和悲伤在这一瞬间迤逦而来,然后他被完全淹没。他慢慢地喝下杯中的酒,他感觉到周凌霞一双深幽的眼睛在扯动他、注视他。深幽之处的混沌无边无际——一种荒芜苍凉的境地中,撕扯和颤动、呼叫与呻吟无所不在,这是久埋在心中的情形,它们并没有因为他离开德鲁而远去。刘堪努力将思绪转向别处。他和那个同学谈德鲁的事,谈德鲁以外的草原,谈酒,最后他们又不得不谈到周凌霞。那个同学说了周凌霞和李孟结婚的事。刘堪说,他已听说了。他还听说了她很快离婚的事,离婚后,她又住回了她原来的房子。那个同学最后说:“她把自己毁了。”
刘堪没有说什么。他不断端起酒杯。他的同学已经有了醉意。他结了账,和那个同学走出酒吧。冬夜的风干巴巴地吹着。刘堪送走同学,然后独自朝自己的住处走去。
周凌霞走向死亡的过程——一跃而下的身姿让刘堪长久回味,那种身姿超越了绝望和无路可走的愤怒,它轻飘的性质具有诗意的飞翔感,而这种飞翔在刘堪的脑子里被无限放大,他的整个世界因此而变得轻而又轻。沉重已经远去,任何负载沉重叹息的企图变得毫无意义。刘堪迎风走着,他觉得他离开德鲁在省城这样一个地方飘荡并没有真正脱离开德鲁,他的命之所在并不在逃离这一过程中。走向自己的幽暗深处,不断地扭动和下沉,这就是自己,而周凌霞从楼上一跃而下的姿态成为他这种状态的一种对照。
刘堪想,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周凌霞死亡的同谋者和参与者,而另一个同谋者与参与者,也只能是周凌霞,这种趋向死亡的责任只有他们两个共同承担。
另一个一直被忽视的人是个旁观者,那就是周燕。那个丫头对一切都心知肚明。那个不断逃学、聚众打架、手持斧头、性格怪诞、沉默而以血为画的丫头,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她的一双眼睛像冰层下泛出的光,它们要刺入的地方更深、更荒芜。刘堪想到周燕的同时想到了她给他的那件被剪碎的衣服,那个丫头的心是被冰包裹着的火山,冰冷而有力。
刘堪回到德鲁。在德鲁西山下的坟地里,他站在周凌霞的墓前。两个月了,漫漫冬日里的坟茔已经荒凉不堪。黑色的乌鸦在远处成群盘桓,开阔的坟地中寂静而阴森。刘堪长时间站着,他想他就这样向周凌霞做最后的道别。只有道别,除此之外,他再无话可说。
之后,他去找周燕。
夜幕降临时他走上楼梯,敲响了门。门开了,周燕出现在门口。对于刘堪的到来,她没有感到意外,她让刘堪进去。
客厅里的灯光是昏暗的。刘堪脱掉风衣坐下来。他说:“我是前几天才知道你姐姐的事的。”
“这对她来说已经无所谓了。”周燕说。
刘堪目光转向别处,对于来见周燕,他在路上已经想到了必然会出现艰难的情形。现在,这种艰难的情形刚刚开始。
“我不想跟你说她的事。”刘堪说,“我来是想见见你。”
“这我倒没有想到。”周燕说。
“我迟早都得来见你,不管发生了啥事,我都得来见你。”刘堪说。
“是那件衣服让你来的。”周燕说。
刘堪闭着嘴,他没有想到周燕会这么白刃相见。
“你的那件衣服被我剪碎了,就那么回事。”周燕说。
“这倒是个好话题。”刘堪说,“我那件衣服值二百多块钱。”
“我可以给你赔。”周燕说。
“我倒想看看你怎么给我赔。”
“你用不着纠缠在那件衣服上。”
“是你纠缠那件衣服的。”刘堪说。
周燕冷笑了一下。她坐在刘堪的对面,目光对着刘堪。
刘堪沉默着,他想他下一步该说些什么。他说:“也许你姐姐一直恨我,还有你,也一直恨我。”
“我没有理由恨你。”周燕说。
“你有千万条理由来恨我。”刘堪说,“其实我什么都不是。”
“你是不是什么对我无所谓。”周燕说。
“的确。”刘堪说。
“你像小丑一样跑掉了。”
“的确。”刘堪说,“像个小丑。”
“听说陈韦的事了吗?”
“听说了。”刘堪说。
“他死的时候还像个样子。”
刘堪觉得自己再无力说什么。他站起来,在屋里转动着。然后,他站在那幅画前。片刻之后,他又将目光转向别处。那双血之手此刻变得锐利而强硬,他在它面前不得不退缩。他重新坐下来。他想,那被剪碎的衣服也许表明了一种结束的意象。周燕用剪子关闭了她的晦涩之门。
这时,周燕打开录放机,曼妙的音乐响起来。这让刘堪感到意外。
“听听音乐吧。”周燕说,“你是不是想走?”
刘堪的确想起身离去,但音乐迫使他不得不留下来。
“想不想跳舞?”周燕说。
刘堪看着周燕,他愣了片刻,然后,他站起来握住周燕的手。他和周燕跳了起来。这是谜一般的时刻,他机械地转动着,不知道面前的这个姑娘的脑子里想着什么。
音乐结束时,刘堪犹豫了一下,之后他说:“我该走了。”
“走吧。”周燕看着刘堪。
刘堪拿起风衣的时候,感觉到腿部被锐利的刀子扎进。他慢慢弯下身子,扭过头,看到周燕一双闪光的眼睛。他低头看到扎进自己腿上的刀子。他拔出刀子,坐在地上。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看到自己的血慢慢流出。
周燕像鬼魅一样站着。刘堪挣扎着要寻找止血的东西时,周燕仿佛从梦中醒来般从容,她找来了绷带,她擦拭着流出的鲜血。用绷带扎住伤口时,她的一双手沾满了血。血色之手在昏暗的灯光下飞舞。
周燕拨响了医院急救电话。
11
刘堪躺在病床上。早晨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整个病房有种温暖的气息。大夫昨天晚上已经处理了伤口。大夫说,伤口够深的了,但没有大碍。刘堪朝窗外望去,冬日的天空有种灰茫感,远处平缓起伏的山头泛着宁静的黄色。他微微将身子向上耸起,看到坐在床边的周燕。昨天晚上她就这样一直坐在他的身边。她默不作声。他的伤口被处理完后,她又恢复了她那惯常的样子。整个晚上,刘堪好几次催她回去,但她固执地留了下来。黑夜渐深,他们无话可说。刘堪沉沉睡去。现在,早晨的阳光将他们的形态重新显现。刘堪又动了动身子。周燕抬起头来,看着他。接着,她站起来,将床头柜上的一份早餐端给他。刘堪感到意外,他想他睡的时间够长了,连周燕什么时候弄来早餐都毫不知晓。他接过周燕手里的早餐,慢慢吃了起来。
“你该去上班了。”刘堪吃完早餐对周燕说。
“今天是星期天。”周燕说。
“你回家再好好睡一觉,我这里其实没啥要看护的。”
“我已经睡好了。”周燕说。
刘堪再无话可说。
大夫和护士推门进来,他们检查了伤口,换了药,又都出去了。整个病房里只有刘堪和周燕。
这是沉静的时刻。刘堪感觉到他在虚茫的飘浮中被一种悠远的、弥散在深处的气息抓住,一些曾经灼伤磨砺过他的情形显出了它们的棱角——划破长空的吼叫,无助而飞扬起的手臂,幽暗深处的炯炯目光。他一动不动地坐着,他想在一切都灰飞烟灭之后,只剩下了他和面前的这个姑娘。这个姑娘现在让他流出血来,鲜红的血将他和她融在一起。
“今天的天气不错。”刘堪对周燕说。
周燕将目光转向窗外,她说:“的确不错。”
“我一直想你的那幅画。”刘堪说。
周燕看着刘堪。
“那是用你自己的血拓上去的,我早就看出了。”刘堪说。
“现在你也流出了血。”周燕说。
“这挺好。”刘堪说,“昨天晚上我没有想到你会给我那么一下,其实我应当早想到。”
“我像一个凶手。”周燕说。
“这挺好。”刘堪说。
周燕没有说什么。她又转向窗外。几只白色的鸽子在窗外的天空飞过,它们的姿态轻盈而飘逸。周燕感觉到自己的手被刘堪握住。她慢慢转向刘堪,然后,她伸出另一只手抓住刘堪的肩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