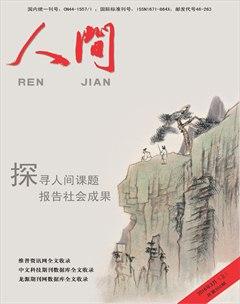慈悲的召唤
周越强
摘要:废名是现代文学当中深受佛教禅宗思想影响的知名作家之一,吴福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三十年》当中评价废名于乱世之中执拗地采取童心视角。“执拗”这个用词深值得玩味,以废名在小说中抛开乱世纷扰、家国忧憾而我行我素地描绘一方天真无污的童心观照下的心灵净土而言,他的确是执拗的。但是如果考虑到废名的禅宗信仰,便不能简单认为废名的这种选择是“执拗”。“执拗”这个词更接近偏执的意思,它使人感到类似天津麻花的扭拧,抛开这个词所传达的评论家对废名显而易见的褒赞情绪——这种情绪深深影响着读者对废名的认知,从而体现了评论家的喜恶对于作家、作品成长的巨大意义。
关键词:废名世界;佛禅;意蕴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00-02
废名是现代文学当中深受佛教禅宗思想影响的知名作家之一,吴福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三十年》当中评价废名于乱世之中执拗地采取童心视角。“执拗”这个用词深值得玩味,以废名在小说中抛开乱世纷扰、家国忧憾而我行我素地描绘一方天真无污的童心观照下的心灵净土而言,他的确是执拗的。但是如果考虑到废名的禅宗信仰,便不能简单认为废名的这种选择是“执拗”。“执拗”这个词更接近偏执的意思,它使人感到类似天津麻花的扭拧,抛开这个词所传达的评论家对废名显而易见的褒赞情绪——这种情绪深深影响着读者对废名的认知,从而体现了评论家的喜恶对于作家、作品成长的巨大意义。从情绪上,笔者是认同“执拗”的,然而这个词却从对于创作者的心灵轨迹的探索中机巧地掩盖了其他可能。即从废名信仰禅宗的角度看,我们既可以认为作家的“化外牧歌世界”的题材是对现实世界人性恶的有意规避,也可以认为作家的选择是从本身充溢着人性善与恶的现实世界当中选择真正符合心意的题材,这是被“执拗”不小心掩盖了的可能。就像希冀顿悟者所期待的纤巧机缘那样,有着相同结果的“有意规避”和“主动选择”之间的差别细若游丝,不易把握。但需要甄别的是,佛教并不是教人去憎恶“恶”,而是教人去融入“善”。
一、题材选择:佛禅思想浸润下的废名世界
每个人看待世界的视角都是个人的,大脑对于世界的理解也是独立的。从条件上讲,观测世界的眼睛的好坏、近视还是远视、对色彩的辨别能力、听力的敏锐程度、不同的喜好、不同的心情、不同的口味、不同的教育程度、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风俗等等,都绝对影响我们对世界的认知。金刚经有云“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恒河,是诸恒河所有沙数,佛世界如是。”“佛观一滴水,八万四千虫。”这八万四千虫便是八万四千个世界。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每个人生活的世界都有独立的一面。当然,当理解在改变的时候,“世界”这个词的概念也在置换,在生活范围概念上打上精神标签。每个人的不同的生活范围、生活状态、不同思想、不同观点等都成为异他世界的独特标志。“世界”的概念并非第一次被改变,“世界”从来不是一个:按不同地域分,有西方世界、东方世界等;按国家发展程度划分,有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划分;按不同语种划分,一种语言属于一种世界;此外还有文学世界、美食世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是基于人类共同目标和理想提出的,旨在打破不同世界之间隔阂与封闭状态的口号。
不同世界与世界之间有很多的共同点,这是他们相互靠拢和接近的基础。这里所关注的则是世界与世界之间的不同之处。唐弢在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对废名提出了较为尖锐的批评,认为废名“忽视作品的思想作用,而以表现朦胧的意趣为满足”。这是一个世界对另一个世界的评判的声音。文学批评是一个主观认识加诸主观的过程,文学批评需要一个标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其他,失去标准,批评就失去意义。批评的意义在于引导文学,有限的精力决定了人类不能在“八万四千”中文学中徜徉,批评则把文学创作的题材、文体、文字、形式、思想等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以此集中了人类的力量,同时限定了更多的可能。唐弢对废名的批评在现在看来是一种政治偏见,废名正是因为这些“缺点”而有了自己的独特价值。
废名的题材选择体现的是佛教世界观下看世界与其他世界观主导下看世界的角度差异,对观测到的同一事物的不读解读,甚至是所看到的内容的根本不同。相比于“不同世界”的想法,认为两个人所看到的内容根本不同的想法更容易陷入偏执。后者的想法认为两个人在关照同一种事物时,他们看到的相同点是很少的,比如两个人同时在看一条晒在绳子上的被子时,他们同时嗅到太阳光杀死螨虫,棉花膨胀起来的味道,同时看到了棉被上喇叭花的细小纹理,看到绳子一头拴在一颗树上,另一头系在一颗半嵌进砖墙里的钉子上,感到暖洋洋的风吹过时,被子的细微摇动。他们同看到了很多,但是相比于他们没有同时看到的,这只是一小部分而已:他们其中一个人看被子时,看见小孩子尿床被洗过的不太明显的痕迹,当他专注于确认这一痕迹时,另一个人抬高的目光看到一只燕子斜身飞入屋檐下的巢里;第一个人看见一条小孩子的被褥,第二个人看见一条被子;第一个人看见一条青虫顺着口中吐得细丝落到绳子上,开始顺着绳子爬,第二个人看见被子下面的土地上有小孩挖的玩玻璃球游戏用的小坑……这是两个人再看同一条搭在绳子上的被子,如果是两各不同生活状态中的人,他们观测的同一时代的东西差别更大。不同专业、不同岗位、不同学历……各种不同带来的结果就是认识的不同,医生不会在割开病人肚子后问接下来怎么办,我们不会强求毛主席射箭能百步穿杨。废名小说的题材选择跟他的生活经历分不开,一来他会写他看到的,二来他也只能这么写,从这个角度看,“执拗”一说便不妥当。
废名小说当中的禅意是他学习禅宗思想的结果。把废名的小说比喻成一串佛珠的话,珠子是废名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禅宗思想则是串起珠子的线。废名出生在黄梅,这个地方是中国禅宗的圣地,有着四祖寺,五祖寺,《坛经》记载六祖慧能也是在黄梅接受衣钵,旋即南下。废名在这样一个地方生活了整整17年,待到进入北大求学时,受到正在撰写中国禅宗史的胡适和追求冲淡平和的佛道一路的周作人的影响,其创作之初,作品中便开始氤氲着浓浓的禅意。正如《坛经》中神秀和惠能所做的的偈言诗属于两个境界一样,有论者认为废名的禅宗思想发展也经历了从“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两个境界。废名看世界是带着佛的眼睛的,他理解万事万物都以佛为导师。对于世俗中随波而流的众人而言自然属于别一世界,对于秉持着世俗眼光的评论家自然属于别一世界。而被周作人等人引为同流,他们是精神世界里的邻居。
二、童心背后:“人生是苦”的宗教印证
废名的小说多描写古老的乡村民俗与淳朴的人性编织的化外牧歌世界,体现对淡泊适意的造化之境的向往与独钟;而废名的诗歌多诉说的是寂寞、隔膜、人生是苦的感受,这种消极情绪无不关联着宗教信仰中的那个“空”字。同时,当我们反过来寻找,就会在废名小说作品的段落间隙里发现人生的苦难。佛教认为人生来充满各种各样的苦难,各种各样的烦恼,甚至一个生命的存在就是痛苦,认为痛苦的延续、烦恼无尽的纠缠就叫生命。佛教弘法的目的就在于“十方所有诸众生,愿离忧患常安乐”。废名诗歌和小说当中的人生的寂寞、隔膜、贫苦生活等莫不是对佛教“人生是苦”理念的自觉印证。
废名的诗歌《街头》可谓是寂寞透顶:“行到街头乃有汽车驶过/乃有邮筒寂寞/邮筒PO/乃记不起汽车的号码X/乃有阿拉伯数字寂寞/汽车寂寞/大街寂寞/人类寂寞”这首小诗短短8行51个字,却直接用了5个“寂寞”。邮筒寂寞、阿拉伯数字寂寞、汽车寂寞、大街寂寞、人类寂寞,随着眼神的游走,看到的一切都披着寂寞的外衣。其实是诗人戴着寂寞的眼镜,真正感到寂寞的是诗人自己。这种与外界隔膜的感受,当独自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极容易感觉到。然而诗人却有才能将整个道路天空染成灰色来渲染寂寞,说眼睛所看到的一切外在事物都寂寞,却唯独不说自己寂寞。
而废名的一些深受顿悟思想影响的记录瞬间感悟的小短诗,更给人以直接的震撼感受,如“猛然听得从街上传来的声音,——好像我父亲喊我小名的声音,却再也没听见什么了!”是一首思念父亲的诗,引发深思的仅仅是街上偶然传来的一声听着像我父亲的声音的声音。这首诗使人一下子回想起多少次街上传来的偶然的声音,回想起多少个午后或清早父亲叫自己的名字,这首诗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感人泪下的力量;又如“我时常记起那天在市场上遇着的那赤脚的女孩子/举起盛着叫卖的西瓜的篮子/走向玩具店问一多纸花的价值”这首诗描写一个没有鞋穿的女孩子,卖西瓜的农村小女孩,一个可怜的小女孩,但是确是和所有小女孩一样的爱着美丽的小女孩,问一朵纸花的价格。这小女孩并不为自己的贫穷感到什么,但诗人却为她辛酸了。
类似的困苦生活也展现小说《竹林的故事·柚子》当中家道衰落的姨妈一家生活拮据,姨妈因为操劳,颧骨高立,形容消瘦苍老,同自己一块长大的柚子妹妹因为公婆早逝,丈夫尚未立足,在娘家替人家缝补衣服赚钱养家;又如《桃园·桃园》当中阿毛自小见惯父母吵架,幼年死去了母亲,小说一开始便讲到阿毛的爸爸王老大一晌以种桃为业,卖桃是家庭的主要收入,生活贫苦。小说中有一段震撼人心的描写,“王老大就闭了眼睛去睡。但还要一句——‘要吃什么东西明天我上街去买。‘桃子好吃。阿毛并不是说给爸爸听,但这是一声霹雳,爸爸的眼睛简直呆住了,突然一张,上视屋顶。如果不是夜里,夜里睡在床上,阿毛要害怕她说了一句什么叫爸爸这样!”病中的阿毛什么也不想,就想到了桃子好吃,这简单的四个字的回答凸显桃子在阿毛幼小心灵中的地位,同时更加令人心酸不已的原因是这个桃园里生长的小女孩没有吃过其他水果,只知道桃子的味道好吃,生活的艰难、人生的困苦在这里显露无遗。即使在《桥》中处处和谐的史家庄,史家奶奶和三哑叔何尝没有生活的苦恼。
作者利用小孩子的眼光和语气表述充满苦难的生活,因为小孩的头脑还不懂的苦难,但读者能从文字背后读出这些苦难来。这里透露出作家作为一个佛教徒的慈悲为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