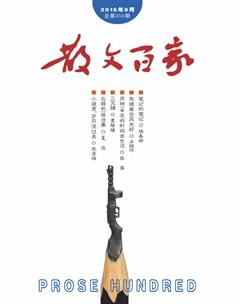我在姥姥家门前流浪
姚凤霄
我茫然地站在姥姥家门前。四下望,沿街墙面涂了涂料,很像日本女人涂了厚脂粉的白脸亮眼张扬,街上看不到一个人。这是城市的某个小区?不,这是地道的乡下村子,村里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孩子们也到城里上学了,留在村子里的人少,寂静得很。
原先一进村子,老房花树,草垛和泥土随处可见,鸡狗鹅鸭自在玩耍,刨土觅食的温馨诗意感扑面而来,村里大人孩子见面就打招呼,一街一路洋溢着满满亲情,现在全不见了,一种陌生感隔膜感兀自生出来,像时下的雾霾一样遮蔽我、淹没我,我感觉自己在无边的空旷里流浪,无着无落。
你是谁?我是我。叫啥名?狗来问。
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本小画书,小画书的书名是什么,我一点印象也没有。我和一个小伙伴头碰头地一起看小画书,笑作一团。后面的内容小伙伴不让看了,我只记住两个画面,我猜想了大半生,曾设计了无数个故事的结尾。我也不知道小画书里故事的结尾是什么样子,是比我想的好,还是比我想的差。
第一个画面:一个强人胸前衣服上有一个圆圈,里面写一个大大的“兵”字,他握着一杆铁头尖枪,从树林里冲到一片豆子地里,嘴里喊着,“杀,杀,杀……快出来,我看到你了……”
第二个画面:豆子地里凛然站起衣衫褴褛的农夫。强人问:你是谁?农夫答:我是我。强人问:叫啥名?农夫答:狗来问。
想到这里,我就忍不住笑,这个笑,跟随我好多年了。这个对话,我也一直忘不了。强人拿着武器杀气腾腾,农夫一点都不害怕,还幽默一把:名字叫狗来问,谁问谁是狗。
野地里的生长,让所有的气势汹汹和一本正经归于一笑,归于恒久的禅意。你是谁?我是我。一个人成为“我”不容易,这个“我”是一种自知自省。强人虽然手里有枪,但他并不自知,只是一个茫然的蛮人。农夫知道这个“我”,有一股从田地里生长出来的底气,不被谁怕,也不怕谁,在天地之间活得自知自由。
人到中年,我由一个懵懂之人,逐渐明白人生的来路和去路,一路走来,梳理出一些关于物质与精神的因果关联。你是谁?我是我。当今社会,一个人勇敢地做“我”并不易,我们常常做不成“我”,以不同的社会角色、不同的面目脸色,出现在人群之中、天地之间。
我站在姥姥家门口,门前一片空地上种了豆子,豆子快熟了,豆子的香气四处弥漫。前些年,退休后回老家的舅舅身体还好,门前花红柳绿、瓜菜飘香,我喜欢得不得了。近来,舅舅老迈行动迟缓了,也遗传了姥爷的眼睛不好,无法打理小园子了。舅舅说,今年春天他让邻居种了豆子。时光让人慨叹,衰老让人猝不及防。
舅舅家有两处房子。舅舅没住新房子,住在老房子里。老房子土木结构,冬暖夏凉,有土炕和大锅灶,做饭吃,比小锅灶香。老房子是八十多年前的老宅了。老宅子是姥爷亲手盖的,屋架木梁坚固得很,墙壁很厚。姥爷是一个能工巧匠,居家过日子,一旦有什么难事,找姥爷就对了。
姥爷一生都是个头脑清醒的乡下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都在搞政治喊口号,姥爷带着八岁的妈妈到海滩上开荒种豆子。妈妈说,那时,茫茫渤海海滩一片盐碱地,远远地看,天和地是连在一起的,望也望不见边。大海滩上不见人烟,没有一棵树,只长芦草和碱蓬。风刮得呜呜叫,青青的芦草看上去有些发白,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总也长不高。海风的咸湿,让芦草活得很艰难。盐碱地硬硬的,种豆子太难了,但这最难的事,姥爷去做了。开荒时,姥爷被太阳晒坏了眼睛,得了“雀蛊”病,天一黑,姥爷就啥也看不见,吃了草药,才慢慢好起来。
春天,姥爷带着妈妈选择草密的地方除了草、种豆,秋天,太阳晒熟了豆子,姥爷便开始收获。虽然豆子产量不高,但足以让一家人惊喜不已。妈妈说,那一年他们收获了一大缸豆子,晒干后藏在草垛里。为什么要藏起来呢?那时是吃食堂大锅饭的年代,不允许自己做饭,锅都被收走大炼钢铁了。饿极了的人什么都吃,野菜树皮树叶虫子青蛙,把地上能吃的都搜掠一空。人们忍饥挨饿的时候,姥爷一家就是靠着一缸豆子掺了野菜过活的。妈妈说,一家老小八口人一点没挨饿,那缸豆子是大功臣。
我记事的时候,姥爷已经是一个留着长长白胡子的老头了。姥爷的胡子很漂亮,银光闪闪,不时用手捋一下,一脸骄傲地说,有孙子的人才可以留胡子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少有人留胡子,姥爷外出赶集常常被人盯着看,但姥爷捋着胡子坦然走过。姥爷平时很少说话,笑意常常挂在脸上。有一次,姥爷问我,手呢?我乖乖伸出两只小手。姥爷却笑着说,没看到手啊,看到两只小狗爪子。我自己低头看看,满手脏脏的,真是小狗爪子。我立刻一脸羞涩,赶紧去洗手。姥爷说出的话,常常让我越想越好笑,就像“问:叫啥名?答:狗来问。”一样。姥爷的话,不说透,让我自己悟。有时充满意味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告诉我怎样做,我懂了他的意思,他就笑了。
秋天的夜晚,漫天的星斗一闪一闪眨巴眼睛,人们都坐在胡同口闲聊天。姥爷说要去捉螃蟹,我很好奇,闹着要跟去,姥爷答应了,说,要等到后半夜才回来,你去了不准睡觉。我说,一定不睡。姥爷牵着我的手,在扁担上挂了罩子灯,一头挑着水桶铁锨,一头挑着苇帘子,到小河的木桥边捉螃蟹。
出了庄子不远,有一条小河,河里长满了茂盛的芦苇,正是秋天河蟹肥美的时候,河蟹随着潺潺小河顺流而下。姥爷拿了苇帘子,放在小木桥的一侧,用铁锨铲泥,把苇帘子布在水里,罩子灯就放在苇帘子旁边,我和姥爷就坐在小木桥下面的石头上等河蟹游过来。姥爷嘱咐我不能出声,一出声,河蟹就吓跑了。不大一会儿,姥爷跟我耳语,看,大河蟹过来了。我屏住气息,瞪大眼睛,远远看见几只大河蟹随着汩汩水流奔着灯光乌压压张牙舞爪游来了,毛茸茸的腿、圆鼓鼓的盖、两只眼睛闪着莹光,到了跟前,被苇帘子挡住去路了,长毛腿横着走,在苇帘子上举起来落下去,苇帘子哗啦啦响。姥爷眼精手快,避开蟹钳,抓了螃蟹盖,一下子扔进桶里。螃蟹们好像约好了一样,一波一波地来,多了,姥爷来不及捉,有的就逃走了。捉完一波,要等好大一会儿,螃蟹受了惊吓,听到响声就不敢过来。姥爷布一次苇帘子很费力,不舍得离开,耐心坐着,慢慢等螃蟹来。
前半夜,我看得好奇。夜深了,我就打瞌睡。姥爷跟我小声说,别睡啊,看看天上的月亮:初一初二月牙生,初三初四明铮铮,十五十六好月明……你看看,今天月亮出来得晚,它露出脸来了吧?我答应着,但眼皮不住地打架。姥爷对我说,你闻到豆子香了吗?河西那片豆子熟了,生产队该收豆子了。我正瞌睡呢,听见了也不应声。静悄悄的夜,清冽的空气潮湿起来,小桥边草虫声四起,流水声依旧不紧不慢唱着,灯影下芦苇的根密密麻麻扎在水里,芦苇毛茸茸的缨子随着细风摇摇晃晃,晃着晃着,我就依偎在姥爷怀里睡着了。忽然,一阵刷拉拉的声音和急匆匆的脚步声,我被惊醒了,睁开眼睛看,月光下,看到一个人挑着一担豆棵,急匆匆走过了小桥。我对姥爷说,好像黛玉的爹过去了。姥爷捂住了我的嘴,小声对我说,别说话,咱们该回家了。
第二天,生产队长说,有人偷了河西的豆子,让大家检举。我听了姥爷的嘱咐,一声没吭。姥爷告诉我,黛玉爹也是实在没办法才偷豆子的。我知道的,黛玉娘常年有病吃草药不能干活,跟我同岁的黛玉患婴儿瘫,走路要拄一个小板凳,我们四处疯跑,她只能眼巴巴地看。她家跟姥爷家住在同一个胡同里。一夜之间,我仿佛长大了许多。
姥姥炒的糖豆好吃极了,糖豆是黄豆沾了红糖和面糊炒熟的,吃起来又香又甜。我七岁的时候到奶奶家上学,林彪已经摔死两年了,学屋(小学校)正批判孔老二、批判《三字经》。姥爷说,批判《三字经》要先背过,以后会有用。一句句教我背,我仰着脖子、扯着嗓子,很快背过了。他很高兴,说,这孩子脑瓜灵、记性好。他用细柳条编了精致的小篮子,让姥姥炒糖豆,盛满了奖励我。那糖豆的香味似乎还在嘴里,我却变老了。站在姥姥家门口,我回不到以前的姥姥家了,我成了流浪在外的陌生人。想到这些,我鼻子一酸,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站在姥姥家老宅前,姥姥家大门的黑漆已斑驳,门楣上的苔藓如古钱,墙头上的杂草开始枯黄了。泥墙上的古老往事,如同层层自我剥离的泥土,正在一点点退后,一点点随风霜雨雪分散消失,正房砖石上的古老气息,也在斑驳流离。退后和流离的东西也像我们命运中的精神指向,慢慢沉寂下来,超越一种庸常,上升成我们生命里的真善美。老宅不张扬,自然熨帖地长在土地里,它与周围环境浑然一体,老宅是有根的。
时光如雾霾遮蔽了久远的人和空间,陌生感、失落感,从头顶贯穿到脚跟。姥爷姥姥都去了另一个世界,我所有的记忆都在空蒙和空旷之中了。我想,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经济能延续下来,都是因为有姥爷这么一大群生活在农村勤劳而自知的人们支撑着,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读传家,吹拉弹唱样样拿得起,吵架斗殴也不会退缩。不管兵匪来袭,还是改朝换代,他们都坚守本分,自给自足,为了生存装孬也逞能,骗人也被骗,哭哭笑笑地生活,一代一代死去,又一代一代活着。
我在姥姥家门前流浪,太阳又晒熟了豆子。我对自己说,物是人非了,不管世事怎样变化,我只做“我”吧。我遭遇的岁月既枯寂也丰盈。眼下是个什么样的光景呢?过上几年再回望吧。时年2015年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