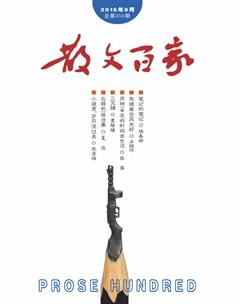苏州,另一半山水等你来
贾志红
芒果树在四月卸下果实,枝叶间顿时寂寞寥落。总监班巴先生站在树下躲避非洲旱季的烈日。龙翻译代表公司向他发出一个邀请:携夫人访问中国。
我听见他噢了一声,短促、响亮,然后眼睛和嘴巴同时张得很大,并保持着这个表情望了我们好一会儿。我和龙翻译相视一笑,他随即也笑了,紧接着又哈哈几声,看着远方张开嘴巴大笑。这个科特迪瓦籍的黑人男子,像他的很多同胞一样,夸张地表达自己的惊喜或是失望。
而我似乎是惯于按捺。比如一个月前我已经知晓公司的这项计划,也知道这个计划将由我来建议路线。有时我在会议室的一幅中国地图上用铅笔画线路,班巴先生就在会议室的另一端和中方总工谈话,他有时候会凑过来,高声大气地和我打招呼,看着中国地图竖起他的大拇指。我礼貌地应一句,不动声色,继续画一条和他有关的线。公司要求这条线贯穿中国的五座城市。我的铅笔在众多的城市之中徘徊。我对城市的选择是苛刻的,我力求一次完美的旅程。我设想它们分别代表一方地域、一种风情或是远古时光的某个闪回。
这份挑剔和细致也源于我对班巴先生的好感。这位桥梁专家青年时期留学欧洲,曾在意大利威尼斯久住。吹嘘自己读过《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文化情有独钟,他热爱丝绸,热爱中餐,筷子用得娴熟极了。
这些元素,不由得令我想到一个中国城市。
它被冠之以东方威尼斯,有可以和威尼斯媲美的水,有贯通城市四通八达的桥,有穿行于河流之上的摇橹船,有丝绸,有故事。
是的,是苏州。唯有苏州。
我的铅笔指向地图上这个具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江南古城。一座被历代文人骚客歌咏透了的城市,却是我从未涉足过的。我圈下一个醒目的记号并决定不再擦掉。以东道主的身份陪同两个外国人同行向往之城,没有人知道我心中连连窃喜。
班巴先生正好走过会议室的门口,花衬衣裹着他高大肥硕的身躯。他吹着口哨,打着响指,像一头欢快的熊。
那是二○一○年,我把《枫桥夜泊》交给法语翻译夏婧,把拙政园、沧浪亭也交给她,同时涌向她的还有京杭大运河、山塘街、平江路。这个刚刚法语系毕业的年轻姑娘被公司安排和我一起接待班巴夫妇。我把我所知道的那个诗里画里的老苏州统统交给她。我和她说,要把苏州和威尼斯一起讲。她眨着洋娃娃一样的晶亮眼睛,像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一样,翻译出一个纸上的苏州。
那一年的夏季,班巴夫妇着非洲长袍来到中国,这是他们隆重的礼服。班巴夫人梳一头繁复细密的小辫子,她说有几百根。是她的两个女佣花费四天的时间用假发接在她卷曲柔软的真发上编织而成的,牢固又逼真,纵使洗发也不会散乱。
我们一行四人,就这样踏入了苏州。
我们当然去了寒山寺,张继的寒山寺。我们听着夏婧用法语朗读这首古诗,我深知纵使是法语,千年以前落魄书生的情怀,班巴先生也是不懂的。其实我也是不懂的。语种转换和文化差异递减了班巴先生收到的信息量,时光流逝也使我走不进古人的忧伤。
我们去平江河上乘摇橹船,班巴夫人大喊,噢,贡多拉。我知道她想起了威尼斯泻湖上的小尖舟。不同的是,在威尼斯那是清一色穿紧身衣的船夫,而平江河上,悠悠摇橹的多是单薄温婉的江南船娘。
班巴先生站立船头,他硕大的身形和这窄小的河道有一些不和谐。遇上过桥,他就猫下腰,他很留意那些小桥,这大约是他的职业关注吧。
从平江路去拙政园,路途不远,我建议步行。途中,班巴夫人在几家丝绸店选购了一些衣物围巾,她满肩披散的小辫子也招致了店员的好奇。班巴先生有时候会带着坏笑从夫人头上悄悄摘下一根,递给店员,在对方的惊诧中,哈哈大笑着离开。
我们进了拙政园,我发现这位桥梁专家在整个游园过程中稍显沉默,这似乎不符合他张扬奔放的性格。依照我的预想,他应该时时发出惊叹才是合乎常理的。从园子里出来以后,在一家冷饮店喝水,他边大口大口地吞咽,边对我和夏婧说,玛利亚姆、艾黛,我很遗憾,我不喜欢这个园林。玛利亚姆、艾黛是我和夏婧的法语名字,一路上他和夫人都这样称呼我们。
班巴先生直率得惊人,他说,拙政园里的山水是假的,像他夫人的发辫一样,很美,但是,是假的。他一直对他夫人的假发辫持调侃态度,有时候还嗤之以鼻。
夏婧愣了一会儿,没有说话。这个初入社会的姑娘,不知道该怎样答复班巴先生。她设想的陪同任务应该在皆大欢喜中充满赞美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不习惯不赞美,我们都渴望赞美而忽略其中的虚假。甚至我也瞠目于这样的异议。我想这是我们古人的智慧,是东方的美学和建筑的完美结合。他大约是不懂东方哲学和审美的,他不懂我们在咫尺之间营造山水的天人合一之意趣。他不懂得这个文化背景,东方人的含蓄内敛和精致。
班巴先生不在意我们的感受,他说,为什么山是假的,是禁锢在一个狭小空间的?植物是按人的意志扭曲生长的?
我和夏婧交换了一下表情,我们沉默了。我想让夏婧问问他,是不是在他的眼里极致的人工美是违背自然的?又突然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庞大,不是我能回答得了的。还是作罢吧。
其实,苏州于我也是陌生的。一座拥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城市,我更多的是从书本上知道它的过往故事。它离我的定居地并不遥远,此前我却一直无缘踏入。我去过遥远的威尼斯,那座水城号称西方苏州,我在那个像苏州一样的城市流连忘返。待到我一脚踏入苏州,我却觉得这个真正的苏州并不像威尼斯。是我遗漏了什么?或者是这座城市遗漏了什么?
匆忙的旅程结束之后,我再次远赴非洲工作。后来班巴先生调离了我们公司,他去了另一个非洲国家。
……
时光一晃又是多年。
有一天,我收到夏婧一条微信,她说她在波兰。她说华沙的市中心宛如乡村,湖泊星罗棋布,树木成林。绿色在这个城市并不是孤岛,并没有圈养,而是同城外的防护林连为一体,是开放的,是宽阔的。她说华沙是她见过的最美的城市。
这个热爱园艺的姑娘,这些年游荡了欧洲很多地方。每到一个异国的城市,她都会给我写几句话,让我分享她的见闻和感受。我回信逗她说,艾黛,你猜玛利亚姆现在在哪儿?她发过来一个问号,我答复她,我在苏州,确切一点说,是在新苏州,太湖东岸,苏州人叫做高新区。
事情就是这么凑巧,我真的在苏州。
我在苏州高新区大阳山下的树山村看梨花。树山这个村子,我是刚刚知道的。朋友说,你若来苏州,就来树山吧,春天来,梨花像雪一样颠覆你关于春天的彩色记忆。
这儿的梨花不是一院两院,甚至不是一坡两坡,而是千亩连绵,无穷无尽。这江南的雪是轻盈的,这雪贴着大阳山的绿,像痴情的江南女子贴着她的情郎,不能分离,没法分离。花朵是植物的爱情表白,这比喻用于梨花又多了一层深意,因了洁白,较之桃花杏花便有了纯洁的升华。但是将花喻为爱情终究还是落了俗套,不如来讲讲树山的生态,这个话题接着地气,想必也是夏婧有兴趣的。朋友说,在树山有两大接地气的主题:养生,乐活。我一听这简单直白的四个字,心里就不由得佩服,它是最简单的、最朴素的,也是最人性的。树山的自然环境极宜果树生长,退耕地还果林便是对自然最质朴的尊重。这尊重当然获得了大自然足够的回报,树山的翠冠梨、杨梅、极品碧螺春,是名声远扬的三大宝。山还是那座山,没有增高一厘,地还是那片地,也没有扩大一分,天地却变得宽阔了。人与环境只是改变了一下相处的方式,像恋人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莺歌燕舞是必然的事。而俯瞰树山村花开花落、果实馨香的大阳山,更有着荡涤肺腑的绿、恣肆心野的花。层峦叠嶂的大阳山不是苏州的小盆景,它逶迤二十里一路西去,直抵太湖东岸,和三万六千顷的太湖共同构成一个广阔的山水带。
这与夏婧描述的华沙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在微信上聊得火热。我们隔着重洋、隔着万里,谈论我们走过或没有走过的地方。
夏婧的来信,也令我回忆起班巴先生。
我在太湖东岸,走在二十五公里的沿湖大道上,一直在想班巴先生那一年在苏州留下的记忆。
我高高地站在堤岸上,迎着掠过湖面的风,看远方的帆影点点,也看近处的小船在芦苇间穿梭。在湖光的潋滟里,一些水鸟轻盈飞翔。我甚至想起贡多拉,那些穿行在亚得里亚海和泻湖上的威尼斯尖舟。我突然想,若是班巴先生此时来到苏州,来太湖之滨,他会觉得苏州和威尼斯相像吗,太湖和亚得里亚海相像吗?这个问题蹦出脑海后我迅速嘲笑了自己,一直在意的那个像与不像,不必再去纠结了。苏州有足够的底气说,苏州就是苏州,苏州只是苏州。
若是夏婧也同来,或许我可以让她翻译《诗经》里的句子读给班巴先生听。“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多么美,没有呻吟式的忧伤。这伊人,该是这座城市。苏州高新区的建设,使得姑苏城不再仅仅以它的园林艺术骄傲于世,真实的仁山智水环绕其间。
不知道班巴先生现在在哪里,他是个满世界跑着建桥的人。如果我有他的微信号码,如果我能用法语和他深度交流,我这会儿就可以给他写封长信了。我会告诉他,苏州有另一半山水,是真真切切的山水,有山有水,真山真水。
或者我还可以更深层地和他探讨一下城市建设。城市重新自然化了,纯生态的乡村、田园、山峦、森林作为城市的元素进入城市。城市和自然有了新的相处方式。
而古城还在那里,必须在那里。苏州会骄傲地对世界宣称:五百年前的古城是什么样,今天的古城就是什么样。
苏州,是一只展翅的大鹏,古城和新区,是它的两翼。两翼羽毛丰盈、均衡,大鹏就飞翔得更高更远。
班巴先生,苏州,另一半山水邀请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