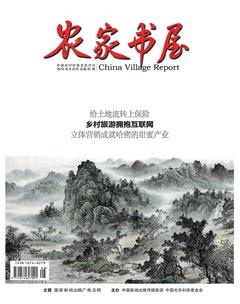沉重的安达卢西亚
江逐浪
最初知道西班牙是因为《堂吉诃德》——不是皇皇巨著《堂吉诃德》,而是有趣的动画片《堂吉诃德》。在那时的心中,《堂吉诃德》与中国的《镜花缘》和英国的《格列佛游记》相似,都是讲一些人的异域冒险,只不过堂吉诃德比他们都更荒唐也更疯狂些。当时听说这是西班牙的文学名著,心中还好大的问号:这也算名著?
等真正捧起杨绛先生翻译的那本厚厚的《堂吉诃德》,才慢慢发现,这绝不是一本搞笑的冒险小说那么简单。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一次次捕捉到了跳动在传奇中的两个字:摩尔。那时已经认识了另一个摩尔人: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就是在那时起,开始对“摩尔”这两个有了些特殊的感受。
公元710年,北非的穆斯林渡过了直布罗陀海峡,在西班牙南部踏上了欧洲的土地,从此,这些皮肤黝黑的“异教徒”被当时的欧洲人称为“摩尔人”。摩尔人的全盛期曾经在西班牙与葡萄牙建立起大大小小许多伊斯兰王国,被称为“安达卢斯”,而当年摩尔人最多的地区,就是现在被称为“安达卢西亚”的浪漫之地。
但是,浪漫的背后是血腥征战。从718年到1492年,就是在这浪漫的安达卢西亚,轰轰烈烈地打响了一场持续近八百年的“收复失地运动”。当年的刀光剑影,至今仍深深地印记在西班牙众地区的建筑艺术中。
1085年,天主教王国从穆斯林手上收复了托莱多。
很多当代学者认为,托莱多的“收复”是欧洲文艺复兴的第一道曙光。托莱多是当时的首都,城内的图书馆不仅藏书量极大,更保存着被翻译成阿拉伯语的欧洲古代经典。欧洲人正是从托莱多的图书馆开始重新接触到那些被基督教教会压抑了近千年的古代文化传统。
今天的托莱多,依旧完整地保留了欧洲人和北非人的文化痕迹。这座城市不大,但它的规制像所有的欧洲古城一样,城外有一条河,城中有一个广场,广场的中央矗立着一座教堂。所不同的,在于那座教堂的模样。这座建筑的整体明显呈现出当时最流行的哥特式教堂的形状,三道拱门寓意基督教所信奉的“三位一体”;可它内部装饰得金碧辉煌却又是明显的穆德哈尔风格,而后者,正是欧洲基督教艺术与北非伊斯兰教艺术联姻的成果。这座教堂的内外风格正如它所扎根的那段拉锯撕扯的历史。
1118年,收复萨拉戈萨。
也许是因为“收复”得更晚,在这里,带有伊斯兰艺术特征的穆德哈尔风格也更显耀张扬。人们不用走进萨拉戈萨那地标性的皮拉尔圣母大教堂,只要站在合适的角度上,就能看到教堂顶上那些绚烂的镶嵌图案。走遍意大利法国等天主教文化腹地的教堂,能够看到更多金碧辉煌闪耀人眼的黄金装饰,却很难看到这样的图案:黄白蓝的颜色组合,几何图案的拼接与变形——那正是拒绝偶像崇拜的伊斯兰艺术风格的典型特征。
1236年,收复科尔多瓦。
科尔多瓦的教堂,干脆就在导游手册上被称为“科尔多瓦大清真寺”。这座教堂始建于公元8世纪,是当时的穆斯林对在建中的天主教堂的改建。在它以清真寺的面目存在时,它甚至是西班牙穆斯林心目中仅次于麦加和耶路撒冷的朝圣地。可尚未真正完全扩建完毕,科尔多瓦被收复,它又重新被改建成了教堂。
走进这座教堂的任何人,都能真实地感受到其中的“清真寺”气息。大到这里残留的伊斯兰教门廊、宣礼楼的建制,小到建筑上密密层层的卷草纹样装饰,都是那段500年占领岁月的遗迹。与它们相比,中间的文艺复兴式教堂反而显得有些不协调——那是16世纪改建后的结果,据说,这结果连当时的西班牙国王都十分不满意,也正因为他不满意,大清真寺的主体最终得以保存。
大清真寺外不远,矗立着一座“收复失地纪念碑”。可是,收复失地的脚步并没有在此停下。
1248年,塞维利亚被收复;1492年,格拉纳达被收复。
格拉纳达是最后一个穆斯林的堡垒,这里也留下了最精美的阿尔罕布拉宫。这里的艺术风格已经没有任何犹豫、妥协与层叠,干干脆脆的,它就是伊斯兰艺术的一颗明珠。
有一首吉他名曲《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虽然已经对它熟悉了很久,可到了那里才明白,这支曲子就是阿尔罕布拉宫!美妙的分解和弦就是那波光粼粼的香桃木宫,精致复杂的震音就是精细繁缛的木雕与穹顶,带有异域风情的旋律就是整个宫殿伊斯兰风格的写照,而那忧郁的曲调则浸透着阿尔罕布拉宫的历史沧桑。
细细体会一些格拉纳达末代君主们的心绪:眼看着自己成为了一座天主教世界里的孤岛,眼看着身边的盟友一个个陷落,耳边听到的,却是城外大军的军鼓与欢呼。他们从精美的阿尔罕布拉宫窗口愁苦地望着远方的山坡,那里有铺天盖地的天主教军队,他们已经无力像科尔多瓦的君主们那样不断拓展他们的艺术精品,他们所能做的,只有修饰再装饰,精益更求精——也许,他们是希望阿尔罕布拉宫能美到让敌人不忍伤害的地步,从而让世界永远记住:我们曾经在这里。
1492年,他们走了,回到了海峡对岸,可他们的阿尔罕布拉宫真的被完完整整地保留了下来。他们的初衷实现了,阿尔罕布拉宫没有重复科尔多瓦清真寺的噩运——没有人忍心破坏那样的美。
1492年也有一支曲子,那是电视剧《士兵突击》里的七连长的最爱:1492,征服世界。
1492年真的是西班牙历史性的时刻,那一年,天主教双王伊莎贝拉与费尔南多收复了格林纳达,彻底取得了胜利;那一年,伊莎贝拉私人资助了哥伦布那即将震惊世界的远行;也还是那一年,他们颁布了对境内犹太人的驱逐令。安达卢西亚的浪漫气质,原本就源于基督徒、摩尔人和犹太人多元文化的混合与融合,不同的民族与宗教在碰撞中相互学习相互砥砺,终于形成了绚烂的阿达露西亚文化。可是,就在八百年的收复失地运动最终结束之后,文化却走向了倒退。
文化的狭隘与倒退是迅速的。从1501年起,西班牙强令各地区的所有摩尔人改宗。这项法令被执行得非常充分,所有拒绝的人都被戴上苦役犯的镣铐,排着长队,奔向那些荒凉而陌生的流放地。到1526年,西班牙全境的摩尔人基本都已被迫改宗,可即使如此,他们的苦难仍旧没有结束,1609年,“大驱逐”开始了。五年间,300万已经改信天主教了的西班牙穆斯林从桑丘面前经过,再次离开自己的家园——上一次他们是征服者,这一次,他们是被驱逐者。命运在800年间,完成了一次残酷的轮回。
被改成教堂的大清真寺也好,被改成清真寺的大教堂也好,他们静静站在安达卢西亚的历史深处,看那些不同的征服者们来了又去、去了又来。那些人留在了时光的深处,可是那些多元文化碰撞出的美,却永远凝结在了文字中、石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