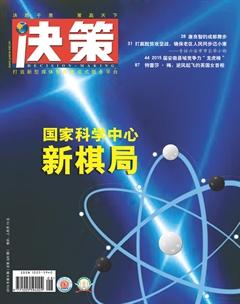罚款“优惠券”:争议下的管理创新
洪平平 刘圣中
[城·事]
夭折的交通管理创新
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交警大队在一项交通秩序整治活动中,推出了交通违规“优惠券”。今年6月下旬开始,该县不少市民都收到了这种“优惠券”。除了对交通法规的宣传之外,该“优惠券”中还注明:市民交通违规被查时,出示本券,罚款可打5折;现场拨打电话,接听者只要答出交通法规,则可免于处罚。正因如此,有人干脆就直接称其为罚款“优惠券”。
据统计,该县县内共有40万辆电动车,每天发生的由电动车引起的事故有10起左右,2015年则总共发生了超过3400起事故。为了降低电动车和行人违规而造成的事故率,让市民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该县启动了一项交通秩序整治活动。自7月1日至9月30日,为期3个月,而6月20日至7月10日为宣传阶段,交通违规“优惠券”正是此阶段的产物。
此事一经报道,遂引发多方热议,一时间将灌云县交警部门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迫于压力,该县交警大队目前已将“优惠券”改为“文明交通承诺书”,同时去掉了“打折”内容。交通违规“优惠券”经历了半月游,结束了昙花一现的命运。
[剖析]
“优惠券”创新的初衷与缺陷
罚款“优惠券”可谓是一种治理交通无序问题的管理创新行为,甚至可以认为是地方主管部门面对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的交通无序问题的无奈之举。尽管这一举措昙花一现,很快就停止了,但围绕这一行为却产生了一次较大的舆论风浪。总体来看,在这次舆论风浪中主要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一种是支持者,他们主要关注这一措施的初衷和效果。他们认为,就初衷而言,灌云县交警大队想通过吸引民众关注的方式来达到宣传交通法规、改变交通状况的目的,这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理应支持和鼓励基层执法部门在当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对具体执法手段进行大胆的探索和创新。在方式和效果上,相较于之前交通管理原教旨式的严苛,灌云县此举很接地气,民众的接受程度和学习法规的积极性有了较大提高,也产生了较明显的效果。这一做法更符合老百姓的习惯和要求,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认可。
另一种则是反对者,他们主要关注这一做法的合法性问题。尽管也有相关法律专家认为,灌云县交警的做法是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基础上进行的灵活执法,是行政执法主体在法治框架内自由裁量的表现,并不存在所谓的违法问题。但还是有较多的法律专家指出,对罚款进行打折优惠的做法,是将法律行为等同于一般的市场行为,存在拿执法做交易的嫌疑。这样不仅戕害了法律的威严,也造成了法律威慑力的缩水。另外,“优惠券”构成一个不可确定的变量,同样的交通违规,却被处以不同的罚款,同错不同罚,有失公平。甚至还有人质疑此“优惠券”是否真的能提升民众的守法意识,降低违章率,而不会起到反作用。
针对以上两种认识,我们认为,不论罚款优惠券的初衷如何,衡量这一做法的合理合法的支点还是它的行事方式和最终结果。因为,所谓初衷是指其目的和动机,这是一个无法确定考量的对象,我们不能用一个模糊的东西来论证管理行为的正当性。任何不正当的行为都可以找一个美丽的借口。既然如此,那么,这种优惠券式创新究竟存在何种问题?又是如何让管理打折的呢?
管理不能“打折”
首先,罚款优惠券的内容模棱两可。正如社会舆论所分析的,这种做法在罚款内容上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模棱两可,而且给人为操作留下较大空间。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和法律精神的。罚款是一种针对不正当行为的惩罚性措施,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字标准,则无法体现罚款的惩罚性、严肃性和强制性。人为空间则可能为寻租行为预留机会,会刺激权钱交易行为的滋生。如果长期这样做,则无法得到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的认可,其罚款的意义将大打折扣,最终则会影响这种做法的法律效力,乃至公权力的社会公信力。
其次,罚款优惠券在形式上等同于市场交易。将罚款和优惠券结合起来,这是借鉴了市场交易的方法与形式。看起来很注重市场契合性和社会接受性,但是这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即特别重要的公共权力是不可以运用市场交易的形式来运作的。市场交易是两个平等个体之间的商品和业务互换,存在于市场经济的场域中。然而,罚款则是公共机构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公共权力对个体行为的干预和惩罚,存在明显的不对等性,是不可以采用市场交易来处理其相互关系的。如果允许这样做的话,那么代表公共权威的罚款都可以进行讨价还价、自愿交易,结果罚款的权威性和刚性则无法坚守,最终甚至会影响到罚款的执行和交通问题的治理。
再次,罚款优惠券在本质上折损了法律权威。最集中的问题还是这一做法将慢慢折损行政执法的法律权威。行政罚款是一种政府公权力的执法行为,代表了一种不可轻视和不可违背的法律权威,其目的是坚守社会准则,改变不正当社会现象。而将行政罚款采用优惠券的方式来折中或者推销,则不知不觉中降低了罚款的强制权威性和目的正义性。类似商场推销的优惠券被运用到公权力上,让公众感受到更多的是公权力自身威力不足和动机不纯:一者不敢执法,所以折中调和;一者大力推销,所以寻求更大的罚款。这样做法的结果自然是公權力的威严大受削弱,在公众眼中甚至可能视同儿戏。
[路径]
基层如何开展管理创新?
从以上案例我们可以反思到,作为基层政府管理机构究竟该如何去寻找最佳的管理创新良策呢?怎样才能让我们的管理创新既能坚守法律底线和法律准则,同时又可以真正地契合现实社会问题,有效发挥创新效力,真正地解决社会问题呢?我们不妨继续以交通治理为例来分析管理创新的基本要求和对策。
第一,“无法律,不行政”。任何管理创新都要以法制为底线,法制既是管理的保障,也是管理的目标。没有依据法律原则的管理创新,也许可能带来一时的效果和变化,但长期来看,这样的创新不仅不能实现管理水平的提升,而且还可能导致管理的转向和倒退。在交通治理当中,依法治理是一个永恒的任务。如何按照法律原则来真正确立良好的交通秩序,才是管理者需要认真考虑的事情。
例如,上面所分析的罚款优惠券式做法,就与一般的法律原则相冲突。正确的做法是罚款不仅不能实行优惠,还要严格执行,甚至提高标准,让违反相关规定的人品尝到不当行为所带来的苦果。舆论也经常批评很多行人抱有“法不责众”的心理,存在所谓的“中国式过马路”的现象。这一方面反映了交通治理问题的困难,另一方面也说明公众对法律权威的轻视。所以,如何在公众心目中树立法律的权威,培养更强的法律意识才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当然,这是一个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来不得半点折扣的事情,需要持之以恒,坚定执着的态度和行之有效的方法才能达到目标。
第二,创新要找到明确的着力点。管理创新一定要有一个可以支撑其运作的明确的着力点。着力点选择不准确,就可能导致整个方案的失败。例如罚款优惠券的做法就把着力点放在优惠券上,这是极不严肃的。还有些地方在治理行人、电动车违章时,强迫闯红灯的行人戴绿帽、穿绿马甲站在路边劝导其他路人。这种做法把着力点放在穿戴不妥服装和强迫劝导路人之上,也是一种有悖文明法治精神的做法。
在我们看来,着力点还是要回归到法制上来。例如,我们可以吸收信用法制的方法来处理这一问题,即针对行人或者电动车主违章行为采用信用记录的办法来予以处理。具体操作可以通过给违章者扫描其身份证,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录到个人信用当中,这样,其信用记录将会影响其他工作和生活的多个方面。以此来实行惩罚,并规范更多的公民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做一个守信用的公民。
第三,常态化治理是最高境界。管理创新的目标是如何尽快实现常态化治理,这是社会治理的最高境界。常态化治理是一种相对稳定有序、节约有效且具有可持续性的治理模式。在交通治理方面,一些地方习惯于使用运动式执法模式。
例如今年3月份,深圳开展了一场被媒体称之为“史上最严”的禁摩限电整治行动,由于事发突然,外卖、快递等民生行业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令此次整治行动最终演变成一场民怨沸腾的舆论危机。实际上这种模式的效力并不理想,很多地方“严打”风头一过,各类交通违法违规行为又会卷土重来。
常态化治理不是单靠某次集中行动,而是有针对性、有步骤、有法制地逐步解决各类问题,尤其是久治不愈的难点问题,例如电动车违章的问题。早期还是需要加大每天街上执勤的力度,尤其是在高峰时段的执勤。还要加大对电动车的监督,采用上文所述的信用记录方法,凡是有违章违规的行为即计入个人信用记录当中,以此来形成一种威慑,从而督促公众珍惜个人信用,规范个人行为,最后逐步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四,治乱要重罚。罚款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权宜的手段。在目前整体环境不佳、公众交通守法意识淡薄、自觉能力不强的情况下,适当采取一定的罚款还是可以的。但是,目前罚款的标准太低,违法成本太低,所以并不能产生有效的激励作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条规定: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这样小的罚款数额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不能产生明显的激励作用。因此,应该学习新加坡等地的做法,加大交通违规中的处罚力度,提高违规成本,將罚款标准提高到数千元。这样才能引起公众重视,从而促使他们认真遵守各种交通规则。
总之,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大胆进行各种创新尝试,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推动力,但是,在创新的时候一定不可以只求新意,甚至为了某种噱头和轰动效应,而忽略了政府管理始终必须坚守的法制底线。法律是政府管理的灵魂和基准,失去了法律的标准和依靠,任何管理创新都是不可靠的,甚至会成为为人所讥讽的笑话。在法律之下大胆创新,改变旧的作风和管理模式,这才是所有公共管理者都应该牢记在心的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