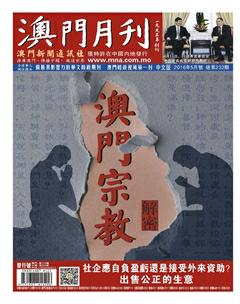學者看宗教:仁者愛人,回歸本源
卜樂

浪漫主義詩人屈原在《天問》這部長詩中向上蒼求問:“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誰能極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明明暗暗,惟時何爲?”上蒼雖沒有直接給出答案,但人類卻從未停止探索答案的步伐,在種種疑問中,宗教似乎在給世人逐步揭開謎底,而宗教之於天地,個人、社會、國家乃至全球又意味著什麼呢?
智者啟迪
2014年,我同時收到位於美國三角研究園的國家人文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和位於普林斯頓的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院士(Fellow/Member)任命。其中的美國高等研究院是世界上第一所高等研究院,創建後接納的第一批院士和終身教授是愛因斯坦及其他逃離納粹德國的傑出科學家。雖然兩所研究院都邀請我去一年,為了有機會體驗兩處的學術生活,我將一年的學術假期分成兩半,2014年下半年去國家人文中心,2015年上半年去高等研究院。國家人文中心座落於一片幽靜美麗的樹林裡;高等研究院也擁有自己的大片青翠樹林、草坪及一個環繞著水仙花的秀麗湖泊,野鹿、野兔等隨處伴人而行。這一年自由自在的學術研究,與世界頂級學者的交流對話,及世外桃源般的自然和人文環境,是我最美好的人生體驗。
在談論宗教前,我們不妨看一看愛因斯坦這位科學巨匠,因為他對於科學研究的無私奉獻及對全人類的誠摯熱愛實際上體現了一種“準宗教”的精神。愛因斯坦赴美後一直在普林斯頓的高等研究院從事研究工作,直至1955年去世。我在那裡的辦公室,就在愛因斯坦原來的辦公室的隔壁樓,我白天經過他的辦公室去工作,傍晚在樓前的愛因斯坦小徑散步,圖書館中陳列著他用過的地球儀等,由此而有許多時間閱讀和思考他的人生。愛因斯坦享有最高的世界聲譽,但他並不相信名聲。他曾經說,十萬年之後,即使今日最著名的人物也無人知曉。因此他的努力工作並非為了個人名利,而只是盡自己所能,為人類發展做出貢獻,由此而體現個體生存的價值。這在一定意義上與儒學的“盡心立命”(《孟子》)相似。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一批德國科學家和思想家迷失自我,支持戰爭和納粹。愛因斯坦則從一開始就鮮明地表達反戰、反法西斯的態度,即使一再受到謀殺的威脅也無所畏懼。晚年他一直為曾寫信支持研製核武器而內疚不已,雖然他的初衷是擔心被納粹搶先制出核武器,從而對人類造成重大傷害。這和儒學的“仁者愛人”及佛教的“慈悲濟世”的理念也近乎一致。
何謂“宗教”
而關於宗教,則說來話長。中文的宗教二字,宗源於祖先崇拜,宗字本義指宗廟,並衍伸出各種意義,如祖宗、宗族、宗系、宗主、宗旨、正宗等。教本指政治教化,擴展指各種思想、教義。宗和教在佛教中被廣泛運用,教本來指佛陀的教義,宗指宗旨、理論、宗系等。宗和教合成一詞,最早應出現在宋代佛教,宗指禪宗各系,教指注重經典教義的各系如天臺、華嚴等,宗教合稱指佛教各派系。英語的Religion則源於拉丁文的religio,意指聯繫。Religion是最為模糊多義的詞語之一,至少有一百多種定義。開創宗教研究學科的麥克斯·繆勒(Friedrich Max Muller)說:“世界上有多少宗教,就會有多少宗教的定義。”基於西方宗教模式的宗教觀念,指包括宗教信仰、情感、儀式、組織等的完整體系。日本學者最早以宗教(shūkyō)一詞翻譯Religion,其後梁啟超於20世紀初介紹進中國。
雖然這一西方模式的宗教觀念並不適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但是從二十世紀初以來卻在中國的社會政治方面產生了一系列重要影響。在1900年之前,中國宗教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大系統,包括所有形態的宗教實踐,各種個人的和集體的信仰、崇拜、修練、儀式、組織等,儒學的祖先祭祀,道教,佛教,各種民間派系,及廣佈於鄉鎮的不計其數的地方信仰和廟宇。中國的宗教系統早已存在,但沒有一個統一的名稱,因為並沒有統一的教會機構和權威。外來的宗教如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等,並不包括於中國宗教的這個大系統之中。然而,在接受了西方模式的宗教觀念後,中國知識份子做出了一些激進的反應。他們將中國原有的宗教系統分裂為宗教和迷信兩種,認為宗教可以接受,可以在國家的建設中起肯定的作用,而迷信必須被批判和拋棄。於是模仿西方和日本的憲法,從民國到共和國的中國憲法也規定了“宗教信仰自由”,但這個自由是有限度的,只限於“真正的宗教”,即所謂五大宗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伊斯蘭教,佛教,道教。而且在很多時候這些宗教也是受壓制的。一直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才提出“民俗信仰”來代替“迷信”,從而使得原本被劃歸為迷信的那些民間信仰開始合法化。我們今天談中國宗教,不應該再將其分為宗教和迷信兩部分,或做其它劃分,而是一視同仁,將所有宗教信仰形態皆劃入同一範圍。
同時,宗教與文化是一起產生的,人類文化最早採用的就是宗教文化合一的形態。現代人類學家說,當人們為死者舉行某種喪葬形式(亦即宗教儀式),這就是人類的族類自覺的開始,也是人類文化的開始。其後宗教和文化始終聯係在一起,無法截然分開。廣義的宗教或準宗教,可以包括各種信仰和信念,各種道德修養和自律,以及各種自我奉獻精神,如上面提到的“盡心立命”,“仁者愛人”,和“慈悲濟世”。
儒學的現代化
如同李澤厚先生所指出,儒學源於古代巫史傳統和禮樂制度,巫史和禮樂都是宗教文化。先秦古典儒學之“道”,是天道和人道的融合,包含了宗教、倫理、政治等要素。新近出土的戰國楚簡中,有不少討論天命和人性關係的文本,如“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等。“性命之學”從先秦到現在一直是儒學的核心學說之一,性指人性,命指天命,故這一學說本身已經體現了宗教和思想的融合。然而吊詭的是,雖然儒學信天命和敬天命,這個天命又往往是人性的完善和個體價值的終極實現,因此儒學的安身立命之處總是在人生和現世,儒學的核心關懷總是人性和人文。孔子說自己“五十而知天命”;然而天默默不言,孔子從何得知自己的天命?這是因為經過努力學習、修養和實踐,孔子最終充分地完善了自己的稟性、能力、知識、品格和志向,從而也就了知上天賦予自己的人生使命,並努力去加以實現,為人類做出貢獻。這也是孟子所說的“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孔子是如此實踐其人生,孟子是如此實踐其人生,愛因斯坦也是如此實踐其人生(雖然他並未有“知天命”的觀念),而他們的人生也由此而煥發出人性的最美麗光彩。
從孟子到宋明理學所強調的自我修養和道德自律,也帶有準宗教的色彩。因此,儒學及其許多思想學說,已經含有宗教成分,並不需要再添加一個“儒教”的詞語或概念。而盡管含有宗教成份,儒學思想的核心總是人性和人文精神。傳統儒學的祭天祭祖是宗教儀式,但所祭的天總是神性、倫理、自然之天的混合,而祖先崇拜更明顯地與親親而仁的人性情感及生生不息的人類延續相關聯。與其它宗教中的上帝、神超越於宇宙之外不同,中國傳統中天地鬼神與生人共存於同一個世界,人類因此而可以參天地、泣鬼神。比起許多中西方學者津津樂道的“關聯式宇宙觀”,李澤厚先生和安樂哲(Roger T. Ames)先生所提出的“一個世界”的宇宙觀更符合中國宗教文化傳統的實際特性。
儒學文化二千年來一直是中國文化的主流,現在也仍然是,並不需要強調和論證。在民族、國家、人類走向全球化、世界文化秩序發生重大變化而人性精神正在流失的今天,我覺得重要的不是強調儒學作為中國國粹、國學、民族精神的意義,而是如何發揮儒學的優秀思想文化資源,去掉其與現代社會不合拍的成分,與東西方的宗教文化及公共理性中的合理成分相結合,為重建世界文化秩序和人性精神做出貢獻。2014年在夏威夷大學召開“世界儒學文化研究會”成立大會,出席會議者有來自儒學文化圈的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日本、韓國、越南、新加坡的學者,也有來自北美和歐洲的學者。我被邀請代表澳門大學成為研究會的合作夥伴。會議的總主題為“儒學價值觀與變化中的世界文化秩序”,所討論的主要問題為:當代“儒學”文化的形態是什麼?儒學的歷史缺陷和局限是什麼?儒學能為湧現中的新世界文化秩序貢獻什麼?我們這一代人應如何改造儒學文化以使之成為引導正面變化的國際資源?這些問題冷靜、實在、深刻、寬廣地引導我們思考儒學在當今世界的重要意義和可能作用,同時也指出儒學現代化的發展方向及其與人類命運的密切關聯。
人間佛教及其對儒學發展的啟發
儘管佛教由印度東傳而來,但其在中華獨特的文化環境中,相互吸收精華不斷發展,逐步本土化,在當代“人間佛教”的理念更是廣為人知。現當代人間佛教的逐漸發展和成功,是佛教現代化的進程,但恐怕不能如同有人說成是“宗教革新”。佛教被稱為最“哲學”的宗教,在歷史過程中發展出一套精緻複雜的哲學體係,諸如印度的中觀、唯識、因明,中國的天臺、華嚴等,並在其傳播過程中形成眾多各具特性的傳統。愛因斯坦甚至曾經說,佛教是最接近現代科學的宗教。一些人將佛教稱為“老人宗教”、“亡者宗教”是誤會,“超度亡靈”等僅是佛教的儀式和表現形態之一,不能代表全部佛教。佛教也不能被簡單地稱為“出世宗教”(雖然佛教中有些人也如此說)。佛陀(Buddha)意謂覺悟者,他在三十五歲覺悟後並未“出世”,而是走遍恒河中游盆地,傳播佛法,救度世人。在佛陀所建立的寺院,僧尼嚴守戒律,樂於助人,成為世人的榜樣。大乘佛教出現後,一方面大講“一切皆空”,另一方面卻大倡菩薩行。菩薩發誓為普度眾生而覺悟,並在覺悟後不斷返回人間,慈悲救濟世人,所謂“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空性”和“入世”並不矛盾,因為大乘佛教“空”掉的只是自我,而不是存在(雖然是缺乏內在實質的存在);當菩薩不再為自我打算之後,全副身心就都用於幫助世人。唐代的古典禪也明確地提出“平常心是道”、“性在作用”等口號,將入世與出世,存在與超脫統一起來。在南傳佛教、日本佛教、韓國佛教等傳統中,佛教徒曾是世俗知識的傳播者、政治統治的輔助者、文學藝術的創造者,等等。例如,日本室町時期的禪僧擔任外交官、會計師、中國文化藝術甚至儒學的教師,並以詩歌創作、書法、繪畫、花道、茶道、園林設計等技巧而著稱,形成著名的室町美學,至今仍是日本文化的代表和驕傲。
當代人間佛教的發展,主要是將佛教的入世濟度傳統現代化,以現代的方式發展宗教事業、慈善事業、教育事業、文化事業等。在這方面,有志發展儒學的人士或許可以從人間佛教的成功獲得啟示:是刻板地模仿恢復傳統儀式,還是促使儒學現代化,讓儒學的人文精神在全球煥發新的光彩,為世界文化秩序的重構做出貢獻?孔子早已指出:“義為禮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