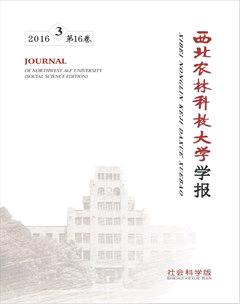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改革:逻辑、原则与制度选择
郑若瀚
摘要: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改革是土地法制改革中的一项核心议题,它在现行土地法体系的多重目标和逻辑下存在显著的制度冲突和权利限制问题,破题的关键是厘清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逻辑和原则。这要求将财产权逻辑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逻辑主线,将多元目标拣选、提炼为两项原则——即农民权利实现机会和承包经营权益的绝对保障,并以这两项原则划定财产权逻辑的适用前提,而未被转化为原则的其他目标则只能在不违背主线逻辑的前提下设定和适用为该目标服务的规则。在此基础上,制度改革的思路将趋于明晰,土地承包经营权将同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经营权共同构成三层次的权利体系。集体所有制仍然是制度前提,土地经营权将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而非土地所有权)为基础获得创设并承载旧制度未竟的使命,就长期而言,曾施加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转让、抵押、期限上的限制将逐渐弱化,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再分配将吸纳更多授权性(自治性)规范,但出于经验性考虑,短期内的制度调整仍有待变通设计与实施。
关键词: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土地改革
中图分类号:F323.2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3-0011-06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创设使得农户获得了相对自主的土地财产权利,同时也缓解了因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而造成的权利空洞化问题。然而,这种特定时空经验下的权利创制,其有效性必然受制于人口、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的制约;同时,由于经验优先的立法策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权逻辑也被置于次要位置以服务于具体政策性目标,这又造成了权利基础的模糊和权利本身的弱化。在土地制度面临重大改革之际,有必要审思和重构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实现其经验与逻辑的统一。
一、问题缘起:多重目标和逻辑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法治语境中的权利有着无可置疑的优位性,土地承包经营权亦不例外。但也须意识到,土地(尤其是农地)有着显著的公共性涵义和特征,因而土地法规范不宜以单一的私权视角表达农地权利。事实上,我们不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现行土地法规范中看到维护公有制、保护耕地、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农民权益等多元目标, 例如《土地管理法》所表达的“加强土地管理,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农村土地承包》所表达的“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这也表明,权利保护仅仅是该目标集中的一项。然而,正是由于多重目标的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制度表达难免贯以不同逻辑,由此引发土地法体系中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它们集中反映在如下问题上:
(一)承包地的调整
承包地的调整规则在总体上遵循着财产权逻辑,注重权利的稳定性,在现行法律规范下,发包方不得在承包期内调整承包地。《土地管理法》将承包地的调整限定为个别调整,且受严格程序限制:“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则作了进一步缩限,即个别调整只能是“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然而在实践中,不得调整承包地的规定却始终承受着合理性质疑。据李昌平等人的调查,贵州农村已经有25%的在村农民无地可种,只能依靠租地耕作维持生活,而农村有25%的土地承包经营主体已经转移进入城市,成为纯粹收租的不在村地主[1]。为此,也难怪有学者不解:“既然立法者连承包人转让土地都担心其失地后的生存问题,那么,对庞大的新增无地农民的生存保障为什么又视而不见呢?”[2]此外,一种相反却更为普遍的情况则是乡规民约对法律的背反,“三年一大调、一年一小调”在许多乡村有着广泛实践。有调查显示,二轮承包以来至2008年和2010年被调查村进行过土地调整的比例分别为375%和40%[3]。以上情势既显示出承包经营权的财产权属性与保障性功能之间的矛盾,也反映出财产权逻辑在产权主体视角与立法者视角之间的分歧。
(二)承包经营权的继承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属性始终模糊,在继承问题上尤甚。从《继承法》第3条的规定来看,财产财产主要包括:(1)公民的收入;(2)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3)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4)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5)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6)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7)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性权利有资格成为可以继承的合法财产,但《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问题的规定却含糊保守。该法第31条规定:“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另外,第50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该承包人死亡,其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在承包期内,其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
这意味着,现行土地法规范只对“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的继承予以肯认,林地和四荒地可以由继承人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其继承问题被转化为承包经营的合同问题;家庭承包方式设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的继承问题则被立法悬置了。即使抛开立法规范对于承包经营权继承的模糊规定,单从“家庭承包”本身的性质而言,其继承问题便有着特殊的困难。由于建立在“户”的基础之上,因而它并不属于个人财产,只要不是全部家庭成员死亡,承包经营权主体就没有发生变更,财产分割亦无可能,继承也因此无法进行。于此,只有在子女同父母“分家”后分别获得承包经营权的情形中,其中某一户的家庭成员全部死亡时,才存在继承的可能。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各级法院对各种情形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都普遍持否定态度[4]。
由此,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逻辑、目标的繁复杂芜。在继承问题上它摒弃了财产权的逻辑,而转向了合同的逻辑,并试图以保障性(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土地均分)的目标代替个体财产权保护的目标,进而也就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弱化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当然,对于财产权逻辑的放弃也部分地源自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特殊的主体构造,它导致了继承问题在实施上的困难。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与抵押
毫无疑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与抵押已经成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中最受争议和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出于土地所有制性质的考虑,农地被禁止买卖,土地流转只能在不改变所有权关系的前提下于使用权层面展开。于是,土地的流转就被转化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然而,这种转化不意味着流转再无其他前提。保障功能、粮食安全等目标又为流转增设额外限制:(1)承包方须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2)受让方须为从事生产经营的农户;(3)须经发包方,也即所有权人同意。由于以上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功能受到极大限度的减损:由于变现能力极低,作为一种财产性权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人为地压低了权利的价值和价格。此外,由于无法向非农户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也就无法得到肯认,农民难以凭借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得生产、经营所需的充裕资金,农民收入亦因此受到消极影响,纯粹从事农业生产通常仅能维系较低的生活水平。于是,现行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陷入了悖论:以保障农民生活为目的,却堵住了农民的致富之路;欲保障充足的粮食供应,却无法阻止农民放弃农业生产。
对以上问题的揭示反映出土地承包经营权所面临的多重目标和逻辑以及由此生成的内在冲突,意欲化解这些冲突,就必须在理解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利基础的前提下找出一种合适的统合方案。
二、破题:厘清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逻辑与原则
土地承包经营权建立在特定的经验事实与制度环境之上,因而能够契合特定时期经济社会条件以及体制的需求。但它也必然遗留致命问题。首先,从地方性的短期经验中提炼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有其历史性特征,保障性的考虑优先于权利的逻辑需要,然而当“保障性”需求呈现不同趋势时,据以立足的经验支撑会发生松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导向也将面临调整。其次,尽管法权的内容源发于基本的经验事实,但其逻辑仍然有独立性;仅仅表达和顺应某种特定经验,可能会弱化法权的实质性内容,从而架空拟被保护的权利。破解问题的关键在于厘清农地权利保护的逻辑与原则,实现经验与逻辑的统一。
(一)多元目标中的逻辑主线
多元目标难免会造成制度选择上的“顾此失彼”,因而对多重逻辑予以统合成为惟一出路。目前,比较流行的统合方案是确立纯粹的财产权逻辑。它主张农地权利的绝对化,在此之上设置的负担仅仅限定为出于土地资源属性的考虑而实施的用途分类与管制,除此之外再无其他限制。在此种逻辑之下,土地权利可由权利主体自由处分,农民将因此增加其财产性收益;与此同时,农地流转会带来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并促成规模经营,提供更高效的粮食生产。这看似多方共赢的整合方案在现实中却仍存疑问。
首先的疑问在于,农地自由流转是否必然增加农民收益或者解决其生活保障之忧?从短期来看,未必如此。一部分小农生产(如种菜、养鸡、养猪)最后直接被家庭消费,这实际上降低了家庭货币性支出;与此同时,在家庭劳动分工中,农业生产往往由老年人完成,他们进入城市后很难转化为劳动力。于是,失去土地将会意味着更高的货币支出,这就需要用更多打工收入来填补[5]。同样值得思虑的情况是,对于不在城郊的农民而言,其可能获得的流转收益非常有限,难以支撑其在城镇安家落户,在这种情境下,“打着为农民旗号要农民土地赶快流转,着急的并非农民,而是另有自己考虑的政府和另有所图的资本”[6]。
另一个疑问则在于,资本主导的规模经营是否必然导致更高效的粮食生产?实际上,中国农业的“过密化”问题仍然广泛存在,单位土地产量的最大化与单位劳动力产量的最大化并不是对等概念[7]。这极可能导致的情况是“农地规模经营虽然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却不能提高单位土地上的产出”[5]。学者的调研为此提供了佐证,例如安徽平镇的情形,资本农业在代管模式下水稻亩产400公斤,家庭农场和中农的水稻亩产则分别可达450~500公斤、500~550公斤[8]。这也暗示着在当下中国人口条件和社会结构中,大规模的农地流转、集中利用同粮食充足供应之间的关系仍然微妙,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最优主体和利用形式并不必然排斥小农。实际上,根据范德普勒格的观察,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工业化国家都存在着“再小农化”的进程[9]。从这个意义上讲,小农经济始终是现代农业体系的组成部分。此外,粮食供应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还隐蔽着另外一重分歧。不可否认,资本下乡对于发展现代农业和推动农村经济增长具有基础性作用,但是同样明显的现实是,资本的逐利动机使其规模经营的偏好更倾向于高价值的经济作物,抑或是开发观光旅游、单纯赚取补贴。亦有调查发现,在农业大省河南省,随着新型经营主体不断涌现,土地流转进入“新常态”,但与此同时,“工商资本流转土地投机色彩较重,有的甚至因为盲目上马形成`烂尾工程”[10]。
有鉴于此,确立单一的纯粹财产权逻辑恐怕并非破题的妥适方案。因此,另一种思路显得更为实际和重要,也即确立逻辑的主线与支线。这不意味着无标准、无规律地“搞平衡”“和稀泥”,而是确立一种逻辑主线,并为其设定适用前提和范域:将财产权逻辑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逻辑主线,与此同时,通过将目标(如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保障粮食安全,保障和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权益,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等)拣选、提炼为原则,再以原则划定逻辑主线—财产权逻辑—的适用前提,而未被转化为原则的目标则只能在不违背主线逻辑的前提下设定和适用为该目标服务的规则,从而形成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逻辑支线。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原则
从根本上讲,关于财产权利的核心关注和讨论集中于权利的可实现性上。倘若是一般性财产(尤其是动产),那么这种财产权利的可实现性就在于其绝对的自主性。然而由于土地本身存在着多重属性和多重目标,这就决定了土地权利的可实现性需要面对多种限定。它不再导向该权利整体的自主性、绝对性,而会是倾向于在关键问题上确立绝对性。具体而言,能够统合各项目标的原则应是农民权利实现机会和承包经营权益的绝对保障,前者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目标的具体化和微观限定,后者则是对保护和增进农民财产性权利目标的落实,在两者的共同规定之下,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财产权逻辑的适用前提亦将得以厘清。
权利实现机会的绝对保障与集体所有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后者给定了集体农地权利的规范意义。需要指出的是,集体所有制根本不(应)否认自由和私权,它所担忧的并不是个体偏好的差异,而是由个体禀赋和机会差异所带来的足以制造绝对不平等的权力差异;它所拒斥的不是资本的流动和利用,而是资本化所裹挟而来的“无产化”风险,印度的土地私有化提供了显见的经验证据,它给印度带来的,一方面是地主和种植园主土地所有制条件下有三分之一农民没有土地,另一方面则是大量农村游击队和城市贫民窟[11]。因此,集体所有制的规定性是应当使农民对于农地权利的享有机会得到实质性保障,使其避免因某些经济权力的宰制而事实性地丧失权利(例如不可逆地转化为农业雇工)。值得说明的是,此种机会是无法仅仅凭借成员权得到保障的。实际上,所有权层面的身份性提供了一种抽象的实现权利的机会,但这种抽象的机会并不顾及不同权利主体之间实力差距,且作为一种集体性的所有权,它在相当程度上消解、弱化了单个主体的权利意志。因而我们才需要在另一个层次——土地承包经营权上提供资格的限定和保护,它是集体土地所有权身份性、资格性的具化和延伸。从反面推想,倘若土地承包经营权向一切主体敞开,一旦农民对其予以一次性处分,在“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以及由此导致的取消承包地再分配这一新的制度环境下,他将很可能仅仅保留抽象的名义上的“成员权”,其个人意志同土地权利的联系便很难再得到重建,不仅如此,同样值得警惕的是:农民通过一次性处分权利所获得的收益能够换取多长时间的生存保障或者是否能为其提供进入城市生活足够支持是极难确定的,尤其是当他面对的是实力远超过自己的资本势力时,其微薄的谈判能力很难为自己创造足够的选择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权利机会的排他性保障是有必要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落实的。这一原则将意味着:首先,在诸多权利层次中,所有权和权能最为完整的用益物权只能为农民所有,只有较低层次的农地权利对外开放;其次,农民始终保有土地承包经营的机会以及实现此机会的制度条件。值得申明的是,对于权利机会的绝对保障并不意味着塑造一种封闭的经营模式,也不应意味着土地承包经营权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目的的排除以及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质性取代[12]。
集体所有制为集体成员在所有权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两个层面提供了权利资格的保障,这也标志着它对于财产权逻辑的限定止步于此。此外,土地合理利用与粮食安全的目标也仅限定土地用途,只要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资格得到实质保障,土地用途不被违法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就应得到充分承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继承、转让和抵押上的不合理限制应当予以摒除。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权重构与制度选择
(一)三层次权利体系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目前,我国农地权利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是“三权分离”或“三权分置”,即所有权定归属,承包权确认资格,经营权用于流转、收益。其中的关键是实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此回应显著的“农村劳动力离农化趋势”和农业现代化需求,并化解目前二权合一制度安排下农民失地之虞同农地流转之需之间的矛盾[13]。更具体而言,它试图有所保留、有所变通地确认财产权逻辑。如前文所述,集体所有权层面所能提供的权利资格保障通常只提供某种抽象的机会,唯有当它可以转化为具体的、可由个体予以利用的权利时才能真正在农民的个体意志与农地权利之间建立起完整联系,因而确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权属性就是必然的选择。然而绝对的物权化将同时导致权利转让的自主性(不受限制地转让给任何主体)和承包关系的长久化(这将导致取消再分配,于是,承包经营权转让后承包关系改变,从而使得原权利主体丧失了重新取得权利的依据),这不可避免地会制造无地农民、农业无产者。为解决这一矛盾,只能再一次进行一种权利的拆解,确保无论如何流转,农民仍然能够保留农地权利回转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三权分置”的方案在基本思路上是较为清晰的,但在法权构造上仍然存在模糊:承包权与经营权同现行法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关系难以明确。如果仍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权就显得冗余,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本已蕴含了资格属性。如果废止土地承包经营权,经营权会同承包权成为集体所有权之下的并列权利,亦即经营权生成于集体所有权,这就将阻断经营权取得和流转同农民个体之间直接的法律关联。
更合乎逻辑、更严谨的法权设置是明确三权分层的思路。三个层次的权利分别为: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集体土地所有权是基础层次的权利,保障农地所有权由集体享有。同时,为了保障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可实现性,应该为发包权的行使留足制度空间,但它仍须以农户对承包经营权的放弃为前提,亦即当集体成员自愿同意采用集体经营的形式而不予发包时,集体可自行经营,与此同时仍然应当保障未同意者的承包经营权,以此实现“发包方与承包方的权利均衡”[14]。
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分别作为第二和第三层次上的物权。二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包含资格属性,具有承包期届满后请求重新获得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后者同样具有用益物权性质,但它在身份性上的限制将得到解除,并获得较为完整的权能——占有、使用、处分、收益。值得说明的是,土地经营权的创设并不违背物权原理。土地经营权建立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之上(而非集体土地所有权之上),其权能并未超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剩余权能的空间,且其设立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明确的暂时放弃权能的意思表示为前提,因而不会造成权利冲突以及物权受侵犯的问题。此外,让渡土地经营权后,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未就此成为空权利,由于承包关系不发生改变,承包经营权主体保留了在土地经营权届满时重获完整权能的直接依据;与此相反,如果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进行直接对外转让,当其权利期间届满,原承包经营权主体重新取得权利的依据和能力就已然模糊难定了。随着土地承包经营权同土地经营权的分层,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问题将由此得到解决,它实际上转化为土地经营权的继承,继承人将以个人名义取得土地经营权(但它会受权利期限的限定);另外,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和抵押也将不再受过度限制。
当然,逻辑性建构并不排除经验性考量。当土地经营权的身份性束缚被解除,它可能意味着大规模投机资本的介入以及经营体制的转向,并促成农村经济权力结构的实质性变迁,与此同时,现有政制体系下农民政治权力尚未真正形成,地方政府权力与资本之间的暧昧关系也尚未厘清,农民难以具备制衡资本权力的力量。接踵而至的问题可能就会是,农民保留名义上的土地权利,资本优势者占有了实际上的权利,与此同时,“雇佣农业工人”游离于劳动法体系,亦在契约关系中承担主要风险享有较低的利益份额。于是,一次权利解放的改革就有可能转变成一次权利转移。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摇身化为营利者与资本联合展开的历次“圈地运动”恰恰证实了这种危险的存在和延续[15]。有鉴于此,一种渐进稳妥的方案或许在于半敞开的土地经营权转让。在一定时期内,土地经营权的转让仅仅限于抵押权实现的情形以及向集体转让的情形,以此将农地转让市场限定在可控范围之内。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与权利再分配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是一个重要的权利再分配制度,它也符合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核心原则——权利资格的实质性保障,当权利期限届满,使尚未获得承包经营权的新成员或者既有承包经营土地显著不足的成员能够公平地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制度在三层次农地权利体系中仍会有关键作用:农民转让土地经营权的期限受制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剩余期限,因而享有土地经营权的主体无法永久性占有承包地从而排除农民的实质性权利,土地承包权期限届满后已经让渡土地经营权的农民重新获得了完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处分权利的自主意志。也正是由于此种保障性前提的存在,承包期内的调整仍将仅限于机动地。另外,现行《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有关承包地自治调整的强制性规定(《土地管理法》第14条第2款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7条第2款)也应修改为授权性规定,即“土地承包合同可以约定: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这有利于处理好农民自主意志与国家理性(父爱主义)之间的紧张,同时也有利于“遏制土地重新调整过程中的权力寻租和腐败问题”[16]。
不可否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性可能会弱化权利的财产性,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从“长期不变”到“长久不变”将会是未来制度调适的总体趋势。但在较短时间内,农民多耕地少的事实及其矛盾仍然难以改变,承包期届满后的权利再分配也仍然会是保障农民农地权利资格的主要手段。当然,当上述情况已然呈现出可以清晰预见的扭转趋势,那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也就不再必要,但它不会彻底消除所有的农地权利期限。届时,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将被转化为土地经营权的法定期限,以此避免农地权利在事实层面的永久性转让,与之相辅的是土地经营权期限届满后添附物的处置规则,为避免资本企业以添附物的处置成本为条件要挟农民无限次地续期,应将处置成本配置给土地经营权主体。
参考文献:
[1] 贺雪峰,刘金志.对农村土地承包期的思考[J].广东社会科学,2009(4):153157.
[2]刘俊.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探讨[J].现代法学,2007(2):170178.
[3]丰雷,蒋妍,叶剑平.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农村土地调整的制度演进及地区差异研究[J].经济研究,2010(5):418.
[4]汪洋.地承包经营权继承问题研究——对现行规范的法构造阐释与法政策考量[J].清华法学,2014(4):125149.
[5]陈柏峰.农地的社会功能及其法律制度选择[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2):143153.
[6]华生.土地制度改革六大认识误区平[J].经济导刊,2014(2):8688.
[7]黄宗智.“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J].开放时代,2014(2):176194.
[8]杜安娜.一个教授的农地考察报告[EB/OL].(20131030)[20150420].http://news.sina.com.cn/o/20131030/071928568896.shtml.
[9]杨·杜威·范德普勒格.新小农阶级:帝国和全球化时代为了自主性和可持续性的斗争[M].叶敬忠,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8.
[10]张兴军,马意翀.土地流转进入新常态,资本下乡跑马圈地现烂尾[EB/OL].(20150209)[20150420].http://house.ifeng.com/detail/20150209/50263764_0.shtml.
[11]温铁军.我国为什么不能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J].红旗文稿,2009(2):16.
[12]韩松.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J].法学研究,2014(6):74.
[13]刘守英.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土地制度改革及其实施[J].法商研究,2014(2):310.
[14]陆剑.“二轮”承包背景下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异化及其回归[J].法学,2014(3):95103.
[15]温铁军.中国地方政府的三次“圈地运动”[J].财经界,2014(10):4243.
[16]罗必良.农地产权模糊化:一个概念性框架及其解释[J].学术研究,2011(12):4856.
Abstract:Right to the contracted management of land is a key issue in the land law system. There are significant institutional conflicts and restrictions on right, because of multiple objectives and logic. When revising existing law, it is important to clarify the principles and logic of the right to the contracted management of land. This requires taking the logic of property rights as a main logical line of the institutions,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select and abstract the two principles from the objectives: to guarantee the chance of fulfillment of rights and to guarantee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on the contracted management of land. These two principals will be used to determine the applicable premise of logic of the right to the contracted management of land, and the other objectives which are not translated into principles should be applied only when they would not violate the main logical line. On this basis, the train of thought of the institutions reform will be clear. Right to the contracted management of land together with collective land proprietary right and right to management of land constitute a new system of rights. In this system, collective ownership should still be the premise of institutions, and right to management of land would be created based on right to the contracted management of land (not collective land proprietary right) to complete unfinished mission of the old institutions. In the long term, restriction on inheritance, transfer, hypothecation and duration of right to the contracted management of land would be weakened, and redistribution of right to the contracted management of land would absorb more autonomous norms. Nevertheless, out of empirical considerations, institution adjustment in the short term should resort to workaround.
Key words: collective land proprietary right; right to the contracted management of land; right to management of land; land re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