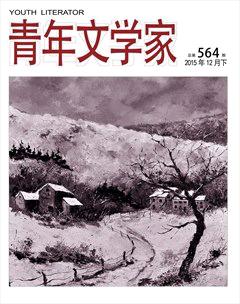由《战国策》的接受史解读古代儒学思想的发展
摘 要:自从刘向编订《战国策》以来,各代对其理解不同,褒者认为其“繁词瑰辩,烂言盈目”,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而贬之者则认为其有剧毒,应以儒学为之去毒。按照现代阐释学的观点,理解是在时间中发生的历史性行为。对《战国策》的理解的差异正见出其背景文化之一——儒学的思想变迁。本文以《战国策》的接受史为切入点,解读古代儒学思想的发展变迁。
关键词:《战国策》;接受史;儒学
作者简介:刘卫华(1977-),女,湖北京山人,湖北大学知行学院人文系讲师。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36-0-02
战国时期列国纷争,各诸侯国为了争做霸主,纷纷延揽人才以壮其国。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口若悬河的谋臣策士便登上了历史舞台,《战国策》就是一部记载策士言行的著作。其言恢宏谲诳、汪洋恣肆;其事权谋诡诈、耸人听闻,其人崇计重利、放言无惮。正是这些特点造成了《战国策》一书引起后人争议的地方,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古代儒学的思想变迁。
原典儒学产生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制社会,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他把人与人之间的宗法等级差别规范化、制度化、伦理化,以礼乐制人。
在对“利”的态度上,儒家学者多耻于谈利。《论语》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将对利的态度作为了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随后发展儒学的学者也同样如此,孟子说:“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董仲舒也曾说:“正其谊而不计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他们都认为应该以义制利,而不是见利忘义。战国策士则思想行为不受礼法拘束,崇计重利。当苏秦说秦不成归来时发出的感叹:“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就公开宣扬了积极追求功名富贵的思想。儒家重行仁义之事,崇尚君子之风。而战国策士则利用时势,利用权术,只要能达到目的,用什么手段是不必忌讳的,苏秦在游说齐闵王时说:“是以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夫权藉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权藉”、“时势”是他们致力之所在,他们虽然也说“圣人”、“仁义”,但他们从不把它看得至高无上,有时反而对之进行批评。
现代解释学认为“理解是一种在时间中发生的历史性行为[5]”,不存在超越时间和历史纯客观的理解,即任何接受史都要受到“先行结构”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一定时间和历史中的先入之见,本文就以《战国策》的接受史为切入点,解读古代儒学的发展变迁。
《战国策》最早由刘向校订成书,云:“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纵横长短之说,左右倾侧。”他指出了《战国策》产生的时代背景,是纷乱的社会中产生的乱世之学。他虽然高度评价了纵横家皆“高才秀士”,能“扶急持倾……出奇策异志,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但同时也指责这种乱世之学是“权于谋诈之弊,终无信笃之诚,无道德之教,仁义之化,以缀天下之心,……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是“救急之势”的权宜之计。
他的观点是有思想根源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从思想上控制了士人,“征圣”、“宗经”成了儒生所信奉的金科玉律,与此相反的纵横之学自然也没有了信奉的市场,趋于衰落。汉武帝对纵横之学特别反感,他策问严助时曾特别指示:“具以《春秋》对,勿以苏秦纵横!”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的刘向自然深受影响。
魏晋之际,欲代魏自立的司马氏打着儒家明教的旗号行不忠不孝之事,激起了士人的愤怒,他们提出“越明教,任自然”,放诞不羁,恣情越礼。在他们眼里,儒学成了一套僵死的模式,正如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描述的“服有例程,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例程。……扬声明于后世,齐功德于往古。”他们多崇尚老庄之学,品评士人的标准也与儒家截然不同,不再是行止坐卧皆有一套礼法规定的翩翩君子形象,而是任诞放达、狂放不羁。
在《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袁悦有口才,能长短说,……后丁艰,服除还都,唯齐《战国策》而已。语人曰:“少年时读《论语》、《老子》,又看《庄》《易》,此皆病痛事,当何所益耶?天下要物,正有《战国策》。”
袁悦将《战国策》当成天下要物,对《战国策》的高度评价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正见出汉魏之际儒学衰微,道家复兴的思想现状。
唐代三教并存,文人一方面把儒学当作立身扬名的途径,同时又从老庄玄学中吸取营养。儒学一直未能恢复独尊地位,这种局面直到才有所改变。
《战国策》的命运到宋代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宋代文人虽欣赏其文汪洋恣肆的语言及气势,但对其思想内容一直评价不高。其中突出代表是曾巩,他在《<战国策>目录序》中认为,刘向的论述虽然很好,但对其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大加批驳,认为是“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甚至认为战国游士“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变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弊其患。……而诸侯及秦用之,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莫之悟也。”他之所以要“访之士大夫之家,……尽得其书”,只是要“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这是采用了放而绝之的方法。至于其他人也大都作如是观,宋代李文叙在其《书<战国策>后》中虽认为“人读之必向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文辞极胜”,但同时也写到“《战国策》所载,大抵皆纵横捭阖、谲诳相轻、倾夺之说也,其事浅陋不足道”。叶适在《习学记言》中也评价《战国策》是“陋浅妄之夸说,……使与道德利益相乱,其为学者心术巨蠹甚矣”。
由上可见宋代文人多赞赏《战国策》的文辞之胜,且受到其“辫丽恣肆”文风的影响。但他们对《战国策》的评价仍然不高,无疑是受到当时理学的影响。
宋代继承韩愈的道统思想,重整儒学,儒学一变而为理学、道学。诗人多将儒家道统由外在的仁义教化内在的心性本体,甚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然而禁欲背后的物欲横流无疑是对趾高气扬的理学的嘲讽。道德观念不再是个人主观的欲求,而成为模式化的东西,儒学在发展中逐渐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而孔子则偶像化为令人们诚惶诚恐的“大成至圣先师”,与孔子的原典精神相去日远,在人性扭曲的时代当然会忌讳无拘无束的生命力,当然也会对《战国策》采取党同伐异的态度了。
明清时期,对《战国策》的理解同宋元没有太大的区别,一方面仍赞其语言之美,一方面对其思想倾向的批驳更加不遗余力。清代谭献在《复堂笔记》中评到:“《国策》乃沉而快,《国策》乃雄而隽。”高度称说其文字之美。而元代吴师道评价《战国策》是“相诈相轻,机变之谋,唯恐其不深”,则批驳其思想倾向。更有甚者,清初学者陆陇其选出《战国策》中的40篇文章,用孟子的观点一一加以批驳,书名就叫《战国策去毒》。
至此,对《战国策》的评说越来越远离文本的艺术价值,而注目于其思想内容是否合乎正统。这种情况显然与儒学的发展状况有关。明清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文人多避实就虚,不敢过问政治,于是儒学发展到明清一变而为明代的实学和清代的考据之学,专注于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在现实中,大多文人不再游离于王权之外,放弃了同王权的抗衡,于是在《红楼梦》的描述中,原初充满人情味的孔子成了泥塑木雕似的贾政。
显然从《战国策》成书以来漫长的历史中,其接受史也呈现了很大的差异,由于大多数文人是站在传统儒学的角度去评说《战国策》,导致儒学兴盛时,文人对《战国策》多持批驳态度,而儒学衰微时,文人则对《战国策》多加称颂,呈现了理解和文本的偏差,而这种偏差正可见出起其背景文化——儒学的发展消长。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1.
[2]孟轲.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
[4]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7.
[5]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6]班固.汉书·严助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刘义庆.世说新语·谗险[M].北京:中华书局,1991.
[8]阮籍.阮籍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9]曾巩.曾巩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胡如虹.论《战国策》的语言艺术[J].湘潭大学学报,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