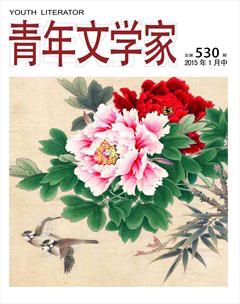《译者的任务》中的解构主义翻译观
摘 要:解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盛行于西方的一种哲学思潮,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则是在这种哲学大背景下产生的。它作为现代西方的新型译介理论,对传统的翻译理论毕露锋芒,高举“延异”、“解构”、“消解”的大旗,在翻译史上掀起了一阵“血雨腥风”。然而,早在30多年前,有一位大师——本雅明,在其文章《译者的任务》中就显示出了解构主义的火花。本文将着重探讨本雅明思想中呈现出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
关键词:《译者的任务》;解构;语言
作者简介:李涵瑜(1991-),女,山西省长治市人,天津师范大学2013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02--02
《译者的任务》是本雅明在1923年为自己所翻译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诗集《巴黎风貌》所做的序言。在这篇发表后一直默默无闻的序言里,解构主义翻译家发现了它与解构主义的相通之处,并将其视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奠基性文献。这篇晦涩难懂又充满宗教神秘主义色彩的文献被后人视为研究解构主义翻译的必经之地,保罗·德曼曾经说过:“如果你还没有对本雅明的这篇文章有所阐述,你就是无知之辈”。看似很狂傲和激进的一句话却淋漓尽致的把《译者的任务》的重要性显示了出来。
在这篇序言里,瓦尔特·本雅明依次谈论了五个方面的问题:1、顾忌受众无益的观点;2、原作的可译性问题;3、“纯语言”的构建问题;4、译者的任务和目的;5、对翻译方法提出的建议——《圣经》的逐字直译法。而“纯语言”则是整篇序言的核心和支架,围绕着这一问题,本雅明开启了解构主义的先声。
一、二元对立的消解
西方传统的哲学史可以说是寻找“逻各斯”的历史,形而上学的哲学寻找了许许多多的词来描述世界的中心:上帝、理性、本源、存在……这种思维形态本身就很容易导致二元对立的模式:比如说对/错,喜欢/讨厌,男人/女人等。而到了解构主义的世界里,德里达首先开启了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强烈批判,反对传统哲学意义上的中心与对立。
《译者的任务》中,在首段本雅明就振臂高呼:“没有哪首诗是为了读者而写,也没有哪幅画是为了观赏者而作,更没有哪部交响乐是为了听众而谱。”这是对作者和读者的二元对立的关系的消解,是对作者主体自由能动性的大大提升,作者不需要再考虑读者的因素而进行自由创作,写作的目的也不再是迎合市场或者读者,这对传统的创作理念以及读者与作者的关系都是一种很大的反叛。接着本雅明谈论了原作和译作的关系,给传统的翻译理论当头一棒,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忠实”作为一大翻译标准长期存在,译作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他依附于原作基础上,并以尽量准确完整的表达原作的意义和思想为己任。译者犹如是作者的影子,牢牢的和作者连在一起。而到了本雅明的翻译世界里,译作和译者成了独立于原作和作者的存在,他们的地位甚至高过原作和作者而且拥有了完整的鲜活的生命。“译作因为原作而产生——然而却不是原作的现世,而是原作的来世……译作总是标志着原作生命的延续……原作的生命之花在其译作中不断获取活力,并以最新、最繁盛的姿态永远盛开下去。”作为“先锋”的翻译理论,它瞄准传统翻译理论中二元对立的思想,消解作者和译者,原文和译文的对立关系,从而把译者和译作从传统翻译中的依附地位中解放了出来。
在这篇序言里,本雅明有一个非常贴切完美的比喻,他把原文比作一个圆,把译作比作一条切线,它和原文在一个切点上重合,但是之后就靠着自己的轨迹发展,所以说,翻译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模仿和复制,它有着自己的生命,并在自己的生命上进行着无止境的旅行。而这一神圣使命的实践者就是译者。
至此,本雅明从一种大胆的,理性的,严肃的眼光出发,对传统的翻译理论进行了一次大颠覆和大换血。这篇序言于1923年刚刚发表的时候,没有人想到它会成为解构主义思想的萌芽以及研究西方翻译理论的必读之作,正是这种在当时不被理解的叛逆之言被同样新潮的德曼和德里达发现并进行阐释,它对于二元对立的消解与之后的解构主义理论不谋而合。这一在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的翻译理论成为20世纪后半叶盛行理论的先声。
二、“语言”地位的提升
进入20世纪,西方文论上出现了又一次大转向,即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在这次的转向大潮中,从哲学思想到文学作品、文学理论,无不喷涌着对语言的热情,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被西方许多学派的理论家所运用,或以它为蓝本进行文论的深化,或者对它语言学方面的某些问题提出质疑。20世纪的西方把语言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19世纪的“理性”在语言的光照下没落退出。伴随着语言中心地位的取得,对文学文本语言的结构、形式、意义的解读远远超过了对文本本身意义、内涵、结构的理解。能指、所指、语言、言语等词汇成为新时代的代名词。
“延异”(differance)是德里达创造出的一个新词,这个词汇的出现对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概念进行了消解,所谓延异,就是说意义的产生不是本身就有的,而是在一系列的能指的滑动中得以实现的。具体来说,延异包含三个方面的内涵:第一,符号即能指的差异性决定语言的意义,能指只是不停地指向其他的能指;第二,意义的确定性是没有的,意义处于不停的“扩散”中;第三,意义的无穷延宕性,一切文字都是在“播散”过程中,他们不指向符号本身以外的任何东西,只是能指链条之间的滑动。这个“延异”的观点使得传统的文字传情达意的功能得到了瓦解和挑战,在解构主义的世界里,文字不仅不表达确定的意义,反而却成为无休止地瓦解文本的工具,由此,通过“延异”,解构主义滑入了一个意义无穷,幽深曲折的符号世界。
在《译者的任务》中,本雅明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纯语言”。这个概念包含了本雅明本人的文论思想、哲学宗教思想等多方面的内容,它也是理解本雅明翻译理论的关键。“纯语言”这个概念是具有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的,这个词最早出自《圣经·旧约》,诺亚的后代们使用一种同样的语言,他们齐心协力想要建造一座“巴别通天塔”,上帝大怒,于是就让人们突然之间使用不同种类的语言,通天塔的建造也就就此告终。本雅明本人就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这则基督教的经典之作也为本雅明的语言共源性和语言差异性提供了基础,而语言的共源性是本雅明语言观的基石。“语言间一切超历史的亲缘关系都藏于某个整体意图中。这个整体意图是每一种语言的基础。……这个总体就是纯语言”由此看来,所谓的“纯语言”就是存在于人类世界中的语言共通性。
“纯语言”的实现要依赖于翻译,在翻译的各种过程中,不同的语言处于激烈的碰撞和冲击中。由此看来,本雅明翻译中对于语言的重视与解构主义的语言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传统翻译中忠实原则的叛逆与解构主义的意义不确定有着很大的相似。而且本雅明主张将意指对象和意指方式分开,和解构主义对索绪尔提出的“能指”、“所指”的分离不谋而合。而且不论是本雅明还是解构主义理论家,他们都打破了文本的同一性、确定性。
如果一概而论,将本雅明看做是解构主义的代表或者认为本雅明的思想和解构主义完全一致,这是不对的。因为,单单从《译者的任务》来看,本雅明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还是有区别的,首先,解构主义主张打破一切,是没有中心的,而本雅明虽然对意指方式和意指对象进行了分离,但他的翻译理论还是有中心可言的,那就是他反复提到的“纯语言”或者说是“上帝的语言”。其次,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没有提出具体的翻译方法,而本雅明却提出逐行对照和逐字翻译的原则。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本雅明《译者的任务》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是有着很深的思想渊源的。不管是对二元对立的消解还是对语言的重视,它都开启了解构主义之风。当年的默默无闻确是如今的声名赫赫,无论经历多少年,经典终究都是经典,也永远不会被磨灭。
参考文献:
[1]《本雅明文选》[M],本雅明著,陈勇国、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译介学导论》[M],谢天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3]《本雅明翻译思想研究》[M],周晔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
[4]《本雅明翻译观与解构主义的形神探析》[J],朱林,安徽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
[5]《纯粹的诗意和哲学——论本雅明的翻译观》[J],吕姣荣,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