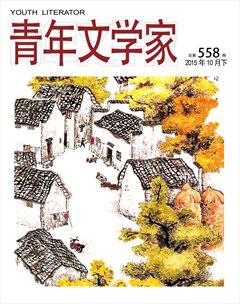城乡对峙下人性的复苏与回归
张倩
摘 要:通过细读沈从文的短篇小说《丈夫》,笔者从丈夫身份的缺失、丈夫人性的觉醒以及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三个方面解读沈从文笔下的城乡对峙下乡村男女从人性的蒙昧最终走向人性的复苏与回归的过程。
关键词:身份;人性;二元对立的城乡观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30-0-02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坛的重要作家,他倾其一生创作以湘西农村为题材的作品,描写当地质朴健康的牧歌式生活方式,歌颂人性的真善美。他崇尚生命,崇尚美好人性,但“他并没有将这种人性片面夸大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单一存在。他发现了湘西乡村社会人性的金子,同时也看到了这种金子与泥沙混杂在一起。”在《丈夫》这部小说中,沈从文用细腻、淡然的笔墨倾力写出了城乡对峙下乡村男女从人性的蒙昧最终走向人性的复苏与回归的过程。
一、丈夫身份的缺失
当丈夫来到城里初见老七时,看到她那城里人的打扮和神气派头,丈夫第一次感到了自己身份的缺失。直到老七问起钱,问起家乡豢养的猪,“这做丈夫的看出自己做丈夫的身份,并不在这船上失去”。其实此时丈夫的身份已经在他的内心中走向了缺失,他的内心深处是在怀疑自己的身份的。
当水保来访时,丈夫介绍自己是“老七的汉子”,小说全篇也始终不曾出现过丈夫的姓名,他始终是以老七的丈夫这层关系而存在的,丈夫从来没有独立的身份。而水保毫不客气地让丈夫转达给老七“告她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时,则赤裸裸地向丈夫宣布了他对老七的使用权。此时丈夫的身份在外人眼中已然缺失。
水保的挑衅激起了丈夫的嫉妒和愤怒,丈夫决意走路时遇到老七,“你走哪里去?”“我——要回去。”“教你看船也不看,要回去,什么人得罪了你,这样小气?”“我要回去,你让我回去。”“回到船上去!”“回去也好,回去也好。”从丈夫与妻子的这一段对话中,我们看到了妻子强势的命令与丈夫怯懦的遵从,丈夫与妻子的角色颠覆了传统社会中的夫妻形象,而丈夫的身份在妻子的面前也呈现出一种缺失的状态。
在看望老七的第一个晚上,船上来了客,一上船就大声地嚷要亲嘴要睡觉,而此时的丈夫却不必指点,自觉地往后舱钻去,“躲到那后梢舱上去低低地喘气”,在大娘陪同玩过后,丈夫上船时,“小心小心地使声音放轻,省得留在舱里躺到床上烧烟的客人发怒”,而到要睡觉的时候,丈夫则“悄悄地从地板缝里看看客人还不走,丈夫没有什么话可说,就在梢舱上新棉絮里一个人睡了。”第二晚,丈夫、老七、大娘和五多在船舱里欢乐地拉琴、唱歌,却被两个喝得烂醉的兵士打断,前来闹事,一船人都吓慌了,而此时的丈夫却“夹了胡琴就往后舱钻去”,让三个女人来应付这个烂摊子,任由妻子被辱骂、被蹂躏。在沈从文笔下,此时的丈夫已不是一个真正的丈夫,她的丈夫身份已不只是在外人(水保)、在妻子面前走向缺失,更是一种从自身走向的缺失,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身份的丧失。
而丈夫身份的缺失在作品中是通过失语的状态得以呈现的:面对妻子的失语,始终不曾同妻子在枕边说说家常私话;面对嫖客的失语,总是嫖客一来就自觉钻到船的后舱里去,任由妻子被嫖客凌辱。而丈夫唯一的一次畅所欲言则是面对水保这个嫖客,末了还被水保嘱咐“告她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我们看到了沈从文在作品中所寄寓的深深的讽刺,看到了他笔下丧失了身份和话语的丈夫深深的悲哀,而身份的缺失实则揭示了丈夫蒙昧的人性,丈夫正是因为蒙昧才一步步丧失了自己原本的身份。
二、丈夫人性的觉醒
“事情非常简单,一个不亟亟于生养孩子的妇人,到了城市,能够每月把从城市里两个晚上所得的钱,送给那留在乡下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在那方面就过了好日子,名分不失,利益存在。所以许多年轻的丈夫,在娶媳妇以后,把她送出来,自己留在家中耕田种地,安分过日子,也竟是极其平常的事情。”
将年轻的妻子送进城里当船妓已成为黄庄的传统或是习惯,这种习惯使得黄庄的丈夫们进入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他们并不曾思考妻子的船妓身份对自己丈夫身份的威胁,对自己男性尊严的践踏,只是单纯地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生命呈现出一种没有进入意识层面的半自然的习惯状态。送妻子做船妓的行为似乎成为黄庄约定俗成的事情,从未有人质疑这一行为的合理性。而丈夫们则在习惯的引导下处于一种蒙昧的无意识状态。丈夫在乡里种田耕地,妻子在城里做船妓讨生活,原本应该以爱情为基础的夫妻关系在生存压力的逼迫下转变成了维持基本生存的经济关系,丈夫对妻子的权利也仅为女人名分、生的儿子和钱财,妻子俨然成为丈夫的生育机器和赚钱工具。而这种生存压力来源于城市畸形的商业经济模式,乡下人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被无奈地纳入到城市商业体系之中,农村原本的供需平衡状态被打破,从而使得乡下人的生计难以维持,生存受到威胁。
老七的丈夫也是众多蒙昧的丈夫中的一位,理所应当甚至是欢喜地将老七送去城里做船妓,然而在来到城里探望老七的三天里,在嫖客们一次次地“挑衅”下,终于走向了意识的觉醒。
丈夫来到船上的第一个晚上,来了客,一上船就大声地嚷要亲嘴要睡觉,然而丈夫关注的却是来客的势派,他想起的仅仅是村长同乡绅那些大人物的威风。
然后就自觉地钻到后舱里,“如今和妻接近,与家庭却离得很远,淡淡的寂寞袭上了身,他愿意转去了。”丈夫的感受也仅仅是没有妻子陪伴的淡淡的寂寞,而在半夜,妻子给丈夫含了一小片糖后,丈夫就释怀了,“尽她在前舱陪客,自己仍然很平和地睡觉了”。当水保来寻老七,并嘱咐丈夫“告她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时,丈夫依然没有被触动,只想着水保的尊贵,“他猜想这人一定是老七的熟客。他猜想老七一定得了这人许多钱。他忽然觉得愉快,感到要唱一个歌了,就轻轻地唱了一首山歌”。丈夫将一个对妻子的嫖客视作尊贵的人,视作财神,甚至面对水保的公然挑衅还愉快地唱了两支山歌,丈夫的愚昧在此达到了一种极致。然而水保毫不客气的嘱咐终于激起了丈夫姗姗来迟的嫉妒和愤怒,丈夫的意识在渐渐地苏醒。当丈夫决意走路时遇到妻子归来,面对妻子强势的态度和一把特意买给他的胡琴,丈夫幽幽地说着“回去也好,回去也好”,就跟了媳妇的身后跑到船上。丈夫原先的嫉妒和愤怒只不过是一种原始的情绪,而并非作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思考后的情感,丈夫仍然处在不曾开启的心智中。所以当第二晚两个烂醉的兵士前来闹事时,丈夫“夹了胡琴就往后舱钻去”,任由妻子在前舱被那两个酒疯子凌辱。但当丈夫听到大娘说老七同那两个兵士睡了时,丈夫沉默了,从被迫的失语走向主动的沉默意味着丈夫的意识被触动了,丈夫开始思考了,开始反思这长期以来“合情合理”的船妓传统了。而丈夫最终的觉醒是在半夜巡官查船后,丈夫想同妻子在床上说点儿家常私话,却又被嫖客巡官打断不能如愿之际。丈夫一早起身执意要回家,再也不能被妻子劝住,面对妻子递给他的七张票子,他“摇摇头,把票子撒到地下去,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捂着脸孔,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原本送妻子去做船妓是出于维持生存的经济目的,在经济与情感的对峙中,经济利益合情合理地成为丈夫的追求,而当丈夫把钱撒在地上的那一刻意味着丈夫已经意识到他和老七之间这种畸形的夫妻关系,经济的满足是无法建构起夫妻关系的,夫妻间需要的是情感的维系,是朝夕相处、共话桑麻的爱情。丈夫带着妻子回乡下了,蒙昧的丈夫在嫖客们一次次无所顾忌地挑衅下终于走向了人性的觉醒,也许这并不是深刻的觉醒,但至少他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作为一位丈夫的身份,夫妻间的爱情远胜于经济利益,认识到了湘西长期以来的船妓习俗的不合理和不可接受性。
三、物质与情感的对立,城市与乡村的对峙
作品中两次从丈夫的视角出发,对嫖客们的衣着打扮进行了细致的描述。第一晚的嫖客“穿生牛皮长筒靴子,抱兜一角露出粗而发亮的银链”;第二天来的水保“那一对峨然巍然似乎是用柿油涂过的猪皮靴子,上去一点儿是一个赭色柔软鹿皮抱兜……手上有颗奇大无比的黄金戒指”。沈从文选取丈夫这种对衣着等物质层面的关注的视角突显了作品中内置的物质与情感的二元对立结构。
作品中一共出现了四次物质与情感的对立。第一次是丈夫刚从乡下来到妓船上时,他的烟管被妻子夺去,被妻子塞了一只“哈德门”香烟,丈夫便一直吸着那有新鲜趣味的香烟。然而晚上嫖客来后,丈夫躲到后舱里,便“把含在口上的那支烟卷摘下来”了。第二次是妻子去陪客后,丈夫感到十分孤寂,“他愿意转去了”,可是半夜里当妻子塞了一小片糖给丈夫后,丈夫就释怀了,和平地睡去了。第三次是水保临别时的嘱咐让丈夫感到妒忌和愤怒,但当妻子从岸上回来带给他一把胡琴时,丈夫的气便消了。“先是不作声,到后把琴搁在膝盖上,查看琴筒上的松香。调弦时,生疏的音响从指间流出,拉琴人便快乐地微笑了。”在这三次物质与情感的对立中,丈夫的惊讶、孤寂、妒忌、愤怒最终都消融于物质的感官享受中,物质在与感情的对峙中始终占据上风。直到第四次,半夜里巡官来访后,丈夫一早起身决意要走,妻子将七张票子塞到丈夫手里时,丈夫的情感没有被物质收买,将票子撒到了地上,此时情感超越了物质,也预示着丈夫人性的觉醒。作品中这种物质与情感的二元对立暗含了沈从文二元对立的城乡观。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沈从文眼中,城市是堕落的,腐化的,是罪恶之城;而乡村是纯朴的,真挚的,是美好之乡。在作品中,丈夫虽然愚昧,但是却简单淳朴,相反,作品中的城里人却在沈从文笔下呈现为嫖客的形象:耽于淫乐的船主或商人,虚伪的水保,烂醉如泥、骂着脏话的兵士,贪婪的巡官……而纯朴的乡村人也因为来到了城市才被物化,才走向堕落,“做了生意,慢慢地变成城市里人,慢慢地与乡村离远,慢慢地学会了一些只有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于是妇人就毁了”。沈从文信仰生命,崇尚自然人性,用其一生的创作歌颂着那种不为社会现存的有形秩序与无形观念压制扭曲的自由意志,歌颂着一切从爱和美出发的人类本性。而乡村在沈从文眼中顺应和承载了人的天性,是孕育人性美的摇篮,相反,城市作为一个充满了秩序与规则的牢笼则扭曲了人们美好的本性,人们深陷其中便自然会走向毁灭。因此,沈从文在作品的结尾以夫妇向乡村的回归喻示了夫妇二人人性美的回归。
丈夫从人性的蒙昧走向人性的复苏,从身份的缺失走向身份的重建,从虚伪的城市回归质朴的乡村,在沈从文二元对立的城乡观中,美好的人性终归战胜了物质的束缚,呈现为一种自然的和谐状态,他始终用他细腻、淡然的笔触构造着他心中的“希腊小庙”。
参考文献:
[1]沈从文.丈夫[M].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
[2]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长沙:岳麓书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