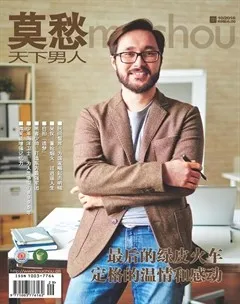提取干细胞再造牙齿
两次艰难的抉择
13岁上高中,15岁读大学,19岁三千多人的中美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联合招收国家公派留学生项目考试中取得第一名,1985年,裴端卿带着优异的学习履历留学美国。
17年后,裴端卿在明尼苏达大学主要从事基质金属蛋白酶与肿瘤侵蚀转移关系的研究。37岁的他已是明尼苏达大学的终身教授,是业内闻名的肿瘤专家。
2001年,裴端卿到英国参加世界癌症研究学术会议,在那里他遇见了留美同学陈凌。陈凌博士是著名的艾滋病疫苗专家,他告诉裴端卿:“中国在癌症研究领域因为缺乏高尖端人才,在世界相关领域学术界没有话语权,中国每年都要花费巨资从国外引进科研成果,那都是老百姓大把大把的血汗钱啊。”看着陈凌痛心的样子,裴端卿心里一疼,他当即决定回国报效国家。
得知裴端卿要回中国,他的美国导师和朋友都来劝他:“你在美国已经拥有了非常高的社会地位,并且拥有自己的实验室,研究经费也非常充足。你现在回国,一切要从零开始,你打拼这些年,为的是什么呢?”
裴端卿打电话给父亲说自己想回国,父亲高兴地说:“孩子,做人不能忘本,你现在学到了真本领,早就应该报效国家了啊。”
2002年年初,裴端卿回到中国,先是在清华医学院就职。“非典”后,他应邀担任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副院长。
裴端卿再一次面临了抉择:是继续自己在美国早已轻车熟路的研究,还是选择第三代医疗技术革命中的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基础研究?选择前者意味着功成名就,选择后者可能就意味着一辈子默默无闻。
看着辗转难眠的裴端卿,妻子说:“端卿,非典中那些在痛苦绝望中无法救治的人你还记得吗?你在美国从事的研究中国有人在做,而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在中国则是医学空白,你选择医学空白领域去做,意义更大。如果不能研究出成果,我们付出了,也不会后悔。”看到妻子这么支持自己挑战医学空白,裴端卿下了决心,“说实话,那时心里有些患得患失,后来妻子的话,让我感到科学研究需要一种淡泊名利的心,才能让自己义无反顾投身到科学研究中”。
尿液中找到“不老泉”
科学研究要想取得世界级的学术成就,需要拥有科研领袖级的战略眼光。中国在干细胞领域的研究起步太晚,与世界距离颇大,然而从IPSC(诱导型多能性干细胞)切入研究,一起步就能站在世界的前沿。
裴端卿组建起了团队,可是大量的基础性工作没有相关的人才去做。裴端卿心急如焚,他向国家有关部门的领导建议说:“从医学院毕业生中选拔相关人才来不及了,能不能举办一个培训班,从医学院大四学生中找一些人我来负责培训,直接让他们介入干细胞的研究?”领导同意了他的请求。
就这样,裴端卿白天带着一大帮学生做实验,晚上给他们上课,恶补相关知识。曾有一段时间,研究进入攻坚阶段,裴端卿每天只能睡三个小时。常常他从实验室回家时,街道上早起的人们已经开始了新一天的生活。
一份汗水一份收获,2006年,裴端卿和他的团队终于发现了维生素C对IPSC诱导的神奇功能,一举将体细胞中的IPSC诱导率由十万分之一提升到十分之一。其中培养基里添加维生素C可提高重编程效率这一理论研究成果,被世界权威杂志《Cell Stem Cell》选为封面文章。
此后,裴端卿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瓶颈期,研究成果迟迟不能转化为现实。队伍中有人开始懈气地说,这样的研究永远是在云端上。裴端卿想尽办法鼓舞士气,小时候父亲讲给他的励志故事,被他一遍遍讲述给自己的团队、同事、学生听。
在后续研究中,裴端卿的论文再登《Cell Stem Cell》封面。这篇论文的核心意义是:在显微镜下,起始纤维细胞经过几天诱导后,陆陆续续变成了上皮细胞,并由此得出干细胞的形成是由间质-上皮细胞转换(MET)来启动的假说。这一假说的证实论文在《Cell Stem Cell》发表,并被科技日报评为我国2010年十大科技新闻之一。
不可思议的是,在一次实验中,裴端卿偶然发现人的尿液含有上皮细胞,并能高效诱导为IPSC。这个史无前例的发现,在裴端卿的团队里引发了一次科学的狂欢。
于是,裴端卿给自己的科研团队制定了一个充满挑战的计划,利用尿液里的细胞再造一颗人类的牙齿。按照裴端卿的最初设想,人体的多能干细胞和相关细胞结合就能形成所需要的人体器官。
裴端卿团队列出了上百种可能的牙齿再造方案,从中,他们又筛选出了十种方案进行探索,每一个方案都进行了数百次尝试,而每一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经过数千次的实验,在不断地失败中,裴端卿发现,将这个看似万能的“多功能干细胞”直接和牙齿的成牙细胞结合似乎很难行得通。
裴端卿向他的美国导师求助,导师告诉他调整一个思路试试:利用干细胞分化成的上皮细胞再次合成牙齿。
一语惊醒梦中人,裴端卿按照导师提供的思路重新进行了实验,三周过去了,成牙终于形成。那晚的实验进行到凌晨四点,当那颗具有人的染色体基因、符合人类牙齿正常结构的成牙栩栩如生出现在容器中时,所有的实验人员全都像孩子一样大呼小叫起来。走在回家的路上,看着已经车水马龙的不夜城,裴端卿第一次发现凌晨四点的这个城市竟然这么美丽。
“再生牙的成功使多能干细胞的重塑有了更多的可能,这些干细胞与滋养细胞共同培养,可以进一步变成血液细胞、骨细胞、皮肤细胞、肝细胞以及神经细胞等。” 也就是说,在不远的将来,科学家或许就可以将这些分化的细胞移植到人体损伤部位以便替换衰老的细胞和组织,实现延长人类生命的奇迹。
不能在探索未知领域的竞赛中缺席
在裴端卿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块标有“共产党员岗”的牌匾。桌后面的墙上,则贴着一幅他用小楷工整抄写的《沁园春·雪》。在遇到科研难题的时候,他会一再背诵这首词,勉励自己和同事战胜困难,勇往直前。
呕心沥血换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回国后的这段时间里,裴端卿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发表在各大国际期刊上,共计70篇论文,引用多达3000余次。
引领医学前沿的研究被一些机构看上,他们找到裴端卿要求合作,国内一家上市医药集团对他说:“你来做我们的研究顾问,年薪2000万。”而裴端卿在广州的住房是普通的三室一厅,两间卧室一间书房,有时老父亲来看他,只能在客厅里打地铺。他数次拒绝了反复登门相邀的人,对方看着他简陋的住房,无奈地摇头走了。
美国斯坦福大学也向他发出了邀请,并许诺提供国家级的实验室,永久美国绿卡,给他的爱人和孩子解决工作,裴端卿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当初回国就已确定终生要为国家服务,高薪和美国绿卡固然诱人,但我有我的追求。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作为科学研究这项复杂浩大的工程,仅靠一两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事业。因此,裴端卿以极其开放的态度打造了属于时代要求的“中国团队”。
西班牙籍科学家米格尔在美国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与裴端卿一见如故。米格尔是肾癌研究专家,裴端卿邀请他到中国来工作,没有想到,米格尔竟一口答应了。到中国后,米格尔在裴端卿的影响下,放弃了擅长的肾癌研究,投身干细胞领域,并取得了许多轰动性的突破,成为第一位非华裔的国家重大研究计划973首席科学家。
2016年年初,裴端卿入选“2015年度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科技创新人物”。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的毕业典礼上,他对一千多名毕业生语重心长地说:“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基因组技术、干细胞技术以及基因编辑技术是能改变人类未来的技术。你们赶上了中国最好的时代,你们要记住,中国占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我们不该也不能永远在人类探索未知领域的竞赛中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