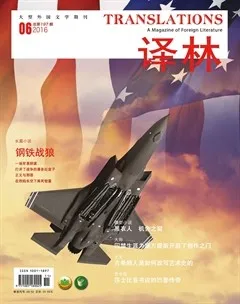律师为何推崇莎士比亚
2015年12月,奥斯卡·皮斯托瑞斯被判谋杀罪名成立,南非最高法院审判长埃里克·利奇称此案为“莎士比亚级别的人类悲剧”。这个评论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刀锋战士”从巅峰坠入谷底的生命弧度。这位残疾人运动员身残志坚,曾克服身体缺陷达到“奥林匹斯之巅”,接着他与美丽的女模特坠入爱河,却最终在情人节枪杀了她——这样戏剧化的转折在我们“吟游诗人”莎士比亚的剧中也该有一席之地。皮斯托瑞斯对窃贼的过度疑虑是他悲剧性的人格缺陷,这种缺陷却由他对枪支的极度痴迷得以证明。今年7月6日,他被判6年有期徒刑,一代巨星从此陨落。

皮斯托瑞斯一案实在极具莎氏风格。事实上,除了埃里克·利奇,很多法官审理案件时都曾引过莎剧中的话。2012年,一个青年由于在推特上发帖开恶意玩笑被判刑(2010年1月,英国南约克的罗宾汉机场由于大雪关闭,这引起27岁的保罗·钱伯斯的不满。他在推特上扬言最后给机场一周时间,否则要空中炸机。后来钱伯斯被逮捕,引发舆论争议,2012年7月,英国高等法院驳回起诉),但后来英国高等法院模仿《李尔王》中的句子,提出社交媒体用户应该“有自由说他们想说的话,而非说他们必须说的话”(出自《李尔王》第五幕第三场),从而推翻原判。2008年,英国法官赛德利在解决邻里土地所有权纠纷时,称那块地是“一小块徒有虚名毫无实利的土地”(出自《哈姆雷特》第四幕第四场)。法国某法院讨论刑事责任时则引用了《哈姆雷特》中的另一句话——“我说这全要怪我的疯病”(出自《哈姆雷特》第五幕第四场)。参议院萨姆·欧文在水门事件听证会上引了《亨利八世》(虽然他把出处误说成《亨利四世》)中的话。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谋划者之一焦哈尔·萨纳耶夫被正式判处死刑时,联邦法官乔治·奥图尔援引《尤利乌斯·恺撒》评论道:“人们做了恶事,死后免不了遭人唾骂,可是他们所做的善事,往往随着他们的尸骨一齐入土。”在这些例子中,正是莎剧台词的使用为审判程序增添了启发性,使之不再呆板单调,也更容易被人接受(当然,有时引经据典只是画蛇添足式的炫耀。比如在1978年,杰拉德·费茨莫里斯法官用了“一个极为肯定的答复”这个词组时,执意要加上脚注注明出处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场第二幕第43行)。
鉴于莎士比亚花费更多笔墨来讨论法律行业问题而非其他行业的问题,律师们推崇莎士比亚也在情理之中(他对于法律了解得如此详尽,有些人甚至认为真实的莎士比亚必定当过律师)。斯科特·多德森和艾米·多德森去年合作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对象是美国现任九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研究目的是选出“最具文学素养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并评出被他们引用频率最高的作家。结果,“引用最泛,阅读最广”的大法官是安东尼娅·斯卡利亚;而不出所料,作家中莎士比亚的被引率高居榜首,与之并肩的还有路易斯?·卡罗尔。这两位大家在其中五位大法官的引用量中各占了16次。受大法官们欢迎的其他作家还包括乔治·奥威尔、查尔斯·狄更斯、阿道司·赫胥黎和伊索(没有女作家位跻前十)。
未来的几十年内,只要诸多大学(尤其是英美大学)仍将莎士比亚作品纳入它们的法律教学中,莎士比亚的语言很可能将继续回荡在法庭里。哈佛大学法学院开办专题会议专门讨论“莎剧中的正义与道德”;伦敦国王学院的“莎士比亚与法律”模块课程由文学系和法律系老师合作授课,以探求“法律对于协调社会中个体地位的意义”。这种现象有其合理之处。南安普顿大学的专家解释道,他们以文学为载体,让法学院学生通过莎士比亚、狄更斯、卡夫卡和其他文学巨匠的作品来学习法律,是为了“培养更具职业伦理的法律人”;戴维·科莫·基德和伊曼纽尔·卡斯塔诺的研究宣称,阅读文学作品使人更能将心比心,摈弃成见,灵活决策。不难看到,这些品质对于法律工作者都是极为可贵的。此外,对文学的敏感性还有助于律师们写出结构清晰、观点鲜明的法律文书。
那么,莎士比亚作品为何在法律界被最为广泛地引用,并对法律思考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正如罗伯特·彼得森在论文《莎士比亚与律师》中所言,在美国法院的800多份司法意见书中,莎士比亚的所有戏剧——即便是相对不出名的《两个高贵的亲戚》和《雅典的泰门》——都或多或少被提及。原因之一是莎士比亚被视为高雅文化的化身,引用他的话加强了判决的可信度,也易于激发听者的历史感。彼得森注意到,莎士比亚“从根本上推动了案件的裁定”,将审理程序推向人们似曾相识的尾声。莎士比亚的普适性则是另一个原因。像《哈姆雷特》这样的戏剧,人们大多读过,即使没读过的人也要强说自己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已经成为全球通用语,即使对于不熟悉文本的人,“莎士比亚悲剧”这个术语也能引发他们关于人世无常、盛极而衰的联想。皮斯托瑞斯枪杀女友当晚各种骇人的细节,置于莎剧某个众所周知的框架中,才能使法官们和社会大众更好地理解这场无谓的流血事件。不管怎么说,斯人已逝400年,本·琼森对他的赞誉依然中肯如故: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智慧“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