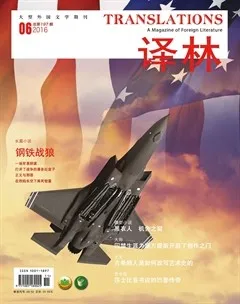人与性的悖论
这篇文章的灵感,源于一本书和一款手机。
书名叫《万年性爱》,手机叫苹果6s。两样东西横空出世,斑驳耀眼,令人浮想联翩。浮想之余,问号连连。
先说由慕尼黑南森和皮卡德记者团队撰写,埃克文出版社今年6月中旬发行的作品《万年性爱》(Zehntausend Jahre Sex)。这本新鲜出炉的专著大挥笔墨,从描写公元前1150年上埃及尼罗河畔的底比斯古城黄色场景开始,到评估公元350年前后镶嵌在西西里岛一座城堡马赛克地板上那群神秘女郎身着的比基尼用途;从渲染1721年被处死的德国变性人卡特琳娜·玛格利塔·林奇的离奇故事,到谈论英国医生约瑟夫·莫提默·格兰维尔于1883年发明的性按摩棒,大大方方,坦坦荡荡地深入人性最私密的角落。最后,此书还与时俱进,介绍了2014年闪亮登场的Tinder应用软件。这个交友聊天、幽会约炮的网络平台,眼下火爆无比。
面对男欢女爱的话题,《万年性爱》一书自始至终的风格,都显得很传统,很经典。即便大谈古希腊人的双性恋,古印度那地界儿的下流事,古罗马人的性高潮,中世纪的暗室,猫肠子做的避孕套,弗洛伊德的雪茄,伟哥的效用,甚至女人的阴毛,都没有离开人类的食色性本色。在亦庄亦谐、栩栩如生地陈述性史时,《万年性爱》以人为本,拿到书店的话,可以堂而皇之地登上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或文学的大雅之架。按流行术语来说,《万年性爱》并不奇葩。
奇葩的,是去年9月入市的苹果手机6s。此物貌似与文章主题无关,却玄机暗藏。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苹果手机6s有几款颜色颇受青睐,比如太空灰和玫瑰金,尤其是后者。事实上,玫瑰金人气之足,当刮目相看,也值得玩味。何以此款手机男女咸宜,不仅淑女喜之,君子亦求之?
玫瑰金,一种集性感与冷艳于一体的色泽,可谓既温柔,又寒气逼人。它的横空出世,意味着什么?如果留心一番眼下的女人时装和化妆品世界,人们不难发现苹果公司的良苦用心:这玫瑰金并非空穴来风,或先锋前卫,而是紧随潮流的炫酷!在这个炫酷的空间里,金属君临天下,已然成为无处不在的关键词。这个关键词在似是而非的刀光剑影里,演绎冷峻的魅力。它一反生硬常态,温文尔雅,甚至不可或缺地定义着女人的性感概念。
笔者想问的是,当今人类追慕的性爱世界,究竟还是不是《万年性爱》所描绘的那个以人为本之地?《万年性爱》的作者们真的与时俱进?或者早就落伍?或者,他们怀揣明亮,甘做埋首于沙堆的鸵鸟,以规避直面21世纪渐行渐远,走向异类的性世界?苹果手机6s的玫瑰金是否在暗示,当今人与性的关系,正剥离人的本真,走向一种可怕的悖论?
以笔者在欧洲的观察,?眼下最抢人眼球的性感女郎,常常一副金属人扮相:钢指甲,铬口红,亘古常青的宇宙人面孔。她们的服饰和手袋之类的,也常在金属扎眼的锐利里,找到与面部色彩般配的瑞丽风光。莫非摩登女性追求的,必须是锐利与瑞丽同在?非锐利,不瑞丽?面对金属化的美人们,男女性爱似乎不再被定义为人类单方面的游戏;无论异性恋还是同性恋,在性取向和性规则里,总有非血肉之躯的无机物,以冷艳预戏,竭尽煽情之能事。
性爱与金属的互动,显示出人类的一种怪异势态,一种趋向于机器的势态。难道人类固有的惰性和自私,在这个势态里找到了既慵懒而惬意,又不乏刺激的浪漫栖所?
1927年,德国著名导演弗里茨·朗拍摄过一部名叫《大都会》(Metropolis)的科幻默片。这部经典大片展望了2026年的人间风貌。影片中,未来的地球人类两极分化,富人在华厦享福,穷人在地下受难。医生洛特万则受雇于人,将女主角玛丽亚的血肉之躯克隆成金属之体。未料金属玛丽亚挑起大规模暴动,引发洪水灾难,造成灭顶之灾。不过,故事的尾声未能逃过传统的套路:血肉之躯成功焚烧金属之体,人类重归自我,并在宗教的力量下,温情脉脉地彼此握手言和。

《大都会》意欲传达的道德寓意,围绕着关键词“爱心”展开。对于近100年前的人类而言,金属无心,人类有爱。而爱心的力量高于一切。人间最终的救赎,绝非机器金属的冷酷无情,而是与之对峙的人性温情。不过,倘若弗里茨·朗今天来拍同样的题材,他的科幻关键词会是什么?还是“爱心”?或者早已变成“金属”?金属人扮相的美艳女郎,会让弗里茨·朗情何以堪,还是欣喜若狂?情何以堪也好,欣喜若狂也罢,最令弗里茨·朗心悸的,或许并非当今女性的金属化扮相和时装,而是那些“不近人情”的冷峻色泽后,人类对自我肉身存在的迷惘和挑战。
德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曾这样评论时装业:对无机(inorganic)性感的迷恋,乃时装界的中枢神经。此话在近百年之后,似乎更加一语中的。21世纪的人类对于性感的表述,难道不是一场有机与无机的世界大战,血肉之躯和金属之身的殊死较量?女性皮肤之润美,正逐步让位给机器技术的酷艳。在男性心目里,女神形象或已不复从前,水灵灵的传统美人似乎不再能够挑起男性的欲火,倒是肉体与金属的混合物,反而能激发出男人潜意识里的性快感。
肉体与金属的混合物激发出的快感,应是欲望和恐惧的并存状态。这种状态究竟是人类与生俱来之物,还是机器异化人类的后果?英国科幻女作家维内斯·琼斯曾在1984年发表过一部小说,名叫《神的忍耐》(Divine Endurance)。这部作品里有个中国女机器人,被维内斯·琼斯命名为吉诺德(Gynoid)。吉诺德是个奴隶,充满蛊惑力的美奴。作为机器人,又身为奴隶,她的蛊惑力来自她的金属性,一种让男性欲火中烧,却不得不望而却步的金属性。望而却步自然不是解决方案,最终出路何在?不得而知。
人类制造机器,竟是为了给自己添堵?或许,人类渴望离开肉体,成为Avatar一般的虚拟化身?

回顾一下在弗里茨·朗之后的电影世界,人们不难发现,?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将科幻当成警世良药。影视界借性说话,其实心猿意马。焦虑的,终究不是女性的金属化,而是整个人类的机器化(当然,不少早期科幻作品也借此抨击西方殖民时代的种族不等和道德不公)。可是,瓦尔特·本雅明在论著《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1935)里指出,艺术家在机器复制时代,失去了固有的本真,因为灵光(Aura)消失在机器的复制功能里。在摄影和电影业的冲击下,原本与宗教仪式虔诚对接的艺术,借大肆扩张的烟幕弹,明火执仗地扼杀着道德审美取向,成为政治价值的附庸。
原来,影视界也语塞。
那么,在政治价值与经济效益的互动里,谁主沉浮?绝不是艺术。当今世界,决定艺术审美和价值取向的,恐怕非经济效益莫属。女性美的金属化,人与性离经叛道的悖论,表层显示的,或是人类的乖戾堕落,内核却老生常谈,受控于市场价值的强势。一直以来,人类好比自以为是的美猴王,千变万化,终究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可是,如果出现人类失控,机器主政的那一天(读者们当然大呼“不会”),即便是如来佛,也可能要大意失荆州了。
2016年7月4日完成于维也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