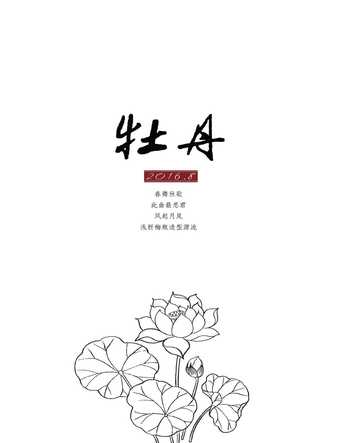形象的物化与态度的流变
李慧君

《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是英国当代著名汉学家雷蒙·道森的代表作品,该书从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视角出发,通过选取大量“被注视者”的“文化物象”进行时间轴分析,向读者生动地展示了“注视者”(欧洲)眼中中国形象的流变。本文着力研究《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的“被注视者”——中国,由于形象本身被“物化”,成为了某个时代的隐喻象征。与此同时,这个形象又被附着在后殖民主义的西方话语里,呈现出双方漫长岁月的历史变迁。
跨文化自然会产生诸多问题,误读就是其中会出现的现象,英国汉学家雷蒙·道森在《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的前言部分谈到:“1958年,我来到了中国,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我过去读过的许多东西是不准确的。”为此,他渴望通过自己的表述改变欧洲对中国的错误看法,他在“欧洲”与“西方”之间周旋,在其他领域的知识里徘徊,收集了大量的佐证资料,完成了这本书,尽管从某些角度看并非完全正确,但雷蒙·道森严谨与求真的态度及竭尽所能的努力必须得到充分的肯定。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都是当代比较文学中研究东方主义的优秀范例,在这样的光环下,作者及作品达到了社会公认的地位。诸多海外汉学家由于观察视角与观察立场的不同,很快便开辟了一条“汉学主义”的研究道路,《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正是“汉学主义”的产物,而赛义德关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最初探讨给“汉学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也正是这种“东方主义”的方法论给海外汉学家带来了很多的启示,以《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为例,书中作为“注视者”与“被注视者”的线索被固定客观地保留,而作为后殖民主义的话语,中国的形象被赋予了一種类似“物化”的形象,如同资本主义的商品一般被有意识地摆弄,只有商品的价值变动才能让欧洲人的态度得以改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根植于西方文明最原始的资本积累欲望之中,并为他们的态度而转移。
一、话语的力量:“变色龙”是对话语境的中庸表达
雷蒙·道森使用“中国变色龙”作为中国形象的总体概括,简单而富有深刻的隐喻,一方面,“变色龙”表达了欧洲态度发生转变;另一方面,暗含着中国的历史变迁。作者在书中描述的语言是平实而谦虚的,并不使用鄙夷或浮夸的口吻。但无论作者如何努力地做到客观而公正,都不可能摆脱本土的语境,远离政治和经济的文化因素,任何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都将面临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的文化选择问题,最重要的是,作者的话语如何能使问题变小或者弱化,“那么,能不能用完全属于本土的话语来和他种文化进行对话呢?”这显然是不明智的,在漫长的历史岁月无意识的熔炉中,要想寻找另一种纯粹的与本土无关的话语是不太可能的,而且这种“纯粹”在文学作品与现实社会中显得苍白和无趣,作者的最佳方案无疑是成为一个“中介”。对照《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这种“中介”其实成为了一种“旁观者”的话语,在文中,作者不遗余力地在以下几个部分弱化了可能出现的双方的文化冲突与欧洲的排外感。
第一,对象的称谓。在整本书中,作者始终对本体——欧洲的称谓为“欧洲”,有时也会称“西方人”;作者把自己与读者称为“我们”,表明“旁观者”的身份;对中国这个客体大多数的称谓是“中国”;而对文中提到的中西文化交流紧密的商人、传教士、历史学家、哲学家等,作者的称谓是他们的名字。作者十分在意称谓的表述,尽可能使用全名,旨在避免因称谓导致“中介”的视角混淆,进而影响态度的无意识先行。作者的在意无疑是正确的,称谓的表述很重要,应该保持“旁观者”的态度,因为作者无法安插任何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情感,所以显得真实而具有说服力。
第二,被注视者的描述。作者的研究对象是欧洲对中国的态度,而态度本身带有主观性的偏见,作者并没有因为偏见就避而不谈、敷衍了事。在第一章里,作者就欧洲对近代中国的印象做出了如下表述:“一个扇子与灯笼、辫子与斜眼、筷子与燕窝汤、亭台楼阁与宝塔、洋泾浜英语与缠足的国度。”这样的表述难免带着一些欧洲对中国的蔑视态度,作者并未刻意遮掩与擅自修改,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作者的初衷,是展现欧洲对中国的“误读”,并不是想改变历史。作者也是“他者”,延伸到作品的另一侧面,“被注视者”——中国在欧洲的眼中是一个神秘而传统甚至有些奇怪的国度,但“注视者”一方却像“淘金”一样满眼放光地随意涉足这个国度,西方有点疯狂的好奇也正是因为处于20世纪的殖民幻想里。作者本身无疑也充满了好奇,但作为研究者,他隐藏他的态度与想象,在描述中避免了“一边倒”的立场。
第三,“变色龙”的空间感。20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在欧洲人心目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形象,作者并没有自己下定论,他通过展示资料、勾勒历史、回顾事件来告诉读者答案。同时他利用文献,利用人物,也利用器物进行长时间的观察,以小见大地反映中国的空间形象,是多维的、立体的、有色彩的。雷蒙·道森在中国的经历使他认识到中国的不同,他耳濡目染长期被灌输的“中国”形象被分解,他站在中间的立场上去解读这种差异,笔者认为,他将自己作为“中介”这样的角色去看待两种文明之间的关系演变,并用“中国变色龙”这样的整体形象概括,是一种中庸思维的表现,这种中庸视域的形成与汉学家的身份有关,也与他在中国的亲身经历有关。换句话说,作者自身文化认同的转变的微妙过程,促成了他中庸分析观的形成。
综上所述,可以确定雷蒙·道森在《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中相对客观地表述了欧洲对中国形象的态度转变,它体现在一些文本细节上,带来了新的阅读体验,而“中国不是龙,是变色龙”的论断更贴近中国的实际,这也昭示着作者的成果——一种无声的话语力量。
二、形象的物化:中国作为殖民地的历史语境
尽管作者尽量做到站在“旁观者”的位置,但也很难避免“西方中心论”的主体批判,文化影响的双向性并未涉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只是历史的缩影,而比起这些,笔者更关注另外一个领域,就是作者在本书中所描绘的“被注视者”——中国的形象,以欧洲为主体的“注视者”因为历史的缘故站在相对较高的位置,因此,中国在曾经一个阶段被无意识地排挤出西方文明圈,成为一个既遥远又陌生、既无知又盲目的形象,笔者用“物化”这个概念来界定这种作为殖民地的语象。“物化”是卢卡奇首先提出来的名词。而物化本质上是人的“事物化”,物化社会也指人被当作机器一样被无意识地摆弄,在《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的描述中,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沦为欧洲的殖民地,欧洲对中国的幻想随之变成嘲笑,而中国变成了一个可以被随意践踏、愚昧无知的国度,这时候,无论从哪个角度,中国都已经成为欧洲人眼中“物化”的形象,不再是个生机活力的世界。
雷蒙·道森在书中列举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物象”来阐述19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对中国态度的转变,这些“物证”见证也象征着由仰望变成鄙夷的态度转变的过程(见表1)。
以上所列的“文化物象”,清晰地展现了“中国”形象在欧洲的完整变迁,如工艺品的早期崇拜到大量复制及掠夺,再到重新审视与鉴赏,“中国式风格”的烙印一直存在于西方,但“中国形象”却始终被“物化”,它体现在:西方人认为中国“缺乏感情”“低于人类”,既“古怪”又“粗俗”,直到如今,他们的教科书及课堂上仍很刻板地介绍19世纪中国的历史,文明的冲突是导致中国形象走向没落的直接原因。
反观之,中国被“物化”的形象从19世纪后一直存在,是中国作为殖民地的历史语境所决定的,20世纪80年代,后殖民主义的诞生阐明了这个道理,后殖民主义强调文化精神被政治控制的要害,并认为“除了政治上、经济上受殖民主义宰制,第三世界国家与民族在文化上也被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控制着。”中国作为殖民地,无疑在文化上也属于“第三世界”,从书中描述的这些“文化物象”,可以看到其任由摆布的局面,同时,作者所列举的“物象”,也是书中的一种意象,象征着中国作为殖民地的一种无力抵抗与丧失意志的“物品”形态。其次,19世纪末在西方资本主义无尽的“藐视与摆弄”下,此时的欧洲仍对中国“低劣”的形象反感,直到20世纪初“共产主义”的悄然兴起,才引起歐洲对其形象认识的一点转变。作者利用共产党中国作为见证,敏锐地指出政治因素对欧洲态度转变的巨大影响,直到作者所处的20世纪末,这种被“物化”的形象,才得以为欧洲做出不情愿的改变。显然,从“物”到“人”,是要跨越漫长的时间岁月的。
三、态度的流变:“我”对“他者”文化的认可过程
在《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中,“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段曲折的历史经历,作者运用大量的文献资料佐证这些态度流变的过程,文章以欧洲的“认知”为原点,以中国为终点,进行全方位的认知探索。实际上,这个过程就是建构对中国的文化认同,但是,建构认同也意味着建构“他者”,作为一种自身的主观定位,“认同”是一种对所谓“归属”的情感。那么,在书中谈到的欧洲对中国,是否也逐渐找到一种“归属”的情感,是否也会吸收中国的文化因子,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笔者整理了书中提及的“注视者”与“被注视者”的态度转变关键词,制作了表2,作为整本书的总括。
从表格中可感知发生这种态度变化的历史背景,是由鸦片战争开始的近代侵略战争,而作者并未涉及过多的笔墨在历史事件的影响之上,这其中的缘由,笔者认为是作者有意地规避文明冲突造成的文化相斥主义,在这样的规避下,读者不会太多地感受到因战争杀戮带来的血腥场面,只能在文明的世界中体会到中国的兴衰起伏对欧洲文明观的影响,这必然会招致来自中国学者的质疑:是否这种刻意的规避只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虚伪。但作者却又在文中有意无意地提到“基督教的优越感”带来的“误解”,也认为“欧洲对中国文明和世界上其他非基督教控制地区的文明持一种蔑视态度”,指出了根植于欧洲人心中的高傲是掩盖扩张历史的一种托词。
现在来解决之前提出的问题。在欧洲“文化认同”的道路上,直到现今,欧洲人是否真正改变了对中国文明的看法,在书中的最后一章《黄变红:20世纪的考虑》中,作者提到:“对现代中国产生曲解的下一个因素就是对共产主义的恐怖与仇恨。”所以,无论嘴上说的多么令人振奋,始终很难出现“归属”的情感,欧洲对“中国”的文化“认同”,到20世纪末,都只能说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可”。任何语句都不可能脱离政治和经济的语境,也就是说,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程度,决定欧洲对其态度改变的程度,这也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作者在书中弱化了这种政治的因素,仅仅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显得不够透彻。
回顾欧洲对中国文明观的态度流变过程,可以说是欧洲的知识认知过程,更可以说是对中国的文化认可进程,但抛开本书的观点,客观地讲,这种认可并不是真心实意的赞赏,而是对后殖民地中国发展迅猛的震惊,转而对中国的文化开始感兴趣,这种政治引致的认可,有可能是打开友好外交的开端,如作者一般的海外汉学家的深入研究成为双方打开心门的一把钥匙。不管“东方主义”的何种歧视与偏见,在全球化的视野下,未来双方的“对话”都将可能如本书所说的“可以毫无偏见地注视”。
四、结语
“他者”并不是一个模糊不清、神秘莫测的形象,在雷蒙·道森的笔下,《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以丰富多样的资料、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了中国形象在欧洲心目中的变迁,尽管中国的形象在某个时期内被“物化”、被误读,但这就是最接近事实的真相。而欧洲对中国态度的流变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不断被真正理解的“他者”,文化的排外与语言的障碍,使双方的“对话”不可能再恢复“平视”的姿态,对于“他者”的认知,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又全面客观。无论“中国变色龙”是把什么样的颜色传达给欧洲,这种作为时代“想象物”与历史“遗留物”的现状已然存在,历史不会变,“我”与“他者”的地位也不会变。在今天全球化的视野下,随着科技时代的来临,信息网络的高速发展,对“他者”的认知将会更深入更全面,而那些殖民地与后殖民地的文化隔阂,也会慢慢消除,成为见证历史的记忆。
(暨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