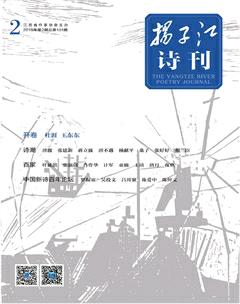新诗史上最大的接受“聚讼”
陈仲义
一、接受主体的深堑鸿壑
接受主体的开放性,诱惑着接受的无边性。层出不穷的接受“黑洞”,不仅吞没一切“喧嚣”,反过来,也“映照”出接受主体本身的“百罅千缝”,导致终端评价千奇百怪,甚至南辕北辙。以新诗史上最具规模、也最具争议的接受个案——“汪国真热”作为解剖对象,在长达20多年接受的膨胀、缩水、变形、走样的还原过程,让我们重新打量此前被忽略的接受主体,该,还是不该拥有“决定性力量”;如何调整接受的“层级”;新诗接受主体的某种“分级”趋势,在不同接受级差上能否进行和平对话;新诗接受的大众轰动效应与精英化驱策下的接受冷遇,是否必然演变为新诗接受的对峙“死结”?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待细细梳理。
20年来,热捧与批判,促成汪国真名噪一时。追捧者坚持:汪国真以广大青少年为阅读对象,当之无愧是“青春诗人”“诗坛王子”“中国诗歌最后一位辉煌代表”。不同于朦胧诗对生命形而上的复杂感受,也区别于“第三代”对生命晦暗、悲观、碎片式解构,汪诗的简洁明朗,虽缺乏深奥的个人体悟,却迎合广大青少年需要。“汪国真现象”标示一个诗人拥有自己的读者群,它既代表一种社会心态,同时也代表一种诗歌方向。
挺汪代表、北大学者张颐武认为,人们低估了汪国真的贡献,浅吟低唱、成为让普通青年理解的小感悟,从而让人们的人生丰富。艺评人廖廖认为汪国真作为一个中国的文化偶像,他有着不折不扣的中国传统文人的底色:温文平和、顺从犬儒,“也许我们不该说汪国真影响了一代人,而是一代人自己选择了汪国真”。鲁奖得主王久辛认为,汪诗有三个精神特征“青春”“励志”“温暖”,“对于高中生与大一、大二的学生,是有意义的”。诗人、剧作家李蝴蝶认为,汪诗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积极心态的复苏。即使他算不上伟大,也要看到汪诗能浸润普通大众的心灵。①
倒汪派学者冉云飞,将汪国真封为“鸡汤鼻祖”,“他的鸡汤文字参与了种种致力于让人装睡的力量,而且贡献颇大。犬儒大盛,不分青红皂白的劝忍劝忘,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对不公不义的维护”。②青年学者杨早认为,本该是反思匮乏与蒙昧的时机,却变成伪青春的记忆狂欢,他谈不上抚慰创痛,却为那个时代“美白”。“某种程度是扭曲、误导和降低了中国青少年的审美品位,以及他们对当代诗歌的鉴赏能力。汪诗走红是一副麻醉剂。”(诗人喻言)“更是一场语言灾难。”(诗人潘洗尘)③
批判的火力不断升级:“作为一个诗人,汪国真极不合格。汪国真所有诗歌的水准,徘徊在顺口溜、励志歌、校园黑板报之间。汪诗不是改革开放的新事物,而是社会主义传统美学的一部分。汪诗的最高成就,也就是流行歌词的高度。”④欧阳江河更加直言不讳:“汪国真的诗,全都是‘假诗。这简直就是对整个诗歌智识层面的一种羞辱。那些表演性成分和精神励志等,我认为是拼凑出来的。而我们的教材居然把它收入,塑造那种四不像的东西,这是对学生的一种毒害,从小学时起就会有树立起一种‘恶趣味的危险。”⑤
其间也有温和的中立派。比如唐晓渡将汪诗与汪诗的影响加以区分,一方面认为汪诗确实比较幼稚浅显,易被中学生所喜爱,但另一方面,他的流行并非他的过错,不应该受到任何指责。他在多元化的诗歌格局当中,也有他的理由、他的意义。⑥张柠认为,汪国真的诗歌通俗易懂,有自己的受众面、传播渠道,有自己的意义。“我们不能强求所有人写我们在大学讲堂里所讲的那种有深度、意象的东西。我们只能说那是无数种诗歌风格中的一种而已,不能说它就是诗的标准。”⑦
凤凰网文化专栏在汪国真去世后做了个专题,实时流量比两周前去世的诺奖作家格拉斯足足高出200倍,可见汪诗在大众层面的影响力。回顾汪国真1991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5 次印刷高达15 万册,《年轻的思绪》4 次印刷高达 20 万册,其“年轻系列”总数突破百万册。汪氏清浅流丽虽属学生手册关乎理想教育的励志篇,但作为青少年亚文化形态的正能量,还是征服了青春期的心理市场,适合花季年华的胃口。
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同年去世的美国诗人罗德·麦克温(Rod Mckuen, 1933-2015),也有相似之处。据旅居芝加哥的非马介绍,麦克温诗选卖掉过六千五百万册,远远超过美国历史上两个最有名的佛洛斯特与艾略特的总和,同样也没得到主流诗坛认可。许多人鄙夷麦克温的诗太明朗、太糖分。《新闻周刊》称他“俗气大王”。名诗人谢皮洛贬他“连垃圾都不如”。⑧截然不同的接受“撕裂”,涉及极为复杂的问题。如果坚定站在问题的各自端点,从单一的角度出发——比如只锁定文本或以大众口味为唯一检测准绳,各自得出的答案就永远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但如果在多重视域交集下,引入更多维度,可能就有许多值得协商的地方。
二、接受主体的“切分”与局限
其实接受领域存在不同的接受身份与接受层级,不好“一刀切”,它往往导致接受的天壤之别,云泥之隔,只不过平时多被“忽略”,如今在汪氏身上更加集中与白热化。假如我们换位思考一下,从十三四岁的阳光嗓音出发,我们会发现,汪国真在稚嫩心灵留下的传声带,即便单向度,也会如《中国少年先锋队歌》那样被唱得格外起劲:“花的河流/必定要奔腾不息/帆的船队/必定要航行在晴朗的天宇/春天的女儿呵/必定要前进在春天的队伍里”。简易的青春文本、流行的校园文化气息,当汪国真把理念转换成单纯明朗的声调,在未谙世事的少年身上极易化为人生动力、素质修养、伦理情操。现成的浅白哲思,迅速被摘句、撷取、抄录成贺年卡的祝词、毕业典礼的赠言、彩笺上的珍重,和课桌底下的秘密传送。这些格言体的励志篇,有千篇一律之嫌,但对于“一张白纸”、对于生长发育期的八九点钟太阳,却有一种“只要明天还在/我就不会悲哀”“当我们跨越了一座高山/也就跨越了一个真实的自己”的即时加油、鼓舞,与鞭策的效用。判断句的大量运用,强行的制导力量,不管这种力量建立在沙化、浮松的基础,它统摄了青年学子的课业、理想、爱情、未来,斩钉截铁地“推上去”,用直接的提问方式,明快干脆的答案,给予所谓正能量的青春指南。纵使缺失历史感,也不探触深层现实、违背温室的生长规矩,但与自暴自弃、消极沉沦的灰色地带无缘,永远是清一色、“高八度”的挺拔姿态。所有这一切,都与一个巨大的、青涩群落的心态紧紧关联,所到之处获得热烈欢迎,自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强大的后台是“国教”背景。
应该承认少量较好文本(《生命之约》《应该打碎的是梦》),相对脱俗:“我不想追波/也不想逐浪/我知道/这样的追逐/永远也追不上/我只管/走自己的路/我就是/含笑的波浪”。一俟脱开汪氏模式,其严重的同质性才略有打破,如《悼三毛》 “撒哈拉沙漠很大很美/她一定是迷了路了/再也走不出来//她迷路的那天/并没有下雨/可是 许多人的心/都被淋湿了//从此/雨季不再来”。可惜,这样的文本很少。
所以,与其把汪国真当做诗人,不如当做一般词作家。理由是文本表意明朗、语言直观,相对简洁,修辞简单,明显的歌词化同校园流行歌曲一拍即合。“不是不想爱/不是不去爱怕只怕/爱也是一种/伤害”(《默默的情怀》)“青春就是幸福/幸福就是翱翔”。歌词化结构,经常通过一个理念,如《感谢》,在春风春天、浪花海洋、红叶枫林、雪花世界等并列物之间做简单演绎,缺乏层次感,情感体验有限,多数结构如模子印出来平板单一。即便如此,由于较注重音乐性(大体格式整饰、几乎篇篇押韵),读来朗朗上口,也会冲淡内在诗情的单薄。启用诗歌最简单手段——重复、排比,制造了情感连贯与情感的直接力量。晓畅的流泻、明朗的逻辑,使得汪诗节奏轮廓鲜明,特别适合校园朗诵会(也于此埋下了作者转向作曲的伏笔)。
然而,从专业、从现代诗以原创为生命的创新角度考量,汪诗就乏善可陈了。一旦置于“隐含读者”“理想读者”“模范读者”“有能力的读者”面前,他的被漠视便势在必然。通常诗歌界有四种接受形态:深入深出、深入浅出、浅入深出、浅入浅出。汪国真无疑属于第四种类型浅入浅出。针对文本,香港诗人廖伟棠毫不客气:“我读到汪国真59岁所写的最后一首诗,比他19岁、29岁所写的毫无寸进(无论思想境界还是语言能力)。一个人19岁的幼稚,我们可以说他是单纯,过了40年人生历练还这样,那就是存心迎合愿意幼稚的人的举措。”⑨这种迎合的幼稚大大暴露文本的美学缺陷与不足,那是连篇累牍、缺失创造性的大白话,缺乏真切疼痛感,只剩下没有血肉的骨头:“如果远方呼喊我/我就走向远方/如果大山召唤我/我就走向大山”,翻来覆去,通篇是干巴的说教,人人皆知的常识,“我没有太多的话/告诉你,走什么路全在自己/不要太看重,名利/和荣誉/不必去呼唤未来/未来就在你的手里”。缺乏生命的痛切,经不起深入推敲,空洞的概念化,是挂在壁纸上的塑料花,少有诗美的掘进和砥砺。
其结果,最终必然落入明显的制作套路。主题、题材、观念、情调、手法,有太多雷同、太多重复。(“背影总是很孤单”“欢乐总是太短”“寂寞总是太长”“往事总是很淡很淡”“感激总是很深很深”)。时间久了,填充式的路子会越陷越深。概念说教,表明情感贫瘠,为文造情,不可能走得太远。难怪有人说,《热爱生命》几乎涵盖了汪国真所有的主题内容,读他一首等于读他所有诗歌。“本质上,汪诗没有创造性,没有独特性。他诗中的好些句子都似曾相识,很难找到表现他个人独持智慧的语言。”王小章直指文本的评鉴可谓一语中的。⑩
纵然是被多人引用,津津乐道,成为汪国真最具分量的名句“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也很难说是他的原创。经查阅,二十出头的公刘,早在五十年代三十多年前——的《山间小路》就写出来了:
一条小路在山间蜿蜒,
每天我沿着它爬上山巅,
这座山是边防阵地的制高点,
而我的刺刀则是真正的山尖。
读者一旦读过“刺刀比山峰还尖”的句子,就不会对“人比山高”发出原创性赞叹。再推远一点,也可以看到是林则徐 “山登绝顶我为峰”,或有人赠张大千“山至高处人为峰”的翻版。由此不难想见,接受主体本身存在着巨大的封闭性与局限性。接受主体有自觉与自发、敏感与迟钝、精细与粗糙、深邃与肤浅、颖悟与懵懂、聪慧与愚驽之分。不同类别、层级的接受主体反应是大相迥异的:一些清晰明了的,可能被视而不见;一些浅尝辄止的,可能无限延义;一些庸常普通的,反被奉为佳篇。因为学养、经历、知识结构、艺术感受力的残缺、盲点、外行,都会明显留下接受的内外硬伤。诚如英加登所指出的“读者的想象类型的片面性,会造成外观层次的某些歪曲;对审美相关性质迟钝的感受力,会剥夺这些性质的具体化”。 k
由此看汪诗接受的两极,少年学子的热烈拥趸与批评界的断然否决,完全属于正常现象。需要省思的是,接受主体的无边开放是否存在绝对的“天经地义”?它如何对待自身的封闭与局限? 接受主体的局限性明摆在那里,是无法逃遁也无法遮蔽的。流行受众,无视自身知识欠缺,顺随时尚风流,不以为俗而以为为荣;精英受众,一味抢滩弄潮、高标探举、唯新是瞻,睥睨基础层面,也无助于新诗初级形态的普及。在大众的轰动效应与精英的冷遇命运面前,双方每一次“交火”,都极易在对峙的语境中升级,又在各自的领地里“自行其是”,或维护各自的“狂欢”、“快感”,或保留各自的“倨傲”、“尊严”。那么,有没有“和解”的必要与可能呢?
三、大众化“轰动效应”的背后
汪诗热出现不是偶然的,表面上看是经由一两位编辑发现而引发的出版机遇,其实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时代语境总体合力下的结果。汪诗的轰动缘由,具体分析有四。首先,不能绕开那一个特定的“历史空挡”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自1989到1992“南巡讲话”之前,诗界出现过一个三四年的“真空”:意识形态高压、自由言论受挫、公知一片沉喑,先锋艺苑近乎荒芜。汪国真适逢其时地出现,与其说他钻了气候的“空子”,莫如说时代提供了舞台。本来,朦胧诗对假大空横扫,可以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但体制性的敏感压抑,加上传统审美惰性,延误了朦胧诗的传播力度;此间汪诗的青春性与中庸性恰恰贴近官方价值立场——和谐稳定的人伦秩序,与主流文化庶几合拍,得到鼓励与顺水推舟毫不奇怪。此间第三代诗歌左冲右突,带有太多探索性实验性,尚不成熟,叫本来就窄门的现代诗继续走向圈子化,其尖端的反叛与锋芒部分,的确很难进入公众视野,甚至屡遭阻击,阅读“失效”。精英观念的超前与激进,只是对精英诗人有引力与凝聚力,却无力感召广大青年学生参与、追随。精英诗歌义无反顾死守自身美学立场,无形中被广大受众抛弃,客观上为汪诗的登场鸣锣开道。设想,要是当时没有意识形态的严峻施压,没有第三代不加节制、走火入魔的实验,现代诗界不被快速嬗替的潮流搅局而保留良好生态,汪诗想脱颖而出恐怕不那么容易。左春和某种程度道出了真相:“汪国真的出现,以他对精神的浅表性安抚,让一个思想退场的年代虚构成让人依赖的心理洞口,其实是一种精神雾霾,从而完成了与权力同构。”l
其二,其时校园文化、青春心理的趋同性达到惊人一致,从众心理长盛不衰,是教育机制的一个弱项。只要“一声响动”,同处那一个青春期,不同班级、不同性别的人群很容易一窝蜂形成“趋之若鹜”的大流。在乌托邦的想象共同体里,躁动不安的青春灵魂,大同小异地寻求慰藉与安放。尽管汪诗无法解决真切的实际疑难,但毕竟提供一种符合国家、政党、社会、家庭要求的文本,并成为个人想象所能接受的精神支点。正是这种接受模式吻合青春期、快餐式宣泄,才赢得广大学子的热捧。平白清浅的格调,再怎样贬低,还是挺适合中学六个年级,加上大学大一、大二年级的胃口。八个年段的总数不可小觑。其中最大受体是70后这一代人,没有经历“文革”阵痛,又迎面外来文化初潮,历史体验和当下文化指引双重缺失,加剧了迫切性,只要触到新鲜的文化萌芽马上“依附”上去。期间流行的港台文学,无法持久地契合他们的心理需求;干涸的心灵更加饥渴地寻求文化雨露,汪诗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缺。
可是,这种青春阶段性的诉求不会总是一路狂欢下去。调查表明,当80后90后以“隔代”眼光反观前辈,境遇、思想、资源,都开始发生变化,可以想见汪诗生命力在未来时间长河中面对新一轮受体,要想持续20世纪90年代的影响,肯定要走下坡路了。某种意义上,汪诗可视为一种温和折中、妥协的“青年亚文化”,部分原因源于青少年较低的辨识文化程度以及较低的审美判断——满足表达清晰、意蕴浅显就达标的接受尺度。这与他们青春体验的局限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相对单薄的知识文化结构、发育期的躁动,更愿意在流通的、大众的、青春的广场上载歌载舞。这,颇像小说界的郭敬明?本质上,可以说汪国真是诗歌界里的郭敬明。有人通过主题、题材、受体、言论、销量、跨界等层面的收集比对,出示了两位青春偶像的共同特征。m如此看来,这样的文化雕塑,只有在校园平台上,才具备发生与接受意义,而校园文化在大文化广场上,永远有一席之地。
第三,其时的大文化初潮伴随着“流行”“时尚”“轻型”“消费”元素 :健美裤、伦巴、三点式、麦当劳、“四大天王”,包括刘墉、张小娴等也进军大陆市场,占据一片天下。在此之前,已有席慕蓉风靡校园,《七里香》等印数超过百万,但是古典式的缠绵忧伤,毕竟留下历史文化隔膜。如果说席诗是青春已逝的似水华年,汪诗则贴身本土校园的青春温床,席诗遗留的心理余温,被汪诗用另一种明快的青春柴火点燃。平心而论,同是流行诗歌,席诗乃属于本真行走,源于自我平常心愫,成就了一种清芬圆润、唯美细腻的风格,远比汪诗高出两档。
第四,汪诗流行成功的很大原因,还在于“顺遂”了传播特性。他关注、迁就读者,坚持文本一目了然,使得读者在阅读“加工”过程中,无须做过多的歧义排除。这样,阅读难度降低、吸收速度加快,读者译码、释码过程得以一帆风顺,感情的共鸣轻而易举,阅读的快感也更容易建立。汪诗放弃高度,降低审美水平,稍比中学平均水平高出一些,在未成熟的心灵引起更多认同;而期间许多优秀诗文本尚远离大众视野,在被遮蔽的前提下,汪诗的小哲理更易被视为“上品”。而出版社看准市场,大力推行营销策略,“捕获”青少年读者易如反掌。
这种在“前网络文化”语境中发迹的“暴发户”,正好是商业出版机制改革下的“宠儿”;作为学术界的“弃婴”,反倒在“国教”运行中以相当比重入选中小学教材,加剧了前所未有的传播。n这并没有什么讽刺意味,反而证明接受的“正能量”何等符合富有中国特色的国情。当然,还得算上各种链条的推动:诸如系列的市场化签售、电视屏幕包装亮相、大中专院校巡回讲演,报刊杂志专访报道,盒带光碟推销,名胜古迹风水宝地题词,以及书法、歌词、作曲的其他才艺,多维加码,在时代总体语境合力塑造下,汪国真一跃完成从诗界“畸零人”到文化明星、再到偶像的全过程,创造了中国诗界最大的轰动接受效应。2015年联合国通过量化统计,给出中国素质排名第164位,盖出于中国文盲比例高,文明程度弱,艺术教育与资源稀缺。考虑到国人整体素质偏低,汪诗在青年读者群中能起到如此广泛的入门“启蒙”, 这一点应当得到肯定。
同时,也不难理解先锋诗界对汪诗轰动效应的嗤之以鼻,一直保持着高傲与不屑。就其文本而言,汪诗意蕴浅显、韵律规整,委实不能满足精英诗界对好作品的要求。因其研究空间不大,最多只能与琼瑶、邓丽君为伍——同存于通俗文化领地。但其惊人的销量与轰动效应,大大加重了精英界的危机感,焦虑中的精英们对其作品的“烂俗”本无暇指摘,但其“媚俗”却大大刺痛了精英立场,从而引起强烈“反扑”。o这就形成了中国新诗史上历时最久,对峙最烈的“水火不容”。当下,人们“只愿接受通俗的快餐文化,说明这个民族的求知能力已经迅速退化,是一种深刻的精神危机”。这样下去,我们的文化塑造只能趋向低能、弱智。“所以我们今天仍然需要检讨汪国真现象,这本身也是在检讨我们自己。”p
四、精英化的“冷遇”结果
与轰动效应形成强烈反差,是多数先锋文本在个人化写作推进下的惨淡命运。那么判断一个作品的价值究竟是由什么决定?流行?时尚?市场?抑或创新性?而创新性受阻又该怎么办呢?面对媒体,汪国真一直振振有词:“人民说你是诗人你就是诗人,不被人民承认就什么也不是。检验作品的标准一个是读者,一个是时间!那么多读者,这么多年,一直喜欢着我的诗,足够了。”q诚然,时间与读者作为接受准绳没有错,然而,汪国真把青少年读者(部分)当作“人民”(整体),岂不是在逻辑上做了一次巧妙偷换?而时间,仅仅过去十多年,能否成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经典,还需要耐心等待。
表面上,这样的雄辩,颇能成立,但在某种程度上,是以隐含的媚俗作为部分通行证的。米兰·昆德拉深刻指出:“媚俗,是把既成的思想翻译在美与激动的语言中。它使我们对我们自己,对我们思索的和感觉的平庸流下同情的眼泪。……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对我们整个生活的包围和渗入,媚俗成为日常的美学观和道德。”r而“媚俗的逻辑必然导致对现实生活的文饰,在无所神圣中冒充神灵,在苍白的荒原上布置塑料盆景。因此,严肃的、深刻的诗人、思想家就得不到大众的拥戴,反而那些平庸的、肤浅的、装腔作势的表演者倒能成为大众热情拥戴的明星”。s所以,在流水线上炮制的诗文本,只是文化快餐的一次性消费,一览无余,失之智性阅读的乐趣。因为文学价值不高,纵然拥有许多读者,一时流行,终究还是走不出经典化关口。君不见,在所有新诗、现代诗的重要选本、年鉴、档案中,汪诗都被“遗漏”。他的位置,当在“当代通俗文化”的某一章节里。
那么反过来,那些不媚俗、不时尚,严肃、探索性文本就一定高出一筹吗?也不一定。严峻的事实是,先锋文本以求新求变为圭臬,在个人化口号推进下,罔顾受众,一意孤行,在普通受众那里,自然不断受到“理解”的多种诟病,像佶屈聱牙、叠床架屋、晦涩重重、猜谜、游戏、故作高深、语词暴力等等,假借先锋特权,放纵个人语法与个人词汇表,目中无人地自我满足、孤芳自赏。
现代新诗的接受“魔咒”一直以来就存在两种交叉:行走在大众“喜闻乐见”的路子上,是人气、拥趸、风光,一路攀升,能迅速打通接受文化的隔离带,却又很难保证优质的艺术品格,这种普泛的初级形态有走向媚俗化的危险。而现代新诗的先锋性“日日新苟日新”,抠心挖肠,远远走在时代前面,令大众的知觉力赶不上他们的步伐,屡遭冷遇、冷冻也很自然。这的确是个不易迁就的两难。激进者宣称,是先锋在引领大众,否则艺术早就夭亡,大众反驳说,放弃通俗,就证明高明?看来现代新诗的接受不宜做笼统的“一刀切”,而应 “切分”为不同层面不同层级,以平息混乱。最大群落的划分是新诗中的先锋部分,精英部分,属于引领性的, 其尖端朝向不断的突围与创新,它对应于高端接受。新诗中的初级部分、通俗部分,属于公识性的,以读者的普泛需求为标的。两者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内的交叉,可获致鱼和熊掌的兼得呢?
罗兰·巴特说:“文学作品的诱惑使读者不再是文本的消费者,而成为文本的生产者。”t这意味着,即使个人自诩的高端文本,一经问世,其生予大权并不在他手中。读者不买账,再尖端的文本也会束之高阁。30年前,笔者在朦胧诗懂与不懂的争论——考察“五主将”的接受光谱时,曾多次打比方:如同在9寸电视机屏幕前,坐在前排的受众,大约离屏幕2米处,是眼睛看得较为清楚的地方,当属舒婷与顾城暂时领先的“势力范围”;坐在稍后的观众,距屏幕4、5米处,看到北岛的文本影像,相对比较模糊,尚需一段时日向前“挪动”的努力;而坐在最后面的,八九米开外,即便睁大眼睛,看到杨炼,多数是些闪烁的条纹与光斑,他们需要更长时间的等待。现在,观看杨炼的位置,已经大大朝前靠拢了,但是远没有达到最舒服、合适的位置。 这一熟稔的观看经验表明,愈是属于个人化的,愈难得大众的通融;在不同层级的接受中,都存在着一个相对适中的“契合点”。
杨炼挺立在个人化的写作前端,近期的“后峰写作”,涉及丑陋、罪恶、病态、古怪、荒谬 ;开掘自身的后劲、耐力,触摸内心黑暗的极限努力,由深度派生难度,自难度激发深度,着力营构“同心圆”诗学,做人生——文本——人生的不断递增、轮回。这位“被大海摸到内部”且“眺望自己出海的”鬼魂,站在深渊与悬崖间,一如封口的石像,静享冷遇与孤独。
继杨炼之后,臧棣的走势更为飘忽。70后赵卡的描述有一定代表性:“他像一个饶舌的忧郁症患者推迟了一首诗对自身的诗意呈现,他的分句审美让诗搭起了锐角和钝角的惊险结构,近乎‘闪电的遗址,人们并不习惯他的逆审美的哥特式巴洛克风格,他的诗反抒情如同小说反叙述,盘根错节的意象干扰了读者的视线,令人恐怖的重度修辞几近一个邪恶狂徒的计划,他毫无顾忌地展示了一种令人恼怒不已的荒谬性,对读者形成的障碍却是难以言表的困惑。说句不太准确的话,臧棣的诗看起来像一种诗的方言,他的诗的确有着常人不可企及的复杂性和难度。”u
这是汪与杨、臧在两极接受上的巨大落差。若果你选择后者,你得做好思想准备,在一段很长时期内被打入冷宫,绝对与凯旋门的狂欢无缘。最多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心腹”,共赴险境;也推石般做些启蒙工作,滴水穿石,来日方长。困窘的原因,是你走得太快太急太远,经常被大众的视线抛在地平线之外,不容待见,加上盲视者往往把彩云误当辉煌,所以你也不要只顾自己往前赶路,你还有一个任务,时时回过头来,等待、召唤剩余的、滞后的队伍。
汪与杨、臧的案例再次表明,受众主体的整体性是完全靠不住的,受众的分化、裂隙与对峙是必然的。尤其在两极的端头,前者投合俗化,赢得消费狂欢,后者勇毅涉险,冒着曲高和寡、无人问津的代价。这是新诗普泛的、后拖的板块,同先锋的、尖端的板块的“拉锯战”,是不同写作主体引发不同接受主体的分裂与区隔。随着整体国民素质的提升,随着现代诗性的渗透、弥布,相信国人的接受会逐渐告别“浅进浅出”的格局,趋于更高的层级。
1上言论见《汪国真去世引发大讨论:纯真记忆还是鸡汤毒药?》,凤凰文化,http://culture.ifeng.com/a/20150426/43637303_0.shtml,2015.4.27。
2伟棠:《拒绝哀悼一个人,但哀悼一个时代》,《腾讯大家》,http://dajia.qq.com/blog/450599090627125, 2015.4.27。
3①。
4小盐:《悼念汪国真的精神误区:青春追忆症与群善表演》,凤凰文化《洞见》栏目第148期http://culture.ifeng.com/insight/special/wangguozhen/,2015.4.27。
5亚顺、柏琳:《争议:汪国真诗,好诗?俗诗?》,《新京报》2015.4.27。
6①。
7宇:《汪国真:我就问你一句话》,《南方周末》2015.4.30。
8美]非马:《汪国真:中国的麦克温》,《新大陆诗刊》第149期,2015.8。
9①。
10章:《价值真空时代的“文化孤儿”一析崔健、汪国真、王朔现象》,《青年研究》1994年第11期。
11·英加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陈燕谷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93页。
12和:《汪国真现象批评》,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98861e0102wcy0.html,2015.4.26。
13撄宁:《汪国真、郭敬明,你们到底有多像?》,《 新京报书评周刊》2015.4.7。
14敏:《试论多重文化视角下的“汪国真现象”》,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
15。。。。。
16荣:《汪国真诗歌与青春文学的文化模态分析》,《南方文坛》2014年第3期。
17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59页。
18章:《价值真空时代的“文化孤儿”一析崔健、汪国真、王朔现象》,《青年研究》1994年第11期。
19罗兰·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20:《反禁忌的禁忌:臧棣的非正式性》,诗生活网站《诗人日志》,2015.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