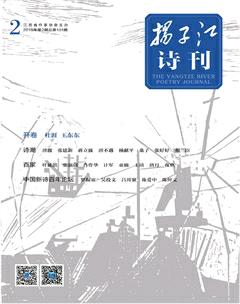王辰龙的诗
王辰龙
影子:马铁虎
你痴迷急速上升的事物。他骑车下班,你
仍追赶竹蜻蜓的落点,直到她推开厨房
第二扇门,去阳台探出声音找你,骂你上楼。
南窗也已系上冰锁,年关近了,另一个下午
绕到化工厂小区的北面,一次次点燃窜天猴
灰色的短尾:最高的那只,误撞药厂宿舍的
屋檐,五层楼,我屏住呼吸……是年的五月,
劳动公园筑好鬼城,在伪地府的出口
我听见你体内的火药肾上腺般地呼啸:
不够……还不够。余下碎银两,我们就奔往
凌霄飞车飞过夏秋与寒假,你却抵达他
某夜的切齿:“永别了,工厂。”继而,他竟
向她和你作四年的暂别。“大北监狱,大北,
监狱。”起哄着挤作一团,他们踢沙土,你
紧跟她,不曾怒目不曾打过来,只是消失于
六单元的暗影之中。他终究回家;你一直在
却没再归来。“下来玩呀,马虎!”我听见我
一跑出五单元便喊,略去你名字里散发
黑硬光泽的部分,它像十余年前的流星,
划过此刻京畿突兀的晴夜:有人正在城北
隔着十一月的狭渊为烟火鼓掌。我想起你。
影子:姐
风发出了响动,我们的耳朵是挂铃般的
眼睛稍稍张开,它们透过温暖的幕纱,
摇向一边,看蹑手蹑脚的流动如何平息。
你总先于我,离开午睡的袒护,如竹蜻蜓,
出入于暑假的下午。小身子已滑过了十个
春天,你以柔软去迷恋糖果,你正爱得发痴
却单把糖衣留下,双目纤美如丽人手,将斑斓
喜看,你抚平塑料彩虹的褶皱。而那些炮弹,
都打给了我,我不归地发胖,并将跃向某一种
未来和八月末:被秋老虎紧盯,流汗。你则会
瘦如水果硬糖,一裹上花花裙衫,就去小城探望
改嫁多年的母亲。好时光如今想起都留在夏天了:
呆日头扒着工人村的建筑,五层楼曝露着红砖
从四面围拢花圃,野草正紧。我们无法掘出深坑
用以掩埋他对她说出的狠话、她对他施加的咒骂。
就找一片铁凉亭边的松土,挖妥了小而深的窠臼,
你落稳本周最爱的糖纸,你覆上汽水瓶底或碎窗的
一角。俯身赏玩,回土,踩实……可你不曾在冬天
再找回它们,即便当年的雨季没有过膝。很多次,
你沮丧极了,不甘心,泪水顺雪原的反光飞入
繁星的行列。而我,陪你一起等待,等冷锋过境。
影子:姥
伏天里的厌食者消瘦依旧,她步入腊月,总是
走得太快,却未尝溅动声息,往后也不曾亮起
声控灯,久久封冻楼道的昏暗,直到一把明锁
弹开门后的微光。紧跟她你踅过公用的长走廊
邻人们堆出的旧物又多出几件,它们轮廓上的
手温正退向你有关疼痛的记忆:是独自回家的
坏时辰,走廊愈发狭长,得小心绕过雕花木箱
闪避卸去了后轮的废车,赢取啪叽的那个夏夜
它们碰碎过你的欢喜佛。三楼高的苏联式民居
这惊觉之前的魔方大厦,你终究还是无法把它
扭转为玩具柜台上的六面兽,一个她许诺中的
礼物,它忽暗忽明在停电的冬夜;而卡车碾响
阴着脏雪的后街,擦亮梦魇的余震,你看她正
用点燃波心的手势熄灭磷火,等待他们的晚归
影子:爷
叫卖更近了,如爬山虎,它攀附
工人村新楼的外墙,尖梢漫出
打糕的诱惑,绿得刚刚好,足以
佯狂成一声钟,响彻你的瞌睡。
把左手从往事里探出,你练习醒来
唤我,一边摸索与喜悦对称的零钱。
而我正在模糊的大雪中走不出来:
肇工街,雪,拥挤多时,我五岁
站了起来,惊喜于被棉花接住;妈
扶起摩托,惊讶于我不喊疼,还乐;
往卫工街继续走,走入另一片白色
听你躺卧酒精气味的暖围,笑谈如何
被司命小仙的血栓箭狠狠命中……
跑回三楼卧室,八月的阳光蝉衣
都来不及抖落,就与你咀嚼此刻
我们最大的福。我后悔,我忘了
向那好游商去讨一个回答。星期一
他还会来吗?甜海的潮汐出入南窗……
这是石头流满你右半身的第六年的
某天下午。点了心的你拈起白纸
它缓缓鼓起蛙的姿态,你教我按
它的臀,蛙便跳出半指之远。你
继而依次拈起八张纸,恍若扯动
大小不一的八个扁木偶:前仆后继
它们在瑜伽中折起身子,成为
塔的局部……我真后悔,祖父,我
忘了问你那可以站立的纸塔顶端是否
藏有时光灵骨,能给二十五一剂醍醐?
高短短的诗
高短短
高短短,1994年生,陕西汉中人。
活着
我与母亲在午后的田间行走
她走在前面,我在后边跟着她
刚刚抽絮的水稻散发出甜蜜的香味
母亲的步伐轻快,似乎并没有
因为她年纪的不断增长而慢下来
“方家庄你祖婆死了,你知道吗?”
母亲没有回头,所以我看不见她的表情
“说是脑溢血,头一晕人就没了。”
我感到惋惜,继而又想起
老太太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
她家的樱桃熟了,院子里都是小孩
一个善良的人离去,我们应该悲伤
但我没有安慰母亲,也没有安慰自己
这世间,必定有很多事情我们无能为力
比如我和母亲之间,无法跨越的
时间的鸿沟,如这条南方的河流
两岸的梯田,种满尚未成熟的水稻
饱满,但不可食用。头顶的飞鸟
像被复制的假象。这便是活着的事物
啄米的继续啄米,落叶的拼命落叶
该生长的,一步也不能停
谁都不愿意保持沉默
谁都不想,白来这世上走一趟
青烟之上
一整个下午,我都盯着一股青烟
香炉里,木香不断燃烧
白色的烟雾从炉子的缝隙里冒出来
萦绕在整间屋子里
我盯着这些曼妙的事物
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
楼下的院子里,分明有那么多
重逢的客人,需要谈话与陪伴
冰箱里,水蜜桃急切地走向腐烂
我爱的人,仍需要不断的深情
而我倾注整个下午的时间
除了得到必要的宁静
和一身的檀木香气。再无其他
我看着这些即将沦为虚无的青烟
像看着另一个形态的自己
漫过我热爱的屋宇和土地
少年偶遇
我们在一间海边的旅馆相遇
两个孤独的人一见如故
他同我说起他的年幼
父亲在他乡的监狱数日子
母亲无心睡眠
走在路上无缘无故就哭了
至于他的兄弟姐妹们
他已经忘了他们那时的模样
反正都不好过。小伙伴们
总会向他投掷鄙夷的石头
一些柳条也曾勒上他细细的脖子
他唯一的朋友
是一条叫小白的土狗
后来村里的一个大男孩
打瞎了它一只眼睛
因为他被一群孩子按在地上时
他用石头砸破了那男孩的腿
那时他和别的孩子一样
不知道什么是对错
后来他们按顺序长大
一个孩子早夭
几个孩子同世俗早婚生子
剩下的,在南方的工厂里
整日抬不起头
世界仍旧是别人的
后来他依旧只有极少的朋友
去过很多地方,认识很多人
得到的多,失去的也多
仿佛已经脱胎换骨
仿佛已经放弃了
对这世界的坏念头
少年变
那一年,我惊讶于自己的蜕变
所有的梦都在逃命。和母亲的争吵
断断续续,从清晨持续到夜晚
我拒绝了一切友好和亲近
爱和恨总是没完没了
为了节制这种悲观的蔓延
我想剃掉头发,被母亲竭力阻止了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反感我
剃掉无用的东西,她认为
女孩子一定要有女孩子的样子
而我更愿意做父亲一样的男人
拥有一身铁一样的壳
坚硬并且长久
后来她还是让步了
允许我可以稍微修整自己
但这并不让我觉得快乐
大街上,那么多的身体
都还孤零零的,没有归处
他们互相献媚与争斗
更多的人倾向于,购买老鼠药
而不是安乐椅。一切简直乱极了
像随时都会演出一场暴风雨
有陌生的小孩叫我姐姐
那么我的身份呢,是什么?
哦,我是一个悲哀的叛逆者
一个不要命的赌徒
我拿着伞像拿着一个莫须有的身份
降雪预报
我是从朋友的口中偶遇那场雪的
当我们一群人围在一起时,一个女孩突然说
“下个星期二,天气预报说会下雪”
真的吗?听到的人惊呼
仿佛已经身临其境,仿佛那场雪
现在就落在了我们的头顶上
多么美好。这么大的世界
什么都有可能会发生
异国的暴乱,一些流离失所的难民
南方还在持续高温,北方已经冰天雪地
有人欢喜,有人走进了死亡的镜像中
生活充满了不可预知。只有这场雪让人充满期待
仿佛它已经落下。仿佛它就是,活着的恩赐
为了接受它的洗礼,我们尚未经历
便已经用够了惊喜的言语和表情
蒋静米的诗
蒋静米
蒋静米,1994年出生,浙江嵊州人。
意马
他们在这里或更好
毕竟他们无法安置自己
有时把头丢在这里
把脸丢在那里
好不容易凑齐了四肢
又缺少可供连结的关节
他们不停叫骂
路人绕行一周才发现嘴巴在膝盖骨后
路人于是不再疑惑
他们决不停止叫骂
只要马三仍未写完这个故事
只要马三仍在牙痛
穿凿自己的头脑以附会
暗中相见的神仙
即使他明知
那已是一具枯骨
突然
像一些感伤的悼词
紫茉莉收拢。突然又触及自身
他们谈论邮递员
和旱季的雨来得一样晚
且不合时宜
合于时世者又耽于时世
尚未谋得一张虎皮
仍驮着用旧的面容
半人半鬼走在大路上
“夜路走多了自然成了鬼”
他们都是老厨子:游刃有余
却也证明刀柄和权柄
并不握在这佯怒的神棍手上
而事情常不如聪明人所料
他也曾以为紫茉莉是种风雅之物
兄弟情深
我们驱逐一个没有左手的人
我们也打死一些羽毛过长的鸡
拧断几根过于细瘦的胳膊
有时光线进入窗户的姿势
缺乏正确的角度
这让我们不安
推平不适宜的道路、弄堂
和香味辛辣的树
作为生物和居民,我们以为已经不需发问
经验老到,惯看生死
突然消失的电线杆和路标
突然生长的绿化带
没人知道一年中
小巷里走失了多少打工佬、流浪汉
和良家妇女
一切越来越美好了
用国家一级播音员标准的普通话
我们有标准的猪肉、美女和类型片
灾难都发生在远处
隔着过期杂志的彩色油墨
人们追问的匮乏和混沌
都要归咎于封建时代
他说,可是
有时他会想念
一颗摔碎的玻璃球
或者浑身泥浆的自行车手
这让我们不安
白遇伯
问路人和指路人互相揭发
揭开左边的头发,是“这是个叛徒”
揭开另一边,则“这是个处士”
他一边分辨自己的手指和指向的作物
终于把自己的腰烤得弯曲
成为褐色车轮里唯一的惨白
可推出异同。除了让梨的孔融
并无一人再说出“如物寄瓶中”
连盗窃虚名的人也不裸身在大街
我们,虚弱的天使
又为何在此处表演饥饿
最终没有人找到吉利的道路
任何一条,竟都于信号灯上高悬
绿眼睛的灾星
它们吞吃雾中可疑的灰尘
和确切的肉
迷了路的人终于也共享
荠菜羹中细碎的饿殍
马迟迟的诗
马迟迟
马迟迟,1989年生,湖南隆回人。
永恒的节日
下雨或者阴天的时候
他常常坐在庭院的一棵树下
那时,火车在高压线下开过
她从厨房出来,猫蹲在花园的一角
他们的小院临近一条古老的河
四月寂静的郊区,鲜有人迹
他们周围居住着几家等待拆迁的农户
偶尔有邻人捎来鱼和新鲜的蔬菜
她总是笑,眼里有数不尽的云
他已经很少外出,有时朋友过来看他
他们会坐在午后干枯的葡萄藤架下
讨论里索斯、济慈或者茨维塔耶娃
鸽群通常是四点钟的时候飞过河流
而更远处的河中,轮船于巨大的日照下
闪耀着灰白的光。在他们搬过来后的五月
他已经清理掉院子里枯败的花草、器物
她换下好看的裙子,暮色纤弱又苍翠
房子的后面是一座没有名字的矮山
山上长满了灌木与高阔的树
夏天深起来时,一些鸟雀便成群地来到
他和他的情人常常在上面出现
绕过坑洼的小路,虫蛾唧唧
六月,他们的谈话日渐疏少
(而事实上,他们通常都很少说话)
每天早上,他独自一人去往河边
头顶上空,天际寥廓、晦暗
他们互相道,晚安和再见,彬彬有礼
后来,那个女人的大部分时间
都用来研习厨艺,或者养猫
偶尔在院子里栽种爬山虎、月季
和牵牛花。她们争执又和好
长日复短日,时间像轰炸机般驰过七月
他的病情逐渐好转,开始写作
八月的时候,很多个夜晚都被雨声灌满
她坐在树下他常坐的位置,在月亮下弄出
微亮的水声。他仍在写一些不为人知的诗
没有人想到他们会生活在一起
他们养起了鹅,买来农具与饲料
在院子里圈起篱笆,栽种蔬菜
他们知道再过几月,这里的事物都会长大
像度过美好的时光。后来
他们又收养了一只狗,每周一
他就会带着他的情人绕过院子西面的
一道竹林与细密的菜畦
去往城市的中央。哦,再后来
他们之中谁也没有意识到
日子会像这样晃闪着,平凡地过去
冬天就要来了,她对他说:
就这样吧,像永恒的节日
虚度时光
秋天进入九月,下旬,铁路桥下
水波平静,轮船在夕照中驶向远方
刚刚他给朋友,写去回信,信中提及
佩索阿与卡夫卡。小区外,高压线
麻雀站成阵列,那种孤独,他看到
梧桐树与樟树,早餐店、杂货铺还有
菜市场,一辆准点的火车,它的轰鸣
充斥耳膜。寂静,是从厨房,水龙头
流下的水线开始的,他想到他的
敌人与友人,他的原罪,在抵抗和潦草的
一生中,充满虚无,哦,虚无
一种心灵的分身术,让他的持续写作
变得毫无意义,一整日
他斜躺在这张暗红色沙发上,思考
而她的腿一直搭在他的身体上,在离他左手
三公分远的距离,一张旧报纸被一只打翻的
茶杯溢湿。她穿短裙,她的内衣,扔在
沙发的一角,而她的另一只脚靠在
茶几上,茶几上摆放着,泡面、零食、啤酒
和遥控器。墙上的电视机还未关
晚风经过书房,纱幔曳地,他给她念
《死亡赋格曲》里面的诗节,长发盖住的
双乳,她用右手轻蹭他的腿,用左手
支撑下巴,注视他,仰望那种声音
磁的旋律,肩胛骨与臀的弧线
像下午三点,叶的细细反光,他们谈到爱
和前女友。她说着,他从地板上拾起
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本,他死去前女友送的
名为《双重人格》的书。而此刻
蹲在墙角的猫,突然发出诡异的叫声
黑天鹅
这天,父亲说的黑天鹅在水面浮现
这只黑天鹅,在一个早上
仿佛人类此刻还未醒觉,四野静寂
我看到上帝创造出的一个颜色
在混沌中接近闪电
那是黑色的闪电,孤绝、阴翳
在河流的邈远之境,时间的空洞里面
这就是父亲说的那只黑天鹅吗?
十二件乐器
它漆黑的脖颈摆动
好像拨动世界的某一个音节
它浮在水面,观照黑的反影
那红的唇,来自一朵火焰
颔首与昂首,就是地球的低分音与高分音
这只黑天鹅,父亲说的
它在祖辈的传说中并未消失
此刻,黑天鹅扑腾起夜的羽翼
在水上奔跑起来,珠花四溅
哗哗哗,音乐在光华中波涌
自由、决绝、反叛的乐章
让这个正确的时辰,变得壮烈而哀戚
哦,黑天鹅终究会飞入雾霭更深的远山
飞走吧,黑天鹅,飞走吧
让我更清晰一些,接近父亲的真理
一个突然寂静的雨天
一个雨天
我在柜台整理旧书
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
我蓦然从厨房转入卧室整理旧书
找不出缘由
我一本一本将它们从书柜里面拿出来
又一本一本放归原处
这一系列的动作
让我感觉到一种缓慢的愉悦
这是一种进入到急遽极致的缓慢
在卧室外面,雨声越来越大
听不到声音,我顷刻间清晰起来
一种骤然的寂静,我蹲下来
想到一些很远的细节
这是老友赠我的四本书籍
米沃什《晚期诗四十八首》、布罗茨基《诗四十一首》、塞林格《九故事》
以及二十月的《双行星与小卷兽》
我幡然悔悟还没有读过它们
而后天,我却要把它们一一送还
因为一个事件,这时候的雨声
从寂静又复归浩大。我看向窗外
神经质般的用衣袖擦拭书上的灰尘
我好想把它们都擦拭干净
复归朋友送我时的模样
可这是朋友送我的
而我现在为什么都要送还?
我还没有认真读过其中的一页
或许命运原本就是一个辽阔而带有神秘的修辞
在四本书里面,我以为占有了它们
在无数平常的时刻,我那些下意识的念头里面
而这里面带有世界它所有的发生
——那些后来的幸和不幸
覃才的诗
覃才
覃才,壮族,1989年12月生,广西柳州人。
花在水里开
可利江,大学东路,西乡塘
这个属于湿地公园,这个一年长满榕树
一年都是春天的地方
我们在傍晚出现,我们要看春天
要看花在水里开
在房子里太久
花的样子,水的样子,树的样子
像异地盛产的食物
在眼睛里,在嘴巴里,在胃里,在夜晚里
健康地穿过,之后永远住下
走在江边小路上,一路安静
友人不说话,爱人也不说话
但他们都在和一些天然的朋友交谈
我这个会说话的友人,这个不会说话的爱人
在此,如自然沉默,美丽
夜晚巨大的声音
寂静落下
几个邻居深夜做饭,炒菜,吃饭
越来越晚的生活,发出巨大的声音
它让铁撞击铁的声音
它让水冲击地面的声音
彻底了很多,深刻了很多
城中村的夜里,不熄灯的邻居
一些忙碌,一些失眠,一些晚归
在感觉漫长的夜里
他们可以听清城中村原始居民
跨夜的谈话、笑声,和生活琐事
在唯一一条伸进城中村的路上
这些夜晚的声音
被很多人听到,多次思考
声音不止
夜晚就继续不止,生活就继续不止
朋友
每天在深夜过了零点
我都会从道路熄灯,店铺熄火的
东门走回住处
在无人而静寂的路上,我越过
无限熟悉的,高大的居民楼
看向远处,高处,唯一的夜晚
可以晴朗得清晰,也可以乌云得模糊
可以好,更可以坏
它们熟悉的面孔像是我的一些老朋友
肆意与随性,晚晚如此
在南宁六年,一群朋友
像极了复杂的天象,有些模糊,泛泛之交
有些明朗,真实,见面如故
在一个地方久了
在无人的时刻或在无人的路上
隔着天上或地面的高度
隔着意识或不切实的想象,我看见或想起
有或无,近或远的朋友
生长,没有尽头
在玻璃,瓷砖,防盗门上
潮湿与回南天渐渐回来了
我门窗紧闭
无能为力地防备它们坚硬的穿透
我居住的郊区,由于水与热
正在大片大片地变绿,生长
这是一种长久的种植
无关人群,地域
它长久存在,也将长久如此
与此相对,父亲与我的种植,村庄的种植
变成每天的铺路与建房子
那些被铺平或立起的石头
那些道路,街道,房子,广场
并未像庄稼那样出自土地,归于土地
它们几年,十几年的生长
并没有作物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