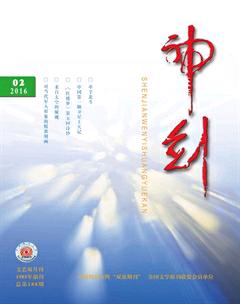从孙承宗说到明和清
石英
如今有一个词儿叫“知名度”在人们口头上和文学上经常出现。有一个四百年前的古人知名度不算太高,今天知道他的人甚至可能微乎其微。然而,知道的人少并不意味着其人便不传奇。其实,“知名度”大小,除了这人本身的分量和价值以外,还很可能有其他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在这方面,完全公平其实同样是很难的。
我说的这个人叫孙承宗,明保定府高阳人,万历进士。天启二年(1622年)任兵部尚书,但他极少在京城“坐”官,而大部分时间亲自镇戍蓟、辽,不息地练兵屯田,修城堡数十,密置火器,未曾稍懈。正因如此,后金悍敌未敢侵犯。但也许更因如此,反为魏忠贤之流所忌,横加排挤而去职。魏忠贤奸阉倒台,崇祯二年(1629年),清兵窜入大安口,形势危急,孙承宗又被起用守通州,后再驰镇山海关,并经力战收复关内的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进而伸展至关外整顿失去的疆土。愈是胜绩有加,愈受到朝堂权奸之阴谗,导致罢职而归里。崇祯十一年,清兵绕道大举攻入长城,一路疯狂掠夺践踏京南地带,悍敌集中兵力猛攻孙的家乡高阳城。承宗以七十六岁高龄之身亲率家人和乡亲守城拒敌,城卒被攻破,孙昂然不屈,自杀殉难。
应该说,明朝末年也是中国历史上各种矛盾最错综最纠结的节段之一:朝政腐败,国势衰弱,内忧外患,均达到极点。但愈是在此种情势下,正气浩然的仁人志士,不畏强暴的抗敌英雄纷现迭出,他们往往以不惜殉身的壮烈之气辉染着惨淡的历史。袁崇焕是这样的人物,孙承宗也是这样的人物,另有某些将领只是因为奉命与农民军交过手而蒙尘,实际上他们中有的也属于在国破家亡之际无愧的雄烈之士。在过去若干年,对于这类人物,乃至更早和更晚些的正气英杰,不知为何竟被习惯地加予“愚忠”的帽子,好像他们的奋不顾身,他们的甘心死节,只是效忠姓朱的或姓赵的某个人的行为。其实人们往往忽略了天地间那般擎天拄地之气,即文天祥在《正气歌》首句所吟:“天地有正气”。许多志士仁人正是天地间这种浩然正气的代表,他们惊天地泣鬼神的非凡行为,足以体现出他们是无愧于人间正气的化身,当然在封建时代,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这些英烈人物头脑或多或少会被忠君思想所影响,但哪方面是主要的,哪方面是次要的,只能说有一点是肯定的:在那个皇权唯一的封建时代,臣子的任何作为任何行动,只能是在“真龙天子”的旗号下才能得以施展;稍有不慎和意外,都将万劫不复。过去许多人往往将智勇杰烈之士视为无异于“傻子”,其实是不妥的。他们结局的至惨——因忠勇反遭戮,并非完全因为认识上模糊,而多半是封建主子的本性使之然,甚至是封建主子与外部敌人有意无意直接间接“定点清除”的结果。
有一个也许是小儿科的常识是:明朝中晚期的统治层已是腐朽崩颓到了极点,明武宗正德皇帝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可算是出格的“大玩家”,如果不是还有些家底,王朝死期未到,刘六、刘七的农民造反不多就可以埋葬了大明;接下去的明世宗嘉靖,二十多年不上朝,醉心于炼丹以求长生,弄了个严嵩父子擅权二十年,国政已是混乱不堪,如果不是尚有个别明白点儿的大臣撑着,戚继光等抗倭名将卫疆杀敌,东南半壁将金瓯或缺:随后的隆庆皇帝短命,万历(明神宗)昏聩奢靡,尽管在位时间不短,但民怨沸腾,尤其是辽东边患日甚一日,已露出覆亡之先兆;至于天启(朱由校)朝,皇帝偏喜木匠工艺,朝政几乎完全由魏忠贤阉党以及乳娘客氏所把持,东厂、西厂、锦衣卫“特务”横行,正直之文武大臣动辄得咎,有患更加酷烈。及至朱由校死,朱由检(崇祯)上台,虽然除掉了魏忠贤和客氏之流,期望挽救颓势。如前所述,不是没有能臣名将,但由于崇祯夙夜惊心,捉襟见肘,疑忌重重,自毁长城,终于导致李自成势如破竹,直薄京城;而清兵与吴三桂联手,关门大开骁骑涌入,自成惨败大明亦彻底覆亡。
另一个简单的逻辑亦应运而生,至少仍见诸某些“学术文章”,认为清朝之所以能够取代明朝,“充分说明”新生事物势必要取代腐朽事物;“新的生产力”必然要战胜“落后的生产力”。是吗?这种说溜了嘴的推论,恐怕连皮相的“理论”也构不成,因为它不符合事实。
不错,后金,或曰“大清”之初,较之“大明”在年头上是短一些,说是“新”一些也还说得过去;然而“新”并不等于代表具有进步意义的文明。稍稍查检一下史实便不难知道:后金自努尔哈赤、皇太极以至多尔衮等等,自起家进而势强,并非只是凭借在战场上一枪一刀地打败了明朝军队,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酷好杀戮与疯狂掠夺。在关外期间,他们占抚顺、辽阳、沈阳,几乎将汉族平民杀戮殆尽;不仅如此,即使在天启和崇祯两朝尚在京城苟延残喘之时,清军骁骑即多次绕过明军把守较严的山海关进入长城,长驱直入直隶、山东,大肆抢掠劫夺,烧杀无已,然后将妇女、财帛装上车辆,满载而归。本文开头所叙的孙承宗就是与清军遭遇不屈抵抗而死。其时为1638年,乃崇祯缢死明亡之六年前;而明军名将卢象升也是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在今河北中南部与清军力战时死难。我们对交战双方且不细分孰为正义孰为非正义,但至少不能说清方是“新生事物”的代表吧?当然,如硬要以当今影视屏幕上之戏说种种随意定位,那又是另一回事。至于清方是否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我想大可不必多占文字篇幅拿着歪理当正说。可能不少懂得一点社会经济发展历史的人都略知一二:中国北宋、南宋某个时间段和明中叶之后,以长江中下游为代表的经济发展已达到相当程度,在当时世界上亦属上游,有专家考据甚至已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清方在经济发展上显然还处于较原始的阶段,至多是以畜牧为主初始农耕的局面。但历史的发展往往会出现这样表面看来颇有点匪夷所思的现象,建立在经济比较原始基础上的政权及其战争机器,利用其所长的一面开足马力硬是冲垮了经济比较发达的敌对方。当然,如果全面地说,所谓生产力并不狭隘地仅指经济上比较繁荣,还应包括其综合国力(如士气等等),然而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以掠夺获取的财富以杀戮与破坏来削弱对方置于“先进生产力”的天平上,是吧?按说这本不是什么多么难解的问题,历史上不乏落后生产力的一方(尤其是在冷兵力时代)击败了经济相对繁荣,生产力相对发展的战争方。因为,当我们仔细地全面加以剖析,将会发现:之所以出现了这样的胜负结果,是有许多必然以至偶然的因素所决定的。这一点,绝不是庸俗的社会经济学所能简单加以回答的。时过二三百年,如果向被奉为著名有作为的“好皇帝”康熙、乾隆地下有知,我们不妨直言相告:你们先辈用以起家的资本,是相当野蛮而不光彩的。有据可查的是:当17世纪头二三十年,清方在外残酷杀戮与压迫手无寸铁的汉人,曾感叹曰:“明朝当然不怎么样,清朝更叫我们没法活。”所以他们中的仅余者又纷纷南逃。袁崇焕就是看到此点,争取民心,以辽人守辽地,结果获得了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但是因为明朝最高当局昏弱到家,从根本上已回天无力,徒有一二点闪光前景出现,也被他们自己扼死在末世的黄昏里。尽管如此,明朝的一些直臣良将面对清方的酷暴,有时知其不成而为之,甚至自身被罢职多次,只要有机会仍然不惜拼死一战,实则是将抗暴、卫疆、忠君、护民融为一体,而不是某种单打一的思维所能全面理解的。
有一种“移代法”或曰“颠倒对照法”也近于为了证明清取代明的绝对必然性,提出之所以出现“康雍乾盛世”,“雄辩地”说明清优于明。但却忘了,这里出现了一个时代段倒置比较的误差。因为明朝初期的洪武、永乐年间也出现过较有作为、社会趋向繁兴的局面,只是未能避免日渐腐朽、盛而至衰的规律。同样的道理在清朝亦然,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之后道光、咸丰朝即出现衰象、列强入侵终至晚清的国将不国。所以,“移时比较法”是根本站不住的。
具体而言,明朝之败亡在于:
1.统治层自身的极度腐朽昏弱,在许多方面可谓是自掘坟墓,如上所述,偶有胜绩,亦为更大的负面因素所抵消,乃至“自愿”葬送。此根本之点令当时多少忧时之士徒叹奈何。
2.敌方(后金——清朝)之强悍酷暴,尤其是骁骑硬弓远胜明方,一般军队均难以抵挡。这在冷兵器时代是无可置疑的优势所在。上溯至唐、宋,面对游牧民族骁敌入侵,结果也证明了此点。袁崇焕所获宁远、宁锦大捷,应主要归之于战略战术之得当,即以坚城利炮防御为主(因野战清军易发挥其优势)。后世人们常说不要唯武器论,从一个方面说是对的,然而不“唯”并不意味着武器的优劣不重要。事实上,袁崇焕守城的成功,与当时明朝自澳门购得葡萄牙制造的“红衣大炮”威力有关。当年戚继光之所以能胜倭寇,也是因为他特别重视武器与其他器械的改进和“研发”。如鉴于明军之刀较之倭刀既短又不够锋利,他亲自动手加以改进,结果效果大增;尤其是他就地取造“土”兵器狼筅,使倭寇十分头疼,感到无法对付,南昌戚家军则迭获大胜。但没想到的是:戚离世几十年后,明军在许多地方都难敌清军。譬如在“军装”的实用性上,明军就居于下风,据说清军的马蹄袖,在北方的寒季作战,手握兵器能够御寒;而明军的衣袖毫无遮拦,由于手冷挥洒不利,仅此一点便输于对手。总之,综合军力清军居于上风。
3.清军的嗜杀、掠夺甚至屠城,从一般心理学而言会激起对方军民更加痛恨,加剧反抗。但对加予方来说,却旨在以高压杀戮以削减对方人民反抗意志。当时的清朝统治者以此攻略不断制造血腥事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即是。他们对占领区的疯狂掠夺其实也是一箭双雕,既扩大了已方战争资源又破坏了对方的生活和再生产的基础。其实,近现代的军国主义侵略者往往也采用灭绝人性的屠戮手段使对方军民产生恐怖心理,以期不敢反抗而乖乖臣服。加之清方惯于利用汉族叛将如洪承畴、吴三桂等残酷镇压南方抗清力量并滥杀无辜,应该说,这一切对于牢牢建立清朝的统治是起到作用的。而血腥的“文字狱”则是这种淫威的继续。应该说,这也是清之所以压倒明的血腥然而有效的手段,可以说,他们将这种手段运用到了极致。显然,他们的“成功”最初绝不是因得人心而得天下,在很多时候,王朝的更迭并非像某些善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自然而完全合乎逻辑。清取代明就是一个不循常规思维而靠血腥高压而取得战术战役胜利的典型。
4.当时明朝境内的农民军(主要是李自成和张献忠)客观上也起到了“内外夹击”的重要作用。也许在起初,农民起义军在天灾人祸忍无可忍之下起来造反,当势力壮大之后便产生夺取帝位改朝换代的愿望。在明朝面临骁敌进逼的其有利的形势而“趁火打劫”,我们不是他们的参谋长不得其详,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他们是尽量避免与清军碰撞而眼见清军如入无人之境。例如,崇祯末年,清军长驱直入明朝腹地,攻城掠地,名将卢象升与之血战,而自成军距此并不远,他们却仍在积极进行攻取北京的准备,并未暂时息战以减轻明军之压力。这在客观上使明军首尾不能相顾,牵制了若干军力不能全力对付强清。及至明亡,清军与吴三桂军合击农民军,后者基本上是一战即溃,全无有效的抵抗能力。李自成军如此,张献忠军亦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顺理成章地被各个击破。
5.实话实说,是明朝气数已尽。“气数”,并非是活该被批判的“宿命论”那么一言以蔽之,而是事物发展到非常阶段诸种矛盾积累叠加的一种复杂态势,一般应认为是近于无可救药,甚至不以某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论这个人的主观意志有多么坚决,有几许令人同情的成分。我总觉得,明朝到了最后崩颓的关头,可算是中国历史上处于类似境况的活标本——顶尖级最走倒霉字儿的典型。当然,“大明”是该亡的角色,但“大清”也并非天经地义非它莫属该坐天下的主儿,而李自成也不是正气冲天理所当然应做皇帝的理想人物。只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应运而生地拣了个大便宜,可一坐上那个龙墩就又兴衰了二百几十年。
话又说回来,开头提到的那个孙承宗,咋就能引出明清两朝这么大的话题来?是不是有点不大相称?莫急,听我慢慢道来。如论开疆拓土,大有作为的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皇帝中的养生泰斗、《戏说乾隆》中的主角爱新觉罗。弘历,孙承宗乃至袁崇焕都还够不上那般顶尖的重量级历史人物。不过,如果不完全醉心于“得到了就是得到了”绝对实用主义的逻辑,落入“胜王败寇”的怪圈,而是还要兼顾到人间正气、真善美的人性这一点,我倒是愿意给袁崇焕和“知名度”更小点儿的孙承宗投上一票。因为他们在那个历史阶段,以自身的气节和血肉之躯诠释了做人的真正含义——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从一个人引发出两个朝代的更迭难道还有啥不相称的吗?当然,唯觉遗憾的是:区区几千字难将两朝兴衰表述得很细很透,不敢说是惜墨如金,只能是长话短说而已。
责任编辑/兰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