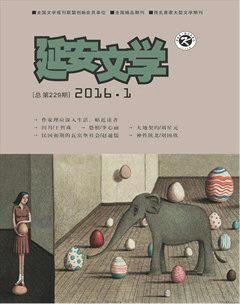诗意的倾诉足以让时光倒流
绿岛
我确定诗人李炳智是那种内敛、敦厚而不事张扬,内心却是澎湃起伏、运行着炙热情怀的西北汉子。能够佐证这一点的,除了他谦和、善良的秉性之外,就是他的诗歌。由此可见,李炳智的诗歌既是他人生的名片,也是他生命轨迹中梦幻与意向相互指引的导航。
从诗集《受困的美人鱼》《一方水土的爱恋》以及大量发表于媒体和网络之上的诗歌来看,李炳智基本是采取一种温和的娓娓道来的姿态,用一种近乎平静、祥和的叙述来驾驭自己的诗歌创作的。于是,在读他的作品时,就产生了一种无所不在的疏朗、宁静、飘逸、典雅的阅读快感和心灵上的慰籍。诗歌中舒缓的意向流韵簇拥着澄明、跳跃的乐感式的语言组合,架构出一方古体诗词中特有的体式和不乏现代情感的抒情方式。
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独特的带有心灵痕迹与情感色彩的表现方式,由此而构成的诗意传递,使得李炳智的诗歌呈现出一种鲜明的、不可复制的、独特的审美意蕴。
那么,这种审美意蕴的核心与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它不是气吞山河的抒情与架构,也不是波澜不惊的细致入微的情节描摹,不是掏空心思的不着边际的生硬想象,也不是故弄玄虚的假大空式的“主流”与“口水”。诗人的李炳智自有属于他自己的独特表达,那就是叙述。
李炳智的叙述,是一种关于折射心灵和透视情感的叙述,是诗人为找到一条回家的路而迈出的每一步坚定的足迹,更是一种看似平和、舒缓实则水深万丈波澜不惊的大意境、大气场。
正是这种纤尘不染的娓娓道来,童子稚气般的来去无痕,风雨初霁天边彩虹的圣光乍现,形成了李炳智诗歌中某种“道场”的巧妙设置。于是,淡淡的禅意伴着悠悠的哀思,浸润着他的诗歌一步一步走向故乡浩渺苍凉的高原。那里既是诗人的故乡,又是养育、培植诗歌的天堂。李炳智的诗歌沿着塬上的沟壑纷纷涌进现实社会的在场,诸多心灵的感受和个人的喜怒哀乐幻化为行走的诗行,于是就有了诗人对于《一方水土的爱恋》转化为《受困的美人鱼》的奇妙想象的延伸。
“我喜欢这样的诗:忧郁、典雅、高贵、真诚。语言呛啷作响,充满了古典汉语的节奏、韵律感和美感。那抒情的口吻则是徐缓的,有一种戴着白手套的贵族式的忧郁,像一位拉着管风琴边走边唱,从高原上一路走来的行吟歌手。”这是著名作家高建群先生为李炳智诗集《受困的美人鱼》所做序言的一段话,很精彩也很形象。而高先生对李炳智诗歌的表述,就是我所言的纤尘不染的娓娓道来,童子稚气般的来去无痕,风雨初霁天边彩虹的圣光乍现的另一种表达,而最终的目的,还是探究诗歌中那个时而有形时而无形的“道场”的设置。用作家杨葆铭的话说,就是:“语言的精粹和意向的唯美。”(《诗生活让人沉静自安》——读李炳智“一方水土的爱恋”)。而杨葆铭先生进一步提到的“能从鸽子翅膀干涩的抖动声中听到起飞的艰难”(《小诗有味似连珠》——李炳智诗集“受困的美人鱼”序),则是对以上命题的合乎理性拓展和延伸,并以此昭示了诗人对于过往路途坎坷经历的感悟和历练。
诗人是成功的,有以下作品足以证明这种成功是真实存在的:
捧一掬溪水/洗尽市井沉积的铅华/乘一弯新月/寻找遥远而梦寐的牵挂//久别的路/延伸在匆忙的脚下/村口的老树/用月影婆娑出一地暗花//小河里高歌的/似乎还是童年的那只青蛙/挑水的小黑哥/月光漂白了满头的乌发//火红热闹的老宅院/让荒废代替了喧哗/洞房里娇羞的新娘/已笑掉了两排白牙//山歌里走出的大叔/长眠在老柳树下/曾一起捉迷藏的兄弟/以一口老矿为家//路旁的小伙子/容颜上写满惊诧/盘问我这陌生人/你要去谁家
——《寻找遥远的牵挂》
一双狗眼/在大十字中央/射出两束不屑一顾的光芒/矫健的卧姿/让飞逝的车轮/凝固出战战兢兢的恐慌//红绿灯/间或明示/人来人往/冷漠的目光/从狗眼里射出/流浪者对生的悲凉//任司者的鸣笛/形成此起彼伏的声浪/那稳坐泰山的心境/逊色了人世的胆量//把藐视交规的举止/异化成无谓的迷茫/莫非是/宠爱与遗弃的交替/成就了这羸弱的昂扬
——《蹲在十字街上的那条狗》
走了这么久/谁解我的乡愁/绵绵的秋雨/弥漫了我相思的路//情越衰草洲/身偎故墙头/用一双杏眼/望断天涯路//童年那棵老树/记忆着曾经的相守/拥着我柔弱的身子/劝我别泪流//寄回的新衣/一层层缠裹/怎抵这/孤独冷清秋/别慕我的锦绣/莫羡我今天的所有/孤独的郊外/冷风嗖嗖//古宅烟缭雾锁/爱巢香艳炫目/孤衾怎抵那/相拥的温柔//拎着一箱思念/踩着孤单的清秋/收获前所未有的酸楚/我要登上一叶舟//任寒气封喉/融烟雨心头/阳光会在/明天的聚首
——《乡愁》
在这些作品中,无论是寻找遥远的牵挂,还是讲述蹲在十字街上的那条狗的身世,更不用说中国文人写了几千年的乡愁,诗人都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平静地站在诗歌之外,然后又平静地用铺叙的方式去完成诗歌文本的创作的。这就是李炳智的独特的方式,他让诗歌中种种大的情感波动和意向的跳跃舒缓、平和了许多。我们几乎见不到那种或金刚怒目或多愁善感,或坐卧不宁或仰天长啸式的大起大合的情感冲突,随之而来的确实一缕浮云一样的安详与静穆。
这是一种古典式的或贵族式的雍容与华贵,在配以古诗词意境中所特有的情感架构和书写句式,形成了一种古今融合、感情纵横、现代自我意识浓烈的审美复合之意蕴,其形式的美与内容的充实、饱满不言而喻。上文所引的《乡愁》,可谓此类诗歌的代表性作品。
下面再看一首铿锵、悲愤的近乎于控诉、声讨的作品:
我想逃离/逃离掩埋30万冤魂的屠场/我想回避/回避陈列室利刃之上的血光//我想忘却/忘却70年前山河破碎的彷徨/我想抚平/抚平那场劫难/留给中华民族的伤//可是/他们不让//他们给杀人如麻的恶魔/带上血迹斑斑的勋章/他们用靖国神社的鬼火/年年岁岁把我们的包容性考量//他们霸占我们的岛礁/他们抢夺我们海洋/他们企图/陷我们于四面夹击的恐慌//面对贼寇的嚣张/挑在刺刀上婴儿惨叫声/又在耳畔回响/遥望武装到牙齿的豺狼/机关枪扫射同胞的幻影/又从脑海播放//我似乎看见那些被活埋的同胞/至今站立不躺/我依稀见得那些被烧杀抢掠的村镇/残垣和焦土依然黑亮//历史悲剧岂容重演/祖国河山怎容再一次横行饿狼//看啊/勿忘国耻/这四个字闪现死难者白骨里/燃起的磷光/听啊/倭寇军演的炮响/企图施展70年前/亡我之心的伎俩//记住啊,记住/贼寇狞笑/那是他们获得猎物得意洋洋/海岸那边张牙舞爪/那是他们预演图财害命疯狂//醒来吧,醒来/把刀枪擦亮/将子弹上膛/侵略者胆敢来犯/定要他们/把70年前欠下的血债/一并清偿
——《勿忘——写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这是一首质感非常沉重的作品,也是李炳智不多见的一种金戈铁马式的悲愤、忧郁的诗歌创作。全诗的表现形式极尽控诉、声讨之能势,一种民族之痛、精神之痛跃然纸上,体现了诗人难以抑制的家国情怀和高尚情愫。
我始终认为,诗歌写作是个人化的、情感化的艺术,是心灵世界的诸多感受借助于诗性的文字表述而达到释放、发泄的一种愉悦和快感。所以诗歌是个体化的东西,它也承担不了重大的历史或现实的负荷,更不能对于严酷的社会现实起到任何的改变、拯救或颠覆作用。诗人峭岩曾说:“诗歌不能改变什么,但它一定能够证明什么。”我认为它所能证明的,只是诗人内心的、深层次情感的在某一时期所留下的痕迹。
李炳智的诗歌,完全摈弃了那种假、大、空的所谓“主流”的时代传声筒式的粗鄙、轻浮写作。他让诗歌回归于心灵世界的同时,将真善美的优雅情怀诉诸于生命的年轮之上。他坚信诗歌就是自己的上帝,没有什么力量和意志可以改变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的初衷。而诗歌将要证明的,则是浮华背后的空空荡荡的宁静,以及时间的绳索捆绑着一群堕落的灵魂走上历史审判台的悲壮。
从诗歌本体上的意义而言,或许李炳智应该意识到在保持和发扬业已形成的创作风格的同时,如何面对创新和突破自己的命题。这一点不应该是炳智一个人所面临的问题,而是所有有良知、有担当、有才气、有魄力的诗人所共同面临的课题。况且,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无序的、混乱的甚至是淫邪的丑陋不堪的诗坛。
从大的人文环境与历史时期来看,当代的中国文坛需要的是斗士的正义情怀,需要的是猛士的殉道情怀,需要的是鲁迅精神的延续和发扬。信念和信仰,正义和正气,才会使诗歌乔木郁郁葱葱。
责任编辑:高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