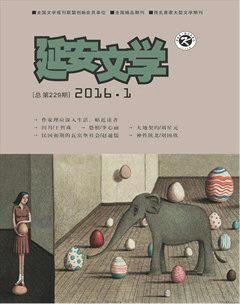马坊书(节选)
耿翔,陕西永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参加第九届“青春诗会”,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出版《西安的背影》《采铜民间》《长安书》《大地之灯》等多部诗集、散文集。曾获老舍散文奖、冰心散文奖、柳青文学奖及《诗刊》年度奖等。
1
屋后的葵花/你不诉说,我也知道金色/落在一个
人身上的感觉。也知道马坊书里/如果没有你的旋转,
我头顶的天空/不会紧跟着一个人/涌现花朵。而我最
熟悉的/一座老屋,也不会接受/金色的淹没。
我在马坊的原野上,没有看到过大片的葵花。按说,这些在形体、色泽上都十分出众的植物,应该享有土地的最高礼遇,应该傲视万物,在马坊的胸脯上疯狂地燃烧。
事实上,它从不去占据五谷生长的原野,它从一切平坦和肥沃的土地上撤退,只把自己金子一样的头颅,埋在某一户人家的后院里。
因此,我只能用屋后的葵花,来称呼这些稀客一样的植物。
也正是葵花的不择水土,使它在我的记忆里,有了一些神秘感。比如一孔塌陷下去的土窑洞,用不了多久,就被一人高的蒿草覆盖了。白天路过这样的地方,还可以伸头看一看,大不了看到一眼荒凉,至多在心里问一声:这是人曾经住过的地方吗?到了漆黑的晚上,就很少有人的脚步光临了,只有风和一只还没有回家的猫,有可能在蒿草里穿梭着。但也有人家,在这样的塌窑洞里种上葵花,不仅驱走了荒凉,还使它成了一处招人去的地方。
这就是兴娃家的塌窑洞。和我们隔了几家,我是看着这孔多年的老窑洞,怎样被风雨一天天侵蚀而塌的。这孔窑洞里安了一台很大的石磨子。最初,窑洞是从中间塌了一个洞,中午阳光能从洞口照下来。我们推着磨子磨面的时候,不断地看着自己从阳让光里走进走出,身上的疲劳就淡漠了些。按说,这样的窑洞补一补,也就好了。可兴娃是个失去一只腿的残废军人,一生都拄着拐杖,也就没有力气修补它,任凭它越塌越大,最后连石磨子都埋没了。好几年时间里,这里都是一个荒坑,兴娃拖着一条腿坐在坑里,很有一种悲残的意味。
等他的叫新社的孩子,在贫穷中长得有了一些力气,我看见他把塌窑洞收拾平整,先在里边种上一种叶子阔大的中药,再种上一丛葵花。到了夏天,葵花从很深的土坑里跃出地面,很黄的葵盘,使这个一直破败的残废军人家里,有了一丝生气。此后的许多年里,我每从新社家的后崖背上经过,要去庄背后,或去木张沟水库,都要伸头看一看这里的葵花长多高了,开花或结籽了吗?
现在在记忆里,只剩下一个画面:
一株开得金黄的葵花下,半躺着一位残废的人。
我们从他的外形上,已找不到任何军人的标志。
他已经沦落为一个村上,最贫穷和最可怜的人。
我总以为,葵花能盛开在兴娃家的塌窑洞里,被全村人年年看见,这很有一种象征意味。也就是说,在兴娃活着的时候,不说他被这个时代遗忘了,至少被这个村子冷落了。在那样的年月里,一村人还真不如一株葵花,记着按时节来陪伴他,给他一些温暖。
此后,在这个窑洞很多的村子里,我只要遇上一孔塌了的土窑洞,都会伸头看一看。我的本意是想在这里看见葵花。确实,我看见了一些葵花,也看见了一些白菜、萝卜等菜蔬。我由此想,马坊人对土地的热爱,是一种很实在的热爱。只要是土地,就有生殖能力,他们一寸都不会遗弃。
我也知道在马坊人的心里,与小麦、玉米相比,葵花开得再好看,也是一种边缘植物。我在一大片村子里,只见过北胡同、耿家山、南场里、张家村、拐胡同这几处偏远的地方,从一些人家的屋后,偶尔有葵花探出头来,让人睁大了无生机的眼睛,终于在村子里看到了一些亮色。
然而这样的亮色,多在村子的破烂处。
等我后来读完我最喜欢的凡高的六十幅名画,写成《凡高书》时,我知道凡高这样的画家,只能诞生在阿尔。我的故乡马坊的土地上,没有他要画的那么多的葵花,也没有他要还原的那么多的色彩。
这些葵花和色彩,在阿尔是疯狂的,在马坊则是沉寂的。
等我在我家的屋后,亲手种植起葵花的时候,我已长大了,也快要离开村子了。那时我家的院子统一往后移了十多丈,一圈子围墙打起来,还没有盖房子时,我央求父亲,顺着围墙种满了葵花。在葵花破土、抽叶、开花、结籽的日子里,我只要闲下来,就一个人走进去,在每一株葵花跟前站一会儿,伸手摸一摸它的秆和叶子,再看看葵盘,是否又长大了一圈?有时候,我会一个人蹲在院墙的豁口上,用一整晌的时间,看葵花在风里摇晃。我那时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直至双腿都蹲麻了,也不想起来。
我后来的许多想象,就是葵花给我的。
我这样看葵花,也好打发成长的烦恼。
自从屋后种上葵花,我每次从庄背后回来,都要隔墙喊一声母亲,直到她从屋子里走出来,一手扶着后墙,一手遮额看我。这个时候,母亲的身后一定有几株我种下的葵花,依着她的脊背、肩膀、头部燃烧着。后来我读凡高的十二幅《向日葵》,看着第一幅中的三朵大花,看着第二幅中一朵已经结籽,一朵正开着花,一朵含苞欲放,看着第三幅中的十二朵花与蓓蕾,看着第四幅中的一束十四朵花,我想那时在母亲身后,有多少朵葵花呢?
如果要我画这些向日葵,我画多少朵,才会画到母亲的心上呢?
但我在一首诗里,是这样说的:“屋后的葵花/没有一只握笔的手/在我之前,触摸你沉静在/村庄上空的一头金色。而一座农家小院里/有了一道,天上的阳光/有了被众神,突然照亮的感觉/扶着你,探出土墙的身子/母亲的眼角,也有了/金子浑身的亮。”
后来随着我的离开,葵花终止了在我家屋后的生长。
但葵花始终站在母亲身后,留给我的绵长的记忆,一直跟着我。就是来到没有一块泥土,可供葵花生长的长安,我依然这样怀恋:屋后的葵花,你不诉说,我也知道金色,落在一个人身上的感觉。也知道马坊书里,如果没有你的旋转,我头顶的天空,不会紧跟着一个人,涌现花朵。而我最熟悉的一座老屋,也不会接受金色的淹没。
确实,葵花在屋后开花的日子,是老屋被金色淹没的日子,是母亲被金色淹没的日子。我到现在还在想:在这么贫穷的地方,怎么拥有这么贵重的色彩?
这么贫穷的人家,怎么活在这么高贵的色彩里?
我知道屋后的葵花早已没有了,母亲也故去多年了。但只要回到村上去,我总想一个人走到庄背后,总想放开嗓子喊一声。随着喊声在风中的传递,我想看见沿着我家的后墙,有旋转的葵花,也有母亲的目光,一起为我上升着。
我会抹去眼眶的泪水,对着我一定能看见的屋后的葵花,这样朗诵:
举着一个人身上的光芒,静守在她的屋后,葵花啊,我看见佛光。
2
吹过午休的村庄/一阵风,从临近的麦穗上送来/狼
的目光,我握镰的手上/没有一把麦芒,直接刺疼肌肤的
那种感觉/我想麦子,在一阵孤独的呼吸里/也闻到饥饿,开始从乡村/威胁到一匹狼。
一直很喜欢《水乳大地》这样的书名。它让我们与大地的联系,突然密切起来。而大地给予我们的恩情,我在心里想了好多年,想找到一句很能感动我的话,作为献给大地的颂词。我从我熟悉的那么多的汉字里,都没能找到它。
我想水乳大地,就是我要找的那句话,也就是我对大地的颂词。
现在,我就行走在马坊这块水乳一样的大地上,心里的感动,像风吹在一片连天的麦芒上,是一种铺天盖地的金色的感动。当我一个人停在麦子的这种包围中,身上却被孤独笼罩着。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也是大地没有想到的。
我知道此刻的我,更想远远地站在麦子的金色以外的人。他们身上没有可以照耀大地、自己和我的金色,但麦子的金色,总是从他们的手中撒出来的。我也想很近地,围绕在他们身边的那些动物,比如一只猫,一只鸡,一只狗,我都会像人一样怀念它们。我也从它们身上清楚地知道,在水乳一样的大地上,其实谁的一生都不容易。
包括狼这种让我们的感情,始终很复杂的动物。
我在马坊生活时,人们的普遍心理,是不会去怀念一只狼的。因此我想,过了几十年后的今天,突然想起要怀念狼,可见这个世界,已经面临着许多本质性的问题,已经威胁到我们的生存了。现在,我要从记忆里,搜索一些有关狼的残片,以表明马坊这块土地上,过去的生物链是很完整的,人与自然是很和谐的。它在我清贫的童年,确实是一块水乳一样的大地。
马坊以它的很苍茫的自然,从小启示我,人的心里一定要有一种敬畏。这种会使我们活得高尚一些的敬畏,必须由大自然来给予。比如,这里的黄土山,一般都很质朴亲切,可以让我们一步一步地去穿越。但突然有一些山或沟,会是另一个样子,会让我们把自由穿越的脚步停下来,然后想,大自然可以任我们畅游,却不容许无节制的入侵。也就是说,人的脚步不是哪里都可以去,一定要懂得留一些地方,至少把它留给在我们心中,一直存在着的神。再比如,牛羊多么温顺,燕雀多么可爱,猫狗多么依人,但请记着,在动物的世界里还有狼。我想早些年,马坊周围的山沟里,所有草木长得那么茂盛,还是狼的出没,阻挡了人的脚步,让草木有了一个安静的生长环境。
我记忆中的狼,很多时候和落雪有关。听大人讲,村北和村西的沟里都有狼窝。到了冬天,忍受不了饥饿的狼,会踩着雪地向村庄靠近。我家的几头猪,就是在落着大雪的夜里,被翻墙而入的狼叼走的。有一次,听见院子里有响动,母亲一把拉开窗子喊叫,我也爬起来向外看。被雪映得很亮的后院里,一只麻色的狼,叼着我家几十斤重的猪,前腿一伸,后腿一收,突然腾空跳跃起来,翻墙逃走了。狼的动作像闪电一样,在我刚睁开眼睛的瞬间,就被完成了。此后的好长时间里,我都觉得那只勇猛的狼,还留在我家的后院里,还在那堵很高的土墙上,拼命地跳跃着。
狼这样入侵村庄的事,年年都会发生的。
我由此想到村人:平时是如何对待狼的?
我的记忆中,没有一只狼被村子里的人打死过。就是村里最恶的人,只要和邻家发生口角,就会肩上铁锨开打,也没有对闯入他们院子的狼,动过手脚。为了防止狼的入侵,许多人家在后墙上,只围一些带刺的稍林。据说狼一跳稍,浑身就会腐烂的。大人也教我们,在路上遇到狼,先用土块划一个圈,把自己围起来,再向外撒一把细土。我不知道这些带有巫性的东西,是从什么时候传下来的,到底灵验不,因为我没有与狼遭遇过。我知道我的母亲,在路上遇到蛇或狼时,是不会出声的,会在原地跪下来,默默地磕上几个头。事实上,她一生多次遭遇过这样的场景,都被她的一跪化解了。因此,我很羡慕村上的老人们,他们几乎没有文化,但他们那颗很淳朴的心,在接近自然的程度上,后来人是赶不上的。
从雪地上出入村庄的狼,会把他们的痕迹留下来。因此,我们在雪地里,常常会发现梅花一样的脚印,不用说,那是狼在这个很寂寞的冬天,留给我们的一些好看的东西。沿着这样的脚印,一定能找到狼窝,但谁也不会去找,只是看上一阵就够了。
和狼一次最近的相遇,是在村西的高硷坡上。这些被庄稼围猎着的地块里,我因每天的挖草,几个人或一个人,都被反复地出入过,却没有遇到狼。一天,我和父亲经过这里,他手里提着镰刀,我跨着草笼跟在后边。前边的土硷上,突然出现了一只狼,站在那里看我和父亲。父亲一生的胆量很正,只见他把我拉在身边,将明晃晃的镰刀举起来,朝狼喊叫了几声。那是一个被苦难和贫穷,磨练得有些苍老的男人的声音,狼也似乎从中听出了什么,不再对视,掉头跑走了。父亲只是象征性地追了几步,回过头继续走路。父亲不是闲散的人,他任何时候出现在田野上,手里都握有一种很锋利的农具。每次遇到狼,完全可以搏斗一番,致狼于死地。父亲说,他一次也没有过。为什么要伤害它呢?老天让它在村外活着,肯定有老天的想法,人是不能与老天争什么的。
这是父亲对自己行为的一种解释。
也是他对动物的唯一的看法。
再一个与狼有关的场景,就是在大片金色的麦田里。
在麦子接近成熟的这个时候,大人一般是不允许我们到野地里去的。因为狼藏在麦田里,人是很难发现的。在我们周围的村庄里,发生过一些狼伤人的事情,大多都是在麦田里。因此,在开镰割麦以前,大片大片的麦田,投在我的心里是一种金色的阴影,是一种危机四伏,是一种不安宁。我想麦子的成熟,会不会因此变得恐怖一些?或许,因为狼的出没,阻止了人的脚步的践踏,麦子的成熟更安宁了。
我觉得这时的狼,就是保护麦田成熟的一条护符。
好些时候,我是站在村头的最高处,盼着吹过正午的村庄的一阵风,能从临近的麦穗上,送来狼的目光。我觉得我握镰的手上,没有一把麦芒,直接刺疼肌肤的那种感觉。我也想临近成熟的麦子,在一阵独孤的呼吸里,也闻到饥饿,开始从乡村,威胁到了一匹狼。真正懂得乡村的人,会知道麦子越是到了开镰的时候,越是一村人最饥饿的时候。这时的狼,会披着一身金色,在麦田里不停止地穿梭,但它和一村人一样,却是饥肠漉漉的。成熟的麦子,对它没有任何意义,它需要的是奔跑在麦田里的野物,以至村里猪羊。后来,我知道更多的时候,带着一身的饥饿,狼会远离人群,这就像天底下的农民,把身子始终埋在苍茫的原野上,想让饥饿,沿着泥土的气息消失。
再后来,我以一位诗人的眼光,想象在麦穗上开始成熟的乡村,应该知道人活在哪一处乡土上,都要敬畏五谷。
也要敬畏带着一身激情,接近过我们的狼。
狼带着一身激情,接近村庄、人群和牲畜,这是我的直觉。我也很喜欢这样的生态环境,人能与狼遭遇,应该是人的另一种幸福。现在的问题是,狼在我们的村庄里,再也见不到了。
是什么让狼突然远离呢?
有人以为,由于狼群的集体消失,人失去了对抗物,人性中的狼性也消失了。他为此长久地叹息着。我没有这样的感觉和想象,反倒觉得是人性中的狼性,在生活中暴露得太多了,让狼也产生了恐惧,也要躲避开人群。
对狼的怀念,仅有文字是靠不住的。我们只有在内心里,彻底退回到几十年前去,看看那时的村庄里,人在什么时候出没?牲畜在什么时候出没?狼会在什么时候出没?那时的男人和女人,又是怎么对待他们以外的万物的?
还是我开头说的,要有一片水乳大地,要有一颗敬畏的心。
狼也是很有灵性的动物。
当它有一天闻到这些,像气息一样在大地上弥漫,在人的身上逐渐恢复,狼会带着一身激情,重新回到人群的周围来。如果有那个时候,我会把我的这些写狼的文字,焚烧在马坊的一块金色的麦田里,或一个落雪的冬夜里。我要让狼从此知道,在我的《马坊书》里,它是我写到的第一个野生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