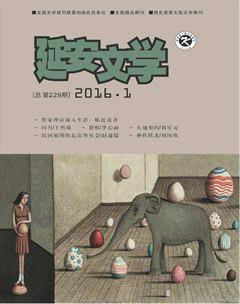小小说茶馆
“夜游神”
拓 毅
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还未结婚。因为到了晚上他就挨家挨户地去窜门,所以村人叫他“夜游神”。
他要去的院落,多地处僻静,且多是男人常年在外打工,家里只留守着年轻媳妇“守活寡”的人家。进得门,便说:“我没电视,来你家看看电视!”说罢,不管窑主人乐意不乐意,就坐在炕沿或板凳上,边看电视,边同窑主人搭讪。见窑主人爱理不理的样子,就知趣地怏怏走出窑门,向另一户人家走去。
就这样,在一个晚上,他会游走几户人家,直至眼涩了,发困打呵欠了,才回归到自己的那孔破窑里,在睡梦中继续他的夜游。
有一个“守活寡”的,对他的光顾不显厌恶。不仅不厌恶,还会同他没话找话地拉扯些没盐没醋的平常话头。窑主人说:“我家那块黄豆好久没有锄了,估计已荒禾了!”他看了一眼窑主人,见窑主人说话时脸色平静。回去的路上还回味窑主人那句“我家那块黄豆好久没有锄了,估计已荒禾了”的话语,心想:明天帮她去锄锄,一个女人家,又要种地,又要照看孩子,真不容易。
到了秋天,黄豆与谷子都上了场,归了仓。晚上看电视时,窑主人说:“孩子他爸来信了,要我们都去城里住哩!”说着,拿出两张百元钞票,递给他:“多亏你了,今年的黄豆与谷子比往年籽头重,打得多!”他看了一眼窑主人,怔了一下,见窑主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就结结巴巴地说:“不,不,我不能要这钱。我给你锄地,又不是为,为,为了钱……”
没过多久,女人走了。村里所有“守活寡”的都带上孩子到城里生活去了。
“夜游神”仍旧在夜间四处游荡。沒有了看电视的地方,他就在村路上踯躅。亮有灯光的窑洞已是很少了,不远处有一孔窑洞还亮着灯光,他知道那是张寡妇还未入睡,还在忙着什么。
张寡妇比他大十多岁,丧夫多年,独居也已多年。她有几个儿子,可都举家外迁。张寡妇年轻时颇有姿色,六十多岁了,身体早已发福,可丰腴的面庞上仍留有早年风韵,稍收拾打扮,仍旧耐看。村人沒有大量外流时,他不愿到她那里闲串,因她家里开着小卖铺,白天,打扑克与搓麻将的,以及凑热闹的挤满了窑洞;晚上,也清静不下来,还有夜战赌博的。只是后来,随着村人的不断外迁,她的小卖铺才逐渐冷清了下来。冷清了的小卖铺反倒成了他经常光顾的地方。
他与张寡妇拉话解闷,还帮她营务庄稼,就像当年给那个年轻的“守活寡”的锄黄豆与谷子一样,比锄自已的庄稼都细心认真。有时还帮她到镇上去“进货”,在不知情的外村人眼里,他就是她的丈夫,她就是他的婆姨,他俩就是一对夫妻。他对张寡妇很在意,有一次,见张寡妇到南山沟里捡柴禾去了,就坐在自家窑洞外的老柳树下,不时向山沟处张望。临近晌午了,还不见张寡妇的影子,就想:莫不是出了什么意外?边想边站起身来,向着南山沟走去。走了一会儿,听得有人在呻吟,便赶紧奔过去查看,只见张寡妇在一深沟渠内蜷缩着身子,痛苦呻唤着。他惊愕地问道:“咋成这样了?”张寡妇就拖着哭腔说:“我只顾捡树枝,不小心,一脚踩空,就跌进这沟渠了。兴许是跌骨折了,腿疼得站都站不起来!”他就赶忙跳下沟渠,费了好大的劲儿,把张寡妇背在背上,背回了小卖部,然后就忙着跑到镇上,给张寡妇的几个儿子打电话去了。
张寡妇的几个儿子闻听母亲骨折了,就赶紧赶回村来,将母亲送到县医院医治。医生给张寡妇的骨折处打了石膏,叮嘱说:“问题不大,只是骨头裂了缝,过段日子就好了!”从医院往回返时,张寡妇对几个儿子说:“多亏被夜游神发现了,要不我可就见不着你们了!”几个儿子一商量,就买了两袋面粉、一篓清油,送给了“夜游神”,算作是酬谢。
几天后,见母亲没什么大碍,几个儿子便又返回州城忙各自的生意去了。他见张寡妇因捡柴禾伤了身子骨,就每天到附近的山沟里去捡树枝,到了晚上,就送到小卖铺侧旁的一个避风地方,码起来。没过多久,那里就码起了一长溜儿干柴禾。一天晚上,他坐在小卖铺的炕沿上,对躺在炕上的张寡妇说:“腿复原了,再不要去捡柴了,我已给你捡下好多了!”张寡妇就感激地看着他,顺手把被口往低拉了拉,饱满的胸丘就在被口处显露了出来。他目光慌乱地扫视着她的胸脯,伸出手往上拉被口,意欲遮掩那撩人的丘壑。可张寡妇却把他的手压住了,目光中满含鼓励神情,并且把他那粗糙的手掌紧按在自己那柔软的丘峰上。他觉得浑身颤栗,喉头发干,呼吸也困难,而就在这时,张寡妇伸出另一只手,把他的头颅使劲往下勾压,于是,他那黧黑的脸膛便与张寡妇白皙的面颊死死重合、挤压在一起了……
几年后,张寡妇因病去世了!
张寡妇“入土为安”后,他长时间郁郁寡欢,鲜有开心时候。他再也不夜间外出游走了,一个人窝在自己的破土窑里,使一把斧头,用一大块柳木雕木人儿。木头人儿的形象是一个女人,胸脯上丘壑分明,头上的发髻也分明,他这是在雕琢他记忆中的人儿,在雕塑已到另一个地方生活去了的张寡妇!
几年后,他也因病去世了。临咽气时,他嘱咐自己的侄儿说:“我死后,就把我雕刻好的木头人儿安放在我的棺木旁,权当就是你婶娘呵!”他殁后,送葬时族人抬一大一小两副棺材,村人们,包括他的侄儿,都不知道这个木雕女人是谁;只有此时在阴间陌路上恍惚游走的他知道这个刻骨铭心的女人是谁!
卖 葱
云 溪
早晨六点钟,太阳还没出来。县城菜市场早已人流滚滚,你拥我挤,问价讨价,喧嚣热闹。胖胖的弥勒佛似的菜贩胖大妈,生意火爆,忙得满头大汗。突然,她停止忙碌,两眼盯住不远处的小女孩儿再也移不开,像着了魔,那么入神,那么专注。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胖大妈此时眼神是复杂的,多变的,温柔,慈祥,还是疼惜?还有点儿悲悯?或者什么都有,抑或什么都不是,反正说不清的复杂。其实,胖大妈眼前的孩子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小女孩儿,六七岁,瘦弱单薄的小身板,碎花小裙上几块油渍显眼地趴在上面,体恤皱巴巴裹在身上,只能隐隐约约辨出红色。黑黝黝的小脸上还沾几抹泥巴和几滴眼屎,人中甚至还有鼻涕的痕迹,稀疏的黄头发扎两条小辫,上世纪扎法,看来是奶奶的杰作。此时女孩儿正蜷缩着身子,歪躺在三轮车下一捆大葱上,可能太累了,也可能起得太早,不顾湿漉漉大葱潮气浸身,不管市场杂乱的喧闹,也不管来往摊贩和车辆碰到伤到,更不管三轮车上的大葱,毫无顾忌地呼呼睡着了,就像躺在席梦思床上,更像躺在妈妈怀里,睡得那么香甜,那么憨态可掬。
半小时前,胖大妈刚打发走一位买葱顾客,就见个老头儿蹬辆三轮,老伴在后推着,看模样都七十多了吧,呼哧呼哧地进得场来。车后还跟个小女孩儿,跌跌撞撞,他们弄来满满一车大葱。看来路程不近,车子不轻,两个老人累得汗流满面,像耕半天地的老牛一样大口喘着气。老头儿还不住地咳。他们紧挨胖大妈找个摊位,卸车卖葱。忽然,老头儿扔下葱捆,捂住胸口倒在地上,呼吸急促,脸色发青。慌得老伴抱着老头儿脑袋连连喊叫。周围人围拢来,七手八脚帮忙,胖大妈打手机叫来120。老伴急慌慌把老头儿送往医院了,留下小女孩看守三轮和大葱。
孩子在三轮车前坐会儿,耐不住困乏,歪在大葱上很快睡着了。
不知目不转睛盯住女孩儿的胖大妈呆愣愣地在想什么。旁边男人大声吼她,叫她快点给顾客称菜,胖大妈才回过神来。但是,她没去称菜,转身向市场深处走去,边走边对大家说:“看这孩子……咱们帮她把葱卖了吧,帮孩子把葱卖了吧。”音调不高,节奏缓慢,却字字清晰,飘荡在菜市场上,像秋风掠过成熟的田野,激起沙沙回响。市场喧嚣声低了,人群中响起一阵窃窃私语。几个大葱摊主停下交易,看看胖大妈,再伸长脖子看看酣睡的小女孩儿,回头对面前的顾客摆摆手,示意不卖了。不卖啦?顾客错愕,随摊主手指望去,看见不远处三轮车上的大葱,眼光又落在地上酣睡的女孩儿身上。顾客转身向三轮车走来,近前看女孩儿甜甜地睡着,张嘴想叫醒她,又停住,不忍心打断孩子梦境。踌躇间,一个穿制服的中年人上前把三轮车上竹篮子拿下来。竹篮上盖块花布,花布下是几块面饼和几片咸萝卜,不用说,女孩儿和爷爷奶奶捎来的午饭。中年人用花布把面饼和咸菜包好,放在孩子身边,把空篮子摆在三轮车前,然后把买菜的钱放进去,自己从三轮车上取捆大葱,破开,拿几根走了。后边人默默仿效,放下钱,拿把葱。放钱,拿葱,整个过程每个人都默默的,小心翼翼地,就连脚步也放得很轻,唯恐发出响动惊醒孩子。
买葱的人渐渐多起来,人们自觉排成长队,弯弯曲曲,一条龙似的,一个一个,井然有序,无声地悄悄进行。几个青年人不买葱,也来排队,也掏几张纸币放到篮子里,一声不吭地离开。
女孩儿依旧酣睡,对面前一切浑然不觉。细心的人发现睡梦中女孩儿稚嫩的脸蛋泛起盈盈笑意,嘴角还微微抽动了一下。他想,女孩儿梦中可能背着奶奶用卖大葱的钱买了新书包,迎着红艳艳的太阳,在上学路上,蹦着,唱着,追逐着上下翻飞的花蝴蝶……
胖大妈回来时,三轮车上大葱卖光了,只剩女孩儿身下那捆了。胖大妈对正要伸手拿葱的老太太说,“大姐,没有了,那捆我要了。”然后把张红红的人民币投进篮子,随后轻轻摇醒女孩儿。小女孩儿醒了,双手揉揉粘着眼屎的眼睛,睁眼不看胖大妈,先看三轮,一看车上大葱没了,小嘴一撇哇地哭起来。
奶奶临走再三叮嘱要看好大葱,可到底还是没了。
胖大妈揽住女孩儿肩头,梳理几下女孩儿的头发,安慰她,“别哭,孩子,你的大葱卖了。你看,钱都在这里,”把篮子拿过来给女孩儿看。
竹篮里堆着花花绿绿的人民币,快满了。
胖大妈没向一脸茫然的女孩儿解释什么,站起来,撩起围裙擦擦手,回头对女孩儿说:“走,孩子,我送你去医院找奶奶,看爷爷的病怎么样了。”
最幸福的事
张爱国
这天,后山小学四年级2班的语文课上,钟老师在讲解了一篇有关幸福的课文后,问:“同学们,你们认为自己最幸福的事是什么?”
“受到老师的表扬最幸福。”刚刚受到钟老师表扬的李扬第一个站起来,得意洋洋地说。
“最幸福的是考了第一名!”李学高说着还挑衅似地看了看李扬——这两个孩子一直在为班上的第一名较劲,而李学高恰恰在上周的考试中获得了第一名。
钟老师微笑着,分别肯定了两个孩子,鼓励其他孩子继续回答。
“我最幸福的是周末!”陈志磊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因为周末,外婆都会为我做很多好吃的。”
孩子们哄堂大笑,笑话陈志磊是“好吃鬼”,但一个个小嘴巴却不由地砸吧砸吧起来。
“今年春天,我爷爷的腿好了,又重新能挑水的时候,是我最幸福的。”龙小留仿佛进入了回忆状态,“去年下大雪的一天,我爷爷挑水时摔断了一条腿,躺在床上不能动。我奶奶又挑不了水,每天都逼着我和她一起抬水。哎,地上都冻得梆硬梆硬的,我和奶奶都摔破了手,还摔坏了几只桶。那时候,我、爷爷、奶奶和弟弟真痛苦啊,连水都舍不得喝。所以,当爷爷腿好了能够跛啊跛地拎水的时候,我能不幸福吗?”
“你爷爷奶奶真笨!看我爷爷奶奶,建了个大水窖,趁天晴把水窖挑满水,就够一家人过冬了……”说话的孩子还想取笑龙小留,被钟老师制止了。
“去年,邻居莲奶奶病了,睡在家里好几天没人知道,是我最先发现的,也是我给她儿子打了电话她儿子才从外地赶回家带她治病的,不然她就死掉了。”“调皮鬼”闵向守大声说,“现在莲奶奶总夸我是好孩子,还常常给我糖吃。我看,这才是最幸福的。”
“这也算幸福啊?”孩子们显然不屑于闵向守,“我也帮一个老爷爷打过电话……”
“我也是……”
“我也有一次……”
“我帮过一个小妹妹,她想她爸爸妈妈了……”
教室里哄闹起来,钟老师拍了拍讲桌,启发孩子们再换换角度。
“我最幸福的事是在今年暑假。”柳静儿说,“我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到了我爸爸妈妈打工的深圳——啊!深圳真大啊,比我们镇上大多了!那天晚上,我爸爸没上班,带我到大街上——啊!深圳的大街真亮啊,千姿百态、五颜六色的灯都有!逛完大街,爸爸还带我吃肯德基——啊,肯德基真……”
“切!深圳算什么?”柳静儿的同桌郭童似乎很不服气,“深圳有东方明珠塔吗?有海洋世界吗?有世博园吗?”郭童指着柳静儿的额头说,“没有吧?但上海都有!我暑假去的时候,我爸爸妈妈一整天都没上班,带我看东方明珠……”
“吹!郭童,你吹牛!你根本就没看到东方明珠塔。”“调皮鬼”闵向守又站起来叫道,“我爸爸打电话和我说了,你爸爸刚走出工地不远就迷了路,然后随便指个什么地方糊弄你,说是东方明珠塔。你其实连东方明珠塔的影子都没看到……”
“我看到了,我看到东方明珠塔的尖子了,我还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好几天呢。”郭童气呼呼地反驳道:“你嫉妒我!嫉妒我和我大姨当时没带你去上海你爸爸妈妈那儿……”
“你们别吵了!去上海比得上去我小姑家幸福吗?”杨鑫博眉飞色舞地说,“我小姑家一直都没大人在家,我和我表哥天天打游戏、打牌、上网,我们想玩什么就玩什么……”
钟老师叫停相互不服、争吵不休的孩子们,又教育了几句杨鑫博,就打算结束这节课,却发现郭素素一直坐在那儿没说话,就问:“郭素素,你最幸福的是什么?”
“我每天都幸福。”郭素素淡淡地说,“每天下午放学后,爷爷坐在院子里抽烟,奶奶在厨房里烧饭,妹妹和我一起写作业。不一会儿,爸爸妈妈从地里回来了,爸爸检查我和妹妹的作业,妈妈洗衣服。吃饭时,爸爸陪爷爷喝酒,奶奶和妈妈给我和妹妹夹菜……”
郭素素还在不以为然地说着,教室里却不知何时静了下来,突然,不知谁哭出了声,一个,两个,一大片。
责任编辑:王雷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