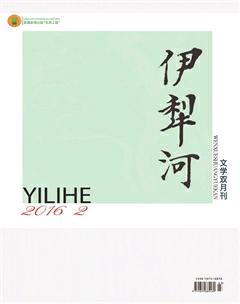孤独的青春(六章)
董喜阳
负 担
一场雪过后,世界摘下了面具。
从此树就成为了树,人就成为了人。
想象跌倒,潜伏在我浅蓝色的洗脸盆里。装饰着器皿的底色,在水中轻轻地吟唱。
阳光像是羽扇纶巾的少侠,踌躇满志,杀进江湖。调节着从关系到关系之间的距离。
犹如一串日子在泪水和眼窝之间迷了路,冰越过心灵的日界变更线——晋升。
一滴水,一滴水嬗变成了隐私,砸在我的心底。
即使在梦里也不愿说出的负担。
颤 抖
天气预报说今夜有雪,我心疼了。
不是怕雪占有了冬天的身子,而是一场迟来的雪,总是令夕阳很尴尬。
从早上到黄昏,严肃的雪上总是有父亲尴尬的脚步。
河流私下很不安静,总是对外面的世界议论纷纷。
大雪在心理上把冬天出卖,冬天在生理上把我出卖。影子在大雪里埋伏,站立在风的对面扮演想家的角色。
索性掬一捧温暖的雪,安放在距离灵魂最近的心口——阳光粗糙得可爱。
冬天就被照耀得颤抖了几下。
超 度
再次遇见冬天,它的身体已经溃烂了一大半。
据说是被巨大的瘟疫袭击,抵抗了数月后终于客死他乡。
真替冬天这样的死法担心,会不会在九泉之下抱憾终生。
每一条奔走的河流都是你的祖先,不知道哪一个菩萨会带你去,见列祖列宗。
阳光晒黑了石头的一角——夜就沉了。
一群乌鸦鲜血淋漓站在十字架上,为作古的冬天举行一场法事。
一只寂寞香的圆寂被圆寂的柴火成全。
为雪花和童话送行的冬天也为自己送行,我在一次意料之中的死亡里超度。
为那些死去的超度,也为那些还活着的。
重 生
打开一本书,是我不认识的汉字,不知道的名字。
就选择在一页纸张的冬天里坐化。没有人为我诵经念佛。
灵魂被雨打湿向另一个方向逃窜。
凌乱的步伐在凌乱的时代显得更加的凌乱。
一把梳子进入我的生活,理顺我每天,原本就顺其自然的生命。
一根发丝很辛苦,每天都要和两根梳毛拼命,犹如是水草和鱼虾都被时间的河流拉扯得疼痛。多年后两根梳毛战死沙场,切割成不同的两半——
一半是来生的眼泪;一半是今世的殷红。
月亮的背面
今夜把月亮埋葬。报太阳软禁一夜之仇。
天空鸣奏起死亡的哀歌,为月亮送行。
被雨水浸泡过的肌肤越洗越白,像是被母亲呵,亲手揉搓过的棉被单。
有些崭新过后的可怜。
星星在你的身后摆弄着肢体,矫情而紧张。像是伸了一个在时间之前就伸过的懒腰,好半天缓不过神来,没有借口不被星星讥讽和嘲笑……
没有理由不退居二线,接受最后的例行公事。
我内心中淤积的雨水和胸中的哀怨相互重叠——重叠是一种宿命,重叠之后的宿命又是一种宿命。
卑微,是空格子里漏掉的最后一点笔墨。阳光充当另一名杀手。
在地狱之门的缝隙里,抛出一把刀。月亮连血带肉的面颊整个被剁开:
从此,月亮在公开出版的教科书里失踪了多年。
奔向远方的列车
一只舌头在车里焦躁不安。想着墙外的舌头同样骚动的情节。
像是被窝里的花朵,看见了阳光,马上失去了想成为处女的可能。
割掉自己的一块肉,写上:“贞节牌坊”。
季节跟随着握刀的节奏颤抖了很久,用心地哄着双轨。开向潮湿性感的远方。
在世纪末的最后一天,白纸开始溃烂。
列车倒立在时代的墙边——左右为难。
远方的坐标也犹如一把门把手,被别人随便,拉来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