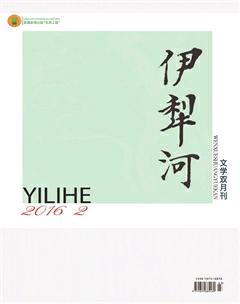凤凰:你把花冠戴在我头上(外一篇)
安歌
在今日的凤凰,流动的不是沱江,而是人流。
沱江两岸,乍看如北京上海的地铁出口,人流如注。然而与地铁人流中人人心里都盛着莫名的归心之箭不同,这里的人心里装的大约是“琴心”——每个人似乎都沿着某个方向走,但方向亦无关紧要。或者头上戴一枚花冠吧,裙袂飘飘,肩上再搭一块刚从某个小店买来的方巾或长丝巾,随便地随着人流随便地走,行走时人人头顶身侧几乎都顶挂着一个酒吧、餐厅或家庭旅馆的名:“极乐鸟”、“醉人间”、“缘分客栈”、“梦婆汤”,或者就是“我在凤凰等你”……便是广场上卖花冠着苗族服饰的老妇,当镜头对准她时,其躲闪的速度之快,也是明明知道自己是可以上镜的。
在白天的凤凰,人大约可分为两类:买东西的和卖东西的,换个说法就是游客和待客者。小巷深处的文庙也闭着朱红的门,却有一苗装老妇坐在文庙前面,面前三个竹筐,满满当当地摆着各色绣花鞋、旅游帽和围裙衣饰,其色彩之绚,也如凤凰处处都在迎客过年。她用的是竹筐,大约也是清晨沿着那细小巷子的石板路背来的。偶遇两位像双胞胎的苗族老妇身着本色似是自家织染的苗服,立在广场,背对游客,在看展览墙上的照片:“苗族‘四月八椎牛”、 “苗族服饰”……中间突然插一张“中韩围棋对抗赛”……她们自己就是苗族,立在那儿看自家的民俗展览,或者也是游客?
面前便是已变成银器店的陈家祠堂。我以前不知陈渠珍其人,到湘西后向文友咨询,朋友告知:陈渠珍曾有个文书,叫沈从文……闻之惊心。便在网上搜索,知陈渠珍生于光绪年间,自少随军,曾入同盟会,后经国民革命、抗战等役,功绩卓然,名声显赫。因曾统治湘西一带数十载,人称“湘西王”。后来朋友又介绍他的《艽野尘梦》给我,随便一翻,是陈带军进藏的故事。便怨朋友,我想看的是湘西呀。他答我:这就是“湘西王”。
或者他指的是精神?
为此书作注的藏学专家任乃强先生在弁言中谓:“余一夜读之竟。寝已鸡鸣,不觉其晏,但觉其人奇,事奇,文奇,既奇且实,实而复娓娓动人,一切为康藏诸游记最。尤以工布波密及绛通沙漠苦征力战之事实,为西陲难得史料。比之《鲁滨孙漂流记》则真切无虚;较以张骞班超等传,则翔实有致。”
毕竟是藏学专家写弁序,笔底结实无节漏。我虽也喜其中之奇人奇事奇景,但更喜那名叫西原的奇女子。
传奇若无人情做线,不过只是风光风景;若有人情甚或深情,这风光风景便有了脉动。时隔24年才追忆这段往事的陈渠珍,心里或者也把时光沙尘涤尽了,然而情却未尽。写藏地与西原初见:“中一女子,年约十五六,貌虽中姿,而矫健敏捷,连拔五竿……”这时他与西原还彼此是客。初闻第巴提亲,也只当玩笑。当事已成真,也只是“知不可拒,笑应之”。 成亲之日再述西原,已是“靓衣明眸,别饶风致。余亦甚爱之”。
全书所述乃是陈渠珍在宣统元年奉赵尔丰命,随川军钟颖部进藏,历经工布、波密等役,至武昌起义后,陈因兵变率余部出逃。进藏北无人区:“道路迷离,终日暝行,无里程,无地名,无山川风物可记。但满天黄沙,遍地冰雪而已。”从11月走到了次年的6月……七个月茹毛饮血生活后,自林芝江达至西安用了223天,出发时115人,到西安只余11人。
可怜骑术精湛的西原经历艰险,万里从君,到了西安,却因天花病卒。逝前的西原是自知的,亦是遗憾的,因为没有能到丈夫的家乡凤凰与其平常厮守;但缘着爱,这遗憾里也有安慰:“西原万里从君,相期终始,不图病入膏肓,中道永诀。然君幸获济,我死亦瞑目矣。今家书旦晚可至,愿君归途珍重。”其情义与担当便在临终之时,也丝毫不减。
西原离世,一代湘西王陈渠珍宏大高远之志全然不见,他此刻也只是个男子,一个连给妻子殓葬的钱也没有的丈夫:“抚尸号哭,几经皆绝”……“入室,觉伊不见。室冷帏空,天胡不吊,厄我至此。又不禁仰天长号,泪尽声嘶也。余述至此,肝肠寸断矣。余书亦从此辍笔矣”——这是西原离世24年后的“辍笔”。
我立在陈家祠堂满眼银器闪烁又黯哑的光中,无泪亦无想。陈渠珍可曾在这里读过书呢?在《从文自传》里,沈从文在陈幕任文书时写当年的陈渠珍“令人叹服的治军能力以及长官的自律: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深夜还不睡觉,年近40也不讨姨太太,平时极好读书,以曾国藩、王守仁自许,看书与治事时间几乎各占一半”。
沈从文之后走上文学道路,有胆量独身进京,此段“书童”经历之影响功不可没。
十点后的沱江岸边,人流已如溪——他们中的一些,大约在古城的某个店铺里挑选衣裳披肩头花手镯,另一些可能在热气腾腾的美食街觥筹交错……老桥洞下也聚集了一些文艺青年,有两三位拿着画架排排坐着,其中一位背后贴着一张A4纸,上书墨字“画像30元”,另一位的招牌是“一分钟画像” ……画者都很正经地手执画版画着;旁边坐了几个年轻男孩,一位手握麦克风,沉浸在自己的歌声中,旁边有执吉它者为他伴奏,他俩之间有一块黑板写着:“‘你好酒吧在那边”。——我看了看那边,沿着桥洞的石头墙一直看向灯光繁盛处,没看明白“那边”是哪边……白日裙袂飘飘的女孩,或也有几位立在桥洞里,或听歌,或被画,或对着文艺青年拍照。画者、歌者、拍者都很专注做自己的事情,桥洞不大,却聚了不少人,虽知是偶遇,但却有相伴与春游的景气,又似一段青葱,掐头去尾剥净,没有过去,也无未来,全然都是当下此刻;便在此刻当下,也已然是凤凰台上忆吹箫。
由桥洞想到“落洞”,或是自然的事情。“落洞”风俗,沈从文在他关于凤凰的文字中有描述:“凡属落洞的女子,必眼睛光亮,性情纯和,聪明美丽。必未婚,必爱好,必修饰。平时贞静自处,情感热烈不外露。间或出门,既自以为某一时无意中从某处洞穴旁经过,为洞神一眼瞥见她,欢喜了她,于是更爱静坐,爱清洁,有时会自言自语,常以为那个洞神驾云乘虹来看她”——这个“落洞”女子三到五年之内是要死的呀——“身体散发出奇异的香味,含笑死去。死时且显得神清气明,美艳照人”……因为洞神来迎娶她了。但沈从文自有他对人世的温和,写下这些文字的手,也是在凤凰童年上学路上,见到前夜被处死的死人的头,便会找棍子来挑死人脑浆的手。挑毕脑浆,继续去上课——从文先生的“温和”是生死在他那里都可以齐平的,也是湘西这片土地蕴育出的温和。其与文字之渊源,亦如那落洞女子与洞神。
从桥洞里走出来,一些“文艺青年”大概进了酒吧咖啡厅,有几位男女在河岸边放河灯……他们可知河灯的故事呢?但是不知也是可以的吧,河灯沿沱江夜行,我没有听见沈先生笔下两岸的对唱,却有河对岸的女子依着窗口喊:对面的哥哥帅不帅?这边行人中便有答:帅!对岸的妹妹来不来?换了个女声又喊:对面的哥哥裸不裸?……想必以沈先生之心,在这河光灯影里听这年轻意气,也当莞尔。如果他在清晨漫步,遇某小巷墙上手书“乱丢垃圾会怀孕”,会不会也莞然?虽则如今所谓的旅游,不过是观光,正如大卫·赫伯特·劳伦斯所言:其中所缺失的是生命信息——“我们到处都去过了,所有事物都看过了,我们是无所不知的。但是表面的东西看得越多,我们就越看不懂内涵,越缺乏深度。目光仅仅在海平面上一扫而过,就声称完全了解了大海……”——那可是在茨维塔耶娜心中,只有渔民和水手才敢说了解的大海啊。
零点后,游人把凤凰还给了沱江。独坐沱江边一石凳上,听河水汤汤,人闲心静,却莫名想问这河水,从文先生说的,让他学到真“知识”的路边店铺,特别是那家能给佛像类嵌极薄的金片的小店如今在哪儿呢?坐着便有一男子提着几瓶啤酒路过,向我摇着酒瓶发出半夜同醉之邀,我微笑婉拒,起身回沱江边的客房。行在石板路上,脚步嗒嗒有声。
西塘井底
这个夏天真热啊,适合躲在地下室凉气里看《聊斋》。看到莲香那节,说桑生生性“静穆自喜”。可真喜欢这个“静穆自喜”,这好是止水涤妄的好,让人安心。突然想到刚刚失恋的女友SL有问:我应该去哪儿“飘流”?然后我眼前就出现了烟雨中的西塘——如果把此刻的她,放置在桑生般“静穆自喜”的旧西塘应该不错。
距浙江嘉善县城11公里的西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吴越两国的相交之地,有“吴根越角”和“越角人家”之称。到元代初步形成市集。作为江南古镇,西塘自然也有小桥流水的静谧,有橹声飘摇里的悠远……在入夜时分,从西塘临河人家家家自有的码头低身下船,坐在乌篷船船尾,听着桨与木船发出的咯吱声,看沿岸串串红色的灯笼……虽只是一小小的船头,小小的一注水,唯单调的橹声映衬流水,但这小桥流水的西塘,亦可如古人云:清衿凝远,卷松江万顷之秋。这万顷之秋之万顷,或者不在松江上,只因与那凝远清衿意气相许。
或许你会在星空清风中,走进西塘临河街,那上千米地长过去、一路遮阴蔽日挡雨的廊棚,人在其中便如雨中山果,灯下虫草,一路的灯火明灭中,这廊棚的体贴亦如高人胸次;而你的行走与观看,或也似袅袅山风,入松篁而成韵,便也成了对西塘廊棚的体贴。亲爱的SL,“体贴”这个词可真是好,体是身体的体,贴是贴着的贴,溶了之后,是流水相忘游鱼,游鱼相忘流水的天机;亦如张潮所言:“庄周之梦为蝴蝶,是庄周之幸也;”若不溶,则是下一句:“蝴蝶之梦做庄周,是蝴蝶之不幸也。”我认为他这两句里结尾的“也”都删掉,要干净利落些。
西塘穿城而过的溪流似乎带走了留下的一切,但西塘又确实在目光中显露着,在它的小桥、流水、橹声、乌篷船,廊棚、码头的海内殷勤里,连带着向晚时分西塘粉蒸肉的气味。——西塘的粉蒸肉新鲜别致,它是用鲜荷叶、上等猪肉拌米粉和配料豆腐皮包裹而成。煮成后的猪肉荷叶沁肺、清爽幼滑。那新调初裁的味道在风雨飘摇中的西塘,有一种温暖人间的妥帖可靠。或者正是它的豪华之志与淡泊之趣把民居门上“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黄字、咸亨酒店的白字挽留下来了。
消停的西塘的旧像是得了人心的。对于偌大世界而言,西塘静穆自喜的心像安静的井底,掉下去就可以有一井的天空。而一井的天空,正合蛙意。或者你认为自己不是蛙,不过,在西塘你也许会这么想:在见过整个天空之后,有一井自己的天空也不错的呢。要换做加拿大诗人阿饵·普迪在这井底,或者也能写下这类诗句:在大雪封路的时候,我最要感谢的是,看清了你小腹上的一根汗毛——SL,很抱歉,不知如何从西塘说到汗毛了,当然,我知道你会明白我的心意:在意的是阿饵·普迪清衿凝远之心。
西塘虽好,毕竟是地上文章;西塘可去亦可离,然己不可离。轻诺者寡信,是以知不可行之事,自不必妄做经营。失恋虽寒,在寒中若可体己之骨清,或者亦可如阿饵·普迪那般感恩:看清了你小腹上的一根汗毛——当然,阿饵·普迪诗中的这个“你”换成“我”或者“自己”也说得通的。
如此这般运送你,或者你会当我立在张潮《幽梦影》的影子里:“窗内人于窗纸上作字,吾于窗外观之,极佳。”以为真在与你隔窗如影般说话,但我还是觉得“极佳”二字,放在这儿,亦如夏雨赦书:听那橹声……
在水乡免不得想到雨,于是竟翻起张潮的“春雨如恩诏,夏雨如赦书,秋雨如挽歌”来。其后的二批甚妙:张谐石曰:我辈居恒苦饥,但愿夏雨如馒头耳。想你不缺馒头,是以不会与张谐石同志;老与张潮唱反调的张竹坡则曰:赦书太多,亦不甚妙。——翻书翻至张竹坡之曰,如遇酌心之友,总要忍不住抚掌而笑,忘却了斯世何世。若张谐石之批被张竹坡见着了,大约亦会有类批:馒头太多,亦不甚妙。也是另一个西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