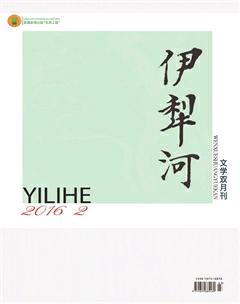洗头少年林树
李剑
我猜是因为我的面相看上去非常随和,不那么美丽,也便不盛气凌人;不丑,使人看着也不会回转脸去。因此,我时常会被当成一个倾听者,不问我愿不愿意,熟悉的或陌生的人就在我耳边絮叨起自己的故事,像是一准看出我心里装着一个大大的密不透风的袋子,专来收集它们。
好的是,他们的眼力不错,我喜欢听故事。故事到我这里,我就把它们装进袋子,在我的想象里一再烹煮、翻滚,它们就成了我的故事。我便把它们取出来,讲给别人听。
这次的故事,有关少年。少年最好,情感细腻如水,咀嚼起来,像柠檬,清清爽爽,还带点辛辣,不小心,会流眼泪。
少年估摸着也就18岁左右。一头染得焦黄的头发,在脑袋上刺楞着。瘦瘦的身子骨蜷在一身黑衣黑裤里。人也是黑的,脸上像蒙着一层薄薄的土,不是不干净,是活脱脱的透出土气。是那种黄头发、黑衣服也掩盖不了的土气。
他见我进店,敏捷地从一张椅子上站起来,说:“剪头发吧?先洗个头吧。”我便尾随他走到洗头的台子上去。
他看到我时,是笑着的。一笑,一脸的阳光倒把脸上的那层薄土给拂去一层。我已经不记得他的话匣子是怎么打开的。只记得他那一声“嗨”特别有力,一股夹杂着烟草气息的热气扑到我脸上——他的故事就开场了。
“嗨!”他说,“我都不知道我妈妈长啥样子!”他带着笑,仿佛说的是别人的妈妈。
家里全是男人味。奶奶40多岁就去世了。爷爷也未再娶,一个人拉扯他父亲娶妻生子。娶来的那个热辣的重庆姑娘,生下娃娃就再在他家呆不下去,给爷爷扔出话:“我不欠你们家的,好歹给你们生了个娃。可是这日子没法过,去趟城里还得坐几个小时的车,到了城里,还没有钱买东西。你们家儿子骗了我,我也不计较。我现在就去跟你儿子离婚,出了这个家的门,咱们谁也不认识谁。”她用一个帆布袋子包裹了自己的东西,挎在肩上,拉着他父亲出门。他父亲那时候也年轻,被老婆这么说脸上挂不住,既不拦也不劝。本来是蹲在门槛上吸烟。见媳妇来拉,烟屁股一丢,站起来,跟着媳妇就走。离就离,谁离了谁还活不了?脸上挂着自以为是的傲气。
母亲出了门,真就再也没回来过。这么多年,也从未有过问候和探望。
少年捋着我的头发,继续像说别人家的故事一样说自己的故事。
母亲走后没多久,父亲就将他丢给爷爷,出门打工。他跑了很多地方,先是去县城,然后又去了伊宁市,再然后,又去了乌鲁木齐。父亲去的地方离家越来越远,带回家的钱却越来越少。爷爷不待见他,仿佛没他这个儿子,他爱回家不回家,爱寄钱不寄钱。但爷爷疼惜这个孙子,用米汤糊糊一勺勺喂他。下地将他背在身上,放在地头,干一会活儿便过来看一眼他,喂口水,塞口馒头,逗弄一番,返身继续去干活。
少年到了上学的年龄,爷爷更是高兴,像是晦涩的生活里闪出一道亮光,耀得人心情明亮。少年懂事,知道家里的处境,每天放学,先不回家,绕到地里,帮爷爷拔几把草,听爷爷说会儿话,接过爷爷的锄头扛在自己肩上,在晚霞里一起回家。
夏天最是好。天黑得晚,每次回家,霞光满天。乡路的尽头,是通红一片。这种情形总让爷爷很开怀,背着手,勾着背,一边走,一边哼小曲。少年在一旁听,有时候也跟着哼两句。
每年过年,父亲会回家。在搬到与父亲一起生活前,少年能掰着指头算出自己跟父亲一起呆过的日子——不过是每年过年前后的一个月时间而已!每年一个月,13年,便是390天,比一年多一点。若是将这时间集中到一年,兴许能培育出互相的理解,建立起彼此的依恋,但分散到13年里,感情的味道就太过寡淡了。
少年也不待见父亲。父亲回来,他无法与他亲近,见了面,生硬地叫一声“爸”,便去爷爷身边,帮着拣菜倒水,或者回自己房里,写作业听歌,不再出来。
父亲感受到了这份冷落,从前是孩子小,可以认为是不懂事、怕生,而今孩子大了,却仍然如此,他心里便涌起凄然。这世上,除了他的老父亲,便只有这一个至亲的人了。倘若一日,老父亲撒手人寰,他要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冷冰冰的孩子?他回乌鲁木齐,找了个一室一厅,租下,从工厂宿舍里搬了出来。去旧货市场上淘回一些家具,两间房里各置一张床一只柜,一个简易的家就成了。
他又回到老父亲处,跟父亲说:我要把孩子带走,跟我一起住。
少年正好放学回家。看到了又突然回来的父亲,诧然,一声“爸”后又蹙到爷爷身边,帮爷爷做饭。
爷爷不语,父亲便又说:你年龄大了,就别累了,孩子跟我走,我自己来带。语气里没有让步。
少年这会儿方明白父亲此趟回来的用意,脸一惊,抬起头,怒冲冲地看着父亲,吼一声:“要走你走,我不走!”说完眼泪就滚下来,扔下手中的菜,站起身,奔到自己房里。门“咚”的一声关上。
爷爷和父亲被这一声“咚”震得愣在那里,互相看一眼,又迅速将目光移开。父亲跳起来,转圈找得手的物件,看到扫把,就一把抓起,也“咚”的一声把儿子的门推开,冲进去,拎起儿子的脖子,扫把就舂衣服一般落到儿子的身上。一边打一边说:你在跟谁说话!你在跟谁摔门!你再摔,老子不打死你。少年便张着大嘴哭,扭着头,扛着父亲的打。
爷爷也冲进来,手里拿着锅铲,“咣咣”地拍在父亲的背上,抖着声音说:“你今天要打死他,我就打死你。”
少年转身,扑进爷爷的怀里。父亲停了手,扫把一扔,说:“你过会儿就收拾东西,明天跟我走!”
第二天早晨,少年跟着父亲,离开了爷爷。走很远,转过头,还看见爷爷站在家门口的树下,像一截矮木桩。
“我一直都不知道怎么跟我爸说话。”少年在给我的头发冲水。他的水冲得细致温柔。没有指甲的手指头轻轻抓挠着头顶。我能感受到温热的水在发丝间流动。
我闭着眼睛问:“后来呢,多和他呆一些日子就好了吧?”
“嗨!”又是这样一声。
“好什么呀!我就没跟我爸一起住几年。”他说。
他成绩好,一心想通过学习谋出体面的生活。大概很多过早便明了生活的不易的孩子多有如此想法,家人盼着他们变龙成凤,他们也相信只要努力学习,就有让疼惜自己的人喜笑颜开的一天。少年的动力是爷爷。他盼着有一天一脚跨进那座山脚下的院子,拿着某个名牌大学明晃晃的通知书,一边跑一边叫:爷爷,爷爷,你看哪!爷爷不管在忙什么,一准都会停手,从屋子里颤出来,站在门槛上,望着他笑。
但父亲对少年的学习并不报期望,甚至觉得是无可摆脱的负累——刚上完小学,这就上了初中,初中完了,还有高中,上完高中,还有大学……这照顾下去何时是个头?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好。厂子里那些工资,除去日常开销,还要留点闲钱打个牌吧?喝点酒吧?抽个烟吧?他妈都不要他,我好歹把他拉扯这么大了吧?还要上学,还要要钱?!
少年常常窘迫到没有午饭吃。家里自然是不能指望的,父亲自有厂子可以解决午餐。偶尔上班前想起来,从口袋摸出几块钱,扔给少年,说:中午自己看着吃吧。但也常忘记,少年便在校园里遛跶,听肚子里的奏鸣曲。
“我们班主任可喜欢我了。她常常叫我到他们家吃饭。”听到这里,我竟感到有些心酸。多么幸运,这样一份善意,让一个成长中总是饥饿的少年有了可归之处。我揣测,或者,也正是这样的一丝善意,让今天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少年并不阴郁冷漠,愿意微笑和倾吐。
少年继续讲他的故事。
初二下学期一天,放学后,他回家跟父亲要钱,这是要交给学校的钱。向父亲要钱,是少年最讨厌做的事情。每一次开口,都像是要把骄傲的自尊踩到脚底下去。他耷着头站到父亲面前,低低说一声:“明天要给学校交钱。”但即便这样,父亲还要把他推开,把他那已踩在脚底的自尊再使劲碾几脚,直至完全看不出模样。父亲吼:“又要钱又要钱,你们学校是吃钱的吗!老子没钱,爱朝谁要要去。”
少年眼泪滚下来。
每一次都是这样,从来都没有变过戏码。每次交钱,班长都要催问他很多次,隔着几个座位冲他喊:“林树,钱带来了吗?就差你了。”一声喊之后,他立即就感觉到四面八方的目光朝他包裹过来。他紧忙转身强装镇定地回答“早上出门忘了”或者“明天早上带来”。
父亲这次似乎是铁了心不给。一连三天,他一张口,父亲就把筷子一扔:“没钱!”
少年终于在心里打定了主意,不去上学了,太难堪了。他的尊严被父亲碾碎一遍不算,还要遭受同学们的凌迟吗?
他给爷爷打电话。一边哭,一边说:“爷爷,我不上学了。”爷爷呼哧带喘地问:“为啥?为啥不上学了?”他说:“爸爸不给钱。”爷爷便撂下话:“你在那等着,爷爷明天就过来。”
少年知道,就是爷爷来,他也不会去上学了。爷爷年纪已大,身体也更加糟糕,他怎能忍心让爷爷继续为自己的学费操劳。但是父亲……爷爷来了,父亲又能有什么改变呢!
第三天早晨,爷爷就到了。父亲还没有去上班。爷爷将一只帆布袋子搁下,看着诧异的父亲说:“不想我来是不是?”父亲只没好气地答:“来也不说一声,突然就来了。”说着就要出门上班。爷爷拦下父亲,口气更烈:“还要跟你说!你学都不让娃娃上了,还要跟你说啥!”父亲转脸问站在客厅里的少年:“你不上学了?”少年仰着脑袋,硬着嗓子回答:“你又不给我钱,我怎么去上学?”说完,眼睛直直地迎着父亲看过来,毫不避让。父亲兜转身子四下里望,看到门后的扫帚,便抓起来,几步跨到少年的身边,挥起扫把就打:“不给钱就不去了?谁还能把你赶回来?谁能不让你上学?”少年心里浮起冷笑,嘴角牵了牵,竟连一句驳斥的话都不屑说,只把头扭过去,听扫把落在身上的声音——这点疼,哪里比得过心寒?爷爷也跳将上来,找不到东西打,便挥着干瘦的臂膀拍打父亲的后背:“你不给孩子钱,你还有理了!我咋养了你这样个儿子!”一边说,一边老泪纵横。少年忽然觉得这个场景有些熟悉——不就是两年前父亲去接他过来时的场景么。
两年——两年时间,就让他曾经那个亮堂堂的梦想戛然而止,像极了爷爷家灶膛里没烧尽的木柴,取出来,用潲水一浇,“哗”全灭了,留下焦黑的炭身和一股子青烟。
少年扬着头回忆,三个人纠缠在一起的一顿打,让他从爷爷处来到了父亲这里,再一顿打,就又会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了吧!如此想着,脸上现出强硬的冷漠和决绝。父亲看在眼里,把扫把一扔,竟有些仓皇地夺门而出。门声响起的同时,也把父亲的话关在门内:“你爱上不上。”
爷爷走过来,抱住少年,脸上有未干的泪痕。他说:“树啊,收拾东西,跟爷爷回去,咱们回去上学。”
少年终于把扬起的头低下来,伏到爷爷怀里,哽咽着说:“爷爷,我不上学了,不上学学门手艺,也一样能过好。”
爷爷抚着他的背,一个劲儿摇头:“不能不上学,你才多大,上学才是出路,听爷爷的话,啊?”
少年看到了爷爷混沌的眼睛里的期待。这一双眼睛,让他更加坚定了他不能重返学校的想法。爷爷老了。比两年前更老了。老到这佝偻着的脊背上根本扛不起他那个亮堂堂的梦想。
“我说,爷爷,不上学你孙子以后也不会饿死,但是现在上学,你孙子可能就会难过死。”这个头洗得格外漫长。少年一手托着我的头,一手仔细地揉搓,话语里有故作看破红尘似的轻松。
我忍不住替他难过:真可惜啊。
他一笑,说:其实我还挺想上学的,为了这个,我还试过去找我妈妈。
听他这样说,我已经不止是难过了。他对他的母亲还寄着期待和幻想呢!
少年的爷爷最终拗不过孙子,一屁股坐到凳子上,低着头叹气,末了,只无奈说:不管啥时候,难过了就回家,去找爷爷。说完,他塞给少年500块钱,就颤巍着身子,摇着头离开。他竟已老至无用,老远跑来,什么忙也帮不了,什么事情也不能改变。这不是他愿意看到的局面,不如不看。少年在背后哭。他替自己难过,也替爷爷难过。
自那之后,他便不再跟父亲说话。日日进出屋门,见到了,眼也不抬,眼睛里再没“父亲”这个人。
他到外面找活干,到餐厅里当服务员,一边做一边想日后的出路。还是想上学哪。最羡慕的不过是一家三口来餐厅吃饭的场景。如果当中的孩子再跟他一般年纪,就要忍不住掉眼泪了。他突然想到,他还是有母亲的啊!母亲当年离家,应该是出于无奈吧。他现在如果能找到她,告诉母亲他的处境,她未必不心疼,未必不留他在身边供养上学吧。
想到这个念头,他竟觉得前途一下子就明媚起来。他甚至开始幻想与母亲一起生活的场景:每天早晨,母亲做好饭,匆匆叫他起床,两个人一起吃饭聊天,一起出门,各自上学上班。这会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就像他当年放了学绕到地里跟爷爷一起回家一样。
有了这个想法,他一分钟便不能再等待。他立即去给爷爷打电话。他的语气里有难以抑制的兴奋。他说:“爷爷,我想找我妈妈。你能找到我妈妈的联系方式吗?”听筒那头一片沉默,他只能听到爷爷的喘息声。他有些焦急:“爷爷,我想上学,我想找到我妈妈,我妈妈会供我上学的。爷爷,你一定要帮我找到我妈妈。爷爷!”还是喘息声。少年终于哭起来。他知道,这算是对爷爷的背叛哪。让爷爷去找一个当初狠心弃家而走的女人,还要去向这个女人坦承,他们父子没有能力照顾好孩子,没有能力供他上学,还要仰仗她。但是,他确实想上学啊。除此之外,他也确实想要看一看自己的母亲啊。
少年不再说话,只拿着电话哽咽。他的委屈,他的未来,比不过那些陈年的纠葛情仇?
爷爷终于开口,声音细弱地像是说给自己听:“树啊,你别哭,爷爷去找。爷爷找到了就告诉你。”
两天后,少年接到了爷爷的电话。爷爷通过村子里一户当年和他的母亲有过往来的老乡找到了少年舅舅的联系电话。少年将这11位数字记在一张纸片上,小心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每想到那有着一串数字的纸条时,他的心就“咚咚”跳,会是怎么样的结果呢?他已经挨不到下班了。他找机会跟厨师长说,他肚子疼得受不了了,他要去医院买几片药来吃。
终于溜到街面上,他四处找僻静的地方。待走进一条偏僻巷子,听不到车来人往的声音,他才从口袋里捏出那张小纸片,仔细展开,然后一个键一个键地按下纸上的数字。
“从小到大,那是我最紧张的时候,连期末考试我都没那么紧张过。”少年又是一阵戏谑的腔调。他问我:“你有过那样的时候吗,心跳得止不住,手心里出汗,又害怕又期待,电话拨通了,甚至想赶紧挂掉,不打了?”我想一想,大概谁的人生里都有一两个这样的瞬间吧,于是点点头。
少年又“嗨”一声,继续说:“刚听到电话里‘嘟嘟两声,我就想挂了,结果就那会儿,那边人接起来了。”
少年的舅舅问:“哪个?”
少年在电话里嗫嚅:“我……我……我找杜喜芳。”
那边人继续问:“你是哪个?”
少年说:“我是她儿子,林树。”
那边不再说话。沉默一会儿,说:“你找她干什么?”
少年的怒气一下子就从心底腾蹿出来:找她干什么?她是我妈妈,生下来就没有管过我,居然还问我找她干什么?
但话说出来,居然还是卑微的:“我想去看看她,我还没有见过她。”
舅舅说:“那我问问吧,不知道她现在在不在家。问完了给你回电话。”
电话挂了,前后不到一分钟。少年慢慢走回餐厅,每一步都像踩在云上,虚妄到内心像升起了大雾,迷迷蒙蒙的什么也看不清。可是,他想看清啊,他想看一看他站在雾那头的母亲,他想看一看铺在他前面的路到底通向哪里。他落魄地走回餐厅,倒真像是病了。厨师长看到他的模样,关切地问:“还没好一点吗?不行就回去睡一觉吧。”
他的舅舅还算是一个讲究信用的人,第二天就给他打来了电话,口气听着似乎比前次热情些,内容也让少年心里的希望又呼啦啦地长出来,一会儿时间就已经是绿油油一片了。
母亲在重庆。舅舅让他买好到达重庆的火车票后说一声。等到了重庆,舅舅和母亲一起去接他。
听到这个消息,少年立即辞了餐厅的工作,一路雀跃回家。他拿出爷爷塞给他的钱,去火车站买了一张去往重庆的硬座票,同时把火车的车次信息发给舅舅。待到达坐火车的日子,他买齐了火车上的吃喝,提着大小包裹满心欢欣地走进候车室——他要去看母亲了,那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女人。心里像升起一轮明汪汪、娇艳艳的太阳,连拥挤的候车室、怪味四起的人流看上去也是明媚的。
“就准备要检票上车了呀。”少年的语气里竟是不屑,“居然在那会儿又接到我舅舅的电话,他跟我说,我别过去了,我妈已经走了,去了哪他也不知道。”少年的鼻子里“哧”的一声。他竟是懒得去指摘他母亲和舅舅的谎言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早已经不需要安慰,他要的只是倾听。
少年听舅舅说完,愣了一会儿。他看到本来坐着的人这会儿全都站了起来——他们要检票进站了,而他不用了。舅舅说:“林树,我就是电话跟你说一下,省得你跑过来,也见不到你妈。”
少年突然觉得,这电话里的声音可真难听。他皱了皱眉,整张脸都扭曲起来。他对着电话吼道:“滚你妈的!”然后将电话狠狠地摔到地上,用脚碾碎。提起包裹,逆着人流向外走去。
他在火车站附近找到一家小旅店,将东西放进房间。又出门买了一打啤酒和一包熟食回去。他第一次想喝醉。父亲常常喝醉,一喝醉就丑态百出。他最是瞧不起父亲喝醉的样子,像雨天里的一只癞皮狗,伏在床上,打响亮的嗝。
他把啤酒一瓶瓶用牙咬开,打开装熟食的包装袋,就一个人吃喝起来。他从来都有这样的体验,当心里空落到无以安置的时候,把胃填满是最合适的。
他喝醉了,还断了片,不记得自己是怎么醉倒,又怎么上床睡觉的。醒来时,阳光照在脸上。房间里滚动着浓烈的啤酒气息,还混杂着残剩的熟食的味道,竟有些让人作呕。他苍白着脸,突然就非常非常想念爷爷。想念乡路尽头的晚霞。想念那一盘黑黑的灶。还想念爷爷哼唱的小曲。
他嘤嘤地哭起来,这世界上唯他不弃的只有那一副干瘦的臂膀了。他捡拾好自己的包裹,又去火车站买了一张硬座票。他要回家,回爷爷的家。只有那里,才是他可以依赖,可以成为一个孩子的家吧。
头发已经洗完。少年也便止了话头,给我把头发擦干包好,扶我坐起来。
我还想听下去,便问:“后来呢?”
少年很轻松地说:“后来我就从爷爷那里来伊宁市啦,到理发店里打工,当学徒。不过,我不太喜欢这个,你说,等我赚了钱,去学计算机可不可以?”我哑然,不知道作何回答——大学本科里学计算机的人也是一捏一大把,很多人尚无用武之地,何况他竟是初中都未毕业呢!若直接说不行,又觉得过于残忍,谁不是靠着一点想头过日子呢。
于是模棱两可地回答:“或许可以吧。你和你爸爸怎么样了?”
“嗨。”他头一偏,一头黄发借机抖动起来,话也跟着轻飘飘地出来:“还能怎么样,老样子呗。今年过年他还回来了,我一句话没跟他说。我没有他这个爸,我只有一个爷爷。”看我从洗头发的台子上下来,他立即说:“小心台阶。”熟练而体贴。
他的故事讲完了。我们再没有说话,我也再没有去过那家理发店。
只是偶尔会想,他脸上的土气是不是少了些了?他心里的那场大雾可曾散去?他是不是能看清铺在他前面的路了?
可又一想,日子弯弯绕绕,千年如斯,对于我这样一个年近而立的人来说,都没能看清前面的路,他一个少年——一个只有爷爷的少年,又哪能轻易看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