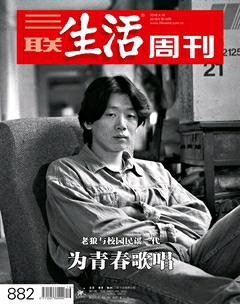设计:时尚的未来,是现在
钟和晏
也许,时尚的未来取决于设计师们现在的行动,能否让设计成为诠释和改造社会现实的工具。
还是2004年7月,国际艾滋病大会正在曼谷IMPACT会议中心召开,大厅中央展示着一些西装、晚礼服、鸡尾酒裙等。尽管会议主题很严肃,那些服装却华丽而撩人。参加会议的荷兰作家哈恩·内夫肯斯(Han Nefkens)特意凑近去仔细看了看,才发现它们都是用涂了色彩的避孕套制作的。
内夫肯斯也是一名艺术品收藏家,但从未涉足过时装领域,这些避孕套服装吸引了他。“因为它们不同于我以前看到过的任何东西。”他买下了其中7件,把它们装进盒子送往荷兰乌得勒支的中央美术馆,他之前购买的艺术品正在那里展出。
“背后有某种理念支持,而且与艺术有相互交集,这样的时装让我怦然心动。这是一个可以投资的有趣领域。”如今,他站在深圳华·美术馆的展厅里回忆说。他和当时中央美术馆的时装策展人荷塞·突尼辛(Jose Teunissen)商讨怎样以可行的方式进一步发展他的想法,决定从2006年开始与鹿特丹博伊曼斯·范伯宁恩美术馆合作,推出了聚焦时装和视觉艺术的“时尚临界线”项目。
参观了多个工作室之后,内夫肯斯不无惊讶地了解到,即使是国际知名的时装设计师,如果作品不适用于商业目的,仍然会面临资金的困难。他决定帮助其中一些人,帮助设计师脑海中酝酿出的奇幻想法获得生命。作为回报,他们设计制作的服装或艺术装置一部分将成为他的藏品,并长期租借给美术馆展出。2008年,他创立了“哈恩·内夫肯斯时装奖”,每两年嘉奖一位探索时装艺术的年轻设计师,提供总计2.5万欧元的奖金,其中1.5万欧元用于委托创作。
过去七八年内夫肯斯的藏品或者委托设计,加上数十件借来的作品,构成了《时尚:当下即未来》展览的内容,由荷兰国际文化中心和品项引入中国,从3月末开始在深圳华·美术馆展出。
展览中的全部35组作品出自世界各地13个国家的年轻设计师,他们几乎都在强调传统工艺和环保概念,其中大部分都乐于取笑现在的时装产业。内夫肯斯评价说:“其实,这些年轻设计师的头脑中只有一个问题:如何保持真实的自我,同时又能在残酷的时尚界生存下来。”
展厅入口不远处,一件真人大小、用金色纱线编织的骷髅,正扭曲着身体斜倚在沙发上。灯光打在他空洞的眼眶和下颌骨上,似乎在向你露齿而笑,一种既魅惑又瘆人的感觉。骷髅背后的整个沙发连同地上铺的地毯,也都是由金色、银色、鲜红、粉红等纱线编织而成的。
这件名为《对话》的编织雕塑出自波兰艺术家奥列克(Olek)。起初,她选择钩针编织这项古老的技术是出于囊中羞涩,负担不起别的创作形式。她将编织视为人的身体与精神相关性的一种隐喻,以此探讨女性特征、女权主义等社会问题。2014年,她为国际妇女节创作了一幅数米长的编织壁画,“如果男人能够怀孕,堕胎将会成为一场圣礼”这句话以醒目的白色字体,嵌入红、黄色的背景图案中。
“我不想设计一件晚礼服之类的服装,更愿意专注于人体形态本身。”奥列克解释说,“时装设计通常有意突出人体最值得夸耀的部分,遮掩住被认为不满意的地方。通过编织一具完整的等比例人体骨架,我想突出人体最基本的元素和轮廓,并表达对人的身份特征的反思。”
同样以编织的方式进行创作,中央美院实验艺术系毕业的装置艺术家王雷选择的材料是纸张而不是纱线。深入研究了卫生纸的属性之后,他把纸在潮湿状态下拧成线,然后织成服装。他的装置作品《手织手纸》就是这样织成的一系列乳白色服饰,外套、背心、连衣裙、围巾等挂在衣架上,每一件下端垂下细细的白线,仍然连接着一卷卷卫生纸。
用时间编织时间,用记忆编织记忆,这里包含了媒介的重构、手工制作的体验和环保回收的概念。手纸的织物是故事的叙述者,带着劳作的痕迹,也夹杂着社会寓意。
同样是手工编织,对于出生于1974年的日本变性人艺术家碧悠毕露(Pyuupiru)来说,这更多是面对个人生活困境的抵御手段,一种难以形容的挣扎过程。长久以来,“一个女人的灵魂装在男人的身体中”这一性别混乱造成她的焦虑和抑郁,只有服装和化妆是一种盔甲,能够改变她的身体和身份。
从2001年开始,她编织出第一件行星主题的服装是“地球”,用三个半月的时间,每天编织10个小时。大约3年以后,她完成了整个“天象仪”系列的9款编织服装,从水星、金星、火星到土星、木星、冥王星等,每一款代表一颗行星。这些“行星”没有固定的式样,而是在编织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她穿上它们拍下照片,配合各种造型和面部表情。
很快,这一“天象仪”系列受到了横滨艺术三年展的参展邀请。事实上,那时候的“她”还是“他”,2007年,她在泰国接受了变性手术。
从一开始,她的作品就没有特定的艺术策略和亚文化目的,仅仅出于一个诚实的决定,反映她对于自己身体的情感,与他人分享她的痛苦和恐惧。她说:“对我来说,身体如一个易碎的玻璃花瓶,表情是倾倒在花瓶中的彩色液体。所谓的身份特征,就是让人把液体倒入花瓶的愿望。”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特质”成为时装设计师的一种基本要素。安特卫普六君子被贴上比利时标签,维克多和罗尔夫(Viktor &Rolf)以及亚历山大·凡·斯洛贝等因为设计概念中明显的荷兰特色,被称作“荷兰现代派”,三宅一生、山本耀司及川久保玲等代表了一种源自和服传统的日本时装特征。在这个世纪,传统、本源和身份认同等概念仍然重要,但它们不再被用来塑造那种“民族特质”。
荷塞·突尼辛现任伦敦时装学院设计与技术学院院长,作为《时尚:当下即未来》的策展人,她分析说:“全球化滋生出一种新的审美观和设计语言,如今的年轻设计师不再寻求原生的民族风格或地域化的工艺特色,他们热衷于运用新技术,构想出新的时装表现方法,对过度的消费主义时尚体系和非可持续性生产方式持批评态度。他们提出的问题都关乎未来的:在这个社会中我们走向哪里?在未来我们怎样定位我们的身份和传统?”
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一件时装产品的价值?设计师的个人背景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比利时概念时装设计师克里斯多夫·科彭斯(Christophe Coppens)是“哈恩·内夫肯斯时装奖”的第一位得主,2012年5月,作为一名成功的时装设计师工作了21年之后,他决定关掉工作室,终结他的职业生涯。他发现这个领域过于僵化和匆忙,只有从中脱身,才能真正摆脱时尚体系的约束。
科彭斯决心与过往的生活和身份彻底告别,他拥有许多出自著名设计师的个人服饰,从身份象征来说,这些衣服已经不再适合他了。他把它们通通剪碎,加上以往的草图本、照片、档案材料、多年收集的藏品和私人物品等,都组合到他的装置“一切都来自当地:景观”中。这样,他将自己从事时装设计的历史,转变成了由循环再利用的材料制作的景观艺术品。
从2013年以来,澳大利亚设计师丽卡达·贝格琳和内拉·提米里奥斯则将焦点对准了“品牌幻觉”。她们捏造了一个商业品牌“Dolci&Kabana”,谁都能理解其中的讽刺意味。她们以产品系列、表演、视频等方式对大品牌日常遵循的商业机制进行研究,试图向观众揭示所谓的品牌形象:品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品牌如何在媒体上通过文字和图像发挥作用?它们如何赢得消费者的认同,让他们幻想自己就是某品牌的一部分?
今年36岁的露西娅·库巴(Lucia Cuba)1980年出生于秘鲁首都利马,一直在那里生活,她更关心服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触及社会问题。政治和行动主义在南美有长久的传统,作为服装行动主义的一个典型案例,她推出了“第六条款:性别、实力和政治叙事”这一持续进行的激进设计项目,试图把时装作为行动和政治的工具,从功能和审美拓展到社会、伦理和政治的视角。
秘鲁“健康法案”第二章第六条款规定,每一位秘鲁公民都有权选择自己偏好的避孕方式,在涉及无法改变的医疗程序时,必须征得当事人的书面许可。但是,在1996年到2000年藤森总统在位期间,超过30万名女性和1.6万名男性被强迫或诱骗绝育。这些人都来自秘鲁最贫困的地区,由于手术经常在不洁净的环境下进行,导致术后并发症甚至死亡。
由社会丑闻激发的“第六条款”项目包括34件不同服装以及12项表演、展览、摄影、讲座等行动,受害者的证词、政治演说、研究文件和法律都是其中的素材。露西娅·库巴的目的是让政府承认这一暴行,并给予受害者应有的关注。
系列中的服装是通过混合媒介制作的,包含了制服和军装的元素,对安第斯传统服饰“polleras”的解构与重新演绎,与暴行相关的图像和符号被刺绣和印制在斜纹棉布和棉质帆布上。当Lady GaGa推出她的一款香水“名声”时,就身穿了其中一件。
时装是人的欲望反射,欲望无穷无尽。不过世界并不以人的欲望为导向,而是凭借一针一线的辛苦劳作而建构。从《时尚:当下即未来》展览中,可以清晰地听到设计师们用他们的针线作品,以分析和批评的视角提出无声的质疑。设计是否具有表达特定社会体验的基本能力?时装是否会满足于完全被商业规则控制、生产的产品只是为了销售?快速周转的时装体系中是否存在精神缺失?也许,时尚的未来正是取决于设计师们现在的行动,能否让设计成为诠释和改造社会现实的工具。
拥抱我/陈思扬
中国澳门设计师陈思扬以“每个人都需要爱,你不是吗?”的想法,设计了六套服装,每一套都会出现“手”的造型,代表一个独立的故事。衣服经过夹棉处理,“手”中塞进了填充物,为了强调被拥抱的满足感,在腰部、肩部和头颈处紧紧拥抱着穿着者。最后,他混合各种布料,以众多手臂重叠出一件夸张的斗篷。
通过“拥抱我”,他希望强调“拥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互动和交流是城市生活中表达爱、远离孤独的行为”。
生物蕾丝/卡罗尔·科莱
作为一种生产手段,“有机生成”利用生物过程,以完全有机的、可持续的方式生产产品。“生物蕾丝”项目是法国设计师卡罗尔·科莱(Carole Collet)持续了十几年的项目研究,一个在资源稀缺的世界结合食品和纺织品生产的激进观念。
她将纺织设计与合成生物学结合起来,通过对生物形态的设计研发出新的纺织品。比如从黑草莓植物的根须部分,生长出黑色的蕾丝样本。科莱说:“未来对细胞发育的控制,意味着我们可以设计出执行特定功能的植物,就像编写的软件一样,控制DNA也能够让我们控制自己的生活。”
结构关联/露西+乔治·沃塔工作室
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是独立的个体?又在多大程度上属于集体的一部分?我们是否该顺从于整体使其持续运转?还是选择保持个体独立性却要面临整体分崩离析的危险?英国的沃塔工作室试图在《结构关联》这件作品中表现和探讨这些问题。
表演者身穿相同的、富有未来感的服饰,通过布带把原本分开的衣服连接在一起,串联出方格的布阵。完全一致的服饰以及将个体融入整体的组合方式,设计师意在抹去人对个体的感受,甚至是人性的消失。个体被弱化成这一几何状整体的组成部分,只有人人听命,整体才能按照预定方向前进。
身体容器/陈丽云
中国设计师陈丽云的作品《身体容器》试图检视时装和时尚媒体之间的关系,她把成堆的纸张切割成细窄的纸条,连接起来再编织成一个容器,将人体从头到脚包裹起来。她选用时尚杂志是因为很多人将时装视为表达个人身份的手段。时尚杂志规定人们该穿什么,决定哪些风格是所谓的时尚,哪些是不被接受的,这是否反而限制了个人表达的自由呢?陈丽云希望以她的作品关注到层层衣服下面真实的人。
她曾经包裹在“容器”里,站在香港街头数小时。有人对着她拍照,其他人加入进来,他们会彼此交谈,但是对容器里的人视而不见,好像她是隐形人。她还去了香港的菜市场,听到人们在争论里面是否有人。
编织是一种关系性的产品,她想把更多的故事编织进去。容器的表面可以辨别出个别文字和图像,更多被深深嵌入编织的线圈之中。但是,公众不需要理解印刷在纸条上的文字,他们观看“身体容器”这一行为就意味着沟通,语言沟通的界限因此被打破。艺术以一种可理解的方式,转化成与生活的连接,它创造了另外一种阅读方式。
长袖子/安托万·彼得斯
在2014年春夏系列“这不是一件运动衫”中,荷兰设计师安托万·彼得斯(Antoine Peters)制作了一件世界上最长袖子的运动衫,灰色针织棉的袖子超过了130米,他为此申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彼得斯着迷于时装,是因为它接近身体。但是他认为服装的力量不仅仅是通过它的功能性或可穿戴性获得的。他要寻找极端,寻找时尚固有的夸张特征。
通过“长袖子”,从字面意义上说,他“拉伸”了时尚的概念。这种拉伸远远超出了人体的范围,占据整个空间,衣服周围的空间变得和衣服本身一样重要。
上图:塞尔维亚设计师安娜·莱切维奇作品《进化的一面》
下图:日本变性人艺术家碧悠毕露编织的行星主题系列服装中的“水星”和“地球”
左图:芬兰设计师明娜·帕姆韦斯特作品《亲密社交》
右图:波兰艺术家奥列克和她的《对话》编织雕塑
秘鲁设计师露西娅·库巴推出了“第六条款:性别、实力和政治叙事”这一激进设计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