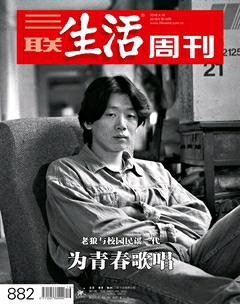时事:巴基斯坦:困于暴恐
徐菁菁
基于宗教的暴恐事件,越来越成为这个国家内在冲突的重要因素。 伊克巴勒公园是巴基斯坦东部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最大的公园之一。3月27日星期天傍晚19点,正是公园里游人最多的时候。一位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在距离公园秋千几步远的地方引爆了含有钢珠的炸弹。截至第二天凌晨,炸弹造成72人死亡,412人受伤,大多数为妇女儿童。这是两年以来巴基斯坦发生的最大规模袭击事件。警方在公园里找到了自杀式袭击嫌疑人法里德(Muhammad Yousaf Farid)的身份证。法里德出生于1988年1月1日,来自旁遮普省的穆扎法尔格尔市。最近8年,法里德在拉合尔的一所宗教学校生活、学习并成为老师。
巴基斯坦极端武装、曾经向获得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的17岁人权活动家马拉拉·尤萨夫扎伊(Malala Yousafzai)发出死亡威胁的“自由者大会”宣布对这场惨剧负责。该组织发言人称,这次袭击针对的是基督教信徒。3月27日正好是复活节,不少基督教家庭正在公园里举行庆祝活动。这同时也是传递给政府一个信息。该组织发言人说:“即使在他们(政府)势力强大的地方拉合尔,也不能阻止我们。”拉合尔是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Nawaz Sharif)的故乡,他的弟弟沙巴兹(Shahbaz Sharif)正是该省的首席省长。
3月28日,在经过了一天的闭门会议后,总理谢里夫宣布,他将为“每一滴血报仇”。巴基斯坦军队第一次进入了拉合尔展开反恐突袭。到3月30日,260余人被逮捕。
但即使是最乐观的观察家,也难以对巴基斯坦未来的安全局势给予积极判断。2001年“9·11”以来,巴基斯坦对恐怖组织的打击主要集中在与阿富汗接壤的北、南瓦济里斯坦地区,以及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北部的巴焦尔和与之相邻的斯瓦特山谷。当巴基斯坦被置于阿富汗反恐的大框架之下时,它自身的危险和复杂局面往往被世界忽略了。
2009年,在旁遮普城镇高吉拉(Gojra),带着枪的蒙面不速之客挨家挨户问里面有没有基督教徒。当人们惊恐地回答“有”的时候,他们便把化学品倾入屋内,点燃大火。有时他们甚至不会发问,直接放火并投掷石块。这场袭击导致高吉拉基督教徒聚集区9人死亡,45户人家的房屋被烧。这只是巴基斯坦近年来发生的众多针对少数宗教派别的袭击之一。这场暴行的实施者被认为是旁遮普省章马吉亚纳市(Jhang-Maghiana)的羌城军(Lashkar-e-Jhangyi)。这是一个从巴基斯坦极端组织“先知之友”(Sipah-e-Sabah Pakistan)分离出来的团体,它是巴基斯坦最血腥的恐怖组织之一。
然而,2013年,在章马吉亚纳市的清真寺里,毛拉阿赫迈德·鲁迪安维(Ahmed Ludhianvi)向蜂拥而来的信众宣布他要竞选巴基斯坦国会议员:“你们发自内心地热爱伊斯兰领袖吗?起来,把钱像下雨那样奉献出来吧!”虽然巴基斯坦禁止在清真寺举行竞选活动,但并没有人阻止鲁迪安维。
鲁迪安维曾因从事恐怖活动和煽动仇恨少数族群的嫌疑而多次进监狱。事实上,他正是“先知之友”的成员之一。这个极端组织在2002年被禁。但它很快改名为“逊尼派联盟”(Ahle Sunnat Wal Jamat,ASWJ),由鲁迪安维担任主席。鲁迪安维的敌人不只是基督徒,ASWJ也向什叶派穆斯林发动袭击。枪手在偏远山区的公共汽车上拖出什叶派信徒,自杀性炸弹袭击者把血腥带到大城市。2012年,巴基斯坦内务部进一步向ASWJ发布禁令,但这并没有对该组织造成任何影响。“我们有成千上万人的支持,如果你压制我们会发生什么?”去年7月,ASWJ的一位领导人迪沙德·阿赫迈德(Dilshad Ahmed)反问《华尔街日报》记者。
鲁迪安维的政治目标是“要求全面推行伊斯兰教律法”,推动进一步加强对“渎神”行为的处罚,并引入对窃贼的砍手刑。他的助手穆罕默德·安瓦尔·赛义德(Mohammad Anwar Saeed)称,应当禁止什叶派穆斯林在他们的礼拜堂外举行任何宗教活动。传统上,伊斯兰教历一月时,什叶派穆斯林在大街上游行,举行祈祷、自我鞭笞等活动。鲁迪安维的追随者戴着象征ASWJ加入的宗教党派联盟的标识走街串户,为他争取选票。但他们绝不会走到什叶派穆斯林家里去,他们说:“什叶派就是猪狗,我们不能要他们给我们投票。”
鲁迪安维2013年的选票在章马吉亚纳市排名第二。但2014年4月,巴基斯坦选举委员会宣布排名第一的候选人涉嫌操纵选票、拖欠贷款,鲁迪安维成功取而代之,成为国会议员。
鲁迪安维的故事是理解巴基斯坦今日困境所不能忽视的信息。他并不是个例。就在谢里夫总理誓言为袭击死难者复仇的时刻,他的政府正在受到冲击。3月28日,数千名宗教人士在伊斯兰堡举行示威活动,要求议会停止任何修改用于维护伊斯兰教权威的《反亵渎法》的计划,并立即将所有违反《反亵渎法》的人处死。他们不断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巴政府封锁伊斯兰堡重要路段,军方在伊斯兰堡部署300余名士兵加强首都安保。美国等国临时关闭了驻巴使馆。
1986年修订《刑法典》时,政府为了安抚和迎合宗教势力,规定对犯亵渎先知穆罕默德罪的人判处死刑。2015年10月,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宣布对《反亵渎法》进行改革,认定该法一直用来攻击宗教少数群体,这种“宗教治安维持制”将大大危害巴基斯坦的法律,并且“已经到了惊人的程度”。2009年,旁遮普城镇高吉拉的恐怖袭击正是以惩治亵渎罪之名进行的。当年7月28日,当地一个基督教家族庆祝了一场婚礼,有流言说有狂欢者把《古兰经》撕碎后抛撒——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发生过这件事。袭击发生前,附近清真寺的一位阿訇进行了一场布道,煽动众人对基督教徒使用暴力。
“罪犯被逮捕之后迟迟无法定罪,案件进展缓慢、结果摇摆不定,甚至完全被放弃,主要原因包括警察无法提供定罪所需的证据,律师和法官都不敢面对限制《反亵渎法》运用范围这一难解之题,为被告辩护的律师还经常受到威胁甚至被杀害。”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人权法律专家阿贾德·马赫穆德·汗(Amjad Mahmood Khan)分析说,进一步的,极端组织可以利用相应法律证明其行为的正当性——“他们宣称屠杀印度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原因是他们侮辱了伊斯兰教,杀害军人家庭孩子的原因是他们的父母暗中支持美国的打击行动。他们行为的理由很明显:镇压对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国家地位造成威胁的人,不论这种威胁是多么间接。”
《反亵渎法》映照出了巴基斯坦种种暴行背后的社会深刻分裂。2010年11月,信仰基督教的妇女阿西娅·比比(Asia Bibi)因亵渎先知而被判死刑,这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争议。女议员雪丽·拉赫曼在国会提议修改《反亵渎法》,而旁遮普省长塔西尔(Salman Taseer)不仅坚决支持提案,还亲自出面请求总统特赦这名基督教妇女,与其共同接受电视媒体采访。身为穆斯林的塔西尔成为极端宗教势力的眼中钉,许多清真寺阿訇公开呼吁杀死这个穆斯林的“叛徒”,认为其同异教徒一样亵渎了神灵。最终,塔西尔的贴身警卫马穆塔兹(Mumtaz Qadri)向他射出了27发子弹。塔西尔成为自前总理贝·布托2007年末遇刺以来被害的巴级别最高的领导人。
塔西尔遇刺案件的争议从未消失。凶手马穆塔兹得到了500多名伊斯兰神职人员的支持,在进入法庭前被赞颂“保卫”了伊斯兰教。直到今年2月29日,马穆塔兹才最终被处以绞刑。
3月28日,围困政府机构示威的人们要求政府追认马穆塔兹为“殉道者”,处决阿西娅·比比等“亵渎伊斯兰教”的基督徒,实行严厉的伊斯兰法。
“机关政府已经表示发生在拉合尔的爆炸与发生在伊斯兰堡的示威并无关系。”巴基斯坦基督教人权律师萨达尔·慕斯塔克·吉尔说,“但他们的诉求是一致的。”
谁的国家
前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员法拉赫娜兹·伊斯帕哈尼(Farahnaz Ispahani)在《净化圣洁之地》(Purifying the Land of the Pure)一书中讲述了一个现象:巴基斯坦非穆斯林人口比例从独立时的23%下降到如今的3%。巴基斯坦的宗教构成不断被“纯净化”,这不仅发生在基督教徒和印度教徒身上。据她说,有6万巴基斯坦人被圣战分子杀害,她把这称作“慢性种族屠杀”。在这个国家占绝对人口优势的伊斯兰群体中,最初,艾哈迈迪教派(Ahmadi)的成员受到迫害,并被宣布为非穆斯林。随后,极端分子开始屠杀什叶派。如今,苏菲派(Sufis)与其他被宗教领袖视为不够正统的“温和”逊尼派又成了极端分子的目标。独立后,巴基斯坦社会对于信仰的宽容度不断降低。一个印证是,去年底,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公布了一项不同宗教、种族和地区对“伊斯兰国”看法的调查报告。报告称,在巴基斯坦,只有28%的人对“伊斯兰国”评价负面,62%的人对极端组织没有意见。
巴基斯坦社会的敌对情绪在建国时就埋下了种子。巴基斯坦的民族基础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民族,而是基于“两个民族”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南亚次大陆的居民中,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在宗教、语言、风俗、服装、节日、饮食等文化方面截然不同,应当依据各自宗教属性独立建国。巴基斯坦独立运动的领导者是那些受英式教育并持有现代化观念的人,而非那些在传统神学院受教育的人。“国父”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annah)主张在西方文化和政治权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世俗的现代国家。但巴基斯坦并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在独立初期,俾路支人和帕坦人就要求分离出去。真纳必须依仗伊斯兰教来缔造一个共同的“伊斯兰认同”来遏制“亚民族认同”。于是,“伊斯兰认同”与“国家认同”等同起来。在这个过程中,真纳这样的现代主义者不得不借助正统的乌里玛(泛指所有得到承认的、有权威性的穆斯林教法学家和神学家)的力量推进其政治目标。巴基斯坦前外交秘书里亚兹·穆罕默德·汗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冲突·极端主义·抵制现代性》一书中指出:国家建立后,乌里玛试图将巴基斯坦塑造为模范伊斯兰国家的急先锋。1948年9月,真纳因病去世,巴基斯坦由此失去了强有力的仲裁者,这就令新国家的前进方向与身份问题成为持续争论的主题。
巴基斯坦到底该成为一个世俗化的现代国家还是伊斯兰化的穆斯林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争论不休。于是,巴基斯坦的国家身份一直是现代主义和传统主义相互妥协后含混不清的结果。1956年通过的第一部宪法承认宗教自由,但它同时认定巴基斯坦是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国家元首必须是穆斯林”。宪法虽然没有直接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但却认为人民的权利是真主赐予的。1962年,第二部宪法改国名为“共和国”,删除了有关法律必须与《古兰经》和《逊奈》保持一致的条文。到了第二年,在宗教势力的压力下,这些条款又被恢复了。
宗教成为政治家的权力手段。1971至1977年,阿里·布托担任巴总统期间,为应对反对党的挑战,自由接受西方教育的布托承诺将《古兰经》作为国家生活的核心部分,建立联邦伊斯兰学院,还发起了关于巴基斯坦历史和文化的讨论,强调伊斯兰教是巴基斯坦区别于其他民族国家的重要标志。此外,布托还宣布了一系列诸如禁止销售酒类产品和把休息日定在周五的伊斯兰教法。
1988年8月17日巴基斯坦总统兼陆军参谋长齐亚·哈克因飞机失事遇难身亡。巴基斯坦方面迄今没有公布这起空难的调查结果。一种猜测是,巴基斯坦的什叶派穆斯林势力是这场空难的制造者。
1977年7月5日,齐亚·哈克领导的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发动政变,对包括阿里·布托总理在内的巴基斯坦人民党全部政治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全国联盟的领导人实行拘捕。此后的11年,巴基斯坦进入了伊斯兰化的快车道。
齐亚·哈克出生在印度北方邦的贾朗达尔,印巴分治后,他的家庭定居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木尔坦。这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位虔诚的穆斯林,自哈克幼年时代起就向他灌输伊斯兰教规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但哈克对于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化改造,更多是出于一种政治实用主义的考虑。作为以军事政变方式上台的领导人,哈克缺乏民众基础。为建立执政合法性,他极力争取伊斯兰势力的支持,试图在伊斯兰教信仰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苏军入侵阿富汗之后,巴基斯坦面临苏联和印度两个方向上的双重威胁,伊斯兰化又成为加强国家团结和凝聚力的现实理由,巴基斯坦被描述为伊斯兰的堡垒。
齐亚·哈克对巴基斯坦的改造对今天的巴基斯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掌握国家实权的军队,他用“信仰、虔诚、为主圣战”的教条展开改造,在军营内建立清真寺和祈祷堂,在训练课程中加入宗教内容,并经常将伊斯兰促进会领袖毛杜迪的著作授予其下属作为最高奖励。宗教知识和宗教责任成为军官遴选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巴基斯坦军队不但是边疆的保卫者,也是巴基斯坦的“意识形态前线”的保卫者。他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法律以保证巴基斯坦在意识形态领域全面实行伊斯兰化,通过推行伊斯兰化的政策和计划,伊斯兰教法成为最高法律。
里亚兹·穆罕默德·汗指出,齐亚·哈克伊斯兰化政策的灵感来源是沙特的体制。他执政时期,沙特在巴基斯坦社会上的政治影响和金融影响日渐增强。这种影响力与伊斯兰化等一系列因素的结合,令人觉得沙特体制值得尊敬。但是,沙特与巴基斯坦的国情十分不同。“沙特拥有庞大的石油经济,人口规模相对而言要小很多,人口多样性也要弱很多,沙特王室与瓦哈比派神职人员之间具有独特的同盟关系。”这些都是巴基斯坦所不具备的。于是,“在巴基斯坦这样一个庞大而多样化的国家,既要按其字面解释来实施伊斯兰教法,又要满足当代的治理需求,二者实在是难以兼容”。
1953年,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穆尼尔·艾哈迈德(Munir Ahmed)主持的调查委员会就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巴基斯坦的尖锐矛盾:各学派的乌里玛对于谁是合格穆斯林这一问题缺乏共识。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人口中,逊尼派占80%,什叶派是少数,占20%。两大派别内部又有更复杂的分类。
齐亚·哈克实行的伊斯兰教法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体现的是逊尼派穆斯林的意志。但什叶派教法与逊尼派教法本身存在一定的差异,对很多什叶派穆斯林来说,以逊尼派教法为基础的全面伊斯兰化就等于全面的逊尼化。于是,伊斯兰化并没有加强社会的凝聚力,反而放大了差异,激化了矛盾。1980年6月,齐亚·哈克政府正式公布了有关天课(Zakat,凡有合法收入的穆斯林家庭,须抽取家庭年度纯收入的2.5%用于赈济穷人或需要救助的人)征收的法令,规定国家将按照2.5%的缴纳比例,自动从穆斯林的银行账户中扣去,并设立天课基金,全国统一管理。这一计划还得到了沙特专项资金的支持。但是,什叶派关于天课征收的范围与逊尼派存在差异。根据什叶派的传统,穆斯林在札克特之外,还需要交纳胡姆斯(五一税),两种宗教税都是穆斯林的个人义务,任何政府无权强制征收。齐亚·哈克的政策会直接影响到什叶派的经济利益,更重要的,它会从根本上改变什叶派自足的宗教体系。
对国内的宗教力量,齐亚·哈克像他的前辈一样只能借力而非掌控,而在他所处时代,巴基斯坦恰好处在伊斯兰世界的大变动之中。自60年代开始,沙特等海湾国家就以穆斯林世界联盟、哈拉迈基金会、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等组织为依托,在经济方面为巴政府提供支持,推动巴的转向。同时,沙特在巴基斯坦修建了大量的清真寺和宗教学校,并对一些逊尼派极端组织提供资助,宣传瓦哈比派思想,支持反对什叶派的宣传和武装活动。伊斯兰学者联合会、巴基斯坦宗教学者协会等机构都公开进行反什叶派的宣传。
另一方面,伊朗发生了伊斯兰革命。这大大鼓舞了巴基斯坦的什叶派。伊朗政府在短短几年中,就向近4000名巴基斯坦学生颁发了奖学金,资助他们前往库姆进行为期6个月到1年的学习。这些学生不仅受到霍梅尼思想的影响,还与来自中东各地的什叶派学生建立了联系,把流行的什叶派革命思想带回了巴基斯坦。伊朗在巴境内赞助建立了大量宗教学校或是伊朗文化中心之类的机构,针对沙特在南亚地区支持的反什叶派宣传,展开反宣传,并对瓦哈比派的思想进行抨击。
1980年7月,为反对实施逊尼派伊斯兰教法改革,全国1.5万多名什叶派穆斯林在伊斯兰堡举行集会示威,政府大楼被困两天。霍梅尼公开警告齐亚·哈克勿对什叶派进行压迫,否则会和巴列维国王有一样的命运。这些压力,迫使齐亚·哈克与什叶派代表签订了《伊斯兰堡协定》,同意增加什叶派在政府中的代表席位,并取消自动从什叶派国民银行账户上征收天课的规定。虽然什叶派的政治权利运动胜利了,但它与逊尼派的关系却日益恶化。在逊尼派看来,天课是伊斯兰教的五项基本宗教功课之一,什叶派拒绝政府征收天课,等于不履行使命,这就成了什叶派不是穆斯林的最佳证据。
无论哪个派别,在宗教学校里成长的年轻一代不仅热心政治事务,而且视武装斗争为必要手段。从80年代开始,巴基斯坦宗教派别之间的暴力仇杀就蔓延开来。
覆水难收
里亚兹·穆罕默德·汗指出,在整个90年代,尽管教派暴力活动被视为毒瘤,政府对其也采取了一定的打击措施,但对于掌权的军队来说,他们依然有超越教派属性的价值。比如在与印度有领土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极端主义武装的活动得到了默许和支持。那个时候,一个判断是,这些武装并没有潜力动摇政府、挑战政令。“9·11”事件之前,军方以教派暴力活动这一狭隘视角来看待宗教性武装活动,基本上将其视为应由文职的政治与行政当局来处理的法律与秩序问题。包括警察在内的地方民事当局在逊尼派武装分子采取行动的时候经常犹豫不决,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这些人员与军方或联邦政府内政部下属的情报部门有联系。
但那时候,政府已经发现,政令的发布被宗教情绪裹挟了。1999年初,巴基斯坦外交部提议修改程序,规定只有经过县行政官级别的筛查之后,才能根据《反亵渎法》立案,希望借此将滥用法律的情况减少到最低限度。1999年10月,时任总统穆沙拉夫批准了这一建议,但不久就被迫推翻其决定。因为他被告知,这一决定已在“基层士兵”之中引起了严重焦虑。
“9·11”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巴基斯坦政府协助美国和国际社会打击阿富汗塔利班的政策激起了宗教极端势力的强烈不满。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邱永辉指出,巴基斯坦伊斯兰教团体中出现了“新伊斯兰主义者”——包括巴基斯坦塔利班、圣战组织和伊斯兰主义者。他们通过公共平台赞扬圣战、经营庞大的宗教学校网络和军事训练中心,培养年轻干部,并使其听从他们发出的“伊斯兰指令”,从而巩固自己的权力。他们不但展开宗教仇杀,他们所宣称的圣战目标,此时已扩大至双重,一是使克什米尔从印度的控制中获得自由,二是使巴基斯坦从世俗政治家的统治下获得自由。虽然中央政府中断了支持,试图从宗教组织手里夺回对社会的主导权,但宗教组织早已变得财大气粗,并拥有坚实的信众基础。相比而言,巴基斯坦政府的力量则要薄弱得多。为了监视发表煽动性演讲的教士及散布煽动性资料的清真寺或教派团体,地方上就要动用警力来收集情报与采取行政措施。然而,巴基斯坦的地方行政架构先天不足,实在无力监视或约束宗教极端主义。
今年2月底,作为打击极端组织行动的一部分,巴基斯坦政府在全国关闭了254家宗教学校。同时展开的行动是打击和禁止发布仇恨言论和极端主义材料。有2345人因此被捕。
80年代阿富汗圣战期间,巴基斯坦宗教学校数量剧增,并获得了官方支持和沙特的资金援助。巴基斯坦在70年代后期境内只有宗教学校几百所,学生7000人,到2001年,已有学校超过1.6万所,学生近200万人。
里亚兹·穆罕默德·汗指出,从齐亚·哈克时代起,政府放任宗教学校的发展壮大,对这些学校毕业青年的就业并没有考虑。这些学校的学生大都来自子女众多的贫困家庭,父母乐于把孩子送进宗教学校,享受宗教教育和免费食宿,甚至获得少量津贴。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男青年从宗教学校毕业。几乎所有宗教学校的课程都严格限于宗教教义。自阿富汗战争以来,宗教学校的课程大肆强调圣战并鼓励具有仇外情绪的世界观。很多宗教学校都拒绝那些与西方相关的课程和理科教育。学校的毕业生并不具备融入经济与发展领域的相应资质,只能进入政府担任较低的文职,或者加入宗教组织,成为清真寺的伊玛目,或参加圣战。这一现象不仅充实了塔利班和其他武装团体的队伍,而且强化了巴国内的教派分野。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的李福泉在研究中指出,巴基斯坦宗教或教派关系复杂。国民97%是穆斯林,其中75%~80%是逊尼派,15%~20%是什叶派。逊尼派又分为四支:德奥班迪学派、巴勒维学派、圣训派以及以伊斯兰促进会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运动。上述支派的宗教观点大不相同,并且都建立了各自的政党和宗教学校,形成了彼此独立的宗教学校联合会。在一些学校,教师按照本学派观点授课,往往驳斥乃至否定其他教派或支派的学说。宗教政党内部盛行的教派思想通过宗教学校对冲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有不少宗教学校直接涉入其中。1995年,巴基斯坦官方确认在旁遮普省就有746所这样的宗教学校。主要的反什叶派组织“圣门弟子军”的所有领导人都是德奥班迪学派学校的毕业生。由于部分宗教学校领导人常常发表攻击其他教派的激进言论,从而成为教派仇杀的重点目标。据调查,一个地区宗教学校的密度与教派仇杀的频率成正比。巴基斯坦一些政府官员和宗教学者也认为,宗教学校对遍布各地的教派冲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几乎所有观察家都赞同,巴基斯坦要扭转宗教极端主义的趋势,就需要将宗教学校教育加以改造并纳入主流,但实现制度变革的种种努力遭到了坚决抵制。
早在2001年8月,政府组建了巴基斯坦宗教学校教育委员会(PMEB),由其负责在卡拉奇等三个城市各建一所模范宗教学校。这一计划预算为50万美元,其目的是形成示范效应,促使宗教学校主动进行变革,把其纳入国家的主流教育。此外,教育委员会计划投入1亿美元,用于支付宗教学校世俗课程教师工资、师资培训及购买课本、图书资料和计算机等费用。凡按要求登记的宗教学校有资格获得资助。11月,教育委员会为所有宗教学校制定了统一课程,其中包括英语、数学、计算机、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和巴基斯坦研究等多种科目。政府还承诺授予符合要求的宗教学校以大学地位。但是,该计划自始即遭到五大宗教学校联合会的抵制。它们拒绝使用统一课程,反对无神论和世俗思想进入宗教学校,主张自行编订教材、制定课程。政府与乌里玛的多次对话无果而终。最后,只有极少数宗教学校进行了改革。2006年6月,政府撤回了剩余的资金。
2002年6月,为掌握必要信息,政府颁布“自愿登记与规范法令”,要求宗教学校须依据1860年的《社团登记法》到巴基斯坦宗教学校教育委员会和各省相关委员会登记。这同样遭到了五大宗教学校联合会的抵制。按上述法令,拒不登记的宗教学校将被中止来自政府的各种资金或援助。但一般宗教学校有三大资金来源。第一种是穆斯林的捐助。在巴基斯坦,高达94%的个人和企业却乐于奉献资金用来支持宗教机构。宗教学校获得的此项资金每年高达700亿卢比(11亿美元),而政府每年征收的天课只有45亿卢比(7500万美元)。第二种是外部资金。这是最大的资金来源,来自外国政府及外国的公民、民间组织和巴基斯坦移民。第三种资金来自瓦克夫土地、圣地、商店和其他商业投资的收入。多数宗教学校并未接受政府资助,而即便是接受资助的学校也主要依赖其他渠道的资金,因此,上述约束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国家在这场权力争夺战中没有取得预想的胜利。2004年10月,在拉合尔的严重教派冲突结束后,穆沙拉夫曾要求乌里玛发布教法裁决,宣布自杀式袭击不符合伊斯兰教义,却遭到后者拒绝。
在伊斯兰堡,大毛拉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创建的红色清真寺在阿富汗抗苏战争时期曾是巴基斯坦向阿富汗输送“圣战战士”的重要渠道。“9·11”以后,穆罕默德·阿卜杜拉的继任者、其子阿齐兹和加齐成为亲塔利班势力的领导人物,并且开始发动圣战反对穆沙拉夫及其与美国的反恐合作。2007年,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责令伊斯兰堡市政当局摧毁这一组织下属的一些清真寺,因为这些清真寺刚好位于穆沙拉夫往返于伊斯兰堡总统府和拉瓦尔品第陆军总部的途经路线上,清真寺中可能藏匿的恐怖分子和自杀性炸弹袭击者对穆沙拉夫的人身安全构成了极大隐患。这直接导致红色清真寺下属两所宗教学校的学生与穆沙拉夫政府发生尖锐冲突,并拒绝做出任何妥协。
在与政府的对峙中,红色清真寺提出了几项诉求:一是要求在巴全国推行伊斯兰教法,二是要求释放所有在这场活动中被逮捕的人员,三是释放被美国关押在古巴关塔那摩基地的恐怖大亨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和其他圣战分子,四是要求所有部落地区的宗教学校宣布学生全部放假,让他们到伊斯兰堡参加反穆沙拉夫活动并最终将其推翻,就像1992年宗教学校学生从巴基斯坦到喀布尔推翻纳吉布拉政权一样。2007年4月6日,阿齐兹还宣布在伊斯兰堡建立宗教法庭,威胁政府如不在一个月内推行伊斯兰法关闭妓院和音像店的话,他们将发动自杀性炸弹袭击。尽管如此,为防止事件扩大化,巴基斯坦政府一直保持了相对克制的态度。2007年6月27日,政府派出600多名军警到“红色清真寺”周围驻扎,对该寺人员进行公开监控。2007年7月3日,“红色清真寺”所属100多名宗教学生突然向奉命监控他们的军警发动袭击,抢夺了一些枪支和无线通信器材。警方被迫施放催泪瓦斯试图驱散学生,但遭到学生开枪还击,双方随后发生交火。巴政府被迫于2007年7月4日凌晨宣布,对2007年7月3日引起流血冲突的“红色清真寺”发起军事行动。此次行动打死了75名武装分子,军方有11名士兵死亡,33人受伤。
谢里夫2013年5月出任总理以来反恐依然是政府的核心工作之一。最初,谢里夫希望推动与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和解——在巴基斯坦,塔利班相当于“加盟品牌”,旗下聚集了许多松散的支线组织。但双方在释放“巴塔”囚犯和在南瓦济里斯坦建立“和平区”等条件上并未谈拢,不欢而散。巴基斯坦军方于2014年6月15日发起“利剑行动”在北瓦济里斯坦部落区和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展开围剿。在此后的一年内,巴发生约400起暴恐案件,近5400人伤亡。一些观察家指出,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2014年12月16日。为报复巴军围剿,“巴塔”袭击了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省会白沙瓦一所军事管理学校,造成至少146人死亡,其中大部分为学生,并有数百人受伤。
2015年1月6日,巴议会以少有的高效率通过了反恐的“2015宪法修正案”,并于次日呈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巴全党大会在短期内起草的《国家行动计划》得到了人民的支持。根据这一计划,卡拉奇开展了“卡拉奇行动”;旁遮普则推行了对恐怖分子“零容忍”的政策。《国家行动计划》还纳入了很多难点问题,如追踪和切断恐怖资助资金,清查外国注资的宗教学校、非法组织和教派集团,清查发布仇恨演说,清查宗教学校乃至进行教育改革。这显示了巴彻底打击恐怖主义的坚定决心。尤其重要的是,谢里夫宣布,巴基斯坦的极端组织不再存在“好的”和“坏的”之分,将对所有的暴恐分子进行无差别打击。2015年2月初,巴禁止与政府一直来往密切的“哈卡尼网络”和“达瓦宣教团”等十个暴恐组织在巴国内活动。不可否认,这些行动取得了积极效果。2015年,巴基斯坦全国恐怖案件为1109件,比高峰期2010年的2061件下降了将近50%,是自2007年有“巴塔”以来,直接与恐袭有关的死亡案件最少的一年。
尽管如此,巴基斯坦-阿富汗2460公里的边境上,在约152条通道中,两国有条件进行管控的只有3条常走通道;“伊斯兰国”正在加紧对巴基斯坦的渗透,其视什叶派为异端,以“圣战”处死异教徒的主张,得到了巴国内“简戈维军”和“真主军”的支持;在政府内部,究竟如何处理极端组织依然存在争议——谢里夫的国家安全与外交顾问萨尔塔杰·阿齐兹(Sartaj Aziz)曾表示,巴基斯坦没必要对付所有的恐怖组织,打击反政府的就够了。而一旦巴基斯坦无法进行“无差别打恐”,其国内错综复杂的暴恐网络就难以剪断,恐怖分子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参考书籍:《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冲突·极端主义·抵制现代性》,里亚兹·穆罕默德·汗著)
3月31日,巴基斯坦基督教徒在Narkali教堂哀悼自杀式爆炸袭击中的遇难者
左图:2014年8月,在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锡比地区,一辆客运列车遭恐怖分子制造的爆炸袭击
下图:巴基斯坦第一任总统穆罕默德·阿里·真纳
2月16日,巴基斯坦某大学学生在进行军事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