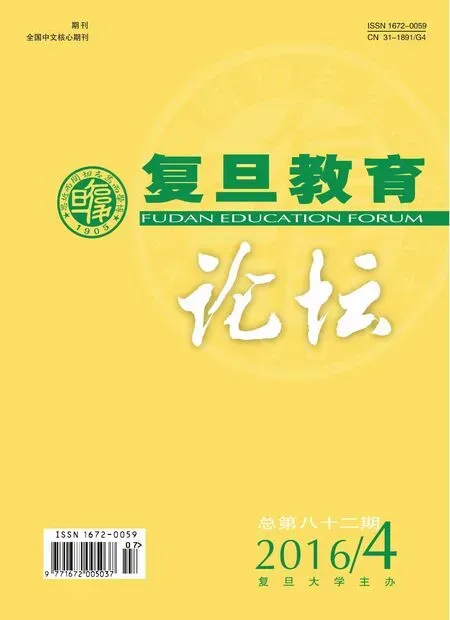公私法域的界分与交融:全球化时代公立高等学校法律地位的演进逻辑与治理意涵
姚荣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北京 100872)
·专题·
公私法域的界分与交融:全球化时代公立高等学校法律地位的演进逻辑与治理意涵
姚荣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全球化时代公立高等学校法律地位的演进呈现出同质异形的现代化特征。一方面,坚持公私法域的界分,恪守公法的独立价值,肯定公法对公立大学公益性保障的功能。广义上的公法人(包括公共机构)成为世界各国公立高等学校法律地位演进的共识。另一方面,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各自独特的法律传统、立法技术与大学哲学内涵,使不同国家公立大学的法律地位又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特殊性。公私法的相互交融,在大陆法系表现为公法人制度的更新与公法属性的调适,在英美法系则表现为公法疆域的扩张尤其是“公共机构”的范畴拓展与公法规制的增强趋势。公私法域界分与交融的“混合法规制”将成为世界各国公立高等学校法权治理的应有之义。公立高等学校法律地位的演进,使公立大学与政府及其与内部师生的法律关系逐渐变化,公立大学治理在合法性与有效性、公共性与自主性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得到缓解。
关键词:全球化时代;公私法域界分与交融;公立大学;法律地位;同质异形的现代化
一、公私法域的界分与公法人化:公立高等学校法律地位的世界共识
公私法域界分的理念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已构成法律分类的基础,社会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无疑是其划分的最初标准。其中,公法主要调整国家公权力的活动,而私法则主要关涉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活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欧洲一体化乃至全球化的影响,两大法律体系公立大学的法律地位开始经历深刻变革。“私法”的契约治理要素开始向公立高等教育领域渗透,大陆法系国家传统的公法人制度面临着更新的挑战。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公法的影响也同样深刻。“公法与私法相互渗透,产生了公法调整方法渗入私法领域,私法调整方法引入公法领域等新现象,但这并没有动摇公私法划分的社会基础。”[1]在交融之外,公私法域的界分依旧保持着特殊的治理意涵。正如施密特·阿斯曼教授所言,“因应人民相对于其他私人或国家组织之不同基本状态所确立之不同的规制模式,公法与私法有必要被区分。”[2]公法价值在公立高等教育领域的凸显与恪守,昭示着公立大学所具有的承担部分公共职能且以社会公共利益为价值旨归的基本组织特性与“事务本质”,已经获得世界各国的共同认可。
无论是欧洲大陆的德国、法国,还是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都掀起了公立高校公法人化改革的浪潮。英国、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也倾向于将公立大学界定为“公共机构”(public institution),受公法规制[3]。在两大法律体系逐渐融合乃至趋同的背景下,公法疆域不断扩张。受民营化与合作治理的影响,通过公共职能与政府行为(state action)理论的更新,英美法系甚至出现了将私人行政纳入司法审查受案范围的趋势。[4]由于公立大学关涉社会公共利益,承担部分公共职能或教育公务,它往往被视为特别的公共机构、自治性行政主体或公法人。广义的公法人,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公立高等学校法律地位的共识。
当然,受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影响,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公私边界模糊[5]乃至公私莫辨[6]等观点,认为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在法人地位上正在走向趋同,公立大学正在通过“私法人化”实现治理结构、组织形式与财政模式的转型。显然,该观点夸大且误读了公私法域融合的趋势和价值,忽视了公私法域界分的功能和特定意义。事实上,公法与私法的交融是双向且有边界的复杂互动,“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以及公私法域界分的传统恪守是共存的。“公、私法融合现象的出现并不能销蚀公法与私法区分的意义,亦即公、私法的融合并不意味着公域和私域的完全混同、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界限的消除,而是反映了现代社会中公域和私域之间复杂的多样关系。”[7]德国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变革的经验表明,目标协议、行政合同等作为“治理工具”所产生的德国公立大学“私法化”特征只是表象,其实质是吸纳私法的“契约”要素,实现传统公法属性的调适,促使公法人制度“自治功能”与“绩效功能”的有机统一。在《黑森州财团法》与《黑森州高等学校法》的相关规定中,则都强调了公法财团的社会公益目的和国家监督职能。作为公法财团的法兰克福大学,仍然受公法调整。[8]“与国家行政日益私有化的趋势相反,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成熟,行会、社团、大学、设施等各种民间自治组织越来越公共化,承担越来越多的公共行政任务,越来越受公法规则的约束,并逐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行政法领域,即‘公务自治’。”[9]
公立大学作为内嵌多元且冲突的价值诉求的法律主体,它与国家、市场以及公民社会的互动是持续、复杂而深入的。如何界定公立大学的法律地位,以实现其在学术自由与外部干预、公共性与自主性之间的平衡,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议题。充分挖掘公法与私法彼此的独特价值,重视公私法域的界分和融合,则构成域外高等教育法制变革的共同经验。
二、公私法域的交融:两大法系公立大学公法人化的演进逻辑
域外两大法律体系的相互融合乃至趋同,突出表现为公私法域的界分与交融,并反映在高等教育法制的变革之中。公立大学公法人化作为高等教育法制的重要观察窗口,较好地彰显了公私法域的交融趋势。其中,大陆法系国家公立高等学校法律地位的演进,主要通过传统公法人制度的更新,吸纳与嵌入私法的“契约”要素,促进公立大学与政府之间“契约治理”关系的形塑,整合公法人制度所具有的自治与效率的双重功能。
(一)自治与效率的双重功能:大陆法系国家传统公法人制度的更新
1.德国公立高等学校法律身份的多元化与“新调控模式”的部分引入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经济平均增长率长期在1%-2%之间徘徊。在此形势下,国家财政陷入危机,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拨款连年减少。“1998年德国爆发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游行活动,实际上是对政府高等教育政策不满情绪的总爆发。”[10]在此背景下,德国于1998年修订《高等学校总纲法》。新法修订朝向三个原则:自由化,即大学须享有更多自由;多元性,自由化激励更多变化与创新;竞争力提升,因多元自由可创造大学教学研究之特色。新法修正重心包括:课程改革与成绩评价;以办学成绩决定大学财政支持;大学组织分权化。在组织法分权改革方面,修订后的《高等学校总纲法》第58条第1款规定:“大学是公法社团法人,同时也是国家设施,或以其他法律形式设立,且在法律范围内享有自治权。”[11]其中,或以其他形式设立大学的条款,赋予各州《高等学校法》关于高等学校法人形态以较大的形成自由。
此后,随着2006年德国《基本法》的修订,联邦不再享有订立高等教育一般原则的权力,《高等学校总纲法》至此失去了宪法依据。2007年5月9日联邦议会法律草案决议废除《高等学校总纲法》,宣告其于2008年10月1日失效。变革后的联邦高等教育管理权替代方案是《分发大学名额之国家契约》和《2020年规定学校协定》。至此,德国公立大学的公法人形态全部放开,公法财团法人形态成为一些州的制度选择。例如,“黑森州议会2009年12月14日颁布《黑森州高等学校法》、《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组织继续发展法修正案》及《其他相关法规修正案》等一揽子法律规范,进一步全面推进本州的大学改革。在2010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高等学校法》第九章(第81-90条)明确了法兰克福大学的公法财团大学身份,由此开始了财团大学改革的进程。”[8]公法财团的法人形态设置表明,各州开始高度重视高等学校法人制度的效率功能,“竞争、效率与效益”成为各州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而目标协议与契约管理等“新调控模式”成为德国高等教育治理体制变革的基本路径。“新调控模式”的部分引入,使得国家管制的传统格局被打破,公立大学成为功能自治的行政主体。而公法思路的恪守,则能够避免大学走向过度“市场化”的陷阱,保障公立大学的公益属性与学术治理体系的相对独立。
2.法国公立高等学校法律地位的厘定与行政合同理论的流变
传统上,法国公立大学被视为行政性公务法人,具有国家管制与学术自治的双重集权特征,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968年“五月风暴”的大规模学生运动之前。受学生运动的冲击,法国议会被迫于当年通过《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该法确定了大学的三个办学原则——“自治、参与和多科性”。至此,法国公立大学与国家的关系开始发生转变,公立大学的法律地位从传统的行政性公务法人向特殊的公务法人转变。《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第3条规定:“大学是具有科学、文化性质的公务法人。”1984年《萨瓦里法》的颁布,创立了一种新的形式——合同。大学可以根据所确定的若干年内教学与科研等方面的发展目标,通过协商与国家签订多年合同,学校要承诺完成发展目标规定的任务,国家要保证提供相应的经费与人员编制。至此,行政合同开始被引入高等教育领域,成为政府与公立大学关系调适的重要法律机制。然而,“合同的实施并不具备法律效力,通常由国家和大学定期协商制定,两者之间,应该是一种相互之间的承诺,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合同。国家对不执行目标合同的大学无法实行制裁,而是主要通过协商谈判机制来处理双方关系。”[12]
直到2007年《大学自治与责任法》的颁布,行政合同制的内涵和外延才开始真正发生改变,并逐渐开始具有法律效力。该法通过实施“总经费预算”和“多年度合同制”重构了公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促使政府从管制者转变为基于契约的宏观调控者,“以契约治理”为特征的新管理主义理念开始真正被引入法国高等教育治理之中。行政合同制度的“市场竞争”特质日益鲜明,而经典的“公共服务”传统则受到冲击。新世纪以来,法国政府的监管焦点日益“从具体细致的管理,转向对高等教育系统的战略管理;高校正逐渐被期望在政府设定的宽泛的法律框架下进行自我管理,以改变政府对高校控制监督的角色”[13]。
3.日本国立高等学校法人化改革与契约式管理的兴起
在日本国立高等学校法人化改革议题提出之前,日本已经开始将增强大学管理的“活性化”、增强大学权力、减少行政机构对大学的干预列入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1991年,文部省对《大学设置基准》进行了修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的两条与高等学校法人化改革具有密切联系。第一,设置基准大纲化。所谓大纲化,就是对设置基准的条文删繁就简,将有关大学办学的规定改细为粗。第二,大学自我评价制度的导入。”[14]显然,这两项改革举措为国立高等学校法人化改革提供了自治的基础。而有关高等学校法人化的构想,其实在1971年中央教育审议会的咨询报告《关于今后学校教育整体发展的基本政策》中就已经提出,只是构想一经提出便遭到文部省的强烈反对。直至1998年日本实施行政法人化改革,日本国立高等学校法人化改革被再次提出。借鉴英国政署制度(Executive Agency)的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于1999年通过《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的立法形式得以确立,并试图将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的大学纳入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范畴。然而,改革再次遭到文部省与国立大学的反对。
此后,关于国立高等学校法人化改革的争论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形成了一致意见,即:尊重国立大学的组织特性和自治传统,参照与“准用”《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部分条款的同时,实施有别于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的《国立高等学校法人法》。国立高等学校法人化改革之后,文部省与国立大学以及外部市场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国立大学内部也逐步改变了由教授力量主导的传统格局。根据国立大学与文部省双方交涉和沟通的条件设定契约,即“中期目标”,形成基于契约的新型治理模式。至此,国立大学与社会、市场的互动合作日益增加,“准市场机制”开始引入国立大学治理。
德国、法国与日本作为大陆法系国家,都具有国家管制与学术自治、国家主义与行会主义的双重传统。受国内经济危机和英美等国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大陆法系国家的大学开始从“国家设施型”大学向“法人型”大学转变,通过汲取私法的“契约”元素,更新传统的公法人制度。它们逐步摸索出一条整合学术自由与外部干预、公共性与自主性之间紧张关系,超越国家主义与完全“私有化”的“第三条道路”。
(二)公共职能理论与公共机构的范畴拓展:英美法系国家公法疆域的扩张
传统上,英美法系并不存在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行政活动原则上适用和私人活动相同的法律。其所谓公法和私法的区别,主要是法律规定的对象不同,不是法律的原则不同。然而,这一传统在20世纪中期以来逐渐被打破。英美法系通过更新公共职能与政府行为理论,使原本相对限缩的公法疆域得以不断拓展。基于此,英美法系普遍将公立大学的法律地位界定为广义的“公共机构”,在行使公共职能或产生公法争议时,需纳入公法的规制范畴。
1.欧盟法的影响与英国公立大学的法律地位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欧洲法律,尤其是公法,根本不为英国律师所重视——戴雪在其名著《英宪精义》中早已判定英国没有也不需要欧陆(尤其是法国)那样的公法体系。”[15]然而,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欧盟法对英国法的影响日益深入。尤其是英国1998年《人权法案》的颁布,使得英国法院开始重新审视欧盟法。英国大学的法律地位因而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变化,涉及特许状大学的判例呈现出将其视为“公共当局”看待的趋势。一些学者的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例如,克汉和汉尼(Kogan and Hanney)认为,直到20世纪90年代,“大学已经成为公共机构和公共政策框架的一部分”。格雷斯·威廉姆斯(Gareth Williams)则指出,“英国大学是拥有合法独立性和财产权的自主机构,其独立性和财政权分别由皇家特许状和议会法保证。英国大学肯定是公共政策框架的一部分,而这使它们成为公共机构。”[13]
值得关注的是,“2004年《高等教育法案》取消了视察员裁决大学与学生的纠纷以及教师聘任纠纷的权利,使其与法规大学的此类纠纷一并归由专门设立的独立裁决者办公室(Office of Independent Adjudicator,OIA)裁决。这实际上加速了将特许状大学纳入‘公共当局’或‘国家之延伸’机构的进程。”[16]此外,受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冲击,一些原本由政府承担的职权转移到私人组织或公私混合的机构手中。英国法院也顺应该趋势,拓展了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将权力的性质以及权力是否具有“公共因素”作为司法审查范围厘定的标准。“英国法院通过判例扩展了其传统关于‘公法因素’的判断标准,将其从单一的‘权力来源’标准,丰富为‘双标准’体系,即同时对‘权力来源’与‘职能的本质’进行判断。”[17]据此,特许状大学被作为“复合性”的“公共当局”看待。当其与学生之间发生关涉“公共因素”与人权保护的纠纷时,适用公法规制。
2.行政法的宪制传统与美国公立大学的法律地位
受行政法的宪制传统以及复合共和制的政治制度结构的深刻影响,“美国的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将它的不信任制度化了。人民不信任所有政府,因此政府的权力受到了限制、分割、制衡和平衡。”[18]在美国人的观念里,只有政府权力才足够危险,值得用宪法来约束;而私人行为,若非和政府紧密结合,则并不具备那种危险的尺度。正因为如此,美国公立大学作为广义的公共机构,往往受到公共制度组织的较多规制。公立高校与私立高校区分的传统,在诸如正当法律程序、平等保护、言论自由等宪法条款的适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当然,公立大学的宪法规制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博弈历程。长期以来,法院并未将公立大学与其师生的纠纷纳入宪法的规制,而是形成了诸如“特权理论”、“优先权理论”、“代替父母理论”等理论,将公立大学的师生与普通公民区分开来。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法院才开始通过一系列判例确立了宪法理论。例如,美国公立大学教师具有“公共雇员”的法律地位,受宪法正当程序条款的保护。
美国不同公立大学之间法律地位的差异,决定了其所受公共规制的范围、类型与强度不同。具有州宪法自治高等学校法律地位的公立大学,往往直接受宪法规制而享有更多的自治权,如密歇根大学。对这类公立大学而言,州宪法往往是其需要服从的最主要的公共规制。除非州宪法有明确规定,其他包括“州行政法”(state administrative law)在内的法律法规通常不能对其形成规制效力,它甚至超越州立法机构的控制。然而,具有州宪法自治高等学校法律地位的公立大学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公立大学是依据州普通法规成立的,必须接受普通法规层面的规制。而那些属于“州的机构”的公立大学,则必须服从“州行政程序法”(stat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以及“州行政法”中的相关规定,如关于公开会议和公开记录的法律规定。[19]
三、介乎公私之间:全球化时代公立大学治理的“混合法规制”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世界各国公立高等学校法律地位的变革呈现出“同质异形”的现代化[20]进程。世界各国都在寻求介乎公私之间的公立高等学校法人制度,以整合公立大学在公共性与自主性、学术自由与社会干预、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潜在冲突。公私法域的界分与交融,作为世界各国公立高等学校法律地位演进与“互动式”法权治理格局生成的制度逻辑,表现为公立大学哲学内涵与法律价值的持续博弈。“通过立法将大学政治论与认识论哲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是大学哲学内涵法律化转型的重要表现。不同法域下高等教育的法律条款,清晰地反映了大学组织在各国法律框架下的属性和变迁过程。”[21]有别于传统的将公法与私法截然对立的法律地位变革思路,世界各国都正在通过公法秩序与私法秩序的“相互援助”和交融,充分释放公法与私法各自的价值,实现公立大学治理的“混合法规制”。
1.超越公私二元对立之争:公立高等学校法律地位的公私交融
正如前文所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公立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浪潮并不意味着公立大学都正在走向“私法人化”。它更多昭示着公立大学资源配置模式中竞争机制的引入和绩效责任的强化,而在法律责任、法律关系调整以及自主权的监管体系等方面,它依旧部分受公法规制。公立高校与私立高校界分的经典命题在法律规制层面获得重新诠释。基于公私法域的界分,世界各国基本形成了关于公立大学作为“广义公法人”的共识。当然,这种共识也正在受到一些挑战。2006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司化法案》对新加坡国立高等学校法律地位的变革就未采用所谓“广义公法人”的思路。该法案指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法律地位将由政府全资投入的法人机构转变为有担保的企业型责任有限公司。新的法人制度设计,将新加坡国立大学界定为“非营利性公司”(non-for-profit company)[22],超越了传统公法学与民商法学思路之间“非此即彼”的公私之争,实现了公立大学、政府与市场力量的动态平衡。应该认识到,单纯的公法人抑或私法人制度设计,不仅存在对高等学校法人制度的“误读”可能,也难以有效整合大学的多元价值诉求。[23]
受大陆法系影响,我国的法人制度也强调公法与私法的分类,但更具有延展性,也更具有功能导向。这为中国公立大学借鉴公私法域界分与交融的域外法律体系变革理念、实现法人制度变革的“本质回归”提供了广阔的制度空间。公立大学的组织特性、功能演进以及办学自主权的多头法源,则构成公立高等学校法人制度变革的逻辑起点。目前,我国公立大学作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法人的法律地位,并未破解其作为“双界性法人”所衍生的“公法化不足”与“私法化过度”的错位难题。从长远而言,可结合我国高等学校法人制度变革的现实困局,制定《公立高等学校法人法》,单独设立公立高校法人这一有别于传统公法人与私法人的“法人类型”。超越公私法的二元对立,形成介乎公私之间的,应公即公、应私即私的“特殊法人”制度设计。[24]
2.契约治理的兴起:公立大学与政府法律关系的公私交融
契约治理的引入,旨在整合公法的公益属性和契约的合意属性,实现公立大学公共性与自主性双重价值诉求的平衡。以德国为例,随着《高等学校总纲法》的废除与失效,德国联邦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合作关系开始通过《2020年大学协定》实现,各州必须完成协议的要求,以实现国家许可范围内大学自我管理权限的扩大。通过目标协议,联邦、州、大学、学院以及系所之间形成了以目标为联结的纽带关系,国家监督与大学自治之间逐渐形成基于“目标合同”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公立大学与政府关系重构的最新动向,正在汲取国际领域的变革经验,将合同式的目标管理引入高等教育治理。在2014年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颇具创新性地提出了关于公立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协议赋权模式。基于协议的赋权模式是一种体现协商、合意精神的特殊的行政契约。应进一步借鉴域外行政合同制度与契约治理的有益经验,促进公立大学与政府关系的法治化以及公权力行使的契约化。
3.迈向公共雇员制:公立大学教师法律地位的公私交融
考虑到公立大学教师职业所特有的公益性乃至公共职能属性及其学术权利保障的需求,世界各国关于公立大学教师法律地位的制度安排都没有采取民商法的思路,即采取契合劳资关系的雇佣制,而是通过公共雇员制度的设计尽可能缓解公立大学教师的职业属性在公共性和自主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学术自由与绩效责任等多重价值的整合。例如,美国公立大学作为广义的“公共机构”,其教师具有公共雇员的法律地位。而在英国,公立大学与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呈现出公、私法因素的混合,被视为一种“契约与身份的混合”。既适用普通法原则,又受特定法规的拘束。公法的适用,主要体现在雇佣保护与反歧视立法领域。[22]目前,我国公立高校教师的法律地位也逐渐呈现出公私融合的特征,倾向于将其定位为特别的公共雇员,这在2014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中有较为鲜明的体现。聘用新制所具有的多重法律属性,“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公共雇员,在公立大学就应当是公立大学的公共教育雇员。这种公共雇员制,既是对传统事业单位成员制的改革,也有别于基于劳资关系的雇佣制。”[25]
鉴于公立大学教师职业所具有的公益属性与专业属性并存的双重属性,应将其法律地位定位为特别的公共雇员,其与公立高校签订的聘任合同应界定为特殊的行政合同。公立大学与教师之间的契约关系,“绝非民事关系中平等主体之间的契约,而是在管理关系基础上的契约。它是行政契约的一种扩张和延伸方式。此类契约受法律、法规的限制、制约更多。”[26]当教师与公立高校发生纠纷时,应根据具体纠纷的性质和类型,选择适用公法或私法规范。若涉及公立高校的“高权行为”或公共职能行使的“公法争议”,如职称评定纠纷,应适用公法规范。除此之外的其他类型纠纷,则应纳入私法规范的范畴。随着公立大学从“授权性行政主体”向“自治性行政主体”的转变,公共职能的履行将被限缩在较小的范围。公立高校与教师之间的大量纠纷,将更多地被视为民事争议。
4.呼唤公法契约关系:公立大学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公私交融
当前,世界各国公立大学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演进,都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或“特权理论”。取而代之的是“契约理论”、“宪法理论”等符合法治思维、彰显法治理性、保障学生权益的理论。[27]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公立大学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也呈现出复杂的公私交融趋势。各国学界和法院正逐步形成将公立大学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界定为特殊的“契约关系”的共识。例如,日本“在过去的学说、判例上有私法上的附合契约、行政契约、学说身份取得契约、私法上的无名契约以及教育法特殊契约等不同见解”。其中,兼子仁教授提倡的“教育法上的特殊契约”是最具影响力的学说。我国台湾学者李仁淼则认为,应将公立学校与学生的在学契约关系界定为行政契约关系。[28]
在英美法系国家,契约理论广泛地适用于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在英国,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已经被数个领域的法律所定义,这些领域按照解决学生与高校关系的重要影响程度分别是《合同法》、《房屋租赁法》、《歧视法》、《侵权法》、《人权法》、与数据保护和信息自由相关的法律,以及《知识产权法》”[3]。高校与学生的契约关系被视为公法与私法因素的混合物。“学生既享有源自合同的私权利,也有用以确保大学在法规范围内恰当行事的公法上的权利。”[29]在“克拉克诉林肯郡与亨伯赛德郡大学”(Clark v University of Lincolnshire&Humberside)一案中,有人认为,大学是一个公共的主体,那么就意味着两者之间的纠纷应当适用公法,司法审查的范围也应该限制在三个月的期限内。法院否定了这种观点并指出,在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中,公法和私法是并存的,而不是对立与相互排斥的,学生可以提出有关合同的要求。[30]在美国,公立院校与私立院校均和学生有明示的合同关系。最常见的例子可能是宿舍合同、餐饮合同、贷款协议。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倾向于将学生手册或者学校目录作为合同,无论是明示的还是默示的。而合同理论的适用也从私立院校拓展到公立大学与社区学院。有法院甚至创新性地提出“准合同”理论来审查学校与学生的关系,并且采用“善意标准”作为司法审查的原则。[31]中国公立大学与学生法律关系的界定,应积极回应域外两大法律体系的最新进展,顺应公私法域界分与交融的国际趋势,将其定位为拟制的公法契约关系。
四、结论与讨论
法律地位抑或法人制度作为一种法技术手段,内嵌着多元且冲突的治理诉求,也是大学哲学内涵不断法律化的载体与表现。公私法域的界分与交融,作为世界各国公立高等学校法律地位演进的共同逻辑,重构了国家、大学与市场之间的法理关系,形塑了新的审视高等教育的法理框架,蕴藏着重要的治理价值[32]。在这一新的法理框架中,政府的监管与财政责任、大学的公益属性与社会服务价值、大学学术治理体系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法治框架下大学及其师生权益的有效保障都得以实现。公立大学治理在公共性与自主性、合法性与有效性、自治功能与绩效功能之间获得了适切的动态平衡。公私截然分立的自由主义与国家直接干预主义等传统法理框架,都无法直接“套用”到公立大学治理的法律实践之中。
考虑到我国法律体系尤其是法人制度的特殊性,简单地将公立大学定位为“公法人”显然不具有可行性。可考虑将公立大学界定为介乎公私之间、兼具公共职能与学术自治双重属性的“特殊法人”与“混合型机构”。基于此,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法律地位变革的治理意涵在于,基于大学各类任务的属性及其对相对人的权益影响程度,建构外部规制与内部规制、国家法律秩序与大学自治秩序、硬法与软法以及公法与私法等各类“法秩序”之间理性界分与良性互动的任务导向型“混合法”规制结构。促进国家公权力的法律规制与大学内部自我规制之间的合作与制衡,健全和细化各类规制的内部构造,形塑契合公立大学自主权规制与保障要求的适切的法律规制结构。矫正“公法化不足”与“私法化过度”、“软法硬化”与“硬法软化”等公立大学自主权法律规制的结构性失衡,破解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的诸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难题。
参考文献
[1]孙国华,杨思斌.公私法的划分与法的内在结构[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4):100-109.
[2]施密特·阿斯曼.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体系建构[M].林明锵,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70.
[3]FARRINGTON D,PALFREYMAN D.The law of higher education [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4]李年清.私人行政司法审查受案标准的美国经验——兼论我国私人行政责任机制的建构[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3):157-169.
[5]陈涛.大学公私界限日益模糊:全球现象与动态特征[J].复旦教育论坛,2015(4):9-15.
[6]何雪莲.公私莫辨:转型国家高等教育市场化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12(1):18-22.
[7]马晓燕.论公、私法区分与融合视角下大学自主权的法律性质定位[J].中国教育法制评论,2008(6):149-166.
[8]胡劲松.德国公立高校法律身份变化与公法财团法人改革——基于法律文本的分析[J].比较教育研究,2013(5):1-8.
[9]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三卷)[M].高家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
[10]周丽华.德国大学与国家的关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69.
[11]董保城,朱敏贤.国家与公立大学之监督关系及其救济程序[G]//湛中乐.大学自治、自律与他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4.
[12]王宝玺.法国大学自治演进分析[J].高教研究与实践,2010(3):8-12.
[13]佩德罗·泰克希拉,等.理想还是现实——高等教育中的市场[M].胡咏梅,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4]田爱丽.现代高等学校法人制度研究——日本国立高等学校法人化改革的实践与启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38-39.
[15]王敬波,等.欧盟行政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87.
[16]申素平.英国高等学校法律地位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0(2):48-50.
[17]杨欣.美、英司法审查受案标准的演化及其启示——以私人承担公共职能为考察对象[J].行政法学研究,2008(1):128-133.
[18]P.S.阿蒂亚,R.S.萨默斯.英美法中的形式与实质——法律推理、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35.
[19]王绽蕊.美国高校董事会制度:结构、功能与效率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31-138.
[20]周光礼,黄容霞,郝瑜.大学组织变革研究及其新进展[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2(4):67-74.
[21]周详.我国公立大学的法律属性与依法治教的推进[J].中国高教研究,2015(11):13-18.
[22]RUSSO C J.Handbook of Comparative Higher Education Law[M]. Maryland:Rowman and Littlefield Education,2013:277-284,146.
[23]罗爽.论高等学校法人制度的根本性质及其意义[J].高等教育研究,2014(3):15-24.
[24]劳凯声.回眸与前瞻:我国教育体制改革30年概观[J].教育学报,2015(5):3-12.
[25]于安.公立大学教师聘用制度的立法新制研究——论《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在公立大学的适用[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 (6):60-64.
[26]胡发明.我国大学性质的行政法分析[J].时代法学,2004(3):57.
[27]姚荣.中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变迁的多重制度逻辑[J].复旦教育论坛,2015(5):25-30.
[28]台湾行政法学会.行政契约之法理各国行政法学发展方向[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9:53-78.
[29]BARRISTER C L,TEMPLE M.Judical Remedies in Public Law[J]. London:Sweet&Maxwell,2000:49-51.
[30]VARNHAM S.Copping Out or Copying?Do Cheats Prosper?An Exploration of the Legal Issues Relating to Students'Challenging Academic Decisions[J].Australia&New Zealand Journal of Law& Education,2002(1):26-28.
[31]KAPLIN W A,BARBARA A L.The Law of Higher Education[M]. San Francisco:Jossey-Bass,2013:839-880.
[32]姚荣.迈向法权治理:德国公立高校法律地位的演进逻辑与启示[J].高等教育研究,2016(4):93-102.
·专题·
收稿日期:2016-03-2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从他组织到自组织:研究型大学协同创新网络演化机理及其政策激励研究”(7150323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71373274)。
作者简介:姚荣,1990年生,男,江苏泰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法律与政策研究。
Boundary and Merge of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Evolution Logic and Governance Implications of Legal Status of Public Universit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YAO Rong
(School of Education,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The evolution of the legal status of public universit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displays the modern features with homogeneous nature and heterogeneous form.On the one hand,with a clear boundary set between public sector and private sector and the independent value of public law reaffirmed,the role of public law in safeguarding public welfare at public universities is recognized.Public Corporation in the broad sense(including public institutions)is the consensus on the legal status of public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world.On the other hand,the differences in legal traditions,legislative techniques and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between Continental Legal System and Anglo-Saxon Legal System result in the relative uniqueness of the legal status of public universities in different nations.The merge between public law and private law is reflected by the update of public corporation system and the adjustment of property of public legal system in Continental Legal System and by the expansion of the scope of public law and the enhancing trend of public law regulation in Anglo-Saxon Legal System.The“mixed legal regulation”of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will be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public university governance around the world.The evolution of the legal status of public universities will gradually transform the legal relationshipbetween public university and government and the legal relationship within public university,and ease the inherent tension between legitimacy and effectiveness as well as between publicity and autonomy in public university governance.
Key words:Era of Globalization;Boundary and Merge of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Public University;Legal Status;Modern Features with Homogeneous Nature and Heterogeneous 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