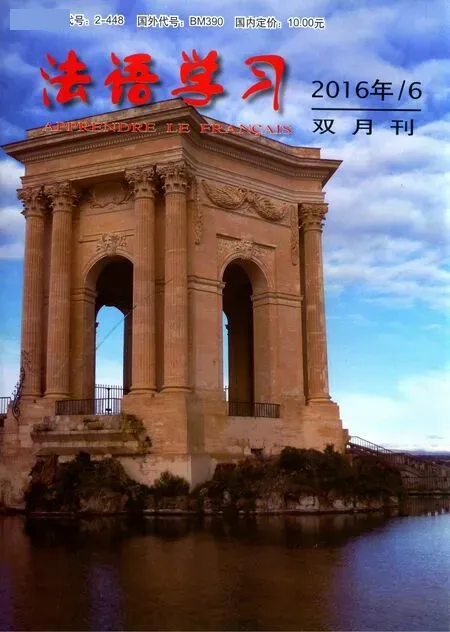当代法国小说创作与“自我虚构”
● 法国南特大学 菲利普·福雷斯特 (正文)● 华东师范大学 蒋向艳 (引言)● 华东师范大学 张晨蕊 (正文翻译)
当代法国小说创作与“自我虚构”
● 法国南特大学 菲利普·福雷斯特 (正文)● 华东师范大学 蒋向艳 (引言)● 华东师范大学 张晨蕊 (正文翻译)
引言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法国文坛继续引领着世界文坛,呈现出一派精彩纷呈的热闹景象:“新小说”派作家罗布-格里耶、米歇尔·布托尔,“新寓言派”小说家米歇尔·图尼埃、勒克莱齐奥、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还有标新立异的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和弗朗索瓦丝·萨冈,以及移民作家米兰·昆德拉和华裔作家程抱一等。在这众声喧哗中,一个一致的声音是:新生代的作家们决心与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决裂,致力于探索新的文学样式。他们传达了“先锋派”立意文学革新的声音。
这一运动即使不能说是轰轰烈烈,也可以说是声势浩大的:那些当得起杰出作家之名的罗布·格里耶、玛格丽特·杜拉斯、克劳德·西蒙、菲利普·索莱尔斯等人都在这一行列中。持续二三十年后,1977年,法国作家塞尔日·杜布罗夫斯基(Serge Doubrovsky)在其处女作《儿子》中提出了“自我虚构”(autofiction)这一概念,直到20世纪末,这一术语及其所指称的小说创作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潮流,取代了原先存在的“自传体小说”。1997年开始小说创作的法国当代作家菲利普·福雷斯特(Philippe Forest)以其处女作《永恒的孩子》(L'Enfantéternel)获得法国“费米娜”文学奖(获该奖的“处女作小说”奖)。他后来出版的小说也连续在法国获奖:《然而》(Sarinagara)2004年获法国“十二月”文学奖;《整夜》(Toutelanuit)2007年获“格林扎内卡武尔”(Grinzane Cavour)文学奖;《云的世纪》(LeSiècledesNuages)2011年获“法国飞行俱乐部”文学大奖,同年也获“布列塔尼和卢瓦尔河地区科学院”文学大奖。随着创作的丰富和成就及影响的扩大,福雷斯特逐渐被公认为“自我虚构”小说这股新浪潮运动中当仁不让的代表作家。
那么,继“先锋派”之后,“自我虚构”小说要表达什么内容?它是否如一些批评者所宣称的那样,是向传统的“投降”,向新自然主义写作的回归?它对哪种世界文学传统有所继承?它在小说创作上又是否具有新的立意,对法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有着新的担当?
下文是福雷斯特这位法国“自我虚构”代表作家对“自我虚构”的论述。
一
我不知道,对法国之外的批评家、学者、读者、作家来说,“自我虚构”这个词是否熟悉。“自我虚构”这个词最早于1977年由一个法国小说家在其处女作《儿子》中提出,意指虚构和自传相结合的文学作品,恰好他还是一个在美国的学者,在纽约大学教了40多年法国文学。
但是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并且是在经常不提及术语的发明者杜布罗夫斯基的情况下,这个术语才为文学批评界广泛使用,小说家自己有时候也以此来指称以前的“自传体小说”,并成为法国当代文学的一个主要特征。
“自我虚构”以及它的文学价值引发了各式各样的论断,但是人们一致认为,这个术语指称出一个理解和评价当代法国文学就不得不考虑的现象。与此同时,这个术语开始向其他欧洲国家散播——意大利、西班牙、德国,以及一些欧洲以外的国家,巴西、日本。三年前在纽约组织了一个国际会议,集结了一些美国和法国的小说家们(包括丹尼尔·门德尔森(Daniel Mendelsohn)、瑞克·穆迪(Rick Moody)、希瑞·阿斯维特(Siri Hustvedt)、凯瑟琳·米雷(Catherine Millet)、卡米耶·洛朗斯(Camille Laurens),还有我),探讨对大西洋两岸的当代作家来说,法国的“自我虚构”是否能够意味着什么。
就我而言,在法语环境中,尽管自1997年我的第一部小说《永恒的孩子》出版以来,我的作品就被认为是继承了“新浪潮运动”,但是我一直在批评“自我虚构”以及它通常表示的意义。
我已经厌倦了总是被视为我本不属于的一场文学运动中的一员,事实上,这场文学运动从未存在,我试着要提出一个另外的术语,不是“自我虚构”,而是“Roman du Je”,听起来像是英国和美国的“I-novel”(自我小说),其实是源自于日本的“私小说”,之后我会解释原因。我必须承认我很不成功。所以我决定仍使用“自我虚构”这个词,同时又要强调出它对我的特殊意义,今天我会试着再次解释。
当然,“自我虚构”在这个术语被提出之前,就已经存在很久了。开玩笑地说,对“自我虚构”的概念存有疑问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奈特认为,既然意大利诗人但丁在《新生》和《神曲》里向读者诉说了他与年轻的贝阿特丽切的际遇,以及他在地狱、炼狱、天堂的经历,而且这些经历都被呈现为是真实的,那么但丁就该被视为一位“自我虚构”作家。
在我看来,“自我虚构”只是对旧内容的一种新说法,每当虚构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明确地或含糊地、用这种方式或是那种方式保持它的自传成分时,就能够使用“自我虚构”这个词。这就是为什么“自我虚构”随处可见,或者至少可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些被视为“自我虚构”代表作家的作品之外也能发现“自我虚构”的原因。
我会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詹姆士·乔伊斯(James Joyce),第二个是大江健三郎。4年前,我受邀为一个新的系列丛书《一书 / 一生》(LeLivre/LaVie)供稿。这个创意来自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想象自己花整整一年的时间一遍一遍地重复阅读同一本书,每一天都写和那本书有关的东西,于是那本书和他每天的生活相交相融,并且形成了一部新的文学作品,展示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联,并且令真实与虚构成为了同一现实的两个方面。我选择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Ulysses),因为我知道这部现代文学的杰作已经被很多人研究过,所以我只有站在一个主观角度才能提出一些如果不算新的,那也算是个人的见解。我的目的是对《尤利西斯》进行自传式的阅读,从而令小说的自传成分显现出来。对我来说,这就意味着突出乔伊斯小说的其中一个方面,因为,这个方面恰好也是我自己小说的核心:我指的是乔伊斯创作的哀悼、哀恸的经历,尤其和是孩子逝去的哀恸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乔伊斯认为,莎士比亚创作《哈姆雷特》也是源自于这样的经历,正如书中斯蒂芬·德迪勒斯在都柏林的国家图书馆所作的著名演讲中解释的那样,而布鲁姆也有着相同的经历,这是乔伊斯所塑造的这一人物的中心线索。
当然,乔伊斯的作品从《英雄史蒂芬》、《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到《尤利西斯》、《芬尼根守灵夜》都有明显的自传成分。然而不止如此。尽管乔伊斯是个小说家,但是他坚持的是自传总是优于虚构。在法兰克·巴金(Franck Budgen)的书《詹姆士·乔伊斯以及〈尤利西斯〉的诞生》中就能找到依据。这个场景在1918或1919年发生在苏黎世。乔伊斯正在进行小说创作,巴金问他最喜欢的作家是谁,以及他是否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乔伊斯回答说:“不,卢梭承认自己真的偷过银勺子,要比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中的一个人物承认一桩从未真正发生过的谋杀案要有趣得多。”
乔伊斯支持“自我虚构”吗?当然这个问题是很荒诞的。但是在我看来,由于我个人对“自我虚构”的定义非常宽泛,也相当模糊,我不会反对将《尤利西斯》的作家算作是这种文学类型的其中一个先驱者,或者说预言者,在法国,这种文学类型在杜布罗夫斯基之后,我们称呼它为“自我虚构”,但是它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别处,并且早已存在。
我的第二个例子是大江健三郎。1999年我第一次见到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时,将他的小说冠以“自我虚构”之名——这个概念对他来说是全新的,他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这很容易理解。自20世纪初,在欧洲文学,尤其是卢梭的《忏悔录》的极大声誉的影响下,在日本有一类文学称为“私小说”:shsetsu的意思是小说,watakushi是日语中一个表示第一人称的词。因此,Watakushishsetsu翻译成英语就是“I-novel”(自我小说),翻译成法语的话我建议翻成“Roman du Je”。就像“自我虚构”一样,“私小说”用虚构的方式表现自传中的事件。从最早期的作品到最近的作品,大江健三郎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就是在改变、颠覆、更新这个概念。正如莫里哀的著名戏剧《贵人迷》中,茹尔丹先生突然意识到他从出生时起说的就是枯燥的散文而不是韵文,大江才意识到自己写了半个世纪“自我虚构”,却从来不知道它的名称。
在1977年杜布罗夫斯基提出这个术语之前,没有人知道“自我虚构”的存在。现在我们知道了,那么会产生什么影响吗?当然会。这让我们更了解这样一个事实:现在和过去的每一个真正的作家,比如说乔伊斯和大江健三郎,他们都已经深知:真正的文学总是基于个人的经历,但是这种个人经历需要一种诗意的实验来呈现,它才能真正存在。
二
我想要说明一下我刚才用的词(实验)。Expérience在法语中是个非常简单常见的词。遗憾的是,这个词很难翻译,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意义。其中一种意义就对应于英语的experience。但是,它也可以指experiment表示的意义。在英语中,experience和experiment有区别,同样德语中也有这样两个词:Erlebnis和Versuch。但是法语中没有,单单只有一个词expérience,具有两种不同的意义。
当然,通过这样观察就下结论未免有点太轻率了。但是,这教给我们一样东西:“经历”并不通过自身存在,也不存在于自身中,只有通过“实验”才能抓到。而这恰恰就是我们从“自我虚构”中学到的: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我们最真实的部分,我们的“经历”,只有当我们用词句呈现出这样一个实验,才能存在。或者,换一种说法,只有当我们将生活转化成一部小说,我们的生活才算存在。这件事很容易完成,因为从一开始,我们的生活就是一部小说,它以小说的形式在我们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这样我们才感知到了自己的生活。
三
“自我虚构”在法国有很多贬低者。如果福楼拜要写一版新的《庸见词典》(Dictionnairedesidéesreçues),他一定会表示其中一条必须是对“自我虚构”的“抨击”,因为这种形式的写作经常被说成是法国文学衰落的主要缘由,是法国小说在美国、在世界上被读者们搁置一边的主要原因。对反对者们来说,“自我虚构”是我们的文学在“先锋派”时代过后衰落的一个征兆,是向新自然主义写作的回归,产生出自我陶醉的,无法解决哲学上、政治上,甚至是文学上的重大问题的小说作品。奇怪的是,也是同一批批评家在“新小说”和“原样派”时代不遗余力地批判先锋派作家们,时代翻页后,他们以再一次毁掉了法国小说的托辞来指责“自我虚构”。阿兰·罗布-格里耶、玛格丽特·杜拉斯、克劳德·西蒙、菲利普·索莱尔斯发起了对法国文学的第一次冲击,那么我们(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我们现在发出的是致命一击。
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通常我并不愿意说支持或者去赞扬“自我虚构”,因为在过去的大约30年里,很明显“自我虚构”创作出了一些非常低劣的作品,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反映现在出现在德波(Guy Debord)的《景观社会》(LaSociétéduspectacle)一书中的人与人之间疏离程度的故事。但是,我坚信“自我虚构”,或者说至少是当代归入这一领域的作品,具有一个全然不同的目标,因为,“自我虚构”并非是一个新自然主义概念的复兴,而是继承了真正的现代性,并且坚持成为实验文学的一种新形式。
杜布罗夫斯基的作品就是一个例证。但是如果我们的视野更开阔一点,那些19世纪90年代开始在“自我虚构”名义下创作和出版作品的小说家确实受到了一帮先锋派作家的影响,先锋派作家在一二十年以前指出了道路:他们中最早的当然是罗兰·巴特(《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还有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痛苦》)、阿兰·罗布-格里耶(《重现的镜子》)、菲利普·索莱尔斯(《天堂》《女人们》),还有许多其他的作家,包括一些前代作家,比如米歇尔·莱里斯(《游戏规则》)、马尔罗(《反回忆录》)和阿拉贡(《布兰琪或者遗忘》《死刑》)等。
如果有人要编写“自我虚构”的谱系,那么就必须包括所有这些名字,还要包括其他很多来自美国、欧洲、中国、日本文学界的名字,他们对这个一直被误认为是源自法国本土的文学现象有着重要影响。在这样一个谱系的基础上,“自我虚构”的实验性成分就会清晰地显现出来。虽然“自我虚构”提出的是真实与虚构之间关系的老问题,但是用了一系列的新方式,将写作本身的问题放到了小说的中心位置,提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我”的概念,考虑到了哲学、精神分析学和文学本身,因为浪漫主义时代就已经教给我们主体的真实而对立的本质。
四
这种采用了多种形式的实验,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传统的自传确有其事的话,它基于并导向的是一种与传统自传的基点非常不同的事物的视域。
这个观点可能会令人很惊讶甚至荒谬,那就是“自我虚构”并不像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它并不关心“真实生活”。它聚焦的并不只是构成我们生活表层故事的那些事实,也不只是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那些或小或大、或悲或喜的事件,而是更深层的、更难捕捉、更难表达的东西,唯一合适的词语就是experience,它始终是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的唯一目的。就像乔治·巴塔耶为其主要著作之一《内心体验》所取的标题一样,这里我指的也是“内心体验”,巴塔耶称为“不可能”的东西中夹杂着些许狂喜,在他和一些现代思想家之后,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真实”。
关键在于,在这种情况下,主体面对的是真实,他因经历这种心醉神迷而松懈了对自我的任何感知。因此自我的概念也被剥夺了意义。自我消失了。“自我虚构”进行的这个实验的结果就是一种最终有着诗性本质的经历。“自我虚构”中的我不再是任何人,却在为文学中的所有人发声。
“自我虚构”和自传一样,它的基础是人生活中发生的事实和事件,但是它根据实验的方案将这些事件结合起来,从而导向一个令自我消失而让不可能的真实存在的经历。这就像艾略特(T. S. Eliot)诗中的著名表述,一个“人格解体的过程”。然而别忘了,卢梭已经知道了一切:难道他不是在《忏悔录》之后写了《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吗?
五
我并不准备对“自我虚构”提出一个新定义。我先前的评论旨在得出一个更有限更温和的结果。我对“自我虚构”所说的,正是我所见的,也就是,正是如我在我的书中所经历和实验的。从《永恒的孩子》到《云的世纪》,还有目前唯一有英文译本的小说《然而》,我的所有小说都是基于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事件,就是我孩子的死亡。这样的事情让人难以面对:它令人无法理解,这就是为什么它需要被一遍一遍地用不同的方式诉说,并且毫无希望发现一种最好的、最终的方式,因为这样一种方式根本不存在。因此,这些小说中的实验性的内容,每一本都在寻求另一个角度,每一本都在尝试接近不可能的真实,并且深知失败不可避免,每一本小说都融合了作者亲身经历的故事以及其他故事,而其他的故事又有关于居于所有文学作品核心的那些共同的欲望和悲伤(例如我的第一本小说《永恒的孩子》,詹姆斯·巴里的《彼得潘》和雨果的《静观集》,还有马拉美的《阿纳托尔之墓》;《然而》,小林一茶的诗,夏目漱石的小说,还有日本文学的其他作品等等),尝试着拉近那些与我相似的故事,来进行延伸,正如我在《然而》和《云的世纪》中那样,也包括了历史本来事件,给予这个故事一个普遍的意义,因而就是非个人的意义。
我的每一本小说都指向一种同样的虚无,让思想停留在虚无的边缘,在这种虚无中,那些一早提出的、伴随文本而生的问题都浑然无解。令作者去直面一个无解的谜题,一个现实的谜题,正如我最新的小说《薛定谔之猫》(LeChatdeSchrödinger)中呈现的,这些借自于矛盾教义和物理空想的谜题虽然无法破解,但是却必须通过小说家创作的故事讲述出来。谁在讲述?我自己吗?作者吗?我并不觉得。就像我之前说的,在真实经历中,人出于对虚无感觉的神往而抛弃了自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反对“自我虚构”是在追寻自我的观点。或者说,如果“自我虚构”是在追寻自我,那么它真正的目的就是去迷路,去迷失。就像我在《然而》中引用过的夏目漱石的话,作家的真正箴言是:“追随天空,抛弃自我”。在空旷的天空之下,在云层的景致之中,我的小说《云的世纪》就这样结尾了。在薛定谔为他的猫所创造的盒子里,生与死同在,而自我最终也消失了。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不存在其他终极的措辞。
⦿注释⦿
本文正文是法国南特大学文学教授、作家菲利普·福雷斯特于2016年3月25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所作讲座的英文发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