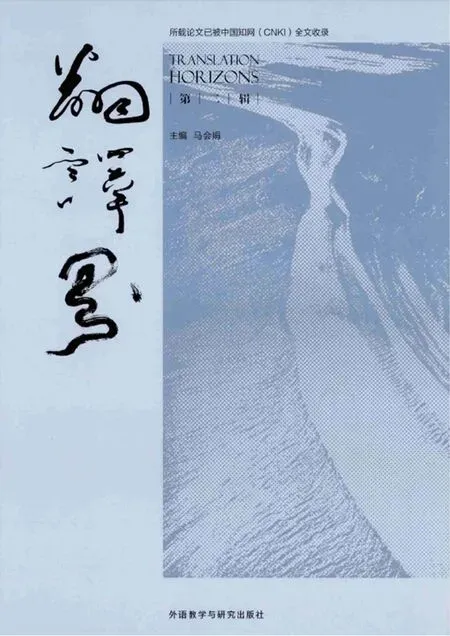翻译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安妮·布里塞特教授访谈
张翠玲
北京科技大学
翻译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安妮·布里塞特教授访谈
张翠玲
北京科技大学
安妮·布里塞特是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翻译学院教授,研究生和博士后学院成员,国际翻译与跨文化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简称IATIS)的创始人之一和前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语交流的顾问。曾就职于加拿大联邦翻译总署,从事口译和笔译工作。研究兴趣包括翻译理论、话语理论、社会学和翻译社会学。目前正在从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翻译流向和翻译实践研究。2014年春天,该教授应邀到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学,为期三个月。在此期间,笔者就近几年的翻译热点问题对她进行了专访。之后,该教授又通过邮件对采访问题进行了补充和完善。采访内容涉及加拿大翻译学的发展、加拿大主要的翻译学学者、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翻译社会学以及翻译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等。
采访;翻译研究;翻译社会学;翻译转向
张翠玲(以下简称张):布里塞特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给我这个机会。您能简要介绍一下加拿大的翻译研究学科状况及发展历程吗?
安妮·布里塞特(Annie Brisset,以下简称布里塞特):加拿大的翻译和口译活动可以追溯到16世纪,那时欧洲人移民到加拿大,和当地居民开始有了接触。法语和英语随后成为加拿大国会和法庭的语言。然而,直到1968年,官方语言法案的实施,双语和翻译才得以制度化。两套法律体系——《英国普通法》和《法国民法典》——是加拿大历史的另一个独特遗产,对法律翻译和学术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翻译教学在30年代才开始进行,当时只有几门课程。60年代后期联邦立法使翻译需求急剧增加,翻译职业教育应运而生。早期的译员培训项目里设置了术语和计算机辅助翻译课程。受到双语政策的惠及,加拿大的计算机辅助翻译、双语语料库、术语学的研究和发展一直都很活跃。最显著的成就,一个是蒙特利尔大学70年代中期开发的TAUM-Meteo计算机翻译系统,实现了天气预报的全自动翻译,另一个是联邦翻译局的术语库Termium(机器辅助翻译系统)。最近,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又开发了Portage机器翻译系统,有望成为译者主要的工作平台。1987年,加拿大翻译研究院(CATS)成立,在此之前,翻译研究一直都是语言学或比较文学的分支。不过,加拿大的翻译研究学者一直和欧美的语言学、符号学和文艺理论学者保持紧密联系,同时又和文化学(后殖民主义、文化人类学、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学者保持联系。而且,加拿大人文社科协会的年会也是跨学科交流的场所。所有这些,加上加拿大的双语现实,让加拿大的翻译研究涵盖了从语言、技术、教学到历史、法律和文学的各类问题。这种多样性体现在Meta(1955年创刊)和TTR(Journal of the 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Translation Studies)两个著名的期刊上,同时还体现在渥太华大学出版社的“翻译视角”系列图书和加拿大学者对国际会议和出版的贡献上。
张:您如何看待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
布里塞特:翻译理论反映的是过去和现在的实践、潜在的原则、历史背景和社会影响。为了更好地理解翻译作为过程和产品、提高译者培训,或让翻译更加有效、可靠、符合伦理,它广泛地借用其他学科。从职业的角度看,翻译理论的目的并不是为实践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而是设计工具和方法,促进决策过程,给予译者力量。换句话说,理论构建于实践之上,反过来又反馈实践。它应该融入翻译教学,而不是作为单独的课程。因此,应该更多地关注翻译教师的培训。当没有给学生提供话语分析背景时,他们会按照句子的意思来翻译,完全忽略文本的话语构造和译文的背景与目的。这些话语背景和译文的背景知识都很关键,但很少纳入培训的练习中。翻译批评也是同样的道理。当目的语文本和它们的源语文本相比时,往往不考虑目的语的话语环境。职业技能是建立在理论知识基础之上的,正如法律翻译需要具备法律知识培训一样,文学翻译课程应该包含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课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专业人员和学生都抵触理论,反而是进一步降低了译者的社会地位。
张: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些加拿大翻译研究领域成就比较突出的学者吗?
布里塞特:从众多的学者当中挑选,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加拿大的翻译研究学者中,有一些在中国已经很有知名度,其他值得介绍的有丹尼尔·西梅奥尼(Daniel Simeoni),他的博士论文“西方译者的‘惯习’:从圣哲罗姆至今”(“History of the Western Translator’s ‘habitus’: From St.Jerome to This Day”),完成于2000年,写得非常精彩,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出版。西梅奥尼是多伦多约克大学翻译研究的教授,他是第一个将布迪厄的理论运用到翻译研究中的人,他同时也和图里(Gideon Toury)以及描写翻译学的学者密切合作。他的一些主要文章都发表在Target上。
另外一位重要的学者是芭芭拉·福卡特(Barbara Folkart)。她是科学家出身,后来转向文学,主攻中世纪文学,随后成为渥太华大学翻译学院教授。她著述丰富,其中,法语专著《话语冲突:翻译和间接引语》(Le conf l it des énonciations.Traduction et discours rapporté.1991.)是翻译主体性研究方面少见的力作。同时作为一名诗人,福卡特还出版了《第二发现:翻译的诗学》(Second Finding: A Poetics of Translation.2007)。这本书以深刻的见解,讨论了诗歌的认知、意境、互文性、作者和译者身份。
在年轻一代的学者中,莎拉·巴斯莱曼(Salah Basalamah)的主要贡献在翻译史、翻译哲学和版权法领域。她的专著《翻译的权力:全球化的文化政策》(Le droit de traduire.Une politique culturelle pour la mondialisation, 2009),是一本对翻译版权跨学科的研究,反思了全球化背景下知识转换的影响。这本书旁征博引,观点新颖,对当今世界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
张:贵校翻译系是世界主要的翻译研究中心,在国际上享有盛名,您能介绍一下贵校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情况吗?
布里塞特:加拿大的大部分院校,翻译教学都隶属于语言学系或语言和文学系,而渥太华大学的翻译学院(STI)是一个独立的学院,是唯一一所拥有会议口译研究生课程的学院,录取对象为三年制或两年制速成本科的优秀毕业生,工作语言是英语或法语,西班牙语是选修。经过三个学期的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就可以选择合作项目,即学校课程和职业培训结合起来的项目。加拿大的本科翻译专业非常标准,基础课程包括翻译方法和理论、文献检索、术语和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专业课程有科技翻译和各类实习课程。
英法∕法英会议口译是硕士课程,有严格的录取标准和能力测试。一年的口译课程非常集中,要求具备翻译能力和经验,还要了解加拿大各机构的历史,因为大多数学生毕业后要到政府机构工作。由于具有博士学位或相关研究成果的师资不足,所有课程都由联邦翻译局的职业口译员教授,这也是世界上常见的做法,但从教学看来,这并不是完全有效率的做法。
翻译学院还提供两年制的翻译研究硕士教育,核心课程包括语言、话语和翻译理论课程,还有一些关于术语学、翻译软件、翻译史等内容的研讨会。学生还可以选修其他院系的课程,如语言文学系、传播系、女性研究系等。最近,硕士项目里新增了文学翻译方向,以吸引法律翻译方向之外的学生,目前由于生源不足,尚处于停办状态。
翻译研究博士点成立于1996年,学制4年。它曾经一直是北美地区唯一的翻译研究博士点。这个博士学位课程有两个研究方向:一个是翻译理论与批评,另一个是翻译技术。第一学年末有一次书面考试,第二学年末进行论文开题。
张:我看到您的研究兴趣之一是翻译社会学,您能解释一下它的核心思想吗?
布里塞特:我早在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之前就对翻译的社会学方向产生了兴趣。很多翻译史学家都直接或间接地考察过宗教翻译、文学翻译、法律翻译或科技翻译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一些翻译理论家如佐哈尔(Even-Zohar)和图里,他们首先进行了翻译文学的社会学研究。然而,90年代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标志着从社会学借用概念和模式的开始。翻译的社会学研究考察译者的地位、翻译职业、翻译作为各种社会系统(政治、经济、法律、媒体等)内的交际行为、以经济和政治为基础的各地区和世界的翻译流向,同时也研究参与决策过程、促使译本产生和传播的各种中介。通过社会学的透镜看翻译,改变了我们对翻译选择背后的理论基础的看法。比如,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差异不能再被看作是译者自己的“主观思想”或“意识形态”。翻译机构要复杂得多,因为它也受制于经济、法律、政治和社会环境,这些都不是译者本人的意识或能力所能控制的。
张:您最近的研究兴趣是什么?
布里塞特:我主要的兴趣一直都是翻译作为话语。分析文本的叙事和论证的微观和宏观结构,建立翻译选择的理论基础,或者将原文和译文放在各自的语境当中进行对比。除了话语的符号学建构之外,我还对某个社会中翻译策略和译本产生的社会话语之间的关系感兴趣。翻译策略的形式和内容是如何在某个特殊的交际语境(如文学、科技)或社会语境(如国家身份叙事)中,与审美、知识、观点、信仰以及价值观发生关系的。在社会话语环境中对单个的翻译或翻译的语料进行研究,适合任何一种文类。
张:您对当今世界的翻译研究现状有什么样的看法?
布里塞特:首先,我本人的知识有限,实在不敢妄谈世界的翻译研究状况。不过,计算机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简称ICTs)的发展,促成了新的笔译和口译实践,对语料库研究、术语研究和其背后的知识表达,以及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的发展,还将继续产生影响。在全球化的影响下,译者的环境和经济状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笔译和口译教学研究,尤其是对教师培训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在科技前沿,神经科学为观察和更好地理解翻译的认知成分提供了新的工具。就翻译研究本身而言,“文化转向”让翻译学者认识到了决定译本产生和传播的权力差异。在那之前,翻译研究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现在翻译研究日益全球化,考察世界各地的翻译历史、翻译实践和翻译学术,尤其是中国、印度、日本、朝鲜、非洲和中东地区,更加注重本族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也因而挑战着西方的概念、模式和研究范式。还有,对翻译的认识论的反思,特别是在非洲,用基于文化的方法来培训译者,正在为翻译和发展打开新的视角。“文化转向”留给我们的哲理和伦理遗产非常宝贵,因为它将翻译中的人置于语言之上。但是从翻译研究的出版量来看,翻译作为话语似乎介于科技和社会学中间。
张:您的专著《翻译的社会学批判:魁北克的戏剧与他异性》(A Sociocritique of Translation: Theatre and Alterity in Quebec)在学术界影响非常大,1991年荣获安·赛道梅尔奖(Ann Saddlemyer Prize),部分章节收录在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主编的《翻译研究读者》(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中。您能谈一下您是如何开始这项研究的吗?
布里塞特:这主要得益于我读了图里的专著《翻译理论探索》(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Tel Aviv, 1980),并随后于1984年参加了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在纽约举办的会议。在会上,我听了霍姆斯(James Holmes)、图里、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和兰伯特(José Lambert)的发言,并与他们讨论了我的博士论文计划。之后又参加了在印第安纳大学和多伦多大学举办的暑期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的研讨班,期间我有幸参与了西比奥克(Thomas Sebeok)、艾柯(Umberto Eco)、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利科(Paul Ricœur)、格雷马斯(A.J.Greimas)以及很多其他著名学者的研讨。除了符号学,社会学批评为分析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建构提供了框架。昂热诺(Marc Angenot)的 “社会话语”概念让我在图里的模式上又进了一步,因为他的模式只限于文学。同时,我也喜欢在加拿大的政治环境中去剧院看演出,这让我把研究的焦点从文学系统转向了当时无处不在的社会交际,尤其是国家身份叙事,包括舞台。
张:自从建立起自己的学科地位之后,翻译研究经历了几次“转向”,您对这些“转向”是怎么看的?
布里塞特:“转向”一词虽然有助于确定西方翻译研究最近的发展阶段,但这个词实在是使用不当。它让我们相信确实发生了范式的转变,但事实并非如此。目的论把翻译作为过程,描写翻译学把翻译看作产品,这些功能主义的方法是研究范式的转变。除此之外,翻译研究的“转向”都是借用其他领域的视角、问题、概念和模式,并不是范式的转变。伴随着脱离殖民化和民权运动,“表征的危机”进入翻译研究领域,这确实改变了我们对“文化”的批评视角,但文化本身并不是翻译研究的新成分。所谓的“文化转向”甚至都不是转向,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是最早的社会学视角,随后图里认为翻译是一种规范指导的“社会行为”,布迪厄使用了“惯习”的概念。同样,“国际转向”是随后的后殖民的讨论,研究翻译和翻译流向中的权力差异。还有“伦理转向”,是最新的概念,虽然对译者伦理的讨论可以追溯到德国浪漫主义的本雅明,最近的有梅肖尼克(Henri Meschonnic)和伯尔曼(Antoine Berman)。翻译的社会学或翻译的哲学并不是削弱了文化研究的影响,是翻译研究的延续而不是断层。
张:您认为翻译研究的下一个转向会是哪里?
布里塞特:我没有水晶球,没办法占卜未来。不过,经济会成为考察翻译实践的主导力量,包括从翻译和发展的关系到翻译和知识经济的关系,中国的翻译学者已经成为这个新趋势的主导力量。
张:有些学者认为翻译研究现在进入了一个瓶颈期,您对这种观点如何评价?
布里塞特:翻译是国际交流的必要条件,交流是我们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日程。国家级和国际翻译会议的数量和出版量的增加,以及翻译研究研究生课程的扩招,都说明翻译研究不是在瓶颈期。
张:最近几十年,翻译研究发展迅速,以致无所不包。有人担心我们会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于是呼吁翻译研究回归本体研究,即语言研究。您对这种呼吁如何评价?如果翻译研究真的回归到“翻译是什么”的本体研究,又能走多远?
布里塞特:国际化的发展让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翻译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它涵盖很多不同的领域。而且,计算机与通信技术改变了我们通常所称的“文本”。多媒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实践,如翻译软件和网站本地化,让我们重新思考翻译是“符际”活动,而不仅仅是“语际”活动。我们一直从其他学科借用概念和模式,如语言学、哲学和社会学。反过来也是一样,其他学科,如生物学和人类学,也在借用翻译的概念。不要忘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也是从人类学的“翻译转向”借用过来的,后来成为通向后殖民研究,甚至文化研究的踏板。这个概念现在被扩展到很多不同的领域,比如即将出版的论文集《翻译的跨学科性》,就涉及了差不多50多个借用翻译概念的学科。其他的例子还有最近的“朝圣作为翻译”和“建筑作为翻译”(把图纸翻译成建筑或把空间翻译成建筑结构)的会议征稿。翻译研究似乎是一个领航学科,一如20世纪的语言学。提谟志克(Tymoczko)把翻译扩大到符际转换促进了学科的交叉渗透,也让翻译研究受益良多。这些现象不会否定或压制转换的语言成分,雅各布森称之为“翻译要求”。
张:翻译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仍然是一门相对年轻和弱势的学科。您认为翻译研究未来的方向会是哪里?
布里塞特:说实话,翻译研究虽然是一门跨学科研究,但我并不确定它已经是一门主要的学科。我自己的经验是,当你介绍自己的工作是“翻译”而不是“交际”时,人们的反应会大不一样。对于初学者来说,词典的定义滞后于翻译实践的发展。虽然职业译者需要是多语和多媒体交际的专家,但是很多人仍然看不起翻译,认为是文书工作,只要语言和打字技能就可以了。根据设计欧洲翻译硕士(EMT)项目的专家的观点,一个全职译者需要不少于5年的大学训练。翻译的学术地位和译者的社会地位是相辅相成的。翻译的学术地位不高,可能是由于大部分翻译课程都是职业化的,是本科层次的。虽然硕士课程发展迅速,但博士课程仍然屈指可数。不得不承认,翻译研究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它伴随着现代语言学和诗学的产生而产生,但只是到了70年代才被认可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在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全球化交流、经济发展、人口流动的影响下,翻译有大量的需求,翻译实践也在发生变化。由于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翻译实践已经带来了大量的研究,积累了很多知识,现在更加倡导其跨学科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认为翻译研究是“弱势”学科。
张:尽管经历了多次转向,但西方的翻译研究仍然是描写性和实证性的,而实证研究本身却是规定性的,显然,仅有描写性研究还远远不够,您觉得是这样的吗?
布里塞特:前面提到过,理论是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之上。观察的本质就是实证性,但我不认为它是规定性的。例如,翻译教学必须对学生在做翻译练习中采取的翻译策略或有声思维报告进行观察,在这些观察的基础上,制定教学目标,只有在这个环节才可能是规定性的。再比如,在商业化的出版机构中,对参与译本产生的各中介的观察,也不是规定性的。这些实证研究对理解为什么翻译选择不能盲目归于译者是非常必要的。观察也证实了我们对翻译的根深蒂固的观点。当然,认为观察或描写都是客观和不带偏见的想法,也是天真的。正如“书写文化”对关于文化的民族志翻译进行的讨论,但这是所有科学领域的认识论问题。图里的描写主义,主要目的是走出自相矛盾的“翻译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规定。代表翻译研究范式转变的描写性方法使得现代语言学,即描写语言学成为可能。我们不要忘记,图里以语料为基础的描写的目标是去发现某些“规律性的”转变,这些转变反过来又指向目的语系统中的“规范”或制约因素。换句话说,图里的模式是描写性和解释性的。你说得对,描写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去验证完全基于理论或理论话语的作品,如基于翻译的“伦理”作品,就是规定性的,因为它忽略了交际的真实情况和社会历史环境。
张:您的解释全面而深刻,谢谢!
(责任编辑 孙婷婷)
张翠玲,北京外国语大学翻译学博士、北京科技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戏剧翻译。
作者电子邮箱:zhang.cuiling@gc.ustb.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