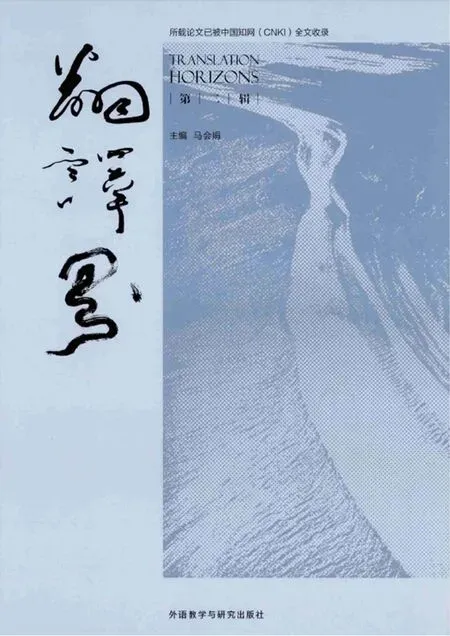文学翻译中绘画形式语言的运用
——以雷克思罗斯汉诗英译为例①
张保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文学翻译中绘画形式语言的运用
——以雷克思罗斯汉诗英译为例①
张保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基于绘画形式语言的理论观点,本文以雷克思罗斯汉诗英译为例,从线条的运用与几何图形的建构两大方面探讨了译者对绘画形式语言运用的艺术特色,旨在阐释译者翻译过程中的艺术认知机制,揭示绘画形式语言的译学价值,彰显文学翻译中跨艺术研究的意义。
绘画形式语言;雷克思罗斯;汉诗英译
1.引言
文史学家程千帆说:“艺术和艺术总是相通的,其中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巩本栋, 2010: 194)意象派诗人庞德(Ezra Pound, 1970: 84)说:“不同的艺术之间实在具有‘某种共同的联系,某种互相认同的质素’。”中西学者的相似论述为我们进行不同艺术之间的联姻研究,即跨艺术研究(interarts studies),开启了思路,也奠定了基础。论及不同艺术联姻后的关系与特色,我国学者马云(2006: 210)说:“一种艺术形式往往成为另一种艺术形式的补充、延伸和升华。”美国学者道林(David Dowling, 1985: 1)说:“不同的艺术形式,如果彼此间不能相互替代,那么至少可以通过相互借用对方新的表达力与表现手法来互相取长补短。”这样的论述则为我们进行不同艺术之间表达方式的互动研究指出了方向。庞德研究专家陶乃侃指出:“庞德加盟漩涡派是为了扩大意象诗的内涵,倡导整体艺术风格,企图从绘画、雕塑、音乐等艺术中吸取不同的表现方法,丰富诗歌表现的媒介手段。”(陶乃侃, 2006: 71)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说:“现代诗歌同时兼有绘画、音乐、雕塑、装饰艺术、嘲世哲学和分析精神的特点,不管修饰得多么得体,多么巧妙,它总是明显地带有取之于各种不同的艺术的微妙之处。”(波德莱尔, 1987: 135)从这里我们进一步看到诗歌、绘画、音乐、雕塑等具体艺术门类之间相互借鉴与吸收不同表现方法的现实存在与表情达意的独到特色。
在翻译界,我们常能听到翻译犹如绘画、摄影、雕塑之类的说法。但遗憾的是,大多数时候,人们只是将这些不同的艺术门类与翻译的关系进行比附阐说,点到即止。我们认为沿着这些“翻译比喻”的指引,可以尝试着对这些不同艺术与翻译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探索与思考,进一步发掘其间相互借鉴、吸收与转换的种种可能及其基本方法,进一步彰显其之于翻译研究与实践的价值与意义。鉴于此,下面选取翻译与绘画为题进行研讨,具体来说,是从绘画形式语言的视角对美国诗人、翻译家雷克思罗斯(Kenneth Rexroth,以下简称雷氏)的汉诗英译实践进行描写研究,以彰显雷氏在翻译中吸收绘画形式语言表情达意的微妙之处及其译学价值与意义。
2.绘画形式语言简介
每一门艺术都会用自己的语言和独特方式来传情达意,来满足人们的审美和精神需求,绘画也不例外。绘画是视觉艺术,其独特的传情达意方式体现在绘画形式语言上。所谓绘画形式语言,“是指由视觉形态要素——点、线、面、色、形、体、质等,依据画家内心情感和审美需求,在画面的结构关系中形成某种形象和状态,是一种与观者交流的特殊方式”(蒋跃,2012: 10)。绘画形式语言的形成是基于人类对自然物象最直接的感觉认识,是对自然物象外在特征的高度概括与提炼。它以具体或抽象的图形来表现人类的直接感觉、情感世界与精神追求,具有直观、快速、生动的特点。因此,绘画的过程便是绘画形式语言组织、运用的过程。绘画形式语言“对于绘画者来说是以视觉的形式去理解和表达作画者内心情感和其理解的世界;对于欣赏者来说,它是渐入佳境的起点;对于评论家来说,它是艺术批评的最终依据”(同上, 2-3)。
不同的绘画形式语言要素(如点、线、面等),具有不同的外在物理形态与不同的表情达意特性,也因之给读者带来不同的视觉心理感受。在绘画中,绘画形式语言表现为具体的图形样式,比如直线、三角形等。在文学翻译中,绘画形式语言经过译者的运思,可通过语言文字的形式来表征或构建,比如twist一词可表征曲线,between一词与空间中的不同表现对象结合可构建出三角形。绘画形式语言在文学翻译中最终凝定为语言文字,但其文字形态依然含有其图形样式在绘画艺术中所蕴含的种种形式意味。
限于篇幅,本文只选取绘画形式语言中的“线”与“面”这两个视觉形态要素对雷氏的汉诗英译进行探讨,以窥其翻译艺术之一斑。
3.翻译中线条的运用
在绘画艺术中,线条一直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人们认识与反映自然形态时最简明的表现形式,它能界定各种形状,暗示所绘物体的体积,显示其质量,展现其生命。线条的形状丰富多样,功能也彼此有别。不同形态的线条“能够明确而肯定地描绘出对象的各种关系和表达作者的情感”(陈琦, 2008: 26)。翻译中对线条的运用并非是一定要勾画出作品中物体的形状与体积之类,而是要借助线条的指向作用引导读者走进意象化的审美空间,去体味、生成与丰富作品的内在意蕴,从而真正实现让译入语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享受”(茅盾, 2009: 575)。
3.1 水平线的诗学意味
绘画构图中的水平线是指与画框上下边线呈平行关系的直线。水平线让人联想到地平线、海平面、广阔的平原、无边的沙漠等等,诗句“春江潮水连海平”(张若虚),“平沙莽莽黄入天”(岑参)即是显例。就水平线的功能与价值而言,书画家蒋跃(2012: 47)指出,水平线在绘画构图中可传递出安定、平静、舒展的感受,也可表现平坦与开阔的情景,还可抑制画面的躁动。这里我们不拟讨论诗文中“海平”、“平沙”之类的文字如何翻译,而着重关注译者如何在译文中创构水平形式线以求高效表情达意的艺术特色。我们知道,英语中可用来表现水平线构图的词汇有along、between、over、through、across等,这些词汇与其关涉对象相结合,可引导读者的视线向前水平延伸,营构出广阔的意象化空间。雷氏翻译中常常是显意识地使用以上词汇创构出比较鲜明的水平形式线,引导读者走进不同的意象化空间,完成对原作诗意蕴含的审美想象与重构。例如:
(1)原文:观书有感 朱熹
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今日江中自在行。
译文:THE BOATS AFLOAT
Last night along the river banks
The fl ood of Spring have risen.
Great warships and huge barges
Float as lightly as feathers.
Before, nothing could move them from the mud.
Today they swim with ease in the swift current.
译文中along(the river banks)沿着江岸而去的线条性构图引导着读者的视线不断向前延伸,形成一个广阔的水平空间,通过这个水平空间读者可进行这样的审美想象:一江春水沿河岸线普涨,水势壮阔,滚滚奔流。显而易见,译文中看不到这样的字面信息,但因along(the river banks)之故它已充分含蕴于译文的字里行间。此外,along(the river banks)所营构的意象化空间还为下文“艨艟巨舰一毛轻”、“今日江中自在行”的表达及选词用字(如f l oat、the swift current等)埋下了伏笔。整体审视,译文含滋蓄味,文脉一气贯通,画境鲜明,诗味隽永。
艺术视觉心理学认为:“同一形式可以结合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对象,产生同类而不同样的艺术效果。”不仅如此,“形式与表现对象结合之后,可以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这就是形式效应的延伸意义,也是形式表现的可塑性”(王令中, 2011: 82)。同是along一词,与不同的关涉对象相结合,其线条性构图产生的审美效果也大有不同。例如:
(2)原文:鸬鹚西日照,晒翅满鱼梁。——杜甫《田舍》
译文:...The sun sets
Behind a fl ock of cormorants,
Drying their black wings along the pier.
译文中的along(the pier)一词勾画出晒翅的鸬鹚沿着“鱼梁/the pier”一字排开,形式上也构成了落山太阳的“地平线”。如此构图,场景开阔宏大,画意浓郁,情趣隽永。译文中未见“满”字,也未说鸬鹚如何众多,但因along(the pier)形成的水平线构图的缘故,这两点尽蕴其中。此外,along(the pier)所构建的水平形式线还传递出“宁静”、“安详”与“闲适”的心理感受,这与原诗主题旨在渲染古朴、宁静、祥和的田舍风光颇为吻合。如此运笔,可谓取得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诗美效果。也正是基于along可以予人这样形式的心理感受,雷氏翻译时一再使用along一词,通过该词勾画出的水平形式线,艺术地传达不同的诗境蕴涵。比如,杜甫的另一诗句“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刺鸣。)”,雷氏译为:Along the sandbars fl ocks / Of white egrets roost, / Each one clenched like a fi st.显而易见,雷氏将诗句中的“静”字略而未译,但“静”字的意义已分明含蕴于“Along the sandbars”所构建的水平形式线之中了。
翻译中除了使用along一词的水平线构图之外,雷氏还频频使用其他“线条性构图”词汇来传情达意,而且也取得了简洁凝练、含滋蓄味的诗画艺术效果。例如:
(3)原文:(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杜甫《题
张氏隐居二首》
译文:The sound of chopping wood echoes
Between the silent peaks.
原诗句表现的是诗人独行春山,春山清幽,伐木丁丁,空谷传响的意境。如何传译这样的意境?雷氏诉诸 between一词的水平线构图,便找到了洞开意境之门的钥匙:两点一线的静寂山峦(between the silent peaks)既勾画出山谷空阔、幽深的景象,又通过鼓荡其间“伐木丁丁”声响的彼此应和(echo),收到了以声衬静的效果。译文未言“山更幽”,但这样的诗境已自然带出。联系前一行诗句来看,这样的译文还强化了“寻访者”置身荒野,孤独无伴,空旷寂寥的切身感受。译句简练,妥帖传神,体现了“字唯期少,意唯期多”的诗美特色。我们知道,between一词可用于表征两点一线的水平线构图,也可用于表征两条线并行不悖的“立体”构图。例如:
(4)原文: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杜甫《旅夜书怀》
译文:...but I grow
Old, ill and tired, blown hither
And yon; I am like a gull
Lost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原诗作者将自己当下的人生遭遇类比为一只在天地之间飘飞的沙鸥,其言外之意是天地辽阔清旷,自己孑然独行,孤苦伶仃,漂泊无依,传达出诗人倍感人生凄凉、悲苦的意味。如此丰沛的诗意,译者仅用between(heaven and earth)一词的水平线构图便得以艺术地再现:读者仿佛能看到朝着苍茫、浩渺的水天交接处诗人/沙鸥远去的孤单身影。有的译者将此句译为:It seems I am but as a sand bird / Blown before the elements.(tr.Rewi Alley); What do I look like, drifting on so free? / A wild gull seeking shelter on the sea.(tr.Xu Yuanchong) 比读之下,更可见雷氏翻译中借用绘画形式语言传情达意的特色。
3.2 锯齿线的诗学意味
锯齿线是指由各种斜线相接的曲线,具有棱角,形同锯齿。锯齿线看起来有如林立的针尖、刀尖、毛刺尖,外形上给人以悚惧感、刺痛感。因而在绘画构图中使用锯齿线可产生紧张、惊险、奇突的形式心理,也可表现痛苦、扭曲、恐怖的意味(蒋跃, 2012: 49)。正是基于锯齿线给观者带来的这类心理感受的缘故,雷氏翻译中再现惊险、痛苦等意蕴氛围时,常常选用含蕴“锯齿状”意味的词汇,以求实现原文与译文之于读者感受的“审美等效”。例如:
(5) 原文: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苏轼《念奴娇 赤壁怀古》
译文:...The
Jagged peaks pierce the heavens.
The furious rapids beat
At the boat, and dash up in
A thousand clouds of spray like
Snow.
原诗句通过描写赤壁高插云霄的散乱山崖,汹涌奔腾、猛烈冲击堤岸的滔滔江水,把读者带进一个奔马轰雷、惊心动魄的奇险境界,使人心胸为之开阔、精神为之振奋。怎样翻译“乱石(穿空)”才能收到惊悚、险峻的效果呢?有的译者处理为“Broken rocks (pierce the clouds)”,偏于概念意义的指陈。雷氏则选用了jagged(having a rough, uneven edge or surface,often with sharp points on it)一词,该词启示出的凹凸不平、尖刺林立的构图形式线将物理的形转化为心理的力,在传达出原文的概念意义之时,巧妙地传达了原文蕴含的奇突、惊险、令人悚惧的意味。从整个译句来看,前有jagged一词,后续pierce一字,意脉贯通,妥帖自然。此外,也许正是基于jagged一词给人惊险心理暗示的缘故,译者便顺势将“惊涛拍岸”改写为令人倍感悚惧且惊险无比的情景:“The furious rapids beat / At the boat”。
从上可见,绘画中不同的构图形式线可表现不同的视觉心理感受与情感。因此翻译中表达不同的视觉心理感受与情感,就需有针对性地选择具有不同绘画形式意味的语言或词语。同为表现锯齿形状的词汇,因其形态特征给人视觉心理感受的差异,其表现的情感强弱与视觉心理感受也彼此有别。例如:
(6)原文: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杜甫《对雪》
译文:Ragged mist settles
In the spreading dusk.Snow skurries
In the coiling wind.
原诗句出自《对雪》,其写作背景是诗人其时生活的长安城被叛军安禄山占领,诗人在逃离长安的路途中,被叛军抓获押回,其性命虽得以保全,但是痛苦的心情、艰难的生活,仍然折磨着诗人。这两句既是写景,也是言情。诗人的满怀愁绪与身心苦痛宛如乱云薄暮般延展、急雪回风般翻腾。雷氏以ragged mist来翻译“乱云”,通过ragged(not straight or neat, but with rough uneven edges)一词予人的绘画形式心理感受来曲达其意。这一译法与前一例相比较,少了一份尖刺(sharp points)所带来的刺痛、惊险、悚惧意味,多了一份崎岖不平(rough uneven edges)所带来的扭曲、痛苦的内涵。
3.3 曲线的诗学意味
与直线相比,曲线因其曲折变化而具有生命流动感,视觉效果上有轻盈、流畅、优美、弹性等情感性质。“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阑斜。”(张泌)、“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刘禹锡)等均表达了“以曲表动”、“以曲为美”的情调与意趣。在绘画构图中,长长的曲线“可使画面活泼舞动,传递着轻快欢乐的感情”(蒋跃, 2012: 49)。在此意义上,语言中含蕴着曲线意味的词汇可使所描绘的情景呈现出“化静为动”的特色,取得“化美为媚”的动态艺术效果。例如:
(7)原文:玉绳回断绝,铁凤森翱翔。——杜甫《大云寺赞公房》
译文:The Northern Crown crosses the sky
Cut by the temple roof,
Where an iron phoenix soars and twists in the air.
以上两句是诗人夜宿大云寺户外抬头仰视所见的情景,也是诗人整个夜间见闻与感受的一部分。其大意是:天上玉绳星的星光被大云寺高耸的殿宇隔断,殿宇屋脊上的装饰物铁制的凤凰高高耸起,张翼欲飞。通常而言,以soar来翻译“翱翔”便已足够,然而雷氏另加上了富有曲线构图意味的twist一词,此词一着,一方面传递出飞动轻快,活泼而富有生气的韵味,另一方面使人感受到殿宇的高耸以及灵动与轻盈。同是twist一词,用于大地上描绘向前流动的山泉时,其构图形式则又传递出另一番意趣。例如:
(8)原文:转来深涧满,分出小池平。——储光羲《咏山泉》
译文:It twists between rocks
And makes deep pools.It divides
Into islands.It fl ows through
Calm reaches.
《咏山泉》是首托物言志的山水诗,明写的是山泉的“不知名”、“无人问”、“恬淡”、“长自清”等特点,暗表的是诗人的个性追求——恬淡自然,飘逸出俗。上引两行是该诗的颈联,写的是山泉的曲折遭遇。这里译者仍然使用了富有曲线构图意味的词twist,语境变了,其引发读者的视觉感受也变了。twist一词既译出了山泉在乱石间曲里拐弯、不歇穿行的生命活力,也译出了一往无前的个性品格与气势。
曲线的形式多种多样,除了自由曲线外,还包括圆或圆弧的几何曲线。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看,曲线具有女性的特征,它柔软、丰满、优雅、轻快、跳跃、稳重等,表现出变化、柔和的节奏(蒋跃, 2012: 14)。基于曲线的这一特点,雷氏翻译中简笔勾勒女性形象或典型特征时,往往选用语言中含蕴圆弧曲线的词汇。例如:
(8)原文:子夜歌 梁武帝
(朝日照绮窗,光风动纨罗。)
巧笑蒨两犀,美目扬双蛾。
译文:THE MORNING SUN SHINES
(A sly smile comes on her lips.)
Her moth eyebrows arch
Over her beautiful eyes.
该诗前两句写闺中少女居住的环境,视线由窗外转入窗内;后两句写少女最富于青春光彩的笑容与目光。窗框有如镜框,女子的形象显映其间,宛然如画,诗意盎然。后两句的大意是:她甜甜地一笑,露出两排漂亮的牙齿;她秋波流转,扬起一对好看的眉毛。再现“美目扬双蛾”的精彩瞬间,雷氏选用了arch(to form or make something a curved shape)一词,该词含蕴着一道弧形,寓静于动,传达出优雅、轻快的视觉心理感受,将少女的神采与内心表现得尤为恰切。又如:
(9)原文:自置五色丝,色透缣囊过。
意在留补缀,恐衣或绽破。——梅尧臣《灵树铺夕梦》
译文:She
Carries her kit of colored
Threads.I see her image bent
Over her bag of silks.She
Mends and alters my clothes and
Worries for fear I might look
Worn and ragged.
原文是诗人悼念亡妻之作,通过选取梦中妻子为自己缝补衣物做着精心准备这一细节,将妻子关爱自己的款款深情表现得尤为含蓄而充分。译文未依照原文如实翻译,而是将妻子为丈夫缝补衣物精心准备的用心化为现时缝补的实际行动,译文与原文表述视角虽有差异,但再现妻子的良苦用心与深切爱意的效果是一样的。取得殊途同归的原因是,译者选用了 bent(to move the top half of your body forwards or downwards)一词,该词所蕴含的弧线既勾勒出妻子的身段,又表现了妻子专注的神情。此词一用,作者意欲表达的不尽之意,均可见之于言外。在华兹华斯(W.Wordsworth)的诗作“The Solitary Reaper / 孤独的收割女”中,我们也可看到诗人使用bend一词来勾勒“收割女”专注劳动的神情与优美的曲线身段:I saw her singing at her work, / And o’er the sickle bending;
3.4 垂直线的诗学意味
垂直线指构图中与左右画框呈平行的线。在绘画构图中,因其自身笔直挺立的形态,给人以挺拔、刚直、明确、向上或下落的感受。在画面中,垂直线可表现高耸、刚直、挺拔的性格,也可表现庄重、肃穆、悲壮的意味(蒋跃, 2012: 47)。诗歌作品中常能见到妙用“垂直线构图”的诗句。比如,读到“大漠孤烟直”(王维)时,可体会到大漠壮阔、雄奇、空旷、高远的意蕴氛围。读到“飞流直下三千尺”(李白)时,既可想象到山之高峻陡峭,又可见水流之迅急,高空直落,具有势不可挡的力量与气势。还有“(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李白),“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等等,这类诗句无不让人的想象沿着其间的垂直线构图不断飞跃、升腾,分享诗人含蕴其间的豪情、志趣与抱负。雷氏的译文中,借用含蕴垂直线构图的词汇来表情达意而获得“事半功倍”的例子也不鲜见。例如:
(10)原文:(塞柳行疏翠,山梨结小红。)
胡笳楼上发,一雁入高空。 ——杜甫《雨晴》
译文:A Tartar fl ute plays by the city gate.
A single wild goose climbs into the void.
原诗通过描写秋天边塞雨后初晴的景象,抒发了诗人分外欣喜的情感。“塞柳翠”、“山梨红”写色彩的明艳、爽朗,“胡笳发”写乐音的清脆、幽远,“一雁孤飞高空”写空间的纵深、旷阔。一言以蔽之,秋天雨后晴空的清、艳、凉、旷迎面扑来。译文为传达雨后塞上高远、旷阔的景象,选用了可以构建垂直线意味的词汇climb(to move up, down, or across something, especially something tall or steep, using your feet and hands)。显而易见,译文中未言“高”“远”“旷”“阔”,但这些意味均已含蕴其间,译句简洁凝练,收到了言已尽而意无穷的诗美效果。climb一词勾画的垂直线暗示出的类似意味,在杜甫诗句“(映物连珠断,)缘空一镜升。馀光隐更漏,况乃露华凝。”的译文中也可见到:The moon like a clear mirror /Rises from the great void.When it / Has climbed high in the sky, moonlit / Frost glitters on the chrysanthemums.需要再次说明的是,垂直线向上与向下的构图与不同的情景结合,也会产生同类而不同样的艺术效果。例如:
(11)原文:(空外一鸷鸟,河间双白鸥。)
飘飖搏击便,容易往来游。——杜甫《独立》
译文:Soaring with the wind, it is easy
To drop and seize
Birds who foolishly drift with the current.
以上诗句描绘了“鸷鸟”与“白鸥”当下相安无事的状态,但其间潜藏着生死劫杀的玄机。高空飞行的鸷鸟享有绝对制空权,要攻击河间惬意游荡的双白鸥可谓轻而易举。如何再现“鸷鸟”的凶猛与搏杀技能?译者选用了具有垂直线构图意味的词汇drop(to fall suddenly, especially from a high place),该词的运用,将鸷鸟的凶猛、迅捷、“秒杀”的特点再现无遗,原文中的“搏击”之意也自然带出。
3.5 斜线的诗学意味
绘画构图中,斜线是指与画框边线不平行的直线。斜线往往使人联想到物体的倾倒、人的跌倒和前冲等,因而与不稳定、运动、变化、速度等感觉联系在一起。诗歌创作中,诗人们常常利用斜线构图来营构诗句,以使其笔下描绘的情景动感十足、生机勃勃,物形意态跃然纸上。“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杜甫),“斜”字的使用,将“燕子”的轻盈飞动描绘得尤为逼真,也自然带出了诗人喜春爱春、闲适自在的心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世人评说“横斜”的构图,曲尽梅之体态风神,可“脍炙天下二百年”(南宋周紫芝语)。雷氏的译文中除了转存原文文字上已含有“斜(线)”的情形外,更多的是依据原作诗境通过创造性运思建构出蕴含“斜线”意味的情景,以引导读者的情感与思维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体味到身临其境的切身感受。例如:
(12)原文: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王维《鹿柴》
译文:The low rays of the sun
Slip through the dark forest,
And gleam again on the shadowy moss.
原文: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王维《辋川闲居赠
裴秀才迪》
译文:The rays of the setting sun
Shine through the evening smoke
That hovers over the village.
原文:朝日照绮窗,风光动纨罗。——梁武帝《子夜歌》
译文:The morning sun shines
Through the fi ligree shutters.
A wind full of light
Blows open her thin gauze robe.
以上列举的三例画线处,雷氏均营构了一个太阳光线倾斜照射的情景。斜线予人的动态变化感受,一方面较为成功地再现了原作的诗境,另一方面很机巧地将读者导入“现实”情境的不断变化之中,参与其间诗意的创造与重构。显然,这已成为雷氏创译时一再使用的既定方式。
4.翻译中几何图形的建构
从上可见,翻译中对不同构图形式线及其诗美效果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单句中含蕴的线条形式上。翻译中由“线”走向“面”的绘画构图意义与价值还未曾涉及。“面”往往通过几何形体表现出来。“几何形体,是人们对自然形象的概括,可引起观者某种心理上的同感,具有暗示作用。”(蒋跃, 2012: 51)与线条一样,不同的几何形体也会产生不同的视觉感受。雷氏译文中运用几何形体进行表情达意的绘画思维特色也很突出,其译文中的几何形体一方面体现在他创造性地运用具有几何图式意味的词汇上,另一方面体现在他组构篇章时有意识的几何形体建构上。试举例说明之。
4.1 三角形的诗学意味
通常而言,三角形是所有几何图形中最具稳定性的。但三角形在构图中由于放置的方位和角度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形式感受。倒置的三角形最不稳定,给人强烈的动荡不安的感受。正置的三角形最稳定,给人以庄严、静穆、沉重、稳定的感受(蒋跃, 2012: 51)。雷氏在译文中有意识地创构出正置的三角形图案来暗示诗作中静穆、沉重、稳定等意味的运思轨迹颇为明显,且看下例:
(13)原文: 回堤溯清风,澹月生古柳。——梅尧臣《忆吴淞江晚泊》
译文:Along the banks a fresh breeze blew against the current.
The pale moon rose between two willow trees.
这是诗人悼念亡妻之作《忆吴淞江晚泊》中的第二联,写的是诗人如今晚泊吴淞江边追忆昔日与妻子同行时的情景,抒发了“昔时美景在,今日人已殁”的感伤情怀。静静地回想,默默地追思,是该诗所呈现出的意蕴氛围,虽未直言,但却蕴藏在诗作不同意象的相互组构中。要再现这样的意蕴氛围,雷氏没有通过语言进行“化隐为显”的直接陈述,而是在译文中勾画了一个正置的三角形(参看例文中画线的译句),通过这个几何图式予人的心理暗示,来表现宁静中的凄苦与追思的意味。此外,“古柳”选译为two willow trees的象征意味很浓郁,也很巧妙!类似这样显意识的做法,在下例中也可见到。
(14)原文: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山居秋暝》
译文:The bright moon shines between the pines.
(The crystal stream fl ows over the pebbles.)
从译例画线的句子中,读者在想象中不难构建出一个正置的三角形图式,这样的图式正好暗示或强化了秋雨过后,山间天色渐晚时那特有的一片宁静的意味,这也是该诗本有的蕴含。同此诗句,有的译者译为:A silvery moon is shining through the pines.(tr.Wang Baotong);A bright moon shines among the pines.(tr.Peter Harris)比照之下,雷氏翻译中进行几何构图的用心与特色显而易见。
4.2 十字形的诗学意味
十字形构图是指画中的水平线和垂直线交织而成的画面。因其易让人联想到基督教的“十字架”,有利于形成平静、肃穆的气氛,启人哲思(蒋跃,2012: 54-55)。雷氏翻译中创用十字形构图来表情达意,更多是基于句子与句子之间的组合关系来完成的。换言之,此时雷氏手中的译笔堪比画笔,形式是文字的组织,但本质是绘画线条的绾合。在此意义上,绘画构图思维直接运用到了译文语篇的组织上。例如:
(15)原文: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杜甫《北征》
译文:Midnight, we cross an old battlef i eld.
The moonlight shines cold on white bones.
古战场的肃穆、宁静令人深思,译者通过上下两句共同构建出的十字形几何图式予以了暗示。具体来说,cross在地上画出一条跨越战场(battlef i eld)的横线,The moonlight shines画出一根自上而下的垂直线,两条线交汇,十字形几何图式形成。这里“月照”的光线说成是垂直线而非斜线,是基于译者将“夜深”译为“Midnight / 午夜”之故:午夜时分,月近中天,当头照耀,垂直线乃成。如此构图,在雷氏的笔下并非孤例。又如:
(16)原文: 玉绳回断绝。(铁凤森翱翔)——杜甫《大云寺赞公房》
译文:The Northern Crown crosses the sky
Cut by the temple roof,
(Where an iron phoenix soars and twists in the air.)
此例上文用来探讨过其曲线构图的形式意味,这里再次选来用于分析其十字形几何构图的意味。译文中cross画出一条跨越天空(the sky)的横线,Cut by the temple roof画出一条直插云霄的直线,两条线交汇,形成十字形构图,暗示出大云寺高耸、庄严、肃穆的情景。
4.3 圆形的诗学意味
绘画构图中,圆形边线给人滚动、饱满、完整、柔和、团拢的视觉感受,很容易引起观众注目,如同舞台上的聚光灯(蒋跃, 2012: 53)。圆形可分为同心圆、破绽圆、螺旋形圆等。同心圆的中心点格外引人注目;破绽圆,类似英文字母C,其缺损之处往往成为视觉的焦点;螺旋形圆给人更为强烈的向心旋转的动感。基于不同圆的不同形态特征,雷氏翻译中往往能根据原作诗情表现的需要作出有针对性的选择,从而使自己笔下的圆成为其创造性传情达意的有效手段。例如:
(17)原文:(花影重重叠绮窗,)篆烟飞上枕屏香。——朱淑真《旧愁 其二》
译文:(Thick shadows of fl owers
Darken the fi ligree lattice.)
Incense coils over the screen
And spirals past my pillow.
原诗写的是挥之不去的旧愁。以上诗句既是景语,也是情语,诗人心中的愁情宛如重重花影,拂去还来,又如弥漫的盘香烟缕,袅袅不绝。译者没有直译“飞”字,而是选择了两个含蕴“圆形”意味的词语coil(towind or twist into a series of rings) 与 spiral(to move in a continuous curve that gets nearer to or further from its central point as it goes round)来再现现实中“飞”的形态与过程,予人生动形象,亲历其境之感。从译文整体来看,两个词语中“圆形”的团拢与旋转作用也可暗示或象征袅袅不绝的情思。翻译中基于类似的阅读经验,雷氏也往往选择含蕴圆形意味的词语来进行传译。在这一意义上,雷氏译笔下的圆形构图便具有了“意象图式”的意味。例如:
(18)原文:(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杜甫《夜宴左氏庄》
译文:(The brook fl ows in the darkness
Below the fl ower path.) The thatched
Roof is crowned with constellations.
以上诗句出自杜甫少有的明快清丽之作《夜宴左氏庄》,是该诗的颔联,写的是诗人夜宴时当晚的奇幻夜景。再现这样奇幻的景致,诗人创造性地使用了具有“破绽圆”形态的词语crown,此词一着,“草堂”显得非同凡响,神奇无比!其勾画出的情景画面,既象征着宴会的团聚,雅士的云集,又引人注目,成为夜宴活动的中心,为下文夜宴活动的展开做好了铺垫。又如:
(19)原文:(梵放时出寺,)钟残仍殷床。——杜甫《大云寺赞公房》
译文:The chanting of prayers fl oats from the hall.
Fading bell notes eddy by my bed.
原诗句是诗人夜宿大云寺所见所闻中的“听闻”部分,诵经朗朗,钟乐阵阵,寺院内外,声声回旋,不绝于耳。大云寺之清静与明朝拟行走于沃野尘沙之对比,令诗人感慨系之。再现大云寺经久不息的钟乐,雷氏使用了含有“螺旋形圆”意味的词汇eddy(to move around with a circular moment),将大云寺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的钟乐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之更加反衬出环境的空阔与清幽以及对诗人心情的濡染作用。
5.绘画形式语言的译学价值
为了便于研习,我们对雷氏译文中含蕴的绘画形式语言“线”与“面”的存在形态及其美学价值进行了分别探讨。所需说明的是,雷氏译文中无论是对“线”还是“面”的运用并不仅限于以上所列举的几个方面,其具体译作中对绘画形式语言元素的运用也并非仅局限于单一的元素,同一译作中多种元素综合运用的情形也很常见,也相得益彰。比如,前文例6中既用了锯齿线(ragged)、辐射线(spreading),又用了螺旋形构图(coiling),语言生动、简洁、凝练,予人身临其境之感。通过以上研析,我们可以看到雷氏翻译中对绘画形式语言的借用其译学价值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实现了译文与原文的审美等效。“绘画形式感的产生源于生活中同类形式给我们的经验,这是绘画作品能够与观众交流的基础。对构图形式的视觉研究既是基于思想感情对表达形式的要求,也是基于对生活形式感受的总结。”(蒋跃, 2012: 56)这一点是中西读者共有的认知基础。因此,翻译中将绘画形式语言嫁接到译文中来,就是将可引起心理共鸣的特定形式构成导入译文,这便奠定了读者阅读时作出相同或类似反映的物质基础,这无疑有利于译文与原文之间“审美等效”的实现,即译文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享受”,也因之更有利于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的理解、接受与传播。
2)创新了翻译的艺术表达途径。绘画形式语言具有直观性、含蓄性与建构性等特点,对欣赏者的想象与认知具有驱动和导向功能,能引发超然“形”外的联想,因而可以表现某种“欲说还休”的东西和“不可言传”的东西。哲学家金岳霖在其《知识论》一书中谈到译意与译味时说:“得一语言文字所表示的意义是比较容易的事,得一语言文字所表示的味是比较困难的事。”(陈福康, 1996: 354)时至今日,译味之难依然是翻译中的大难。如何译味?进一步说,如何译出原作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与“味外之味”?通常情况下,人们多从语言学与文学视角进行探讨。这里从绘画形式语言这一视角切入,不失为又一条实用而有效的途径。借助译文中含蕴的绘画形式语言,进一步说,借助绘画形式语言的“含滋蓄味”以及所构建的“有意味的形式”,译文读者可以从中有所感悟,有所共鸣,有所寄托,有所玩味。一句话,真正体味到“言近旨远”,“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意趣。因此,将绘画中的视觉语言转换成文字语言运用到翻译中,也就是将绘画形式语言的直观性与独特表现力带到译文中,这样的翻译丰富了译文的艺术内涵,拓展了译文的艺术表现方式,也强化了译文的艺术表现力。
3)彰显了翻译的艺术认知机制。雷氏的汉诗英译作品常被研究者称为“创意英译”(钟玲1985, 2003; 刘岩, 2004; 朱徽, 2009; 葛中俊等, 2010;郑燕虹, 2012),更有论者直接将其划归自由创作之列,不再拿它当作翻译讨论。比如,“在雷氏的译文中最动人最优美的部分,往往是跟原文出入较大的片段,是他将原文当成供自己自由发挥的原材料的产物。在这些部分,他经常甚至超越了常规的翻译界限而进入创作领域”(朱徽, 2009:135)。“雷克思罗斯只是将原作当作自己创作的素材,以原作的情感激发自己的情感体验,进而‘创作’出译作”(葛中俊等, 2010: 49)。一般说来,如果仅从语言的形式与内容上对其所译作品进行字比句次的对照,很多时候因语言形式、语义表达与原作相去甚远,确实给人自由创作的印象,难以将其认作翻译。然而,若转换视角从绘画形式语言的运用来看,不少译文背后的翻译认知机制还是显而易见的,译者的翻译意图与目的也是十分明确的。因此,翻译中绘画形式语言的介入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与解释雷氏汉诗英译过程的本质特征,也可对目前翻译研究中占绝对主导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形成有效的补充与拓展。
6.余论
雷克思罗斯既是美国重要的文学家、诗歌翻译家、戏剧家,也是一名出色的画家(Gutierrez, 1993: 134)。作为画家,他熟谙绘画的技艺及其表情达意的价值与效率,也在其诗歌创作与翻译实践中进行了成功的运用(张保红, 2015: 81-114)。雷氏从绘画形式语言的角度实现了翻译中的诗画联姻,成就了其译文的一大特色,这也是其长期以来“致力于语言的创新表达与破除艺术形式之间人为界限”不懈探索的成果(Hamalian, 1991: 375)。本文只是初步探讨了雷氏翻译中的这一跨艺术特色,沿着这一思路对雷氏译文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展开。
Dowling, D.(1985).Bloombury aesthetics and the novels of Foster and Woolf.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Gibson, M.(1972).Kenneth Rexroth.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Inc.
Gutierrez, D.(1993).Kenneth Rexroth: A tissue of contradictions.Literary Review,(1): 134-138.
Hamalian, L.(1991).A life of Kenneth Rexroth.New York: W.W.Norton &Company.
Pound, Ezra.(1970).Gaudier-Brzeska: A Memoir.New York: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Rexroth, K.(Trans.).(1956).One hundred poems from the Chinese.New York: New Directions.
Rexroth, K.(1961).Assays.New York: New Directions.
Rexroth, K.(Trans.).(1970).Love and the turning year: One hundred more poems from the Chinese.New York: New Directions.
波德莱尔.(1987).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福康.(1996).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陈琦.(2008).江水如蓝. 北京: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葛中俊等.“隐士”杜甫:雷克思罗斯英译杜诗文本价值观. 当代外语研究2010, (11): 47-51.
巩本栋.(2010).千帆诗学.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蒋跃.(2012).绘画形式语言.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刘岩.(2004).雷克思罗斯的杜甫情结.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3): 5-8.
马云.(2006).铁凝小说与绘画、音乐、舞蹈——兼谈西方现代艺术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茅盾.(2009).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载罗新璋、陈应年编《翻译论集》(修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陶乃侃.(2006).庞德与中国文化.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令中.(2011).艺术效应与视觉心理——艺术视觉心理学.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张保红、刘士聪.(2012).文学翻译中绘画因子的借用.中国翻译, (2): 98-103.
张保红.(2015).印象派绘画与汉诗英译——以王红公汉诗英译为例. 翻译季刊, (4): 81-114.
郑燕虹.(2012).肯尼斯·雷克思罗斯与中国文化.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钟玲.(1985).体验和创作——评王红公英译的杜甫诗.郑树森编.中美文学姻缘.台北: 台湾东大图书公司.
钟玲.(2003).美国诗与中国梦.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朱徽.(2009).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英美译家汉诗英译研究.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 吴文安)
①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YY016)、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13-0742)与广东省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项目(312-GK31037)的部分研究成果。
张保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博士、翻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翻译、中英诗歌。
作者电子邮箱:zhangbao19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