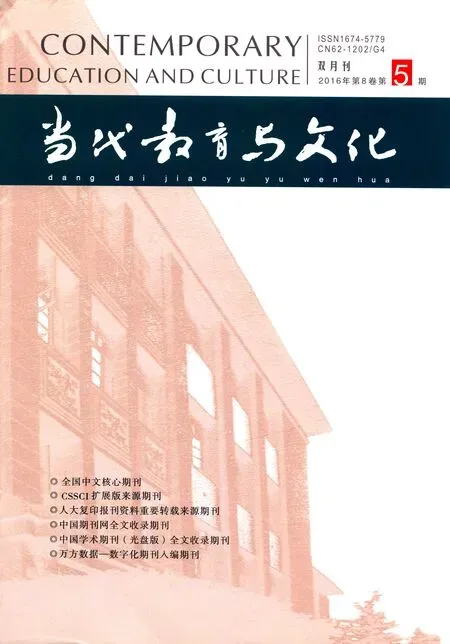胡德海先生教育学术风范述略
潘洪建
(绵阳师范学院,四川绵阳 621050)
胡德海先生教育学术风范述略
潘洪建
(绵阳师范学院,四川绵阳621050)
胡德海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学家,他在诸多领域特别是教育基本理论领域提出了许多独到的学术见解,为我国教育理论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其学术性格与治学风范主要体现在:执著学术,淡薄名利;严谨治学,追求真知;独立思考,创新立说;学贯中西,融通古今;循循善诱,深入浅出。研究胡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学术风范,对于我国教育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具有特别的意义。
胡德海;教育思想;学术风范
胡德海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学家,他在教育基础理论、教育史乃至民族教育等领域开展了深入而持久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到精辟的学术观点,对我国教育理论构建与学科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胡先生从事教育学术研究工作60余载,发表了众多论文与著作,回顾、总结胡先生的学术性格与治学风范,对于我国教育学术发展和青年学者的成长,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一、执著学术,淡薄名利
作为一名学者,胡先生长期从事教育学术研究工作,他几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孜孜以求,从不懈怠,即使在被打成“右派”的艰难岁月,也没有放弃学习与思考。胡先生对学术的热情与执着,源于他对教育工作的深刻认识、对教育活动的真挚热爱、对教育事业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胡先生正值中学时代,抗日烽火燃到他的家乡,他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与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立下“为国学习”志向。由于战争的原因,他小学毕业后无学可上,多次转学,后来考入金华高中读书。在金华中学读书期间,他对文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时的他开始思索今后的人生道路,做出了影响一生的两个决定:第一,学文科,不学理科,将来系统研究世界、社会与人生问题;第二,学师范,不入仕途,终身做学问,将来成为一名学者。在大学学习期间,胡先生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著作,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和体会。他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审视社会现象,梳理所学知识,开始对教育问题有了自己的思考和认识。他发现,当时的教材、国外专家的讲学都存在一些问题,诸如教育理论陈旧、知识残缺不全,体系不完整,教条色彩浓厚,理论与实际脱节等,暗下决心,确立了努力创建一个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的志向[1]10。1953年,胡先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来到地处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工作(当时叫西北师范学院,1958年改为甘肃师范大学,1981年恢复旧名,1988年改为现名),成为一名高等学校的教师,从事教育学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中,他对教育学理论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与认识,强化了立志创建自己的教育学体系的宏伟志向。胡先生后来的学习、思考与研究大多是围绕这一志向展开的,他先后在国内权威期刊陆续发表一系列文章,步步逼近自己的梦想。1987年退休后,他一边继续上课,一边着手撰写《教育学原理》一书,用了整整10年的工夫,1997年完成书稿,1998年公开出版,此时,胡先生已迈入古稀之年了。可以说,这本著作花了胡先生毕生的精力,凝聚了胡先生大量的心血,该书的出版实现了胡先生构建一个完整的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夙愿。《教育学原理》一书出版后,立即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获得高度赞誉,被誉为“20世纪教育学的扛鼎之作”。该书后来不断再版、重印,2005年被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列入“研究生教学用书”,成为研究生学习的基本读物。
《教育学原理》的撰写用了十年时间,而思考与研究则长达四十年,对个人而言,可谓一项十分浩大而漫长的工程,没有对学术的热爱与追求,没有高度的事业感与责任心,没有坚忍不拔的精神与顽强持久的意志,要实现这一宏愿是难以想象的。更难能可贵的是,《教育学原理》这本书是在他退休之后完成的。就常人而言,退休就意味着事业的终结,退休后自当静养,享受生活,而对胡先生来说,退休却是学术研究又一起点。记得胡先生在上课时说过,他真正的研究是在退休后才开始的,因为退休前事务繁杂,难以静下心来从事专门的研究,只有退休后才能专心读书、思考与写作。可以说,胡先生不愧为终身学习的光辉典范,值得我们后辈学习与效仿。
我于1993年上西北师大攻读硕士学位,1994年上半年那个学期有幸目睹了《教育学原理》一书的手稿。当时,西北师大教育科学研究所为研究生开设了教育学原理,这门课程主要是博士研究生的专业必修课,硕士研究生可以旁听或选修(李定仁先生让我们选修了胡先生的课)。每次上课,胡先生都带着他的“稿子”,书稿写在用过的纸张背面,书写工整、规范,字体颇大,刚劲有力。他有时照着稿子讲,有时脱稿阐释。他的观点、论证与阐述独到而深刻,让我们耳目一新,充分感受到教育学术的魅力所在。不知先生现在是否还保持着那份手稿,如果还保存着的话,可算是难得的“文物”了,因为今天我们已习惯电脑打字,写字的机会越来越少。正是受胡先生的影响,我养成了在用过的打印纸背面书写和打印的习惯,以至于三年用不完一本打印纸,我的低碳生活也开始影响我的学生与周围的同事。
胡先生甘于寂寞,淡泊名利。他有志于学,心无旁骛,将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读书、思考、研究之上,潜心学术研究,在物质方面的要求极低,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去过胡先生家的人都知道,他家陈设简单而朴素,没有高档家具,没有豪华装修。在我的印象中,他先前居住过的两处寓所都是水泥地面,基本上没有装修,现在住的房子尽管比先前大些,但仍是简装,对于一个陌生人来讲,可能很难相信这是一位著名学者的家。胡先生自1978年以来一直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课,他自己查阅资料,编写讲义,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西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博士生培养立下汗马功劳,可谓劳苦功高,但他只是认认真真做事,不求什么名分。胡先生给许多硕士生、博士生上过课,对他们进行严格的思维训练和学术陶冶,但真正“亲自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却很少,在我们的印象中,他仅仅指导过一位研究生的论文(即1985级研究生班的钟志贤,钟志贤现为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学者)。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胡先生一直给博士研究生上课,是博士生指导团队(该团队主要由李秉德、李定仁、胡德海、南国农、赵鸣九等先生组成)的重要成员,但他从未向学校提出过“博士生导师”的要求,直到2002年,学校为了申报教育学原理博士点,请他“出山”,在教学论专业做博士生导师。2003年,教育学原理博士获得招生授权后,他才作为教育学原理专业的博士生导师正式招生。胡先生参加工作仅四年时间,1957年“反右”就运动开始了,他失去了作为教师的资格,下放劳动近二十年。平反后重返工作岗位十年,即告退休。这对他来讲,正式工作的时间太短暂了,而他需要做的事又太多、太大、太难,因而倍加珍惜,夜以继日地学习与工作。由于年龄原因,胡先生1987年退休,但他老当益壮,退而不休,仍然坚守工作岗位,教书育人,默默奉献,受到人们由衷的敬仰。胡先生求真理,做真人,视名利为浮云,甘于寂寞,以读书、研究为人生最大的快乐,因而能经历人生的风风雨雨,度过艰难岁月,经受考验,守望学术,最终收获学术上的丰硕成果。
二、严谨治学,追求真知
胡先生治学以严谨著称,其为学之道是,“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序,言之有文”,他主张“以广泛的阅读为基础,以深入的思考为主导”。他不仅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退休后,他潜心阅读与研究,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在系列专题研究的基础上,由点到面,渐成体系,用了10年时间撰写颇显功力的学术著作《教育学原理》,许多学校将这本书列入研究生必读书目。实际上,这本著作的“创作”从大学就开始了,立志、构想、思考与研究前后长达40年。胡先生自己也觉得该书的出版“拖的时间够长了”,并“引为抱歉与不安”,但他又解释说:“我有时也这么想,为了坚持学术的严肃性和质量为先的原则,以及考虑到我自己毕竟也还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思考、不断提高的缘故,我的这部著作,想早日付印面世,实际上不大可能,而倒有其晚出的必然性。甚至还可以这样说,这部书与其早出,还不如晚几年出更好,因为学因时进,20世纪90年代今天的我到底又多了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思考,思想和功力无疑会有所长进而更趋充实与成熟。”[2]3《教育学原理》的写作“十年磨一剑”,而我们今天为了考评,急功近利,“一年磨十剑”,因而难以磨成良剑。胡先生为学的严谨作风,值得我们学习与仿效。
胡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勤勉著述,讲学不辍,不妄言,不遮掩,求真务实的作风溢于言表,弥漫于字里行间。他将追求真理作为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与研究旨趣,其研究既有对现实的冷峻思考,又有对历史的回望总结,还有对未来的美好展望。
“文革”后,胡先生获得政治上的“解放”,重获研究的自由,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对我国教育中的现实问题,他直言不讳,充分发表意见,表现了一位教育学者的胆识与智慧。如他对共和国成立后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深刻反思与检讨,对邓小平的“三个面向”充分肯定和热烈欢呼,对全面发展理论深入讨论。胡先生1984年发表文章《我国教育工作的正确方向》,他指出:“种种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甚至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的言行,不仅直接关乎知识分子的利害得失,并且总是对教育事业干扰、破坏乃至明白的否定。它是社会主义之敌,现代化事业之敌,也是发展我国教育事业必须克服的第一个思想上的障碍”,“我以为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指示,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它解决了我国教育工作的根本方向和战略方针问题。”他在1982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生产目标与教育目标》一文中探讨了我们的教育目标,他指出,“多年来,我们党和政府曾发布过许多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方针,但对社会主义教育提出基本的任务,以作教育工作长期的依据和目标,似还不够明确。由于这个缘故,教育工作就容易为某些即兴的指示所左右,主观随意性就必然乘虚而入,唯意志论就容易盛行,理论上就一定混乱,实践上也一定会遭受损失,这已经是我们都清楚的历史教训”。关于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理论,1984年,胡先生发表文章《论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与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指出,“我们今天重新研究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个理论问题,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为了回答历史曾经给我们留下的课题。从积极意义上讲,当然是为了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科学和教育实践,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所要求的;而从消极意义上看,则也是总结我国30多年来教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的需要,是整个教育领域拨极“左”之乱,反马克思之正,从理论上正本清源的重要课题。”并深刻反省到:“从1957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为止,这20年左右时期中的种种教育措施,考察一下教育战线不断受到极“左”思潮、极“左”路线干扰破坏的历史,看看历年来有关教育工作的指示、决策、言论等等文献和提出的口号等,就不难看出,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特别是从1957年到1976年这20年中,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从其指导思想上来检查,可以说始终就没有得到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决,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也就长期没有纳入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1]242-244。这些话在现在看来可能算不上什么,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其反思与批判深刻而尖锐,讲这样的话需要足够的勇气、智慧和责任担当。
除了对现实的检讨和反思,胡先生还关注一些重大的历史事实、事件、人物的研究与评析,从历史研究中总结经验教训,透视历史之镜,引导现实,寄寓未来。胡先生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接受了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新知识的熏陶,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与教育有着特殊的情感,由此引发了他对我国教育历史发展的探究。胡先生1998年在《论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家》一文中回顾了中国上古时期、古代时期、近现代时期主要的教育家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评价了他们的贡献与影响,概括了不同时期教育家的学术思想、精神气质、特征类型。对容闳、雷沛鸿、韦善美等近代教育家作了专题研究,系统介绍、全面研究了教育事业改革家雷沛鸿的教育思想,著有《雷沛鸿与中国现代教育》一书,为雷沛鸿教育思想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胡先生2003年发表《论20世纪中国的教育改革》一文对20世纪不同时期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历史展开考察与探究,进行了总结与概括。对于这些宏大而复杂的历史课题,我们常常朦朦胧胧,雾里看花,说不清道不白,而先生视角独特,举重若轻,高屋建瓴,细读这些文章与著作,我们能从中获得历史的智慧与教益,让历史昭示未来,亦能让我们感受胡先生广阔的视野、宽厚的文化修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
还最值得一提的是,胡先生对中国第一批官派留美学生的研究。这项研究始于1986年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康涅狄格州州立中央大学,在访问与讲学期间,他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搜集了留学生在美国学习生活的第一手中英文珍贵资料。回国后,继续收集留学生们在国内的事业发展与人生命运等资料,用了十余年时间终于写成《容闳与中国第一批官派留美学生》一文。胡先生在给我们博士生上课时提到容闳及第一批留美学生的事情,后来我到他家拜访,闲聊中先生又提及此事,我也很感兴趣,于是他将一份书写工整的复写稿(不是复印而是复写,即用复写纸誊写后的稿子)拿给我看,厚厚一本,我翻了翻,叙述十分详尽,颇为惊奇,因为我从没有看到过这么长的稿子。胡先生说,三万五千字,篇幅太长了,不便在刊物上发表。我突然想起绵阳师专学报。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绵阳师专工作(2002年升格为绵阳师范学院),曾与学报是一个部门,相互之间很熟悉,于是当即表示,将稿子拿回绵阳,争取在绵阳师专学报上发表,胡先生答允了。我知道,这是胡先生辛勤劳动的成果,没有任何研究经费,完全是凭着自己的兴趣与历史责任感展开的一项研究,成果非常独特。当我将稿子拿给学报编辑部时,编辑部老师十分高兴,但审稿后他们也觉得文稿太长,而学报版面有制,只能发表该文前半部分。不能全文发表,我心理很内疚,觉得对不住胡先生。后来,我看到该文的后半部分《中国早期留美学生返国后的前程、事业与结局》于2002年在《甘肃社会科学》发表,这才放下心来。对于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胡先生文中提到“1986年,我以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康涅狄克州州立中央大学讲学,得知坐落在康州新港赫赫有名的耶鲁大学便是我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的母校,而当地正是当年容闳所率领的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生在美学习、生活的中心地带,因此更加注意阅读搜集有关中英文资料,并于是年12月17日下午2时,由康州中大华裔教授傅维宁博士陪同,专程驱车至哈德福城之西带山公墓,凭吊了长眠在那里绿荫深处已74个春秋的容闳博士碑墓,现在事情过去已多年了,但光景仿佛如昨,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心总觉得有一种责任需要把我所看到和搜集到的有关资料整理出来写成文章,公诸同好,这不仅对这位为中国近代化而努力了一生的先辈及其事业是一种应有的纪念,同时对我国留学教育也可借此提供或补充一点史料。我在此须郑重说明的是,我的这篇文字材料,许多地方参考了美籍华裔教授傅维宁博士所提供的材料和他写的有关文字。”[3]299在这里,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胡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与高度的学术责任。
三、独立思考,创新立说
理论研究需要沉思,没有独立而深入思考,就不可能有所创新与突破。胡先生特别强调独立思考和学术创新,他说:“理论研究要说理,要讲道理,教育理论研究是基于个体对教育现象问题的理性的思考,而不是盲从,从于权威,从于利益,从于时尚潮流,从于众口一词,或从于个人的滥情。”[4]他还说,“成就一件作品,需要愚笨和坚守,学术本来就是有闲者或清心寡欲者的人生取向,而学者治学的最高境界,就在于对学术的无穷乐趣,在学理上有所追求和不可压抑的激情。不抱任何功利的目的,即不以学术作为利禄的工具,却愿意为它付出毕生的精力。我以为,学问著作之事,既要相互观摩,彼此切磋,亦贵能孤往,既然不以时代群趋为是,就应由沉潜而千虑一得,以待来者。”[4]。胡先生在学习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好学深思,不轻易盲从苟同别人的说法,对学习的内容有着自己的认识与思考,具有自信自强的个性。胡先生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除了教学工作,他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学习、思考与探索上,他的研究范围几乎涉及所有的、最基本的教育理论问题,诸如教育的起源、存在形态,教育现象、本质、功能,教育、人和社会的关系,教育目标、内容,教育与自我教育,教育学的概念与教育学体系等重大问题。对这些问题他都发表过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见解独到、深刻,对教育学科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于教育的起源,胡先生质疑劳动起源说。他指出,劳动起源说的立论依据是恩格斯“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一旦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劳动起源说是对这句话的简单推演,存在着对恩格斯原意的误解,对劳动理解的简单化、机械化等问题。基于哲学上的需要理论,胡先生充分吸收文化学的研究成果,通过严格的论证,令人信服地得出“教育起源于人类社会生活需要”的结论。
关于教育的历史发展,胡先生进行了开创性考察。他检讨了有关教育历史阶段划分的理论,参照黑格尔、马克思的相关理论,考察整个人类教育长河后指出:纵观人类发展史,人类教育经历了自在教育和自为教育两个阶段,其中,自为教育阶段又可划分为初期、中期、全面自为阶段。他认为,从自在教育走向自为教育,是人类教育发展之必然。
关于教育现象,胡先生主张,探讨教育的本质,必先研究教育存在的形态即教育的现象问题,然而“翻开国内出版的教育学,几乎都少不了有教育本质一章,而教育现象则往往付之阙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值得我们为之补正”[3]138。他指出,“纵观人类自古迄今,以及世界各个地方、民族、国家的教育,我以为教育现象可概括为三种,一是教育活动,二是教育事业,三是教育意识现象或称教育意识形态,三者之间是紧密关联的。”[3]139胡先生对教育现象的理解十分独特,他对教育现象的划分得到学界广泛的赞同。
关于教育的本质与功能,胡先生认为,教育本质问题主要是基于对教育存在形态的功能和作用的揭示。由于文化传承是教育最基本的使命,因此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传承人类精神文化的手段和工具,教育的基本功能则是传承文化,将文化作用于人,使其成为“文化人”,既“成人”又“成才”,教育对人的作用及其结果最后体现为教育对社会的作用:提高民族的文化素养,为社会培养各级各类人才。
关于教育、人和社会的关系,胡先生经过反复的思考和深入的探索后,认为人与社会互为目的和手段,提出并论证了“以个体发展为基础,以社会进步为主导”的观点,纠正了人们长期在理论上将教育与人、教育与社会简单并列,在实践上只强调人的发展服务社会的倾向与偏颇。胡先生还认为,教育与人的关系问题主要属于教育活动的范畴,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主要属于教育事业的范畴。
关于教育学的概念与教育学体系,胡先生思考的时间很长,也思考得最多。他认为,教育学和教育科学是两个完全一致的概念,教育学不等于学校教育学,它也不是一本书或单一学科所能包容的,教育学是以一门所有教育现象为研究对象,是由众多分支学科组成的学科群(胡先生在《教育学原理》一书中对教育学科群进行了全面的勾画)。《教育学原理》一书的出版实现了他教育学体系构建的学术梦想,为教育学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此外,胡先生曾担任西北师范大学首任民族教育研究所所长,在担任所长期间,他对民族教育问题做了较多的关注与研究,进行了实地考察、调查研究和理论探索。他和夫人蒋小素副研究员编著了《甘肃省民族教育大事记》(1949-1983),以大事记的形式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甘肃省民族教育发展的历史。他明确提出“民族教育就是民族地区教育”的思想,澄清了人们对“民族教育”概念的模糊认识。他总结共和国民族教育工作的经验,提出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策略与路径,对于民族教育事业与民族教育理论的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
胡先生特别注重学术创新,他在给刘庆昌教授的《教育者的哲学》一书中序言中有一段自我表白,他写道:“多年来总的说,我比较偏好读学术性、理论性或学术性、理论性较强的文字,没有多少学术性理论性的文字有时免不了也看,但看过后,总觉余味有限,值得留下思考的意蕴不多,多年来,我正是在这种学术心态的支配下,自觉不自觉地所找所读的书竟为文、史、哲等方面的论著居多而教育类的文字相对比例倒较小。当然这也不是说,凡是学术性理论性强一点的文字我一概爱不释手,而是还有选择,那就是,我又只欣赏那些确有自己的思想见解、有一定创见的东西。”[3]390阅读胡先生的著作与文章时,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字里行间流淌着的他的学术思想与创新气质。
四、学贯中西,融通古今
胡先生强调,教育学术研究要有宽广的胸怀,要观全局,把握整体,并富有激情,“好学深思、知书达理的读书人,应该站得高、看得远,走向大系统、大思路、大视野,在精神上当有一股‘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豪气与激情。”[5]2胡先生阅读量很大,既有中国思想家的著作,又有西方哲人经典,这些著作关涉众多科学,领域十分宽广,从而使他具有思路广阔、视野开阔的学术气质。无论在教学活动还是写作过程中,他总是古今中外,纵横驰骋,引经据典,随手拈来,令人折服不已。
1942年,胡先生进入初中,他对书本和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读书中获得极大的乐趣。大学时代,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特别的兴趣,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的同班同学顾明远先生说“他在学习的时候,好学深思、刻苦钻研,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是我们班上的优秀者”。毕业工作不久,“反右”运动开始,他被打成“右派”,但他并没有悲观绝望,没有放弃学习与思考,而是在“劳动改造”中阅读了大量的文史哲和英语著作,拓展了学术研究的视野,因而能“有极高的造诣和深邃的创见”。可以说,胡先生的学术创建得益于他广泛的阅读、深入的思考与广阔的理论背景。
在西方学术方面,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阅读与深入研究,胡先生特别欣赏西方存在主义、生命哲学、解释学、人本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他广泛地猎涉了黑格尔、萨特、海德格尔、尼采、叔本华、伽达默尔等思想家的著作,涉足的哲学、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系统论、进化论、结构主义、人本理论等学术,逐步形成了自己对自然、世界、社会、人生的理解与看法,为思考教育学、研究教育理论、建立宏阔的教育学体系奠定了坚实而宽厚的理论基础。
在中国学术方面,胡先生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历史、文化与哲学经典,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思想资源,特别是对中国文化与哲学的研究尤为深入,国学功底深厚。胡先生在上课过程中,为了阐释、说明有关教育理论与现实问题,他常常引用我国古代经典,如孔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朱熹、张载等人的作品,充分显示了他扎实的国学功底。如在讨论教育与自我教育的关系时,他创造性地使用易经“太极图”,说明教育与自我教育相互依存、相互消长、循环不已的辩证关系,复杂、美妙的关系,通过一副太极图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再也没有比这种表达形式更为直观灵动的了。胡先生还向我们介绍了王国维、胡适、陈寅恪、冯友兰等大思想家、哲学家的研究著述和学术观点,开阔了我们的学术眼界,使我这个“门外汉”对国学发生了一点兴趣。记得胡先生说过,中国儒家思想集中体现在“十三经”之中。在胡先生的影响下,我曾在兰州市滨河路的古籍书店购买了一套精装繁体的《十三经注疏》用来“补课”。因为,我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传统文化被视为“封建主义毒草”,外国文化属于“资产阶级思想”,统统需要铲除掉。此外,还要“斗私”“批修”。这样,我们这一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就尤为贫乏,仅仅局限于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几篇古文和现代文中零星的那点国学常识,对于自己的老祖宗文化知之甚少。购买、阅读《十三经注疏》可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但遗憾的是,由于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去阅读、欣赏,厚厚的两大部至今还躺在我的书架上没有动过,只有等待退休后去读了。
胡先生古今结合,注重吸收传统思想精华探讨当代教育问题,阐发自己的学术观点。他在讨论人生与教师修养问题时,着重考察了“修养”一词的演变与发展、本质与内涵、文化渊源、时代价值,从人生到教师,从人生价值到教师作用,从人生修养到教师修养,层层展开,不断深入。基于人生修养的探讨,他将教师的职业修养提升到人生观、价值观的高度,大大地拓展与深化了我们对教师修养的认识,这与今天我们仅仅在知识、技艺层面讨论教师专业成长,大异其趣。胡先生的讨论更有深度,视野也更加广阔,如何在更高、更广的层面与范围讨论教师专业成长问题,胡先生开辟的从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入手的路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统和研究视角。
不仅如此,胡先生还推陈出新,发扬光大,对于传统哲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如关于孔子的学说,“作为思想家的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一个‘仁’字,而‘爱人’是‘仁’的本质含义。”“把握孔子这位思想家的中心思想‘仁’,主要仍在自立、立人,自达、达人这个基点上。即应把握住‘自己’与‘他人’这两个根本方面。而且还可以据此精神进一步拓展开来,如自爱、爱人,自尊、尊人,自信、信人,自强、强人等诸多方面。这就是说,作为一个仁者,首先要自爱、自尊、自信、自达、自立、自强,并且还要懂得并做到爱人、尊人、信人、达人、立人、强人。只有这两个方面都做到了,才算达到了‘爱人’的‘仁’的要求,而前者如自爱、自尊、自立、自强是根本,是为仁也即为人者的根本条件。后者如爱人、尊人、立人、强人等方面是‘推己及人’的要求和结果,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3]369又如,关于修养的概念及其地位问题,他说:“在笔者看来,人们如果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认识,必须对修养这个概念及有关思想理论首先把握住,而如果真的在思想理论上对修养问题有所认识了,那也就可以说对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有了基本的把握。不仅懂得中国传统文化是传统修养的背景,而且明白正是传统的修养反过来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多年来,国内有些伦理学专著中,把修养仅仅视为道德教育的一种方法,坦率地说,笔者对此是不敢苟同的。”[3]367-368这些见解十分深刻、精辟。
正是学贯中西,融通古今,胡先生的学术研究与理论建构才获得丰富的思想资源、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宽广的学术视野,也才能产生精辟独到的学术见解,建构别树一帜的教育学理论体系。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胡德海先生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较高的抽象思维和思辨能力去选择中、西文化现有的思想成果,塑造出一种新的、富有创见的、思维缜密的教育学理论体系。胡先生用哲学、文化学和人类学理论阐释教育的起源;以系统论的方法构建教育学体系;用进化论的思想探讨教育的基本理论;用结构学原理分析教育事业的结构;运用结构主义原理剖析教育的本质和功能;用人本理论诠释教育的价值取向。[6]这一评述是十分中肯的。
五、循循善诱,深入浅出
胡先生长期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教书育人是他的天职,教育工作对他有着特殊的意义,他对教育工作也具有特别的情怀。
1949年初,高中毕业后的他应聘到浙江金华汤溪私立二中,做过一个学期的教师,初次尝到了教书的乐趣。1953年,胡先生大学毕业,怀揣梦想到西北师大任教。“文革”后的1978年代,安排到西北师大附属中学执教英语和语文。1980年胡先生获得政治上的“解放”,重返西北师范大学教坛,为本科生、研究生上课,此后一直没有离开过教学岗位。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坎坷的人生境遇,磨练了他坚忍顽强的意志,造就了他自强不息的个性,同时也还锻炼了他的身体素质(胡先生的夫人蒋小素老师曾对我说,胡老师以前身体很单薄,1957年打成“右派”后,下放到“五七干校”,天天劳动,他的身体慢慢地强壮起来)。胡先生乐观地面对人生的不幸,他以读书来打发时光,提升自己,追逐梦想,他在阅读中找到生活的乐趣,养成广泛阅读、勤于思考的习惯。
对于教学工作,胡先生恪尽职守,认真不苟,精益求精。每次上课,胡先生总是提前到达,准时上课,按时下课,在同学们的印象中,他的课从来没有耽搁过。胡先生精神饱满,习惯站着讲课,讲话铿锵有力,中气很足。他严肃认真,不苟言笑,温和儒雅,宽厚仁爱,同学们从未见过他发脾气。胡先生的课很有特色,他将教学与研究合而为一,他所讲的内容就是他思考、研究的东西,每次上课,同学们都能分享到他的研究成果,他的讲授过程就是一个学术思考与探索的过程。他坚持问题导向,常常带着问题授课,或针对现实中的问题,或针对理论中的问题,进行探究批判,既回顾历史,又抨击时弊,在此基础上阐发自己的观点,因而总能吸引学生,同学们兴趣盎然。胡先生的教学与他的学术研究一样,不断创新,超越自我,《教育学原理》一课,我在硕士生、博士生阶段各上过一次,他每次都有新的见解,我们都有新的收获。
在课堂上,胡先生常常发人之未发,带给学生新的思考,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教育问题,体验教育学术智慧的创造过程。在课堂外,如果有什么疑问向他请教,他总是那么热情、耐心地为你指点迷津,解开你心中的迷团,让你看到问题的来龙去脉与事物的实质所在。记得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周末有时到他家去玩,请教学习上的问题,他给了我不少指点和帮助。我硕士论文的题目是“活动教学研究”,由于选题较新,研究文献太少,在写作过程中产生了不是困惑,专门到他家就论文提纲问题向他请教:是将“概念界定”放在前面还是将“历史发展”放在前面,如何界说活动教学,他帮我分析不同做法各自的优点与问题,最后建议将“概念界定”放在论文的第一部分,还就论文提纲的其他问题提出了宝贵意见。他赞同我将教学形态分为“系统教学”与“活动教学”,给我许多鼓励(需要提及的是,我曾打算放弃该题目,改写“教学论教材比较”,但当时在读的徐继存博士说,教材比较缺乏理论上的根据,所以做罢)。
胡先生厚积薄发,深入浅出,他常常将抽象深奥的道理以形象生动的语言加以表达,使枯燥难懂的东西轻松易懂。如在讲解“人的本质”时,胡先生从文化学、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人的本质,认为人是“复杂的肉体与文化的综合体”,他形象地说,人出生时十分柔弱,只会哭叫吃奶,后来在家庭、学校、社会中获得知识与文化,文化与肉体结合使人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转变成为有文化的社会人,他在黑板上写下公式:人=肉体+文化。在这个意义上看,教育即传递文化、培养人的活动。在讲述“教育的产生”时,胡先生将人类文明发展50万年的历史浓缩为50年,他说:“如果我们依靠想象而将过去的50万年缩减为50年,那么,根据这个假定,人类需要49年才懂得完全放弃长期形成的游猎习惯而定居在村落里。在第50万年头的前半年里,出现了书写,这还只是在有限的地区内,从而提供了保存和传播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希腊人取得的成就,仅仅是后三个月的事情,基督教盛行于世,是在后两个月,印刷术的发明,约有二周之久,人类使用蒸气机还不到一个星期,而形成我们现在生活的特殊环境,直到第50年的12月31日才出现。人类之所以在大自然中获得如此无与伦比的巨大进步,就在于出现了‘文化’这一人类所独有的现象。文化是人对自身生物性和大自然的加工,它对人的生物特性和自然界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和调整。”[3]12050万年的历史经过他这么叙述就清晰易解了。在讨论大学教师的业务素质时,胡先生这样说:“大学教师的知识结构,应由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新兴学科知识三部分组成。就像一棵树,基础知识是树根,专业知识是树干,新兴学科知识是树的枝叶。树根交织如网,盘根错节,深扎沃土,除了稳定树干外,还时刻为树干输送丰富的养分。树的枝叶形状如伞,进行着光合作用,为树干输送养料。而树干的壮大,又促进了树根和树叶的生长”。[7]303
胡先生善于引导学生学习,他要求学生在不同学习阶段,追求不同的发展目标。他说:文化知识具有三个层次:常识、知识、思想,小学学习常识,中学学习知识,大学学习思想。我后来在给研究生、博士生上课时对胡先生的这句话中的第三句进行了演绎:本科生阶段学习专业知识,开拓知识眼界,研究生阶段学习专业理论,进行学术训练,而博士生阶段学习专业思想,开展学术创造。胡先生鼓励弟子创造,他对思想创造做过一句精彩的概括,他说,思想家一生的创见与思想,都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其余的话无非是这句话的阐释与注解。笔者认为,胡先生的这一概括,非常到位,他启迪我们:学习某一理论、学派,不要被表面文字所迷惑,要着力把握其精髓,注意透过文字表达领会其精神实质。再进一步讲,我们的学术思考与研究,不要太泛,要适当聚焦,围绕一个问题展开持续、深入的研究,并形成自己的创见与观点。胡先生鼓励弟子独立的学习与研究,他常常说,“路是自己走出来的,道理是自己认识的,学术结论是靠自己研究得来的”。同时,胡先生十分强调研究者的理论素养对于学生研究的意义,他说,“理论素养不足,对于一个学教育学的人来说,只能意味着短视和偏见,也就等于患了先天性‘理论贫乏症’,其发展前途必然是极其有限的”[2]3。对于我们这些从事教育学术研究的人,这一告诫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胡先生除了自己读书、思考、研究与教学,还他十分关心学生的专业成长和事业发展,关心他们的生活与工作。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孙丽华博士曾打算来扬州大学工作,胡先生亲自打电话给我,要我向学院推荐,提供帮助和方便,我非常感动。胡先生为了弟子的成长呕心沥血,孜孜不倦,80高龄的他还在认真审阅弟子的论文,提出修改意见,仔细阅读弟子的作品,亲自执笔作序。除了关心自己的学生弟子,还十分注重提携后学,支持其他青年学者的学术研究,如受邀给素不相识、当时在洛阳师专工作的刘尧的《教育评论学研究》专辑撰写文章,鼓励刘尧的学术研究,并客气地称其为“先生”,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跃然纸上。胡先生谦和、洒脱、正直、坦诚,求真理,做真人,特立独行,他执著的学术追求,宽厚的学术修养,卓越的学术成就,高尚的学术品格,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值得我们效法、光扬。
[1]高闰青.胡德海教育思想研究[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
[2]胡德海.教育学原理[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8:前言.
[3]胡德海.教育理念的沉思与言说[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4]胡德海.置身于教育学术的天地[J].高等理科教育,2010,(3).
[5]胡德海.教育学原理(简缩版)[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前言.
[6]高闰青.在阐释中生成意义——胡德海教育学思想的学术造诣[J].当代教育与文化,2009,(3).
[7]胡德海.人生与教师修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王鉴/校对王明娣)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HU Dehai’s Academic Style
PAN Hong-jian
(School of Education,Mianyang Normal College,Mianyang,Sichuan,621050,PRC )
Mr.Hu Dehai,a famous educationist in contemporary China,has put forward many unique academic views in many fields,especiallybasic educational theories,and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al theories in our country.His academic characters and scholarly style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Firstly,he has dedicated himselfto academic studies,showing no interests in pursuing fame and wealth.Secondly,he has rigorously followed the academic norms in conducting research and is always seeking fortruth.Thirdly,he thinks independently,and opts to innovate and establish new theories.Fourthly,he has mastered a broadrange of knowledge,western and oriental, as well as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Lastly,he is good at giving systematic guidance and explain profound theories in simple language.Studying Mr Hu’s educational thoughts and academic styleis of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our country.
Hu Dehai;educational thoughts,academic style
2016-08-15
潘洪建(1964—),男,四川苍溪人,教育学博士,绵阳师范学院特聘教授,扬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G 40
A
1674-5779(2016)05-0038-09
——《教育学原理研究》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