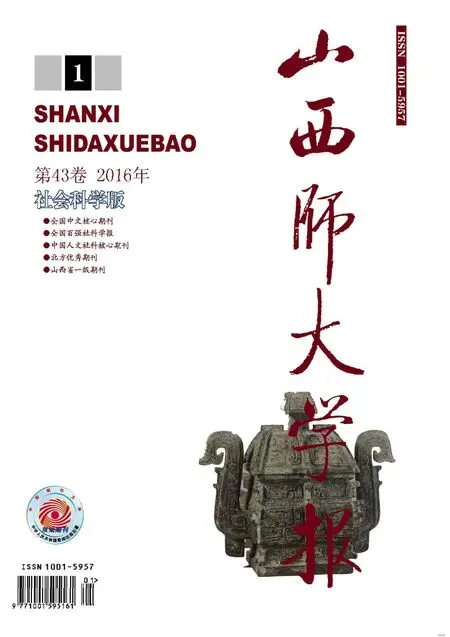批评性话语分析特点及发展趋势
胡 燕,孙咏梅
(1.北京协和医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北京 100005;2.首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9)
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旨在分析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不仅研究语言是什么,而且研究语言为什么是这样;不仅对话语的意义感兴趣,而且对话语如何产生这种意义感兴趣。它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揭示意识形态对语篇的影响,语篇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以及二者是如何源于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又是如何为之服务的。[1]批评性话语分析是对主流语言学的反叛和补充。20世纪,语言学研究的主流学派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形式主义语言学,他们认为语言是抽象的、封闭的、静止的、自足自在的系统,将语言与社会割裂开来,提出二元对立的语言研究模式,如语言与言语、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横聚合与纵聚合、语言能力与语言使用等。批评性话语分析完全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将语言研究与其社会功能联系起来,使语言研究由静态走向了动态。
1979年,R. Fowler在Language and Control一书中首次提出批评性话语分析这种语言研究方法。1989年,Fairclough的《语言与权力》、Wodak的《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批评性话语分析逐渐走向成熟。至今,批评性话语分析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萌芽到壮大的发展过程。本文将分析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特点,探究其面临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趋势,希望能为国内从事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学者提供些许借鉴。
一、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特点
(一)研究目标的明确性。批评性话语分析关注社会中的不平等、不公正现象,揭示语言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并致力于改进这种不平等。批评性话语分析不仅仅是分析,更是批评,通过分析语篇中的语言形式来揭示那些隐含的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以及统治阶级如何运用语言来实施意识形态控制和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2]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目标是探索社会政治语境中的话语交流是如何被实施和复制的,如何被用于抵制社会中的支配、控制和不平等以及权力的滥用等。[3]
(二)研究范围的广泛性。批评性话语分析旨在探索话语中呈现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因而任何话语中明显或者隐含的权力和控制关系都构成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研究内容。批评性话语分析不仅关注与性别、年龄、种族、阶级等社会因素密切相关的大众语篇和政治语篇,还关注教育、医疗、商业等机构话语中不同社会角色所隐含的权力和不平等。Blommaert将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研究领域总结为:政治话语研究、意识形态研究、种族研究、与种族有关的移民话语研究、经济话语研究、广告话语与推销研究、媒介语言、性别研究、机构话语、社会工作话语、官僚话语、教育话语等。[4]在如此广泛的研究领域中,批评性话语分析经常考查的主题包括: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就业和司法上的不平等,战争、核武器和核力量,政治策略和商业行为,等等。[5]
(三)研究领域的跨学科性。为了确切理解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批评性话语分析家注重吸收社会学、语言学、认知科学等不同学科的合理内核,通过调节不同理论,特别是社会学和语言学理论,实施理论整合。[6]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任务就是要超越社会学理论对文本分析不足和语言学理论对社会学理论问题探索不够这一状况,并通过“内化”使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7]
批评性话语分析借鉴了相关的社会学理论,例如,批评性话语分析借鉴了Gramsci的霸权理论,认为文明社会是靠“霸权”,也即赢得大多数人的同意或默许来维持现行体制和制度,强调意识形态能够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有效的控制,从而关注电视、报刊等大众媒体如何对社会成员实施控制的。而Foucault的话语理论使批评性话语分析家认识到话语与权力是一种辩证的同构关系,话语既是权力的产物又是权力的组成部分。同时,Harbermas的交往行为理论,提出批评科学必须关注语言和社会交际的关系,其话语评价标准为批评性话语分析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语言学领域,批评性话语分析主要借鉴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它是一个将语言和社会语境联系起来的多功能的理论,非常适合语篇分析。[8]此外,系统功能语言学也关心语言作为“社会符号”受制于社会结构的同时又反过来建构社会的现象。功能语言学为批评性话语分析提供坚实的分析基础,使批评在语言分析中“扎根”。批评性话语分析除了吸收社会学理论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还借鉴了社会符号学、认知科学、心理学、语用学、文体学、修辞和会话分析等学科的研究成果。
(四)研究流派的多样性。由于借鉴理论不同,在批评性话语分析内部形成了不同的派别,例如,Fairclough的三维分析框架、Wodak的话语- 历史分析方法以及van Dijk的社会认知研究模式。这三个流派从不同角度探究语言背后隐藏的权力和意识形态,为批评性话语分析提供多维和全面的分析视角。
Fairclough的三维分析框架试图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范式。Fairclough把文本、交际和社会语境看作是话语的三大要素,据此提出了三维分析框架,即语篇、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语篇是话语实践的产物,这个过程包括语篇的“生成”、“传播”和“接受”,所有这些都是由特定的社会实践条件决定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三个层次:“描写”语篇的形式结构特征,也即文本分析,包括对语言运用和话语交际的分析,多运用系统功能语法进行语言学描述;“阐释”语篇与话语实践过程的关系,是描述和解释层面的中介;“解释”话语实践过程和它的语境之间的关系,分析权力、不平等现象,揭示权力和意识形态如何产生作用。接着,Fairclough & Chouliaraki提出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五个步骤:第一,锁定一个与话语有关的社会问题;第二,通过对话语所在的社会实践网络、话语与该社会实践中其他成分之间关系的分析以及话语本身的分析,确定处理该问题的难点;第三,考虑解决该问题是否涉及社会秩序;第四,确定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五,进行批判性反思。[7]Fairclough的话语分析模式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是批评性话语分析学派中最系统和完善的,为大众语篇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Wodak的话语—历史分析方法,把话语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研究。Wodak把话语定义为“从某一特定角度,表示某一特定社会实践领域的意义”,这一定义与Fairclough的话语定义相似。Wodak & Weiss认为,社会现象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因果关系。话语实践与其所处的行为场域存在一种辩证关系。在这种建构与被建构过程中,语境是一个重要因素,该分析框架把语境分成四个层次:语言和文本内在的上下文关系,语段、文本、体裁和话语间的文本和话语间性关系,语言外在的社会学变量以及语境涉及的机构框架,更为宽泛的社会历史语境。语境的四个层次对应着分析框架的四个分析层面:语言分析、话语理论、中等程度理论和宏大理论。第一个层面是描述性的,其他三个层面的分析旨在建构一种语境理论。Wodak借语用学的观点和方法发展了四步分析策略:第一,确定一个与种族或歧视等话语相关的话语主题;第二,考察话语中使用的话语策略;第三,分析语言特征;第四,对特定语境中的语言进行形式分析。[9]
van Dijk倡导社会认知模式,并建构“话语—认知—社会”话语分析的三角模式。在van Dijk看来,话语与社会结构是由“社会认知”这一媒介联系起来的。这里的社会认知强调了人类认知的社会性与群体性,常指比较抽象的思想观念、信仰系统和意识形态等,主要通过语篇来习得并付诸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得以修正。话语是一个交际事件,是各种意义的表现形式,包括互动话语、书写文本以及相关的手势、面部表情、印刷布局以及其他符号等。[10]
二、批评性话语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
批评性话语分析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这种通过语言分析来批判社会现实的研究视角也招致不少批评和争议。批评的主要争议可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过于关注社会现实中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批评性话语分析通过分析大量真实具体的语料,向人们揭示隐藏在话语中的权势和不平等,同时致力于改进这种不平等。然而,这种方法在一些语言学家看来是消极的。Caldas- Coulthard & Coulthard率先表达了对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不满,希望一向“侧重于政治的”批评性话语分析家们能够“影响世界、改造世界,并帮助创建一个没有性别歧视、肤色、种族、年龄和社会阶级歧视的世界”。[11]Kress指责批评性话语分析只是对有关的社会组织、社会行为和涉及的人进行批评,但没有提出过任何积极的改进方法。[12]之后,Kress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到,有必要对语篇分析提出一个“新的目标,不是批评,而是设计”。所谓设计,就是抛开前人的消极做法,通过有意识的语篇分析,规划一个美好的未来。[13]Luke也主张“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形势下以建设性的方式使用权力”。[14]
二是对话语的解释缺乏客观性和系统性。Widdowson[15], Stubbs[16], Toolan[17]等学者指出,批评性话语分析所研究的文本数量有限,缺乏代表性,对话语的解释缺乏客观性和系统性;批评性话语分析家带着某种政治目的在语篇中寻找语言证据,因而不可能做到他们自己所声称的在“认真的”、“严格的”、“系统的”语篇分析基础上进行社会批判。
因此,面对批评和质疑,语言学家身体力行,积极探索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新方向。
首先,与积极话语分析相结合。针对批评性话语分析过于消极的指责,语言学家探索更为积极的话语分析。Martin指出,仅仅满足于揭露和批判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他主张话语分析应该采取积极友好的态度。这个积极友好,不仅适用于自己和自己一方的人,而且适用于自己的对立一方,其目标在于通过这样的分析,朝着“和平语言学”的远大目标努力,最终建成一个宽松、和解、共处的人类社会。他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能与批评话语分析彼此互补的“积极话语分析”体系。[18]自上世纪90年代末,Martin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了积极话语分析的动机、语料选择和分析方法,得到了 Wodak等人的积极支持和热烈响应。
积极话语分析家主张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各种社会矛盾,希望通过话语分析创建一个和谐社会,而不是推翻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根基和分析方法。因此,积极话语分析可以被看作是对批评话语分析的补充和延伸。Martin在一篇论文中对比了澳大利亚两位总理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态度。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为了土著儿童能够接受所谓的先进教育,强行把他们从父母身边带走交给陌生白人家庭抚养,这一事件给土著儿童和家长造成极大的伤害。Martin运用积极话语分析对澳大利亚总理Keating的发言进行分析发现,Keating将事件的所有责任都归咎于白人,勇敢地承担起历史责任,以期得到受害者的宽容,达到和解的目的。[19]然而,针对同一事件,另一位澳大利亚总理Howard却拒绝以政府名义向土著民道歉,Martin采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发现Howard极力推卸责任,只愿意以个人的名义表示道歉。对Howard总理的批判凸显了Keating总理勇于承担责任、寻求和解的积极态度。由此可见,批评性话语分析是解构,而积极性话语分析是建构,解构是为了建构,建构以解构为前提,积极话语分析的“和平语言学”目标便是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最终目标。
其次,与语料库语言学方法相结合。为了弥补文本数量不足的缺陷,20世纪90年代,一些语言学家开始尝试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进行批评性话语分析。语料库语言学方法的优势在于其强大的量化分析,将其运用到批评性话语分析中,有助于弥补文本数量的不足,同时有助于人们探究语言使用过程中不同的现实建构方式,揭示语言使用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Mautner最先倡导运用语料库技术进行批评话语分析,她认为语料库索引功能有效打破了定量与定性研究的界限,语料库提供了强大的量化分析的基础。[20]其他学者如Stubbs[21]、Baker & McEnery[22]、Piper[23]等运用语料库中的词频、词语搭配、主题词等技术分析新闻语篇中隐藏的意识形态以及话语建构方式,揭示了社会的不平等。国内的学者也在关注语料库语言学与批评性话语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趋势,例如,有些学者探索语料库技术在批判话语分析研究中的作为空间[24]及有效运用的方式[25],另外一些学者运用语料库技术研究翻译行为中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26],或者探讨话语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27]。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过程中运用语料库语言学方法,有助于增加话语的样本数量,有助于更加客观、系统地解释话语,从而得出规律性的结论。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批评性话语分析取得了丰硕成果,对语言研究贡献巨大,它清楚地阐释了语言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加深了人们对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互动关系的认识。同时,批评性话语分析也因其存在的问题而遭受非难。面对质疑和批评,语言学家不断探索新的理论和方法,推动批评性话语分析朝着纵深方向发展,以建构和谐世界为目的的积极话语分析和以量化分析为基础的语料库语言学方法代表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研究的新方向。
[1] 廖益清.批评话语分析综述 [J]. 集美大学学报,2000,(1).
[2] Fairclough N.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New York: Longman, 1989.
[3] van Dijk, T. Multidisciplinary CDA: A plea for diversity.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1.
[4] Blomaert, J. Discours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UP,2005:26.
[5] 辛斌.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6] Chouliaraki, L and Fairclough, N.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16.
[7] Fairclough N. Analysis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8] Fairclough 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New York: Longman Publishing, 1995.
[9] Weiss G, Wodak 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Palgrave, 2003:22.
[10] van Dijk. Ide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Study. London: Sage, 1998.
[11] Caldas- Coulthard, C. & M. Coulthard (eds.). Preface. Text and Practices: Reading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xi- xii, 1996.
[12] Kress, G. Represent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questions for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In Caldas- Coulthard & Coulthard (eds.), Texts and Practice: Reading in Critical Analysis 1996:15~31.
[13] Kress, G. Design and transformation: new theories of meaning. In W. Cope & M. Kalantzis (Eds.). Multiliteracies: literacy learning and the design of social futures. London: Routledge, 2000.
[14] Luke, A. Beyond science and ideology critique: Development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Vol. 22, 2002.
[15] Widdowson, H. G. Discourse Analysis: A Critical View.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996,(1):57~69.
[16] Stubbs M. Whorf's children: Critical comments o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A. Ryan & A. Wray (eds.) Evolving Models of Language.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BAAL, 1997.
[17] Toolan, M. 1997. What i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Why are People Saying Such Terrible Things About it?. In Toolan (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 (vol.III) 2002.
[18] Martin JR. Negotiating difference: ideology and reconciliation. in M. Pütz, J. N. van Aertselaer & T. A. van Dijk (Eds.). Communicating Ideology: Language, Discourse and Social Practice. Frankfurt: Peter Lang, 2004b.
[19] Martin JR. 2004a.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solidarity and change. Revista Canaria de Estudios Ingleses. 49:179~200.
[20] Hardt Mautner G. ‘Only connec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rpus Linguistics (UCREL Technical Paper 6) . Lancaster: University of Lancaster, 1995.
[21] Stubbs M. Text and Corpus Analysis. Oxford: Blackwell, 1996.
[22] Baker P, A McEnery. A corpus- based approach to discourse of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 in UN and newspaper text. Language and Politics, 2005.
[23] Piper A. Some have credit cards and others have giro cheques: ‘Individuals’ and ‘people’ as lifelong learners in late modernity. Discourse and Society, 2000.
[24] 唐丽萍.语料库语言学在批评话语分析中的作为空间 [J].外国语,2011,(4).
[25] 钱毓芳.语料库与批判话语分析 [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3).
[26] 朱晓敏.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的《政府工作报告》英译研究——基于语料库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考察 [J] .外语研究,2011,(2).
[27] 钱毓芳,田海龙.话语与中国社会变迁:以政府工作报告为例 [J].外语与外语研究,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