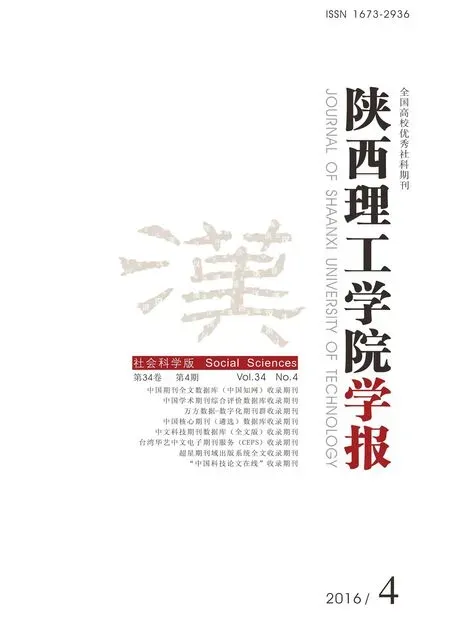周炳垣与《汉南杂咏》
熊 黎 明
(汉中市人民检察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周炳垣与《汉南杂咏》
熊 黎 明
(汉中市人民检察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周炳垣,一位亲身经历了太平天国西征军转战汉中的退休官员,避难四川后,他用一百首纪事长诗讲述了汉中的战事,揭露了汉中官吏的腐败,反映了尖锐的社会矛盾。这些诗后来被完整地收录于《汉南杂咏》一书中,但之后的县志对周炳垣的这些诗进行了大量删减,以致难睹全貌。《汉南杂咏》不仅收录了周炳垣的诗作,还收录了东海新吾氏对周炳垣诗作的注释,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版本价值。由《褒城周氏族谱》等文献可进一步了解周炳垣生平并考知《汉南杂咏》的成书时间当在1882年初夏。
周炳垣; 《汉南杂咏》; 《褒城周氏族谱》
清同治二年(1863)八月二十日,太平军攻占汉中郡城(今汉台区城区,旧称南郑县城),对当地经济社会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但这作为汉中历史上一件大事,并未引起史学界的足够重视。如梁中效教授在《太平天国西征军暨李蓝义军陕南战事史料汇编》一书序言中指出:“这是汉中及川陕近代化征程上不得不面对的历史事件,以往学术界关注不够,甚至在太平天国研究领域,还有人认为太平军未到陕西。”[1]1其实,作为汉中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无论汉中地方文献还是全国性文献对此都有记载,但数量不多,且大多散见于解放前汉中出版的少量专著及县志资料中,《汉南杂咏》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珍贵史料之一。该书的主要作者周炳垣是汉中人,亲身经历了太平军攻打汉中事件。事后,他以“居围城数月”[1]159在野官吏的视角,用百首纪事长诗客观真实的讲述了官兵与太平军作战过程及失败的原因,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记录太平军在汉中地区活动的民间地方史料,囿于个人立场,他称太平军为“贼”,但这并未影响该书的史料价值。
一、 《汉南杂咏》及《褒城周氏族谱》
《汉南杂咏》存世稀少,且未能引起研究者广泛关注。2014年,笔者有幸觅得线装木刻本《汉南杂咏》,经简单点校整理,业已刊印。在整理《汉南杂咏》过程中,笔者一直在搜寻“周炳垣”的有关资料,但资料极度匮乏,仅1991年出版的《太平军在汉中》和1993年出版的《续修南郑县志校注》两书中略有提及。不久前,笔者有幸搜得周炳垣的族谱《褒城周氏族谱》,通过族谱,笔者对《汉南杂咏》一书及其作者周炳垣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此谱于民国七年编纂,民国八年付梓,为线装石印本,正文一半页12行32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封面有清末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城固人田明德篆书“褒城周氏族谱”题名。卷首有序言、凡例,全书上下两卷合为一册。上卷为世系图第一、世系表第二;下卷为族居记第三,茔墓图第四,言行录第五,艺文录第六。族谱的编纂者为褒城周家第十四代子孙周菼(字伯言),此人系周炳垣族曾孙,清光绪丁酉(1897)科拔贡,历任四川省绵竹、邛崃等地知县知州,与田明德等人私交甚密。据《褒城周氏族谱》记载:周家世居汉中褒城县(该县1958年撤销),其“先世多隐于农”①周菼编纂.褒城周氏族谱·言行录[M].民国八年(1919)刊印.页四.,繁衍生息至周炳垣已是第十一代。此时,周家逐渐开始兴旺,人才辈出,周炳垣的父亲周兆熊(字渭占)系乡里秀才;周炳垣兄弟六人,炳垣排行老三,大哥周益隆(字祜庭)为附贡生,“以老儒终乡里”②周菼编纂.褒城周氏族谱·言行录[M].民国八年(1919)刊印.页四.;二哥周百揆(字时叙)系廪生,曾任福建省莆田县知县等职;周益隆的儿子周锡龄(字与九,号东渠)系增贡生,长期在四川省盐源、泸州等地为官,曾升任四川宁远府知府。汉中被太平军攻克后,周炳垣“挈家”避难于其侄子周锡龄处,周锡龄即周菼的祖父,或因如此,族谱中较为详细的记录了周炳垣的生平信息。周家虽“贤哲代兴,蔚为望族”③周菼编纂.褒城周氏族谱·卷首[M].民国八年(1919)刊印.页一.,在外地为官者亦多,但一直未修族谱,直至民国戊午年(1918),周菼“奉讳回籍葬亲,兵警不得归,遂绕道游大江南北。至冬,溯岷江而上,岁聿云暮,萧憀岑寂,乃成族谱一书”。④周菼编纂.褒城周氏族谱·卷首[M].民国八年(1919)刊印.页二.该谱为我们了解周炳垣和研究周氏家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 关于周炳垣其人
《褒城周氏族谱》中记载:“炳垣,渭占公三子,字午峰,道光丁酉科举人,选授直隶涞水县知县,诰授奉政大夫。嘉庆己已十一月十七日生,同治戊辰年三月二十一日卒,葬黄土地。”⑤周菼编纂.褒城周氏族谱·世系表[M].民国八年(1919)刊印.页十七.可知周炳垣出生于嘉庆十四年(1809),道光十七年(1837)中举,旋任涞水县知县,逝世于同治七年(1868),享年59岁,葬于褒城县黄土地。在同辈中,尽管周家“学而优”者颇多,但多为“贡生”、“廪生”之类,周炳垣是唯一的举人出身,由此可见其才华出众。
族谱中不仅载明了周炳垣的生卒等基本信息,在“言行录”中还收录了他与大哥周益隆的部分言行。据《褒城周氏族谱》,周益隆平常对家人比较严苛,周炳垣乡试登科后赴邻居家饮酒,可能因心情高兴贪杯而喝醉了,回家较迟,周益隆“立待于门,壮声诃斥”⑥周菼编纂.褒城周氏族谱·言行录[M].民国八年(1919)刊印.页四.,周炳垣“即门外跪而受教”⑦周菼编纂.褒城周氏族谱·言行录[M].民国八年(1919)刊印.页四.。由此小事,可见知周益隆之为人以及周氏之家风。当然,周益隆虽对家人较为严厉,对外则“待人尤有恩礼”⑧周菼编纂.褒城周氏族谱·言行录[M].民国八年(1919)刊印.页四.。褒城县小麦收割季节,做工者多集于市场以待雇,人们到市场上争着挑选雇佣精壮劳力。周家当时经济宽裕,种小麦较多,需要雇佣大量做工者,周益隆告诫家人“不得与人争”⑨周菼编纂.褒城周氏族谱·言行录[M].民国八年(1919)刊印.页四.,要等到别人挑选完毕之后,雇佣那些别人不愿选用的做工者。旁人不解,问其缘故。周益隆答:“(如)我争先取精壮(劳工),其老弱者将不得食,故不为也。”⑩周菼编纂.褒城周氏族谱·言行录[M].民国八年(1919)刊印.页四.其仁义之言感动了许多人,周益隆去世后,乡人无不惋惜感叹。遗憾的是,“言行录”中有关周炳垣的记录较少,我们无法对其进行系统认知,幸好族谱“艺文录”中完整收录了徐绍田撰写的《周午峰先生传》:
午峰周先生,原名域广,后更炳垣,陕之褒城人也。其先世以孝友、诗礼传家,为汉南巨族。幼颖慧,比长,制举业外,旁及医卜数之学,而于绘事尤称天授。道光丁酉,举于乡。戊戌试礼部不第,遂留京师,得以尽交当世贤豪,学日进,而艺日精。甲辰,大挑一等。丁未,会试复被黜。从此益寄情于画,专以工笔写人物、花卉,能于待诏十洲之外,别开生面,人得其寸缣尺楮,争宝之。咸丰辛亥,选直隶涞水令。未几,以母老告养旋里。会川鄂发匪交讧,逼近汉中,观察张公郡守李公闻先生名,争欲延办团练,先生知事不可为,辞之。同治改元,郡城果陷于贼,乃挈家避于蜀,适其侄东渠任泸州,迎往任所。旋以疾卒。
先生性冲淡,恬于名利,晚号“终南遗叟”。好作画,而不署名,故世鲜知者。平生精赏鉴,收藏最富。乱后并所为诗文,尽付一炬。今所存者,仅《汉南杂咏》,待梓而已。①周菼编纂.褒城周氏族谱·艺文录[M].民国八年(1919)刊印.页六.
由《褒城周氏族谱·艺文录》的记载可知,周炳垣博学多才,兴趣广泛,一生富于收藏和鉴赏。太平军攻打汉中之前,周炳垣因赡养年老的母亲已辞官返回家乡,生平有过许多诗文作品存世,但遭遇兵燹后,其诗文书画作品及收藏“尽付一炬”。至徐绍田为周炳垣立传之时,仅《汉南杂咏》流传了下来,且尚未付之印刷。
据《汉南杂咏》记载,周炳垣的百首纪事长诗(纪乱词)完成于四川“蜀都公廨”且被四川按察使牛树梅“拜读”[1]179。褒城周家历史上有多人在蜀从政,与四川官场高层人物时有往来,例如周炳垣的侄子周锡龄长期在四川做官,政绩显赫且受到时任四川布政使刘蓉等人的赏识。周锡龄在四川四望关任通判时,正值“蓝大顺、李永和方耽耽犍厂,而官署已焚”。②周菼编纂.褒城周氏族谱·艺文录[M].民国八年(1919)刊印.页十四.周锡龄“毅然往集商民为团练,声威甚著。嘉定府某禀其‘干预地方制军’,骆文忠公、藩司刘公蓉则大赏异。藩司(刘蓉)旋督军至犍,询(周锡龄)‘平寇方略’,该故宦(周锡龄)谈形势机宜如指掌,刘公叹曰:‘真经济才也’!其冬,遂檄权泸州”。③周菼编纂.褒城周氏族谱·艺文录[M].民国八年(1919)刊印.页十四.这从侧面反映出:周炳垣的“纪乱词”之所以能在“蜀都公廨”顺利完成并有机会被四川高官阅读,或许得益于周家在四川官场广泛的人脉关系。
三、 《汉南杂咏》的史料价值浅析
《汉南杂咏》由三大部分组成:
一是序言,包括东海新吾氏和周炳垣两人分别为“纪乱词”所作之序。
二是周炳垣的一百首纪事长诗(纪乱词)和东海新吾氏于诗后所作之注释。
三是四川按察使牛树梅读后感一篇。
《汉南杂咏》收入周炳垣的一百首叙事长诗,以“逆氛初起自川东,大吏知兵驻汉中。食尽民粮不用命,犹将悭吝蔽宸衷”[1]160开头,从邓添亡农民军(隶属蓝大顺农民起义军)进攻汉中宁羌(今宁强县)阳平关写起。长诗重点叙述了官兵与太平军和蓝军交战以及官府盘剥压榨百姓情状,并将汉中“围城”和城陷后种种惨状勾勒的淋漓尽致。诗中还披露出汉中官场黑暗、腐败的诸多细节,如汉中知府杨光澍、南郑县令周蕃寿等许多官吏贪生怕死、不战而逃,并借机大发战争横财,汉中已是“四民遭劫官肥囊,直把官场作盗场”[1]174的混乱局面,周炳垣进而总结道:“弥天大祸压终南,贼在七分官在三。”[1]178总之,百首长诗力透纸背、字字皆血、如泣如诉,正如牛树梅读后所言:“凄雨酸风,血痕满纸,为亿万青燐黄馘,诉冤天帝,读之令人气噎。”[1]179牛树梅时身为四川按察使,虽未直接参与汉中战事,但在太平军攻占汉中郡城后曾受命协助陕西巡抚刘蓉劝捐筹集军饷。他对周炳垣的百首长诗甚为赞赏,但认为周炳垣的观点有些绝对,他提出:“惟当时亦有形势所驱,出于无可奈何者,未可一概论也。”[1]179笔者认为周炳垣的观点并不偏激,尤其是对地方官杨光澍等人的评价基本是公允的,百首长诗具有极强的史料性。周炳垣在诗中对杨光澍种种劣迹进行了无情的揭露,称其“翼长还兼府篆丹,黄堂请出沐猴冠。使君来历从何处?剥削民财计万端”。[1]168当时,杨光澍被不少人称为“良臣”。周炳垣针锋相对地指出“霖雨成殃岂是霖?负乘何止寇来寻。糜烂其民还强战,细把良臣说与今”。[1]177在一些史料中,杨光澍也被塑造成一位一心为民的好官,如光绪《续云梦县志略》中称其“先后在汉中者六载。及去,扶老携幼之民(都来送行),(杨光澍)攀援不得行,佥曰:‘公活我,不忍离也。’”[2]627杨光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杨光澍,字霖川,湖北省云梦县人,同治元年(1862)八月,原汉中知府李定南病殁,杨代任汉中知府。次年,太平军围攻汉中府城,杨充为翼长,屡战无功,后杨“径往青石关一带,招致亡勇三四千,就食大佛洞中”[1]169,并很快将洞中避难的数百余家难民“尽行逐出”,“声言救援郡城”[1]186,官兵口粮勒令附近各寨供给,“贼破诸寨,勇并不往救”。[1]169汉中城陷后,杨“例应查议”[3]64。或许出于对“例应查议”的恐慌,郡城收复后,杨在协办善后抚恤事务中表现尤为积极,且深得陕西巡抚刘蓉赏识。刘在向清廷上疏中称杨“不辞劳瘁,洵属诚朴耐苦,练达有为,知府中不可多得之员”[3]64,请予杨以“宽免处分”[3]64。经刘求情,清廷将杨“免其查议,仍照例革职,留营效力,以观后效”[3]120。为进一步替杨光澍“洗罪”,使其免于“留营效力”,1864年6月,刘蓉又向清廷专呈奏折,称杨在善后工作中“修堰清产、招佃布种、劝捐筹赈,以及雇贷耕牛、借给籽粒,一切琐细之故,苟有可便吾民利吾民者,亦无不代为筹策,多方计画。以故各邑褴褛之士绅,疲癃之耆老,无日不集于杨光澍之门。杨光澍亦无时不与之款接殷勤,不啻聚父子弟昆,相与共谋室家之事”。[3]121恳请朝廷“准将已革道衔候补知府杨光澍改为革职留任,仍署汉中府知府篆务”[3]121。刘蓉甚至扬言:“汉南半壁有杨守在,吾无忧矣。”[2]627经刘蓉再三说情,杨光澍最终官复原职。但是,太平军围攻汉中时,杨光澍并无战功,这一点连光绪《续云梦县志略》也不得不承认,“光澍充翼长,迭攻,而城不克”。[2]627实际上,杨非但无战功且根本不懂用兵之道。《思痛录》记载“(杨光澍)其勇见贼即溃,溃而复招,见贼复溃,于是屡招屡溃,徒耗粮饷,百姓忿恨已极,名为‘杨猪贩子’,以其养无用之勇如养猪,见贼即溃,如贩卖也”。[1]186查知府有守城之责,无论什么原因致汉中城陷,杨光澍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杨光澍之所以可以成功“脱责”以至于成为“有功之臣”,主要归功于其在办理善后事务中的出色表现得到了上司刘蓉的赏识。从《汉南杂咏》中看,周炳垣的百首长诗写成于同治三年仲夏(即1864年5月)。此时,太平军刚撤离汉中不久,刘蓉主导的善后工作才刚刚开始,一个月后,刘蓉才专呈奏折以杨在善后事务中的突出表现恳请清廷对杨“仍留署任”[3]121。周炳垣在诗中向杨光澍发难之时,汉中百废待兴,杨在协办善后事务中或许还尚无建树。另外,周炳垣对杨光澍的点名批评主要集中于杨在战时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未涉及其战后表现,因此,从杨光澍战时表现来看,周炳垣对他的评价应当是公允的。
就《汉南杂咏》史料价值而言,除百首长诗外,笔者认为东海新吾氏为“纪乱词”所作注释的史料性最强。注释对周炳垣的百首纪事长诗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并罗列了大量的史料作为支撑,这些注释以叙事为主兼有议论,被后世文献大量引用或摘录。
如诗“日中捐户汗流枷,万岁牌前跪若麻。世业虽然归冷落,当年曾觐帝王家”。后注释:“捐户之跪万岁牌也,各属有之,惟汉中为最酷。设于署之二堂,必于日中,令捐户带枷跪绳,民不得不倾家以从。”[1]173该注释被民国十年编修的《续修南郑县志》卷六“纪事志”[4]576所引用。
又如诗“安危大计出裙钗,子女和戎事未偕。岂意城亡家被掳,至今遗臭在衙斋”。后注释:“洋邑屡攻不下,毛帅无可如何。有僧人,旧与蓝逆有识。周令遣至洋邑通关,买民间处女及红顶花翎、财帛各件,干役同僧人送至营中讲和。蓝逆全行壁回,命暂寄署中,不久城破来领。大吏不问,想系知情。辱国损威,莫甚于此!”[1]164该注释被陈才芳几乎未作改动地摘录入其私人著述《思痛录》一书中[1]184。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不一而足,但东海新吾氏为何许人也?目前尚未寻到史料记载,望有识之士广为搜罗。
《汉南杂咏》中周炳垣所作“汉南被劫纪乱词自叙”同样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自序系周炳垣同治三年(1864)仲夏在“蜀都公廨”而作。周炳垣在序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导致汉中被太平军攻占的主要原因是“人皆敛赀齐团,补防兵之未逮,乃官以守城而重索,吏以养勇而勒捐,锋刃未及,精力渐疲,堡寨而居,骨髓将竭”。[1]159太平军撤离汉中后,在清廷处理善后事务时,汉中地方官员借机想尽办法继续欺压人民,中饱私囊。怀着对黎民百姓的同情和对地方官吏的不满,周炳垣感叹道:“上宪伤心惨目,奏请蠲赋赈饥,煮粗粥以延残喘,当途者徒归中饱。查绝产以备善后,奉命者擅入己囊,犹复事事议捐。年年科敛,神明不蔽,胡竟等于茫茫?上帝好生,岂总归于梦梦?”[1]160周炳垣笔下的“官”、“吏”、“奉命者”实际上暗指杨光澍、周蕃寿以及“局绅”、“差役”等人,这些人战前对老百姓剥削讹诈,战时贪生怕死,战后借救灾仍继续与民夺利。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战后仍手握重兵、权倾一方,为清廷所倚重,甚至被封为“救时之奇材”[1]168。周炳垣第一个站出来大胆揭发他们的种种恶行是要冒一定政治风险的,更何况在清代文纲严密,遣词用语颇多顾忌的大环境下,秉公直书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
值得一提的是,自序对太平军攻占汉中郡城前后的诸多细节进行了描述。比如围城之后,汉中城内粮食奇缺、瘟疫流行,人口数量锐减,百姓生活困苦,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周炳垣写道:“围困既久,杼柚皆空。县主之剥削无遗,卢勇之搜括殆尽。死于饥者十去其六,没于疫者四分之三。鸟鼠空而药亦充饥,脔胔竭而人无可割。”[1]160这是目前所知郡城被围后城内百姓困苦生活最早的非官方记载。他进而写道:“溃围之日,士农工商,不满一万。放生之余,男妇老幼,仅止三千。”[1]160这段文字为我们研究本次战争给汉中造成的人员伤亡提供了宝贵资料。长期以来,许多地方史料中对太平军攻破汉中郡城后民众的伤亡情况大多语焉不详。周炳垣称太平军攻破汉中郡城之后,城内存活下来的百姓总数不过三千余人。笔者认为:周炳垣提供的这个数字是相对准确、比较可信的。理由如下:一是汉中城于1863年(同治二年八月二十日)被太平军攻陷,城陷后,周炳垣“挈家避于蜀”①周菼编纂.褒城周氏族谱·艺文录[M].民国八年(1919)刊印.页六.。这篇自序写于1864年(同治三年仲夏),也即汉中城破的第二年夏天,距离“城陷”仅半年多,当属“记忆犹新”之作。二是据时任陕西巡抚刘蓉于1864年(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向清廷上奏的《陈汉南被贼州县困苦情形疏》中称“盖当孤城未破之先,死者已十八九矣。城中生齿数逾十万,其后溃围,逃出者不过三数千人,死丧之威,至是而极”。[3]62此为清代官方掌握情况,其统计数字与周炳垣自序“放生之余,男妇老幼,仅止三千”[1]160的说法相互印证。
作为目前所知最早介绍太平军在汉中活动的专著,《汉南杂咏》中还介绍了战争造成的财产损失。如城破后,城内“纵横髑骷入泥沙,焦土成墟草不芽。冠盖名区归瓦砾,春来频弔有啼鸦”。[1]173环顾四周“庙貌蒙尘各倚斜,烧残树木惨无花。怆怀欲赋黍离句,恐惹冤魂四处嗟”。[1]173此两首诗应当是次年汉中郡城“克复”后不久,周炳垣重回郡城之所见所闻。初春时节重回故地,但“冠盖名区”已尽“归瓦砾”,昔日美好的家园早已不见踪影,周炳垣目睹了满城“庙貌蒙尘各倚斜,烧残树木惨无花”的凄凉景象,其悲怆的心情可想而知。处处断壁残垣,满目疮痍,睹物思人,重回家园带来的只是无尽的悲伤。这两首诗也说明战争给汉中城市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这种人为破坏在汉中历史上影响极其深远,甚至在时隔八十多年后,我国著名地质学家王德基等人在《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一书中还指出:“太平天国之役为最惨,兵连祸结达两年,洪阳军迫近县城(汉中郡城)时,陕安道蕃寿饬令商民将东关房屋自行拆殿(毁),移居城内,商民未尽听命,待兵临城下,仓皇间付之一炬,大好街市,化为灰烬。县城被围半载以上,城内死亡殆尽,城破时十户九绝。洪阳军进城大事搜劫,未几火起,民房、衙署、庙宇几被烧尽,仅存府署及若干庙舍,化为瓦砾。此种人为浩劫,其影响南郑之盛衰,固极大也。”[5]97
四、 《汉南杂咏》版本价值及付梓时间小议
《汉南杂咏》中百首纪事长诗和注释尽管历代南郑县志多有摘录,但摘录内容多不完整。据统计:光绪二十年版《南郑县志》录诗79首,民国十年《续修南郑县志》录诗27首,两者摘录的诗歌数量均不足百首,难睹全貌。重要的是,县志摘录中对东海新吾氏于诗后所作注释进行了大量篡改、删减,以致失其原义。
比如:在《汉南杂咏》中周炳垣第一首诗后注释为:
邓逆由阳平关入寇,奉上谕:“陕西现无知兵大员,命毛藩宪带勇驻扎汉中防勦。”阴平一战小捷,贼势大震,辄令鸣金收军。邓逆连夜遁至西乡,与蓝逆合股。斯时,蓝逆已围西乡,巴令登陴誓守,力尽援绝,城陷赴难,半月尚无确耗。藩宪意在赴任,遂以“民情悭吝,饷项无出”具奏,飘然而去,置军情于不问,官绅留之不住。至宝鸡,奉廷寄复回。蓝逆已据洋县,心腹之患不可复制,而百姓竭其财力以供兵饷。不能为民除害,复以“悭吝”入奏,此真不白之冤矣![1]160
在《续修南郑县志》中该段文字则表述为:
邓匪由阳平关入寇,上谕:“陕西现无知兵大员,命毛震寿为陕西布政使,带勇驻汉中防剿。”乃驻扎月余,并不接仗,兵勇各处骚扰,民不堪其苦,名之曰“毛贼”。震寿意在赴任,遂以“民情悭吝,饷项无出”具奏去。至宝鸡,复奉廷寄折回,时蓝匪已据洋县,为心腹患。百姓竭财力以供兵饷,复以“悭吝”入奏,真不白之冤矣。[4]774
后者明显遗漏了官兵在阴平一战中虽取得胜利却犯了“辄令鸣金收军”的错误,致使“邓军”和“蓝军”胜利会师、西乡失守等重要史料。
又如诗“有险不将门户扛,徒存侥幸在胸腔。一闻封豕从东至,落日空留大将幢”,《汉南杂咏》一书诗后注释为:
发逆已破兴安,藩宪移知观察拨兵防堵。适有投效一军,约计千人。斯时,出纳大权归于县局。周令不肯,强而后可,及已回覆,竟成子虚。事关全郡安危,敢于播弄上司,卒为发逆所窘,是误人者实以自误也。[1]161
在《续修南郑县志》中则为:
发匪已破兴安,毛藩移知观察,拨兵防堵,周令不肯,强而后可,及已回覆,竟成子虚。事关全郡安危,敢于播弄上司,卒为发匪所窘。是误人实以自误也。[4]774
县志摘录中将周令贻误军机致使一支千人武装投靠成为“子虚”乌有之事隐而不著,造成诗后注释语义不明,文字不通,令读者不明何为“竟成子虚”以及周令因何事而“播弄上司”?
经对比,《续修南郑县志》摘录中将《汉南杂咏》注释断章取义、掐头去尾的例子还有很多。同时,《续修南郑县志》摘录中还直接删除了褒城县“儒学”罗秀书(《褒古古迹辑略》编者之一)“从贼不死”[1]162后仍“腼然立于明伦堂上”[1]162等等诸多注释内容,因此,《汉南杂咏》中的注释和诗歌内容完整,原汁原味。尤为珍贵的是:《汉南杂咏》收录东海新吾氏的序言中,不仅交代了周炳垣撰写纪乱词的原因“胥烈胥哉!猛逾苛政,狄听者尚且寒心,当局者能无扼腕?此午峰先生纪乱词之所由作也”,[1]159而且交代了新吾氏撰写诗后注释的动机“因诗系事,不计拙工,矢口直书,无非哀愤”。[1]159这些均属县志中未收录之内容,故《汉南杂咏》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
笔者所藏《汉南杂咏》版本为:线装木刻本,不分卷,一半页10行21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板框19.1×13.0cm,开本26.7×16.4cm。封面为清代书法家孙海(字吟帆)“午峰先生遗稿”题字,扉页有“壬午初夏,爱莲书屋藏”字样,全书刻印精良,疑为私刻本。该书版心象鼻处(鱼尾上方)标有“纪乱词”三字。书中虽未明确记载成书年代,但录有清同治八年(1869)孟秋(农历七月)东海新吾氏于“汉南萍舍”为“纪乱词”所作的序言,序言写到:“(纪乱词及注释)不特他日可备輶轩之采,且使吾乡孑遗知后此之出水火而登袵席。”[1]159这说明:一、纪乱词的注释系东海新吾氏于周炳垣去世后第二年才完成,此时距周炳垣的“纪乱词”完成已逾五年。二、“纪乱词及注释”在1869年已经成书且准备在汉中出版发行。由于《汉南杂咏》末尾收录有四川按察使牛树梅的读后感,可以说《汉南杂咏》不单纯是周炳垣的“纪乱词”,它由“纪乱词及注释”和“牛树梅读后感”两大部分综合而成,有三位作者,因此,《汉南杂咏》的成书时间可能要比“纪乱词及注释”稍晚一些。
关于《汉南杂咏》的具体成书及刻印年代,有人认为应系民国七年之后,因为民国八年付梓的《褒城周氏族谱》收录有徐绍田所作的“周午峰先生传”有“今所存者,仅《汉南杂咏》,待梓而已”①周菼编纂.褒城周氏族谱·艺文录[M].民国八年(1919)刊印.页六.的记载。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我认为《汉南杂咏》的成书刻印时间应当是清光绪八年,即1882年,理由如下:
一是《汉南杂咏》扉页上印有“壬午初夏,爱莲书屋藏”。一般情况下,线装书扉页标注“某某书屋藏”是指书的刻板所藏之处。因此,该书的刻板应为“爱莲书屋”所藏,且刻板时间为“壬午初夏”,故壬午年初夏即为成书刻印时间。“壬午”系指何年?经查每60年为一个“甲子”,1822年、1882年、1942年均为“壬午”年。结合本书内容,1822年明显排除,可能的时间为1882年和1942年。1882年为清光绪八年,1942年为民国三十一年。从版式上看:该书为典型的清代风格,如在诗的排版中,凡遇“万岁”、“圣明”、“皇恩”等字眼时,前均另起一行,且比其他行高出两格;在对诗的注释中,凡遇“奉上谕”、“奉廷寄”、“奉旨”字样,均在“上谕”、“廷寄”、“旨”之前空两格,以示尊敬。另外,书中多毛笔圈点之处,皆为清代圈阅之风格。
二是仅根据《褒城周氏族谱》判定《汉南杂咏》成书刻印于民国七年(1918)之后,证据并不充分。该族谱确于民国七年编纂,但并不能证明徐绍田所作的“周午峰先生传”也一定系民国七年完成,该传记仅系周菼编纂族谱时收录的一个资料,在族谱中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要断定《汉南杂咏》的“付梓”年代,徐绍田为周炳垣立传的时间是一个关键点,且不迟于徐绍田去世的时间,但徐绍田是何许人也?史料阙如。因此,单凭族谱无法判断《汉南杂咏》的“付梓”时间,从族谱“周午峰先生传”的内容可以断定该书成稿后并未迅速刻板印刷。
综上,笔者认为《汉南杂咏》的成书刻印时间应为1882年初夏。
五、 对几个相互抵牾线索的探讨
一是太平军进攻汉中郡城时,周炳垣本人是否参与过守城,各种史料说法不一。东海新吾氏在《汉南杂咏》序言中写到:“汉南被兵,执事者闻先生名,延办团练。先生居围城数月,知事不可为,托疾辞去。未几,郡城及旁邑果以次沦陷。”[1]159民国十年《续修南郑县志》在摘录“纪乱词”按语中指出:“午峰时居围城办防数月,知事不可为,讬疾去。后郡城及临邑相继沦陷。”[4]783说明周炳垣参与过守城,且长达数月,后知事不可为才辞职。但在《褒城周氏族谱》“周午峰先生传”中却载明:“会川鄂发匪交讧,逼近汉中,观察张公郡守李公闻先生名,争欲延办团练,先生知事不可为,辞之。”①周菼编纂.褒城周氏族谱·艺文录[M].民国八年(1919)刊印.页六.说明周炳垣知事不可为,没有接受任命办理“团练”,并未参与守城。
二是周炳垣晚号是“汉南逸叟”还是“终南遗叟”,《汉南杂咏》和《褒城周氏族谱》说法不一致。前者周炳垣在“汉南被劫纪乱词自叙”中称自己为“汉南逸叟”[1]160,后者徐绍田在“周午峰先生传”中称周炳垣晚号为“终南遗叟”②周菼编纂.褒城周氏族谱·艺文录[M].民国八年(1919)刊印.页六.,两者莫衷一是。
三是周炳垣到四川避难居于何处,《褒城周氏族谱》中说法不一。在“周午峰先生传”中:周炳垣“挈家避于蜀,适其侄东渠任泸州,迎往任所”。③周菼编纂.褒城周氏族谱·艺文录[M].民国八年(1919)刊印.页六.说明周炳垣刚到四川避难时住在其侄子东渠公(周锡龄)做官之处,即泸州。而在该谱“族居记”中:“同治壬戌,东渠公赴泸州直隶州任。全眷避难来川,时午峰公已告病归田乃随祜庭公入蜀,寓居成都拐枣树街。”④周菼编纂.褒城周氏族谱·族居记[M].民国八年(1919)刊印.页一.说明周炳垣到四川避难时住在成都,而泸州和成都两地相距近三百公里。
总之,在搜寻有关周炳垣与《汉南杂咏》史料的过程中,类似问题还有不少,笔者在此抛砖引玉,就教于同仁,以待有心者做进一步研究。清军与太平军在汉中的战争对后世影响深远。在汉中地方文献中,以专著形式记录和反映这场战事的文本并不多见,周炳垣既是这场战争的受难者和幸存者,也是太平军在汉中地区活动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事后,他不遗余力地将这段经历创作成百首长诗,为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这场战争留下了宝贵的文字材料,因此,今后仍有必要对周炳垣和《汉南杂咏》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1]郭鹏,张西虎.太平天国西征军暨李蓝义军陕南战事史料汇编[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
[2]吴念椿,程寿昌,曾广浚.光绪续云梦县志略[M]//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3.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3]刘蓉.刘蓉集(一)[M]//湘乡文库.长沙:岳麓书社,2008.
[4]朱林枫,等.续修南郑县志校注[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
[5]王德基,等.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M]//地理专刊第三号.四川:中国地理研究所,1946.
[责任编辑:曹 骥]
2016-05-30
2016-09-04
熊黎明(1982-),男,陕西汉中人,汉中市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研究方向:汉中地方历史文化研究。
G257.3
A
1673-2936(2016)04-004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