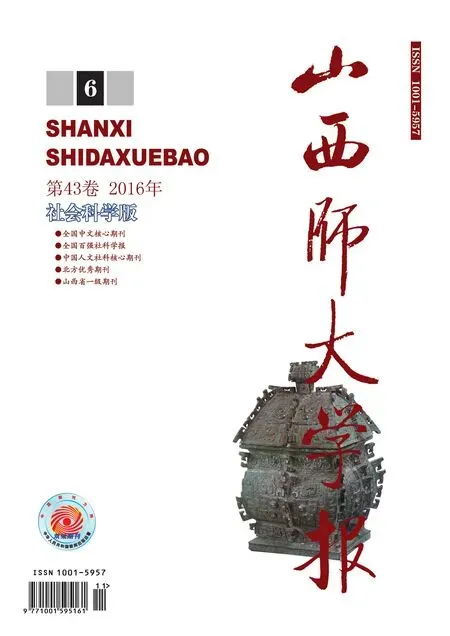自由与平等的生长点:前提的互释与界域
杨 荣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 长春 130012)
自由与平等是人类的内在价值诉求,特别是近代理性启蒙以来,成为人类实现自我的重要标志,更是构成谈论正义不可或缺的两个核心价值原则。然而,当前重要的不是对自由与平等的“启蒙”,而是对自由与平等根基和前提的澄明与反思。当人们热切地追求自由与平等的时候,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便是忽视或遗忘了其存在的内在根基或前提——宽容意识与多样性的承认,以致迷失了方向。如果前者是伦理前提,那么后者便是思维前提。正是因为这两大前提使自由与平等在人们内心萌生并得到不断的巩固发展,也成为民族国家在处理国内与国际事务时所贯彻的基本原则。与此相反,内在根基与前提的忽视与遗忘不仅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紧箍咒”,而且也成为政治愚弄人民的“话语盾牌”。因此,回溯根基与前提既是自由与平等进行自我确证的内在要求,也是在时代精神的指引下建构自身的强烈呼唤。
一、伦理前提:宽容意识
宽容不是超义务的道德负载,也不是无义务的道德无涉,而是切近现实的微小美德。虽其微小并不意味着不重要,它不仅和自由与平等同等重要,而且也构成自由与平等的前提条件。试想一个不宽容的人,何以自由与平等地对待他人?一个不宽容的社会何以自由与平等地得到发展?一个不宽容的国家何以自由与平等地寻求民主?宽容之为宽容突出的特征便是对“不合常理”“不守成规”“特立独行”等的承认,“凡性格力量丰足的时候和地方,怪僻性也就丰足;一个社会怪僻性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中所含天才异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力量成正比的”。[1]79中国有先秦诸子百家的群英荟萃,西方有古希腊哲人的各抒己见;中国有儒释道的三教合流,西方有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矛盾缓和;中国有李世民广开言路、开门纳谏造就的大唐盛世,西方有林肯化敌为友成就的联邦统一。日常生活中的这种事例比比皆是,廉颇因宽容而负荆请罪,李斯特因宽容义收学员。如果说上述只是一些具体的表现,那么对其系统论证在哲学史上也是蔚为大观,不仅有“主体间性”的对等、“视域融合”的交流,而且有“交往理性”的实践和“重叠共识”的平衡。
“主体间性”是与“主体性”相对立的,“主体性”要求一种“主—客”的二元对立模式,而“主体间性”则主张一种“主—主”的对等模式,人与人之间不再是“我”与“他”的等级关系,而是“我”与“你”的对等关系。胡塞尔试图以先验的主体间性打破莱布尼茨的封闭单子,摆脱“唯我论”的困境,认为要实现“自我”与“他我”的显现,必须通过共现(Appr·sentation)和统觉(Apperception)这一中介,由“在场”共现“不在场”,由“显”统觉“隐”,以确认“他我”的在场和显现,进一步通过配对(pairing)呈现“自我”与“他我”的原始给予性,“在他者中生活,同经历,同体验,同思维,同欢乐,化入他者的存在,并因而奋进他者的生命奋进之中”。[2]21胡塞尔虽然开启了“主体间性”研究的先河,但是,他对“他我”的承认还是囿于“主体性”的漩涡,“他我”仍是意向性的对象和“自我”的一个附属物。海德格尔以“此在”代替了胡塞尔的先验主体,提出了“共在”理论,认为“此在”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先验直观,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在世。“此在”在世意味着不是独立于世界的先验筹划,而是与世界融为一体的浑一关系。浑一关系即是“共在”,不仅是与器物的“共在”,而且也是与他人的“共在”。“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3]146“共在”以宽容的态度承认了“他者”与“自我”在世界中的对等地位,给予了他者应有的合法性地位,超越了主体形而上学地对“他者”的宰制与统治。
如果说“主体间性”是在以承认“他者”合法性地位的基础上构建的对等关系,那么“视域融合”则是在为“主体”正名的基础上提出的对话方式。古典诠释学认为,理解者要达到对文本的理解,把握文本的原意,必须克服时间间距这一历史鸿沟造成的主观成见和误解,进而达到历史的客观真实。因为每一个文本的作者必定是处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与境遇之下的,克服理解者自身所带有的特定历史条件和境遇,设身处地地还原当时的真实历史情景,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作者文本的原意。但是伽达默尔认为,古典诠释学是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基础的,既然承认了作者所处的历史条件与境遇,那么为什么要否定理解者自身的历史条件与境遇呢?理解的历史性是客观存在的,不容忽视,更不能消除,没有理由承认前者的历史性,而否定后者的历史性。历史性的内蕴是文本作者与理解者的传统与成见,不需要用文本作者的传统与成见抹杀与否定理解者的传统与成见,反之亦然。二者是内嵌于历史性之中的,真正的理解不是要克服时间间距,而是正确评价与适应历史性。传统与成见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历史的变化之中的,只有旧的传统和成见与新的传统和成见相结合的地方才能创造新的价值。“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与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4]384—385理解是以传统与成见为前提的,并在历史中得到不断的修正与更新,也只有承认彼此的传统与成见,才能使理解者丰富与发展自己,同时扩充文本作者为特定时代所遮蔽的重要价值,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和理解者的视域与文本作者的视域不断融合,达到伽达默尔所说的“视域融合”。
哈贝马斯受诠释学与语言学的影响,以理解为目的、语言为媒介建构了他的“交往理性”理论。他认为语言是人类认知与交往的寓所,与劳动等其他行为相比更具有普遍性,因而使人们获取科学知识与实现交往的活动成为可能。然而,一直以来人们却以理念、资本作为媒介,将自身立于被统治的地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呈现出依附与互为手段的样态,以绝对理性与工具理性扼杀交往理性的语言性、程序性、包容性和多维性,使人脱离现实的生活世界,固守于特定文化的场域,难以建立开放的对话机制。因此,必须摒弃绝对理性、工具理性的独白式的单维理性,发展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与主观世界三者融合的多维理性,这样行为者之间才能平等商谈,各抒己见。“向交往理论的范式转型实际上是回过头来从工具理性批判终止的地方重新开始”[5]369,以理解代替认知作为交往理性追求的最终目的,让主体表达出符合有效性的要求,并对其进行程序论证,排除一切强制的动机,承认主体在交往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真正体现真实性、正确性与真诚性,以处理自我与他人、自我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当前跨地区、跨文化、跨领域等的发展已是不可逆转的世界历史潮流,地区冲突、文化矛盾、领域摩擦日益凸显,尊重彼此之间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政治设计就成为理解何以可能的前提性条件。理解便是以宽容视之。
罗尔斯则将目光聚焦于政治哲学的研究,在正义完备性理想幻灭后,在宽容意识的引领下,适时地提出了构建良序社会的基石——“重叠共识”。认为在理性多元存在的情况下,依旧寻求同一的理性来支配其他完备的理性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实,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宜的理性学说,既要承认理性多元存在的事实,也要承认理性多元存在的必要性。如若用非理性的暴力胁迫达成稳定性,只能如霍布斯所言的自然状态一样,人人利己,战争不断,最后以恐惧臣服。这样的稳定性只能是暂时性的,在现代立宪民主政治中,稳定性是靠公民对民主制度的真心认同。而在政治正义方面没有达成共识,只会导致社会的持续不稳,因此必须用公共共识取代中心权威,用彼此平等保障互惠合作。正如罗尔斯所说:“政治自由主义寻求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我们希望这一观念在它所规导的社会中能够获得各种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的重叠共识的支持。”[6]10在具体实践上,达成“重叠共识”除了上面所说的承认理性多元之外,其次就是要达成“宪法共识”,理性多元所代表的利益团体与政治派别可以根据协定制定宪法。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既规定着公民的基本权利,也规定着民主政治的基本程序与原则,使公民权利与政府运作双受惠。但这也只是权宜之计,“重叠共识”不仅要求建立在正义观念之上,而且也要求包括基本的正义,这样达成的“重叠共识”就不会因为利益、宗教、道德的原因而出现反复。除了上述的宽容意识之外,拉康也用“镜像”透视着“自我”与“他者”,萨特则把“我们”“语法形式的运用”归结为“共在的实在经验”[7]531,勒维纳斯更是突出了“他者”的绝对差异性,确立了伦理学的第一哲学地位。
二、思维前提:“多样性”的承认
“多样性”的承认是与“同一性”的迷恋对立的,在哲学史上,“同一性”的迷恋深刻地体现在对终极实在的固守、终极状态的痴狂和历史脚本的迷信。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人们总是倾向于找到一个根基与基底。早期自然哲学有泰勒斯的“水”、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和巴门尼德的“存在”,古希腊有柏拉图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近代有笛卡尔的“我思”、莱布尼茨的“单子”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无一不是在追求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终极实在,每一位哲学家都深信自身所探求到的终极实在是世界的原始始基,没有比这一始基更为始基的始基,以此作为解释世界或改造世界的不二法宝,呈现出“诸神”混战的“厮杀”场面;企图以“一”支配“多”,抹杀多样性、否定个性,获得统治世界的至上权力与至尊地位,求得世界的长期稳定。殊不知“同一性”正是导致冲突不断、号角常鸣的根源。人们正如生活在世界中的“囚徒”,都固守着利益的唯我性和思想的“纯洁性”,陷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僵局,结果往往是以两败俱伤收场。如若回顾这一段哲学的发展历程,另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常常会出现不断的“超越”。如果说泰勒斯的“水”还是具象的始基,那么巴门尼德的“存在”就是不折不扣的抽象始基;如果说柏拉图的“理念”分离了世界,那么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则实现了世界的统一和解;如果说笛卡尔的“我思”还是思维的自说自话,那么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就是世界的客观精神。“现在”是对“过去”的发展,“后者”是对“前者”的完善,这便是“超越意识”,实质是对终极状态的迷狂。“新的”优于“旧的”,“最新的”优于“新的”,“更新的”优于“最新的”,进步、发展、革命和解放成为时代的时髦话语。“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思想的伟大再生”[8]143。 “超越”意味着“现在”与“后者”的完满、至善,以“现在”淹没“过去”,“后者”抛弃“前者”,用“同一性”的逻辑“追新逐异”。相信依靠人的理性,可以摆脱自然对人的统治与支配,使人由幼稚走向成熟,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在那里一切“都被对称地安排在和谐的秩序中”[9]174,没有矛盾、冲突和摩擦。支配历史不断“超越”,通达终极状态的则是先验的“理性”,它预定了历史发展的轨迹,如同自然界的发展一样,只能按照所规定的“脚本”产生、发展、高潮和结局。一切都必须严格遵从“剧情”的先后顺序,不容许有任何的改动。“自由”充其量只是对“历史脚本”的认识,面对“历史脚本”的必然性人们只有忍受。不论人们难受还是不难受,痛苦还是不痛苦,都应当服从或者是选择放弃徒劳而无益的反抗和斗争。对“历史脚本”的迷信,实质是人丧失了在历史进程中的实际作用。把刚从“神圣形象”中解脱出来的人又推入了一个更为伟大的“非神圣形象”之中。概而言之,不论是对终极实在的固守、终极状态的痴狂,还是对历史脚本的迷信,都是一种“同一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其特征突出地表现在:超验本原的绝对统摄、二元对立的等级模式和非历史的永恒在场。“多”源于“一”,“一”统治“多”,多样性被裁剪、阉割殆尽。
20世纪以来,现代哲学意识到传统哲学的缺陷,要求“重估一切价值”,进行一次世界的“袪魅”,承认多样性。从认识论的层面,人们不再执著于一劳永逸的真理,倾心于发现真理的独断旨趣,而是寻求在现实的生活中“创造”真理,容许真理的“可错性”。“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0]3只有在实践的过程中真理才能生成自身、创造自身。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相对的真理。“最简单的真理总是不完全的,因为经验总是未完成的。”[11]191承认真理的“创造性”和“可错性”,从另一方面将破除主观符合客观的“符合论的真理观”,这也就是破除了以“符合论真理观”作为绝对命令的意识形态的幻相。当人把自身当作真理的“传声筒”时,也即把“传声筒”的功能权威化了。进而把特殊普遍化,把普遍权威化。破除“一”的真理观,是人们承认“多”的真理观之丰富性与多样性的内在要求。从存在论层面,人们不再追求先验的本质,相信本质先于存在,而是要求从人的本真生活中“自为”地发现自我。倡导“存在先于本质”的生存理念,人之为人,不是与动物一般的“自在”,而是有意识的“自为”,本质也不再是“会制造工具”“理性”等的先验构造,而是“面向事情本身”的交往活动,因而,人不是抽象的存在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56从历史观的层面,人们不再相信历史的“决定论”和“宿命论”,不再受制于“历史脚本”的宰制,而是积极参与到历史的活动当中,抛弃英雄史观对人的思想的钳制,相信人们自身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3]118—119如果这是从宏观角度对历史观的理解,那么在微观的角度,人们需要抛弃“一元”社会的单调无趣,强调社会的多元化,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宗教信仰的差异性。在如此多元的社会中,没有任何一个“脚本”能够预言将来的一切,“风险社会”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而“风险社会”的治理也只能在相互的交往中合作治理与共同抵御,尤其是现今存在的如核危机、恐怖袭击和生态污染等国际性、全球性的重大问题。
三、结语
自由与平等是人类的内在追求,然而,无论在历史的长河,还是在现实的生活中,人们常常遗忘了它的存在,导致互相残杀,甚至带来几乎毁灭人类的世界性战争和奥斯维辛的恐怖。追根溯源都是宽容意识的缺失与多样性的抹杀。宽容意识与多样性的承认作为人类理性精神的自觉,是深刻的历史教训使然。为了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对其进行理论的反思是时代精神的要求。宽容意识与多样性的承认作为自由与平等的前提,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在一定程度上,多样性的承认是在思维领域的革命,而宽容意识则是在实践领域的践行,前者承认差异性和个性,后者则以“和而不同”的实践智慧宣扬着前者。与此相反,后者在实践领域得到的逐步认可,也进一步催生了多样性的样态。从另一个侧面,宽容意识与多样性的承认不是贵族的奢侈品,而是普通人民大众的道德底线与价值基础,也是自由与平等得以健康生长的必要条件。历史上宗教的迫害、种族的偏见和文化的大清洗无一不是以相反的例证呈现着这种必要性。没有宽容的“准生证”和多样性的“保护伞”,自由与平等将成为虚置的装饰。然而,宽容不是无限退让,多样性也不是虚无。如果一再的宽容,将会带来沉重的道德负载,不仅是对个人,甚至是国家和社会。一个人无限退让将丧失自我,一个国家无限退让将使民族备受凌辱。如果一再鼓吹多样性,将会成为制造混乱的理论根据,不仅有民族分裂势力,而且有国际恐怖分子。无边界的宽容与多样性将会使秩序紊乱、社会失控,人们的幸福生活将遥不可及。康德早在“现象”与“物自体”之间,提醒人们边界的重要性,维特根斯坦也在“可说”与“不可说”之间划界。在宽容、多样性与规劝、惩罚之间明确其界限,是理论与实践的内在要求。因此,既要强调宽容与多样性作为自由与平等的前提相互阐释其重要性,也要明确宽容与多样性应有的理论与实践界限,真正有效地促进自由与平等的良性发展,这是自由与平等不可或缺的重要生长点。
[1] (英)密尔.论自由[M].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2] (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3]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4]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5] (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 [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6] (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1.
[7] (法)萨特.存在与虚无[M]. 陈宣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8] (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9] (英)伯林.自由论[M].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1] 列宁全集:第38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