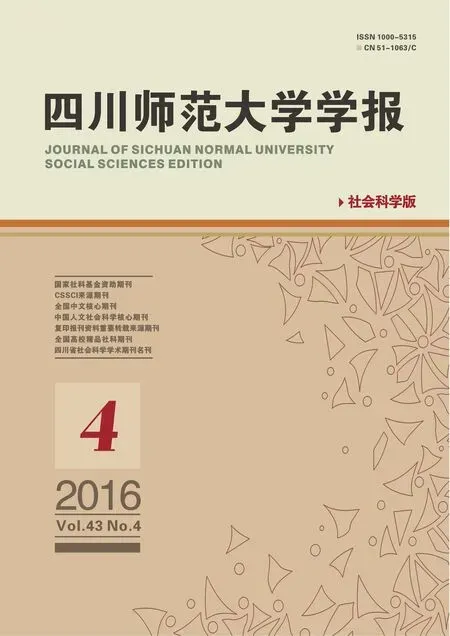商业美学下的符号修辞实验
——评《九层妖塔》中的“空间编码”
赵 勇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
商业美学下的符号修辞实验
——评《九层妖塔》中的“空间编码”
赵勇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
摘要:符号学视野下,当前艺术电影在商业美学中的复杂面向,体现了创作过程的符号文本修辞术。陆川在《九层妖塔》中以神话象征系统为基础,有意落入具有较强理据性的历史文本,造成了空间对峙的修辞效果。电影文类的转型,并不必然导致艺术电影完全走向商业美学,一个成长的电影类型框架恰恰需要文本内符号元素的多元流动与置换。
关键词:商业美学;符号修辞;《九层妖塔》;空间编码
一直以来,在电影文化中,艺术电影总是作为类型电影的“对立项”存在。其文本形式标新立异,内容超然晦涩,主题冷面先锋,从而对抗类型电影“自动化”阅读期待。艺术电影解读的困难之一,就是其与日常生活审美之间具有文本断裂感。而商业美学逻辑要求打破艺术文本与其他社会文本的区隔,通过将其整合为无差别的文化符号,以此保证资本的殖民,从而形成一个市场化的全文本消费链。在资本市场包围下,电影产业化呼声甚嚣尘上,艺术电影处境艰难。 中国新生代导演陆川,其之前的作品一贯持存着某种特立独行性,与日常审美和资本吁求保持着审慎的距离,但其新作《九层妖塔》似乎有着异样的步调。
《九层妖塔》这部影片有着清晰的类型诉求,被认为是陆川对“市场妥协”的姿态。它改编自网络小说《鬼吹灯》,这是个先文本,不像陆川以前的影片具有原创性;而自《画皮》系列以来,大银幕上“妖孽横行”,《西游之降魔篇》、《狄仁杰之通天帝国》、《捉妖记》等,再扩大到电玩游戏领域的“降妖”模式,构成一个令人亲切的广泛相关性的文化“联合文本”,一改人们对陆川“文本难解”的印象。电影广告促销揭秘电影生产:“高科技制作”如何再现魔幻场景;陆川访谈透露的对“地心历险记”的有意借鉴——这些“共同文本”,最终与片名的强编码符号“妖塔”,都如此清晰地指向一个新的文化体制的转型——不折不扣的魔幻商业题材。“体裁的最大作用,是指示接收者应当如何解释眼前的符号文本,题材本身是个指示符号,引起读者某种相应的‘注意类型’与‘阅读态度’”[1]137。
一“镇妖塔”的解释漩涡
观影过后,有些期待会落空。人们会发现,像“降妖通关”、“人鬼情未了”等典型场景似乎被有意悬置了。胡八一(赵又廷饰)和杨萍-Shirly(姚晨饰)的恋情只是个框架信息,因为胡八一的“发现之旅”才是“真”文本。
整部影片设置的谜题有两个。第一,九层妖塔是什么?本来这不必大费笔墨,因为上文提到的大量伴随文本已经唤起了观影期待,在民间俗文本中,有《封神榜》、“白蛇传”、《西游记》等等,九层妖塔具有镇妖的价值。可是,陆川却把对九层妖塔的解释过程当作重头戏。如:杨加林教授的先知性的提示,胡八一在图书馆废寝忘食地“按图索骥”加旁白,光头馆长(李晨饰)的“循循善诱”。这些“政出多门”的复调性解释话语,需要观众积极努力才可能会“拼贴”出一个象征整体(这在其他类似的型文本中,也就是一个叙述契机,在故事中甚至很像一句异常简明的佛家偈语),而且这也严重干扰了“降魔对决”的进程。第二,打开妖塔的秘诀和障碍是什么呢?那就是胡八一必须和杨萍-Shirly一起完成这个关键词“合作”。这也是俄国民俗学家普罗普所提的叙事功能。神怪魔幻题材的惯常情节,是在有效地进行短期人物关系对抗性的磨合后,快速进入主要叙事任务:妖塔被打开。因为只有众妖出现,才会出现后面典型的大规模“人-妖决战”高潮戏桥段,这也是类型期待。灾难发生,正负价值颠倒,需要主人公来扶正。这符合亚里士多德说到的,不是用叙述语言,而是对戏剧性事件的“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2]15。可是陆川却让杨萍-Shirly人物角色长期“缺席”叙事主战场,将本来与胡八一张力性的对抗关系不断悬置延迟。
因此,这两个谜题反而构成了突兀的“反常规”动作,一定程度干扰了类型观影的愉悦。但也因此甚是可疑:这既可能是因为作者尚未领会类型创作经验而出现的“噪音”符号,干扰了叙述的惯常流程,也有可能是作者“有意为之”的意图信息。因为少数影迷和学者相信,像陆川这样的艺术家圈层也会时常有“冒犯文化常规,更新艺术类型”的创作冲动。
“今天,当一门个别的艺术恰巧被赋予支配性作用的时候,它就成为艺术的楷模:其它艺术试图摆脱自己固有的特征而去模仿它的效果……处于从属地位的艺术通过这种艺术效果的混合而被歪曲和变形。”[3]当下广告文本盛行,这是商业美学的主要标志。广告文本的趣味是艺术性让位于商品符号,是“强编码”文本,文本内容和结构可随意拆分剪裁以供流通和消费。因此,当下不少电影开始向广告文本学习创作路径,尤其是所谓的高概念电影的配方策略,局部精致但整体破碎,有的更宛若巨型植入广告的《变形金刚》等。
陆川不能拒斥这个潮流,因此虽然影片中镇妖塔的故事时空断裂,完全靠画外音旁白的语言连缀,但惊心动魄、瑰丽奇幻的画面宛若时尚明信片和探险游戏,又让人身心舒畅。陆川这次转向,明显是要获得电影作为产业的巨大价值。
通过对相关电影文本中“捉妖”人物的考察,会发现这些人物性格和品质具有很强的世俗性日常化特征。《画皮1》甄子丹扮演的捉妖师,好喝酒,机智诙谐,逍遥于民间市井,让背负重托的陈坤好不羡慕;《西游降魔篇》中的唐僧简直比悟空还泼皮无赖耍滑;《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中,狄仁杰断案不只是为国为家,也有着自己隐秘的动机(判案上瘾与价值无关,可比较刘德华很多神经性喜剧中的型文本特点);《捉妖记》让男人怀“鬼胎”体验代孕妈妈的感受。这些人物虽然肩负捉妖的叙事任务,但他们不管身份如何,都披上了常人普世的价值观和世俗情感,有着稍显自私的动机,大多油嘴滑舌,滑稽可笑,价值观追求稚粗,有的甚至明显低于普通人的行为准则,因此主人公一般带有被嘲讽的喜剧性。但在陆川的这个降妖故事中,胡八一这个角色却有着与以上人物不同的特征。
胡八一这个名字虽然很日常,很随意,但身份却是王族后代,潜伏民间,有贵族血液。他与所处的世界有些格格不入,有些孩子气地怀疑和拒斥周围的人,固执又伤感(赵又廷型文本的潜质)。文本的戏剧重心不在于险恶的危机情境和孤胆英雄的外部对抗,而是以内卷化的人物心理世界为主要表达对象。对故事人物内在的身份混沌、目标模糊、认识局限的表现构成影片作者的意图定点。
下面将对陆川之前的电影人物谱系作纵向比较观察。在《寻枪》中,姜文扮演的警察丢枪后魂不守舍,意识涣散,但有着警察职业的神圣感和责任感;《可可西里》在艰苦的西藏荒原没有物质给养,仍孤身作战,队长的死亡有一种历史的庄严;《王的盛宴》中一介莽夫的刘邦开始反思自己的疯癫本质;《南京!南京!》里一个“卑微的敌人”,日本士兵却在反思宏大话题的侵华战争的价值。陆川的电影不管题材如何,他里面的主人公都有一种高贵的单纯或者如康德所讲,人物主体有一种先验的“物自体”[4]倾向,他们有反省意识,在文本叙述开始便有与生俱来(如《南京!南京!》、《王的盛宴》)或者命中注定的牺牲和对责任的担当(《可可西里》、《寻枪》)。
在《九层妖塔》中的胡八一继承了陆川艺术文本中人物的这些特点。胡八一的画外音旁白连结起整个故事的时空世界,这是个典型的艺术文本模式。画外音旁白在“追溯”自己的成长身份:他作为王族成员抵制住自己的个人私情,杀死眷恋的恋人兼敌人杨萍-Shirly,从而封锁九层妖塔这些大义之举。这并不是经过抵制世俗诱惑得来的心理转变,而完全是对自己身份使命的最终确认。陆川的这些人物有较为“高尚”的情操,没有被设定为彻底世俗化、甚至喜剧化来拉近观众距离。加拿大的弗莱把这些人称为“高模仿”人物,这是普通人达不到的人物品质,“他具有的权威、激情以及远比我们更强的表达力量,但他所作所为,既得服从于社会评判也得服从于自然规律”[5]4-7。但同时陆川的这些人物因此具有一种非个人悲剧的倾向,那就是折磨他的是外在规范的约束。他行为选择的价值体现在“社会文化”层面的力量。
二“红色记忆”的理据性滑落
《九层妖塔》归属于神怪魔幻片类型。神话类故事天马行空,时空抽离现实环境,最关键是有叙述机制的超能力性质,人物和怪兽造型设计更是很有想象空间。它的叙述机制是非现实的,因此神话影像系统遵循自己的“一般现实逻辑”,“它是一种独特的审美价值判断标准,它属于描述性的,而非演绎推理性的”[6]5-8。神怪片距离现实主义范畴的“入世”要求最远。它的自成系统是指里面神话式的叙述机制、超能力、“异形式”的人物、虚拟的环境等都不能与现实直接对应,它不是“逼真”的再现世界,而是人造“仿像”的抽空世界。因此我们看到的神怪片呈现出浓烈的虚拟性。故事的环境空间基本没有具体指向性,很模糊,无法空间定位;而时间则指向遥远的过去或未来的某点,无法推算。因为只有“远距”现实,叙事才更具有异域性及神话性,不被现实逻辑束缚,正如《山海经》奇诡的见闻总是发生在遥远的中原之外。因此,神怪片相比其他类型具有一种艺术文本理据性滑落的倾向。也就是说,它不指向能引起人们追寻逼真现实世界的任何依据,它是封闭自足的空间,不是现实世界的直接映射。拿《九层妖塔》来说,鬼怪出没的场所应该在现实时空之外,以保证不会侵入现实幻觉,否则超能力的叙述机制会被挑战,比如“起死回生”、人鬼通婚的逻辑、妖塔非稳定的建筑格局、杨萍-Shirly的超人力量等等,这些在神话影像系统中能自圆其说的元素都将经不起历史逻辑和现实经验逻辑的推敲。
陆川在这部影片中植入了具有怀旧式的历史文本。故事人物身份是考古队员,里面有人物杨加林教授,反映了历史上的“罗布泊事件”;片中的插曲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毛文化”;中国几次大的科考发现这样的现实文本也被使用进去。可以这么说,正是历史符号落入神怪“型文本”才使得这部影片有着某种“标新立异”的观影感受。尤其陆川对这种插入的“历史符号”的文本,不但没有抹去其“现实性”的特征,反而不断强化其“历史真实性”,比如用当时特有的新闻片效果,鲜明地“再现”石油城集体性的文化演出活动等等。总之,陆川在这个神话类故事中,让我们有机会以奇怪的方式“穿越”到了当时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集体大生产和集体文化休闲中去。这不啻是陆川有意扩大电影符号解释全域的动机,还将具有怀旧情结的观众也纳入进文化市场中来。
当然更重要的价值可能恰恰是陆川对“历史考古式”的发现。“新历史主义的中心点就是对主体性的质疑和历史化”[7]。在陆川其他几部影片中,有一种对正统历史叙述模式进行质疑的态度,并试图用影像符号以新历史主义的方法去分析解构主体历史写作的问题。在《南京!南京!》、《王的盛宴》中最为直接和明显。《南京!南京!》从日本人的“敌对”角度试图关注侵华战争史的书写多大程度上受到民族主义和冷战意识形态等影响;《王的盛宴》则再次解构了以《史记》为代表的汉史被涂抹了多少文学笔法;在艺术文本的使用上,陆川在《可可西里》中的固定长镜头,多次将悲剧性场景“冷眼旁观”,保持感情距离;《南京!南京!》中的现场摇镜头、黑白摄影等等纪录片式的处理手法,具有严肃的科考性用意。总之,以上的陆川笔法都服务于对“历史”的分析上。可以说,陆川是有着鲜明历史观的导演,这是他作为艺术家群体的文化特征之一。对传统史观的质疑,必然与我们所见的电影中的常规历史演绎不同,他的作品因为是新历史主义的批判,以解构主义考古历史,因此便带有一种反讽历史的特征。这还体现在陆川对影像系统性质的认识和形式突破上。
神话影像系统是《九层妖塔》主要的表现机制,而那些被植入的“红色记忆”又与具有鲜明可验证的“历史逼真性”混杂交错在同一个叙事文本中。因为两者“一般现实逻辑”内在差异,便自然会出现“同层次元语言冲突”。红色记忆和这个神话象征系统有完全不同的元语言。不同的元语言集合如果产生相反的冲突的解释意义,就会产生“解释漩涡”[1]237-238。比如红色记忆让“上一代人”“缅怀”熟悉的过去,那个“过去”正是他们自己身体成长史的真实积累,不容戏说,否则就是否定缅怀者的主体历史,就是割裂自己。可是,神怪片模式的虚构性、游戏性又要求我们必须逃往神话时空。
陆川在历史的建构和解构两端滑动,在逼真和虚拟中间游弋。“解释漩涡”将几种价值观和冲突意义并列,互不取消,影片文化整合的传统冲动被导演自己终止,这种碎片化对应的是后现代文化。红色记忆的严肃性在神话影像的“游戏虚拟性”,更突出对比了双方的巨大价值差异性,永不弥合。这是一种历史反讽模式。符号学认为,“任何解释都是解释”[1]50,没有一元性的符号解释。对“红色记忆”符号文本来说,它“误入”这个神话系统,这部分观影者的历史认同感有被消解戏谑的危险:集体时代单一化的建设和文化生活显得“虚假”荒谬。
考古队本应该是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态度的,却遇到“妖塔”和“石头城”中人-妖大战,实在讽刺。科考发现“真伪”难辨,胡八一在王族、鬼族和749“国家队”的诱骗利用,这些都一改传统建构的“红色记忆”图景。从这个角度上,陆川的文化先锋性便有所暴露了。
接下来新的问题是,作为神怪片的主体,神话影像系统是否会因为导演的这个创新冲动也会让自己“面目全非”失去符号价值呢?理据性丢失是测量神话影像系统的一种方式。符号学家赵毅衡的建议是“第一个测定法是替代,第二个测定法是解释”[1]253。影片开头考古队和军队系统挖掘文物的场景是否可以其他文本替代?在神话系统中此处的叙述功能是“接触”,比如在这个功能不变的前提下,人物身份换成一个盗墓队伍或只是民间考古队,我们剔除“红色”身份符号,这是否会对整个影片文本有大的影响呢?显然不能这么做。国家队背景的科考队和军队具有体制象征意义,后面叙述高潮是进驻石油城,而重要推手就是749队。这说明这个符号编织紧密,不能理据性丢失。再看另一段,杨萍和杨教授借“文献性纪录片”的影像形式被介绍,此处系统对应的叙述功能是“时空穿越”,这个时空穿越的“超能力”呈现方式是纪录片质地,这个技巧很巧妙,将时空穿越的把戏带来审美“刺点”,这说明美学技巧不带有元语言冲突性。可是这个纪录片视频播放在叙事中是有具体位置的,它被胡八一所在的考古队所“看到”,这个信息被“转述”给胡八一,构成重燃对杨萍的眷恋寻找之途。这个叙述功能是“告知”,我们可以置换成另一个告知模式,比如杨萍-Shirly既然具有超能力,完全可以“越狱”,然后主动来找胡八一“亲自告知”。这是有可能的,完全符合神话系统的建构。所以这个段落的运用说明,它可以相容于系统,因为,可以被替换,这个红色记忆(考古发现的文献视频)也同时具备“理据性丢失”的特点,是成功的段落。前者例子中其内容理据性在文本中很强,不可替代,但形式文本符号的性质却内在“格斗”;后者内容上具有理据性丢失的特点,说明这个“历史文本”会很好地融入这个虚拟文本,真-假的逻辑对抗便被遮蔽了,自然而然形成了巴尔特推崇的“刺点文本”。它破坏了虚拟的文化常规,风格跳跃[8]40-44,让人印象深刻,但又避免了两种符号性质的冲突。
由此我们发现陆川在运用这些技巧来实现其历史反讽的意图。他采用的“历史符号”落入“神话型文本”的方式,是可行的,并不必然出现文本不可解。可是,同层元语言冲突的存在,也需要作者对文本细节符号的兼容性做出具体调整和安排。
三西部印象的重新编码
在电影文本中,西部被各种文化体制符码所征用。在精英文化中,西部是与物质文明的诱惑相对峙的“乌托邦”,朴素纯粹,是各种价值救赎的“原乡”,如《盗马贼》、《青红》等;在主流文化中,它尚未进入现代化文明进程,是落后、待开发的启蒙之地或国家政治修辞,如关于少数民族的“十七年”电影时期作品;在商业文化类型电影中,西部是原始神秘,文明的蛮荒,具有粗野气质,如西部武侠片序列。《九层妖塔》中的西部映像被多重符码所交叠。
神怪片的叙述环境具有高度虚拟性,主要空间理据性滑落。《九层妖塔》的故事照理说是西部或更具体地说是新疆荒山和戈壁上的石油城,它不应具体指向具体实存的某个现实空间,或者说退一步,为了某种效果也可将空间适度进行理据化修辞。
影片故事空间大概有三部分:考古队所在的荒山,也就说九层妖塔所在地;北京某图书资料馆,胡八一“释迷”主要场所;新疆石油城小镇,妖怪肆虐的灾难之所。应尤为注意,西部作为整体与北京的空间对峙所带来的文化意义。
在商业美学中,西部被简化为冒险猎奇之地,原始味道十足,所以西部空间本应该是叙述主体,这样《九层妖塔》就是典型的降妖除魔的故事了。然而,在片中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北京文化空间的特质,首先是它在短暂地呈现出改革开放以后城市文化的浮躁热闹之后,便一直紧紧局限在一个小图书室,并被进一步编码为王族(高贵的种类,有拯救人类的使命)守护者之门。更重要的是这个北京空间,被一再地拓宽文本体量,不只满足于作为西部空间的故事引子,而成为相互颉顽的力量。起初是其独特的位置,它不位于前面或后面,作为西部空间叙事的“封底”,它夹在西部空间叙述的中间,打断了其流动的整体感。胡八一在北京的图书资料室查鬼族秘密不是过场戏,而是与影片叙述重心和作者意图息息相关,这样“释迷”而不是“降妖”成为了基本情节线。这是北京空间叙述被有意放大的效果。同时它处于衔接荒山发现妖塔和石油城调查妖怪这两个被割裂的西部空间的切点上,也就是说,西部空间的合法化叙述和情节转向竟然是依靠北京空间的释迷任务。
因此,陆川把西部空间和北京“文明”空间进行了重新符码化。符码是元语言符号,符码规则便是北京空间对西部空间的切割方式。它让影片“文化产品”的理据性陡升,是艺术圈文化体制的常规动作。
主体人物身份来自北京,探险降妖在西部戈壁,叙事任务是释迷、考察和降妖。这决定了北京作为“文化”空间向西部“原始”空间征服的象征性意义。列维-施特劳斯指出,“神话思维总是在对立的状态中向着解决协调的方向进站”[9]224。并因此可以进一步总结出一系列语言学式的二项对立结构:北京——文化的,秩序的(冷静的),主体性的;西部——原始的,危险刺激的,失序的,被对象化的。
在惯常的艺术话语中,西部原始文明具有对现代性反思的疗救价值,然在此处,北京的图书资料室被重新加码为王族死而复生之所,而石油城和妖塔所在地则被象征为灾难复燃之地。这又是一个二元对立的象征体结构。文化对某个比喻集体地反复使用,或是使用符号的个人有意对某个比喻进行重复,都可以达到意义积累变成象征的效果。陆川一方面强化了神怪片叙述环境的刻板印象,如原始危险之地,同时将两个空间设置为征服关系、解释性关系。这样空间的意识形态格斗局面形成了,从而进一步服务于“历史反讽”,这种简单的征服和解释关系将神圣-粗鄙的历史和现实空间的“讲述”方式置换为不可靠的历史叙述者了。
四后卫还是先锋?
从文化研究的视野来看,社会分层导致文化趣味差异和区别化,而文化分化又进一部导致审美意识的分化,观众和电影圈艺术家群体都在复杂地变化,进而当下艺术文本全域出现百舸争流、五光十色的局面。就电影系统内部而言,各种类型突破话语边界互相借重资源、混搭、跨界、“大电影”的命名,这些是社会、大众、艺术话语场沟通活跃的体现。“在晚近的文化转变中,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过去那种以差别为根据的文化排斥和垄断已经相当衰弱,普通民众不再是被排斥的对象。相反,他们成为文化的主要诉求对象”[10]153,一种“共享文化”正在形成。陆川这次的创作实践,不能仅仅看作是进入商业片体系,而应被看作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互相介入的结果,共享文化是社会的“分层-整合”机制在起调试作用。影片将“逼真”的历史符号“红色记忆”落入神话影像系统象征界引起了解释漩涡;俗文本叙事机制与二项对立式的空间秩序相结合带来了历史反讽。这些无疑让这部影片带有某种商业外表下潜藏的内在文化的先锋性特征。“当大众文化采取激进的政治立场和疏离策略时,即使它仍保留了较多的表面商业特征和波普性,也可进入先锋的层面”[10]153。
如何让电影文本保持文化和艺术创新性,如何对接以广告文本为主体的商业美学要求,陆川在试探新的可能,“艺术不能废除有助于小圈子性格的社会分工,但它也不能把自己‘通俗化’而又不削弱它的解放效果”[11]16。在精英文化圈内部分化加剧,呈现出表面的“市场妥协”的姿态时候,不能把这个转向看得过于悲观,更应该在深层的文化研究层面来关注文本符号使用的具体状况。某些是全面导向商业文本,像某些电影的伴随文本(电影以著名文艺导演和监制为卖点,强调小资式的文化对抗)假借精英符号修饰商业消费的内核,这一种文化后卫现象才是真正的“负面的”社会整合,它在吞噬电影作为艺术的生存空间。文化先锋还是商业后卫,这样的区分有助于我们避免陷入将电影简单化看作是在艺术和产业两轴间的纠缠。
参考文献:
[1]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3]格林伯格.走向更新的拉奥孔[J].易英译.世界美术,1994,(4):10-16.
[4]艾宏扬.康德物自体的解释与分析[J].文史哲,1986,(6):93-96.
[5]诺斯洛普·弗莱.批评的剖析[M].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6]黄琳.影视艺术:理论简史流派[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1.
[7]生安锋.透视文化、重构历史:新历史主义的缔造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教授访谈录[J].当代外语研究,2010,(3).
[8]罗兰·巴尔特.明室[M].赵克非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9]LÉVE-STRAUSS C. Anthropologie structural[M].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63.
[10]周宪.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11]马尔库塞.现代美学析疑[M].绿原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唐普]
An Analysis of Spatial Coding in the “Chronicles of the Ghostly Tribe”
ZHAO Y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emiotics, the appearance of art film in commercial aesthetics is complicated, which reflects the use of symbolic rhetoric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on. In the “Chronicles of the Ghostly Tribe”, the director LU Chuan intends to mix the mythical symbol system with the strong historical texts. Therefore, the rhetoric effect of the space confrontation is crea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enre of film is not necessarily leading to the commercial aesthetics of the art film. A growing movie type framework requires multiple flows and permutations of symbolic elements in the text.
Key words:commercial aesthetics; symbolic rhetoric; Chronicles of the Ghostly Tribe; spatial coding
收稿日期:2015-10-21
作者简介:赵勇(1981—),男,河北沧州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6)04-01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