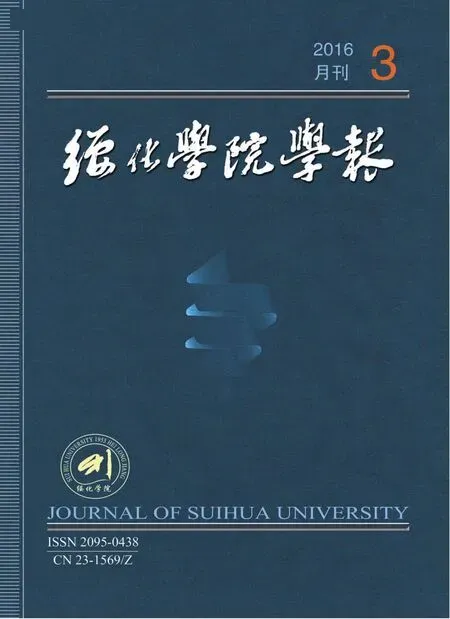清末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改革及其历史意涵
廖大伟 张华明(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1620)
清末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改革及其历史意涵
廖大伟张华明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1620)
摘要:清末新政作为清政府于1901-1911这十年间进行的一次比较全面的改革,无论是内地或是边疆都纳入到新政的范围之内,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诸多方面。可谓是清朝尝试的一次重大改革与转型。贡桑诺尔布作为边疆地区实行新政的代表人物,因地缘、族缘、人缘显有代表性。
关键词:清末新政贡桑诺尔布边疆蒙古
清末承袭康(康熙)乾(乾隆),以盟旗制和札萨克制治理外藩蒙古。札萨克蒙语为“执政官”,即旗长,一般世袭罔替,同时封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及台吉、塔布囊等级别不等的爵位,所以王公与清朝皇帝,内蒙与清政府之间,实际处于半独立、半自治状态。
清代蒙古区域广袤,因历史原因及与清皇室亲疏关系,分内属蒙古与外藩蒙古,内属蒙古各旗以朝庭命官治理,与内地州县基础相同,外藩蒙古各旗则由札萨克管理。而外藩蒙古因地缘因素加上同样的原因与关系,又分内札萨克蒙古和外札萨克蒙古,内札萨克蒙古有6盟24部49旗,①外札萨克蒙古大约有12盟8部150旗,如此如以一旗一札萨克推算,外藩蒙古王公应该是个不小的群体,从慈禧“六旬庆辰”懋赏外藩蒙古王公83人,超过“在廷臣工”,仅次于各省文武大臣的规模来看,这个判断大体不谬。
清末外藩蒙古王公群中,内扎萨克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部右翼旗的贡桑诺尔布为人瞩目,比较突出,他是清末资政院十四位外藩蒙古议员之一,且列名第二,此实属不易。《清德宗实录》《宣统政纪》出现名字23次,②也相当可观。作为清代最高官修记事文献,凡次现名均非同一般。内扎萨克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部左翼中旗扎萨克和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与贡桑诺尔布同时代,个人情况(包括与清宗室联姻)基本相仿,③而且部落地位④与世袭爵位还要占优,然而现名也不过13次。⑤迄今有关贡王的成果已然不少,尤其集中于当年改革部分,⑥然而从贡桑诺尔布的局部改革来反观整体的清末改革,它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似乎还有必要挖掘。⑦作为藩部地区某地带有某个人化色彩的创新改革,其内在动力如何,与外界何种关系,该如何看待它的成败,它又何种程度上能够反映清末改革的影响力和复杂性。
一、1901年至1905年:清廷慎重而我自先行
清末新政与预备立宪,时间长达11年。在这较长时间的改革过程中,藩部地区很晚进入中央视野,实际上将其与内地省份区别对待。
1901年1月29日上谕,“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抒己见,[1](P140)而对外藩进行管辖的官员则不在其列。同年4月21日朝廷设立“督办政务处”,督办政务处是清政府为施行“新政”而设置的中央办事机构。其负责制订“新政”的各项措施,接受各地官吏章疏,办理全国学校、官制、科举、吏治、财政、军政、商务、邦交和刑律等事务。督办政务大臣和参与政务大臣全由宗室和汉员包揽,其他藩部王公同样无人在列。这样做是有一个传统,清廷对藩部的管理有别于内地,到了光绪朝也同样如此。及至改革举措推进,也都集中在中央层面和内地空间,藩部地区迟迟得不到明确的旨意。
对待藩部有别于内地清廷向有传统,康熙即认为外藩蒙古“不可以内地之法治之”,宜顺其性,逐渐开导,后来者也始终认为藩民“风气未开”,地方比较“瘠苦”,所以很长时间这些地区一直以屏障作用而见重于朝廷,顺其自然的求稳心理始终占据上峰。但是客观地看,改革毕竟有风险,对待基础不一、情况不同的地区,适当地谨慎处理,区分轻重缓急有其必要,何况当时藩部地区确实不比内地,经济基础、教育水平和社会习俗等方面均难适合同步进行,因此当改革未取得一定经验或达到一定程度时,让其骤然紧跟,要其整体推进,这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清廷态度谨慎,但藩部中有人已经不甘人后,其便是喀喇沁部右翼旗的扎萨克贡桑诺尔布郡王(以下简称贡王)。该时段贡王在本旗(喀喇沁部右翼旗大体相当于今天赤峰市喀喇沁旗、宁城县和河北省围场县、承德市、平泉县及辽宁省建平县的一部分)革新主要集中于军事、教育与文化领域,具体表现为练兵、兴学、办报和实业。这些改革举措和创新实践,虽仅限于一位札萨克的权力范围,但影响和意涵已经超越了所在区域,穿越了历史表面。
一练兵。庚子国变之后,1901年春,贡王仿照内地先进,开始编练新军,聘请原保定武学堂毕业生周春芳为军事教官,在旗内选拔青壮年与府内年轻差役整编军队,采用北洋新军的教范与操典进行编练。[2](P117)之后还挑选王府军中乌尔固木吉、铁丹、纳木格其三名士兵,剪掉辫发,穿日本军服,进入日本在北京东交民巷的驻屯兵营,学习器械体操和军号。[2](P119)迄今虽不知贡王编练新军的实际效果如何,规模有多大,但能在外藩蒙古地区不见人先,内地各省也不见普及的时情下敢于尝试,⑧这不可不谓革新大胆,勇为前驱,因为他的试行在清廷明令各省“另练有用之兵”之前。
耐人寻味的是,清廷对贡王超前的军改行为不仅没有反对,而且有所支持,1902年4月在其“练兵筹饷”的奏折上批复“着照所请,务当认真经理,期有实效而免虚糜”,这说明清廷虽谨慎对待藩部的改革但不刻板。而之所以持谨慎态度乃是担心骤然而起也许适得其反,于大局不利,如果真能务实改革,稳步创新,又在允许与可控的范围之内,那又何乐而不为。况且“兴边”“实边”本来便是传统命题和政策方略,只不过编练新军藩部以前未有过,但毕竟合乎新政时潮又不越传统底线。由此,清末改革“灵活”的一面与非铁板一块的“空间”分析应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复杂性的意识比简单化的判断应当更被视为可取。
二兴学。从1902年起到1903年底,贡王在本旗陆续兴办了崇正学堂、守正武备学堂、毓正女子学堂等三所新式学堂。⑨这些学堂或自己主政,或由福晋负责管理,学舍和经费主要靠自己解决,学员则来自本旗贵族及平民子弟。学校条件、教学水平和学员待遇在当时当地已是相当优越了,教习基本上采取外聘,甚至有的来自国外,至于教材与授课涉及蒙、汉、日等多种语言文字。崇正学堂开学之初,坐落于王府西侧的一座院落,只是任命本旗生员为教员,罗布桑车珠尔、朝鲁等人办理校务。草创之初,没有学员应招入学,第一期学员为该旗官员子弟和王府内的青年随员。贡王之后颁布一系列奖励入学的措施,至1904年学校逐渐步入正轨。[3](P118)之后创办的毓正女子学堂,开办时有学生24人,开设蒙、汉、日文及,中外历史、地理,算术,音乐(唱歌),美术(图画),体育(体操)及家政、手工(编织)等课程,[4](P632-633、P589、P609-610)而日本女教习河原操子⑩正是贡王从上海务本女学“挖”来的。[4](P599、P605)至1905年毓正女子学堂办学效果已经初显,是年《东方杂志》报道其“近已有学生六十人,能以蒙古语写作,又能读英日文,算法、手工亦略知大概”。培养下级军官的守正武学堂聘请日本现役军官为正副教官,行日本操典,用日语授课,喊日本口令,日本化色彩非常浓。[2](P119)武备学堂培养的人才里有以培养军官为目的,专习武备的学员。学堂中的枪支、弹药、书籍、教具皆来自于京城。虽然相对于系统正规的军事训练,守正武学堂还尚待完善,但其已经迈出了向西式新军训练方向上的第一步。后期最先兴办的崇正学堂已设立宿舍、饭厅、小型图书馆,能免费招收本旗适龄儿童及青少年,不愿住校者还有马车接送,且其教材采用的是自行编撰的蒙、汉文教材。[2](P117)《蒙学堂小学章程》[2](P201)中记录了崇正学堂的四个学科阶段的不同课程及相关教法。除传统的习字,读经外还有体操的课程记录和教法。即使在整个中国,这三所类型有别的学堂当时也都属于新潮、开明和先进的,尤其毓正女子学堂这样的新式女子学堂于内地也不多见,与之当时也仅苏州、广州、上海三地总共数所而已。[5]更何况这三所学堂几乎同一时间在外藩蒙古一个旗级行政区域里出现,对此敬佩之余不免令人惊讶。
为什么贡王会有这般高起步、大投入和深用心,这可能出于他对兴学堂、办教育强烈的寄重、远大的抱负和深厚的民族复兴情结。在崇正学堂开学典礼上的致辞上他说:“我身为王爵,位极人臣,养尊处优,可以说没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可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因为我亲眼看到我的旗民子弟入了学堂,受到教育,将来每一个人都会承担起恢复成吉思汗伟业的责任。”[2](P117)其《创办崇正学堂而作》[2](P157)一诗中,贡王的民族复兴情绪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朝廷百度尽维新,藩属亦应教化均”和“无限雄心深企望,养成大器傲强邻”两句更是体现了其教育兴蒙的急切愿望。为了实现教育兴蒙的梦想,1903年秋他还从这三所学堂选拔学生分别到北京东总布胡同东省铁路俄文学堂、北京贵胄学堂、北京测绘学堂、保定简易师范学堂、保定军官学堂、上海务本学堂、上海南阳中学堂及天津北洋实习工厂学习、实践,甚至选派女生留学东京实践女子学校,[2](P122)另聘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人类学教研室主任鸟居龙藏及夫人分担崇正、毓正两校主任教员。[2]P121)贡王开明,勇于开地区风气之先,除了受清末改革大潮的影响鼓动外,也与他的见识有关。少时家父延聘名师教授其蒙汉藏文化知识,十几岁又入京为御前行走。1903年春经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的介绍,与祺承武(御前大臣喀尔喀亲王那彦图长子)、宪章(肃亲王善耆长子)等人秘密从天津私搭日本邮船东渡日本,观看了在神户举办的博览会,考查了日本的政治、经济、教育、军备等情况,结识了日本朝野名流,会见了日本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3](P221)、东京实践女学校校长下田歌子,[2](P118)并赋诗相赠,可见并非泛泛之交。[3](P160)这次访问让他眼界大开,对他影响很大,深切地认识到本地区的落后和进行改革的必要。其诗作《博览会誌游日本客中》[3](P158-159)中有“商业国所赖,劝业引绮贝”的感叹和“地大物博者,何以反较输”的反思。当时人们普遍想要学日本,“日本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向日本学习”,[6]P(1475)日本之所以能够走向发达,关键就在于“遍设各学,才艺足用”。[7](P152)其诗作《东京有感》中也有“从今鼓舞当年勇,政教让君卅六年”的期望。这种想法在贡王革新实践中表现得很明显。正如《贺崇正学堂联》中所写到的:“崇文尚武,无非赖尔多士;正风移俗,是所望于群公。”[3](P256)其正风移俗,开化蒙民的愿望相当迫切。当然也应该注意到贡王所以能如此兴学,甚至聘用日本人,这也离不开清廷的默许,那些日籍教员到来,学生外出求学,不少都经过中央政府及高官的介绍。政府对其兴学堂、办教育基本持放开的态度,前提是不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
三办报。1905年冬贡王在崇正学堂内办起了报馆,出版报纸《婴报》。[2](P122)《婴报》除登载国内外的新闻外,还有科学常识、各盟旗动态以及短评。《东方杂志》曾有报道:“蒙古喀剌沁亲王近就该王府创办一《蒙文报》,系汇选各报译成蒙文,总馆设于京师。凡内外蒙古及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处均设分馆,专为开通蒙人风气,以期自强。闻已聘定雍和宫喇嘛罗君子珍为主笔。其馀办事各员,亦以喇嘛居其多数。”《婴报》总馆亦设于京师,内容也为选取其他各报内容译为蒙文。所以笔者认为,该文所说《蒙文报》即为《婴报》。也有文章分析认为,《婴报》为蒙汉双语,[8]无论何种语言为主,这些知识与各地的信息通过《婴报》传播于本旗及更远的地方,对旗民识字运动和大众知识普及很有意义,这也是外藩蒙古地区出现的第一份报纸。
四实业。清末新政开始后,贡王就想开采本旗金矿,以求增加收入,带动实业,改善生计。1903年3月已有报道称俄、德商人得知喀喇沁“金矿甚多”,“迭次往勘,知为大利,随向中国政府禀请允准承开全旗所属金矿。”但贡王“坚决不允”。[9](P83)1904年8月由热河都统松寿代奏,“请将本旗巴达尔胡川金矿与荷兰商人白克耳集资开采,以裕蒙藩生计”,但清廷的态度是“暂缓置议”。1905年9月考察东蒙地区随员姚锡光上练兵处“筹办该旗练兵及学堂等项事宜”,也敦请中央派员次第兴办蒙古新政,建议具体为:1.蒙古军队之征集与训练,应依现代军事办法;2.蒙古土地由汉人耕种者,应由单一土地税则;3.现由热河都统所征收之鸦片税,应提高一成,并将所得转入蒙古各旗衙门,作为发展教育之用;4.对于蒙古盐产应建立统一税制,其收益亦由中央政府与各旗均分;5.东部内蒙应设立一官办银行,以加速经贸发展;6.蒙古各旗所有土地,应被承认,其由土地所得之收益亦由蒙古各旗与有关各县平分;7.自蒙古各旗输出之家畜,应制定标注税,其收益由各旗作为教育及军事训练之用。[10](P11-25)但这些建议依旧未采纳。兴办实业贡王有一定的积极性,1904年派往天津北洋实习工厂学习织布、染色等技术的四名学员归来,其在王府东坯场子村便设立了一个综合工厂,请他们做技术员,招收青年旗民为学徒工。后来又从天津高薪请来一位织毯师傅传授技术,他自己也经常亲临工厂视察。经过一段时间努力,生产的“洋布”“洋腊”“洋胰子”地毯等日用品除了供应旗内还部分投放了市场,工厂收到了一定的经济效益。[11]从此,喀喇沁旗的民族工业开始起步。进一步开发蒙区并给予相应财政支持也是合理的请求,只是清廷有顾虑有保留。之所以有顾虑有保留,一是羁縻心态作祟,稳定政策为主,有些领域不希望藩部走得太早太快,尤其担心与国外联手削减对中央的向心办。二是革新需要资金,而中央财政有限,筹集困难,所以一时还难以顾及藩部地区。
由上可见,在1901年至1905年这五年内,贡王在清廷尚未明令要求的时情下率先进行了本旗系列改革创新,并能取得一定成效,受到舆论界的重视。这些革新举措对于当时当地而言,相当超前,即对于整个藩部地区也属大胆和有力,并或多或少起到了新思想的传播和新楷模的示范作用,甚至于对清廷主导改革步骤、考虑区域布局也都产生一定影响。此外,虽然贡王的革新举措是在清廷未明令要求的时情下主动而行的,但它的基本方向、革新领域和具体事项符合时代潮流精神,也没有超越清廷可以默许的范围,假如说清廷严令禁止而非默许,这一地区的这般改革也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二、1906年至1911年:纳入布局却后续乏力
清政府正式启动外藩蒙古内札萨克地区改革进程始于1905年底。是年11月清廷命理藩院尚书、肃亲王善耆“驰往蒙古查办事件”,实际是派往调查研究,拟出蒙区改革方案。不久黑龙江将军程德全上奏各蒙开发“亟宜设法经营”,得到清廷肯定,着管事亲王、理藩院及各将军都统督抚等“各就地方情形,妥筹办理,详晰具奏”。1906年3月内阁中书钟镛进一步提出蒙古事宜十四条:“曰建议会,移建理藩院,变通理藩院官制。行殖民策,移八旗兵饷于蒙古,复围猎之制。借债筑路,设银行,铸造银铜圆。兴矿产之利,屯垦之利,畜牧之利,森林之利,榷盐之利。”这十四条建议已经明显超越了开垦筹款、移民实边的传统政策,也不再停留在练兵、兴学等具体事项上,而是涉及到政制改革和要求农林牧副矿甚至金融全面开发。是年10月,经过对蒙古东部地区实地考察,善耆向朝廷提出了经营开发蒙古的八点建议,即“一屯垦,二矿产,三马政,四呢碱,五铁路,六学校,七银行,八治盗”,而对最棘手的资金问题,他提出“一面集资,一面兴办”的想法。清廷基本接受了这些建议,并立刻饬令相关部门“筹议施行”。这一“筹议施行”,标志着外藩蒙古内札萨克地区终于纳入改革的整体布局,但仔细分析善耆的报告,还仅限于实业、资源、教育、社会等内容,并没有提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说明清廷即使此时仍还有所保留,对敏感的问题不愿涉及,对该地区改革的步子不想迈得太快。
然而既然已经纳入布局,相关的调整总得有所表现。首先为推进藩部地区改革,清廷将理藩院改成了理藩部。这似乎仅仅换一个名称而已,实际上机构职能有了改进,增设调查局和编纂局,组织起对蒙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地理、资源等方面的调查,并列出了包括牧政、开垦、铁路、矿产、森林、渔业、盐务、学校、兵制、商务、织造等多项内容的调查提纲。此外,中央其他部门及人员也对蒙区改革提出了建议,采取了措施,如“邮传部奏,展筑张绥铁路”,学部奏“订拟蒙藏回各地方兴学章程”,“派员分查蒙藏回各地方学务”,甚至于有人建议在蒙区筹建行省”。此建议虽经督办政务处讨论又饬直隶总督、山西巡抚及热河、察哈尔都统等“体察情形,通盘筹画”,但最终因牵涉太多事关重大而没被采纳,结果只是在满汉交错地区增设了一些府厅州县,添设了一些地方各官,以适当满足蒙地放垦的呼声和需求,但总体把握上清廷还是希望平稳,不希望激化民族矛盾,毕竟“旧制势难遽废”。
开启蒙地改革,伴随着清末改革向前推进的大背景。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拉开了序幕。是年11月清廷设立考察政治馆,研究各国政治制度。1906年五大臣回国,奏请立宪。同年8月,清廷颁布“预备立宪诏”,宣布“寸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改革的进程和以往经验的积累,使得清廷对藩部希望有了更新。1908年9月清廷明确要求理藩部接手进行藩部地区应行筹备立宪事宜,明确表示:“理藩部职在考查藩情,整饬边务,皆与宪政息息相通,理应同时并进”。在这样更好的背景之下,是年贡王上陈了八条建议:“银行宜早为设立也,修铁路宜速修也,矿上宜速开采也,农工商宜速加证也,外交宜及预备也,教育即宜普及也,新军即宜编练也,巡警即宜创办也。”[12](P393-400)这样的一个革新幅度让清廷难下决心,于是模棱两可地“饬部会同议办”,并要求先制订“各蒙旗办事定章”再说。可是直到清朝灭亡,蒙区“筹备立宪事宜”还一直处于空头状态,咨议局未建立,各盟旗也未有过相关选举。
1906年后,贡王虽然也有过一些设想,但锐气已不同以前。1910年与科尔沁亲王等王公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并不景气的蒙古实业公司,[13]除了得到一些荣誉,比如1906年清廷“以喀喇沁郡王贡桑诺尔布兴办学堂,赏扁额曰‘牖迪蒙疆’”。1906年2月崇正学堂增设初级师范一班,学制为三年。其于革新已乏善可陈,甚至原有的成就也在慢慢削减。1909年贡王呈请理藩部代奏要求入陆军贵胄学校听讲并留京当差,[3](P259-260)1910年守正武学堂“裁减人数,改名衙队。学堂之名义虽然存在,而其性质办法,则纯然王府衙队矣”。[14](P172)
为什么整体形势变好却步伐变慢,为什么纳入布局却后续乏力,关键在于经费无着,难以支撑。如守正武学堂“因出卖孟格沟、唐头沟地四百余顷”才得以开办,维持了几年后经费短拙,不得不裁人改名,变成了衙队。[15](P172)自筹资金困难,那么为什么清政府不及时拨款,加以支持,问题中央财政也相当困难。庚款要赔,借款要还,各项新举又一再需款。到了1903年,国家财政收支亏额已达到3000万两。[15][16](P721)到了1905年,赤字更上升到3300万两。[17](P667)无怪乎清廷一天到晚讲“共体时艰,讲求实效,省虚耗之饷以仰副朝廷力图富强之至意”,无怪乎会唠叨“赔款浩繁,加以举办要政,各省筹捐集款,重累吾民”,“早切疚心”。看来进取的王爷变得碌碌无为,问题在于炊之无米。
除了无米之炊,恐怕还有蒙地放垦,财政归属中央,王公无利的原因。因为财政困难,所以朝廷动起了蒙地的脑筋,变禁垦为放垦,鼓励流民,还美名其曰“振兴蒙务,开浚利源”。贡王就曾就相关事宜与中央商榷:“……无如田皆蒙产,地又辽阔……祗以政事分权限,不以蒙汉分权限。”[12](P401-403)但政府开禁后,流民垦荒毫无限制,农牧之间、满汉之间矛盾加剧。而对于蒙古上层,关键是民垦到官垦的性质变异,民垦得利在基层和蒙人,官垦得利归官府和中央,原可私相操作的资源变成了政府解决财政困难的筹码,内心的不满由此陡升,消极失望也开始产生。
三、结语
贡王的革新很特别,因为地缘、族缘、人缘具有代表性。蒙古王公在蒙古族社会政治生活中居主导地位,对辖区有很强的号召力,与外界接触也相对较多。开明的王公对本旗的改革掣肘较小,但要受制于清廷的态度和清政府的政策。贡王无疑属于蒙古族的翘楚,近代化的先驱,但他的动力来自兴族与保国两者的兼合。从该个案可以看到清末改革的波及面有多广,传播率有多快,影响度有多深,然而它的成败也同样折射出清末改革的勃兴与困顿。清末改革很复杂,国内的,国际的,内地的,边远的,满汉的,藩部的,上层的,基层的,城市的,农村的,如果不加以分别地看,合拢地观,也许得出的是个片面结论。
清末蒙古王公除贡王外很少有如此开明的思想,付出实践者更是少之又少。虽然一些毗邻内地的蒙古王公在思想上已有所改变,少数王公也开始筹办学校,派遣青年去内地求学,但如贡王如此大规模、全方位者蒙古王公中并无他人。
贡王改革最大的贡献是他孕育了蒙区未来,培养出了一批学生。同理清末改革的历史贡献也不限于当时,而更在于其后。大气候鼓动了小地方改革,左右了小地方改革,小地方改革也融入和推动了大气候。小地方个人色彩固可浓郁,但大环境毕竟不可抗,大气候毕竟不可违,是以个性难却时势大局,贡王之举与清末改革便系这么个关系。
注释:
①据嘉庆《一统志》,内札萨克蒙古原有“部落二十有五,为旗五十有一”,乾隆时将归化城土默特二旗归绥远将军管辖,从此内札萨克蒙古变为24部49旗。
②据《清德宗实录》、《宣统政纪》统计。
③那木济勒色楞1879年出生,1884年承继亲王爵位,1898年正式行使扎萨克权力,1902年娶清宗室克勒郡王晋祺女,1903年任哲里木盟盟务帮办,1904年任御前行走,1906年任哲里木盟副盟长,1909年任盟长。贡桑诺尔布1872年出生,1885年娶清宗室肃亲王善耆的妹妹,1886年任乾清门御前行走,1894年加辅国公衔,1898年承继扎萨克权力和多罗都棱郡王爵位,并担任卓索图盟盟务协理,1909年驻京当差,次年出任资政院议员。
④科尔沁部与清皇室渊源深厚,历史上曾有“塞牧虽称远,姻盟向最亲”的诗句,那木济勒色楞所在的科尔沁部左翼中旗,又是该部落二十个旗中四大亲王旗之一。而贡桑诺尔布出身的喀喇沁部,虽然与清皇室也关系不错,但相对科尔沁部则略逊一筹。清末所有上谕懿旨,科尔沁部一般排名外藩蒙古各部之首。
⑤据《清德宗实录》《宣统政纪》统计。
⑥主要有白拉都格其《辛亥革命与贡桑诺尔布》,《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美]札奇斯钦《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与内蒙古现代化》,《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2册,台湾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编辑委员会1981年编印、[日]中见立夫《贡桑诺尔布与内蒙古之命运》,《内陆亚细亚、西亚细亚社会与文化》,日本东京1983年印,未刊本、张国强《贡桑诺尔布对赤峰地区近代化的贡献》,《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张彩云《清末“新政”时期贡桑诺尔布教育实践活动探究》,河北大学教育史专业硕士论文,2011年、娜琳高娃《试述蒙古族第一所近代女子学校—毓正女学堂》,《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白荫泰,邢莉《崇正学堂与贡桑诺尔布的教育观》,《民族教育研究》2011年第3期、李淑霞《贡桑诺尔布与赤峰地区民族教育事业》,《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居特固勒、阿云嘎《贡桑诺尔布的改革图强及其与日本的关系》,《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宝力格《贡桑诺尔布思想述评》,《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88年第6期。
⑦参见赵云田《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
⑧仅北洋地区与湖北省已编练新军。
⑨冯诚求《东蒙游记》记录了三所学堂的地理位置:“喀喇沁王府,南拉齐山,北大头山。……府内有毓正女学堂,府右有崇正小学堂;距府八里许,有守正武备学堂。”转引自郑晓光,李俊义主编:《贡桑诺尔布史料拾遗》(上),内蒙古出版集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3页。
⑩河原操子,日本长野县人,早年毕业于长野师范学校女子部,后考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未及毕业就因病辍学,执教于长野高等女子高中。后结识当时日本著名的女教育家下田歌子,下田歌子介绍其于横滨大同学校任教,1902年应聘到上海务本堂执教。其1903年秋受命于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及武官青木宣纯,通过肃亲王善耆介绍进入毓正女子学堂执教,暗中收集有关俄国的情报,为日俄战争做准备。何原操子应聘到毓正女学堂后不久,贡王曾亲自写信给日本公使馆翻译高洲太助表示感谢。1906年河原操子回到日本,之后仍与毓正女学堂学生有书信往来。
参考文献:
[1]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M].北京:中华书局,1958.
[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一辑)[C].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2.
[3]郑晓光.李俊义主编.贡桑诺尔布史料拾遗(上)[M].呼和浩特:内蒙古出版集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2.
[4]朱有瓛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5]河原操子撰.邢复礼节译.喀喇沁杂记[A].赤峰市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C].赤峰市政协,1986.
[6]毛泽东选集(全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康有为.请开学校折[A].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C].上册, [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8]张丽萍.内蒙古近代报业的开端-兼论蒙古最早的近代报纸婴报[J].国际新闻界,2012(2).
[9]郑晓光.李俊义主编.贡桑诺尔布史料拾遗(下)[M].呼和浩特:内蒙古出版集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3.
[10]姚锡光.筹蒙刍议[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8.
[11]贡桑诺尔布与近代蒙古族历史之最[N].内蒙古日报. 2013-12-18.
[12]朱启钤编.东三省蒙务公牍汇编(卷五)[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
[13]汪炳明.“蒙古实业公司”始末[J].内蒙古社会科学, 1984(3).
[14]汪国钧著.玛希、徐世明校注.蒙古纪闻[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
[15]张神根.清末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划分评析[J].史学月刊,1996(1).
[16]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17]彭泽益.中国社会经济变迁[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王占峰]
作者简介:廖大伟,男,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张华明,男,东华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
收稿日期:2015-09-15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6)03-09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