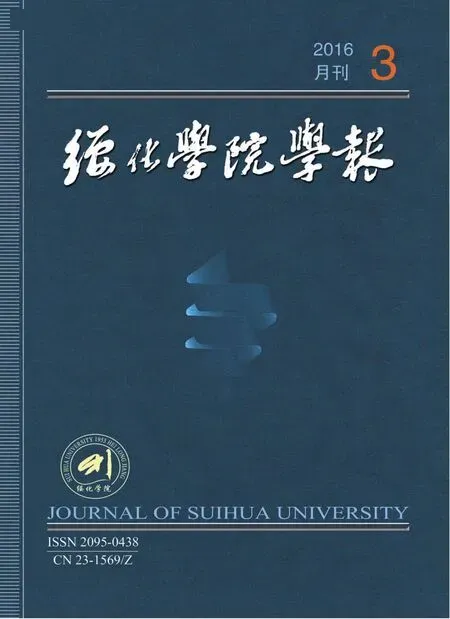萧红的身体叙事——以《生死场》为例谈女性与文化
唐诗诗(河南大学文学院 河南开封 475000)
萧红的身体叙事——以《生死场》为例谈女性与文化
唐诗诗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0)
摘要:在《生死场》中,萧红以北方乡土中国为范围,描述了战争爆发前后乡村人们的生存状态,作品对女性的苦难描写是非常突出的,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现实分不开,也与萧红的生平紧密相连——用身体做笔,写下了一曲女性存在的悲歌,既有身体的意识性与麻木的对比,也有身体的“刑罚”创痛以及悲剧性的身体“幻灭”,一步步的身体“沦陷”,引发文化反思。
关键词:身体叙事;《生死场》;文化;悲剧
萧红临死前对自己漂泊一生做了总结:“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我是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多么讨厌啊!”[1](P183)萧红的此番彻悟、怨言,与她飘零、动荡的一生息息相关,从为了躲避婚约与家里断绝关系、出走,到与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与骆宾基等在战火硝烟中辗转流浪大半个中国,在敌机的追逐下,颠沛流离于哈尔滨、青岛、上海、日本、北京、西安、武汉和重庆,贫病交加,最后客死香港,“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1](P182),年仅31岁。其中包括险卖到妓院、情感变故以及孩子夭折等一系列遭遇,而作为女人独有的体验——“生育”,给萧红的心灵留下了难以平愈的巨创,在生活中、创作中都时时隐现。
萧红有过两次怀孕的经历。先是怀上汪恩甲的孩子后被弃,只身困在东兴顺旅馆里面,差点被卖妓院,大街上洪水上涨,挺着大肚子的萧红最终被红十字会的难民船营救;和萧军分手之后,武汉危急,端木撇下萧红去了四川。萧红怀着八个月的身孕只身入川,在宜昌码头,她被缆绳绊倒,使尽全身力气却也挣扎不起,只好躺着等人来扶,像一只无助的四脚朝天的甲壳虫。战乱不断,最终两个孩子都没能留在身边,一个送人,一个夭折。萧红作为中国的版“娜拉”勇敢离家出走,是为了逃避父辈订的婚约和传统的人生道路而出走,即独立和自由的代价却是巨大的。战乱、贫困、饥饿、流离失所,个人虚弱的体质,疾病不断,都深深刻在了这个充满才华的弱女子笔下,混合着血和泪。贫困和饥饿是萧红生理上的第一道难关,第二道“生育”的关卡,这个社会施加在女人身上的责任与义务,由于没有对应的男性责任和关怀,变成了女人的苦难和不幸。《生死场》里,萧红亲身体验的痛楚在角色身上放大了。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生死场》笔墨主要集中于女性身上:在那一幅幅女性躯体伤痛、受难的流血描画中,混含着她自己亲历过的流浪、漂泊与受难的人生体味。
萨特将躯体、虐待与受虐当作是存在的范畴,身体因而成为了文化史的负担。那么萧红的女性观又是怎样以身体和生育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展现乡土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谱就一曲文化悲歌呢?
一、作为母亲的麻面婆和王婆——身体的麻木与叛逆
母亲在男权社会中是受到尊敬的。人们赋予她各种美德,“为她创造一种宗教,禁止回避它,否则就是渎神渎圣”[2]P242),母体天生笼罩着光环,然而萧红让作为母亲的麻面婆颠覆了这种认知。
麻面婆是猥琐的,且具有象征体——她的同样不健全的儿子罗圈腿,“走路时他的两腿膝盖远远的分开,两只脚尖向里勾着,勾得腿在抱着个盆样”[3](P16),是麻面婆生命意义上的延续——残缺、丑陋与退化的的生存状态。麻面婆是女性群像中最像机器般无知无感生活着的一副面孔。她“正合乎舞台上的丑角”“性情不会抱怨……像一滩蜡消融下来……她的性情不好反抗,不好争斗,她的心像永远贮藏着悲哀似的……永远像一块衰弱的白棉”。[3](P16)她的身体没有容纳自主能量的地方。其生育在萧红看来,并没有女人如获新生般惊喜的体验,而是沦为了生育的机器,逆来顺受。罗圈腿的丑相就是对麻面婆母亲形象的矮化和否定。在第九章里面,传染病席卷了这个久远的村落。冥顽的麻面婆抱着孩子,“就是给病死也甘心,打针可不甘心”“始终惧怕打针”[3](P65),最终难逃死亡宿命。过午,麻面婆把孩子送到乱坟岗子去,“她看到别的几个孩子有的头发蒙住白脸,有的被野狗拖断了四肢”。[3](P66)血淋淋的现实是愚昧、麻木与软弱造成的,如果罗圈腿的存在还肯定了麻面婆母亲的身份,而孩子得传染病死去则彻底宣告了麻面婆生命的枯竭、无果。对于这个唯唯诺诺、对丈夫俯首帖耳,不敢埋怨,任劳任怨的传统女性,萧红是彻底与之决裂的。
刚烈的王婆与麻木的麻面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她会在劳动的间隙唠叨自己的无穷的命运,因为内心的苦缠绕了身体的每个角落,以至发生了怪异行为:“她的牙齿为着述说常常切得发响,那样她表示她的愤怒和潜怒。在星光下,她的脸纹绿了些,眼睛发青,她的眼睛是大的圆形,有时她讲到兴奋的话句,她发着嘎而没有曲折的直声。”[3](P17)人们形容她是“猫头鹰”,她就愤怒抗议,“自己怎么会成为那个怪物呢?”[3](P17)她不停地向人们讲述她的小钟。她把三岁的小钟放在草堆上去喂牛,跌落在铁犁上死了。然而小钟在王婆喋喋不休的讲述中似乎又活了过来。女儿之死带来的悲痛让她更加拼命地劳作以求忘却。儿子因做土匪被官府杀死,王婆选择服毒自杀,当棺材抬到乱坟岗子时,却奇迹般的死而复生。她要求女儿继续和官府对抗、报仇,女儿又不幸死去。噩耗连续袭击,王婆痛苦难抑,内心却清楚“革命就不怕死啊,哪怕是露脸的死,比当日本狗的奴隶活着强得多”,悲痛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她的反抗、叛逆通过身体来实现——无休止的劳作让身体处于疲惫状态来抵消心灵之殇,以死亡的形式换取黑暗的结束,“事实上,她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她的肉体表达思想。”[4](P183)王婆身体流淌的能量对外在于她的世界秩序的改变是不可忽视的,既代表了女性的在场,也表现了女性权利的争取。
作为母亲的麻面婆和王婆,一个麻木猥琐,一个有意识抗争,她们不是男性笔下脉脉温存的、可疗救创伤的避难所:男性神圣化的母亲背后,“聚集了一群女性白魔法师,她们用草药汁和星星的闪光为男人效劳:祖母、目光慈祥的老妇人、好心肠的女仆……”[2](P243)在女人变老变丑、女性肉体魅力消失之后,欲望对象就变成了具有仁爱品性的仆人,即“赎回母亲,就是赎回肉体”。[2](P244)萧红的女性意识使母亲不再是男性欲望的客观对应物,不再是温驯的仆人,再不必笼罩传统母亲的光环示人,而像猫头鹰一样以凌厉的姿势反扑不断弥漫的黑暗,王婆的反抗是悲壮的。
二、身体遭受刑罚的女人
“在心理学意义上,‘自我’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躯体的五官四肢无疑是认识“自我”的素材。婴儿逐步了解到五官四肢的归属,了解到自己对于五官四肢的支配权力,最终确认躯体与‘自我’的统一。一个极端自私的人不会背弃他的某个耳朵或脚趾——躯体的范围也就是自私观念所庇荫的起码的范围。躯体产生的一切感觉——痛、痒、饥饿、兴奋、松弛、紧张——均以物质的形式阐明或注释了‘自我’这个概念。”[4](P148)萧红笔下的女人无自主意义的生育,源自于“生育是一场刑罚”,疼痛的被强加、苦难的被赋予、疲惫的被遭受,一切的被动都显示了女人自我的被隐藏。
《生死场》中的女人生存的艰难之处,在于女性本身这个性别符号。田地劳作和永远无尽头的家务使身体疲惫、身形佝偻;青春期短暂的肉体欢乐带来了怀孕、生育——这正是女性身体刑罚的开始,让她们产生惊恐和战栗,因为生殖对女人来说无异悬于生与死的边缘。对于人类来说,生殖是“种”的繁衍和延续,而对于女人来说,除了无法承受的世俗非议,还有事关生死的身体之痛。第六章萧红用“刑罚的日子”来集中展示这场群体性灾难。
五姑姑的姐姐、金枝和麻面婆在生育上面临的苦痛是一样的。暖和的季节,“全村忙着生产”的日子里,女人们的苦难开始了。“大狗四肢在颤,全身抖擞着,经过一个长时间,小狗生出来”,“有的母猪肚子那样大,走路时快要接触到地”[3](P51),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产。而女人们所遭受的,似乎比动物还多,时常像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五姑姑的姐姐难产,“苦痛得脸色灰白,脸色转黄……全家为了死的黑影所骚动”,醉酒的丈夫拿烟袋投她,拿冷水泼她,她不敢哼一声,听到门响,男人要闯进来,她便恐惧、慌张。孩子生下来就死了,“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3](P52)在夫权为天的社会里,女人的繁殖任务比动物都艰难,生产过程还要伴随着丈夫的辱骂、暴力,濒临于死亡边缘。金枝、麻面婆及李二婶子的生育,有过之而无不及。金枝临产前一天还被丈夫纠缠着做房事发泄本能,险些出生命危险,产后十天后又拖着病弱的身体去干活,屋里“小金枝哭着在呼唤她”,生命在昏天暗地里循环往复,女人的灾难也在循环往复。
“生死场”,这个北方乡村的生存与死亡,“种”的繁殖与延续,在一代代女人的苦难里继续着,安安静静、无知无觉。“身体的可利用性、可驯服性、它们如何被安排,如何被征服、如何被塑造,如何被训练,都是由某种政治、经济、权力来实施的……都是由一种惩罚制度来实施的。”[4](P4)反观“生死场”里的孕育子孙后代的母体遭受的身体惩罚,恰恰充分证明着一种落后的“文化、生存制度”的存在,规训女性服从男人的形成,这是几千年来母系文化向父系文化臣服的沉积,已然成了文化痼疾。
生育的社会学意义,言及女性对男性的服从。萧红集中笔墨的带血书写是对生殖与女性命运之间关系的一种观照。身体对于女性来说局限性更多,“女性比男性更受到物种的折磨”。据存在主义的观点,人们不断地超越,朝向更多自由以实现自由,“人类总是寻找摆脱特定命运;通过发明工具……维持生命变成活动与计划。而在怀孕时,女人像动物一样被身体束缚了……男性的活动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将存在本身构成价值。男性活动战胜了生命错综复杂的力量,奴役自然和女人。”[2](P92)生殖和繁重的家务让女性很难如男性般调和家庭生活和劳动,处于奴役地位的女性的存在本身似乎毫无价值,更无自由,生命如蝼蚁,方生方死。
三、身体“幻灭”,美丽沉沦——月英和金枝
十七岁的金枝未婚先孕,她的感觉是:“过于痛苦了,觉得肚子变成个可怕的怪物……等她确信肚子里有了孩子的时候,她的心立刻发呕一般颤嗦起来,她被恐惧把握著了……金枝仿佛是米田上的稻草人。”[2](P29)童贞崇拜与社会禁忌让身体成了罪恶之源。后来小金枝被发怒的爹给摔死,“年轻的妈妈过了三天她到乱坟岗子去看孩子。但那能看到什么呢?被狗扯得什么也没有。”女人用生命换来的孩子被粗暴地父亲摔死,从怀孕到生殖再到死亡,女人所承受的痛苦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却又消融于无结果、无意义中。身体并非永恒的,身体会发生病变、变形、残缺、腐烂、消亡直至归于尘土。这一系列的过程,是人类永远无法避免的悲剧,庄子曾言“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女人尤甚。“哪怕生命具有最吸引人的形式,其中也存在老年和死亡的酵母。多次怀孕使她变胖……岁月的流逝……变得衰弱、丑陋、衰老。”“老女人、丑女人不仅是没有吸引力的对象,她们还会引起混杂着恐惧的厌恶”。[2](P225-226)一个美丽的身体因为遭受丈夫虐待变得不堪入目,肉体魅力消失,“他者”失去观赏价值就会被丢弃。月英是打渔村最美的女人,生病了丈夫不管她,“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变绿,整齐的一排前齿也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她像一头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3](P41)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月英的臀下腐烂了,小虫在那里活跃。王婆替她擦身的时候发现了蛆虫在咬噬她的肉身。鲁迅曾痛斥中国礼教吃人的本质,习焉不察,习以为常,而萧红向我们展示的这幅惨象,难道不是落后文化的吃人本相吗?女人是被残虐冷漠的丈夫给“吃”了。
月英被男人糟蹋死,金枝最后成了妓女。妓女这个词在乡村语境中是堕落的荡妇,具有卑劣的道德品质,金枝背负沉重的道德枷锁生存着。月英和金枝的身体“污损”了。一个是物质上的“污损”,一个是精神上的“污损”,然而相似的却都“幻灭”了。在这个生死相连边界不清的生存空间里,在沉重的男权文化的压迫下,女人不过是旋生旋灭、生死循坏中蝼蚁式的生灵,女性在这里承受了深重的精神和肉体的苦难。
鲁迅评价萧红的《生死场》力透纸背,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将女人的苦难表现得非常刻骨,写出了生的坚强,死的挣扎。萧红将亲身体验的苦难同群体的生存境遇相联系,从“身体”的角度出发把女性生存的命运问题引发出来,让人深思男权文化的劣性,这是萧红《生死场》的文化价值之所在。
参考文献:
[1]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
[2]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3]萧红.萧红精品选[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
[4]汪民安.身体的文化政治学[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王占峰]
作者简介:唐诗诗(1992-),女,河南许昌人,河南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201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收稿日期:2015-11-04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6)03-006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