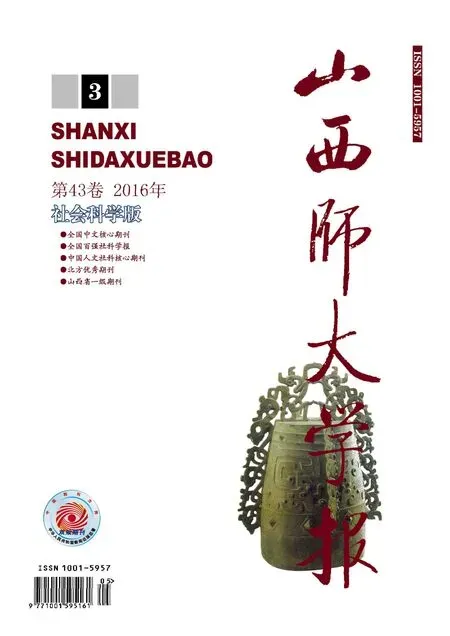西方游历小说人物的“角色”地位与功能简论
亢 西 民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众所周知,人物是小说的基本构成要素,在叙事文本建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小说情节的连缀和展开,作品主题以及作者创作意图的表达,都往往离不开人物的参与。然而,细加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在西方小说史上,作为小说主人公的人物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类型的小说中,所扮演的“角色”、地位与叙事功能却大不相同。游历小说作为一种主要的西方小说类型,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原始小说中就已经出现。在文艺复兴至18世纪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更是主霸西方文坛,成为西方小说的主流类型,至今依然绵延不绝,时有所见。[1][2]因此,人物在西方游历小说中“角色”地位如何,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无疑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 西方游历小说中人物的“角色”和地位
在西方小说发展史上,人物在游历小说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经历了一个由边缘到中心,由从属到主导,再逐渐消解淡化的过程。
文艺复兴至18世纪是西方小说的游历小说时代,这一时期,以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拉伯雷的《巨人传》、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为代表的游历小说,作为西方近代小说史上第一个主流小说类型,崛起于西方文坛。由流浪汉小说、冒险开拓小说、游历游记类小说三支劲旅汇聚而成游历小说家族,其突出特征就是都有一个游历性主人公,通过这一人物四处游走、不断移动的足迹,把一个个人物、事件、场景串接在一起,由此形成“一线串珠”式结构和“故事中心”的文本建构格局。游历小说对故事的关注与侧重,不仅与亚理斯多德所开启的西方文论传统重故事情节、轻人物性格塑造的理论偏向有关,同时与文艺复兴大发现时代所激起的新兴资产者、市民阶层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发财致富的时代精神,以及浪漫主义时代因自然美的发现而引起的旅行热具有密切关系,并由此对作家的创作产生导向和制约作用。
在游历小说“故事中心”的建构格局中,人物相对处于从属和辅助地位。尽管也不排除出现《堂吉诃德》这样人物性格成功塑造的佳作,但总体而言,作家小说创作的重点不在人物性格刻画,而在奇诡险怪、引人眼球的事件的择取和铺排,人物在小说中只不过起到一种连缀事件的穿线作用,与故事情节相比,人物显然处于次要地位。在《格列佛游记》中,作家并不把笔墨聚焦在同名主人公的性格刻画上面,人物在小说中的作用仅限于把四个不同海岛的游历串接在一起,不同岛屿种种奇特怪异的故事、事件才是作者和读者关注的重心所在。小说主人公的地位、作用正如雅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在谈到勒萨日的游历小说《吉尔·布拉斯》的同名主人公时所说,他“完全不是人,而是一条缝合小说情节的线”。[3]27
值得一提的是,有不少游历小说,如被称为16世纪西班牙第一部流浪汉小说的《小癞子》、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以及《格列佛游记》等作品,游历主人公还同时扮演着第一人称故事讲述者的角色。人物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自己的游历故事,既是冒险故事的经历者,同时又是故事的叙述者。但一般而言,不管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的游历小说,作者和读者关注的重点依然是故事叙述者所讲述的“故事”,而非故事的讲述者或穿线人物。
19世纪西方小说进入以家庭社会小说为主流的小说黄金时代。在以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为代表的家庭社会小说创作中,作家把艺术聚焦的重点由故事、事件转向人物性格与命运的刻画,具有典型意义的家庭社会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塑造成为艺术创造的重心,形成“人物中心”的文本建构格局。小说创作“人物中心”文本建构格局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19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巩固,社会秩序相对趋于稳定,一般社会成员的生活兴趣由外向内发生转变,生活方式也逐渐趋于稳定的家居生活;就小说的形态演变而言,也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小说读者的阅读经验、审美心理不断走向成熟,而自然从对故事的兴趣转向对人物性格命运的关注,由此而导致文学观念发生变化,以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方式再现客观生活的新的文学观,取代了以前以游历主人公不断游历的方式串接展示生活的文学观;同时,在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沦落底层的小人物、流浪儿的生存处境与命运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上述种种原因促使作家把目光转向人物性格及其命运的刻画。
这一时期的游历小说创作题材发生了变化,由成人历险转向儿童历险和科幻历险,出现了一批以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斯蒂文森的《荒岛探宝记》为代表的儿童流浪、探险题材的游历小说和以儒勒·凡尔纳、威尔斯为代表的科幻题材游历小说作品,但总体而言,与上一时期相比,游历小说创作已风光不再,处于衰减消退阶段。受家庭社会小说“人物中心”建构格局的影响,游历小说的主人公成为关注的焦点和被叙述的对象,其地位亦随之上升,并从边缘走向了中心。
小说创作向“人物中心”的转变,不仅意味着作家不再满足于以故事事件的奇诡险怪吸引读者,而是把艺术创造的兴趣转向人物性格、心理、服饰外貌的刻画与人物生存处境和命运的关切。同时就故事讲述而言,前一时期作者所倾心的大量的毫无逻辑因果关系的事件的罗列性展示,让位于对一系列具有严密逻辑因果关系的事件的叙述,作家更加关注情节线索的安排、故事讲述的策略与技巧手法,在人物成为文本构建中心的同时,小说故事讲述的艺术亦随之走向成熟。如狄更斯的《老古玩店》的主人公小耐尔美丽善良、聪颖早熟,形象十分可爱感人。为了生存,她带着外祖父四处流浪漂泊,极力与命运和恶势力进行抗争,其遭遇和命运也始终紧紧吸引着读者,作品故事讲述的艺术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20世纪以表现主义小说、意识流小说、新小说、黑色幽默小说等为代表的现代、后现代小说崛起,成为西方小说的主流。这一时期占文坛主导地位的现代与后现代小说从观念到表现内容、形态特征都发生了嬗变。小说创作的宗旨不再是反映现实、再现客观,而主要是显示自我、表现主观,从而使小说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内向性、表现性特征。在创作形式和技法上也打破了传统,进行新的创作实验,或者干脆采用“反小说”的形式对传统小说从内容到形式进行彻底的颠覆与反叛。人物塑造不再是小说文本构建的核心,取而代之的是作者或人物意绪的主观性陈述和呈现,小说创作“人物中心”被“意绪/哲理中心”的文本建构格局所取代。“意绪/哲理中心”小说建构格局的形成,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面对高度发达的物质、科技文明和危机重重的社会现实,使中小资产阶级深感“物”对人的沉重挤压,以及忧虑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给人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因此对现实、未来产生悲观情绪。加之先后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人们对理性、人道的崇拜和人类自我完善能力的信赖,孤独感、幻灭感、荒诞感、悲剧感成为社会成员普遍的现代意识,从而促使作家把审视的焦点从社会问题扩展转移到了人的心灵世界和精神生活,表现的内容由对社会现实的再现转移到了对社会给人心理造成的痛苦、压抑以及种种主观感受的表现。同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萨特存在主义等非理性主义哲学也为作家认识和表现人的意识活动和对社会人生的感受提供了理论工具,而最终导致了西方文学观念及其创作由再现客观到表现主观的方向性大转移。
这一时期的游历小说创作,除了偶尔一见的传统类型的游历小说创作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出现了现代人的精神游历小说,同时,还出现了一些魔幻、玄幻、科幻类型的另类游历小说。这一时期的游历小说创作,除少数秉承传统的游历传统小说之外,更多的则是受现代与后现代主义小说“意绪/哲理中心”的影响,不仅故事情节逐渐淡化、碎片化,人物塑造也出现内向化和“物化”倾向。作者对社会及人们生存状态的哲理感悟、以及人物的意绪成为小说表现的对象;小说中人物的中心地位被消解、边缘化,人物性格刻画、形象塑造不再是小说文本构建的中心,作家聚焦的重点不是外部世界的游历冒险,而是向人物内心的精神游历方面转移拓展。
某种程度而言,这一时期的意识流小说都具有一定的精神游历因素。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通过主人公布鲁姆从清晨至午夜在都柏林的“人海”漂流,展现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自我追寻的心理漫游史;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写的则是人物看到墙上的一个斑点后,须臾间思绪联翩所引发的一连串幻觉和遐想。小说完全是以人物的意识流动作为建构中心的,以人物的思绪而不是故事或人物性格刻画构成了小说的骨架,展示了发生在人物内心精神游历的“足迹”。在这类小说中,人物的游历更多地不是体现在物理的空间层面,而是在心理的精神层面。在以J·K·罗琳的《哈利·波特》为代表的魔幻、玄幻小说中,人物在魔幻世界和空间中的冒险游历活动,与其说是物理的地理的,不如说是精神的,人物在魔怪精灵世界的魔幻之旅,实则是人物的精神探险和遨游之旅,由此而彰显和张扬的是人的主体精神和灵魂自由。
二、西方游历小说中人物的功能与作用
游历小说中人物的功能与作用与小说中的角色地位密切相关,主要体现在结构功能、叙事和观察展示功能、承载表现意识形态功能等方面。
首先,游历小说人物具有穿线连缀的结构功能。游历小说与其他小说类型的最大不同就是时空的频繁切换,主人公居无定所、四处游走,通过主人公不断移动游走的足迹,将纷繁、杂凑,甚至互不相关的人物和事件串接起来,从而把小说建构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在小说中主人公作为游历者或兼具第一人称的故事讲述者,主要承担“穿线连缀”的结构功能,起着连接人物和事件的作用。
游历小说的鼻祖《奥德赛》就是通过奥德修历险返乡的足迹,把一连串互不相连而又充满凶险和诱惑的经历和事件相串接,以凸显主人公坚定的返乡之志和崇高的英雄品质。人物的这种穿线功能和手法被后来的游历小说所继承,并发扬光大。在《小癞子》中,同名主人公先后跟随瞎子、修士、穷乡绅等几个不同主人,由此生发出一连串不无滑稽悲剧色彩的人生故事;他在各个不同主人那里的经历和见闻构成小说的整体情节结构,但这些单个故事之间几乎毫无联系;每个故事之中,小赖子之外的其他人物相互之间也不发生关系。如果把《小癞子》中的故事、事件重新排序或加以增减,也不会对小说产生大的影响。但倘若把各个故事中的“串线”主人公小癞子抽掉,那么作为一部小说的叙事情节就会荡然无存。由此可见“串线”人物在游历小说中至关重要的串线作用和结构意义。
《堂吉诃德》可谓游历小说中串接种类最为繁多的一个样本。小说中不管是风车大战、骑士册封、冲杀羊群,还是与酒囊大战、与雄狮比武,这些荒唐滑稽、令人啼笑皆非的种种囧事皆堂吉诃德亲身所为,通过这一人物把它们都连缀起来了。但作品中,还有几个长短不一、情节各异的故事则是他人的经历,如维德马上尉讲述的被俘虏的故事、牧羊人的爱情故事,以及神甫当众朗读的一份拾到的手稿《一个具有好奇心的鲁莽汉子的故事》,这些衍生的次要故事与主要情节没有任何逻辑关联,也并非叙述主要情节所必须,其人物也不是堂吉诃德,但其故事与唐吉诃德的经历相交叉,并不使得作品的结构变得零散,这不但得益于作家高超的写作技巧和情节安排,更应归功于主要人物堂吉诃德对这些情节的穿线连缀功能。堂吉诃德或者是这些次要情节故事的倾听者,或者是旁观者,这些互不相关的故事都在堂吉诃德身上找到了相交点,人物在这里对故事情节的串接作用也由此得以实现。
即使在《尤利西斯》这样的精神游历小说中,人物的穿线功能也有完美体现,小说中莫莉、斯蒂芬、鲍伊岚等人物都与布鲁姆有关:布鲁姆是莫莉的丈夫、鲍伊岚的情敌,以及斯蒂芬臆想中的父亲,他们各自的不同经历和精神游历在布鲁姆处汇合,布鲁姆个人的精神游历和行动踪迹又将其他人物的经历贯穿起来,使意识流小说中本来凌乱的情节开始变得规整和有迹可寻。
其次,游历小说人物还具有一定的叙事和观察展示功能。在第一人称叙事的游历小说作品中,人物既是游历故事的经历者,同时又是故事的叙述者,人物直接承担着叙事功能,直接向读者讲述主人公所经历的一切。而在第三人称叙事的游历小说中,游历主人公则既是经历者又是观察者,作为读者的代表四处游历冒险、观察和游览。跟随人物不断的游历活动, 读者和人物一起遍览现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目睹人间种种丑剧、人生百态,人物在此承担着观察审视生活和展示生活、再现生活的功能。与读者的不同在于, 人物始终不曾离开那个书本中的生活舞台, 一直在游历和“演出”,读者则一直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和书本世界之外。跟着《小癞子》的主人公,我们看到修士的吝啬、神甫的荒淫,以及和小癞子一样的贫民生活的困苦;跟着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主人公的流浪经历,作家为人们展示出社会底层童工的悲惨命运、小人物生活的艰辛、金钱对人性的腐蚀、资本主义对底层人们的摧残伤害;跟着《长夜行》的主人公巴达缪从欧洲走到非洲,从非洲抵达美洲,遍及大半个地球的游历,人们看到战争的残酷、军队的腐败、非洲的落后、殖民主义的残忍,从城市到乡村人情淡薄的世间百态。在约翰·班扬的梦幻寓言小说《天路历程》中,即便作家用梦幻手法和寓言的形式讲述主人公基督徒为消除罪孽而寻求天国的故事,所到之处全被隐晦的称为“毁灭城”“死阴谷”“失望沼泽”等,我们还是能够从中看到当时英国社会矛盾尖锐、人性沦丧的社会现实,游历小说展示生活的功能也同样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游历小说的观察展示功能不仅仅表现在对外部社会生活、人生百态和重大社会问题的观察展示方面,同时还体现在对形形色色的不同类型人物及其隐秘的内心世界与人性的洞察透视上面。
再次,游历小说的人物还具有意识形态上的承载和表现功能。游历小说与其他类型小说相比,具有更为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这种意识形态属性在早期“故事中心“的游历小说中,主要是通过人物所串接的事件以及作者对于事件的观点、态度加以展现的,在“人物中心”或人物占据主导地位的游历小说创作中,人物往往成为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和表现者。游历小说的人物在小说中,不仅是社会生活种种事件的经历者和体验者,同时也是观察者和评论者;游历人物游历冒险的动机、目的,以及他们的人生观念、信条与理想,往往都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一般流浪汉小说中的人物,在居无定所的游荡中总持有一种特殊的生活信条,并在这种信条的指引下经营自己的游历生涯,其所作所为都被深深打上了个人意识形态的烙印。《小癞子》中拉撒路刚开始流浪之际并没有特别的信念指引,只是迫于生存需要不得不四处游荡。残酷的生存竞争教会了小拉撒路谋生的一切手段,坑蒙拐骗,无所不为,也让他意识到最便捷的生存之道只有一个——为了温饱放弃一切。坚信这条人生信仰的拉撒路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无动于衷地背负耻辱,所有这些在拉撒路看来不过是为了得到宽裕的生活付出的微不足道的代价。这种为了生存温饱而不惜放弃一切道德操守的生存信条,几乎是流浪汉小说中挣扎在饥饿线上所有流浪汉的生活观念。这些流浪汉的主人公不仅对于这些人生信条津津乐道,对于放弃道德操守而换来的生活所得甘之如饴,小说作者对于这些也少见尖锐的批评与责难。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意识观念也在不断变化,人类的游历活动不再是简单的出于生存的需要,而是更多地与人类好奇冒险的自由本性和时代精神激发的追求财富、知识、真理的热望相关联。《鲁滨逊漂流记》中,同名主人公外出航海的冲动不仅仅是为了寻找一块面包来维持生存,而是当时英国一个“真正的资产者”(恩格斯语)对海外财富的渴望和殖民的向往。一旦流落荒岛之后,鲁滨逊就用自己信奉的基督教文明将美洲本土文明抹去,他为自己救出的俘虏取名“星期五”,他不想知道也不屑于问他本来的名字,其本质便是一种文明对另外一种文明的压制和漠视。鲁滨逊把“星期五”的美洲本土信仰斥为迷信,并竭尽全力将其清除,直到“星期五”的本土信仰被彻底抹杀,他真诚地相信自己的基督信仰拯救了一个野蛮人的灵魂。然而小说中“星期五”作为土著的聪明是鲁滨逊所不能理解的,星期五能用羊头骨做会发出美妙音乐的乐器,用石头做捕兽器,对于这些美洲土著特有的迥异于基督教文明的本土文化,鲁滨逊所代表的殖民者并不能够平等看待,从而显示出西方殖民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
战争是考验、透视人的理想信仰和人性、人格的试金石和放大器,理想信念的高下、人性的善恶、人格的崇高卑劣,往往只有在最极端的战争环境、在生死危难之际才能够被极致表现。格拉斯的《铁皮鼓》正是这样一部以二战时期德国为背景反思战争、拷问人性的作品。作品的深刻之处在于通过主人公奥斯卡的观察揭示法西斯战争爆发的原因、以及人的劣根性在其中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法西斯为何能在德国如此肆虐?大多数群众为何狂热地拥护希特勒?成千上万的人为何成为法西斯暴行的实施者?为什么这些参与者并非全部都是被迫的,有的不仅出于自愿,而且认为这样做是献身自己遵循的神圣信仰?《铁皮鼓》从深入剖析人性、人的灵魂入手,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小说写到一个缺乏主见的但也还算得上正派的市民马策特拉,在1934年受当时社会纳粹狂热信仰和盲目从众心理的影响,跟随其他人一起加入纳粹组织,但这时他还并不十分肯定自己的选择,所以一直都处在与政治若即若离的暧昧状态。他先是戴上党帽,过一段时间才穿上褐衫,接着又穿上党裤,最后确定这样做没什么大的危害时才登上皮靴、穿全套党服去参加纳粹集会。在这里,作者给我们展现的是这样一个普通市民的理想和信仰何等脆弱和易于改变,那些平日里虔诚善良的普通人在极端战争环境下,受某种冠冕堂皇的所谓神圣理想和狂热信仰的激发,内心自私隐秘的欲望被释放出来,开始聚众作恶。这种恶在个人身上是必须受到惩罚的,但在集体则变成一种强硬的保护机制,每一个人都不需要为自己的恶行负责,因为集体恶的意识可以承担这些结果,而人只要成为这种集体狂热意识的实行者就行。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战前善良的民众变得凶残的重要原因。除了这些主动作恶的人,那些不作恶的人也被动变成集体利益主宰的工具,决心永远置身于成人世界之外的奥斯卡也在纳粹的演讲台下,作为鼓手一味敲他自己的鼓点,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纳粹组织的活动。在这样一种集体意识占据主导话语权的时候,个人只能沦落为集体的工具,具有特异性的人性也被集体意识泯灭。事实上,除了战争这种极端情况外,人性非光明的一面在其他条件下也会被激发出来。在小说中,我们看到奥斯卡用他那能震碎玻璃的声音划开玻璃,诱惑别人偷窃。这些偷窃者身份各异,有穷人也有富人,有老人也有年轻人,甚至还包括奥斯卡认为可能是自己生父的扬。奥斯卡耐心十足地引诱别人去偷窃并非出于善良的动机,更不是为了帮助别人,而是如他所说的“受邪恶左右”,他认为自己设置的诱惑的陷阱是帮助人们认识自己灵魂中非光明的有效方式,通过这种考验,所有的人可以重新发现自己的良心,考验自己的道德。
人物意识形态功能的承载和表现是游历小说最能激发读者内心情感和理性思索的地方。从表现社会底层人们的生存追求到时代英雄冒险开拓、对财富的渴望,以及人们对理想信念、精神家园的不懈追寻,对生活信仰、人性弱点的反思,游历小说中的人物在不停地行动和探寻,读者也随之在不断思索,或许这正是游历小说至今依然能够打动读者、具有悠久的思想魅力之所在。
[1] 亢西民.欧洲小说源流刍论[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2] 亢西民.西方小说形态论纲[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
[3] (俄)雅克多5什克洛夫斯基.故事和小说的结构[A],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M].方珊,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