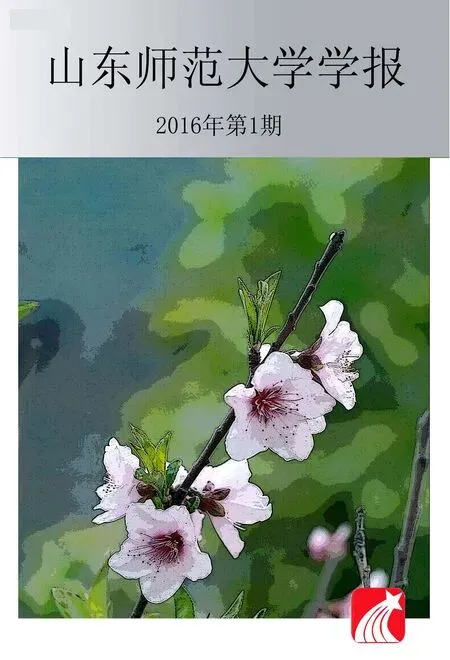书在读我——关于读书的“颠倒歌”*
杨 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书在读我——关于读书的“颠倒歌”*
杨 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摘要:此乃读书的“颠倒歌”,把“人读书”颠倒为“书读人”。在以往书与人的互动关系中,人多为主体。但当人书地位倒转,书占据主动地位之时,书将质疑和挑战人的阅读。书本反客为主,首先是以群书触发人的问题意识,要求进行多维度思考,以小见大,举一反三,由此及彼,以新的领悟及阐发回应书本知识,从中发现生命。其次是群书要求人持谦逊之姿,调动主体潜力,尊重书本所反映的时代与地域文化特征。其三是群书要求人将已得知识融会贯通,追本溯源,做有据的推断,不可妄加蠡测。群书读人,需要以书为本,调动多维的方法,借前人的智慧激活自我思想,方可开卷无愧,掩卷有得,亦正乃“书在读我”之乐趣所在。
关键词:书读人;颠倒歌;返本归原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6.01.001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讲座教授。
一、枕上得来的话题
宋朝的欧阳修是一代文章宗师。他四岁丧父,母亲郑氏教他读书。家贫买不起更多的纸,就用芦荻画地学书。考进士的时候,两试国子监,一试礼部,都得了第一。他喜欢用数字表达自己得意的事,后来居住在颍州,家中集古一千卷,藏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他就以一翁老于五物间,自号“六一居士”。他自称作文的灵感多来自“三上”,即“马上、枕上、厕上”。“三上”之说,出自欧阳修的《归田录》:钱思公(钱惟演,吴越末代国王钱俶第七子,西崑体诗歌的领袖,当过枢密使,参与修撰《册府元龟》,钱惟演家藏书极富,可与秘阁[国家图书馆]相比)虽生长富贵,自少嗜好读书。在洛阳时,曾对他的幕僚说:“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每次上厕所,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其笃学如此。欧阳修说:“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①欧阳修:《归田录》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4页。
为什么要提起欧阳修的故事呢?因为我在一天早晨躺在床上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个题目:“书在读我”。这就切合了欧阳修的“马上、枕上、厕上”,题目的构思正是来自枕上。既然书要读人,那么我们就要明白书是何物。《说文解字》说:“书,著也。”②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17页。小篆的“书”字,是上面一支笔,下面一个“著作”的“著”字。但在甲骨文中,“书”字是上面一只手拿笔,在一块方板上书写,“著于竹帛谓之书”。《易经·系辞下》讲了文字和书的起源:“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刔。”汉代郑玄注解“结绳”,说是“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①孔颖达:《周易正义》卷八,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56页。有了“书契”之后,百官靠它治理政务,百姓用它了解世界,官民就以书契来决断万事。书的功能好生了得,它胸罗万卷,是知识的宝库,人们从中了解治理政治社会的方法,提供各种各样的决策参考。人的见识在浩瀚的书海中,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因此,书读人,就是以包罗万象的知识来考察人的一孔之见了,以大观小,岂不令人诚惶诚恐?
人读书,和书读人,角度完全颠倒过来。读书的角度一变,领略到的知识滋味就全然不同。书读我,书是活的,书中隐藏着聪明的古人、前人(包括中国人、外国人)的智慧和生命,可以从多种多样的角度,给人们的思想注入智慧和生命的泉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以开阔视野,敞开心窍,接受书中智慧和生命的灌溉。由此书读人的路径,也是通过眼学、耳学、手学、心学,尤其是脚学,反灌到人们心中。这种反灌,来自书里书外。民间传说,是一种流动着的书。河南民间流传舜帝与二妃的故事,说是四五千年以前的舜帝不太喜欢尧帝的大女儿娥皇,而喜欢尧帝的小女儿女英,想立女英为皇后而找不到理由。于是就赠给女英一头骡子,而把一头老牛赠给娥皇,告诉她们谁先赶到他那儿谁就是皇后。女英骑着骡子,一路领先,春风得意,感到胜券在握,不料骡子中途产下一只骡驹,耽搁了许多时间,眼睁睁地看着娥皇骑牛跑到前头,抢先赶到舜帝的面前。舜帝枉费心机,未能如愿,把气都撒到骡子身上,命令骡子以后不许生骡驹。因此直到现在,就只有牛、马能够生牛犊、马驹,骡子没有生育能力。这一物种本源的想象,不是熟读典籍而不接触民间的知识者所能想象出来的。民间传说中的舜帝,比文字记载中的舜帝更多人间的情感。但它毕竟还是人在议论骡子,全是人在说话,骡子没有话语权。所谓“学海苍茫,敢问路在何方”?这就牵引我们进一步反思,在先秦诸子那里,黄帝及尧舜的传说在春秋战国时进入思想创造的前沿,诸子何尝是在“伪托”,他们何尝只是来自“王官之学”,他们常常透过口头传统,窥探中国文化的本源。于是诸子书启示我们,引导我们走向苍茫大地,以脚丈量着中国文化的血脉是怎样发生、怎么流派纷呈的。诸子书处在主动的位置,促使我们不以僵硬的教条去套先秦诸子的智慧,而应该借先秦诸子书激活我们思想的活力。这就是书读人的妙处。
书处在主动的位置,书主动说话,书中的人物、动物、植物也跳出来发言,就会使我们对问题的结论发生反客为主的根本性改变。我曾经强调,读书做学问,要“眼馋心勤”,眼馋就是看见好书就恨不得拿过来一口吃掉;心勤就是把书吃下之后要细细地在心里头咀嚼消化;消化的办法,既要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要学会“百尺竿头,懂得转身”。为学之妙,在于改变脑筋。有些百思不解的问题,只要一转身,换了一个角度,就豁然开朗,生发出新的思路和意义。已经书写下来、或者没有书写下来的书从它们的立场出发,促使我们开眼,开通思想的新经纬。有一个外国的幽默故事,是可以使我们开眼醒脾的。它说:母鸡和奶牛在拉家常。母鸡埋怨人类对她采取双重标准,叽叽咕咕地说:“你看你看,人类自己节制生育,却拼命地挤兑着我们母鸡多下蛋。”母牛哞地叹了一口气,抬头望着苍天说:“母鸡妹妹,我受的委屈更是无处诉说,天下那么多人天天喝我的奶,但是就没有一个人叫我一声‘妈’。只好我整天自己叫自己‘妈呀,妈呀’的叫了。”书中的母鸡、母牛开口说话,告诫我们不可固执己见,要懂得多视角前后左右看世界,这样才能开窍。书读人,是从各种角度读人,我们也要懂得转换角度,才能吸收书中从舜帝到骡子、母鸡、母牛的丰富智慧和不拘一格的思维方式。人读书与书读人的转身互换,讲究的就是“通透”,心灵通达透彻,精神游翔天地,知识糅合着生命,处处发出智慧的笑声。
这头奶牛和这只母鸡简直成了精,它们一转身就变成文化的牛和鸡,开口说的是文化人的话。它们一开口说话,就“幽”了人类一个“默”,使人类无言以对,很是尴尬。这就要求我们行走于苍茫大地,接纳八面来风,才能超越自身的狭隘。必须沟通人、牛、鸡,正如必须沟通文、史、哲。中国有一句古谚,说:“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明代三大才子之首是杨慎(杨升庵),他是正德年间的状元,《明史》本传说:“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杨)慎为第一。”①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九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083页。他编辑的《古今谚》就收录了“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这条谚语。我们听到书中鸡啼牛鸣,腔调出乎意料之外,是否也会面色如土?鲁迅应美国人伊罗生之约,和茅盾共同编选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他1934年在上海为之作的序言中曾经引用了杨慎记录的这则谚语。鲁迅说:“至今为止,西洋人讲中国的著作,大约比中国人民讲自己的还要多。不过这些总不免只是西洋人的看法,中国有一句古谚,说:‘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②《草鞋脚》小引,《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21页。鲁迅是希望中国的文学艺术,应该由中国人给出一个有主体性和创造性的说法,以中国的声音和世界进行深度的对话。我们有自己的心肝肺,我们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发出自己的深刻、独特、又具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声音。澳门的学者也应从中受到启发,走到学术的前沿,建立影响卓著的“澳门学派”。澳门从16世纪起,曾经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因而不能单纯地靠外人来读澳门,而是澳门人自己读澳门,还要以澳门读中国,澳门读世界。有学者说,“澳门性”,就是“小地方,大文化”。这种“大文化”的文本,刺激着阅读地域性和世界性相渗透、相融汇的“小地方”,阅读人心中的“时空崩溃”和精神再造。用大视野读澳门,面向海洋吐纳风云,才能读出澳门的真谛。
那么,书睁眼读人,开口说话,对读书人、研究者评头品足,会不会使人惊吓得目瞪口呆,面色如土呢?书读人,使人开窍,使人不固执,人与书将心比心。我们读书,一向提倡问题意识,提倡刨根究底,提倡返本还原。我们总是会追问,书的作者是谁,为何把书写成这个样子?老子、庄子是谁?为何把《老子》《庄子》,写成这个样子?由此而追寻书中的生命痕迹、智慧形态、微言大义以及它所表述的原本意蕴,这样就能把书读活,读出一部“活的《论语》”,“活的《老子》、《庄子》”。书既然被激活了,它于是站出来“读人”了,它也会反问:读书者、研究者诸君,那么你们是谁?为什么对我们区区之书,用红笔、蓝笔画道道,圈圈点点,还得出如此这般的结论?书读人,要反问人是否够格,是否具有“四心”:一是诚心。你们热情、诚实,感到开卷有益,对我们书别有一份尊重,还是浅薄荒唐,糟踏书,让我们感到痛心?二是恒心。你们面对着我们书,是否孜孜不倦,有阅读的恒心和毅力,还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三是贴心。你们是深入我们书的内在脉络,“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③苏轼:《稼说送张琥》,《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39页。,从大量的材料上托出创新的见解,还是找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概念,给我们书乱贴上五颜六色的各种概念标签?是否设身处地,体谅到有些标签贴得使我们书感到舒服、还是不舒服?四是慧心。你们是把我们书当成没有生命的故纸堆,满足于读死书,还是能够慧眼观书,融会贯通,点醒我们蕴蓄着的生命?书在用冷峻的眼光考量着人读书的诚信度和解读的能力,只要你“四心”俱足,就会对读之时,书乐,人也乐。南宋末年的翁森《四时读书乐》诗云:“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明人吴应箕辑《读书止观录》卷三云:“万金之富,不以易吾一日读书之乐。读书者当观是。”④吴应箕辑:《读书止观录》卷三,合肥:黄山书社,1985年,第35页。能够如此,书与人就生命互换,趣味交融了。
二、老虎分南北的启示
书是沧海,海纳百川,烟波万顷。个人的知识无论怎么渊博,对于浩瀚无垠的书海而言,不啻于涓涓细流。因此对于如此沧海,只能采取流水朝宗的谦虚态度。古代臣子朝见帝王,“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觀,冬见曰遇”①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348页。。《尚书·禹贡》说:“江汉朝宗于海。”②孔颖达:《尚书正义》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11页。孔颖达疏:“朝宗是人事之名,水无性识,非有此义。以海水大而江汉小,以小就大,似诸侯归于天子,假人事而言之也。”因而近人黄药眠《我梦》诗云:“我梦作羽薄的白云,飘流光海无踪——但我终是江波一滴,向着大海朝宗!”沧海一般的许多书都是腹笥便便,胸罗万卷,眼光灼灼地看着读书人,看你能否入乎其里而知其趣,出乎其表而通其妙。因此,我们也应该眼光灼灼然,运用识力,选取适合书籍本身的思想方法,游翔书海,多维度对书中万象进行意义类比编码,引发出智慧的爆发和思想的原创。既要我读书,发挥自我的主体潜力;又要“书读我”,检验我们返本还原,进行有根原创的能力。由此书为吾友,吐纳知识而成沧海。
在中国古代群书的知识海洋中,有很多关于老虎的故事。虎故事不是一堆死材料,多是虎虎有生气的,但它们散布于各种各样的书籍之中,为了避免叠床架屋,互相踩踏,就应该选择一个明快敏捷的角度,如庖丁解牛那样将之进行分类和编码。群书灼灼逼人的眼光,使我们诚惶诚恐地选择了人文地理学的利刃,使虎故事在连通“地气”时进行有意义的排比编码。唯有如此,知识海洋中的一滴水,也能成为有生命的一滴水。《说文解字》云,虎乃“山兽之君。”古代的中原是有老虎的,连甲骨文也记载了商王打死一只老虎,在虎骨头上刻字,一块儿陪葬。甲骨文的“虎”字,以巨口利齿、斑纹利爪为特征。中国西部的古羌族,是以虎作为图腾,古羌族分流出来的彝族、纳西族和土家族,都是用虎作为图腾崇拜的神圣对象。所谓“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加上老虎,就占据了东南西北中央五方:龙,东方也;虎,西方也;凤,南方也;龟,北方也;麟,中央也。老虎从西方虎视眈眈地窥视着研究者,看你如何编排它们、解读它们,切不可落了一个“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窘态。
文化典籍在春秋战国之世群峰崛起,引导我们思索老虎故事的成熟与中国思想方式的成熟,存在着某种同步的状态,出色的虎故事就出现在这个时期。故事一旦成熟,是可以影响人的思想方式的。春秋战国时期有三个虎的故事最有名,一个关联着圣人,两个关联着国王。一个是《礼记·檀弓》的“苛政猛于虎”③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92页。。孔子过泰山侧,听闻一个妇人哭得很伤心,孔子问她为何如此恸哭,她说老虎把她家三代的男人都吃掉了。那么,为何不搬走呢?因为这里没有苛政,没有苛捐杂税。孔子叹息:苛政猛于虎!从政治维度、时间维度进行解释,这个虎故事是用孔子的仁学和德政思想批判苛政。但是,如果换为空间维度、人文地理的维度,为老虎的生态设想,就发生了意义变化。它透露了人的政治经济活动,使一部分人进入了老虎的生存领地,所以产生了人虎的对抗,老虎才凶狠地把你家三代男人吃掉。这个是齐鲁之交的泰山老虎。
第二个有名的虎故事,是《战国策·魏策二》的“三人成虎”④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卷二十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233页。,魏国的老虎。魏王派庞葱(又作“庞恭”)陪伴太子到赵国邯郸做人质。庞葱临行前忧心忡忡地对魏王说:“现在有一个人说,街市上出现了老虎,大王您相不相信?”魏王说:“不信!”“有两个人说,街市上出现一只老虎,大王您相信吗?”魏王回答:“这我就有些怀疑了。”“那么要是三个人都说街市上出现一只老虎,大王您会相信吗?”魏王就回答:“寡人信之矣。”庞葱说:“街市上明明白白没有老虎,然而三人这么说,就成了真有老虎。现在赵国的邯郸离我们大梁(今河南开封市)远于街市,而议论我的人何止三人?但愿大王明察。”这就是所谓古人有言:“众口铄金,三人成虎,不可不察也。”以往从故事本身论故事,其意义就是谣言重复多遍,好像就成了真实,有如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所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①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463页。。铄金毁骨,意思是毁谤太多,使人无以自存。但是,如果从空间维度、从自然生态的角度考察,由于人的密集活动,魏国的老虎在城市里已经绝迹,近郊也不易见到,但远郊山区还有。魏国据有山西南部、河南大部、河北小部,这些中原地区的老虎已经和人形成了排斥关系。
第三个有名的虎故事,是《战国策·楚策一》②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卷十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11页。中的“狐假虎威”。江乙对荆(楚)宣王说:“老虎到处寻找百兽来吃,抓到一只狐狸,狐狸说:‘虎先生,你是不敢吃我的。天帝使我作百兽中的老大,现在你要吃我,是违背天帝的旨意的。你如果以为我的话不可信,那我就在你的前面走,你跟随在我后面,看看百兽见到我,胆敢不逃命吗?’老虎觉得有道理,故尔与之同行。百兽见了都逃走。老虎不知道百兽是害怕自己而逃跑,以为它们害怕狐狸。”从时间维度、从政治社会意义来看,“狐假虎威”是以狐狸假借老虎的威风吓退百兽,比喻依仗别人的势力来吓唬人,即所谓狐假虎威,狗仗人势,虚张声势,倚势欺人。如果换为空间维度来贴近看这只楚国的老虎,在人虎关系上,人对老虎还保持着一定的审美距离,把老虎当成笨伯,嘲讽着它傻乎乎上当受骗,并无凶残的本性,其中还带有一点幽默感;老虎周围的食物链是完整的,有狐狸、有兔子之类的小动物,人与虎并没有发生对抗。这个是楚国,也就是长江流域的人虎关系。这种人虎关系的存在,实在令人感受到“谣俗分南北,江山割楚齐”。
为何要列举三个虎故事呢?书海游翔,需要有准确的指南针和航海图。只有总揽群书,综合对比,才能发现老虎类型的版图分布。泰山的老虎、魏国的老虎属于北方的中原的老虎,那里已经发生了人虎对抗;狐假虎威的老虎属于南方的楚国的老虎,这里还保留着人虎之间的神秘关系。书在读人,往往不是孤零零的一本书在读人,而是东南西北各种书,聚焦起来读人。这就使得书读人时,被读的人要设置心灵的指南针、方域的航海图,对群书综合会通、相互对比。多种书对比着、聚焦着读人,举一反三,就不怕你人不开窍。由于地理的差异,南北不同地理空间上生物群的差异,就可以从空间维度上把握住中国两千多年的南北分驰的虎故事的叙述类型,形成了北方系统的虎故事和南方系统的虎故事的鲜明对比。在北方系统的虎故事中,人与虎是对抗的,是英雄主义的写法;在南方的虎故事中,人与老虎是带有人情味,相互关系染上了一层神秘感,是非英雄主义、反英雄主义的写法。二者的类型分界虽然不可绝对化,但其大体面貌存在着南北分流的特征。两千年来的书籍都在看着我们,甚至忽南忽北地与人捉迷藏,考验着我们能否举出南北两个老虎系统的充分而坚实的例证。
古代南方多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书引导我们先看南方山野间的老虎。晋朝干宝的志怪小说集《搜神记》,多讲鬼怪神仙,如蒲松龄《聊斋志异·自序》所谓“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③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页。。干宝讲了庐陵就是欧阳修的家乡江西吉水的一个虎故事。说有个老虎跑到村子里,叼走了一个会接产老太太,原来是山里母老虎难产。老太太帮助母老虎产下三个虎仔后,老虎把她送回家。这只老虎以后每天给老太太叼去很多小动物,来酬报她。志怪书使这老虎变得精灵,竟然知道谁有产婆的本领,不仅不伤人,而且知恩图报。还有传为唐朝太子宾客刘禹锡写的《刘宾客佳话》,刘禹锡诗云“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他在四川、湖南这些地方流放有二十三年,写了一个发生在浙江诸暨、西施故乡的虎故事。说是诸暨有一个老太太在山里走路,看见远处小道上有个老虎在痛苦爬行,爬到了她面前,伸出前掌,原来前掌有个大芒刺,老太太就把它的芒刺拔了。你看南方老虎,老是跟老太太打交道,这就是南方老虎的诡异之处。因为老太太心慈手软,无力跟老虎较量,就出现了另类的人虎关系。老虎很惭愧,未能报答,站了一会儿就走了。以后那只老虎每天夜里都给老太太家里叼来小动物,老太太生活改善了,吃得肥肥胖胖的。但是她多嘴,跟亲戚说老虎怎么怎么样给她叼食物。老虎好像有灵性,当晚就给她叼来一个死人,害得老太太吃了一场官司。老太太讲清楚是老虎叼来的死人,就被无罪释放回家。这老虎当晚又叼来小动物。老太太爬到墙头上说,虎大王你可不要再叼死人来了。老虎对人是知恩报恩,心也通灵,你多嘴就给你来个恶作剧,这种关系实在是带点万物皆灵的神秘主义。①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82页。
明朝冯梦龙是苏州人,曾经编撰过《喻世明言》(又名《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白话小说。冯梦龙是很推崇智慧的,他说:“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他的《古今谈概》以幽默的智慧,对南方老虎说三道四:“荆溪吴康侯尝言山中多虎,猎户取之甚艰,然有三事可资谈笑。其一,山童早出,往村山易盐米,戏以藤斗覆首。虎卒搏之,衔斗以去。童得免。数日山中有自死虎。盖斗入虎口既深,随口开合,虎不得食而饿死也。其一,衔猪跳墙,虎牙深入,而墙高难越,豕与虎夹墙而挂,明日俱死其处。其一,山中酒家,一虎夜入其室,见酒窃饮,以醉甚不得去,次日遂为所擒。”②冯梦龙:《古今谈概》卷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75页。荆溪属于温州雁荡山的南山区,此处老虎傻头傻脑,误食误饮,出尽洋相。如此说虎,可见人与虎并无多少敌意,还觉得它们憨态可掬,令人开心。
还有安徽黄山的老虎,也是那样令人发笑。明代谢肇淛生于钱塘(今浙江杭州),祖籍福建长乐。他的一部颇有影响的博物学著作《五杂俎》,分天部、地部、人部、物部、事部等五个部分,多记掌故风物,其中写了安徽黄山上的老虎。说是有个壮士晚上在山涧小屋里,看磨米磨面的水磨。一会儿进来一只老虎,把壮士吓坏了。老虎一把将壮士抓过来,坐在自己屁股底下。老虎一看水磨转个不停,也看入迷了,忘记屁股底下坐着一个人。老虎屁股底下的壮士,过一会儿缓过神来,明白处境危险,这怎么脱身呢?他睁眼一看,看着老虎的阳物,翘翘然,就在他的嘴巴上方,他一口就咬住老虎的阳物,疼得老虎哇哇叫,一下子就落荒而逃。第二天这个壮士就到处夸口,说他把老虎赶跑了。笔记中这样评点:过去的英雄是“埒虎须”,如今的壮士是“咬虎卵”。③谢肇淛:《五杂俎》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42页。这是一种消解英雄的写法,南方的老虎变得这样愣头愣脑,屁股底下坐着一个大活人也忘了,还要端详琢磨水磨的工作原理,活该被人咬伤阴部,这种老虎和人的关系简直就匪夷所思。地理空间维度一进来,南方老虎大惊失色,自己虽然有些神秘莫测,却也免不了如此不堪。
书中的老虎,实际上已经由自然生物转化为文化景观,融入了区域文化的视野。《淮南子》说:“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释之冰。”④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41页。草木蒙茸,衬托老虎的神秘;冰雪厚积,凸显老虎刚猛。较之南方的老虎,北方的老虎就可以夸口自己威猛,它们不是吃素的,面对的也不是等闲之辈,其间散发着英雄主义的气息。比如说,黄须儿曹彰,魏文帝曹丕之弟,曹植之兄,是曹操的儿子中武艺最高强的一个,从小就善于射箭、驾车,臂力过人,徒手能与猛兽格斗。曹操说:“黄须儿竟大奇也!”王维《老将行》诗云:“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须儿。”当时,乐浪郡属于汉代辽东四郡之一,在朝鲜平壤附近。乐浪郡进贡了一只大白虎,锁在笼子里面,整天发威大吼,笼外的好汉们听了,个个都心寒胆战。黄须儿曹彰,就进入铁笼,把老虎尾巴绕在自己的胳膊上,使劲抖了几下,就把老虎治服了。后来,南越国献上一只白象给魏武帝曹操,曹彰用手捏住象鼻子,象就乖乖地趴在地上不敢动。曹彰面对的是非常凶猛的老虎,自己又是非常勇猛的人,这是人虎对抗的英雄主义写法。最著名的北方虎和英雄的故事,当然应该算是《水浒传》中的武松打虎。景阳岗的老虎是吊睛白额大虫,使附近行人和猎户都闻风丧胆,“原来那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的绝技。武松与老虎打斗,最后把老虎按在地上,“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尽平生之力,只顾打。打得五七十拳,那大虫眼里、口里、鼻子里、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那武松尽平昔神威,仗胸中武艺,半歇儿把大虫打做一堆,却似躺着一个锦布袋”。《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有诗为证:别意悠悠去路长,挺身直上景阳冈。醉来打杀山中虎,扬得声名满四方。①施耐庵:《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96页。
案头著书、街头演艺、舞台说书,地及南北,就使文化在地域间的流动,深刻地影响了文化景观的呈现形态。书在流动中读人,读出了人间百态,连同老虎也改变了身段。英雄主义的武松打虎故事,传播、旅行到南方之后,它会变得诡异多端。比如这只老虎到了鲁迅的家乡绍兴,那里“目连戏”的游行表演中有武松打虎的插曲,鲁迅的《门外文谈》对它作了记载。就是说农夫某甲就扮武松,某乙就扮老虎,扮演武松打虎,某甲很壮,某乙很弱,打斗起来,强壮的武松把老虎打得哇哇叫,老虎就说:你干嘛这样打我啊?武松说,我要不狠狠打你,你不把我咬死了吗?某乙就说:那我们换一下,我当武松,你当老虎。结果强壮的老虎就把武松咬得哇哇乱叫乱跑。老虎说:我不狠狠咬你,你不把我打死了?鲁迅说,比起希腊的伊索,俄国的梭罗古勃的寓言来,这个目连戏中“武松打虎”是毫无逊色的。②鲁迅:《且介亭杂文集》,《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其实,“武松打虎,虎打武松”这种颠倒错综,以民间的幽默消解了英雄,颠覆了《水浒传》的经典叙事。
武松打虎故事传到淮扬,别有情趣。古书可是把扬州描绘得非常风光、非常有情调,即唐朝徐凝诗中所谓:“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老虎碰上绍兴的黄酒,扬州的明月,喜欢得不亦乐乎,不知陶醉成什么样子。笔者欣赏过扬州评弹说唱《武松打虎》。这个评弹是说武松喝了十八碗酒后,上了景阳岗,醉劲上来,就在青石板上睡着了。一会儿来了一阵风,出现虎吼,武松就惊醒了,他瞪大眼睛到处找老虎,没有发现,找不到藏在树丛中的老虎。老虎躲在树丛子里说:“哈哈,武松你没有发现我,我可发现你了。”老虎变得像小孩子那样顽皮,简直跟人玩耍捉迷藏。武松与老虎开打,武松的棍子不是打在松枝上折断的,而是打到老虎的前面,老虎歪着脑袋说:“这是什么?是不是香肠啊?”“咔嚓”一口,就把棍子咬掉了半截,老虎好像在吃淮扬大餐。老虎似乎变成顽童,在紧张的气氛中添加了轻松,从而对英雄主义的叙事作了智性的超越。
与武松开打的老虎往南走,沾染了逗乐开心的习气。这只老虎往北走,走到蒙古,又沾染上漠北草原的风尚。清朝蒙古有个喀尔喀蒙古语翻译本《水浒传》,今藏乌兰巴托。蒙古人不懂得用南拳北腿打虎,骑在马上弯弓射箭,把虎射死,并非难事。蒙古好汉有三种绝技:骑马,射箭,摔跤。《水浒传》翻译,需要随风入俗,才会令人惊心动魄。武松跟景阳岗老虎搏斗,武松抓住老虎的胳膊,老虎抓住武松的肩膀,人与虎之间一招一式,来了一个蒙古式摔跤,在景阳岗上滚来滚去,把摔跤写得格外精彩。景阳岗上还有个水坑,武松最后把老虎摔到水坑里,窝着它的头,骑着它的背,挥拳猛打。景阳冈上的老虎哪里见过蒙古式摔跤,只好败下阵来。总之,老虎在北方,在人虎对抗中,都要抖擞威风,准备采取英雄主义的姿态。地理空间维度的加入,造成了老虎重新排队,出现了南北两个老虎系列。这些描写虎故事的书按捺不住要说话了:老虎分别南北来排队,种种表现如此不堪,这不能怪老虎,老虎没有话语权;老虎如果有话语权,它们会反问:这是写我们老虎吗?是写你们人类,北方人强悍而粗鲁,南方人机智而狡猾,或如鲁迅所言,“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①鲁迅:《花边文学》,《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435页。——你们把你们的地方民性折射到跟我们老虎的关系上了。
所谓“江分南北岸,月照去留人”,群书使人关注南北文化的差异,从中获取解开古代文明多样性的钥匙。清人方薰《山静居画论》卷上讨论绘画与禅宗,也强调南北分野,他认为:“画分南北两宗,亦本禅宗南顿北渐之义。顿者根于性,渐者成于行也。”②方薰:《山静居画论》,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7页。这也折射了南北刚柔的风气差异。老虎如果能读书,会说话,也会振振有词地辩解说:你们不要把北人称少女为“妞妞”,南人称少女为“娘娘”,都按在我们老虎的头上,好吗?书读人,书中的老虎就跳出来和人辩论,实在令人大吃一惊。更有甚者,那些存活在古书中的老虎,还责难人:人类也应扪心自问,你们人是如何作贱天物,糟踏自然,在古书中还写着北方老虎凶悍、南方老虎诡秘的多样性,如今却弄到几乎只能在动物园的铁栏里看老虎的地步了。岂不痛哉也乎!悲哉也乎!以书反观人的生存环境,就要从书面踏上地面,在当今世界人口猛增和城市化提速,严重影响自然资源和自然物种的环境之时,如何改变那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索取方式,切切实实地从国土整治、环境保护、资源合理利用以及改善民生等综合维度上,建立人与自然的良性平衡与和谐互利的关系,已成为人类生活普遍关注的历史命题。
三、女子小人的疑难
书会给人出难题,疑难愈大,愈能锤炼人的文化阐释能力和兴趣。许地山说过:“要做书虫必须具备五个条件:第一要身体健康,第二要家道富裕,第三要事业清闲,第四要志趣淡薄,第五要宿慧超越。”③许地山:《牛津的书虫》,《许地山散文》,上海: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19页。许多条件我们并不具备,但“宿慧超越”,就是心灵通透,务求开窍,则值得我们不断修炼,自我发掘。书读人的时候,给人出了一大堆难题,有的还是千古之谜,难得人们傻瓜一样抓腮挠发,百思莫解。书读人,留下了难解之谜;人反过来读书,破解难解之谜,其间苦涩莫大焉,乐趣也莫大焉。难题出乐趣,难题愈大,乐趣也就愈大,它考验着我们思想能力的强度。北魏菩提留支译《入楞伽经》卷四云:“求乐境界生诸天中。彼须陀洹不取是相而取自身内证回向进趣胜处。”④《入楞伽经》卷四,《集一切佛法品》第三之三。须陀洹(梵语:Srotāpanna),又译为预流、入流,是佛教修行证得的第一个果位,意思是通过修行断尽“见惑”,开始见到佛道,进入圣道之法流,通过证悟,“信根成就,即是慧根”。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⑤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266页。他强调新材料、新问题,其实以新的思想方法,缀合新旧材料碎片,进行返本还原的研究,断疑立信,也可达最高的觉悟,游翔书海,此乐何极。
比如《论语·阳货篇》说:“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①刘宝楠:《论语正义》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09页。对于这则孔子之言,如果孤立地只读一书,就莫明本源,莫得本义。就这么字面上并无多少繁难的一句话,使得千古经师、注疏家、孔学的崇拜者陷入疑惑、沮丧之中。孔子此言在当今妇女解放、女性主义思潮中,屡受诟病,虽有辩解者巧舌如簧,曲为其说,也无助于为孔子解套,遂成《论语》“子曰”的一大疑难。宋代邢昺疏解说:“此章言女子与小人皆无正性,难畜养。所以难养者,以其亲近之则多不孙顺,疏远之则好生怨恨。此言女子,举其大率耳。若其禀性贤明,若文母之类,则非所论也。”②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卷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99页。他所举的典故,源自《诗经·周颂·雕》:“既右烈考,亦右文母。”③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083页。文母,大姒也。周文王之妃,周武王之母。大姒生十男:长伯邑考、次武王发、次周公旦、次管叔鲜、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铎、次霍叔武、次成叔处、次康叔封、次聃季载。大姒教诲十子,自少及长,未尝见邪僻之事。及其长,文王继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这是汉代刘向《列女传》卷一《母仪传》的话。因而文母这类女子自然不能包括在内,而与小人同列。
宋代朱熹《论语集注》则作另外的解说:“此小人,亦谓仆隶下人也。君子之于臣妾,庄以莅之,慈以畜之,则无二者之患矣。”④朱熹:《论语集注》,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141页。他以身份低贱的仆隶、臣妾,概括小人、女子,也是以偏概全。如此“增字解经”的做法,是不足为训的,如清人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下》云:“经典之文,自有本训。得其本训,则文义适相符合,不烦言而已解;失其本训而强为之说,则阢陧而不安,乃于文句之间增字以足之,多方迁就,而后得申其说。此强经以就我,而究非经之本义也。”⑤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十二,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编:《高邮王氏四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3页。今人某氏在《百家讲坛》将《论语》通俗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她把“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中的“小人”解释为小孩。她认为:“这句话可以有几种解释,把小人理解成与君子相对的不道德的人,这是一种解释。第二种是把小人解释为襁褓中的婴儿,也就是我所说的,把小人单纯地理解成小孩,因为女人与小孩有共同的心性。我个人更喜欢这种解释,因为这种解释更有性情,更贴近我们当下的社会现象。”以“我个人更喜欢”来解释经典,背离了《论语》中大量使用的“小人”一词的本义。《论语·述而篇》云:“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⑥刘宝楠:《论语正义》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84页。《颜渊篇》云:“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⑦刘宝楠:《论语正义》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04页。诸如此类,在《论语》二十篇中,“君子”一词出现106次,“小人”一词出现24次,这些都是含有严格的道德褒贬判断的。把“小人”解释为“小孩”,不合《论语》的惯例。孔子三岁丧父,母亲含辛茹苦将他抚养成人,即便有男尊女卑思想,也不会泛泛地说“女子难养”,把“女子”与“小人”相提并论的。人们不要忘记,孔子言孝,在“能养”上还要加一个“敬”字呢。书在读人,它面对人们手忙脚乱地维护“圣人”、曲解“圣训”,大概也觉得好笑吧,笑中含有几分酸涩。
书读我,考验着人对于书之本义的真诚。要提升这种真诚的档次,一是不应局限于单本书读我,而是群书读我,力求融会贯通;二是我也不是消极的纯粹的“被读者”,而是在被读中潜观默察,以正读和反读激活思路,抵近本源。被读与反读相对而行,就使书与人发生心灵的撞击,撞得火花四溅,撞出探寻的兴致和创造的激情。两千年的诠释迷惑表明,书与人的心灵碰撞要获得文化结果,关键在于重回孔子此言发生的历史现场,弄清它的具体针对性,把《论语》当成“活的《论语》”来对待。离开具体的历史现场而将孔子之言普泛化,认为片言只语“一句顶一万句”,可以包治百病,这是造圣人的方法,却也每每使得圣人要为自己的片言只语,负无限制的责任,陷入难以解脱的尴尬。
根据汉儒的说法,《论语》编纂始于“夫子既卒”。“既卒”的时间刻度,只能是为夫子守丧期间。公元前479年,64个弟子为孔子庐墓守心孝三年(25个月大祥),在群体斋戒、祭祀中,达到“祭如在”的心理峰值,激发了对孔子的深切怀念。众弟子为了实行“三年无改于父(师)之道”的至诚至孝之心,陆续忆述夫子的文字有十几万字之多。如果全部采录,所用竹简就非常繁重,不便于作为传道的载籍。主持者在评议选择中,去芜存菁,即便采录的材料也删去背景,再作精简润色,保留下来的多是精炼化了的“子曰子曰”,简直是在沧海中探取骊珠,读其书要领略诸弟子对夫子的这份孝心和孝行。《论语》这种编纂方式,有利于孔子之言成为历代统治者安邦治国的鉴戒,成为广大民众立身修德的箴言,却也使得不少孔子之言游离了历史现场。然而七十子及其后学对夫子忆述的文字,未得入选著录者,也散落在先秦诸子和两汉群书之中。只要我们明白战国秦汉书籍在官方和民间不同地域人群中不断口传、记录、组简流传、汇辑整理的体制,不被由此形成的“历史文化地层叠压”弄花了眼,以致看到个别或少数后出的文字就怀疑伪书满眼,不去究其原委,而是对历史遗存采用尊重的态度,就可以缀合材料碎片,有若文物考古以碎片复原陶罐那样,还原出古人的生命征象和历史现场。书读人,人不能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地怀疑饱经风霜而顽强地留存下来的经典群籍总在作伪。我们是在为大国文化探寻根本,就要对此根本充满信心,激活它的生命活力。
苍茫书海呈现的孔子生命曲线,丰富复杂而牵连着理智和感情。孔子作为一个刚毅的男子,他的政治生涯曾经两次遭遇女子,都发生在他政治上摔跟头的倒霉时候。失败给人的教训最是深刻。一次是《论语·微子篇》所载的“齐人馈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①刘宝楠:《论语正义》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17页。。此事发生在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孔子54岁,他由此从鲁司寇的高位上折了下来,感到鲁国政治不足与为,踏上周游列国之途。另一次是《论语》、《孟子》、《吕氏春秋》、《史记》告诉我们的,孔子离开鲁国到卫国开始周游列国,两入卫国之时发生了“子见南子”公案。时在鲁定公十五年,即卫灵公四十年(公元前495),孔子57岁。三四年间接连发生两次女子沾污政治,造成孔子政治生涯发生重大波折的事件,深刻地影响了曾经沧海的孔子的政治观感和政治理念。
“子见南子”公案,起码涉及《论语》中五章文字,关注得不可谓少。至于《论语》外的文字,为数就更多。但是,《论语》将同时或先后发生的事件分散处理材料,散布于《雍也》、《子罕》、《卫灵公》、《阳货》诸篇,可见这桩公案在儒门引起过广泛的精神震动,但《论语》的编纂者不愿把材料堆积在一起,形成一个众所关注的严重事件。由于材料处在散落状态,两千年来只是仰头看圣贤书,未见有前人穿行于群书的字里行间,对这些材料碎片进行缀合贯穿,因此导致此公案有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使其中的孔子之言难得确解,甚至发生严重的曲解或误解。书在读人,要求我们理解编书者的良苦用心,花点心思钩沉索隐,贯通其来龙去脉。《论语》这五章是:
1.《论语·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②刘宝楠:《论语正义》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44页。(按:此章记述得最直接)
2.《论语·子罕》: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③刘宝楠:《论语正义》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49页。(按:此章由于《史记》的叙述,已经与此公案发生联系。)
3.《论语·卫灵公》:子曰:由(子路),知德者鲜矣。①刘宝楠:《论语正义》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14页。(按:此章与上述二章相联系,以子路同孔子的师生关系、与引进者的亲戚关系,而与公案脱不了干系)
4.《论语·卫灵公》: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②刘宝楠:《论语正义》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25页。(按:此章比《子罕篇》的同一记述,增加了感慨系之的感叹词)
5.《论语·阳货》: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③刘宝楠:《论语正义》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09页。(按:此章与公案的联系相当隐晦,由“女子”、“小人”的意义指向,产生了蕴涵更丰富的关联)
群书中的材料碎片考验着人们的联想力和贯通力。连缀贯通就可以发现,这些孔子之言,都应该从编年学上系于鲁定公十五年,即卫灵公四十年(公元前495),孔子周游列国第二次进入卫国之时。《孟子·万章上》说:孔子离鲁初入卫,“于卫主(客居于)颜雠由。弥子(瑕)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④焦循:《孟子正义》卷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57页。即是说,孔子去鲁,于鲁定公十三年,即卫灵公三十八年(公元前497)第一次来到卫国,婉拒了子路的连襟弥子瑕提议孔子居住在他家中,以便通过南子,以谋卿大夫之位。居卫期间,卫灵公按鲁国的薪俸把孔子养起来而不用,还有监视举措。
10个月后,孔子想到陈国,途中被拘于匡地,经过蒲乡返卫,住在蘧伯玉家,发出“美玉待沽”之叹。57岁的高龄使孔子感到,寻找机会施展政治抱负和才能,已是非常紧迫了。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此之谓也。这才采取权变的行为,姑且通过弥子瑕的线索,晋见南子。弥子瑕是卫灵公的男宠,子路看透了他这个连襟的卑下“小人”作风,颇是不悦,使得孔子只好对天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直至汉代的《盐铁论》卷二还板起道貌岸然的面孔批评孔子:“《礼》:男女不授受,不交爵。孔子适卫,因嬖臣弥子瑕以见卫夫人,子路不说。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见南子,非礼也。礼义由孔氏,且贬道以求容,恶在其释事而退也。”⑤王利器校注:《盐铁论》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51页。孔子是因小人的中介,而见此女子的,过了400年还招致汉人如此訾议。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七说:“《论语》‘子见南子’注,‘孔安国曰:行道既非妇人之事,而弟子不说,与之祝誓,义可疑焉。’此亦汉人疑经而不敢强通者也。”⑥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二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489页。奈何今人不顾《论语》本义和事件的历史现场,用了种种说辞而强为之通哉!《朱子语类》卷三十三谈论“子见南子”说:“此是圣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会它。向有人问尹彦明:‘今有南子,子亦见之乎?’曰:‘不敢见。’曰:‘圣人何为见之?’曰:‘能磨不磷,涅不缁,则见之不妨。’”⑦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38-839页。这里使用的是《论语·阳货篇》孔子的话:“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⑧刘宝楠:《论语正义》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86页。坚硬得磨不薄,洁白得染不黑,比喻人的意志坚定不移,不受环境的污染。宋儒也只好用圣人的话为圣人解嘲了。
群书言之凿凿,互相印证,记录了人的生命和命运,传达着人的喜怒哀乐。领会到这一点,书读人就不算白读,因为书把写书的人、被书写的人和读书的人,连通一气了。在历史现实中,如此颇受訾议的这场“子见南子”的好戏,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损伤了孔子的人格尊严,他甚至感到“丑之”,这是不可以简单的解嘲了事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此事的结果云:“(孔子)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①司马迁:《史记》,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413页。孔子在这里以“德”自居,以色指南子的“女色”和弥子瑕的“男色”,是简而言之的。孔子毕竟是当过鲁司寇,弟子盈门的名人,竟然被女子和小人拿他开涮,悲愤之情可想而知。由于此事是子路的连襟弥子瑕引起的,孔子又对子路说:“由(子路),知德者鲜矣。”如果在这种场合孔子因“丑之”,愤而说出《论语·阳货篇》中那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岂非入情入理?又何劳注疏家曲为之词,如邢昺把禀性贤明的“文母之类”排除在外?如朱熹把“女子”辩解限定为“臣妾”,作出不足为训的添油加醋、增字解经?
唯有回到本真的历史现场,才会发现,《卫灵公篇》“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章,与《阳货篇》的“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章之间,存在着隔章呼应,相互阐发的关系。合而言之,“未见好德如好色”的“色”,包括南子的女色和弥子瑕的男色。分而言之,所谓女子对应于南子,指的是女色;小人对应于弥子瑕之类。孔子之言乃是为其在卫国遭遇的特殊情境而发,指责为政者不能沉迷于女色和小人。他提倡戒女色而勤政,远小人而亲贤。这与孔子“为政以德”、任贤使能、戒忌女色小人的政治观,是一脉相通的。因此,要使这一系列的孔子之言落地生根,就必须返回发生于卫灵公四十年,即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孔子57岁时的那个历史现场。而不可为了论证孔子超凡入圣,就将其言行无端普泛化,使之脱离具体情境而失去发生学的根据。《论语》读人,读入人心;人心反观《论语》,有必要从史书《史记》、子书《孟子》、《吕氏春秋》中获得解读的纵横坐标。唯有如此,群书读人,才能使人返回书的本源、本义。如果迷失了书的发生学的根据,人读书就失去根本了。
最后,我们还要总结一下,书读人,人读书,那么什么是“读”呢?所谓“读”者,是打开书之心,同时也打开人之心,两面心镜互相映照,以心印心,心心相契,心心互质。以书为岸,寻找心灵停泊的码头,又是心灵出发的加油站。平心而论,书并非总是板着面孔给人出难题,它也会以心换心,温馨地告诉人读书的方法。《说文解字》云:“读,诵书也。”那就是大声朗诵书了。段玉裁作注解时,展开了新的意义层面。一是“汉儒注经,其章句为读”,古代诵读文章,要区分句和读,极短的停顿叫读,稍长的停顿叫句,“读”也就是今日的逗号。读书要有句有读,不能读破句子,而且要细嚼慢咽,不能囫囵吞枣。二是他引用西汉扬雄《方言》卷十三说:“抽,读也。抽绎其义蕴至于无穷。”②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90页。要从书中演绎出奥妙无穷的意义,这就需要深读细读,读得入木三分了。怎样才能做到深读、细读呢?朱熹《童蒙须知》这样谈论读书:“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熟读,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予尝谓读书用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法,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③朱熹:《童蒙须知》,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第374页。读书讲究“三到”,“心到”最要紧,我们应该以心灵的眼睛去读书,读出书的本义和生命。宋人许《彦周诗话》说:“古人文章,不可轻易,反复熟读,加意思索,庶几其见之。东坡《送安惇落第诗》云:‘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仆尝以此语铭座右而书诸绅也。”④许:《彦周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83页。反复熟读深思,自可做到“心到”,使书中生命一点一点地钻入心里,把自己的心反反复复地钻入书中。东坡诗云:“非人磨墨墨磨人。”墨磨人,磨出人的智慧,磨去人的青春。书钻研人,也是要钻凿、研磨人的心智,磨成细末以重塑,钻出深洞以探源。一方面是书,一方面是人,二者互为本质性的存在。人读书,书读人,一要讲究方法,二要有一股“钻劲”,在木头疙瘩上钻出火来。唐朝慧能《六祖坛经》云:“若能钻木取火,淤泥定生红莲。”①《六祖坛经》卷三,《疑问品》第三。木能钻火,泥能生莲,都是有热量的生命行为,可以借用来形容活人读活书,活书读活人。说到钻木取火,就牵连出中国火的发生的经典故事。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皇霸篇》引《礼含文嘉》云:“燧人始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复腹疾,有异于禽兽,遂天之意,故曰遂人也。”②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页。一旦发明了火,就可以熟食,有助消化,是人类生存史的一大进步。人与书对读,也须心头有一把火,把字里行间的意义煮熟,便于消化吸收,才能化为自己的血肉,这是人书对读加深一步。《论语·阳货篇》宰予提到“钻燧改火”,燧是用来磨擦生热,以取得火种的工具,古分阳燧、木燧两种。马融注曰:“《周书·月令》有更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钻火各异木,故曰改火也。”③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33页。钻木取火讲究木头的材质和施工的时令之契合,看起来讲得整整有条,其中不知包含着多少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书读人,也要讲究书的材质和被读人的精神状态之契合,这其中也包含着许多甘苦。尽管这种取火方式有种种讲究,宋朝朱熹还是将取火的方法,转换为读书的方法。《朱子语类》卷四十七记述:“问‘钻燧改火’。直卿曰:‘若不理会细碎,便无以尽精微之义。若一向细碎去,又无以致广大之理。’曰:‘须是大细兼举。’”④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四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90页。书要人接受,既要深入细节,更要把握大端。“读书种子”在与书打交道时须下足钻木取火的功夫,才能实现生命的精彩。哪怕粗茶淡饭、居室简陋,“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也能成为刘禹锡《陋室铭》的亮点。
书与人的因缘,有时简直是生死不渝,生既以书为友,死亦以书为伴。连荆州战国楚墓、长沙马王堆汉墓、临沂银雀山汉墓都有大量竹简入葬,人死了还尊崇读书,以竹书来守护灵魂。有幸的是通过随葬的简帛,后世才读懂在墓里长眠两千年的古人。这些简帛书中潜伏着智慧,又得以复活,发挥了“好学近乎知”的功能,以好学催生觉悟,觉悟到书有人之魂、人为书之灵的本质。河北定州汉墓出土《论语》残卷,尽管《学而篇》残缺最甚,但人们还是记住了“学而时习之”是孔子的第一遗训,置于全书近五百章之首,而且还启迪世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但“读书”一词,在《论语》五百章中只出现过一次。《先进篇》记述子路推举他的师弟高柴(子羔)到费邑担任行政长官。高柴身不满六尺(按照战国一尺相当23.1厘米,身高不到1.40米),相貌丑陋,孔子以其为愚。孔子对子路说:“你这样做,是害了人家的子弟。”子路说:“那地方有人民,有社稷,何必非读书才算是学习呢?”孔子说:“所以我讨厌你这种巧言狡辩的人。”⑤刘宝楠:《论语正义》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64页。孔子主张读书是从政的一种必备的内功,“学而优则仕”,担心高柴一去做官吏,不肯再学习上进,蹉跎岁月,断送自己广大的前程。《孟子·万章下》也讲到读书,孟子对弟子万章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⑥焦循:《孟子正义》卷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26页。读书要知人论世,才能尚友古人,尚友四方,才能满腹经纶,朋友遍天下。书可以拓展人的心胸,拓展人生存的世界。
对于凡夫俗子如此,即便对于衮衮公卿,《汉书·霍光传》也注重评议其学识,班固赞曰:“霍光……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临大节而不可夺,遂匡国家,安社稷……虽周公、阿衡(伊尹,名挚,小名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学亡(无)术,暗于大理,阴妻邪谋,立女为后,湛溺淫溢之欲,以增颠覆之祸,死才三年,宗族诛夷,哀哉!”①班固:《汉书》卷六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67页。遂使宰辅重臣因“不学无术”贻害国家,毁灭身家,成为政治学上的千古鉴戒。不学无术或许还有拯救的方法,若既已不学无术矣,却要以权术把自己装扮成富有学养,就成了无耻,就不可救药了。东汉王符在《潜夫论》中讨论治国安民的政治道理,他把《赞学》列为第一章,说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②王符著,汪继培笺:《潜夫论笺校证》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页。。他把读书明义,作为“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的知识论前提。可见,书读人,是人类生命灵性上的大事,也是人类生存政治学的大事,忽略不得。一个不喜欢读书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个不喜欢读书的人是浅陋的。唯有人爱读书,书爱读人,才能造就一个高素质的文明社会。书在读我,我要开卷无愧于书,掩卷有得于书。书读人,可以使人春风入怀,变得睿智而强大。人生大笑能几回,对着自己喜爱的书,是可以任其读我,如沐春风,开怀大笑的。
(本文根据2015年4月15日作者在澳门大学图书馆的讲演整理而成)
责任编辑:李宗刚
The Book Is Reading Me:“Reverse Song”about Reading
Yang Yi
(Literature Institute,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ASS],Beijing,100732)
Abstract:The present paper is on the“Reverse Song”about reading in which“The man reads the book”is inversed into“The book is reading the man.”I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 between Man and Book,Man used mostly to be the subject.However,when the positions of the Man and the Book are reversed and the latter takes an active position,it will question and challenge the reading by the Man.As it obtains the initiative,the group of books will trigger off the problems consciousness of the Man,and,first of all,they will require him to see the whole with details,to draw inferences about other cases from one instance,to proceed from one point to another,and to feed back book knowledge with a fresh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in order to find the essence;secondly they will ask the reader to modestly mobilize his subjective potential and revere the features of the ages and regional cultures reflected by it;and thirdly,they will demands Man to digest the knowledge he has learned,trace its source,and make reasonable inference instead of unreasonable inference.In a word,in the process that the group of books read the Man,he must take the Book as the priority and activate his own reasoning through the wisdom of the predecessors so as to begin reading with no repentance,and finish reading with gains.And this is just the pleasure of“the Book Is Reading Me”.
Key words:the book is reading the man;the Reverse Song;to go back to its very source
作者简介:杨义(1946— ),男,广东电白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5-08-29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6)01-00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