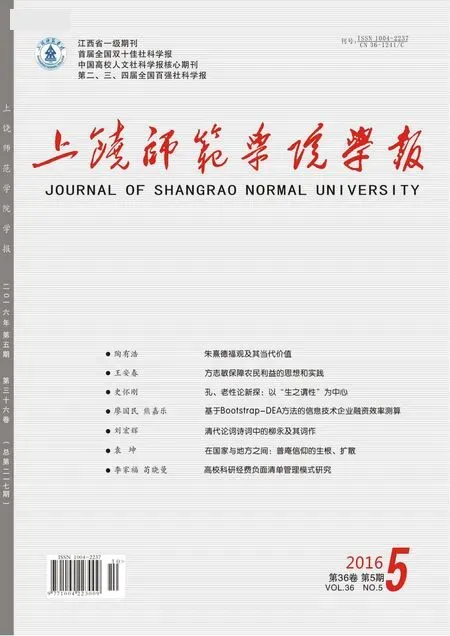在国家与地方之间:普庵信仰的生根、扩散
袁 坤
(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在国家与地方之间:普庵信仰的生根、扩散
袁 坤
(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普庵信仰根源于江西宜春,在明清时期向南方诸省扩散,形成了普庵神信仰圈。在普庵信仰民间化的过程中,地方官府、乡绅成为普庵信仰传播的推力,封建王朝对其也屡屡进行加封,普庵信仰成为国家控制地方社会的手段。而普庵信仰之所以被国家崇祀并成为国家正祀,正源于其本身所具备的文化功能:道德教化、安稳社会秩序。
普庵信仰;封建王朝;地方官绅;社会控制
关于普庵信仰,学界已有研究成果。谭伟伦《印肃普庵(1115-1169)祖师的研究之初探》一文通过对民间宗教仪式中普庵信仰不同形态的研究,发现民间社会中流传的整套普庵仪式与江西慈化寺并没有多大的联系,民间流传的普庵法事也可能只是对高僧的攀附。这套普庵仪式衍生于慈化寺,通过俗家弟子流散于民间,并不断与民间宗教文化结合产生了新的形态,也就是佛教民间化的过程[1]。叶明生的《福建泰宁的普庵教追修科仪及与瑜伽关系考》则通过对福建西北山区普庵教科仪的考察,发现它具有道教的某些形态,是一个“半佛半道、亦佛亦道、内佛外道、援佛入道”的教派,从其“追修功德”仪式来看与道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形成也源于唐宋时期流行于闽浙赣地区的瑜伽教[1]。杨永俊则考察了禅宗与赣西北客家醮祭民俗的关系,发现客家的传统道教信仰积极杂糅了普庵信仰,最后产生了以普庵为主祭的醮祭新形式,正因为这样,客家文化才得以在赣西北立足生存下来[2]。
本文则从国家与地方两者对普庵信仰的态度来看待普庵信仰在宜春以及南方诸省的扩散,并试图窥视普庵信仰在民间化的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
一、普庵其人及其信仰圈的形成
普庵禅师,临济宗第十三代高僧,江西宜春人,姓余字印肃,生于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27岁时在寿隆院落发为僧,一年后在宜春城北开元寺受戒,后游湖南,拜谒沩山牧庵禅师而大悟,继承临济法脉,史载:
普庵禅师,名印肃,袁州宜春县余氏子也。当宋徽宗政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辰时生。年六岁,梦一僧点其心曰:“汝他日当自省。”既觉,以意白母,视之当心有一点红莹,大似世之樱珠。父母因此许从寿隆院贤和尚出家。年二十七岁落发,越明年受戒。师容貌魁奇,智性巧慧。贤师器之,勉令诵经。师曰:“尝闻诸佛元旨,必贵了悟于心,数墨巡行,无益于事。”遂辞师游湖湘,谒大沩牧庵忠公。因问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忠公竖起拂子,师遂有悟,后归受业院。[3]
到了公元1153年,普庵39岁,因信众的请求住持慈化寺并开始营建慈化寺,到公元1168年完成,据记载,慈化寺鼎盛时期有殿堂十座,修法人数逾千,是禅宗又一重要道场,被世人称之为“天下大慈化”:
癸酉岁,有邻寺慈化者,众请住持。寺无常住,师衣衾纸衣,晨粥暮食禅定外,唯阅华严经论。一日,大悟,遍体汗流,喜曰:“描不成团拨不开,何须南岳又天台。六根门首无人会,惹得胡僧特地来。”自此之后,发而言句动悟幽显,有不期然者。一日,忽有僧名道存冒雪至,师目击而喜曰:“此乃吾不请友矣。”遂相与寂坐交相问答。若笑若喝,僧曰:“师再来人也,非久当大兴吾教。”乃指雪书颂而行。师乃庵隐南岭,其号曰普庵,忘怀于世。[3]
从此看,此时的普庵只是一个普通的僧人,因为礼拜高僧而有所悟,后来又住持慈化寺并努力研习《华严经》而小有名气,至于僧人道存所说“师再来人也,非久当大兴吾教”的谶语也只能说明普庵有善知识不同于寻常人而已,并不见得有十分厉害的法能。那么,普庵究竟在何时成为一个“济人无量”的通神呢?史载如下:
至斯慕道向风者众。师乃随宜为说,或书颂与之;有病患者,折草为药,与之即愈。或有疫毒,人迹不相往来者,师与之颂,咸得十全。至于祈雨祈晴、伐怪木、毁淫祠,灵应非一。由是工役大兴,富者施财,贫者施力,巧者施艺,寺因兹鼎新。延及数千里之间,辟路建桥,乐为善事,皆师之化。[3]
普庵住持慈化寺之后,往来的信众不绝于途,且都是有求而来,治疾病、驱毒疫、祈雨求晴等都在普庵的帮助之下一一解决。值得注意的是,普庵消灾的方式除了有物质上的借助,如针对疾病“折草为药”,还有仪式上的“书颂”,也就是书写一种类似于咒语的祝词来达到消除灾害的效果。从此看来,普庵在住持慈化寺之后,随着声名日高,信众越来越多,开始陆续产生了一些灵验的传说,这些灵验故事的出现使得普庵的身份,从一个现实中的高僧转变为有奇特法能的神祇。
当普庵被神化之后,民间对于普庵的信仰也逐渐扩散开来。从袁州慈化镇到万载、靖安、铜鼓等地,都存在一套普庵信仰的科仪。普庵信仰在赣西北形成了一个小信仰圈。到了明清时期,普庵信仰开始大范围向外扩散,湖南、贵州、重庆、福建、广东、台湾等地都有以普庵堂为形式存在的普庵信仰,如:
(福建宁化)南泉庵,去城三十里,成化间建。离寺里许,古木碧涧,纡折相引。[4]
(福建甘棠)西安宫,是宫起建者,在明天顺三年。中堂祀普庵佛,东祀顺正大王,西祀别神。城西门外近柯家园,其旧迹也。其地高耸,山水如画,荔菜为景,松木阴翳。[5]
(海南琼山)普庵堂,郡城东水关上,元建。明初,府城展城,堂废。弘治间,乡人获其像,复庙祀于此,故老佛。[6]
(广西藤县)普庵堂,在城隍庙东。[7]
“普庵堂”也称之为“南泉庵”,顾名思义主要祭祀普庵神。普庵信仰在中国南方的普遍流传,不仅表现在各地为祭祀普庵而修建寺庙的数量,以及普庵神传播范围之大距离之远,一些文学作品中也记载了许多关于普庵的故事,试举两例:
郑一观者,隆庆时福清农家也。雅好持斋诵经,凡桑门之徒过者,无不留宿,罄家所有,资其衣粮。先是有一少年,不知何自而来,挟数百金,占籍于邻村。容貌清雋,器度温雅。一观因许以女,招之入赘。其日,适有道士求宿。一观以婚辞;强之,乃许趺坐中堂,手结普安印,凝然不动。须臾,婿至,鼓乐沸天,灯光载道。及入门,见道士,一时俱没。道士叱之曰:“畜生来前,复汝故形,赦汝死罪。”婿即化为老猴,伏地乞命。道士敕遣之,一观大惊,拜请何居?道士手指前山,化为电光而去。明日,寻其迹,得废寺故基,丛莽中有普安佛像,俨然夜来道士也。[8]
深口普庵堂听廷镇谈佛
许有壬
皂盖朱幡老释迦,山林来治旧生涯。
清阴满座日移树,精义入神天雨花。
尘事已知皆土苴,山僧谁讶不袈裟。
欲将洛咏从溪语,又恐春风去我家。[9]
上则故事记载于明朝徐勃的《榕阴新检》中,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普庵就是降妖除害的神灵,但足以说明普庵信仰在民间所产生的影响之深、普庵灵验在民间盛行之广。许有壬,元朝文学家,因为在普庵堂听僧人谈佛而颇有感悟写下了这首诗。这些文学记载丰富了普庵信仰的文化内核和精神底蕴。
普庵信仰从江西传播到南方诸省,形成了一个以江西为中心并向福建、广西、广东等地以及东南亚扩散的大信仰圈。从目前所见的历史文献来看,普庵信仰向外扩散的路径大致为:宋时从宜春走向赣西北,在元明时向邻省福建、湖南等地传播,到明清时期开始大范围向广东、广西、台湾等地远距离扩散。
普庵信仰之所以在明清时期开始大规模向外传播,是因为明清时期江右商帮形成并壮大,大批江西商民奔走于全国各地,他们在带去江西土特产的同时,也把江西的传统信仰带到了各地,如贵州贵阳的普庵堂,就是由江西吉安商人彭如玉在元至正间创建的,以传普庵法事,成为贵阳寺庙之始[10]。其次,明清时期,“江西填湖广”的政策造成江西人在各地定居,西南地区的普庵信仰应该是这次大迁徙的产物之一,如广西玉林的普庵堂,即为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由江西移民所建[11]。
如上所述,普庵其人在住持慈化寺后,因为声名远播而越传越神,圆寂后产生了诸多灵验故事而被塑造成一个无所不应的通神。普庵信仰在宜春产生后逐渐向赣西北、福建、广东、广西、台湾等地区以及东南亚扩散,形成一个散布于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的信仰圈。
二、王朝、官府、乡绅与普庵信仰
在普庵信仰向外传播及其信仰圈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国家权力开始渗透进来,王朝和地方官府、乡绅开始关注普庵信仰的传播,成为普庵信仰逐步向外扩散的推力。
普庵禅师于乾道五年(1169)七月二十日圆寂,世寿55,僧腊二十八。普庵因为生前就有高名,死后又灵验不断,故多次受到国家的赐封。从南宋嘉熙元年(1237)到明永乐十八年(1420),普庵前后受到7次赐封:宋理宗皇帝嘉熙元年(1237)五月因祈雨辄应被诏谥为“寂感禅师”;宋淳佑十年(1250)二月再次祈雨止旱诏封为“妙济禅师”;宋宝佑三年(1255)十月,因祈止京都瘟疫,受封为“真觉禅师”;宋度宗皇帝咸淳五年(1269)四月因祈雨止旱诏封为“昭贶禅师”;元朝成宗皇帝大德四年(1300)七月因感恩庞加封为“大德禅师”;元朝仁宗皇帝皇庆元年(1312)三月二日加封为“惠庆禅师”;明成祖皇帝永乐十八年(1420)十二月十三日加封为“至善弘仁圆通智慧寂感妙应慈济真觉昭贶慧庆护国宣教大德菩萨”[12]。
由此看来,封建王朝对普庵的赐封主要分为三个时期:宋朝后期、元朝中期、明朝前期。宋朝对于民间神祇的加封手段是空前的,史载“自天宝、皇祐以来,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宫观陵庙,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并加崇饰,增入祀典。熙宁复诏应祠庙祈祷灵验,而未有爵号,并以名闻”[13]。宋朝虽然在赐封数量上占据首位,但是在深入力度上远不及明朝。明成祖曾在永乐十八年(1420)下达诏令,为普庵加封,诏曰:
朕惟佛道以慈悲为体,方便为用,超卓万有,拯拔群伦。广利济以无边,妙神通而莫测。不有丕承于法绪,曷能茂振于宗风。惟普庵禅师万行圆融,六通具足,端严自在,变化无方。誓学悟于群迷,普利益于庶类。如溥甘霖于六合,膏泽均沾;犹现满月于千江,光辉旁烛。眷此宏彰于灵化,式宜荐锡于名称。今特加封“普庵至善宏仁圆通智慧寂感妙应慈济真觉昭贶惠庆护国宣教大德菩萨”。[14]36
不仅如此,朱棣还专作《普庵实录序》,序曰:
朕尝取而观之,究其慈心慧力,莫非御灾捍患,拯危济急。化人为善,而积其善因;戒人为恶,而脱其恶趣。所以振扬宗风,上裨益于王化,下利泽于生民。功德之盛,不可思议焉。然非有以表彰之,曷以称朕归崇尊显之心哉。是用进加鸿号,并为序诸编端,锓梓以传。[14]35
明朝对普庵信仰的推崇,还表现在对普庵所建寺庙——慈化寺的修建上。慈化寺在元代至元年间曾因火而毁,但几年后,元帝就下诏敕建慈化禅寺。到了明朝洪武十八年(1385),明太祖赐建龙亭,赐书“天下第一禅林”;正统十年(1445),英宗又赐额“南泉山大护国慈化禅寺”;成化二年(1466),又赐额“广慈护国大慈化禅寺”,其间慈化寺又屡兴屡废,封建政府多次帮助慈化寺复建。
为何封建王朝都致力于对普庵信仰的推崇呢?或许正如明成祖所说“所以振扬宗风,上裨益于王化,下利泽于生民”[14]35,通过对神祇的加封从而达到国家对地方的教化和控制,是其根本原因。
在国家权力向普庵信仰渗透的同时,地方官府和士绅也逐渐参与进来:
余自隆兴二载中夏,以明天子命守四县巡检,置司于黄圃寨。去院才步武,闲相与往还,语娓娓可听。一日,与师闲坐堂,啜茶而罢。余曰:“慈化屋老,地气索寞,盍因其时而革故鼎新,可乎?”肃师泊然无意。既而,醴泉刘居士,讳汝明,字用晦,与余为乡人,钦闻其风,从余扣谒,愿奉营费。师弗许,固请,止受三百纹。命弟子圆通总其役,乃降神伏魔,移居泉中,以重建梵宇。自此,远近之人,富施以财,贫施以力,工施以艺,争先为之。经始于今年春正月戊午,落成于是夏五月乙巳日。殿堂丈室、厅库厨廊、楼阁、山门次第具举。[3]
乾道二年(1166)袁州巡检官丁骥和乡绅刘汝明延请普庵出山,并在南泉山创建慈化寺,先后建成殿、堂、厅、山门等重要建筑。在这次寺庙的修建中,丁骥身为官方代表起到了倡导推动的作用,而乡绅刘汝明则给与大部分经费支持。此外,当地其他士绅、信士也都因财因力积极参与进来,“自此,远近之人,富施以财,贫施以力,工施以艺,争先为之”[3]258。
在福建福清县,我们发现也存在着士绅促进普庵信仰的传播并致力于维护普庵庙宇的事例:
普庵堂,在县十字街左,即雷氏祖祠。举人瑶莅政兖州,因携神香火奉祀,故名。后因火,玄孙举人衡重建。[15]
这则故事不仅印证了我们上述所析普庵信仰的传播方式,也告诉我们,普庵信仰深入到了一些家族内,他们几代人都支持着普庵堂的修建、维护着普庵信仰的传播。
普庵信仰传播到各地之后,普庵堂功能也发生了转变,其从祭祀普庵为主到变为祭祀当地有名望的人物,如福建清流县普庵堂就祭祀了当地名宦三十五人、乡贤十七人、节孝五十一人[16];有的则成为学校,如广西玉林县普庵堂在清末民初则成立了中区小学;有的则成为公共慈善机构,服务一方,如浙江杭州“营普庵堂以施茗饮,浚汤泉二所,以利浴者。”[17]这反映了普庵信仰在传入一地之后,积极融入地方文化,被地方社会所接受并加以改造。
总之,正是因为国家对普庵信仰的超前关注,使得普庵信仰成为官方神祇受到王朝的祭祀而得以广泛传播,也因为地方官府、乡绅对普庵庙宇的修建和支持态度促进了普庵信仰在地方的扩散。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封建王朝正是通过对普庵信仰的加封和崇祀,达到了对地方社会的控制。
三、普庵信仰的社会功能:道德教化、安稳社会
从上述讨论中,我们看到了国家权力向地方社会的渗透,民间信仰成为国家正祀地方化的中介。我们在观察普庵信仰民间化的过程中,发现流传着四十余则与普庵有关的灵验故事,这些灵验故事有一部分反映了普庵在宜春地区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例如求雨救灾:
直至理宗嘉熙元年丁酉,大旱,祷雨无应。诏天下祀典未封谥及先有封谥者,重加封谥。由是,江西漕丞履斋吴公潜,以师道行奏闻。上见“普庵”二字,即雷鸣雨降,天颜大悦,遂下其奏。不数日,天下同奏是日得雨,遂封寂感禅师,塔曰定光。[14]413
宋理宗时期,地方请求加封普庵的奏折一直被压着,直到天下大旱而又祷雨不应,遂转应于普庵神,数日之后天下皆雨,于是皇帝赐封普庵神。众所周知,水旱灾害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破坏力、发生次数最多的自然灾害,据统计,从秦汉到民国,自然灾害(包括水、旱、蝗、疫、风等等)共发生四千七百余次,其中水旱灾害就占据两千余次[18]。水旱灾害不仅导致了社会动乱,激发社会矛盾,甚至间接造成了某些王朝的更迭。所以在这里,普庵之所以得到朝廷的封号,是因为能够降雨救旱,从而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
当然,普庵所具有的法力还远不止这些,再举一例:
寺前有泉池,灵怪非常,凡有径过,必陷泥中,求出不得。师欲建梵字,一日乃唤泉神出曰:“汝等有何神通?泉神现红光射天,两目流血。”师云:“汝奉帝命守护此地,安得往往陷害良民?罪不可忏。”时泉神有五百眷属咸出哀告,愿求忏悔,曰:“小神为一郡泉神之祖,当令一切子孙,闻普庵正法,不敢为害。合掌皈依。”师乃首肯,更不加治。[14]393
降服恶神,安抚民心,普庵神似乎不仅在凡间有威望,在神界也享有极高的威信。所以,对于泉神的为非作歹,普庵只需语言上的训斥,就能使泉神皈依向善,并献地示好:
师一日至泉边树下禅定良久。有一神出现,身长八尺余,红发绀面而启师曰:“小神奉上帝敕,守护此地五百年,直待普庵僧。汝何僧敢擅坐此?”师云:“某即普庵也。”神遂合掌礼拜曰:“敢不奉献,遂建道场。誓愿皈依,同积神功。”[14]392
道德教化也是普庵信仰的内核之一,古人十分注重以儒家仁义道德为标判的价值观教导,尤其是将其置于神灵之下以民间信仰为外衣达到无形胜有形的作用。普庵作为禅宗善知识,教导人们要弃恶扬善,不要为非作歹,心术不正之人必将受到正义的惩罚,所以对于偷盗成性不知悔改的人,普庵也给以严惩不殆:
忽一日工匠来告师曰:“被人盗去被二床。”师曰:“莫问,待赔与汝。”匠人数以告师,且怒曰:“若不祛之,则盗心愈炽,众难安矣。”师乃书颂曰:“贼人入院作窃,诵经唪咒剖决;莫令时节到来,须教七孔流血。”书罢,师云:“速去。”次日,贼家人来哀告云:“我家起心不善,偷去僧物;今来有罪,愿赐赦原。”师云:“悔已晚矣。”其人七孔流血,竟不可释。[14]398
在这里,我们发现,普庵施法的方式就是“诵经唪咒”,也就是民间所谓的“普庵咒”,据说只要吟诵或张贴“普庵咒”,就可以达到驱邪避凶、消灾解难的神奇功效,甚至还可以驱赶蚊虫、逢凶化吉、风调雨顺。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传统社会,人们改造大自然的能力也十分有限,通过向神灵诉求是普遍存在的事情,寄托于民间信仰成为人们规避社会危害的方式之一。所以,人们相信,生活中难以实现的祈愿只要通过普庵神就可以一一实现。再如,普庵神也并非一味惩恶,对于诚心悔过的人,普庵还是会给以救度,使之从善:
萍乡屠人易姓者,久慕师之德化。乃谓其妻曰:“我久欲去慈化礼拜普庵和尚,今必行矣。”其妻曰:“汝身屠秽,岂可朝谒圣僧?”屠人秉性凶勇,既发心已,不纳妻谏,乃奋身而来。师曰:“汝放下得不?”屠曰:“放下得。”师曰:“汝回头看。”方才转头,但见平日所屠生灵,皆随在后。屠乃战栗礼拜。师曰:“尔放下得不?”屠又答曰:“放下得。”再转首,其生灵悉皆遁去。遂投师出家,师不允曰:“尔是在家菩萨。”易乃弃屠业,夫妇同斋戒。师后为更名曰仲能。易后为大善知识。纠集善信朝礼后,师以法语付之。[14]406
通过这类灵验故事,普庵从一个真实的高僧被民间塑造成一个有求必应的通神,我们也从这些灵验故事中看到了普庵信仰在民间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能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保护一方人民的生命安全、除害消灾、稳定社会秩序,也是普庵信仰所具有的文化功能,所以“师入涅后,济人无量。四方水旱疾疫,随叩而应”[14]413。封建王朝因此也对普庵神屡屡加封,通过崇祀普庵信仰,既满足了民众的心理需求,对人民进行必要的道德教化、消灾化难,更巧妙地安稳了地方社会秩序,通过对民间信仰的掌控达到了对地方社会的控制。
四、结论
普庵是临济宗第十三代高僧,因为有神奇法能而受到江西宜春民众的信奉,并被塑造成一个随叩而应的民间俗神,其在宜春生根并逐步扩散到福建、广东、台湾等地,形成了普庵神信仰圈。在普庵地方化、民间化、信仰化的过程中,地方官府、乡绅致力于普庵堂的修建,成为普庵信仰传播的推力,而普庵堂在民间地化后,其功能也发生了转变,表现出不同形式的地方特色;国家则通过对普庵神的屡屡加封,达到了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掌控地方社会的效果。普庵信仰成为国家与地方互动的场域,其也正是在与国家、地方的互动之下而千年不衰。
[1] 谭伟伦.民间佛教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205-244.
[2] 杨永俊.普庵禅师与赣西北万载客家醮祭民俗[J].宜春学院学报,2005(1):62-67.
[3] 《宜春禅宗志》编纂委员会.宜春禅宗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234-258.
[4] 祝文郁.宁化县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64.
[5] 安海乡土史料编辑委员会,校注.安平志校注本[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297.
[6] 戴熺,欧阳灿,蔡光前,等.万历琼州府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110-112.
[7] 永乐大典方志辑佚[M].马蓉,陈抗,钟文,等校点.北京:中华书局,2004:2995.
[8] 徐勃.榕阴新检[M].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65.
[9] 许有壬.许有壬集[M].傅瑛,雷近芳,校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245.
[10] 侯清泉.历代名人与贵州[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39.
[11] 李克.玉林文化遗产[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21.
[12] 宋永和,叶明生.普庵信仰在福建民间之文化形态探讨[J].闽江学院学报,2010(6):14-21.
[13]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2561.
[14] 蓝吉富.禅宗全书[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36-413.
[15] 陈桂芳.清流县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109.
[16] 李如龙.福建方言[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192.
[17] 王国平.西湖文献集成[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792.
[18] 冯焱.历史上水旱灾害及其影响[J].海河水利,1995(5):5-10.
[责任编辑 邱忠善]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Areas:Rooting And Spreading of the Pu'an Worship
YUAN K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31, China)
Pu’an worship originated in Yichun, Jiangxi, and spread to South Chin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orming the Pu’an belief circle.In the popularization process of Pu’an worship, the local authorities and local gentry became the main force to spread the Pu’an worship;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lso gave them ennoblement repeatedly, and the belief became a means to control the local society. Pu’an worship became the national worship and then the formal worship, just because of its cultural function, moral education function and the function of steadying the social order.
Pu’an Worship; feudal dynasty; local official and gentry; social control
2016-09-05
袁坤(1990-),男,江西新余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文化史。E-mail:13517085737@163.com
K24
A
1004-2237(2016)05-0079-05
10.3969/j.issn.1004-2237.2016.05.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