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跨中外 通达古今
——诠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型的反思
洪汉鼎
横跨中外通达古今
——诠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型的反思
洪汉鼎
摘要:“西方与东方”、“古代与现代”的关系,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借鉴西方哲学来发展中国哲学,乃是在按照西方模式建构中国哲学,而对古代经典进行诠释,则是强迫古代经典现代化。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不论中外关系,还是古今关系,凡“学”都是学“共相”,学优于自己的东西,从观念的进展来看,都是一种融合过程。当代诠释学的宇宙恰好包含这两个主题,它既横跨中西又通达古今。从诠释学角度探讨中国哲学的“中西”与“古今”之争,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心灵的共振既能够逾越中西又能够通达古今。
关键词:中国哲学;诠释学;中西关系;古今关系
BridgingChina and the West, Connecting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Hermeneutics and Reflection on Modern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Hong Handing
East-West relationship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are very important issues in China’s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other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A popular view is that, to develop Chinese philosophy with reference of the West, means to construct our philosoph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estern model, and to interpret the classics means to compel the ancient texts to be modernized. This opinion is untenable. In fact, whether with regard to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or as to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any “learning” means to learn “the universal”, to learn anything superior to oursel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ogress of idea, this is a kind of fusion process. In a sense, these two subjects are just contained in the universe of contemporary hermeneutics, which stretches across China and the West, and binds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In sum, discussing these two topics in Chinese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s,we can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resonance of human being’s minds could both bridge China and the West, and connect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传统哲学需要实现现代转型,似乎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此似乎又提出了异议,所谓中国哲学理论的“失语”问题开始引起反思。异议者认为,近代以来由于借用西方话语来进行所谓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中国学者在国际对话中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中国哲学在语言表达和文本解读上长期处于“失语”状态。通过赛义德所谓“东方学”,这种异议被强化到了更尖锐的程度,上述“失语”被认为是中国学人的一种“自我阉割”。西方对东方思想的支配和控制、西方对东方的文化霸权,很大程度上竟是通过东方学者对自己文化的“再现”来实现的。东方学者通过西方叙述框架和概念系统再现自己的历史,对自己的传统进行所谓“现代阐释”和“现代转换”,被认为本质上乃是对自己传统文化的“阉割”。
这里涉及到中国的文论和哲学的现代转型,也就是所谓现代化或世界化的问题。按照某些人的看法,这种“现代阐释”并非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和世界化的必经之路。从20世纪初胡适“整理国故”开始的所谓现代转型过程,被认为只能导致失语或自我阉割,因为这里的现代化、世界化其实就是西方化,而“西方即现代”、“西方即世界”其实是附属于西方文化霸权的一种殖民话语。于是,要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似乎必须另走一条相反的道路,即“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简言之,必须摆脱一切西方概念和叙述系统,回归我们民族原本的语言和概念,回归原点,走过去两千年的老路。

这里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西方与东方”、“古代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当代诠释学的宇宙恰好包含这两个主题,它既横跨中西又通达古今。我们完全可以从诠释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哲学的中西与古今之争。
一、中西或中外关系
首先,从近代中国学术史角度看,中西方是否真的可以分开?早在民国时期,王国维和陈寅恪就认为,这两者是统一而不可分的。王国维说:“余非谓西洋哲学之必胜于中国,然吾国古书大率繁散而无纪,残缺而不完,虽有真理,不易寻绎,以视西洋哲学之系统灿然,步伐严整者,其形式上之孰优孰劣,固自不可掩也。”*王国维:《哲学辨惑》,《王国维文集》第3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5页。此说开中国哲学研究必须借鉴西方哲学之“形式系统”的先河。王国维说:“欲通中国哲学,又非通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王国维:《哲学辨惑》,《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5页。又说:“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遗书》第3册,上海:上海书店,1983年,第647页。陈寅恪也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的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8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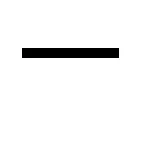
在这里,有必要对“国学”一词略加评议。近年来,“国学”一词在中国渐成显学,以致有“国学丛书”出版,有些大学组建了国学院,北京大学还搞了“乾元国学”教课班。但是,“国学”概念实有令人困惑之处。“国学”一词始于晚清,近人王淄尘在《国学讲话》中说:“庚子义和团一役以后,西洋势力益膨胀于中国,士人之研究西学者亦日益多,翻译西书者亦日益多,而哲学、伦理、政治诸说,皆异于旧有之学术,于是概称此种书籍曰‘新学’,而称固有之学术曰‘旧学’矣。另一方面,不屑以旧学之名称我固有之学术,于是有发行杂志,名之曰《国粹学报》,以与西来之学术相抗。‘国粹’之名随之而起。继则有识之士,以为中国固有之学术,未必尽为精粹也,于是将‘保存国粹’之称,改为‘整理国故’,研究此项学术者称为‘国故学’”*王淄尘:《国学讲话》,转引自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39页。,而“国故学”,以后又渐演化成“国学”。显然,“国学”一词乃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兴起之后的产物,它与当时所谓“国货”、“国烟”、“国医”、“国乐”一道,目的是为对抗外国入侵的“洋货”、“洋烟”、“洋医”、“洋乐”,以及“洋学”。就此而言,“国学”一词饱含着对西学东渐的焦虑,甚至可说是对西学的反动。另外,如果从语言学角度认真思考,则“国学”一词颇为可疑。钱穆在其《国学概论》中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就列为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弁言”,第1页。而换个角度看,“国学”一词可用于任何国家,德国学者可以用“国学”称呼他们的德国学术,美国学者也可以用之称呼自己的美国学术。就此而言,“国学”是一个普遍通用的概念,正如“国家”一样。按照国人使用该词的用意,“国学”应替换为“中国学”或“汉学”,正如德国所谓Germanistik(日尔曼学)。不过,这些学问主要是语言文化方面的,而非一般学术理论或哲学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19世纪末晚清帝国的守旧派官僚张之洞看来,学习西方也不是一种错误。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两者不可偏废。在《劝学篇》中,张之洞说:“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张之洞:《劝学篇》,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706页。所以他主张:“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可偏废。”*张之洞:《劝学篇》,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9740页。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各个民族的文化有其自身特征。文化既有时代性,也有民族性。文化的时代性指该文化在社会发展某个特定历史阶段上的时代特征,它反映的是世界各民族在相同的时代或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的落后与先进的差别。文化的民族性则指各个民族文化自身所具有的特征,特别是各自具有的不同传统。就民族性而言,文化确实没有高下优劣之分,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就文化的时代性来说,各个民族文化则存在发展程度上的先进与落后的差别。如果用文化的这两种属性来分析近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那么从文化的时代性来看,五四时期讨论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性质上属于古代特别是封建时代的文化,而西方的文化则属于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它们是一古一今;但就文化的民族性来考察,中西文化体现的是两种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彼此各有特色。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今天,这种观点特别具有“持平”的重要意义。今天的中国不再处于救亡时期,而是国家强盛、经济繁荣,拥有当代先进的科技。现在的中西方关系不再是落后与先进的关系,现在的中西方交流也不再是单向交流,而是一种双向的交流。我们学习西方更重要的目的是创立我们自己的学说理论,不再追求西方化、西学化,而是追求国际化、世界化、先进化、普遍化。就此而言,中国的哲学,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哲学”,正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一样。这里,中心词是共相,而非殊相。共相应当以普遍而先进的内涵为主,而非一种特殊的个别之物。
二、古今关系

这一观点其实也为中国哲学家所认识到。程颐在其文论辑录中说:“圣人之语,因人而变化;语虽有浅近处,即却无包含不尽处。如樊迟于圣门,最是学之浅者,及其问仁,曰‘爱人’,问知,曰‘知人’,且看此语有甚包含不尽处?他人之语,语近则遗远,语远则不知近,惟圣人之言,则远近皆尽。”*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76页。儒学正典对于儒家哲学家来说不是超人的启示,而是每个人原则上都能明见到的圣人见解。他们的解释并非先在其原初意义上阐释正典,而后再根据自己的明见对此意义进行肯定和吸收。相反,如果根据本己的经验和思考获得了某种明见和真理,那么他们会相信,出自伟大圣人和贤人的儒家正典一定会证实这种明见和真理。例如王阳明在1508年龙场悟道后,就试图通过保留在记忆中的“五经”论断来证明自己这种领悟,并发现这些论断与自己的领悟是一致的。王阳明非常强调“自得”、“得之于心”。在1520年的一封信中,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王守仁:《答罗整庵少宰书》,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6页。阳明弟子王艮则说:“‘经’所以载道,‘传’所以释经。‘经’既明,‘传’不复用矣,道既明,‘经’何足用哉?‘经’、‘传’之间,印证吾心而已矣。”*王艮:《语录上》,《王心斋全集》第2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页。学习经典,无非是自己知识的印证。此种看法,张载也有,他强调“心解”,即:“求义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万物纷错于前,不足为害,若目昏者,虽枯木朽株皆足为梗”,“且滋养其明,明则求经义将自见矣”*张载著,章锡琛点校:《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76、275页。。朱熹则谓之“心印”,将心比心,以自己的心体验圣贤的心。正是经典型或古典型的这种无时间性的当下存在,体现了历史存在的一种普遍的本质,即通过变化而形成自身,既是他者又是自身。对于世界各民族来说,这种经典型或古典型的历史,各自形成了互有区别的漫长的精神传统。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或文化传统。
伽达默尔说:“这种关于古典型概念的解释,并不要求任何独立的意义,而是想唤起一个普遍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过去和现在的这种历史性的中介,正如我们在古典型概念里所看到的,最终是否作为有效的基石成为一切历史行为的基础?当浪漫主义诠释学把人性的同质性设为其理解理论的非历史性基石,并因此把同质性理解者从一切历史条件性中解放出来时,历史意识的自我批判最后却发展成不仅在事件过程中而且也同样在理解中去承认历史性运动。理解甚至根本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主体性的行为,而要被认为是一种置自身于传承物事件中的行动,在这行动中,过去和现在不断地进行中介。”*[德]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第295页。译文略有改动。
施莱尔马赫曾经把同质性(Kongenialität)和同时性(Simultaneität)作为古典作品理解和解释的基础,认为古典作品的意义可以无须现代的参与而客观地发掘,只要理解者与古典作品的作者达到同质性,并返回到该作品原来的时代,则理解和解释就会成功。历史主义者也曾经主张,我们必须舍弃自己现时的当代境域而置身于过去传承物的时代,只有这样,我们对传承物的理解才会正确。对于这些观点,伽达默尔反问道:“说我们应当学会把自己置入陌生的视域中,这是对历史理解艺术的正确而充分的描述吗?有这种意义上的封闭的视域吗?我们想起了尼采对历史主义的谴责,它毁坏了由神话所包围的视域,而文化只有在这种视域中才能得以生存。一个人自己现在的视域总是这样一种封闭的视域吗?具有如此封闭视域的历史处境可能被我们设想吗?”*[德]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第309页。
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永远是陌生性与熟悉性的综合,过去与现在的综合,他者与自我的综合。文本的意义既不可局限于原作者的意图或文本的原意,同时,文本也并非完全开放可以任由理解者或解释者按其所需地任意诠释。也就是说,理解者或解释者并非仅从自身的视域出发去理解文本的意义而置文本自己的视域于不顾,当然,理解者或解释者也不可能为了复制或再现文本的原意而舍弃自己的前见和视域。这种既包含理解者或解释者的前见和视域又兼顾文本自身视域的理解方式,伽达默尔称之为“视域融合”:“其实,只要我们不断地检验我们的所有前见,那么,现在视域就是在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被把握的。这种检验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与过去的照面(Begegnung),以及对我们由之而来的那种传统的理解。所以,如果没有过去,现在视域就根本不能形成。正如没有一种我们误认为有的历史视域一样,也根本没有一种自为(für sich)的现在视域。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德]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第31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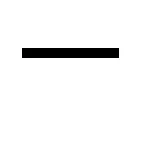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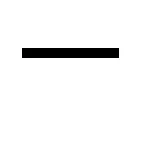

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文字传承物的历史生命力就在于“它一直依赖于新的占有(Aneignung)和解释(Auslegung)”*[德]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第401页。。所谓的解释就是:“让自己的前概念发生作用,从而使文本的意思真正为我们表述出来。”*[德]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第401页。一切解释都必须受制于它所从属的诠释学语境。
传统是活的,历史要在不断的重构中生发出新意。凡是不能与时代、社会的当下需要建立起活生生联系的传统话语,就不可能获得真实的生命力。如果有人想用“以中解中”、“汉话汉说”这种提法表达“中国哲学的重建”,那么,如果说后一个“中”和前一个“汉”理解为“传统的中”和“传统的汉”,则前一个“中”和后一个“汉”就必须理解为“今中”和“今汉”——民族生命/意志在当今时代的现实需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满足民族生命的舒展,打通传统与现实、历史与未来。这样,“中国哲学的重建”就与当前生活世界联系在了一起。
三、伽达默尔与施特劳斯关于“古今之争”的争论

施特劳斯与伽达默尔的争论是这样发生的:1960年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出版,伽达默尔将该书寄赠施特劳斯。施特劳斯在看了《真理与方法》之后,于1961年2月26日给伽达默尔写了回信,在信中施特劳斯称赞伽达默尔这本书是“海德格尔学派成员写出的最重要著作,它是一部长期工夫之作(a work de longue haleine),它再次展现了期待的智慧(the wisdom of waiting)”*[德]施特劳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迈尔编,朱雁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03页。。不过接下来,施特劳斯就对伽达默尔进行了批评,他首先指出伽达默尔的学说乃是“在很大程度上把海德格尔的提问、分析与暗示转化成一种更加学术化的形式”*[德]施特劳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第404页。,而转化的基本原则乃是所谓“方法的”(methodical)与“实质的”(substantive)的区分,而这种区分在施特劳斯看来,乃是与海德格尔所谓的“生存论的”(existential)与“生存状态的”(existentiell)区分相关的。因此,施特劳斯认为,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彻底化与普遍化只不过是与海德格尔所谓“世界—黑夜”的临近或西方的没落同时发生的东西。继而,施特劳斯就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经验理论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特别讲到它具有一种应时(occasional)的特性,并具体提出以下几个难题:⒈解释者必须反思他的诠释学处境,但诠释的文本也必须有其自身的真理,即“我必须把它当作正确的而接受它,或把它当作不正确的而拒绝它”*[德]施特劳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第406页。。我们不能用视域融合来忽视其真理,“假如一种对柏拉图学说的修正证明是优于他自己的叙述,却很难讲柏拉图的视域被扩大了”*[德]施特劳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第406页。。⒉人的有限性难道就必然导致不可能有充分的完备的正确的理解吗,所有解释者难道不都希望达到同一高点吗?⒊解释者必须理解作者自身设定的东西,因此解释者对作者的理解并不比作者对自己的理解更好。施特劳斯举出莱因哈特的“古典的瓦普几斯夜会”为例,说莱因哈特的巨大价值就在于能够理解歌德自己明确思想过但没有以读者能直接理解的方式所表述的观点,莱因哈特作为中介因而“仅仅是代文本作传达并因此而最为睿智、值得称道”*[德]施特劳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第407页。。⒋针对作者与解释者的区别有如范例与追随范例者的区别,施特劳斯提出有些文本不是范例,如《尼各马可伦理学》和《利维坦》。⒌关于解释者的创造性,如果历史学家从经济史语境去研究修昔底德,这是一种创造性吗?
除上述五个问题外,施特劳斯还提出下述疑问:效果历史概念有问题,它把对解释者并非必然成为论题的东西看成了对其必然成为论题的东西。另外,施特劳斯还认为伽达默尔的艺术概念也成问题。知识,特别是哲学的知识,不是艺术,哲学与诗有本质性的张力,阿里斯托芬的《云》早已阐明了诗歌与哲学的对立。在这方面,对“阿里斯托芬喜剧最深刻的现代解释(黑格尔的)远不及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对阿里斯托芬所作的阿里斯托芬的呈现”*[德]施特劳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第409页。。关于伽达默尔的相对主义,施特劳斯也提出意见:既然我们的认识是相对的,那么我们怎么会有绝对与无条件的认识呢,特别是当伽达默尔谈到“完满经验”的时候。
针对施特劳斯的批评,伽达默尔在1961年4月5日给施特劳斯回了一封信,对施特劳斯提出的几个问题作了回答。首先,伽达默尔回答了他是否只是无改变地发展了海德格尔的问题:“我可以诉诸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先验意义,但是通过我试图把理解设想为一种生发事件(Geschehen),我则转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德]施特劳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第412页。并且,他还说:“我的出发点并非完全的存在遗忘,并非‘存在黑夜’,恰恰相反,而是——我如此说是反对海德格尔和布伯——这样一种断言的非现实性。”*[德]施特劳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第412页。这里,我们可以对柏拉图的理解为例。海德格尔在柏拉图那里看到了存在遗忘的黑暗时代的开端,而伽达默尔则在柏拉图对话里发现了理解事情本身的本真方式。伽达默尔认为文本最好被解释为对问题的回答,以致解释的关键就是理解文本所预设的问题。对于施特劳斯说他的诠释学经验理论具有“应时”的特征,伽达默尔回答说,这一点绝不构成对恰恰宣称这一点的理论的反驳,而是这一理论的一个先声。伽达默尔对于前五个问题也一一作了回应。⒈关于视域融合,伽达默尔说,它是历史意识兴起之后的一种特殊的应用形式,因此它只是历史意识的后果,它所证明的是,它只有得到应用才会有认识。⒉对于人因有限性不能达到正确理解这一点,伽达默尔说,施特劳斯太过片面地理解他的论题。⒊关于莱因哈特的歌德解释,伽达默尔说,莱因哈特的解释除了代文本作传达外,其实还有另一方面,也许在五十年后人们会比今天更清楚地看到这另一方面是什么。“为什么他阐释这一点而非另外一点、这样阐释而非那样阐释,他忽视了什么、过分强调了什么。这样一个使您和我都怀着感激地获益的精彩的、值得称道的阐释,恰好说出了我们的意思。”*[德]施特劳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第413页。译文有改动。⒋伽达默尔认为《利维坦》可能也包含一种值得追随的真理,而非仅是错误教导。⒌伽达默尔认为,经济学史家在做这种洞察时也不得不对他自身进行反思,在这里正有其理解的创造性。

施特劳斯在收到伽达默尔这封来信后,立即在同年5月14日写了回信。首先,他要求伽达默尔反思他的新诠释学的处境,而这种反思将必然揭示一种彻底的危机,“一种史无前例的危机”*[德]施特劳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第418页。,而这正是海德格尔“世界黑夜”的临近所意指的东西。其次,施特劳斯再次强调,一种地道的解释所关心的就是如某人所想地理解某人的思想,因此“如果一种诠释学理论不比您所做的更加强调解释本质上代文本传达的特性,我依然是不能接受它”*[德]施特劳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第418页。。最后,施特劳斯明确地把他与伽达默尔之间的根本区别表述为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s(古代人与现代人之争),在这场争论中,他们各自站在不同的一边,并说他们关于诠释学的分歧其实只是这根本区别的一个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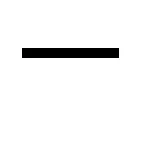
伽达默尔说,施特劳斯乃是被他“对现代灾难的洞察”所推动,诸如正确与不正确的区别这样一种基本的人的要求,自然要假定人必须能够超越他的历史条件性,但是任何历史思想本身也有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伽达默尔说:“单纯地论证说古典思想家乃是另外地、非历史地思维,这并不能说明今天我们就可能非历史地思维。”*[德]伽达默尔:《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第416页。这里的意思很清楚,比如,施特劳斯所强调的柏拉图的国家观念或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经验与近代的政治观念有很大的不同,但要真正理解柏拉图的国家观念或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经验,难道真能离开近代的政治观念吗!单纯地论证说古典思想不同于现代的思想,这不能说明我们确实可以抛弃现代视域而非历史地思维。
当然,伽达默尔也反对简单地将现代应用于过去。他说:“所谓要借助现代才能把所有过去都完全揭示出来,这难道不正是一种现代的乌托邦理想?我认为把现代的优势观点应用于一切过去身上并不是历史思维的本质,相反倒标志出一种幼稚历史主义的顽固的实证性。”*[德]伽达默尔:《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第416页。但是,历史的过去并不是什么固定不变的东西,它的意义不断地随着时代的改变而变化。伽达默尔说:“历史思维的尊严和真理价值就在于承认根本不存在什么‘现代’,只存在不断更换的未来和过去的视域。说某种表现传统思想的观点是正确的,这绝不是固定不变的(也绝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历史的’理解没有任何特权,无论对今天或明天都没有特权。它本身就被变换着的视域所包围并与它一起运动。”*[德]伽达默尔:《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第417页。
其次,伽达默尔指出,尽管施特劳斯正确地批判了后人能比作者更好地理解的观点,然而,当他说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必须像作者自己的理解那样理解作者,他就低估了一切理解的困难。他似乎认为,我们有可能理解并非我们所理解的而是他人所理解的东西,并且仅仅像这位他人所理解的那样进行理解。施特劳斯曾以古典政治哲学为例,说它的基本概念是“友谊”,而不是近代起源于笛卡儿的“我你我们”关系,如果我们用现代的概念去构造古典政治哲学,那就是错误。伽达默尔说:虽然在此例中我完全同意施特劳斯,“但我还要问,是否可能通过由历史科学训练过的眼光‘阅读’古典思想家,同样地重构出他们的意见,然后可以在可信任的意义上认为这些意见是正确的,从而使我们不费力气地获得这样的见解?——抑或我们在其中发现了真理,因为当我们试图理解它们时我们总是已经进行了思考?但这也就是说,它们所陈述的东西对我们之所以显示为真,乃是因为借助于正在流行的相应的现代理论?我们无须把它理解为更正确的东西就理解它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我还要进一步追问:如果我们发现亚里士多德所讲的要比现代理论(当然他根本不可能知道现代理论)更为正确,那我们就说亚里士多德不可能像我们理解他的方式那样理解他自己,这种说法是否有意义?”*[德]伽达默尔:《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第418页。


四、语言中介

这里涉及到中国学界目前广泛讨论的比较哲学或比较研究话题。说实话,笔者不大赞成这种意义上的“比较哲学”,即借用抽象的方法,建构不同质的哲学的最小公倍数来研究它们的同与异。打个比方,1、3、5三个质数本来各具自己的特殊性,但通过最小公倍数15来进行比较,就会出现抽象化的结果。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所有试图比较或概括中西哲学的说法,都不免有“以偏概全”的危险。真正的比较研究乃是对跨文化思想传统的哲学研究,即首先通过比较而认识一种普遍性的共识,再通过这种共识来诠释、理解和发展一种哲学。也就是说,通过对比而加深对自身和他者的理解,而且是同情的理解,并进行创造性的整合而发展自身的传统。接纳新学说、新思想、新方法,首先必须在自身的思想文化系统中建立起共识的基础。两种根本不同的东西,其中一个绝不会影响另一个。要使两种不同的哲学传统相互影响,首先必须达成共识。如果中国哲学是以西方哲学为模式构建起来的,那么它就不应当被称为中国的哲学,而应称为中国的西方哲学。所以,当我们说中国的哲学时,这种中国哲学与其说是按照西方模式构建起来的,毋宁说是现代世界哲学审视下的中国哲学。因此,这里没有什么西方模式,有的只是现代共识的先进模式。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要发展,只要它不是被封闭的,就总是要朝着最先进的方向发展。
不论中外还是古今的学习关系,实际上都是一个语言中介问题。学习外国语言和阅读古代语言,都离不开自身的现有语言。语言是思想的表现,因此,这种学习关系既是外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又是自身思想文化的发展。实际上,语言只有在它休闲即非应用状态,才可以被当作一个对象;而在使用时,即当语言在履行工作时,对于当事人来说,语言的主体性就取代了它的对象性。它们被充满了它们所意指的东西,并且没有形式内容的分离。在使用时,语言总是在说什么东西。儿童并不是先学会他们发声的普遍形式,然后再学会如何把这些普遍形式应用于个别事件;他们其实是横向平行地学会的,即从使用到使用。他们从讲话中学会讲话,从应用中学会应用。伽达默尔论证说,语言是最具自身性的(most itself),假如语言最少被对象化,假如形式和内容、话语和世界无法分割的话。母语是横向习得的这一观察,对学习外国语言也有意义。尽管洪堡曾经说过,学会一门外语肯定是在迄今为止的世界观中获得一个新的角度,但他继续说道:“只是因为我们总是或多或少地把我们自己的世界观,或者说我们自己的语言观带入外语之中,所以这种结果很少被人纯粹而完全地感到。”*[德]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第445页。在这里,作为一种限制和缺陷被谈及的东西,实际上表现了诠释学经验的实现方式。把一种新的角度引入当事人现有世界观中的,并不是对某门外语的领会,而是对这门外语的使用。确实,洪堡关于把我们的语言观带入外语中的观察是正确的。伽达默尔称它为视域融合,诠释学经验的范式。通过这种范式,我们不离开旧的视域而获得一个新视域,这种新视域允许更大的观看、学习和理解的范围。在学习外语时,尽管我们会很深地置身于陌生的精神方式中,但我们绝不会因此而忘掉我们自己的世界观,也即我们的语言观。学会一门外语和理解一门外语,只是指能够使在该语言中所说的东西被自己说出来,而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自己的世界观即语言观一起带入的话,我们就不能达到这种要求。伽达默尔说:“尽管我们会很深地置身入陌生的精神方式,但我们决不会因此而忘掉我们自己的世界观,亦即我们自己的语言观。也许我们所面临的其他世界并非仅是一个陌生的世界,而是一个与我们有关联的其他世界。它不仅具有其自在的真理,而且还有其为我们的真理。”*[德]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第445页。从诠释学观点来看,这就是一种语言融合。为了实现这种语言融合,既不可以忘记自己原有的语言观,也不可贬低其他语言而不让它们发生作用。任何语言都可以被任何其他语言使用者所学习。即使在我们研究另一种语言时,我们也从来不是一味地贬低这种语言,讲话者也绝不会因为他的母语本身能融合其他语言而必然被限制在他的这种母语的界限内。因此,我们也无须使自己摆脱我们的母语或破坏它,而只需利用它的开放和发展的内在能力。因着这种能力,语言具有无限扩张的可能性。的确,每一种语言都带着它自己的世界观,但这种多样性的事实本身却也意味着,其他语言和其他世界观为我们自己语言和世界观的扩大提供了多种具体的可能性,因为我们能学会在它们之中生活和讲话。如果我们确实学会了它们,它们就与我们自己的语言和世界实现了融合。
伽达默尔说:“如果我们形式地对待语言,我们显然就不能理解传承物。如果这种传承物不是以一种必须用文本的陈述来传达的熟悉性(Bekanntes und Vertrautes)加以表现,那么我们同样不能理解它所说的和必然所说的内容。”*[德]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第446页。另外,伽达默尔还说,学会一门语言就是扩展我们能够学习的东西,诠释学经验就在于:“学会一门外语和理解一门外语,只是指能够使在语言中所说的东西自己对我们说出来。这种理解的完成总是指所说的东西对我们有一种要求(Inanspruchnahme),而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自己的世界观,亦即自己的语言观’一起带入的话,则这种要求就不可能达到。”*[德]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第446页。
总之,人类心灵的共振能够逾越中外,并通达古今。
[责任编辑邹晓东]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伽达默尔著作集汉译与研究”(15ZDB026)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比较视域下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现代化路径研究”(14AZD09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洪汉鼎,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