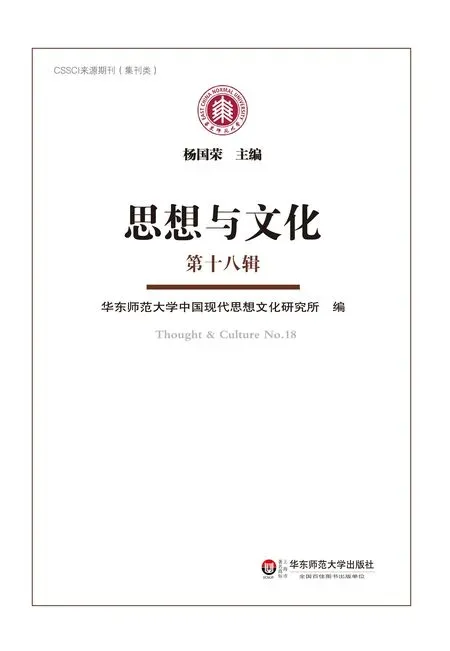思与在的辩证展开
——《庄子·天下》篇首章诠释
郭美华
根据钟泰概述,《天下》可以视为整个《庄子》的后序,表达了庄子哲学的旨趣: “此篇历叙道术由全而裂之故,以及《诗》、《书》、六艺之用,墨翟、禽骨釐以至关尹、老聃之优劣,而后述己所以著书之意,与乎察士辩者之异同,盖与《论语·尧曰》之篇、《孟子·尽心》篇之末章,上追尧舜授受之渊源、下陈孔子与孟子自己设施旨趣之所在,大略相似。故自明陆西星《南华副墨》以及王夫之《庄子解》皆以此为《庄子》之后序,其为庄子自作,无可疑者。”*钟泰: 《庄子发微》,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54页。《天下》篇可以简单分为两部分,传统上从“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至“道术将为天下裂”为“总序”部分,其余为分述评论各家之言。我们将“总序”视为《天下》篇首章,以思与在的关系为中心,以豁显其中的蕴意: 庄子之意并非是要突出一个超绝的天下或道本身,而是要在丰富多样的思与言中彰显真实的存在。
一、 思与言的整体与天下的敞亮
《天下》篇开首就以为天下有多样的治方术者: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 “无乎不在。”曰: “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尽管除内篇外,《庄子》外篇、杂篇每篇的篇名是取第一句话的起首二字为名,但就其实质内容而言,将“天下”与“治方术”相勾连而论,无疑崭露了特定的意旨。
治方术者,即思和言。天下者,也就是一般所谓在者及其整体。天下与治方术相连而言,则所谓天下,即不可离却思和言之天下。思与言,是人的主体性力量。简单而言,可以说,《天下》篇开篇豁显的即是不可离人而言天下。此亦荀子所谓“错人而思天则失物之情”*《荀子·天论》之意。
不过,天下显现于方术之治,其中有三层义理待分梳:
其一,天下及万物之在,与人的思与言何种关联?或者说,离却人的思与言,在者是否仍然有其在?
其二,思和言总是具体个体之所为,有无所有主体共同认可的道术?或超越于具体思考言说的普遍真理?
其三,不同个体由于其主观性差异,不同的思与言之间,彼此的关系如何?
从常俗观点看,有物在才能对物加以思考和言说。但是,物之显现其在,只能经由思和言而具体呈现。物之先在,是具体的思和言反省自身而有的推设。这里,似乎有一种逻辑上的悖谬之处: 只有思和言的反省才能推定其所思所言之物的在,这是思和言先于物之在;而思和言之所以能思能言,必先有其所可思所可言,所可思所可言作为物之在,先于思和言。这是两种不同的“先在”,二者具有不同的意义,二者的真实根基何在?这是《天下》篇主旨之中内蕴的一个问题。《天下》篇似乎一开始就将问题转换了: 它不问能思能言与所可思所可言的关系,而是问——普遍真理(道术)何在?
这两个问题有何差别呢?
能思能言与所可思所可言的关系,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心物关系。但问普遍真理(道术)何在,则是群己关系——即我之能思能言及所思所言与他人之能思能言及所思所言的关系(所思所言与所可思所可言的涵义不同,所思所言是思与言的观念性内容本身,所可思所可言是思与言的对象)。
每一个能思能言的“治方术者”,都以为自己的所思所言是最为切近真理的,甚至就是真理本身,他人的思与言以及其所思所言对此无所增益。在此种谬解之中,有人甚至将其自身之所思所言僭越为超绝性的实体之在。这最需要警惕。道术作为真理是能思能言之所求索的目标,既是所可思所可言,又是所思所言。道术不离对道术之治,真理不离思和言。如果预设道术作为具体思与言之先的实体,则道术等同于一物,即所谓“道之为物”,这就如同前面所说的会出现思与言同道术的悖谬。因此,《天下》篇一开篇就将心物关系转换为群己关系,它追问的是: 道术存在于何处?
道术即存在于所有思和言以及一切所思所言之中,所以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在不是说道术均匀地存在于草木瓦石、虫鱼鸟兽和人群之中,而是说,道术就存在于所有不同的思考和言说之中。
思和言就是对于道术的敞明。所以,《天下》篇在强调“无所不在”之后,紧随着对于“神明”从何而来的追问: “神何由降?明何由而出?”降是由上而下,出是由下而上: “神者天,故曰降;明者地,故曰出。”*钟泰: 《庄子发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56页。《易传》认为,天垂象,地呈文。降如垂,源自天;出犹呈,发自地。神降自天,明出自地,神明之为神明而彰显自身即敞亮自身在天地之间,并由敞亮自身而敞亮了天地万物,或者说经由敞亮天地万物而敞亮自身。
居于天地之间者是什么?《易传》所谓易道,是“兼三材而两之”,即在六爻成卦所显示的变化法则中,上两爻象征天,下两爻象征地,中间两爻象征人。这表明,“人是居间的”,“我们始终是居间的”。*海德格尔著,赵卫国译,《物的追问》,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216页。《系辞》说: “言行,君子所以动天地也。”人居天地之间而以言行动天地,如《咸》卦所说,人在天地之间动天地,使得天下行,地上行,使得天地相遇于人,三者相遇之所遵循,此即所谓道。*参见拙文《从“天人之际”看〈易传〉“三材之道”的意蕴》,《人文杂志》,2007年第4期。庄子乃至道家所谓道,具有相近的意蕴。
《天下》篇论天降神,地出明,神明即是思与言之本质。神与明意涵相同,明而申言之曰神,一方面彰明神明之居间,一方面强调明之自然而不可究诘。神即是所谓神妙不可致思,它意味着一种视野转换: 不要追问明从何来,而即此能明以明其所当明。换言之,人能以思和言来敞明在者之在,不能去追问人为什么能思能言;而是要以此能思能言去真切地思和言,由思与言以及所思所言而敞明所可思所可言。
然而,无所不在的意思,不是抽象地说道术存在于思和言之中,而是具体地存在于所有的思与言之中。既在我之思与言之中,也在你之思与言之中,又在他之思与言之中——道术存在于所有现实的思与言(及其所思所言)之中。
对于道术或天下之在的敞明,从心物关系向“无所不在”的群己关系转化,这意味着某个特定个体不能将自己一己的思与言及其所思所言僭越伪装为“道术”本身。居于天地之间的居间者,人,所有人并每一个人,潜在地都是一个个的能思能言者。道术就存在于一切能思能言者之被允许自由自主地运用其思、自由自主地运用其言的思与言的活动之中。而现实的思与言,总是彼此差异的,彼此之间是非淆乱,争论不休。思与言的自由自主运用,相应地就必然是不同观点意见的自由争论。因此,道术作为真理,就存在于不同的思与言之自由的展开自身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自由争论之中。惟其如此,道术才得以敞明自身。道术即是每一个能思能言者之能自由自主地运用其思、自由自主地运用其言以敞明自身。道术之敞明,就是使得每一个自为主宰的能思能言者如其自身而敞明自身。
神明,作为敞明道术的思与言的本质,就其可能性而言,是每一个居间的存在者的内在力量。但是,神明的光亮并非均匀而普遍地散在于所有居间存在个体的。道术以每一个体思与言的自由自主的运用为其呈现/敞明自身之本质,但是,在历史与现实中,并非每一个居间存在者都能对其能思能言进行自由自主的运用。有的个体有其神明之质,但却不运用其思和言;有的个体又将自身的思与言膨胀而至于如日月之光而耀了万物和他者之神明。所谓膨胀而耀,就是居间者整体之中的有些个体,他的神明之光,过于强烈,湮没了其他居间者的光耀,或者由于过于光耀而使得其他居间者的神明暗而无光。居间者整体中,有的个体不愿运用其思与言,有的个体膨胀地使用其思与言,有的个体不能使用其思与言,有的个体不能充分地使用思其与言。所以,居间存在者之具体的思与言以及其所思所言,便有不同的轻重厚薄程度的显现。
在此意义上,神明作为对道术的敞开,就以圣王为特出的表现。圣者耳聪目明以至于能通天下之情,王者言行卓绝而能贯天地人为一。在上古,圣者即王,而王未必即圣。但圣与王之能磅礴其思与言之神明,则根源于“一”。
我们须得追问: 一是什么?
“一”即是圣与王之所以为圣与王的那个根基,即天地人之一体。由上所述,最可注意者,是与所有居间者之一体存在。圣王的思与言之神明,源自所有居间者浑然同在之整体。
神明对在者整体的敞亮,可以说,所有神明就是此整体自身之力量。整体中之特定居间者的神明,就是整体自身之神明。整体敞亮自身,经由居间者中的特定个体而实现。
整体有绵延,个体有发展。整体之一,内蕴着多。多的一个方面的含义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方面的含义是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
相应地,居间者整体中的特定个体,磅礴其神明,无论其如何磅礴其光,一方面其光必须首先照亮其自身在整体之中的界限,守其所当止而不逾越,使得整体中的其他相与居间者能自神其明;一方面,他必须照亮自身绵延存在的变化流程,既明觉于当下之展开,又不昧于过去之远去和将来切近。此即所谓“原于一”。
二、 思与在相融之真的分层与统一
天下之为一,以居间者整体之一为根基。但居间者整体并非每一部分均匀散布的分子,所以《天下》篇紧接着说:
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
天人、神人、至人、圣人降而至于君子、百官以至于民,这是一个有着分层的整体,亦即是一个双重性的整体存在。
一方面,是“本然的存在整体”,人群分为不同的品次,有能明而能言能思者,有无明的不能言不能思者;有明耀而多言多思者,有明弱而少言少思者;有明而不言不思者;等等。如此整体,一切能言能思所言所思,都可以视为整体自身内在的显现,或者说存在整体的自我彰显。这样的整体,可以括天地为一,“天地本无心,以人之心为心”;而人者,又以圣为其通,以王为其成: “圣之为言,通也;王之为言,往也。体道之谓圣,故曰有所生;行道之谓王,故曰有所成。”*钱基博: 《读〈庄子·天下篇〉疏记》,见《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94页。
另一方面,本然存在的不同品次,自身都显现在“言说思考”之中。或者说,一切言说思考,其内涵都表征着特定人群的生存样式。比如,民者之生,农家为其言说思考;官吏之治,法家为其言说思考;君子(略读书者)的仁义礼乐,儒家为其倡言致思。
一切思辨言说,总是与特定的生存样式相融一体。思辨言说是存在自身的自觉。但存在整体的双重性,使得存在与自身的自觉往往出现分离和对峙。思辨言说易于走向对于存在的疏离而自私用智——即单纯的精神觉悟与天地浑然一体的实存活动分离。
因此,庄子叙说诸家之论,就是以二者的一体或分离为说,以思和在的一或离判别诸家。这里对于天人、圣人、神人乃至于至人的道家式强调,则突出了思与在二者统一于自然之义。
宗者,自然;天者,亦自然之意: “冥宗契本,谓之自然。”*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北京: 中华书局,1998年,第604页。所谓天人,就是领悟于生命之本质而融身其中而不言不思的存在样态。
所谓精,就是能领悟之能力。守住这一能领悟之力,对于此世之境有种领悟,而决意求索不放失,就是神人。神人之意蕴,就是异于凡俗的存在样式。
所谓真,就是有限的明觉。明觉于此世之不足执著,而能实地去离妄求索其真,将此世生存的限制推至其极限,就是至人。
所谓圣人,就是能在将天人、神人、至人融为一体的存在样式。
在庄子《逍遥游》的言说中,至人是无己的存在,神人是无功的存在,圣人是无名的存在。人突破此世的限制而达于其极致,就是无己;因为有己就是有自身有形的限制,无己则消解了有限之形的限制。此世存在者都有其形限,有形限而有其现实之功用。然而,至人没有了形限,则无以在此世有其功用。它表明至人以一种异于此世的方式存在,此世为人,则相异之存在方式就是神。所以,至人达其极致,相对于此世之人,就是神人。此世有形限的存在,有形则有名,以在时空中彼此相区分。有形有名者在此世,无形无名者在彼世。无形者无名,但是,当其与有形有名者相对而言之际,可以以对有形有名者的否定而获得一种名——“无形无名者”也是一种形名。凡夫存在于此世而人,至人存在于彼世而神。但神而在彼世,只要生命延续,还得反而归于此世。此而尘世,彼而神界。世人有形有名而局限在此之尘世,神人则破除形名而趋于彼之神界。彼此两界截然分途割裂,此世而不得其觉悟,彼世而不得其实存。两者相通,可以居于此世而得悟,可以逗留于彼世而实存,在尘世与神界两者之间自由往来,即是圣人。圣之为圣,本质之义即在于“通”。圣人通尘世与神界而不可定名于尘世,也不可无名于尘世;不可有名于神界,也不可无名于神界;欲以尘世之名名之,圣人又逗留在彼之神界;欲以对尘世形名之否定而界称之,圣人又留居在此之尘世。在逍遥游的意境里,圣人就是人存在的完满样式,是真正的自由之在。*参见拙文,《出离与返回: 作为过程的逍遥》,《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4期。在一定意义上,庄子后文所谓“内圣外王”,其蕴意就在于说明,内圣即是可以觉悟达于极致而逗留于彼之神界;外王的意思,就是可以不失其觉悟而与物混处、居于此之尘世。而内圣外王之统一,就是觉悟之精神与生命实存之尘世的统一。
对于庄子来说,天人和神人两个概念是不可或缺的。
缺乏天人和神人的圣人,往往成为儒者僭越之虚伪。
圣人“和光同尘”,光必须神而至于彼界,然后回照此界乃可。没有让觉悟达于极致而逗留于彼之神界的和光,就不能有反而归居于此界的同尘。在庄子,神人居于遥远之神圣净洁的姑射山上。姑射山虽在大地,而隔离于尘世。神人的生存样式也与尘世大相径庭。
如果没有真正的光至于神界的觉悟,而只是强调在此之尘世的混同在世,则往往会是无神而纯粹伪装之在。浅薄俗儒妄称圣人者,无一例外。所以,在孔子的儒家视野里,究极而言,圣人是一个虚位,不似孔子而后孔门弟子乃至孟子和后世儒者所谓,真圣在儒。
有神人和神界,以及神人、神界与俗人和尘世的分立,这是庄子作为道家的一个根本之点。由此,在彼之神界与此之尘世的自由来往与通而为一的生存样式中,超越于思辨言说的真正觉悟就融摄在如其自然的生命流程之中。因此,所谓天人,就是不立言不致思而浑然天地一体的觉悟之在者。圣人则是立言致思的觉悟者。在一定意义上,天人就是不立言不致思的圣人。
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分析研究会于1984年筹建,1987年12月经国家科委批准并在民政部注册正式成立,具有独立社团法人资格。
思辨言说是对于在世的觉悟,但本真性的在世觉悟则超越于思辨言说。这种超越,在在凸显的是觉悟与生命实存的一体相融。这种相融,是内蕴的丰盈的“自然”之所意味的东西: 自身之真与他者之真乃至天地自身之真的相融;圣人之返归于整体而非僭越于整体之上。就此而言,圣人内涵着天人、神人、至人的意蕴,使得道家的圣人概念迥异于孔子之后儒家虚构的圣人概念。
三、 天下与体用: 思与在互为体用的过程性整体
《天下篇》上引“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以及首章末尾文字,实质上可以视为其后分述的一个综述:
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对此,王夫之以“体用显微”作了一个深一步的诠释:
盖君子所希者圣,圣之熟者神,神固合于天均。则即显即微,即体即用,下至名、法、操、稽、农、桑、畜、牧之教,无不有天存焉。特以得迹而忘真,则为小儒之陋;骛名而市利,则为风波之民,而诸治方术者,竞起而排之。故曰鲁国之大,儒者一人而已,亦非诬也。乃循其显者,或略其微;察于微者,又遗其显;捐体而狥用,则于用皆忘;立体以废用,则其体不全;析体用而二之,则不知用者即用其体;概体用而一之,则不知体固有待而用始行。故庄子自以为言微也,言体也,寓体于用而无体以为体,象微于显而通显之皆微。盖亦内圣外王之一端,而不昧其所从来。*王夫之: 《庄子解》,《船山全书》第十三册,长沙: 岳麓书社,1993年,第465—466页。
中国哲学中的体用概念,大致类似于西方哲学中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佛家中性与相的关系。但西方哲学中本质与现象有二重化倾向,佛家则重在破除相、消解相的实在性,而中国哲学强调的是体用不二,体用一如。船山以体用关系来理解《天下》篇思与在的关系,有着极深的义理内蕴。
就具体内涵而言,体用关系可以有两点意义: 一是实体与功用的关系,即有某种实体就有某种属于该实体的功用。不存在没有任何功用的实体,也不存在没有实体担当者的功用。特定的实体,总有特定之功用;特定之功用,总是特定实体的实现或表现。单就这一层面而言体用,常易于陷入思辨的构造之中。但如果将世界整体视为某种“实体”,世界整体之功用就是世界自身的显现,那么,实体与功用的含义可以在下一层次,即整体与显现的意义上来理解。二是整体与显现的关系,即整体的存在总以某种方式显现出来,而显现总是多样性的部分之基于相互关联而实现出来的。就整体与显现而言体用,存在两种显现方式: 即自在显现和自为显现。自为显现是渗入了主体性的言和思,整体以主体自己肯定自己、自己觉悟自己的方式展开自身,这就是整体自身展开的自为,或自为显现。所谓自在显现,则是主体言和思尚未自觉的潜隐之状,它为自为显现所推设,并且作为自为显现所以可能的基础。有所自觉即是显明在光亮之中,尚未自觉是隐微潜存于寂寥之中。自觉之显是自为,寂寥之潜是自在。整体自身是自在与自为的统一,二者统一于有理性存在者(万物之灵)的具体的知行活动之中。在理性存在者的具体知行活动的展开过程中,自为与自在两种显现方式统一起来才是整体。整体与显现的关系,可以用大海水(整体)与众沤(显现)之喻来理解。这个比喻,为熊十力所重视。大海水由无数的沤组成;大海水的澎湃通过众沤之涌荡而呈现;众沤之涌荡只是大海水澎湃的显现,每一沤都不能脱离大海水而存在;没有脱离众沤之大海水,也没有脱离大海水之任何一沤。*熊十力在不同的地方反复提到这个“大海水与众沤”的譬喻,来说明整体与部分或体与用的关系。比较详细的一个论述,可以参见熊氏著《十力语要》,北京: 中华书局,1996年,第40—42页。涌荡在眼前的水浪、水泡,近在咫尺,为我们生动的情思与觉悟所把捉,是显;涌荡而来的水浪、水泡,从天际之海水源源而来,天际之海水,不为我们生动的情思与觉悟所把捉,是微。大海水的显与微,在我们的想象里融为一个整体: 我们由显明于生动情思与觉悟的涌荡,想象且领悟了一个作为背景的无边无涯的大海水整体。
大海水与众沤之喻,是地面上的比喻。我们也可以用秋日夜晚的天空与星月之喻来理解整体与显现的关系。秋日之夜,仰望天空,闪亮的星星月亮,点缀在浩瀚天空。我们所见者,是这亮堂堂的月和星,但恰好是这星月的亮堂,无边天空作为整体性的背景,才得以彰显。点点繁星布满天空,是为群星灿烂,那样的夜晚,我们可以自悟于自身的小小光亮;若是寥寥星辰,几颗星星若隐若现,天空显得静谧而幽隐。寥寥之星辰,闪亮着自身,一方面是其自身之显现,但更为本质的是,它们以显现自身的方式显现着天空之整体。换句话说,天空作为整体恰好就是通过寥寥之星辰的自我(星辰)显现而显现自身(天空)的。
在理性存在者的历史与现实之在的汪洋大海或无边天空中,弄潮儿或寥寥星辰在一袭光亮中显现自身,而他们的显现自身,牵引着无边的关联者呈现。人世之寥寥星辰以语言和思闪亮自身;语言和思又广泛流布于人世的每一角落,渗透在人世之整体中;或可以说,语言和思自身就是人世(作为理性存在者的整体)显现自身的功用;语言和思显现自身在所有理性存在者的自明自觉的活动中;耀眼之星辰,与乎黯淡之星辰,彼此牵涉,更透显了广漠无边的日用而不知的大众——作为幽隐而潜在的理性存在者。恰如鲁地“儒者一人而已”,一人即已彰显鲁地之有儒;人世之寥寥星辰,也昭示了人世之有言和思。没有人世整体的言和思,寥寥之星辰无以为其亮;没有寥寥星辰之闪亮自身,人世之整体无以显现其广袤。
即此而言,船山以体用不二诠释庄子《天下》篇,就突出了整体与部分(乃至个体)之间的相互辉映。这种相互辉映,要求我们恰如其分地理解体用不二的涵义。也就是说,要破除静态理解,要避免从单纯的概念抽象性角度就体用的概念内涵来玩文字游戏,而是要在动态的、实质的存在过程中去理解,将体用不二理解为诸多环节的统一。
首先,破相显性是第一个环节。即,人在与事物的交互作用中对事物进行反思,通过对现象的否定寻找真实,其实质是现象界用自我否定的方式来呈现自身。比如,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闪电突然划破苍穹,那闪电就成为一种对于黑夜之整体的撕裂,引向对于这无边黑夜(现象)的否定,而于闪亮中趋向于求取发亮者。
其次,摄用归体是第二个环节。即,要求破除现象的束缚,而实现对事物现象背后实体的把握。黑夜为闪电划破,闪电之光亮否定了黑暗之现象,但闪电之所从来的发光者,并未直接在闪电之光亮中呈现自身。黑夜作为幽隐整体,其亮光之思,因为所照亮的夜间景物飘忽不定,思自身(那道闪电)便预设了一个确定不易的实体作为光亮的发出者。这一预设的光亮发出者或光亮的实体,它超绝于为其照亮的景物、区别于被其所划破的漆黑夜晚,它自为持守,它即是不变的、所以能亮的自身。由此,夜晚以及夜晚的那些飘忽的景物,便一起归属于这精神性的实体。精神性的实体是不变的体,而它所照亮的景物与划破的夜晚,则是流变不定的用。用以其流变之不定而假,而虚;体以其不变之持守而真,而实。
再次,称体起用是第三个环节。即,自为持守的精神实体,在现象世界中实现出来。漆黑夜晚的闪电,被预设为不变的精神实体的光亮;它照亮夜晚和夜晚中的景物,夜晚和夜晚的景物都飘忽流变;飘忽流变为实体的闪电所照亮,其能照者为体,其所照者为用;体不变而自为持守,用流变而无可确定。但是,流变之用作为所照,构成着能照之体的多样性内容——没有对于流变之照,体之所以为体则不得其显明。光亮总是有所照耀的照亮,不照一物的光亮,比漆黑更为黑暗。因此,自为持守了的光照之体,在破除景物与夜晚之飘忽后,返回来,如其本质而照亮夜晚和景物,并以对黑夜和景物的照亮而真正地实现自身。而就人之寓存于此世而言,称体起用也就是作用见性。所谓作用见性,也就是人经由自身自觉的思与言的活动而显现世界整体的本质。这一环节,其实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它是前后诸环节的本质性中介。
再其次,即用显体是第四个环节。如上,光亮之所以为光亮,正是因为其有所照亮,其所照者即是飘忽不定的无边之物。让能亮者亮起来,让一切幽隐潜在于寂寥之中的飘忽者到场,就是光亮之为光亮。“让……亮”,并有不定的“×”到来。这是经由“让×亮”而显现自身之能亮。“让×亮”是用,而由此用更深刻地彰显了能亮之体。能思能言者之所思所言,就是“让×亮”的本质性所在。能思能言与所思所言,就是用,离却这用,无以显现“×”。
最后,摄体归用是第五个环节。如果说,发光的实体当且仅当其耀眼之光闪现才成其为发光者;而亮之所以为亮,当且仅当其有所照耀,才成其为亮。那么,无所照耀的实体自身,纯粹无所照耀的光亮自身,便是不可理解之物。能发光之实体,实体之所闪现的光亮,便依存于被照耀的万般景物——没有在光亮中显现的缤纷色彩,光亮就如同黑暗。用作为万象,是斑驳的、摇曳的、多彩的、流变的。但恰好是万象之斑驳摇曳多彩流变,才真正彰显了光亮——光亮正是让事物如其自身显现自身而成其为光亮。作为被显现的“×”,其显现方式就不仅有唯一的“答案”,而是有无边无际、无量数的解答——不同的作为能思能言者的主体,都由自身给出异彩纷然的回答。于此,不再有在事物的多样性、差异性展现之外的精神实体。世界作为整体的实情就是: 无边的、绚烂的、流变的绽放。
对于有理性存在者的这个世界而言,这五个环节彼此牵连而成一个绵延不绝的整体过程。这个过程,具有内在的生存秩序,缺一不可。不能用任何一个环节去否定其他环节。而五个环节连缀而成的世界显现过程,也就是理性存在者运用思和语言彰显自身的过程。由这一过程内具的辩证秩序而言,体用不二最终要求回到具体而实在的感性生命中去。
就有理性的存在者寓存于世而言,理性之思与世界之在,互为体用。一方面,可以说,世界之在是整体,理性之思是显现;不能脱离理性之思而言世界之在,也不能脱离世界之在而言理性之思。一方面,也可以说,理性之思是体,世界之在是用,理性之思照亮世界中之物;能照为体,所照为用;不能脱离理性之思的照耀而言世界及其中的万物之在,也不能脱离所照的世界及其中的万物而言无所照耀的光亮自身。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整个《天下》篇,就是在体用不二意义下,强调思与在的统一。由此,我们对于《庄子》齐物与逍遥的意蕴,也可以得到一个前后照应的理解,即二者都基于整体性与差异性的相融。齐物并非要在世界整体之外树立一个超绝的存在者,逍遥并非是要在万物之外突出特定的唯一者,天下也不是要给出一个天外存在者。抹灭了纷然致思发言者的所谓“道”的自存,并不是天下之为天下的真意。《天下》篇的真意,就是天下就是天下之一切,就是每一个与所有一切的统一。
——读《居间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