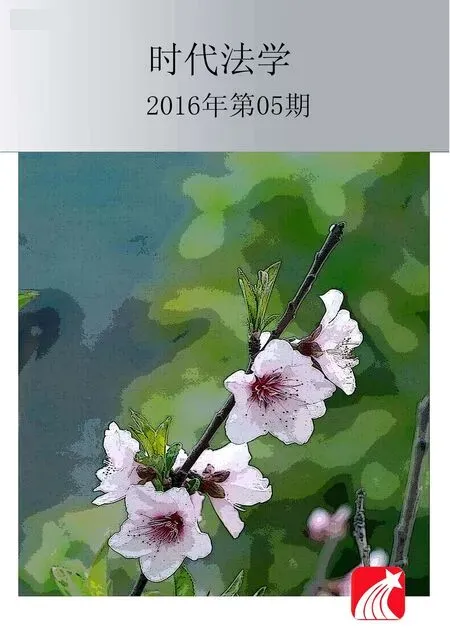论南海仲裁案的非法越权管辖——兼议中国政府“不接受不参与”的正当立场与策略(一)*
高 菲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办公室,上海 200122)
论南海仲裁案的非法越权管辖
——兼议中国政府“不接受不参与”的正当立场与策略(一)*
高 菲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办公室,上海 200122)
就菲律宾对中国提起的南海仲裁案,虽然中国政府明示此涉国家主权仲裁庭无权管辖,仲裁庭还是作出其享有管辖权并受理本案的裁决。鉴于该裁决有片面解释公约、漠视中国立场、偏向菲方、非法越权管辖之嫌,拟逐一剖析裁决各项决定,揭示其非法越权管辖事实及危害。从国家政治外交层面而言,我国不接受不参与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但就策略技术而言,官民若均不参与则有失偏颇,失去全面了解情况、当面驳斥菲不当请求等等方面的最佳机会,易让仲裁庭滥兴“法律沙文主义”越权管辖作出不利中国的管辖权及实体裁决。若既坚持官方不接受不参与原则立场,又可以任何民间方式参与所有程序,两相结合呼应,知彼知己,及时应对,依法对法,见招拆招,绝不相让,则百战不殆,似为上善之策。
不接受不参与;民间参与;非法越权管辖;政治外交方式;法律方式
一、关于南海仲裁案及其仲裁庭作出的《管辖权及受理裁决》
2013年1月22日,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约》”)第287条和附件七的规定,菲律宾政府就“有关中国对菲律宾在西菲律宾海的海事管辖权所产生之争议”*参见菲律宾外交部函件No.13-0211封面“...with respect to the dispute with China over the maritime jurisdiction of the Philippines in the West Philippine Sea”, 2013年1月22日,马尼拉。,及“对其西菲律宾海海事权益清楚设立菲律宾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参见菲律宾外交部函件No.13-0211封面“...to clearly establish the sovereign rights and jurisdiction of the Philippines over its maritime entitlement in the West Philippine Sea”.事项,向中国政府提交了旨在就所涉事项开始仲裁程序的书面《通知和权利主张》(“《仲裁通知》”)。
2013年2月19日,中国政府将《仲裁通知》退回菲方,明确表明不接受不参与该仲裁案的立场;2014年12月7日,中国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立场文件》”);2015年2月6日和2015年7月1日,中国驻荷兰王国大使分别两次向仲裁庭寄两封信件,一再强调中国政府对该仲裁案不接受不参与的立场,并明确声明:中国政府作出的声明、所附的文件、中国政府驻荷兰大使的两封信件,均不能在任何形式上被解释为中国政府参与本案仲裁程序*见仲裁庭2015年7月7日第一天管辖权开庭庭审笔录第1页第6段,2016年2月11日下载于国际常设仲裁院网站,见www.pca-cpa.org.。
2015年10月29日,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仲裁庭”)作出《管辖权及受理裁决》(“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一致作出决定如下*仲裁庭有关本案管辖权的决定内容,见《管辖权及受理裁决》第149页,有关中文均为笔者自行翻译,不是官方翻译文件,至今,笔者亦未见有官方中文翻译件。仲裁庭作出的《管辖权及受理裁决》(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的英文原文可参阅国际常设仲裁院网站www.pca-cpa.org.:
1.认定本仲裁庭为依据《公约》附件七规定正当组成。
2.认定中国不出席仲裁程序不能剥夺本仲裁庭的管辖权。
3.认定菲律宾提起本案不构成滥用程序。
4.认定不存在不可阙如的第三人因其缺席而剥夺本仲裁庭的管辖权。
5.认定2002年中国和东南亚《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本裁决第231和第232 段所指当事人的共同声明、《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依据《公约》第281条或第282条规定,不能阻止依据《公约》第十五部分第2款提起的强制争议解决程序。
6.认定当事人已经依据《公约》第283条规定的要求交换了观点。
7.认定依据本裁决第400、401、403、404、407、408和410段标注的条件,本仲裁庭享有审理菲律宾提交的第3、4、6、7、10、11、和第13项请求的管辖权。
8.认定并确认本仲裁庭是否享有审查菲律宾提交的第1、2、5、8、9、12和第14项请求将涉及到审查非专属先决审查的问题,因此本仲裁庭保留其在实体审理阶段享有并考虑对第1、2、5、8、9、12和第14项请求进行裁决的管辖权力。
9.指令菲律宾澄清第15项请求的内容、缩小其范围,保留在实体审理阶段享有审查第15项请求的管辖权力。
10. 保留进一步审查和指令本裁决未决定的所有问题。
综观上述仲裁庭作出的《管辖权及受理裁决》(“《管辖权裁决》”),可以直观地得出一个结论:仲裁庭完全支持了菲律宾提出的观点,全部驳回了中国政府立场文件及其它场合发表或表明的主张。对此,笔者认为,仲裁庭作出的上述管辖权裁决,其结论是完全错误的,其论证是不公正的、不完全的、偏袒偏向的、断章取义的、违反公约规定本意的,因此完全没有约束力;即使作出,也是形同虚设,没有任何国际法上的法律意义,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人民,对此均完全不予接受。
兹就《管辖权裁决》作出的各项决定逐一反驳如下。
二、南海案仲裁庭违反《公约》附件七及《程序规则》规定组成不当裁决应予撤销
(一)《公约》及《程序规则》关于指定仲裁员的期间及起止时间规定
《管辖权裁决》作出的第一项决定是认定该仲裁庭为依据《公约》附件七的规定正当组成。但南海案仲裁庭是否依据《公约》附件七规定正当组成,不仅取决于该案仲裁庭的每一位仲裁员是否依据《公约》附件七规定被正当选定或指任,而且取决于所涉仲裁员的选定或指任的期间是否符合《公约》附件七规定的期间。
鉴于《公约》附件七第3条有关仲裁庭组成的规定中,虽然明确规定了所涉案件当事国或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等分别选定或指定仲裁员的期间,但却没有规定所涉期间的起算标准及方法,而所涉期间的起算标准及方法正是仲裁庭组成是否正当的基本要素之一。
鉴于南海案仲裁庭于2013年8月27日作出《程序规则》以补充*南海案《程序规则》在“仲裁庭”项下明确规定:“本程序规则补充《公约》附件七的规定(These Rules of Procedure supplement those contained in Annex VII to the Convention)。”调整南海案的仲裁程序,其第2条明确规定了本案仲裁文件的通知送达及期间的计算标准,从而弥补了《公约》附件七第3条没有规定选定或指任仲裁员期间起算标准的不足。
因此,南海案仲裁庭的组成正当与否,尤其是由第三人即国际海洋法庭庭长代为中国政府指定的第二名仲裁员及其他三名仲裁员的指定正当与否,就不仅仅取决于是否符合《公约》附件七规定的指定仲裁员的期间,而且取决于是否符合包括该案仲裁庭经征询当事人且主要是菲律宾一方当事人的意见之后制定的本案仲裁《程序规则》规定的期间起止时间的计算标准及方法*如果有人问到,仲裁庭组成后才作出本案仲裁《程序规则》,如何本案仲裁《程序规则》可以约束本南海案仲裁庭自身的组成?笔者的回答是:一本案《程序规则》是《公约》附件七有关仲裁程序的补充,与《公约》附件七一起约束本案仲裁程序;二本案《程序规则》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其第3条明确规定,本案仲裁程序被视为于2013年1月22日开始,因此包括此后本案进行的一切程序及仲裁员指定至仲裁庭组成的全部过程在内;三《程序规则》确认了以前所进行的所有仲裁程序均包括在内;四亦与仲裁庭享有决定其管辖权的权力是一种拟制的权力之仲裁的基本原则及原理相同或关联,即假设仲裁庭已享有管辖权,否则仲裁庭若无管辖权如何可以通过审理以便最终决定其是否享有管辖权?如何可以自己拔着自己的头发生长?由于仲裁庭的管辖权不是法定的,而是当事人行使意思自治原则约定的,因此,既约定就有可能约定不真、存在瑕疵及是否成立生效等之辩,故为了仲裁制度的完善以及顺利进行,必须适用这种拟制的管辖权原则。事实上,除非当事人对管辖权没有异议,否则,仲裁庭的管辖权就首先是拟制的、暂时的、有可能被撤销或取消的,直到裁决作出后未被撤销或仲裁裁决已履行或被执行完毕为止。。
据此,关于送达本案仲裁文件的收到日期,依据《程序规则》第2.3条规定,通知应被视为依据第2段(即第2.2条,笔者注)规定发出的当日收到*3. A notice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received on the day it is delivered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2. And article 2.2 provides that “If any address has been designated by a Party specifically for this purpose or authorized by the Arbitral Tribunal, any notice shall be delivered to that Party at that address, and if so delivered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received. Delivery by electronic means such as facsimile or e-mail may only be made to an address so designated or authorized. ”。第2.4条规定,为依据本规则规定计算时效期间,期间的计算自收到通知之日起的次日起算。如果所涉期间的最后一天是所涉当事国的法定节假日或非工作日,该期间延长至该日次日的第一个工作日*4. For the purpose of calculating a period of time under these Rules, such period shall begin to run on the day following the day when a notice is received. If the last day of such period is an official holiday or a non-business day in the State of the Party concerned, the period is extended until the first business day that follows.。第2.5条规定,除非另有规定,所有时效终止于海牙有关日期当日的午夜12点*5.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all time limits expire at midnight in The Hague on the relevant date.。
(二)第二名仲裁员在《公约》及《程序规则》规定期间未届满即代为指定不当且违约
本案中,菲方于2013年1月22日向中国政府提交《仲裁通知》,依据《公约》附件七第3.(c)条规定,“争端他方应在收到本附件第一条所指通知30天内指派一名仲裁员,最好从名单中选派,并可为其公民。如在该期限内未作出指派,提起程序的一方,可在该期限届满两星期内,请求按照(e)项作出指派。”
鉴于依据《公约》附件七第3.(c)规定,中国指定仲裁员的期间为收到菲方仲裁通知的30天内;依据《程序规则》第2.3条规定,中国收到菲律宾仲裁通知的日期为菲律宾发出仲裁通知的当日,即2013年1月22日;依据《程序规则》第2.4条规定,中国指定仲裁员的期间起始日期为自收到菲律宾方仲裁通知之日起次日起算,即自2013年1月23日起算;且如果所涉期间的最后一天是“所涉当事国”中国的法定假休日或非工作日,中国指定仲裁员的期间应延长至该法定节假日或非工作日次日的第一个工作日;依据《程序规则》第2.5条规定,所有时效终止于荷兰有关日期当日的午夜24点。据此经核,2013年2月23日为周六,中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实行一周五个工作日制度,周六正是中国的法定休息日,不是工作日,应该排除周六与周日延长至次日的周一计算起始。据此,中国指定仲裁员期间的最终终止日期应为2013年2月24日荷兰海牙午夜时间12点。
至于起始日期,依据《公约》附件七第3.(e)条规定,菲律宾请求海洋法法庭庭长为中国代为指定第二名仲裁员期间的起始时间应为2013年2月25日零晨12.01分开始。
据此,依据《公约》附件七第3.(e)条规定,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在与双方当事人协商后”,为中国代为指定仲裁员的期间应为,自2013年2月25日零晨12.01分时开始至2013年3月25日午夜12点整。
但事实是,菲律宾于2013年2月22日要求国际海洋法庭庭长依据《公约》附件七第3.(c)条和3.(e)条规定为中国代为指定本案第二名仲裁员。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则于2013年3月23日为本案,事实上和理论上也是为中国代为指定了第二名仲裁员:荷兰国籍人斯坦尼斯劳.帕拉克法官(Judge Stanislaw Pawlak)。无论是菲律宾还是国际海洋法庭庭长均人为地提前两天终止了本案第二名仲裁员的指定期间,也就是人为地提前两天终止了(无论中国是否参与本仲裁案)中国政府依公约享有的指定仲裁员的权利期间。
也就是说,菲律宾没有在《公约》第3.(c)条规定的指定第二名仲裁员的30天期间届满后的两周内再请求国际海洋法庭庭长代为指定,而是不待(本质上作为他方当事国的)中国享有的指定第二名仲裁员的期间届满,就迫不及待地提前两天提请国际海洋法庭庭长代为指定第二名仲裁员,侵犯了他方当事国中国指定第二名仲裁员的权力/利,导致本案无论是管辖权裁决,还是以后仲裁庭作出的实体裁决,只要中国愿意提起撤销程序,都避免不了应被撤销的命运!
(三)指定第二名仲裁员期间未满即代为指定同样不符并违反中国法律规定
概括地说,法律关于期间以及期间起止计算的规定,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各国国内法,其规定本质上应均一样。
就本案而言,本案《程序规则》第2.4条规定:为计算本规则期间之目的,期间应自通知收到之日次日起算。如果期间的最后一天在所涉当事国是法定休假日,或非工作日,期间应延长至法定休假日或非工作日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For the purpose of calculating a period of time under these Rules, such period shall begin to run on the day following the day when a notice is received. If the last day of such period is an official holiday or a non-business day in the State of the Party concerned, the period is extended until the first business day that follows.。
据此,作为补充《公约》附件七程序规则的本案《程序规则》,有关期间起止时间计算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民法通则”)及其解释的规定实质完全一致。如依据《民法通则》第154条,按照日、月、年计算期间的,开始的当天不算入,从下一天开始计算。期间的最后一天是星期日或者其他法定休假日的,以休假日的次日为期间的最后一天。期间的最后一天的截止时间为二十四点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民通意见》”)第198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的期间不是以月、年第一天起算的,一个月为三十日,一年为三百六十五日。期间的最后一天是星期日或者其他法定休假日,而星期日或者其他法定休假日有变通的,以实际休假日的次日为期间的最后一天。
据此可见,南海案仲裁庭第二名仲裁员的代为指定,无论是依据国际法即《公约》的规定,还是依据仲裁庭制定的补充《公约》附件七本案仲裁《程序规则》的规定,抑或是依据中国《民法通则》及其《民通意见》的规定,均构成违法,应承担相应的违法责任及违法后果。
(四)第二名仲裁员代为指定不当的法律责任及其违约责任承担
违反《公约》及《程序规则》规定代为指定了南海案的第二名仲裁员,其法律责任及违法的法律后果是什么,应由谁承担?!
本案第二名仲裁员的指定程序违法,首先导致本案仲裁庭的组成违法,其次导致违法仲裁庭所进行的所有仲裁程序均违法、所有的开庭违法、作出的所有决定及裁决违法,最后也是最严重的法律后果是:直接导致其作出或将作出的所有裁决,不管是管辖权裁决还是实体事项的裁决,均违法且均完全可能将被享有管辖权的法院撤销。
鉴于无论是菲律宾,还是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两者均未在《公约》附件七第3条规定的期间内分别请求指定及或依据请求指定而代为指定第二名仲裁员,均严重违反《公约》及仲裁庭自己后为本案制定的《程序规则》规定的指定仲裁员的期间,理论上均应承担因该违反《公约》行为而带来的严重的不利法律后果。
不过,真正承担因违反《公约》规定代为指定第二名仲裁员的期间不当从而带来严重不利法律后果的主体,不是国际海洋法庭庭长而应是菲律宾,且只能是也必须是菲律宾,因为正是由于菲律宾在中国指定第二名仲裁员期间尚未届满尚缺两天时间条件下便迫不及待地急不可奈地提前向国际海洋法庭庭长提出代为指定本案第二名仲裁员的要求,才导致国际海洋法庭庭长据此相应地也提前两天完成了对第二名仲裁员的指定,从而事实上及本质上均导致中国作为当事国一方指定第二名仲裁员的期间尚未届满即因菲律宾一方的非法剥夺而丧失,严重侵犯并剥夺了中国作为当事国他方指定仲裁员的《公约》权力。事实上依据《公约》规定,不管中国是否接受该案仲裁庭的管辖,也不管该案仲裁庭是否确实享有仲裁管辖权,本案所有仲裁程序包括本案仲裁庭的组成,都必须首先依据《公约》及《程序规则》规定正当进行及正当组成,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更不得滥用《公约》规定的请求第三人代为指定第二名仲裁员的权力/权利以损害他国当事人的合法正当权益。本案中,且不论其他包括仲裁庭是否享有管辖权的问题最终如何解决,若其先决问题即仲裁庭的组成本身即非法不当,何来仲裁庭的正当管辖权?!
(五)中国即使被迫作为当事国一方其公约项下的任何仲裁权力/利亦都不得任意受到贬损
虽然中国不承认本案仲裁庭的管辖权,也绝不参与本案任何仲裁程序,但这绝不等于菲律宾及本案仲裁庭就可以据此不依《公约》及《程序规则》规定而任意地胡作非为,必须依据《公约》规定正当地进行仲裁程序。这一点,本案仲裁庭非常清楚明白,也一直在重复地抑或是“喋喋不休”地宣称如下观点:
“(1)仲裁庭已提醒中国,仲裁庭将一直对中国敞开大门,以便中国在本案进行的任何阶段都可以参加本案仲裁程序*For the purpose of calculating a period of time under these Rules, such period shall begin to run on the day following the day when a notice is received. If the last day of such period is an official holiday or a non-business day in the State of the Party concerned, the period is extended until the first business day that follows.。
(2)依据附件七第5条规定,仲裁庭负有‘保证任何一方当事人享有充分的开庭及陈述其意见的机会’*见《管辖权裁决》第12页第18段,第19页第50段等。。
(3) 《公约》附件七第9条对当事国不参加仲裁程序的情况作了明确规定:争端一方缺席或不对案件进行辩护,不应妨碍程序的进行。据此,即使中国不参与也阻止不了本仲裁庭进行仲裁程序。中国仍旧是本仲裁案的当事人,……应受本仲裁庭作出的任何裁决的约束*有关《公约》的官方中文译文,本文仅对个别文字有些微调整,并非一字一字均依据官方的中文译文,特此说明。此段内容见《管辖权裁决》第11页第11段。。
(4)即使仲裁庭认定,中国对本仲裁案的来往通讯构成对仲裁庭本案管辖权的抗辩,但是仲裁庭仍旧负有依据《公约》附件七第9条的规定,查明其确实对本案争议享有管辖权的义务*见《管辖权裁决》第24页第1.4段。。”
既然无论中国是否参加本案仲裁程序,仲裁庭都认定中国仍是“本仲裁案的当事人”,且“依据《公约》第296(1)条规定以及附件七第11条规定,中国都应受本案仲裁庭作出的任何裁决的约束”*见《管辖权裁决》第11页第11段。。既然依据《公约》附件七第9条规定,仲裁庭必须查明其对本案争端确实享有管辖权,并且查明当事人提出的仲裁请求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确有依据,否则仲裁庭不得对本案作出实体裁决,那么,本案仲裁庭的所有程序,尤其是仲裁庭的组成这一属于仲裁程序核心的重要程序,就应该符合《公约》以及仲裁庭制定的本案仲裁《程序规则》的规定。本案别说是事涉多国国家重大主权权利及主权利益的国际仲裁,就是一普通平等民事主体之间争议的商事仲裁,其仲裁庭的组成也必须依法依规则规定进行,不得剥夺任何一方当事人指定仲裁员的权力/利,否则所涉仲裁裁决就完全可能被有管辖权的法院撤销。
(六)本案管辖权裁决的国籍及决定仲裁裁决国籍的要件
本案仲裁应属临时仲裁,虽然依据本案《程序规则》第5条规定以及仲裁庭第1号行政指令,本案仲裁在常设国际仲裁院登记,常设国际仲裁院指定其高级顾问Judit. Levine女士作为本案仲裁程序的登记官员,本案仲裁程序文件由常设国际仲裁院归档,本案仲裁费和实际费用亦由常设国际仲裁院收存。
依据本案《程序规则》第14条规定,本案仲裁程序地(seat of the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shall be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为荷兰海牙*Article 14 1. The seat of the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shall be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但本案《程序规则》没有规定本案仲裁的仲裁地(place of arbitration)。鉴于仲裁程序地通常更多地是指仲裁程序进行的地方,包括仲裁裁决作出的地方,强调的更多的是其物理的或地理的属性及特征,而仲裁地则主要是指其具有的法律属性而不是地理属性,即仲裁地通常决定了所涉仲裁裁决的国籍,比如依据《常设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第18条1款规定,“裁决应视为在仲裁地作出。”*Article 18 1. ...The award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made at the place of arbitration.除非双方当事人另外约定了仲裁裁决的国籍。据此,本案《程序规则》没有明确规定仲裁地而仅规定了仲裁程序地,似为一大缺陷。
据此,在本案《程序规则》没有另外规定仲裁地的条件下,仲裁程序地应该被视为仲裁地,反之亦然,同样可以决定本案仲裁裁决的国籍。毕竟,制作仲裁裁决本身即是仲裁程序的一部分,规定了仲裁程序地,即完全可以视为规定了仲裁地,除非当事人对仲裁地或者仲裁裁决的国籍另有规定*或者是由于英文单词使用的不同,即seat和place之间的差异,但本质上法律含义相同或相似。。
仲裁裁决的国籍对国际商事仲裁或投资条约仲裁都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涉及到对外国仲裁裁决的执行问题,据此仲裁地的规定就成为任何一个国际仲裁案件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即使当事人或当事国在所涉的公约、条约或契约中没有规定仲裁地,在所涉案件应适用的仲裁规则中,不管是机构仲裁规则,抑或是临时仲裁庭自行制定的临时仲裁程序规则,通常也均对或均应对仲裁地作出规定。像目前本案这样特别重大的国际争端案件,临时仲裁庭就更应该依据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即使任何一方当事人的意见都没有,也应该参考《常设仲裁院仲裁规则》有关“当事方事先未就仲裁地达成合意的,仲裁庭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仲裁地”的规定*参见《常设仲裁院仲裁规则》第18条1款。,将确定仲裁地的责任明确规定由仲裁庭直接承担,并在其制定的仲裁程序规则中对仲裁地作出明确规定,否则就是个瑕疵或缺陷,不足以称之为正当的完善的国际仲裁。
目前大部分的国际商事仲裁规则中都对仲裁地的确定作了规定*比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15规则第七条,国际商会2012仲裁规则第18条。。这就表明,虽然实践中仲裁条款很少约定仲裁裁决的国籍,但却可以通过约定仲裁地或仲裁程序地而代替约定并作出指引,或者通过适用的仲裁规则规定的仲裁地的确定而代替规定并作出指引,从而以仲裁地或仲裁程序地决定仲裁裁决的国籍。鉴于无论是仲裁地还是仲裁程序地都蕴含着裁决作出地或裁决地的概念,而裁决地的概念如此重要以至于若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则有关的仲裁裁决撤销就至少有一半的可能无地无国可去亦无确定的法院可为管辖,因为参考依据《纽约公约》第1条1款(戊)项规定,只有裁决地国的法院以及裁决所依据法律的国家的法院才享有撤销仲裁裁决的权力*《纽约公约》第五条一款(戊)规定如下:裁决对各造尚无拘束力,或业经裁决地所在国或裁决所依据法律之国家之主管机关撤销或停止执行者。。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国际仲裁,因为无论是国际商事仲裁、国际投资条约项下仲裁,还是国际仲裁,都不可能漂浮在空中而没有具体的程序进行地,都不可能不归属于某国某地,因而本质上均应由程序进行地及或裁决作出地国包括裁决所依据的法律的国家的法院管辖。更有甚者,在国际争端仲裁条件下,由于适用的法律是国际法,可能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国法律可专门为此作出属地属国性质指引的规定,因此,明确规定包括裁决作出地在内的仲裁地,就更至关重要应非规定不可了。
但遗憾的是,本案仲裁庭指定的《程序规则》,该规定的几乎都规定了,但恰恰没有明确规定仲裁地,虽然规定了仲裁程序地,理由何在。
也许,退一步说,本案是国际公法上国家与国家之间争端的仲裁,事涉国家主权等重大国家利益,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国际商事仲裁,甚至国家与投资者之间的投资条约项下仲裁也无可比拟,本应一切都规定完善,但由于国家之间有关主权的争端多是通过谈判协商解决而较少通过仲裁解决,且全世界也就一个国际常设仲裁院,通常国际争端仲裁均在海牙进行,海牙自然就成为仲裁程序地,这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仲裁地乃至仲裁裁决地的确定似乎就变得不那么重要,所以本案仲裁庭忽略了?!
还有,也许是更重要的,由于是国家之间争端的仲裁,鉴于仲裁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及国家信誉的至高无上,争端当事国不会既同意仲裁又不同意执行仲裁裁决,除非根本不接受仲裁作为解决其国与他国之间争端的解决方式,故人们几乎绝少想到或意识到,越是国家之间争端的仲裁,因为事涉当事各国国家主权利益和人民利益,绝无小事,就更应设有撤销程序,以备若裁决不公裁决就应被撤销,反而是有意无意地均忽略了这个重要问题,从而既没有必要规定仲裁地,也没有必要从仲裁地确认仲裁裁决的国籍?!
更有甚者,又因国家之间争端的仲裁通常会在常设国际仲裁院在海牙进行,仲裁程序地自然就是海牙;且国家之间争端的仲裁通常也涉及不到仲裁裁决的法院强制执行问题,故事涉国家之间有关主权、主权权利及其他重大国家利益的国际仲裁裁决的国籍,似乎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从而可以忽略不作规定?!
或者,本案仲裁庭是故意地不对仲裁地作出规定,而仅规定了仲裁程序地,从而从仲裁裁决的国籍上就扼断了当事国可能提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的程序?!否则,作为曾亦任刚结案不久的荷兰王国诉俄罗斯的“北极阳光案”(“Arctic Sunrise” cas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 v. Russian Federation) 中首席仲裁员的本案首席仲裁员Judge Thomas A. Mensah法官应该对《常设仲裁院仲裁规则》的所有规定都非常熟悉,为何却在其主导制定的本案仲裁《程序规则》中独独只将《常设仲裁院仲裁规则》第18条1款规定的“裁决应视为在仲裁地作出”忘记,而恰恰、独独记得《常设仲裁院仲裁规则》第18条2款规定的“仲裁庭可在其认为适当的任何地点进行审议”等?!
换句话说,本案仲裁庭制定的《程序规则》第14条仅规定了仲裁地点(Seat of arbitration ),却未规定仲裁地 (Place of arbitration)。其“仲裁地点”的规定与《常设仲裁院规则》的规定一致,但唯独遗漏了“仲裁地”的规定,是有意还是无意?!
比如,本案仲裁《程序规则》第1款明确规定:“本案仲裁程序地应为荷兰海牙”。这一点与《常设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第18条1款规定的“当事方事先未就仲裁地达成合意的,仲裁庭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仲裁地。裁决应视为在仲裁地作出”完全不同,主要是遗漏了“仲裁地的确定”以及“裁决应视为在仲裁地作出”的规定。
又比如,本案仲裁《程序规则》第14条2款规定:“仲裁庭可在其认为适当的任何地点进行审议。除非当事方另有约定,仲裁庭还可在其认为适当的任何地点为其他任何目的举行会议,包括进行开庭审理。”此规定与《常设仲裁院仲裁规则》第18条2款规定的“经征询当事人,仲裁庭可以在任何其认为适当的地方开庭。仲裁庭还可以为进行审议或相关目的而在其认为适当的任何地方会面举行会议*Seat of Arbitration, Article 14.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provides that “Upon consulting the Parties, the Arbitral Tribunal may conduct hearings at any location it considers appropriate. The Arbitral Tribunal may also meet at any location it considers appropriate for deliberations or related purposes”, while Place of Arbitration, Article 18.2 of the ARBITRATION RULES 2012 of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provides that “The arbitral tribunal may meet at any location it considers appropriate for deliberations.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by the parties, the arbitral tribunal may also meet at any location it considers appropriate for any other purpose, including hearings.”的规定相比,除语言及顺序略有不同外,意思完全一样。
既然这些开庭、合议、会议的具体地点的规定,可以意思完全一致,为何在仲裁地、仲裁裁决作出地的规定上,就完全不一样了?仲裁庭是有意无意地忽略?还是有意无意地不作规定?!更何况,本案的首席仲裁员同时也是荷兰王国诉俄罗斯的“北极阳光案”中的首席仲裁员。在该案中,仲裁庭制定的该案《程序规则》第14条的标题即为仲裁地(Place of Arbitration),第14.1条规定“仲裁程序地为维也纳。”*Place of Arbitration Article 141. The place of the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shall be Vienna.2. Upon consulting the Parties, the Arbitral Tribunal may conduct hearings at any location it considers appropriate. The Arbitral Tribunal may also meet at any location it considers appropriate for deliberations or related purposes.”看来,首席仲裁员还是清楚仲裁地与仲裁程序进行地之间的法律意义上的区别的。难道在首席仲裁员看来,仲裁法上的place 与 seat意思完全一致,毫无区别?
另外,本案仲裁庭作出的《管辖权裁决》,也没有特别地将仲裁程序地抑或仲裁地作为一重要项单独列出说明,这与通常无论是国际商事仲裁裁决、还是投资条约国家与投资者之间的仲裁裁决抑或是其他国际仲裁裁决都明确确定了仲裁地的作法大相径庭,也与本案《管辖权裁决》事无巨细将本案所有内容甚至包括仲裁庭认为应该列上的其他内容都列上的风格完全不同,其原因笔者至少可以大胆地推测为:完全是本案仲裁庭有意故意地忽略!有意地故意地不对更多地具有法律属性的仲裁地作出规定。因为,没有仲裁地,就没有仲裁裁决在何地作出,也就表面上没有仲裁裁决的国籍,比如本案“管辖权裁决”就没有在封面上也没有在内容上明确本案仲裁裁决的作出地,据此就表面证据而言,似乎难以撤销所涉仲裁裁决!当然,这仅是笔者的管窥之见。
但无论如何,鉴于本案仲裁程序地是荷兰海牙,本案裁决的裁决地通常也应是荷兰海牙除非仲裁庭另有规定,但本案仲裁庭没有其他的另外规定,据此,本案仲裁裁决的国籍自然也应是荷兰了。
综上,本案仲裁裁决的国籍为荷兰。
(七)本案管辖权裁决及可能作出的实体裁决均将可能被裁决地国荷兰的法院撤销
当仲裁案件规定或约定了仲裁程序地或仲裁地的时候,仲裁裁决就具备了某一国家国籍的特性,同时也具备了依据裁决地国家的法律撤销仲裁裁决的可能性,这是参照并依据1958年《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戊)项有关撤销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家法院为裁决地所在地国的法院,或裁决所依法律之国家之主管机关的规定所得出的结论。所谓享有撤销仲裁裁决的主管机关通常即指一国的法院。既然本案仲裁裁决的国籍是荷兰,本案仲裁裁决是否可以依法撤销就要看一看荷兰仲裁法是如何规定了。根据《荷兰仲裁法》第1064条第2款规定,撤销裁决的管辖法院是:
“撤销申请应向依照第1058条第1款将裁决正本交存其登记官的地方法院提出。”依据第1058条1款2项规定,“将终局裁决或部分终局裁决交存于仲裁地点位于其地区内的地方法院的登记官。”鉴于本案不是荷兰国内仲裁而是国际仲裁,且依据本案仲裁《程序规则》规定,常设国际仲裁院是本案的登记机构,登记官由常设国际仲裁院指派,本案仲裁所有仲裁文件应交于常设国际仲裁院登记归档,因此如果中国政府要提起撤销本案仲裁裁决之诉,则应在常设国际仲裁院所位于的地区内的荷兰地方法院提起撤销之诉,除非荷兰法律另有规定。
关于撤销本案裁决的理由,依据《荷兰仲裁法》第1065条1款1项和2项,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是(1)缺乏有效的仲裁协议;(2)仲裁庭的组成违反适用的规则。关于缺乏有效的仲裁协议,下文再述;仅就仲裁庭的组成违反适用的仲裁规则而言,上文已明确表述,此不赘述。
可见,本案仲裁庭由于其组成违反《公约》规定,依法可以提起撤销之诉。
另据悉,在尤科斯诉俄罗斯案(Yukos Universal Limited (Isle of Man) v. The Russian Federation)*PCA Case No. AA 227,见pca网站。中,俄罗斯正在荷兰法院提起撤销仲裁裁决之诉,虽然这只是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投资条约项下争端案件而不是国家之间的事涉国家领土主权的国际争端案件,但毕竟一方当事人涉及国家的主权征收行为,与普通的商事国际仲裁案件大不同。且既然尤科斯案与本南海仲裁案的仲裁程序进行地均为荷兰海牙(否则没有理由在荷兰海牙提起撤销裁决之诉),就意味着两案的仲裁裁决国籍均为荷兰裁决,依据荷兰的仲裁法,俄罗斯当然可以据此在荷兰海牙提起撤销仲裁裁决之诉。既然尤科斯案件可以在荷兰提起撤销之诉,南海案件,待事实裁决作出之后,为什么就不可以依据荷兰仲裁法在荷兰海牙地方法院提起撤销之诉呢?!
关于撤销裁决的期间,依据《荷兰仲裁法》第1064条第3款规定,“撤销申请可在裁决一旦具有既判力时提出。在裁决交存地方法院登记官三个月后,申请权即告取消。但是,如果裁决和执行许可一起正式送达另一方当事人,该方当事人可以在送达后三个月内申请撤销,不论前句提及的三个月期限是否已届满。”
第4款规定,“撤销临时仲裁裁决的申请仅可与撤销终局或部分终局裁决的申请一起提出。”这意味着,本案管辖权裁决不能单独撤销,必须等待本案实体裁决作出后一并撤销。笔者希望本案仲裁庭能及时纠正错误不再继续管辖并作出实体裁决,当然这在目前条件及局势下,可能性似乎不大。因此,我认为:一旦本案实体裁决作出,中国政府或中国民间,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本人目前尚未思虑成熟),就要及时地在荷兰法律所规定的期间之内对本案管辖权裁决及实体裁决一起在荷兰海牙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撤销本案裁决之诉。
第5款规定,“所有撤销理由应在传票令状上说明,违者处禁。”
综上,一言而蔽之,本案仲裁庭的组成因第二名仲裁员的代为指定程序及期间违法,不当剥夺了中国指定仲裁员的权力/利,依法完全可以撤销。
另外,依据《公约》附件七第3.(c)条规定,“争端他方应在收到本附件第一条所指通知三十天内指派一名仲裁员,最好从名单中选派,并可为其公民。如在该期限内未作出指派,提起程序的一方,可在该期限届满两星期内,请求按照(e)项作出指派。”其中,“最好从名单中选派,并可为其公民”的规定是对《公约》项下争端当事国各自享有指定一名仲裁员权力/利的特别规定,完全不同于其余仲裁员的指定,不受《公约》附件七第3.(e)条规定的“应属不同国籍,且不得为争端任何一方的工作人员,或其境内的通常居民或其国民”的限制,这正是为了彰显国际仲裁解决国际争端的优越性,即争端当事国依据《公约》各自均自由享有指定一名仲裁员、且该名仲裁员可以是其公民的权力/利。
但遗憾的是,本案第二名仲裁员的代为指定却不是这样。虽然《公约》并未强迫第三人指定第二名仲裁员时一定要依据《公约》规定的条件进行,但既然《公约》明确规定了第二名仲裁员的指定可以是该争端当事国的公民,那么,从公平起见,或至少从形式上或表面证据上的公平起见,第三人,不管是否是国际海洋法庭庭长,也不管哪国国民任国际海洋法庭庭长,该第三人在为争端当事人代为指定第二名仲裁员时都应该充分考虑到《公约》对指定第二名仲裁员可以指定该争端当事国公民的特殊规定,从而据此从该争端当事国提名的其本国公民的仲裁员名单中或海洋法庭的法官中推举一人指定为第二名仲裁员*当然,由于中国不接受《公约》项下的强制仲裁,应该是没有推荐仲裁员名单,因为在各国推荐的仲裁员和调解员名单中没有找到中国的名单。但无论如何,中国一直在推荐国际海洋法庭的法官,同样可以在此名单中推荐中国籍的法官任本案仲裁员,这不存在回避的问题,而是公约明确规定的权利,与中国不接受不参与的立场无关。,岂不更能障显国际仲裁的独立公平和公正,但遗憾的是,本案没有这样做。
顺便提及,由国际海洋法庭庭长指定的“北极阳光案”中的仲裁庭组成与本案仲裁庭组成的成员中,有两名是相同的,一名是首席仲裁员Thomas A.Mensah法官,另一名是荷兰教授Alfred H.A.Soons。既然一连两案中有两名仲裁员是相同的,且明明有中国籍的国际海洋法庭的现任法官在,国际海洋法庭的庭长,您为何不指定中国籍法官作为本案中代为中方指定的仲裁员?!以便至少就表面证据及表面现象而言,您是依据《公约》规定,充分考虑了所涉当事国中国指定仲裁员以及指定其国民作为仲裁员的权力/利,但遗憾的是,您没有这样做!
仲裁员/仲裁庭是仲裁案件的灵魂。在仲裁庭组成中,为何不充分地尽可能地考虑到仲裁员所代表的各大法系甚至不同国家的普遍性而仅集中在某些国家推荐的仲裁员手中,甚至完全忽略争端当事国推荐的国际法庭的法官*《公约》所涉各国推荐的仲裁员名单中,没有中国政府推荐的名单,笔者猜测,这是由于中国不承认《公约》的强制仲裁管辖,因此中国也就没有必要就《公约》规定的强制仲裁程序推荐仲裁员名单。?!
另外,在2013和2014两年中仅有的四个涉及海洋法的案件中,有三案国际海洋法庭指定了Thomas A.Mensah法官为首席仲裁员,一案指定了荷兰教授Alfred H.A.Soons为首席仲裁员。这是否意味着国际海洋法庭的21名法官中,其他找不出首席仲裁员了。
从仲裁庭的组成中可以看出当今国际海洋法争端解决中的弊端。
三、中国不参与本案仲裁程序表面上不会剥夺仲裁庭对南海仲裁案的管辖权,但实质是由于中国政府认为仲裁本案的仲裁庭根本不享有管辖权从而实质上“剥夺”了仲裁庭的管辖权
《管辖权裁决》的第2项决定为:“认定中国不出席仲裁程序不能剥夺本仲裁庭的管辖权。”
中国政府自始起即明确反对菲律宾提起本仲裁案,宣告菲律宾提请本案仲裁事项的实质是南海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问题,超越《公约》调整范围,不涉及《公约》的解释或适用*见中国《立场文件》第2页第3条。,并将有关仲裁文件退回菲律宾。
仲裁庭作出的上述第2项决定认定是否正确,是否具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中国作为事实上的本案当事国一方,自始起即拒不接受且绝不参与本案仲裁程序是否正当,利弊得失如何,且待笔者分析之后,自知分晓。
(一)《管辖权裁决》第2项决定是否具有法律依据
《公约》附件七第9条不到案规定:“如争端一方不出庭或对案件不进行辩护,他方可请求仲裁庭继续进行程序并作出裁决。争端一方缺席或不对案件进行辩护,应不妨碍程序的进行。仲裁庭在作出裁决前,必须不但查明以地争端确有管辖权,而且查明所裁请求在事实上和法律上确有根据。”*略去官方中文译文中仲裁法庭的“法”字,修改“所提要求”为“所裁请求”。
本案《程序规则》第25条作出了与上述《公约》附件七第9条相似的规定*Failure to Appear or to Make Submissions Article 25.1. Pursuant to Article 9 of Annex VII to the Convention, if one of the Parties to the dispute does not appear before the Arbitral Tribunal or fails to defend its case, the other Party may request the Arbitral Tribunal to continue the proceedings and to make its award. Absence of a Party or failure of a Party to defend its case shall not constitute a bar to the proceedings. Before making its award, the Arbitral Tribunal must satisfy itself not only that it has jurisdiction over the dispute but also that the claim is well founded in fact and law.。
据此的确,无论从上述《公约》和本案《程序规则》规定,还是从仲裁的基本原则、理论及实践而言,仲裁案件的一方当事人/国不出席仲裁庭审或不参与仲裁程序抑或对仲裁案件不作出任何答辩或抗辩,均不得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当然,仅据此也不能剥夺依据规定经正当程序组成的仲裁庭对所涉仲裁案件的管辖权。
同样,任何仲裁案件的当事人/国不参加仲裁程序,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被申请人将仲裁机构寄送的仲裁文件以拒收的理由退回以表其拒不参与仲裁程序的态度,也比比皆是,但这均阻止不了仲裁程序的正常进行,也阻止不了依正当程序组成的仲裁庭享有的对所涉仲裁案件的管辖权,更阻止不住当事人应受所涉仲裁裁决的约束,除非所涉仲裁裁决因违反正当程序而被撤销或不予执行。
当事人不参与仲裁程序阻挡不了仲裁程序的继续进行,其根本理论支撑及保障之一即是仲裁庭享有自裁管辖权(competence—competence jurisdiction)的原则。即仲裁庭享有自己决定自己管辖权的权力*即competence—competence principle, 广泛见于《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及各国仲裁法和世界各国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中,包括中国仲裁法(第21条,只不过将此权力规定由仲裁委员会行使而不是仲裁庭行使)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历届仲裁规则中,暂不细述;常设仲裁院(PCA) 2012仲裁规则第23.1条对仲裁庭管辖权抗辩条款规定:“Pleas as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arbitral tribunal Article 23.1. The arbitral tribunal shall have the power to rule on its own jurisdiction, including any objec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existence or validity of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For that purpose, an arbitration clause that forms part of a contract, treaty, or other agreement shall be treated as an agreement independent of the other terms of the contract, treaty, or other agreement. A decision by the arbitral tribunal that the contract, treaty, or other agreement is null, void, or invalid shall not entail automatically the invalidity of the arbitration clause.”。这一原则作为仲裁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目的只有一个,维护作为替代诉讼制度同样以法律方式解决当事人/国之间争议/端的仲裁制度,能够得以顺利进行并达到解决争议及或争端的目的,这无可厚非!
据此,本案仲裁庭作出的上述“认定中国不出席仲裁程序不能剥夺本仲裁庭的管辖权”的决定,就其法律依据而言,包括就仲裁的基本原则及理论而言,的确具有法律依据。但是:如果仲裁庭的确不享有所涉仲裁案件的管辖权,如果所涉案件进行的仲裁程序有违法、违反仲裁程序规则之处,且据此所涉仲裁裁决可被撤销或不予执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如上所述,本案中,中国政府自始起明确反对菲律宾提起本仲裁案,明确表明不接受本案仲裁庭的管辖权,不参与本案任何仲裁程序。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声明中国政府发出的立场文件、递交常设仲裁院的有关信件等在任何意义上任何形式上均不得被解释为中国参与本案仲裁程序*见《管辖权裁决》第2页10段,鉴于此规定及此态度及《公约》附件七第9条的规定在本案管辖权及受理案件裁决中,在仲裁庭为管辖权而进行的三次庭审中,随处随时可见,具体出处均略,亦见管辖权问题第一次开庭时首席仲裁员的开场白,第一次庭审笔录第1页。:“本立场文件旨在阐明仲裁庭对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没有管辖权,不就菲律宾提请仲裁事项所涉及的实体问题发表意见。本立场文件不意味着中国在任何方面认可菲律宾的观点和主张,无论菲律宾有关观点或主张是否在本立场文件中提及。本立场文件也不意味着中国接受或参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中英对照),第2段,2015-01-19发布者sisu04来自:中国外交部网。
对于中国不接受不参与本案仲裁,仲裁庭也一直是以《公约》附件七第9条规定的“争端一方缺席或不对案件进行辩护,应不妨碍程序的进行”以对抗,并据此认为,中国不参加本案仲裁程序不能阻止本案仲裁庭进行仲裁程序。且“中国仍旧是本仲裁案的一方当事人,依据《公约》第296(1)条规定以及附件七第11条规定,中国应受本案仲裁庭作出的任何裁决的约束。”*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中英对照),第11第11段,2015-01-19发布者sisu04来自:中国外交部网。
就人天生具有的心理倾向而言,除非所涉证据明确表明仲裁庭不具有管辖权,否则一般的人、一般的仲裁庭在处理事关其是否具有管辖权问题时,总会趋向于只要有一点点联结点、一点点表面证据为证就会作出其享有仲裁管辖权的决定,即便以后在实体的审理过程中,完全可能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或理由,最终以仲裁庭无管辖权为由而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仲裁庭也会在所不辞,作出自己享有仲裁管辖权的决定或裁决。这本也无可厚非!
同时,当事人及或当事国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拒不参加所涉案件仲裁程序是当事人/当事国的权利,他人无权干涉与过问,只不过不参加仲裁程序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即所涉仲裁庭不会因为被申请人拒不承认其管辖权或不参加仲裁程序而据此认为所涉仲裁庭不享有仲裁管辖权,也不会因此而不继续进行仲裁程序或不作出仲裁裁决,被申请人也不可能因此而不受仲裁裁决的约束,除非仲裁庭的确不享有所涉仲裁案件的管辖权!除非所涉案件进行的仲裁程序有违法、违反仲裁程序规则之处且据此所涉仲裁裁决可被撤销或不予执行!本案情况,即是如此!
据此,中国不接受本案仲裁庭管辖权是正确的,因为“中国已根据《公约》的规定于2006年作出声明,将涉及海域划界等事项的争端排除适用仲裁等强制争端解决程序。因此,仲裁庭对菲律宾提起的仲裁明显没有管辖权。基于上述,并鉴于各国有权自主选择争端解决方式,中国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当然,由于中国不接受《公约》项下的强制仲裁,应该是没有推荐仲裁员名单,因为在各国推荐的仲裁员和调解员名单中没有找到中国的名单,但无论如何,中国一直在推荐国际海洋法庭的法官,同样可以在此名单中推荐中国籍的法官任本案仲裁员,这不存在回避的问题,而是公约明确规定的权利,与中国不接受不参与的立场无关。,不管本案仲裁庭是否接受中国政府的主张,此事实客观存在!
关于中国政府不接受本案菲律宾政府提起的强制仲裁,事实上还涉及到一个先决问题需要解决,即菲律宾政府提起的本案仲裁是否涉及到中国对部分南海岛屿礁享有主权以及行使主权权利问题需要先作出决定,仲裁庭才能决定其是否享有管辖权。笔者认为,仲裁庭应该具备通过表面现象看到本质的能力,且应该在查阅了大量的文件资料和中国有关法律以及中国政府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的数份有关声明等的基础上对其是否享有管辖权作出正确判断,从而裁决其无权管辖本案。但遗憾的是事实恰恰相反,仲裁庭却作出其享有管辖权的相反裁决。
(二)关于仲裁庭第二项决定是否具有事实依据的问题
仲裁庭作出的第二项决定“认定中国不出席仲裁程序不能剥夺本仲裁庭的管辖权”是否正确还取决于事实依据,即其当然前提是:所涉仲裁庭必须是依据正当程序以正当方式组成。
上文已述,本案仲裁庭第二名仲裁员的指定不符《公约》规定,不符本案《程序规则》规定。据此本案仲裁庭的组成不符《公约》规定,不符《程序规则》规定。本案仲裁庭作出的所有仲裁程序、仲裁裁决,因仲裁庭的组成违法不当,不具任何法律效力,不能约束任何一方当事人,且不当违法组成的仲裁庭作出的仲裁裁决依法应被撤销。
据此,本案仲裁庭作出的上述第二项“认定中国不出席仲裁程序不能剥夺本仲裁庭的管辖权”决定,因其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即缺乏其仲裁庭是依据《公约》和《程序规则》合法正当组成的这一重要事实,完全不能成立。
顺便提及,关于本案仲裁庭的组成,本案仲裁庭似乎很有底气,没有花费多少笔墨,仅在《管辖权裁决》第16页中第28段至31条简短的四段中就将本案仲裁庭的组成叙述完毕,完全没有考虑至有关本案第二名仲裁员组成的时效起算错误从而本案仲裁庭完全是非法不当组成,其直接后果是导致所涉裁决应被撤销,更不要说强制执行了。这样的仲裁继续下去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未完待续)
On the Illegal Ultra Vires Jurisdiction of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Concurrent Discussion of the Proper Position and Strategy of Non-acceptance and Non-participation by Chinese Government (1)
GAO Fei
(Chin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Arbitration Commission Shanghai Office, Shanghai 200122, China)
As to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submitted by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the Tribunal has made an award deciding it has the jurisdiction no matter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lready expressed that the case is entirely related to the state sovereignty so that the tribunal has no jurisdiction at all. Considering that the award is suspected of unilateral interpreting the Convention, ignoring Chinese position, partial to the Philippines and illegal ultra vires jurisdiction etc., this article is intending to analyze decisions of the Award one by one, revealing the truth and harm of the illegal ultra vires jurisdiction, stating concurrently what the Chinese position of non-acceptance and non- participation to defend the state sovereignty is absolutely right as far as political, diplomatic and state, but it is biased if both official and people are all non-participations as far as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it shall lose best chances to understand the whole situation and refute the inappropriate requests of Philippines face to face, to restrict the Tribunal who may appear biased in due time, to fully persuade the Tribunal to accept China’s legitimate views in order to get the good results as well as to show the Chinese style and legal soft power to the world; it is easy to let the Tribunal to abuse “legal chauvinism”, ultra vires jurisdiction and make an 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substances against China, and what is more, it gives grounds for talk damaging the image of China. But if we insist the basic principle position of non-acceptance and non-participation by Chinese government while we may participate in all arbitration procedures in any unofficial way, it shall be the best tactics and it is never not too late by combination of two and echoes, knowing enemy and ourselves well, response in time, arguing and refuting according to law, adopted piecemeal and never give up, therefore, we can win the case without dangers.
non-acceptance and non-participation; people’s participation; illegal ultra vires jurisdiction; way of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way of law
2016-05-16
高菲,女,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秘书局上海办公室,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法。
DF90
A
1672-769X(2016)04-01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