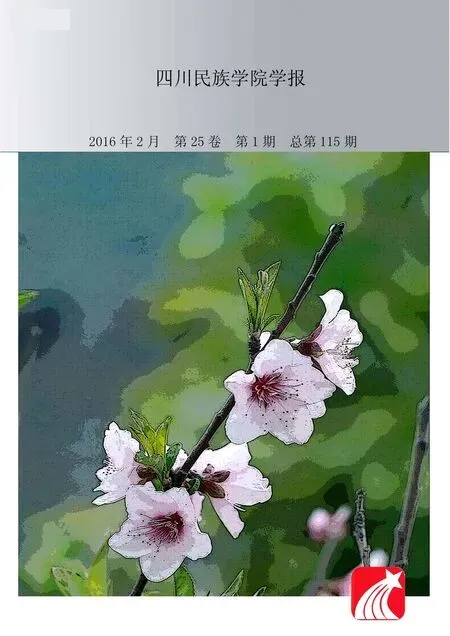河南省叶县司庄村蒙古族族源、族风、族称恢复刍议
郭新榜
★民族研究★
河南省叶县司庄村蒙古族族源、族风、族称恢复刍议
郭新榜
【摘要】元朝的建立与覆亡过程中,有不少蒙古族散居河南境内,发展为现今的河南蒙古族,平顶山叶县便是河南蒙古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该地司庄“易汉”之蒙古族在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深受当地汉族影响,但又有所不同,表明不同民族在民族融合、文化演进后依然会有一定差异性,这种文化差异性反映了民族的不同性。近些年当地村民要求恢复蒙古族族称的愿望悄然强烈,并得以实现,体现了在不同历史时期,当地“易汉”之蒙古族在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方面的基本情况。
【关键词 】河南省;叶县;司庄;蒙古族;元朝;明朝
On the Recovery of Mongolians' Ethnic Origin, Customs and Title in Sizhuang Village in Ye County
Guo Xinbang
【Abstract】In Yuan Dynasty's establishment and fall, many Mongolians lived scattered in Henan provinc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s the Mongolian lived is in Ye county. The Mongolians in Sizhuang village is influenced by the local Han in many ways, such as language, customs and habits. But Mongolians also retain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which indicate there will be some differences remained after ethnic fusion. In recent years, Sizhuang villagers have wanted to restore the Mongolian name and succeeded. This reflect Mongolians' basic situation influenced by the local Han in national identity, cultur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Key words】Henan province; Ye county; Sizhuang village; Mongolian; Yuan Dynasty; Ming Dynasty
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带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蒙元政权建立与倾覆过程中,这里成为根据地、主战场,蒙古族不断散居河南。宋金对峙时,河南曾一度为金所辖,蒙古灭金后,“遂留镇抚中原,分兵屯大河之上,以遏宋兵”[1],使得大批蒙古将士进驻河南。元世祖忽必烈曾向姚枢询问治国之道,姚枢针对当时的问题,提出了三十条救治意见,其中一条便是“布屯田以实边戍”[2],并被采纳,开始“立经略司于汴”,并“屯田唐、邓等州”,“敌至则御,敌去则耕”[3],河南成为忽必烈攻取荆襄和两淮的前线,又有不少蒙古将士屯戍于此。元朝统一后,更有大量蒙古官员长居河南。元明鼎革时,社会动荡不安,河南又是战乱频仍之地,驻守河南的元军屡有败迹*比如“至正十一年(1351年)秋,白莲教领袖刘福通等人打败元军,先后占领亳州、项城、罗山、确山、息州(今息县)、光州(今潢川)、舞阳及叶县,众达10余万人”。见《叶县志》。,为挽救颓势,不少高官显宦被派到河南。然而,明军的南北夹攻使不少蒙古族官民滞留河南。“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三月,明军攻克南阳,俘获元朝将领20余人,时驻守叶县的元军,或逃或降”[4]。同年徐达率军攻占汴梁,黄河以南蒙古官员的北逃之路被切断,使其既无法南逃又不能北上,君臣离散,民人流亡,只好散窜隐迹于汉人之中,世居河南。《叶县志》也说“叶县的蒙古族,是元代遗居本地的蒙古族马秃塔儿和宣帖木儿的后裔,后改为马姓、宣姓,多居住在廉村乡马庄、宣庄,其语言、风俗、习尚、服饰已与汉族无甚差异”[4]。匡裕彻、任崇岳在《河南省蒙古族来源试探》一文中指出,“平顶山是河南蒙古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主要分布在市郊区北渡乡荆山村、廉村乡宣庄和马庄,叶县仙台乡西北拐村和老程庄”[5]。然而,另有一部分蒙古族存在,县志及两位学者均未言明,比如平顶山叶县龚店乡司庄村的蒙古族。现就该地蒙古族的族源、习俗等方面略加陈述,以求证于相关学者,不当之处,烦请雅正。
一、司氏家族族源简述
据《叶县志》载,河南平顶山市叶县蒙古族多马、宣两姓,然而,依笔者调查,除此之外尚有司姓。据司栓修*平顶山市叶县龚店乡司庄村村民,在搜集资料过程中,他提供了一些资料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同志讲述,司氏家族原系蒙古族,祖籍蒙古大草原,元朝初年迁入中原,后来在平顶山市叶县龚店乡司庄村落户。《河南省叶县地名志》称“元朝时,蒙古族司姓居此”,“清代易汉族”*清代,蒙古族与满族关系密切,无“易汉”之必要,恐误。[6]。该村“易汉”之蒙古族自元朝发展至今已传数十代,族众现已达500多口。
司栓修同志说,司氏家族本不姓司,元世祖忽必烈平金败宋,建立元朝时,司氏先祖随同大批蒙古贵族一道进入中原,官封“司农”。当时元朝统治者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这种民族歧视政策致使民族矛盾激化,各族地主与蒙古贵族相互勾结,也可担任主要官职,拥有大量土地,蒙古族人也会被迫流亡,沦为乞丐,司氏家族就是其中之一,由“司农”沦为平民。另外,蒙元政权不能做到轻徭薄赋,以政裕民,致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裂痕不断加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酝酿之中。
元朝末年,蒙元暴政积攒已久,其统治力每况愈下,受压迫的各民族不堪摧折之苦,便揭竿而起,密谋反抗,爆发了“红巾军”起义。当地盛传,蒙古统治者为防止汉人反抗,对其实行严密控制,只准汉人十家用一把生活用刀,并分派一名蒙古头领管制,以确保蒙古族统治者的安全。在此情况下,被统治区民众往往噤若寒蝉,起义军难以传递消息。适逢中秋将至,据说智囊人物刘伯温献计,在中秋节互赠的月饼里面夹上“八月十五杀鞑子”的纸条,约定在八月十五起义。此法极具杀伤力,大批蒙古人殒命,当时司氏先祖已沦为平民,与汉人关系甚好,被部分汉人藏匿保护起来,幸免遇难。明朝立国以来,由于滞留中原的蒙古人数众多,且漠北蒙古势力依然不可小觑,所以,明政府对蒙古族防范严密,明政府曾下令禁用蒙古姓、禁穿蒙古服、禁说蒙古语*“洪武元年,诏蒙古服、蒙古语、蒙古姓,一切禁止”。见顾炎武《日知录》。。滞留在河南的蒙古族为避免民族歧视与压迫,往往改为汉姓,与汉族杂居而处,互通婚姻,不断融合。司氏先祖为求生存,以“司农”的“司”为姓,混迹于汉人中,四处流亡,于明朝中期逃至今平顶山市叶县司庄村。崇祯五年(1632年)发大水,司氏先祖逃难于叶、襄、南阳、漯河、郑州等地,至第二代世祖时返回司庄,繁衍至今。
二、司氏家族族风考查
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长期融合后,纵然有脱胎换骨的变化,其民族心理、民族习俗也很难有彻底的改变。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司庄村村民在社会习俗等方面受当地汉族该方面影响较大,且其族称已“易汉”数百年,但其族俗与当地汉族又有所不同。比如,当地司庄村村民“中秋不愿月”(即不过八月十五)、“人死不插影背风”、“不立亡人碑”、“不压坟头纸”、“不给死人送盘缠”等习俗与当地汉族迥然相异,《河南省叶县地名志》也说当地“居民不过中秋节,人死不插影背风”[6]。
我国许多少数民族都过八月十五中秋节,当地蒙古族为何八月十五不愿月呢?正如上文所述,因为中秋节曾是杀鞑子之日,为蒙古族的忌日,该节日对汉族等民族来说是团圆之日,而对当地“易汉”之蒙古族来说,则是生离死别之时,对他们而言,八月十五恐怕一度是其挥之不去的梦魇,故不过此节日。当地汉族在丧葬方面有“立亡人碑”、“插影背风”的习俗,而当地“易汉”之蒙古族在丧葬方面则“不立亡人碑”,也“不插影背风”。他们“不立亡人碑”、“人死不插影背风”并非表明其无功禄、无财难立,而是不敢注明或不愿注明司氏先祖前段历史,说明当地“易汉”之蒙古族对其族源始终讳莫如深。“不过八月十五”、“不立亡人碑”、“不插影背风”在当地蒙古族中代代相传,时至今日,已由习惯而成风俗。另外,当地汉族在丧葬方面也有“压坟头纸”的习俗,即在坟墓的顶端用石块压一张16开的草纸作为“坟头纸”,并在节日、死者忌日以及家族中办红白喜事时更换*如今,该习俗渐趋简化,虽“压坟头纸”,但很少去更换。,当地“易汉”之蒙古族在丧葬方面也没有该习俗。“送盘缠”也是我国许多民族的丧葬习俗,“送盘缠”就是给死者送一些在阴间享用的物品和钱财,通常是在死者出殡后的第二天傍晚,由死者儿女带着纸人、纸钱等物来到坟前烧毁,意思是让死者带到阴间使用,该地“易汉”之蒙古族也没有该习俗。因为,蒙古族原本信仰萨满教,虽有人、神、鬼、怪思想,但无阴世阳间观念,故不会有为死者“送盘缠”到阴间使用的思想。16世纪,蒙古族由信仰萨满教转为皈依藏传佛教,其教义主张“轮回、转世”,无去阴间生活之说,也不会有为死者“送盘缠”的做法,“送盘缠”到阴间享用与商品意识紧密相连,蒙古族当时尚无此先进思想[7],最终也未形成该习俗。所以,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龚店乡司庄村蒙古族节日习俗、丧葬习俗方面虽深受当地汉族影响,但在特定历史因素作用下又有别于当地汉族,表明不同民族在民族融合、文化演进后依然会有一定差异性,这种文化差异性反映了民族的不同性,这些负载不同民族文化基因的民族群体在行为上与当地其他民族多有不同之处。同时也表明,“同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客观进程,认同则是对同化结果的一个主观确认”[8],而认同程度的大小依同化程度高低而定。
三、司氏家族族称恢复
民族作为社会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属于历史范畴,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变动性”,所以,民族成份和族称的识别与更改便在情理之中。我国民族识别任务在上世纪50年代已基本完成,但由于诸多原因,需要进行民族成份更改或恢复的客观情况依然存在。1990年5月10日,国家民委、公安部发布了《关于中国公民确定民族成份的规定》,就更改或恢复民族成份的依据、具体更改办法等做出了明确规定,成为我国确定民族成份的重要法规依据。由于历史原因,个别民族被划为非自身应属民族成份的,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尊重本民族意愿的情况下,可根据《关于中国公民确定民族成份的规定》予以恢复。在民族识别、恢复过程中既要考虑语言、心理状态、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又要“对这个民族的长期社会历史发展情况、民族地区历史、民族来源和民族关系以及今后民族繁荣发展和民族团结等因素,进行综合的科学分析”[9],还要坚持民族自愿的原则,以上这些均是民族识别、恢复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的,只有这样方可确定民族的成份和族称。平顶山市叶县龚店乡司庄村村民汉化已久,汉语已是其通用语言,但不能以此将其定为汉族,因为,虽然共同的语言是民族识别的一个重要依据,但是,我国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一语多族,一族多语的情况均存在,故不可拘泥这一标准。“共同的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共同心理状态,多表现在精神风貌、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集中体现在自己属于某个民族的心理认知,并且,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民族由于共同的民族心理,还会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恢复和强化,以显示自己有别于其他民族。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龚店乡司庄村村民有别于当地汉族的习俗,认为自身是蒙古族的民族心理早已引起地方政府的注意和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叶县民族宗教局、龚店乡人民政府多次派人进入司庄村进行调查取证,因前几年该村对党的民族政策了解不够,没能及时、尽早恢复蒙古族民族成份。近几年来,随着党的民族政策更加深入人心,当地村民要求恢复蒙古族族称的愿望悄然强烈。在多数族人的要求下,乡政府、宗教局又重新派人进入该村走访、调查、取证,宗教局最终行文下发《叶民宗2001》26号文件,恢复了当地司氏家族的蒙古族族称。自此,司氏族人才算认祖归宗、正本清源,恢复了本来面目。为纪念这一振奋人心的大喜事,该地族人纷纷捐款,立碑流芳,并于2004年农历7月初7进行揭碑典礼,参加典礼的有叶县民宗局领导、龚店乡人民政府领导、司赵村两委工作人员及数百乡邻及族众,场面十分隆重。
综上观之,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最初往往具有强制性,但随着历史的潜移默化作用,会体现出自觉性,甚至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感。比如明政府曾下令禁用蒙古姓、禁穿蒙古服、禁说蒙古语,王朝更迭后的蒙古族只得委曲求全。在强制认同下,蒙古族积习日久,又在逐渐实现着自觉的国家认同,比如明朝宣德年间当地蒙古族司齐跻身官场,被封为监察御史,其后世子孙司文举明末考中进士,进爵翰林院,且被皇帝赐匾:“名著怀清”*据传巴寡妇清家族世代经营丹砂(提炼水银的主要原料),相当富有,曾出巨资帮助秦始皇修长城,并为其皇陵提供大量水银。秦始皇为其筑“怀清台”,予以表彰。《史记·货殖列传》有载:“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故“名著怀清”有表彰功绩之意。该匾后来在家族纷争中被毁,清乾隆五十八年司氏后代又续立,1966年,文革期间再度被毁,现已无存。。司文举有三子:光有、光良、光士,分为长门、二门和三门,长门、二门还为继承祖先光耀门庭的这块匾,互不相让,对簿公堂,打了三年官司,耗尽家中钱财,门匾被毁,也未能分出胜负,从此过起了清贫的生活,此事集中表现了该地蒙古族对新政权的国家认同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认同过程中,当地蒙古族也在实现着对本民族的自我认同,即民族认同。民族认同多表现为民族的自我认同及个体的民族归属感,当地蒙古族村民已易汉数百年,且语言、习俗多已汉化,但该民族群体骨子里始终认为自己属于蒙古族,自2001年民族族称更改为蒙古族后,开始不断地与北方蒙古族建立各种联系,在习俗方面也开始向蒙古族习俗恢复。
参考文献
[1]元史·卷一一九·塔察儿[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p2258
[2]元史·卷一五八·姚枢传[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p2928
[3]元史·卷四·世祖纪一[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p40
[4]叶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叶县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p14、p537
[5]匡裕彻、任崇岳.河南省蒙古族来源试探[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6]叶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河南省叶县地名志[M].福州: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95年,p289、p289
[7]陈烨.蒙古族丧葬习俗中的游牧遗风[J].民俗研究,1992年第4期
[8]杨丽云、董新朝.从经济活动看民族同化与认同[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9]施联朱.怎样识别一个民族[J].中国民族,1982年第11期
[责任编辑:古卿]
作者简介:郭新榜,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基础部讲师。(云南丽江,邮编:674199)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824(2016)01-002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