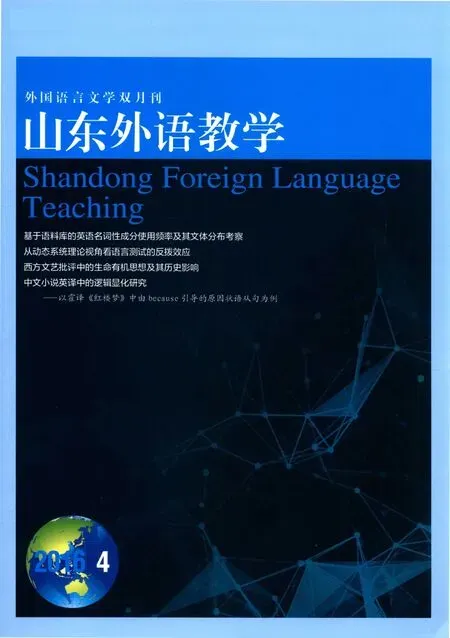西方文艺批评中的生命有机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季明举
(曲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西方文艺批评中的生命有机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季明举
(曲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西方文艺批评诸流派大多有着绵延不息的悠久诗学传统,其中包含了生命有机思想:从古希腊时期到当今“数字化”时代,对待艺术的鲜活生命态度和艺术审美的有机整合意识就一直是一种生生不息的艺术批评模式。这一生命有机思想始终以反理性主义、反技术物化的生动面目出现,在西方文艺批评史上留下了鲜明的足迹,并对当今“全球化”时代文艺理论探索摆脱科技主义、“数字化”洪流的桎梏,回归艺术本体与自觉构成了重大的启示。
西方文艺批评;生命有机思想;艺术整合意识
1.0 引言
西方文艺批评中有一个在发展演进轨迹上清晰可辨的强大生命有机思想:从柏拉图“灵魂说”到中世纪普罗提诺的基督教“太一”美学,从18世纪柯勒律治、华兹华斯的“艺术生命”原则到歌德“有生命的整体”观,从19世纪谢林艺术哲学“无差别的同一”到卡莱尔的艺术“生命起源”理论,从20世纪尼采的生命意志论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美学,对待艺术的鲜活生命态度和艺术审美的有机整合意识就成为一种生生不息的文艺批评模式。这一审美传统绵延达二千多年,自始至终以反理性主义、反技术物化、倡导生命直觉的诗学面目出现,在文学艺术领域产生了跨越历史时空的巨大影响,在西方文艺批评史上留下了生动而鲜明的印迹,并对当今“全球化”时代文艺理论探索摆脱科技主义、“数字化”洪流的桎梏,回归艺术本体与自觉构成了重大启示,即首先艺术是生命的,不是僵死的,它是血肉丰满的鲜活存在;其次艺术是有机整体的、统一的,其诸要素间相互依存、有机互动并共同生成;第三,对艺术这一生命有机体的审美体验或许更多要立足于诗性直觉,而纯粹形式主义的、工具理性式的思维方式不完全适合于艺术关照。本文力图对西方文艺批评史上的这一强大生命有机思想进行历时性的归纳与描述,以期进一步阐释其在西方文艺理论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和历史影响。
2.0 古典派艺术有机思想
宇宙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万物皆为整体所包容。生命是宇宙“灵魂”最伟大的神秘力量。部分为整体所规定,无生命的东西被有生命的东西所诠释。这种有机思维方式在古代异常发达并长期左右着人们对世界的审美认知。可以说古人的生命统合意识比今人要强烈得多;古人的思维更具直观性,审美方式上更具艺术性。这典型反映在柏拉图的文艺美学观念中,柏拉图是西方艺术有机整合思想的始作俑者。他笔下的蒂迈欧提出“造物主创造出的世界机体中贯注着生动的灵魂”,“不妨说世界因此成了一个生物”。(柏拉图,2003:32)在《文艺对话集》中柏拉图又说“美是永恒的自存自在,以形式整一性永与它自身同一”,真正的艺术美是一种“理式”,是“神圣的、纯然一体的美”。(柏拉图,2000:53)由于柏拉图主张艺术“灵感说”,认为“抒情诗人陷入迷狂像酒神的女信徒”(同上),他的艺术整合思想又带上了极具生命意识和非理性色彩的玄妙特征,成为二千年来整个西方文论史上一切宗教的、神秘的、浪漫的、直觉的唯心主义观念之源。另外,亚里斯多德也曾为艺术有机思想的发展做出过贡献。他认为“自然事物有别于人为的事物,因为自然事物所具有的是一种内在的动力源泉,而非外在的有效力量”。(转引自Robinson,1934:384)这种对事物自然性与人为性的理论区隔以及对自然事物“内在动力”的阐发后来演变成为艺术生命有机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即艺术的浑然天成性和内在自我驱动。不过与柏拉图相对照,亚里斯多德真正关心的“不是什么事物正在生成,而是生成什么事物”。(同上:382)他的艺术有机观念更多着眼于业已定型的规范事物,着眼于对整体原则的强调,而疏于对生命意识的张扬。亚里斯多德受毕达哥拉斯学派“数与和谐的原则”影响很大。他评论艺术着重其整体机制。在《政治学》里亚里斯多德说:
美与不美分别就在于美的东西和艺术作品里,原来零散的因素结合成整体。(转引自朱光潜,2000:76)
在亚里斯多德看来,整体是必然的,部分是偶然的。有机整体的美是事物内在驱动力的要求,也是事物保持和谐的根本。“美在整体”的思想是亚里斯多德最基本的美学思想。朱光潜先生认为正是根据这种艺术有机思想,亚里斯多德才断定悲剧作为生活动作的展示是最高的艺术形式,从而建立了他“动作或情节整一”的古典派戏剧理论。这一理论直接影响了后世浪漫派有机论的艺术有机整合思想。
古典派艺术有机思想的代表人物除了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外,还有后来的贺拉斯、朗吉努斯、普罗提诺、中世纪的神学家伯麦和圣.奥古斯丁等人。值得一提的是普罗提诺。作为罗马晚期柏拉图主义的狂热信徒,普罗提诺将柏拉图的“最高理式”引申为“太一”,即宇宙生命之本源。“太一”是最高的真善美三位一体,世界创造是艺术性的,是“太一”向万千世界不间断地“流溢出美”的过程(胡经之,1999:108),即由宇宙法则“溢出”世界灵魂,由世界灵魂“溢出”个体灵魂,最后“溢出”感官世界。个体灵魂渴望摆脱沉重肉身的障碍,通过有机灵魂赋予艺术灵见即神秘直觉,回归灵魂的家即神温暖博大怀抱,与神融为一体。个体灵魂对生命本源的向往便形成美。“太一”“流溢出美”是一个向下的有机生命进程;而个体灵魂对“太一”的向往与回归又构成向上的、直觉生命美的历程。普罗提诺的艺术思维显然是一种神秘有机循环论,将柏拉图生命意识发挥到了极致并直接影响到圣.奥古斯丁“三位一体”(完美整体)、“道成肉身”(生命实现)的基督教有机艺术观。奥古斯丁将美定义为“整一”或者“和谐”,认为上帝的真理不是通过纯粹的逻辑推定,而是通过救主基督“活生生的生命肉身”(奥古斯丁,1963:318-319),让人们直觉到生命美及其被邪恶毁灭的悲剧。这一观念无疑和普罗提诺的“太一”生命说密不可分。事实上在中世纪,整个基督教美学几乎都是普罗提诺、奥古斯丁宗教有机思想的延伸。
中世纪到18世纪初期,随着“文艺复兴”人文个体精神、17世纪政治斗争思想、18世纪理性启蒙主义观念的熏陶,以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快速进步,欧洲艺术哲学家们热衷于理性思考和逻辑分析。随后古典主义又大大发展了“整体”、“和谐”、“有机秩序”之类的美学新形式,如狄德罗对戏剧“三一律”原则的强调,布瓦洛对“自然理性法则”的推崇等等,古希腊和中世纪那种包含浓重神秘气息的艺术有机思想已大为淡化,分析观念和结构意识日趋显著。尽管如此,有机的灵魂和古老的生命意识在“新时代”仍然以改头换面的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如17世纪来自英国“剑桥学派”的夏夫孜博里热烈鼓吹新柏拉图主义思想,提出“灵魂之源四处扩散,使万物充满着活力,并使整体充满生机。……美在于旺盛的生命”(Robertson,1951:49),似乎让人们再次听到了远古生命的呼唤。概言之,古典派有机思想的核心是:宇宙是自然的、有生命的东西。美是趋向整体一致,是以直觉方式来体验完整的内在生命。
3.0 浪漫派艺术有机思想
欧洲浪漫派对艺术有机思想发展的贡献最大。所谓艺术有机思想很大程度上是指浪漫主义的。将“生命作为有机体”(life as organ)这一自然定义用来诠释艺术个性是西方浪漫派的一大美学发明。欧洲浪漫派突破了严格意义上讲属于本体论以及逻辑学的审美范畴:艺术有机思想在亚里斯多德以后很长时期片面发展了这类结构、形式方面的外在整体因素,从而忽视了灵魂、生命方面的内在直觉因素。浪漫派在与古典主义的斗争中又重新祭起了“宇宙循环论”和“世界灵魂”的大旗且广有斩获。从人类文明发展背景看,18世纪自然科学的进步引起人们对生命起源、生命过程以及生命衰萎现象的浓厚兴趣,生命的秘密一个又一个被揭开。而闻名18世纪的自然哲学(以培根为代表)借助自然科学进步也曾对生命有机形式作过详尽论述,试图刻画整体的自然风貌。这为艺术有机思想的革新进一步奠定了扎实基础。而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并行发展一方面导致笛卡尔理性主义弥漫欧洲,另一方面也引起人们的置疑。其中勇敢地突破理性主义桎梏,为浪漫派有机美学发轫的便是经克罗齐推崇而扬名的意大利哲学家维科。维科在他的《新科学》中将人类历史划分为“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并热烈地赞美神和英雄时代人们信仰的真诚和灵魂的纯洁。不同时代人们的心理与个性在传承中实现着动态性演变,因此非常有必要编辑“一部心灵的字典”。(Bergin & Fichte,1944:126)自这一观点出发,维科研究美学问题不再是像过去就某一静止的方面,而是就生动的发展整体来观照。他意识到在“人的时代”,神话被遗忘,直观和形象思维越来越少,“诗”失去了原初生命力,所以热烈呼唤人类原初的诗性智慧,将生命个体作为价值尺度。维科美学观为陷入唯理主义漩涡中的人们打开了一个崭新的视野。其中18世纪德国艺术有机思想的创立者,“狂飙突进”运动的先驱赫尔德就直接受益于维科。一般认为,欧洲浪漫有机思想发端于德国:当时德国与其他西欧国家相比经济落后、封闭,这反而使它较少受到古典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浸染,较多保持了纯朴天然的民族个性。赫尔德呼唤民族意识,宣扬历史情感,反对理论体系,提出了探索语言的生命之源,还主张全面研究民间艺术元素。他还创立了关照艺术作品“活生生的自然”视角,试图按照直觉、想象、自发等概念构建新的浪漫主义“有机诗学”。(杨冬,1998:207)只是这一雄心勃勃的美学工程注定要由后人来完成。
英国诗人柯勒律治是早期欧洲浪漫派艺术有机思想的代表,艺术“有机体”学说的创立者。他在维科新理论影响下率先反抗、批判笛卡尔、休谟的机械主义唯理原则,热烈倡导艺术“心灵论”,革命性地把“有机体”作为隐喻,以生命过程取代机械过程来统摄对艺术的描述。柯勒律治说:“艺术从本质上来讲是有生命的,它生成和创造着自己的形式”,“在生命中整体从内部产生,生产和成长是生命的第一力量”。“生长转换的内在原则是主体性原则”。“生命整体的各个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总体存于每一部分;但又表现为生命,它寓一于众,从而合众为一”。(艾伯拉姆斯,1992:260-261)他形容“莎士比亚有如一株自然植物的成长,其作品每一行、每一调都成长出下一个”,宣称艺术是一种“鲜活的、创造生命的观念,它们在根本上与自然中的萌发原因相同”。“有机体是天然固有的,是内生的、自动形成的”。(同上:264)柯勒律治的艺术有机思想可归结为三个要点:首先,艺术是主体内在生命形式,即生命自生系统,艺术创作是无外在意志、无意识的天然过程;其次,艺术是自给自足的有机体,具有天然趋向统一的神奇力量,总体总是优于部分,部分总是依赖总体;再次,建立起关照艺术的自然生命视角,即自然类比方法。柯勒律治彻底摒弃了他称之为“积木与灰泥”(同上:260)的机械主义思维模式,从静止、客体的古典机制论走向了动态的浪漫有机论,已构拟出欧洲浪漫有机美学的雏形。
歌德在众多浪漫有机论者中十分引人瞩目。他除了是一个诗人,还享有自然科学家的声誉,曾仔细进行过生物研究和动植物观察,并将这种观察与对艺术创造的感受紧密地结合起来。他得出的结论是:生命运动是生物的自然过程,同样,艺术创造是艺术家心灵中的自然过程。在《论德国建筑》一文中歌德形容哥特式建筑是“在天才的心灵原野中长成的有机产物”,“从他(天才)的灵魂中产生了各个部分,这些部分交织在一起,成长为一个永恒的整体”,这样的艺术“无论是原始态,还是文明态,都表现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并且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转引自艾伯拉姆斯,1992:260)。在歌德看来,生命即完整,完整即生命,因此艺术永远是“有生命的整体”,艺术的存在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这种“完整体”“是他自己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丰产神圣的精神贯注生气的结果”,是歌德所说的“第二自然”。(温克尔曼,1978:136-137)歌德最爱拿艺术与有机生物作类比,在《歌德谈话录》中诸如“生命”、“自然”、“完整”、“血肉丰满”之类的字眼比比皆是。其实歌德自己说得十分清楚:“说到底,在艺术实践中,我们只能与自然一争高低,因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学到了她创造万物时所从事的神秘活动”。“必须把艺术品当作自然品对待,并把自然品当作艺术品对待”。(同上:325)这是典型生命有机思想,尽管其中掺杂了诸多现实主义模拟意识。歌德通常否认自己是浪漫派,他在与席勒进行论战时有一句名言:“我说古典的就是健康的,浪漫的就是病态的。”(朱光潜,1979:405)在当时的德国,耶拿浪漫派的确表现出“软弱、感伤和病态的”一面,歌德意图与这种“病态”划清界限,但他所鼓吹的,“新鲜、健康的”古典主义恰恰是浪漫派对艺术“生命有机体”的一个基本诉求。这种古典主义确切地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有机浪漫主义,而非机械僵化的古典主义。歌德主张艺术具有生长性,是有机的,艺术品乃精神的有机果实,这样就超越了柯勒律治仅仅将有机生物与艺术品作隐喻性类比的诗学范畴,事实上发起了一场真正的美学和艺术批评革命。
浪漫派将自然有机观在文艺美学领域的精彩运用,促成了审美价值新标准的形成,即把艺术有机整体性视为最重要的审美原则。随着生物科学的迅猛发展,艺术的内在“自然有机法则”到了19世纪演变为艺术最公正客观的规律之一,艺术有机思想已成洋洋大观之势。但真正将有生命观念变成一种美学常识和美学理论的要归功于谢林——西方艺术哲学的集大成者。谢林与黑格尔一同栽种过“自由树”,但后来走上了不同的美学道路:前者成为主观唯心主义者,在“同一”的有机哲学中宣扬神秘的生命直觉;后者变成客观唯心主义者,在“绝对精神”里寻求历史和逻辑的有机演进,其差异在某种意义上正如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谢林以“有机体”概念为基础,构建了可以吐纳宇宙的超验主义“同一”哲学。在《自然哲学》和《超验主义理想体系》这两部著作中谢林自主、客体入手,将主体和客体并置,认为二者都来源于一种神秘先验的有机整合力量。这一力量将主客体,自我与非我融为一体,形成“绝对的同一”,“无差别同一”。(谢林,1996:18)在谢林看来,宇宙万物都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整合,已无时空差异。自然是生命的精神,精神是生命的自然,存在的仅仅是出发点:从客体出发便是自然哲学,从主体出发就是先验哲学。由于谢林是个艺术至上主义者,认为艺术是宇宙中最高门类,“同一”哲学很自然地转入美学领域,形成先验主义美学观。他所鼓吹的“神奇整合力量”(同上:11)事实上就是指美:美是调和冲突和对立的动态手段,把真和善整合于艺术中,即真和善在美中相遇并融为一体。在这个实现交融的有机整体中,主体与客体、形式和内容、理想和现实,一切都浑然一体。那么这股散发着强烈生命气息的神秘整合力量如何为人们感知?谢林随即推出“艺术直觉论”:即认识艺术和美只有在内部,通过神秘灵魂运动即直觉来完成。所谓直觉就是不通过逻辑概念,而是通过内在生命过程有机地感知事物。这种无意识活动叫艺术直觉。艺术直觉非无源之水,而是来自灵感,即内心对精神生命的强烈追求。具备了这一内在灵感的人自然就是艺术天才。谢林所建构的庞大美学体系第一次实现了艺术生命内涵的整合,谢林本人也因此成了历史上最具影响的文艺、美学大师之一。
19世纪欧洲浪漫派思想家中处于显要位置的还有谢林的学生,英国批评家卡莱尔。卡莱尔是德国浪漫派美学的热烈追随者,其文艺观几乎完全师承赫尔德和施莱格尔兄弟。他对浪漫派美学理论的最大贡献不是理论体系的构建,而是自觉地将艺术发展与一个民族心灵的历史结合起来考察。卡莱尔认为“一个民族的诗歌史是它历史的精华史,该民族的心灵面貌通过诗歌以连续的生长阶段清晰地呈现它面前”。(转引自韦勒克,1991:98-99)民族文学正是民族精神顺乎自然的发展。柯勒律治说:“莎士比亚有如一株植物的生长”,重在以类比方法阐发艺术家的生命意识;卡莱尔则形容莎士比亚“像一颗橡树从大地的怀抱成长起来”,“就像根系,就像是作用于地下的树液和精华之气”(卡莱尔,1988:92-93),似乎更强调艺术的生命根性。他说“要想创造而不是制作任何东西,生命之根就必须这样地扎下去”。(转引自艾伯拉姆斯,1992:345)挖掘艺术的生命之源成了卡莱尔美学的最根本理论动机。另外,卡莱尔明确区分了机械主义和有机主义,给了当时占据主流的英国古典主义美学以致命一击。他的名言是:“人为的就是机械的,自然的就是有机的”(同上:341),为此他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有机思想语汇,如“死亡与生命”、“制作与创造”、“机械与有机”、“做作与真诚”等等,从而大大地丰富了浪漫派艺术生命有机思想的内容。
浪漫派借助19世纪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和文化大潮,以蔚为大观的艺术有机思想和艺术整合意识的论述,最终奠定了在西方文论史上稳固的地位。事实上浪漫派大师是成群诞生的。除了上面提及的代表人物外,热烈响应和传播并以独到思想见解继承发展了艺术有机思想的还有来自英国的华兹华斯、扬格、济慈、美国的爱默生、俄国的斯拉夫派和A.格里高利耶夫等。他们在19世纪著书立说,激扬文字,共同汇聚成欧洲强大的艺术有机思想传统。他们把艺术认知方式从注重技巧、手段的古典机械论束缚中解放出来,所弘扬的主题是艺术“生命意识”、“浑然天成”、“灵感创造”、“有机演进”。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浪漫派美学的蓬勃发展,艺术创造中那些来自生命直觉、无意识和非理性的方面得到了有史以来最认真、最全面的论述。
4.0 现当代艺术有机思想
19世纪中叶起到20世纪,直至“数字化”的今天,西方艺术批评中的生命意识并未泯灭于科技进步和技术主义的洪流之中。除了脍炙人口的柏格森生命美学,尼采艺术哲学就是一个诱人的话题。尼采是德国19世纪富有强烈生命气息的哲学家,其巨大影响却主要在20世纪。他鼓吹“狄奥尼索斯崇拜”,宣称“艺术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的冲动”,“只有作为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的理由的”。(尼采,1986:325)关于文化的概念,尼采给出的定义是:“文化首先是一个民族在其所有的生命表现中所具有的那些艺术风格的统一。”(转引自胡经之,1999:58)这些彻底摈弃唯理主义,“以各种方式种植对生命,对自己生命爱”(胡经之,1999:77)的思想可以在谢林美学里找到类似表述。德国另一位和尼采同龄的美学家狄尔泰虽然没有尼采那样崇高的世界声誉,但其“生命诗学”同样是西方艺术生命长河里的一股洪峰。狄尔泰天才地预见到即将来临的技术主义时代,“理想主义的激情已失却其鼓舞人心的魅力”(转引自胡经之,1999:34),所以需要把生命本质当作精神科学特别是艺术的研究对象。他进而提出了“总体的人”是“血管中流淌着真正的血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认识主体”。“诗的本质是生命问题,是一个通过体验生命而获得价值超越的问题”。“生命深层体验就是人生诗意化,诗揭示生活本质”。(同上:323)狄尔泰相信,人的生命体验和诗性表达不能够借助逻辑思维来实现,而只能由一个生命融入另一个生命,使得生命之流汇合在一起,方能实现精神跨越。狄尔泰这种对人生诗化的呼吁以及对生命完整意义的追问分明是对西方古老艺术生命旋律的重奏。
20世纪当代西方批评里也不乏艺术的生命话语。匈牙利文艺理论家卢卡契在他的现实主义美学阐述中提出了艺术“有机总体性”的概念(胡经之,1999:402),认为文学典型的特质在于“一切真正的文学用来反映生活的那运动着的统一体,它的一切突出的特征都在典型中凝聚成一个矛盾统一体,这些矛盾,一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的、道德的和灵魂的矛盾——在典型里交织成一个活生生的统一体”。(同上:18-19)卢卡契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对人的个性分裂和“物化”,认为“人道”是艺术最本质的内容,因此艺术的首要任务是从整体上表现人的心灵力量,守护人的历史完整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即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针对非人化、单面性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更像是有机论浪漫主义美学。他把艺术审美力量看成了拯救当今世界的最后力量,强调艺术的个体解放功能,提出以诗(艺术)的方式来拯救陷入技术主义“物化”的西方社会。(同上:475)虽然马尔库塞所面临的当今人类生存困境与18-19世纪浪漫派时期不同,但在抗争唯理主义的侵害上却异曲同工。另一位“西马”代表人物本雅明为资本主义数字化新闻节奏和机械化生产节奏而“震惊”,终生堕入了对“往事的喃喃低语”(同上:514)中,力图用传统的“象征”来对抗当代的“寓言”。在本雅明看来传统的“象征”对应着人类理想的历史,“象征”体现出人类内在经验的圆满性,即个别与普遍结合在一起,内容和形式一道构成艺术品、文化产品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有机整体”:一切暂时的东西被纳入到一个整体中,一切历史性片断被纳入到连续统一体,成为生命的有机显现。而“寓言”则对应着一部资本主义消费时代沮丧而令人心碎的历史。人成了被技术物化的奴隶,其艺术经验和审美嗅觉日趋萎缩。本雅明因此推出了他“体验的寓言”、“震惊的美学”,其实质是要延续为当今科技主义洪流所遮蔽的艺术生命话语。
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以其“诗意的栖居”和“还乡的喜悦”(海德格尔,2008:73)闻名遐迩。“诗意的栖居”意味着对人的存在采取艺术的态度,而所谓“还乡的喜悦”未尝不是诗人触摸到民族生命根基的内心欢愉。海德格尔称“一个民族此在的真理最初是由诗人奠定的”。“在世界上诗享有最高的栖居权”(同上:18),诗依托生命本源守护着“真理的生成与发生”。只有艺术才能够跨越时空隧道,拯救陷入沉沦中的生命于万一,因为生命于忧烦的“此在”中无声无息延续,无声无息中断,人却退居到了物质主义之下。一个艺术家(诗人)的使命就在于启悟人们向着“彼在”迈进,最终在“还乡的喜悦”中“诗意的栖居”于民族生命根基之上。海德格尔不乏本雅明的浪漫情怀,宣称当今现代艺术缺少与生命的有机联系,是一种“破坏性的东西”;现代艺术不再是一种精神信仰,而是成了“缺乏生存历史根基的无用的上层建筑”。“依据人类经验和历史,一切重要伟大的事物都源于一个事实,那就是人拥有一个家园,人置根于传统之中,比如当代文学大都是有害的”。海德格尔因此反问道,“难道任何真正作品的繁荣不是依赖于扎根其民族土壤吗?”。(同上:69)海德格尔的反诘正是艺术生命话语在当今“全球化”时代里的旷野呼告。
5.0 结语
整体来看,西方文艺批评史上存在着一条轨迹鲜明的,由艺术生命有机思想所构成的“生命路线”。这一“生命路线”绵延二千多年,即便在当代艺术哲学中依然十分清晰: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率先推出了古典派艺术有机思想;18世纪浪漫派艺术有机思想在欧洲得到长足发展,如赫尔德历史循环论、施莱格尔兄弟艺术神话哲学等;19世纪浪漫派艺术有机思想继续在西方空前发酵,出现了谢林艺术哲学、柏格森生命美学、尼采的生命意志论以及狄尔泰生命诗学等;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尔库塞、本雅明和存在主义的海德格尔等人也不断向当今世界发出回归生命本真的谆谆呼吁。这显示出西方文艺批评传统中生命有机思想的强大历史生命力。事实上,艺术生命有机思想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不同历史背景下,以不同的言说方式同工具理性主义进行着顽强抗争,力图挽回被技术主义、机械化、数字化洪流所淹没的生命感受,实现“诗意的栖居”,其根本宗旨在于呵护人的行为主体性和生命完整性。西方艺术生命有机思想无疑具备西方文论史上所有唯心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美学流派所固有的消极因素:如鼓吹泛美主义、神秘主义、反物质文明等,但依然掩饰不住它作为一朵鲜活西方文艺理论奇葩的艳丽和芬芳。
[1] Bergin, T. G. & M. H. Fichte.GiambattistaVico:Autobiography[M]. New York: Isaac, 1944.
[2] Robertson, J. M.Features(Volume2)[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3] Robinson, R .Aristotl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4] 艾伯拉姆斯. 镜与灯-浪漫主义及批评传统[M]. 童庆生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5] 奥古斯丁. 忏悔录[M]. 周士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6] 柏拉图. 文艺对话集[M]. 朱光潜译. 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7] 柏拉图. 蒂迈欧篇[M]. 谢文郁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8] 胡经之. 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上、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9] 海德格尔. 人——诗意地栖居[M]. 郜元宝译. 南宁: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8.
[10] 卡莱尔. 英雄与英雄崇拜[M]. 张凌志译. 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1988.
[11] 尼采. 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M]. 周国平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6.
[12] 韦勒克. 近代文学批评史(卷3)[M]. 杨自伍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13] 温克尔曼. 歌德谈话录[M]. 朱光潜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14] 谢林. 艺术哲学[M]. 魏庆征译.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15] 杨冬. 西方文学批评史[M].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
[16] 朱光潜. 西方美学史(上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7] 朱光潜. 西方美学史(下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The Organic Ideas in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its Historical Influence
JI Ming-j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
Most schools of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have a long history of poetic traditions of their own. The organic ideas of life is one of them. The organic ideas of life refer to a dynamic and lively mode of literary criticism, covering the times from the ancient Greece to the digital age. It is a sense of organic synthesis, combining people’s refreshing views of art with their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The organic ideas present themselves in the forms of anti-rationalism and anti-materialization, leaving footprints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They constitute a great revelation for the present literary theory exploration to get rid of shackles of scientism, digitization and return to art itself and life consciousness.
The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organic ideas of life;sense of organic synthesis
2015-05-28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根基主义及其民族文化审美理论”(项目编号:13BWW03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季明举(1966- ),男,山东临沂市人,教授,博士 。研究方向:西方文论、俄罗斯文学。
10.16482/j.sdwy37-1026.2016-04-009
I106
A
1002-2643(2016)04-0062-07